- +1
我终于下决心换掉开了七年的车,来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 |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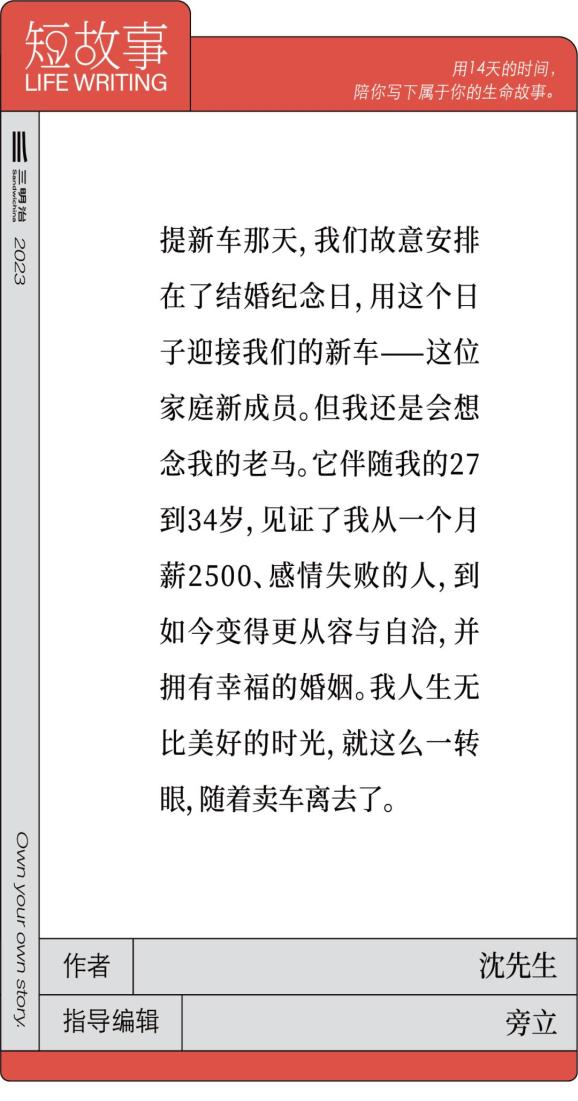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我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打开,细密的白色泡沫瞬间汩汩冒出。夜已经深了,我有点疲惫。
一小时之前,我在十公里外的一个黑灯瞎火的城乡结合部,在一个安静的路边,把我的车卖了。确切地说,是跟二手车平台完成了交割手续。倒春寒的夜晚还是挺冷,我把车停在路边。平台收车的业务员说自己得了甲流,正在发烧,让我离他远点。于是我们俩像是特务接头:他敲我车窗,给我一些资料让我填,然后从他的车窗递进去。
他在写写画画,还打一些电话,然后再把电子合同发我,我在车里看完,完成电子签名。再去敲他车窗,拿回身份证,把车钥匙交给他。
结束了。钱瞬间到账。收到的钱并不多,跟工资是一个数量级,说白了,没什么感觉,并不开心。今天晚上,就会有物流把车拉走去往2000多公里外的那个城市。到那边,它会变成一辆网约车,每天接送几十个陌生人吗?或者,会迎来一个烟瘾很大的新车主,让车厢里充满呛人的烟味,织物内饰被不小心烫出烟疤吗?又或者,会被新车主换上丑陋的内饰,套上色彩和质感都很突兀的方向盘套,装上劣质且味道刺鼻的菱形格子脚垫,然后在方向盘上贴满水钻?它的车身上会被贴上一些网络烂梗的标语吗?它的蓝牙车机会从此播放一些口水歌吗?我七年没出过险的老马,会被磕碰得一身伤痕吗?
我不放心。由于需要对方提供一些手续,我加了买家微信。我本来还想发个微信跟他说,我车况很好,没出过事故,而且自己加装了很多东西,甚至,心里有个声音想说“好好对待这辆车”。他发语音过来,是我不太熟悉的浓重又有点粗鲁的口音。
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是个车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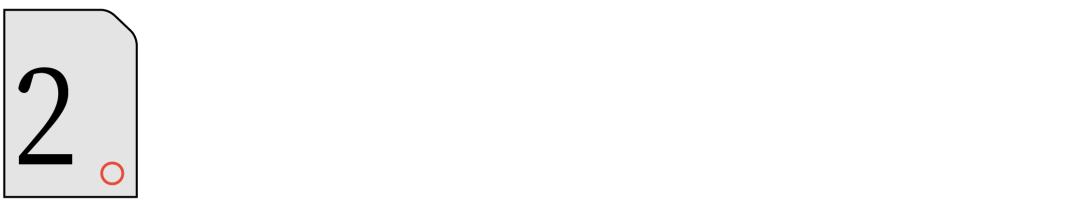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冒出想拥有自己汽车的念头,跟我爸有关。
我出生在离北京几百公里外的A市,小时候一直住在这里。初中的时候,爸妈搬到北京工作,也在北京买了房,不久,也买了我们家第一辆车。那是辆银色的凯越轿车,不大,我和爸妈个子都很高,一家人坐在这辆车里,特别逼仄。这款车在当时卖得不错。很多年以后我记得某个汽车KOL说,在当时的汽车全球化研发生产背景下,挂着美国别克品牌的凯越,其实是一辆完完全全的韩国车。高中我也来到北京上学。当时住校,每周末,就是爸爸开着那辆凯越接我回家。后来,大学我去了南方。而爸妈,在我高考之后离婚了。
老家A市的房子,虽然又小又破,但承载了我完整的童年记忆。毕业回北京后,有一次,我跟我爸开车回去,把那个房子卖掉。那时候,我爸已经把车换成了一辆丰田汉兰达。这是一辆足够大的SUV,坐在里面视野很不错,把后座放平,甚至可以让我身高一米八、腿脚不便的爷爷躺在里面——我爸用这个方法带晚年的爷爷回了山东老家。
A市房地产泡沫严重,是挺有名的鬼城,老房子更是卖不了多少钱,也就20万出头。怪不得卖车时的心情很特别,总觉得这感受曾经经历过,原来是那年卖掉老房子的时候。那老房子,很多很多年没回去了,也没有人住。我知道,这将是一次告别。我将告别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在这个小家的一切记忆。
记得非典那年,我正上初中,一个人在家,每天三餐去奶奶家吃饭。爸妈都被困在北京回不来。每周一去学校领一次作业回家自习。那会儿朋友们天天聚在我家用电脑打拳皇97,我家成了游戏厅。更小的时候,小学,在这个家里,我被逼着学钢琴,一边弹琴一边哭。我还记得有一次趁我妈做饭,我一声不响地用水彩笔在墙上画满了米老鼠。爸妈并没有说我,但从那以后,家里贴满了壁纸。
打开房门,吸顶灯还能亮。然而,当年打拳皇的笨重台式机和电脑桌不在了,钢琴也不在了。我撕下了天花板上的一块壁纸,交待我爸说:“放在你车上帮我带回去,我要留着。”我已经想好了,回北京后会把这块壁纸裁成规规整整的正方形,在上面写上关于这个小家只言片语的记忆,然后裱起来。
我跟我爸不住一起,平时见面不算多。回北京后,再次见到他,索要那块壁纸,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已经扔掉了。”
我知道他也不是有意为之,他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人,没有我这么感性。他应该也就是在某次收拾后备箱的时候,顺手就扔了。可是在我看来,那个后备箱里,他那些去工地会用到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用的标书、甚至中华和整箱茅台,都没有那张壁纸重要。对于我,那是一段记忆的湮灭,至此,连一点念想都留不下。
从那时起,我第一次觉得,有个自己的车多好啊。车是一个密码箱。

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落北京户口,我进入了一家国企。拥有某名校硕士学位的我,拿着2500元的月薪。那是2015年,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厅里,同龄人甚至更小一些的人靠一个PPT就能拿到百万融资。我的发小老韩,一个有天赋又无比勤奋的律师,跳槽到更大的律所做了合伙人。他主攻的方向就是初创公司的投融资业务。那段时间,他那些像他一样年轻或者更年轻的客户,开始在任何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细分赛道,切出一块蛋糕,靠着资本市场的加持,一路狂飙。
我跟老韩高中时候特别要好,周末晚上一起出去喝酒,然后走回宿舍,路上比谁能走直线不超出一块地砖的宽度。大学一起在南方,后来找的女朋友都是上海人,她俩还是大学校友。那些年,北京还有很多烤串路边摊,2016年初夏的某个夜晚,我俩坐在东三环不远处某个野串摊的小塑料凳子上,撸串喝酒,他突然说:“今天我来(买单),客户刚给打了20万。”我其实内心很为他高兴。但当时拿着2500月薪的我表现得特别平静。我挺敷衍的,大概就平平地说了句“牛逼”之类的话,然后拿起酒瓶子,跟他碰了一个。我用表面上的不在意、无波澜,掩盖当时内心极大的失落。
很多年之后,我早已意识到,这种故作镇定的表达事实上相当不自然,反而显得窘迫且狼狈。作为朋友,如果我是坦荡的、自在的,我应该会特别真诚、兴奋,由衷为他感到高兴。老韩作为一个年轻的律师,与我分享这样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职业成就,当然也期待自己的朋友能给出真诚的祝贺。
不久之后,因为工作需要,老韩提了辆奔驰。事实上,我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在那段时间买了第一辆车。你知道,当一个年轻人拥有了一辆汽车,在那段时间会是兴奋的,会时常聊起关于一辆车的方方面面,外观、功能、文化、社交、新的目的地。汽车意味着奔赴一种新的生活,活动半径极大拓展,对于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有了掌控力。
我也想像朋友们一样,拥有一辆车所代表的新生活。只不过,在朋友们经历这种变化的同时,我月薪还是2500元。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我妈用微信给我发了一张截图,后面紧跟着一个笑脸的表情。点开截图一看,她摇到号了。
我并没有特别兴奋,只是感到压力。拿着2500月薪的我,早已经习惯了坐地铁通勤。很多东西,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会觉得离不开。但其实在你拥有它之前,也并不会觉得缺少什么——车就是这样。不过跟我爸说了这事,他特别高兴。爸妈离婚之后,我跟我妈一起住。没有车。而他一直觉得我应该有一辆。
就这样,我用我妈的指标、我爸的钱,准备买车。
那段时间,我把几个头部汽车KOL的视频基本上看遍了,到店里试车,整个过程很快:就是它了。颜色选白色。马自达,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选择,但是,我喜欢这辆车——无论是驾驶的感觉,还是优雅又富有动感的外观。
几年之后,我给它起了名字,叫“老马”。说句玩笑话,北京人对“老马”这个称呼天然有好感。首钢的马布里、国安的马季奇,都被北京人称呼为“老马”。老马,意味着我们是一家人。
拥有了一辆自己的车,果然感觉很不错。就像古代的将军,终于拥有了合意的战马,或者是武士,打造了趁手的兵刃。我对这辆车研究得很认真,弄清楚了各种隐藏的按键功能。我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心心念念的物件,哪怕买个MP3,我都会特别认真研读说明书,更不要说这是一辆汽车。我喜欢这辆车,甚至加入了某个车友会,特别中二地定制了一个带编号的车友会标牌。我还去专业做马自达的汽修店,做了一些升级改装。迫不及待挂上正式车牌开出去,结果第一天就收获了一个违章。
对了,买老马的另一个原因是,在2016年,已经有很多车没有播放CD的功能了。只有马自达这种偏执的、以制造生产木塞起家的日本企业,还提供能听CD的汽车。而我,从中学开始,已经攒下了几百张的CD收藏。倒不是刻意怀旧,而是我偏执地认为只有CD这种实体的、物理的介质,购买后里面的音乐才永远是你自己的。这个时代、这片土地都很奇怪,无论你在音乐平台买多少年的钻石会员、也无论你的VIP网盘有多大容量,可能突然有一天,某首歌、某个歌手,就消失了,无论在互联网还是livehouse,仿佛从没来过。
我买的老马,是低配版本,只能听CD和收音机。我改装了一个车机,然后它便有了触屏,这样在保留CD播放功能的同时,也能连蓝牙了。而拆下来的原车CD机,我改装成了家用音响,至今仍在家里服役。

坐在自己的新车里,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分手的女朋友。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上海姑娘,她叫阿水。我们是大四在一起的。我回北京读研的时候,她为了我来北京工作,那是她第一次长时间离开上海。北京这座城市,对于一个刚毕业没有任何根基的年轻人,并不算友好。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一个在国企打着可有可无的工、挣着可有可无的2500元的年轻人,没办法让人家看到希望。当时我太幼稚了,在心理上,也远远没有做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准备。我们租住在北四环的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里。某一天深夜她出差回来,在机场打了很久的车。到了楼下,她没有门禁,刚好那天我不在家,因为是半夜也没有邻居出入,她进不了楼道。就这样,在北京的深夜,她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直到崩溃大哭。事实上我没有去机场接她,只是因为来回打车的钱。
阿水特别伤心,感到无比孤独和无助,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于是,在一起四年后,我们分手了。
一年之后,我们重新复合,感谢命运没让我们错失。直到现在,无论阿水是出差、加班、应酬,只要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去接她。这么说可能有点可笑,但因为有了老马,一辆出色的、省油的日系车,钱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我只需要下楼,发动车子,花一个小时开到机场,出现在接机口,就能给她特别大的安全感。多简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长大了。我明白了,一个从未离家的上海姑娘,为了一个男人来北漂,这意味着怎样的托付和付出。我也开始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对另一个城市产生归属感,其实就来自于那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能让人免于受困在夜风中,便足够。
并且,因为有了老马,北京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巨大城市,开始有更多角落向我们敞开怀抱,展现出它的可爱。
北京的可爱之处,有很多在地铁到不了的地方。这座城市的西部和北部被群山包围。拒马河从京西峡谷穿流而过,高山湖泊明珠般点缀在北郊。这大山中,还点缀着古人类遗迹、千年古刹、帝王陵寝、明清旧村,还有六百多公里长城。北京的可爱,还来自于作为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资源。顶尖的国际赛事、各种不同类型的演出和展览,都在诱惑着这个城市的居民——所有这些都很美好,除了散场之后打车的时刻。
多有魅力的城市啊!不过坦白说,作为这2000多万人口中的一员,在我们没车的时候,上面这些基本与自己无关。

当我们两个人,与这座城市的更多角落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结,我们自己也便获得了归属感。
是时候结婚了。老马给了我们一个家庭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北京其实挺奢侈的,虽然就这么单一个车牌照——两块铁皮——你看呐,当你傍晚站在过街天桥上,华灯初上,看着三环主路两侧因为红色刹车灯而被点亮的车龙,你会觉得无论这辆车多老、多旧、多便宜,只要有车的人,就是old money。至少证明,在摇号政策之前,他在北京,已经有了一点根基。这无论对于后面来北京的人,还是当时还年轻的北京土著,都不公平。无论你是否承认,北京这座城市对于后来者越来越不友好。这么看来我们是何其幸运。
我们开着老马,去登记结婚,领完证去大吃了一顿。很多人说,在北京,如果不开车,一天只能干一件事。这是真的。选婚礼场地的时候,因为有车,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跑遍海淀、朝阳、顺义,看不同的场地。装修的时候,因为有车,我们也会更多地跑整个城市的各种婚博会、家装节。因为有车,一天跑好几个建材城成为可能,或者去宜家,买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直接扔在车上,再去下一站,效率奇高。好看的柜门把手、一个小铁柜子、两把盗版的设计师餐椅、MUJI的一套打折床品、特力屋的清仓餐具、建材城的一个精美吊灯。统统扔在车上。对了还有,婚礼的婚纱我们是开车去天津找的。天津这些方面比北京便宜很多,非常值得跑一趟。而前提,还是最好有辆车。
结婚以后,我们像那些电视广告里描述的城市中产家庭一样,去超市买很多很多东西,整箱的饮料、啤酒,山姆超大包装的那些烘焙食品和水果。而我自己还可以像那些艺术家一样,把自己之前的画,还有收藏的海报、图片、版画,用车拉着去装裱,装好框子再用车拉回来。后来这些东西都成了装饰我们新家的最可爱的部分。我也终于可以删掉手机里存了很多年的面包车司机的电话。
2018年,我终于离开了那家月薪2500元的公司。我和阿水赶上了互联网狂奔的末班车,先后跳槽到了同一家大厂。毫无悬念的,跟以前的月薪相比,我的收入增长了不少。就职同一家公司,我们还能一起开车上下班。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在变好。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2020年的春节。印象中,北京已经很多年没下过这么大雪了。所有的商场、餐厅都不让进,开车出去兜风,成了我们那段时间仅有的娱乐之一。一辆车,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边界的延伸,意味着我们拥有除了家里几十平米的斗室之外另一个可以不带口罩的室内空间。我们可以开着车,去看看这突然无比陌生的城市。
东三环主路国贸桥上,一切被大雪覆盖,白茫茫、空荡荡,两边鳞次栉比的高档写字楼扑面而来,特别不真实。我记得有人说过,东三环这一段特别像洛杉矶。我没去过洛杉矶,我只觉得像极了《流浪地球》。三环主路上,一辆车也没有。放在一个月前,哪怕是半夜都不可能如此冷清。
就在这国贸桥上,之前一年的随便哪个周六的晚上十点半,应该是这样的场景:车流动得很慢,不知道是前面有事故,还是交警只留一条车道查酒驾。工体的球一小时前散场,国安依然进攻乏力,主场没能让球迷满意。几万球迷涌出来,此刻车子已经到了国贸桥,车屁股上贴着国安的队徽。工人体育馆一场演唱会刚散场,过了十点,不可能有安可的。歌迷带着兴奋的余温散去,从北门出来,满脸愁容,他们要和三里屯的人抢网约车。酒吧街已经有人开始撤了,太古里的苹果和阿迪达斯也已经关门,网约车好不容易从优衣库东边或南边接上客人,堵车,掉头,一路向东,上了三环主路,便加入了把导航软件的道路变成猪肝红色的车流之中。很多人沿着朝阳路一直向东,也有些人会走国贸桥,往南去百子湾、劲松甚至亦庄。那里花园和机电院里的餐厅,这个点终于开始不用排队了,翻台加快,在这些餐厅和酒吧的客人,会在稍晚一些也驾车开上三环。希望他们能好运,到时候事故已经排除,或者不查酒驾了,这样能在十二点前到家。
如果你乘坐“特8快”公交车,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在国贸桥上会有点恐惧。因为这车在最外侧车道开,从车窗看下去真的太高了。在国贸桥下,八王坟公交车站依然排着很长的队,人们需要乘车回到河北燕郊的家。依然有源源不断的人从三环边的甲级写字楼涌出,或者疾步快走,或者骑着共享单车,奔赴八王坟公交车站。而在不远处的通惠河南边一点,有许多卖小吃的摊贩,烤冷面、铁板鱿鱼、臭豆腐、狼牙土豆,无非这些。然而,这种摊子在北京已经很少很少了。
而2020年冬季的某天,国贸桥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当时更加不会想到的是,在此后三年间,开车兜风,都是一种非常主流又非常重要的娱乐。周末,我们就开着老马去门头沟或者房山的山区转,没有目的地,或者导航一个根本不开放的地点,比如潭柘寺。然后就沿着山路开。中间到某个观景台或者宽阔的路肩,停下车,下来看看花开,听听鸟语,呼吸一下山里的空气。北京山区的路原本其实也挺繁忙,如今难得看不到摩托车和自行车,就只是回头看盘山开上来的路,看下面山坳里的青翠,也觉得万物可爱。然后,上车接着走,看到某条没见过的小路,直接拐进去,走到不能走为止。通常,旅途中止于某个村口,大同小异的,那里会有一个限行杆,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村民。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不会有交流,直接掉头换条路,或者回去罢了。
车给人自由,这句话从未像这三年般实在可信。车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安全,它早已超出代步工具的功能。有一辆车,那么当离开北京,但突然不让买返程火车票的时候,就还有回家的可能。有一辆车,那么当因为手机里的星星或者黄码,全世界都不欢迎我们的时候,至少不至于睡桥洞底下。
在那三年,老马的后备箱里常备着露营的椅子、桌子。在随便某个街角,只要风和日丽,我们便就近停下车坐在路边,看看并不繁忙的街道,和戴着口罩匆匆而过的人们。我们也因为老马而得以出逃,比如前年的十月,我们去了内蒙乌兰察布,去看火山遗址。驱车五个多小时进入草原,旷野下的火山营地只有几辆同样从北京逃出来的车。秋风吹得草已经变黄,风很大,把裹着防风罩的木屋吹得咿呀作响。我们几个朋友,背靠着老马,围坐在一起生火造饭。羊群就在不远处,牧人赶着它们回家。太阳正从火山背后落下,深红色的光晕镀在羊的身上,又在草原上拉出它们长长的影子。
入夜,漆黑的天穹上,肉眼可见灿烂银河。

2023年,正常的世界在回归,老马也七岁了,服役了快九万公里。说起来,换车这件事情,我和阿水去年就讨论过。但作为当下的互联网行业中年人,毕竟随时在担心失业。非必要大额开支,从更早时候的“需要犹豫一下”,一律变成了“不考虑”。而且我对老马是真的有感情。阿水比较想换,但我总是半推半就。
直到今年初春的某个夜晚,空气中还颇有凉意。加完班,我坐在车里给阿水打电话:“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车的电瓶估计又该换了,打不着,我叫了接电,大概40分钟才到,我就在边上随便吃点了。”
阿水说:“好吧,你好辛苦啊,不过,我认真的,咱们换车吧。”
于是换车这事情再次被提上日程。最终阿水说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让我下了换车的决心。她说:“等小沈出来,咱们就更舍不得花钱了。”
没错,她有宝宝了,再过几个月,我就当爸爸了。
我打电话告诉我爸换车了,他很高兴。我想,他应该是觉得我终于自立了吧。老韩知道我们换车了,要把他们的儿童安全座椅给我们。看起来换车真是一件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事情,除了我还是有些想念老马。
哦,我们故意安排在结婚纪念日提新车,用这个日子迎接我们的家庭新成员。至于给新车起什么名字,我们还没想好。

这个故事写起来不太容易,无论是因为故事本身,还是这半个月难以保证的写作精力,还好有旁立的指导和鼓励才得以完成。很多事情,不写下来,真的慢慢就会随时间忘记。就比如几年后,我或许还记得独自驾车在北京东三环这件事,但我会忘记当时的感觉和情绪。
卖车这段时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有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拥有一辆车,那其实人生是可以用车来区分的。读的学校、任职的公司、居住的城市,要么只能陪伴某一段特定的时间,要么充满着变数。而只有车,差不多固定的年限更换,换过几台车,一生就过去了。有点类似于昭陵六骏,那就是唐太宗的六匹马。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已经开上新车了。新车很好。但有点伤感的是,这应该是我拥有的最后一辆燃油车了,而且它听不了实体CD。有些历史的大势,真的是不可改变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敏感一点,努力记住当时当下的感受。这篇文章送给我的第一辆车,老马,也送给我自己的这七年,以及这期间相关的所有人。它是我的编年史。
原标题:《我终于下决心换掉开了七年的车,来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