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斯科塞斯谈《花月杀手》,80岁时终于理解了黑泽明
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May 16-27, 2023


非竞赛单元

花月杀手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编剧: 艾瑞克·罗斯 / 马丁·斯科塞斯
主演: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 罗伯特·德尼罗 / 杰西·普莱蒙 / 莉莉·格莱斯顿 / 布兰登·费舍
类型: 剧情 / 悬疑 / 惊悚 / 历史 / 犯罪 / 西部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2023-05-20(戛纳国际电影节) / 2023-10-06(美国点映) / 2023-10-20(美国)
片长: 206分钟
作者:By Mike Fleming Jr
原文链接:
https://deadline.com/2023/05/martin-scorsese-interview-killers-of-the-flower-moon-leonardo-dicaprio-robert-de-niro-1235359006/

译者:被动的观众
电影一直在反映时代的脉动,就算整个世界都沉默,即使一点声音,都会成为一股力量。(豆瓣@被动的观众)

译者:酶
是在罗德岛吗?
早在2016年,大卫·格雷恩的《花月杀手:奥色治系列谋杀案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尚未出版就已口口相传,成为畅销书种子。此前,Plan B将格雷恩2009年出版的《迷失的Z城:一桩亚马逊的致命案件》成功地搬上银幕,詹姆斯·格雷担任导演。格雷恩这部最新的纪实小说标题意味悠长,吊人胃口,之后公之世人,依然不负众望。
小说问世后,迎来了七位数的翻拍竞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和J·J·艾布拉姆斯等都曾接触过此项目。最终,Imperative Entertainment的丹·弗里德金和布拉德利·托马斯以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书版权。马丁·斯科塞斯参与执导,迪卡普里奥和罗伯特·德尼罗联袂主演,原定派拉蒙负责发行。
《花月杀手》具备了一部经典西部片的所有特质。迪卡普里奥饰演主角汤姆·怀特,一名刚正不阿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有着德州游骑兵出身的背景。上世纪20年代初,怀特受埃德加·胡佛指派,前往俄克拉何马州,调查奥色治族印第安人绝望的求助一事。事件的背景是奥色治族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域,有着储量丰富的石油,他们因而成为世界上富甲一方的族群。而与此同时,这里的印第安人陆续死亡,数字惊人——而且死因疑云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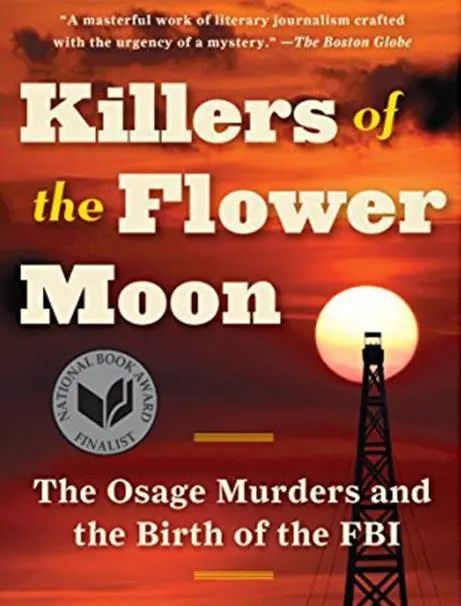
《花月杀手:奥色治系列谋杀案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这是一个完美编织的谋杀悬疑故事,但要是拍成电影总感觉有些不对劲。斯科塞斯、迪卡普里奥和德尼罗开始意识到翻拍情况要复杂得多。更明确地说,创作出一个白人救世主视角的西部片是不合适的,因为白人也是施害者:他们是暗中潜入奥色治族的外来者,利用这些印第人的淳朴天真并从中获利,而当地腐败不堪的执法部门更是助长了他们的残酷罪行,小镇居民也同时窥视着印第安人朋友的钱财腰包。
因此,斯科塞斯重新开始,抓住机会去讲述一个在现代社会引起共鸣的故事,迫使观众面对自己的黑暗深渊:金钱能驱使他们走多远?照着这思路,迪卡普里奥灵光一现,电影故事的中心不应该是围绕着执法者汤姆·怀特展开,相反的,电影主角应是屠杀印第安人嫌疑犯欧内斯特·伯克哈特。显然,伯克哈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他与奥色治族的成员莫莉结婚,膝下有三孩。汤姆·怀特(杰西·普莱蒙斯)的出现,让莫莉陷入死亡的边缘。欧内斯特只是为了钱吗?
据报道,马丁在创作方向上对黑暗现实的挖掘,以及愈发烧钱的高额成本,让派拉蒙望而却步,退出投资发行。不过,苹果公司全球视频部负责人扎克·范·安博格和杰米·埃利希特却慧眼识珠,视《花月杀手》为一部史诗大片的爆款潜质,亦是他们刚起步的电影项目的一大滩头阵地。苹果争取到了这个项目的发行,正如他们曾经在圣丹斯电影节去争取《健听女孩》的发行——后来为流媒体赢得了首座奥斯卡最佳影片小金人。但最终协商下来还是保留派拉蒙一定的操作权利空间,协议要求派拉蒙负责全球范围内的院线发行,而颁奖季时电影则会登陆苹果TV+。
尽管在创作维度上翻天地覆,斯科塞斯仍然邀约德尼罗加盟,这是他俩的第十次合作。德尼罗出演比尔·黑尔一角,他是欧内斯特的叔叔,在奥色治族员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慈爱的族长和盟友,而背地里他另有所图,让侄子做尽恶事。德尼罗说:“我几年前读过这本书,汤姆·怀特这个角色更突出。于书而言,这很恰当,但马丁和里奥的想法是关注比尔和欧内斯特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又是有意义的。他们想更多地关注到这种动态关系,而不是汤姆·怀特来到小镇拯救世界。”

《花月杀手》剧照
德尼罗解释说,这种创作上的转变使故事更加个人化,更为丰满,深入地探索人性、弱点和贪婪的探索。“去呈现那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侄子和叔叔之间的动态关系,是最有意义的。” 德尼罗说,“可能大家将这些称之为平庸之恶,或者只是权力的邪恶腐败,但我们在其他历史社会中已然看过这种情况,包括二战前的纳粹。也就是说,对一种对人性令人沮丧的认识,让人们走向了罪恶深渊。(黑尔)相信自己爱印第安人,也感受到了他们爱他。但他又觉得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汤姆·怀特和联邦调查局在蛮荒的西部建立了法律和秩序,而实际上,那里的法律是由当地人约定俗成的,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深蒂固,没有人对此负责。这说白了就是种族主义。”
德尼罗和迪卡普里奥曾出演父子,回想起来,让德尼罗扮演迪卡普里奥的叔叔是一绝妙之举,这让角色配置融入了父子亲情的色彩,也颠覆了银幕外他俩在观众心中父子CP的印象。迪卡普里奥说:“我的演绎生涯始于《男孩的生活》,当时鲍勃一起试镜,然后得到角色。和德尼罗共事,看到他的专业精神和塑造角色的方式,对我的生命体验和职业生涯都颇有影响。我和马丁合作的所有电影都离不开这些影响,而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所有人都还能一起合作,简直不可思议,是段独特的经历。他们都是我的电影英雄,于我而言,非同寻常。”
对迪卡普里奥来说,最初的剧本没有发挥出原本故事应有的史诗潜力。“它没有触及奥色治族的核心。感觉太像是侦探工作的一次调查,而不是如法医般去深刻解剖在一段动荡不安时期下俄克拉荷马州的文化和动态张力。”

迪卡普里奥在戛纳
迪卡普里奥热衷于挖掘一部电影的内在气质,和一方水土背后与生俱来的灵性。“我们在那里拍摄时正值塔尔萨大屠杀100周年纪念日,”他说,“拍摄地距离奥色治族恐怖统治发生的地方只有半小时车程,而在100年前的同时,也发生了第一起奥色治族谋杀案。一个世纪后我们叙事了这段历史,简直天缘巧合。”
在原剧本基础上微妙改动,新颖之处在于强调了道德价值观,也让电影变得更符合一贯的斯科塞斯范儿。迪卡普里奥说,“我们做了很多,深入人性的阴暗面,但也要了解其间复杂。帮助马丁回归到他所擅长的,去讲述一个洞察人性的故事。电影中,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一个大熔炉俄克拉何马州。此地,解放的奴隶在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奥色治族也随之兴起。而与此同时,三K党、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冲突如火如潮地相随袭来。在一些白人定居者眼中,这就像是一场把有色人种当作韭菜割的淘金热。”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片恶之花的土地绽放了一段恋情。“确实,在文化层面上,欧内斯特和莫莉的恋情代表了一种扭曲与复杂。”迪卡普里奥说,“嫁给白男的奥色治族女性不胜枚举,但这些白男实际上是来掠夺她们的,他们争夺她们的领导权,入侵她们的石油经济。在剧本的初稿里,有一情节让我大为吃惊。欧内斯特向莫莉坦白他的真实意图,他参与到了这一邪恶计谋中。但他们仍然彼此相爱。正是这种扭曲的复杂性,造就了一段黑暗真实的美国奇闻轶事。”
这就是电影偏离原著的所在之处。“创作剧情的最大挑战莫过于避免让电影走向谜团疑云,而是尽早地揭露欧内斯特的真实面目,然后看着这段扭曲的关系如何演变。处理莫莉、德尼罗的角色亦是如此。这样改编并非轻而易举,用时数年才得以摸索清楚剧情和人物。”

《花月杀手》工作照
实际上,用时之久都足以再拍一部《爱尔兰人》了。迪卡普里奥回忆道:“创作进展愈发硕果累累。虽然原著小说就已经精彩十足,但我们有了新的想法后,我与大卫·格兰恩交谈,他鼎力支持。要是能够深刻反映当时的文化语境,彻底剖析美国白人和土著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全新叙事将是完美十足。我是真的认为我们做到了。最后,它卓有成效地呈现出来了。”
迪卡普里奥说,另一种方式的呈现会让人感觉生硬。“当你看到我们的角色后,你就会察觉有些不对劲。你在电影前20分钟就会注意到这种氛围,这一处理手法,可以让我们真正地穿越回去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是史诗电影的黄金时代,如今已然罕见。”

《花月杀手》剧组亮相戛纳
在本次采访中,“纽约之王”马丁·斯科塞斯回顾了他与老搭档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伯特·德尼罗在创作之路上的同担共苦。
DEADLINE: 在《花月杀手》中,因为石油金钱,奥色治族成员惨遭剥削,更是丧命于此,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漠然置之,这些描绘都令人痛心。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斯科塞斯:在读大卫·格雷恩所写的故事时,我的反应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因为这种观念,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如果奥色治族人毫无用处,如果他们最终终将淘汰,那为何我们不提前送他们一程呢?最终,我们真的为此感到内疚吗?我不是在指你我,但假设我们也曾失去理智过,做过类似前人对奥色治族人的行径,是否会感到愧疚?还是会内心自圆其说?
DEADLINE: 如果你可以从中获益,是否就会合理化自己的罪行?
斯科塞斯:在文化层面上,(奥色治人)的行为是否不同?是的,在所有层面上奥色治人都不同于他人。在金钱和私有财产上,他们没法适应欧洲人的行为,资本主义的模式。后来,我们(美国白人)来了,而且我们也不会离开。要么你加入我们,要么你必须离开。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爱过你们,也敬佩你们,然后冷不丁地提一句,只是你们的时间到了。
我最近听到有人说,高管被解雇后,他的时代也就随之结束。而后来的上位者,属于他的时代就悄然到来。这是我们身为人类的自然规律吗?

《花月杀手》剧照
DEADLINE:对于自然更替的问题,你的电影给出了一个凄凉的答案。
斯科塞斯:答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被金钱利益驱使,所有的土地就在你眼前,但原著人拿这块土地做什么?欧洲人在想,我们来到这里,看看这个地方。看看这些财富!而印第安人他们在做什么?杀水牛。他们在猎场相互斗殴,他们群居度日。难道没人打算拥有这块地吗?用欧洲人的话说,印第安人不明白金钱的价值,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DEADLINE:所以你并没把大卫·格雷恩的原著小说拍成一部悬疑惊悚片,没有去大量聚焦联邦调查局如何立案,使之真相大白。相反的,你决定把电影设定为对人性的探索?
斯科塞斯:我和埃里克·罗斯和一同写作时,视角是以联邦调查局介入展开,揭开谜团疑云。迪卡普里奥看完剧本,看着我说:“这部电影的核心在哪?”确实,想象一下,当联邦调查局的人走进来,一段剧情展开,你在银幕上看到一个由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角色,他叫比尔·黑尔,你就立马知道他是个反派。这一切毫无神秘可言,就是一个警察的破案故事,谁在乎呢!打开电视有的是破案节目看。
我们能找到的关于欧内斯特的文本素材少之又少。更多的文字是关于比尔·黑尔、莫莉和其他人。我和艾瑞克甚是喜欢剧本初稿,里面有我从小到大看到的西部片元素,当时我很想就这样拍了。但我说,“除了莫莉·伯克哈特,其他人唯一有心的人,就是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也正是如此,他们相爱了。”
我们去了俄克拉何马州Gray Horse居地,奥色治族人热情招待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人们站起来说话。一位女士站起来谈起了故事:“你知道的,欧内斯特和莫莉彼此相爱。别忘了这一点。” 我想,‘哇。故事就是这样。他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
DEADLINE:推测一下,如果这一版本从白人男性的角度来讲述,会更符合西部片的精神。
斯科塞斯:这样的版本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研究过汤姆·怀特,他就是个钢铁直男。在书中,他父亲是个执法者,教导他做事清廉,要有同情心。我们对汤姆·怀特做了很多功课,想要更深入挖掘这一人物。他的困境是什么?也许他喝酒了?最后我说:“我们究竟在干嘛?拍一部关于汤姆·怀特拯救万物苍生的电影?”
DEADLINE:经历了这些,你开始质疑那些从小看到大的西部片里对正派/反派,尤其是印第安人的叙事描绘。这样的认知颠覆对你有多大影响?
斯科塞斯:嗯,相比民间传说,正派反派的传统叙事更多地与神话有关。从邦妮和克莱德,娃娃脸尼尔森,再到西西里黑手党,很多持枪歹徒变成了30 年代里那种联邦调查局取昵称的通缉对象。罗伯特•沃肖的文章《悲剧英雄:黑帮党徒》阐述了这一点:观众觉得,黑帮反派应该最终有人收拾,罪有应得。西方的神话就属于这个范畴。
约翰·福特和霍华德·霍克斯他们拍了很多黑帮传说,当然,还有最具传奇色彩的《原野奇侠》。但我们从小看的电影里,对印第安人的刻画大部分都是不公平的。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西部片是《阳光下的决斗》,片中莱昂内尔·巴里摩尔叫詹妮弗·琼斯为印第安女人(贬义)。当时我才6岁,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为什么他们对这些吉普赛人,印第安人这么生气?就像英国电影《残月离魂记》里,菲利丝·卡沃特扮演一个有着吉普赛人血统的贵族,晚上她会跑出去和吉普赛人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我当时不太明白(笑)。我想这更多的是与性有关,而不是人类学和社会问题。我是看《红河》这样的电影长大的,在电影里,印第安人把马车围成一个圈,乔安妮·德鲁肩膀中箭。那一幕令人难以置信,蒙哥马利·克利夫特拔出箭,把毒液吸出来,而她眼睛都不眨。我认为,这一类型电影的一大问题是所有印第安人角色都不是印第安人参演的。比如《酋长之子塔赞》(1954,道格拉斯·塞克执导)中,演印第安人的就是美国白人演员罗克·赫德森。

《花月杀手》剧照
DEADLINE:在电影里,你呈现了1921年塔尔萨的大屠杀,白人至上主义者摧毁了黑色华尔街。这些画面是你对当时白人态度——稍有挑衅就会变成暴力——的延展性刻画吗?
斯科塞斯:我不知道。我们几年前才完全意识到塔尔萨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都知道这块土地一直都有种族间的暴乱与私刑。但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毁灭性后果,他们出于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感而党同伐异,想要抹除所有弱势下位者和不同肤色的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彻底绝情,了解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做的事……我认为,这些都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行为。他们把整个国家都当成一个大实验,所有人都牵连到一起。
DEADLINE:如果是迪卡普里奥来演汤姆·怀特,如同他演《华尔街之狼》里的凯尔·钱德勒般,效果会是你们的故事把这个角色感情搅得一团糟,扭曲着李奥,剧情走向不可收拾。
斯科塞斯:李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是能进入角色,这也是我们经常合作的原因。你会感觉他挑选角色就像是去怪异之地前行,前方困难重重,曲折蜿蜒,但不知何故,我们合作总会达成默契。通常在他的表情里,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眼睛里,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情感。我一直这么跟他说。他是个天生的电影演员。我给他拍一个特写,他可能什么都不用去想,然后我可以把任何素材和他的镜头穿插在一起,人们看到的反应会是,“哦,李奥在表演,面部表情回应着之前的镜头。”这就是典型的库里肖夫效应。你可以对李奥做这样的实验。他的电影脸被镜头锁定了,他的眼睛,他最轻微的动静,我们都一清二楚。多年来,西尔玛·斯库梅克跟我一起剪辑李奥的镜头,她经常说:“看这个画面。这里的眼球运动,我们应该保留这个镜头。”这很有趣,我们可以透过的他的眼神知道电影发生了什么。
DEADLINE:李奥的首次银幕突破是在《男孩的生活》(This Boy’s Life ,1993),他在片中与罗伯特·德尼罗演对戏。据说这是德尼罗告诉你的,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
斯科塞斯:不完全是。那时候德尼罗通常不怎么说话。记得那是在1992年或者93年的时候,自我们拍完《好家伙》(Goodfellas)后,已经有近10年没有合作过了。《好家伙》之后,德尼罗又拍了《男孩的生活》。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些我不不太清楚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向我推荐别人。他说,“我和这个小男孩(李奥)一起拍戏。你必须找个时间跟他合作。这孩子真的很棒。”

《花月杀手》剧照
DEADLINE: 他说为什么了吗?
斯科塞斯:他不怎么说话(笑)。他会说:“李子很好。”或者,“你用他就对了。”又或者,“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有些东西。”
DEADLINE:这是你和德尼罗的第十部携手之作,同样也是你和迪卡普里奥(DiCaprio)第六次合作的作品。但除了一部短片之外,这是你第一次将他们二位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耗时如此之久?你什么时候会让他们两位共同出演一部影片,比如说《无间行者》(The Departed,2006)这样的电影?
斯科塞斯:就这个事情我们和鲍勃(Bob指德尼罗)有商议过,但是他当时不想做。你看,我和有些人合作过很多次,因为我发觉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处在一个边缘地带。回首往事,我感觉我是何其幸运创作过如此多使我功成名就的影片。其中这个“边缘地带”指的是,这些年来有很多演员我本来很想与他们合作,但我不适合商业思维。我是有努力尝试过,很幸运是和保罗·纽曼(Paul Newman)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合作了。现在万事遂意,但在拍摄《好家伙》之前,我和鲍勃有十年没有联手合作了。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各行其事,然后我们制作完成了第二,第三部影片,此后的十九年时间里我们就没有再合作了。同时,如果合作是指拍电影的话,我和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合作过两部影片,有几年时间我想和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合作.
还有一些尝试合作过的演员的名字我不想提,也不合适说。我欣赏的人很多。感觉都错过了。然而,我发现,在很多电影的主题上,鲍勃和我之间似乎有着一种舒适度似的,顺便提一下,这非常不易,但我们知道在这个舒适度下,我们想要影片呈现某种效果。至于具体指什么,也许不可名状,但我们可能联袂而至。
不过我们也有很久没有一起共事了,因为你也知道,人都会变的,但是他想做的事依然没变,《赌城风云》让我也坚信了这一点。就电影类型而言,《赌城风云》(Casino)的摄影风格就成了他和我的最终选择。后来我与莱昂纳多在《飞行家》(The Aviator)里也是如此。他和凯特·布兰切特出镜画面让我目瞪口呆,我觉得太赏心悦目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学到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学到了。也许他还是个小孩子,还在不断成长中。我有几个女儿。我没有儿子,所以也许这就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为人父母一样。但是,哇。
我们拍《无间行者》时他正是意气风发,饰演的那个角色,比利,真是太棒了。那个被卷入凯尔特街头(Celtic street)战争的孩子,他们杀了来自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意大利人只为寻欢作乐。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街上处于枪林弹雨中。他们就像,正如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在他的评论中所说:“这部电影就像对良心的审视,当你整晚熬夜想办法告诉牧师: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是,哦,神父,我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他的人物特性,他做到了,让人叹为观止。他不是一个信教徒,但他体察这人间百态,而且我觉得这个男孩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在和鲍勃完成《赌城风云》之后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我制作了《达赖的一生》(Kundun)和《穿梭阴阳界》(Bringing Out the Dead),还有《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我们对电影制作和其他东西事无巨细地检查。他想让我做《老大靠边闪》(Analyze This),我说“我们在《好家伙》里边已经做过了。我跟他谈了其他的项目,有一次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和你一起做的是哪种影片”。我说,“好。”于是历时九年我们创作了《爱尔兰人》。之后也不断地研究探讨。“那《无间行者》呢?”“不,我不想。”“好的”。

《无间行者》剧照
DEADLINE:他拒绝了《纽约黑帮》吗?
斯科塞斯:那次我们只是口头商议。说真的,他说:“你在干什么?”“我做这个。你感兴趣吗?“ “算了吧”“好的”。我们总是谈论这种事,因为从我们十五六岁的那段时间开始,他就是我周围唯一一个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是谁的人。他对纽约的那个地方很熟悉。他会说,“如果一场戏不适合我演,我也能接受,但如果别人演会更出彩,那一定要让别人演!” 这完全出于我们之间的本能和他的勇气与谦逊。
现在来看,那是过去的一段时期了。10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想的吗?是的,他依然和以前一样!但他现在还是以前的鲍勃吗?不,就像莱昂纳多说,“这东西的核心在哪里?”我说是欧内斯特(Ernest)。他爱她,她也爱他。但是...他什么时候知悉他是在毒害她呢?他们给她胰岛素真的是用来治疗糖尿病吗?所有这些都是未知的。但他显然在伤害她,一个人深爱对方,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很明显,他是被他舅舅比尔操纵了。这是人物特性上的弱点。他就像《沉默》(Silence)里边的吉次郎(Kichijiro)一样。
DEADLINE:那个一直背叛传教士,搞砸一切在忏悔中寻求赦免的角色?
斯科塞斯:是的。他就是个灾难。
DEADLINE:从故事展开的方式上看,你确实不知道欧内斯特(Ernest)是否在矢口否认事实,还是说他就是有所不知。医生说这种药有助于缓解她的糖尿病,他可能只是谨遵医嘱。
斯科塞斯:这才是关键。就是这个场景。那一幕直到我们拍摄那天才写好的。我们只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工作。当他点头的时候,当莱昂纳多说到“好吧,你明白,那只会拖慢她死亡的速度。”他说:“我拒绝接受现实,接受了你们所有人强迫我做的事。”
DEADLINE:莉莉·格莱斯顿(Lily Gladstone)饰演的莫莉(Mollie),是这部电影的良心(conscience)。你给她什么样的指导了吗?莫莉坚韧不拔寡言少语,但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斯科塞斯:莉莉有她自己的想法。她的大脑和心里充满了聪慧和理智。这几乎是本能。当莫莉(Mollie)说“你知道的,卡奥迪(Coyote)想要钱” 他说,“是的,我爱钱。我们来找点乐子吧!” 她说“你说得对。我支持你。”她爱他。那是莫莉的事。直到庭审结束,她才离开他,我想她只是真心爱他。她谈论他的眼睛之类的事情。她姐姐说:“哦,我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家伙。但是,你知道,他们都想要你的钱。莫莉说:“没关系,他舅舅很有钱,他对钱不是很渴求。” 我会在这里使用“美丽的失败”(beautiful failure)这个短语,而她的“美丽的失败”是她的信任和爱。也许我们将其看作失败,但这对她来说不是失败,因为她爱着、并信任着。她有心,她无法接受他会做出故意毒害她这样的事。

《花月杀手》剧照
DEADLINE: 但是莫丽的亲戚们都在她周围可疑的环境下濒临死亡。
斯科塞斯:然后她始终相信他置身事外。
DEADLINE:你已经描述了你和德尼罗之间的简语。这种简语(shorthand)在和迪卡普里奥合作中也适用吗?
斯科塞斯:和莱昂纳多,我们没有简语,都是全语(It’s longhand)。我们一起闲逛聊天研究各种事情。我给他东西读,还有音乐。他对音乐也信手拈来。就像我说的,他让我想到欧内斯特,而不是汤姆·怀特(Tom White),尽管书中关于欧内斯特的描述性文字寥寥可数,但是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一个爱着他的妻子,但却毒害妻子的人。他说,“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做吗?“ 他想进入那个人迹罕至的领域。这就是激情。是的,我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片场。周末的时候。电影就是生活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鲍勃也一样。
DEADLINE:最近对科波拉进行了一次长采访,他说在电影公司插手《教父》事务之后,他只想和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写《教父2》。但他有一个完美的年轻导演来接手:你。派拉蒙拒绝了他。你还记得么?
斯科塞斯:他告诉过我,说实话,我不认为以那个时候的我以及那时所掌握的能力能对付得来这部电影。他把一部电影拍得既雅致考究又技艺精湛,和《教父2》一样是史诗级别的,我不认为...现在,我会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的那种老成是长年累月的。我还有这种急躁的感觉,就像野孩子跑来跑去一样。
我发现自己不太擅长于描绘地位更显赫的黑帮人物。我更接近街头。我适合塑造市井上那些小有成就的人物。我做到了,尤其是在《好家伙》里,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成长了。我看到我周围的人不是在会议室或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聊天。这需要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另一种艺术水平。他和我来自不同的世界。《教父2》的故事更像是托马斯·马洛里(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这是美妙的艺术。

《教父2》剧照
DEADLINE:我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把《辛德勒的名单》让给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你的《达赖的一生》《沉默2016》(Silence)还有现在这部《花月杀手》这样惊心动魄的电影超越了影片《街头黑帮》。你当时觉得《辛德勒的名单》不适合你,是不是认为《辛德勒的名单》像《教父2》一样,不在你熟悉的世界里?
斯科塞斯:哦不。《教父2》弗朗西斯只是跟我提到过。为《辛德勒的名单》,我请斯蒂文泽里安(Steve Zaillian)和我一起编写剧本。我正准备执导。但是我在某个时候是有点保守。别忘了那是1990年。1988年,我拍了《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那部电影的重点就是开始一段对话,对话是对我来说仍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本性——真正的本性——爱,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耶稣。我不是在文化上矛盾,这是我们体内的东西。上帝在我们心中吗?我真的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我喜欢探索这一点。我想就此展开对话。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所以,我做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我用了一种特定的方式,而《辛德勒的名单》因为反响不好而夭折。我尽力了。我环游了世界。任何争论我都接受。我可能是错的,但我不确定教条会不会出错。不过我们可以争论。
以《辛德勒的名单》为例,我经历的创伤大到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有些犹太人对《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编剧是非犹太人而感到沮丧。我听说人们抱怨辛德勒利用犯人来赚钱。我说:“等一下。”我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就事论事说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我记得这些年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直向我提起这件事。他举起了我们在去戛纳的飞机上看到的这本书,他说,“这是我的黑色电影,我会成就它的。“那是1975年的事了。我说”嗯,我有《基督最后的诱惑》,我一定会成功的.“
我当时用了这句话,“我不是犹太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日记必须由一个犹太人来完成,我认为史蒂文也了解到。他来自……(停顿)费伯尔曼(The Fablelmans set)一家在哪,凤凰城吗(Phoenix)?他告诉我凤凰城只有200个犹太人。我不敢相信。因为我来自下东区,和犹太社区一起长大。我不是无私的,但我觉得他才是真正应该经历这一切的人。我担心我不能公正地对待情况。
DEADLINE:这段旅程改变了斯皮尔伯格的一生。当你终于看到《辛德勒的名单》,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斯科塞斯:我这么说吧,你可能会说这是在转移话题,我敢说如果是我拍的话,它不会像现在这样远近驰名。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些想法。大部分都在于我有一个不同的结局。我对这部电影拍案叫绝。但我知道我的电影不会有那样的成绩,他们不会在学院放映。你会说:“可是你有这么多提名啊!”是的,是的。但是,当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和我没有因《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获得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提名时,就注定了会那样。我意识到,闭口不言好好拍电影吧。
《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我们曾经想过我们会获奖,但我说,“不会的。” 我当时不以为然。至少它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在80年代,我完全籍籍无名。从《喜剧之王》(King of Comedy)到《好家伙》。还没有《基督最后的诱惑》。我意识到,‘你别拍这些电影,马蒂。你别做这些事。闭嘴,拍好自己的电影吧。如果你愿意,也许你应该在欧洲拍电影。也许你应该做低预算,独立的电影。但我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开始,然后他们最终又回归到主流那一套了。在80年代,我使用成本策略拍摄《下班后》(After Hours),然后做了一部《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的工业电影。《最后一次诱惑》耗资很少。然后我又拍了另一部工业电影《好家伙》。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好家伙》,我也是受到严苛的对待的。1989年没有特殊待遇,甚至华纳兄弟对我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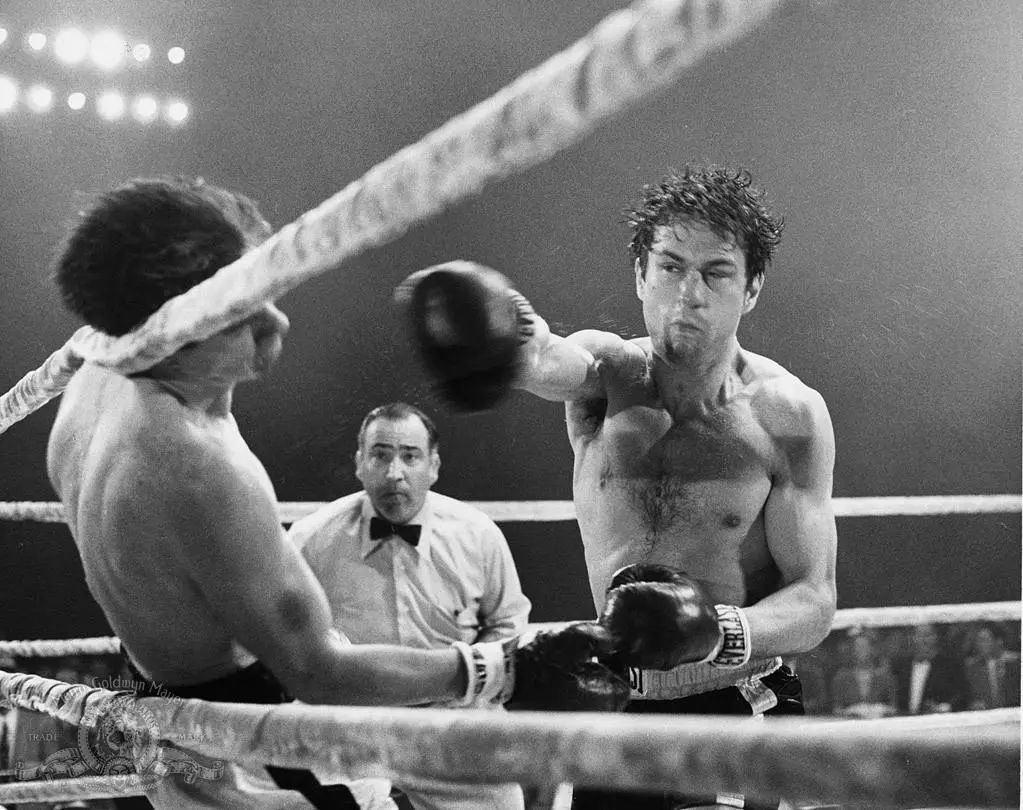
《愤怒的公牛》剧照
DEADLINE: 为什么?
斯科塞斯:因为预算,该死的。就因为预算,这事我有责任。《好家伙》拍摄周期大概超出预期15天,【第一副导演和第二组导演】乔·雷迪(Joe Reidy)在70天时才完工。他们说,55天内做完。我们试过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甚至有个医生告诉我,“不要喝咖啡,因为这可能会让你太过于精神紧绷。”我们在第70天结束了。
DEADLINE: 完全契合你最初的计划。
斯科塞斯: 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做吧,做吧,省点钱,做快些”,“我懂。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做的时候,简直是被摧残着。当时的情况就是,“天啊,两天过去了!天啊,又过了一天!”天啊,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噩梦。
他们做得很好,也很享受这个过程,最终表现得也很棒。只是,在那段时间,他们略逊一筹。我知道,但他们本人不知道。我能感觉到,那个影片很特别。《花月杀手》不一样。我们一天天地做,在不断推进中才发觉。太疯狂了。我是说,我把它构造好了。某种程度上算是异国情调。这段时间并不轻松。
DEADLINE: 听起来这个慢慢发觉的过程让你感觉精力充沛。
斯科塞斯:是的。就《好家伙》而言,这是尼克·派莱吉(Nick Pileggi)和我发自内心的,但没立于书面上,然后是一个不断推进、推进、推进的事情。这也要设计在书面上。有些事是心血来潮的。比如,乔·佩西(Joe Pesci)会进来说,“我想拍这样一个场景……”整部电影里,我们都是这样,“照做就是了。”我们试拍时这样做,排练的时候又重写。
DEADLINE: 这是“我怎么这么搞笑”的场景么?
斯科塞斯:他说,我出了点事,我们在一家餐厅。“我说,‘告诉我’,他说,‘我不能在这里说’。我说,‘那好,去我家吧’。我们就这么做了。他说,‘我要表演出来。他照做了。我说:‘我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它甚至没有在剧本里啊。我没写进去。我们要挤出一天时间来拍摄。那天马克坎顿和华纳兄弟的其他几个人在一块,我们听到镜头外的笑声,就是他们发出的。

《花月杀手》剧照
DEADLINE:就在最近,《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thers)赚得盆满钵满,而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执导的关于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代言耐克(Nike)运动鞋的电影《气垫传奇》(Air)的票房却与好评不相匹配。《花月杀手》背后的媒体叙事痴迷于它的放映时间和2亿美元的预算。苹果公司决定将通过派拉蒙电影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发行这部电影,这可能最终会成为连接流媒体和影院的未来,因为P&A使它比只在流媒体上上映更具有文化意义。雄心勃勃的院线电影的未来将驶向何方?
斯科塞斯: 这确实是个问题。谁说电影会延续过去几百年的方式? 在过去的25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五年来事情变了,就在过去的一年里,事情变了。谁说它会以这种方式继续存在呢?人们会在周六或周日的下午或晚上去电影院,在可容纳1000或2000名观众,有着大屏幕的影院里看《漩涡之外》(Out of the Past )或《玉女奇男》(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之类的电影吗? 我希望这种方式可以保持不变,因为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电影的。我知道,在大屏幕上与任何观众观赏任何电影,都比你一个人看要好。这项技术的本质就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比如,在那个世界里有特定电影,连我都会说,“让我们等一等,在流媒体上看看吧。”
但你是在跟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说话。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他们应该在影院里共同体验电影。像《超级马里奥兄弟》这样的电影就非常适合年轻人。但他们也会日趋成熟。那他们生命中的这部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电影就是娱乐消遣,或者,他们怎么说的来着,那种小剧团晚上的演出?
DEADLINE: 小剧团晚上的演出(Tentpoles)。
斯科塞斯: 是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电影吗?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80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就像一个触手似的东西。那陶德宽银幕真是精妙绝伦。我永远不会忘记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的彩色介绍。然后火箭升空,大幕拉开,放映开始,在巨幕之上,这篇精彩的游记《80天环游世界》的故事被这块银幕娓娓道来。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如此。我确实认为,必须集中精力培养观众对电影的鉴赏能力,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意味着影院这边也要出力。
院线方说,“我们放映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电影。”什么东西都被分门别类了。但是,如果屏幕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呢?不是一有银幕的,比自己家的还狭小些的房间。这意味着一个人携三两好友一起去电影院,被那部电影所触动。那个人可能会出来编写剧本或小说,这个剧本会变成一部在未来会给影院带来更多收益的影片。世事难料。因为也许,就那斯皮尔伯格和我来说,我们去看《祖与占》(Jules and Jim),他会与特吕弗和费里尼成为朋友。他们的电影深深影响了他。我想我们可以在影院里以《花月杀手》为媒介,为那些想要看这种类型影片的观众创造这样的体验。
人们说我花了多少钱,其实是说苹果公司花了多少钱。如果苹果公司给了我一定的资金,我会想,“好吧,我必须按照这个金额去拍影片。”,你可能会说,“你还获得其他投资了吗?”但有时钱不是越多越好。你要努力实现你的承诺,相信我,我做到了。这和《爱尔兰人》情况不一样,在《爱尔兰人》中,网飞(Netflix)给了我们额外的钱来制作电脑生成图像技术(CGI)。

《爱尔兰人》剧照
DEADLINE:当媒体报道你的预算时,迪卡普里奥改变角色使得派拉蒙暂时撤销了主要投资方和放映时间,这会让你感到有压力吗?
斯科塞斯: 的确如此。一开始就在电影院放映是有风险的。但这个风险是关于这个题材的,然后对于运行的时间的风险,这是一种契约。我知道我可以在电影院坐下来看三到四个小时的电影,或者在家看五到六个小时。如果有观众喜欢影片,“我保证。你的生活可能会变得丰富。这是不同的电影;我真的这么认为。好,我已经拍好了,所以,嘿,答应我要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
为这个影片,这个故事,和这些人,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下午,体验电影里反映的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那个小世界.这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体悟的更丰富。
DEADLINE: 您已经八十岁了。你还有激情回到摄影机后面重执导筒吗。
斯科塞斯: 必须的。必须的。是的。我希望我能有八周的休息时间,同时拍一部电影(大笑)。整个世界都向我敞开了心扉,但一切都晚了。太晚了。
DEADLINE: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科塞斯:我老了。我阅读,观望。我想讲故事,但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当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把奥斯卡奖颁给黑泽明时,黑泽明说:“我现在才开始看到电影的无限可能性,但已经太晚了。”那个时候他83岁了。当时,我问:“他是什么意思?”现如今我能理解了。
-FIN-
原标题:《斯科塞斯谈《花月杀手》,80岁时终于理解了黑泽明》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