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阿贝尔:木瓜溪——1992年冬 | 花城中篇
木瓜溪:1992年冬
阿贝尔

导读
1992年,刚调到木瓜溪中学的冬树老师,在校长的鼓励下给桑果姑娘写了一封求爱信,不曾想居然收到了回信,两人最终喜结连理。领证那天,冬树在党政办门口看见县里的愣头青们在盘问两个陌生人,怀疑他们是来“抽猪苦胆的”。一时间谣言四起,各家各户因为担心养的猪被害,慌忙杀猪,这两个陌生无辜的年轻人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找不到活计,露宿街头,被殴打驱逐……小县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随着新年的到来悄无声息落下帷幕,新的陌生人又来了。
一
早先,木瓜溪的同事都以为冬树是直接从桃花江调来的,其实不是,来木瓜溪之前冬树在黑白河还待了一年——9月去,7月走。
来木瓜溪时冬树依旧单身,也依旧年轻。一个单身老师,无论是在扁担一样两头挝的老街上买东西下馆子,还是在随时都能听见空堂课的老师把乒乓球打得嘀咯嘀咯响的校园里晒太阳听收录机,别人都看得出你是单身。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都没个异性朋友来访,周末也不外出,不用打听就晓得你是单身,还没处对象。那时,人们普遍都很羡慕新来报到的老师有对象陪着,下了车,两个人抬着行李走过扁担街,在人们羡慕而好奇的目光里走进校园。不说柔情蜜意,单是一对儿就让人啧啧称赞。办完手续,走进用刚拿到的钥匙打开的旧教室隔成的寝室,两个人扫地,两个人铺床,两个人挂蚊帐……那种温馨有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味道,单身汉是体会不到的。
来木瓜溪三年,冬树都是一种单身的状态。之前在黑白河和桃花江是不是单身都不晓得。不一个人发呆、一个人上街或关了门喝闷酒,就看不出他失恋过。他只是爱唱歌,走路、洗衣、打篮球都歌不离口。一个人在屋里唱,逢场天上街也唱,一个人散步对着大山大河也唱。

“我真希望变成我们洗衣台前的那棵紫荆树!”粮站守寡的仓库管理员说,“我要是那棵紫荆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听冬树唱歌了!”
“我还希望变成我们厨房前的那棵柿子树呢!”尚显年轻的学校食堂的炊事员不服气地说,“我要是那棵柿子树,我会觉得冬树的每一首歌都是唱给我的。我敢打赌,我会结出比柿子树结的还多还甜的柿子!”
没有人知道除了粮站守寡的仓库管理员和学校食堂的炊事员外,还有没有人想变成那两棵树。丁字街缝纫摊的秦姑娘没看见过冬树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信用社的唐姑娘和开馆子的幺姑娘也没看见过,如果看见了没准也想变成那两棵树……真动人啊,水龙头的山泉水哗哗流淌,有时完全是喷射,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歌声那么动听,冬树的眼眸多情又专注,稍显迷离的目光落在树干或树枝上,落在树笼的鸟儿身上。学校卢姑娘、俞姑娘、李姑娘是看见过冬树唱歌的,不只是一边洗衣一边唱,一边打球一边也唱,一边摘葡萄或一边改本子一边也唱,但她们从来没说过,至少是没公开说过她们想变成那个篮球、那架葡萄或那些涂了改改了涂的作业本。
缝纫摊的秦姑娘长得水灵,雌激素刚刚好,眼眸和脸蛋的光泽是女人一生中最鲜净、最饱和的。冬树把牛仔裤拿去交她补、交她缅边,或者把外套拿去交她钉纽扣,不过是想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如果真要叫他和她谈朋友又不干了,嫌她没文化。信用社的唐姑娘长得没秦姑娘好看,也没秦姑娘水灵,却是信用社的正式职工。她不仅比秦姑娘成熟,也比学校的卢姑娘、俞姑娘和李姑娘成熟,初见像个少女,有几分调皮,熟悉了便发现她骨子里的圆滑世故和脸上的暗斑(据说是做过人流的标志)。女人们和她交往都隔着三分,别说跟她处对象了。关于唐姑娘,木瓜溪有不少传说,都是暗传,从未有人拿到台面上讲,包括她的绰号——“伏尔加”(县上来的部长坐的苏制轿车)。
幺姑娘没法跟秦姑娘和唐姑娘比,她就是个开馆子的,长得敦敦实实,平常一身油,看人的目光也是油。但她人好心善,冬树翻一碗烧白,她送一碗白菜汤。自然,冬树万背时不会找她谈朋友,别说送白菜汤了,就是送烧白送卤牛肉也不会和她谈朋友。不谈朋友,馆子还是要下的,免费的白菜汤还是要喝。特别到了冬天,馆子里有火,灶孔里的老酒树烧得水淌,坐在火盆边看幺姑娘炒菜,或菜端上桌笑盈盈看着你吃,油腻算什么?温暖是第一位的,从军大衣暖到心窝子。
学校有未婚老师九男三女,比例严重失调。晚饭后轧马路,单身汉走一起,谈论的全是“配对”的话题。
有时,轧马路的也不都是单身汉,当中会混进一两个已婚男人。教物理的M便是一个,他老婆在江油,他一个月跑一趟,雷打不动,平常在木瓜溪冒充单身汉。不过他是过来人,尝到了女人的甜头,倍感煎熬。和单身汉在一起他是教科书,有时喝了酒,小范围还是科教片——他闭上眼,一边讲解,一边示范。
冬树目睹过一次M不雅的示范便不常跟他往来了,也不常跟围着M打转的同事往来了,喊轧马路不去,喊喝酒也不去。冬树不是觉得M有多坏、多下流,他自己也想那些事儿,有时特别特别想还一个人在被窝里做。他只是觉得不雅,M不雅,或者说不美,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美。他觉得那点事属于个人隐私,应该有一种配得上的美,而非亵渎。
在被窝里,冬树没想过学校的未婚女老师,也没想过信用社的唐姑娘和开馆子的幺姑娘。真要说,他只想过缝纫摊的秦姑娘。那种很单纯的想,很单纯,也很激越。白天见了,说了话,晚上在脑壳里重现,像一幅画,像镜头,尽管也有身体,但不是现实的、真实的,有身体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俞姑娘的眼睛长得好看,天生传情,难免让人误会。不过,冬树不会误会。在冬树眼里,她没有想象的空间。她放话说“非公检法不嫁”,冬树不觉得她世俗、攀高枝啥的,只觉得天真。俞姑娘读沈从文的《边城》,喜欢翠翠。不过,还是有人误会她了,不信邪,不是“公检法”也敢写信表白,被拒绝了还不死心,直到别个把求爱信贴在厨房的墙壁上,像改小学生作文一样用红笔改过错别字,签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才肯罢休。

二
1992年冬,也可能是秋,冬树不再是单身了。木瓜溪的秋冬没有界限,深秋和初冬重叠在一起,从一场一场的秋雨重叠到一场一场的雪,从河岸的彩林重叠到峭壁的华山松。
秋天和冬天重叠,冬树也在自己的二人世界里重叠,跟桑姑娘重叠。当然,还不是天衣无缝的,还是有限——有底线地重叠。周末或空堂课的下午,在经过一个潮湿的夏天石灰墙又变白的寝室——冬树的寝室或桑姑娘的寝室——一盆红彤彤的炭火都燃熄了,窗外已开始打麻影,两个人还重叠在一起。他们终究还不能像立冬前后的木瓜溪那样有一线(准确地说是一绺)最深邃、最精致的重叠,即是人们常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得守住底线。在桃花江,冬树的一位同事便是因为没守住底线铸成大错的,铁饭碗耍脱不说,至今还在狱中。冬树的文朋诗友中也有没守住底线的,很麻烦,对方有了,四处托人找卫生院或私人诊所堕胎,搞得神经兮兮的。冬树守住底线不单是有前车之鉴,也不单是桑姑娘要守贞,而且是他觉得守住底线本身是一件很雅、很美的事,既有身体接触,又有柏拉图之恋。
12月12日。星期六。农历冬月十九。上午,冬树和桑姑娘去乡政府拿了证。整个下午,冬树都在打扫卫生,布置“新房”。不只是打扫布置,还借了高凳,用自行车从十里之外的梯子驿驮回半袋石灰,筛选后制成石灰水粉刷寝室。
这是颇有意思的一天,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日。冬树是教语文的,也代历史,所以记得。为什么选择这天拿证?冬树也说不清,或许觉得这一天“有名”、容易记住,或许是撞上了。照说,选这么一天去拿证并不好——不吉利,再“有名”也是“事变”,婚姻讲白头偕老。
就算是水到渠成吧!两个人有所保留地重叠了那么久,彼此了解了那么久——性格的了解、兴趣爱好和理想的了解,以及身体的了解。不早不晚,水就在12月12日到了——流淌到了。水到之后渠自成,在水流的后面呈现,是堰渠,也是水迹,更是两个人爱情的轨迹。
“这么卖力,莫了今晚有什么想法?”墙刷到一半,坐在火盆边的桑姑娘对正在高凳上忙活的冬树说。
“有没有想法你晓得?”冬树说。他卖力地用长刷的一角一小块一小块地刷着墙,连边边角角也不放过,脑壳里是一个童话般的雪白的二人世界。
“我晓得啥?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回食虫。”桑姑娘站起来,望着冬树的后背咯咯地笑,笑过问冬树晚饭想吃馒头,还是面条。
“面就算了,我想吃肉包子。”冬树转过身来,看着已是自己法定妻子的桑姑娘说,“你去买一斤卤肉,我们喝一杯,拿证是大事,庆祝一下,再说我也累了,解解乏。”冬树戴着一顶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撕掉了外圈的草帽,衣服和裤子上全是石灰浆,像穿了身迷彩服。
刷完墙,冬树又收拾了地板。他并不觉累,他说解解乏不过是找喝酒的由头。屋外的天还亮着,桑姑娘买卤肉还没回。房间里没什么家什,架子床是固定的,只需揭掉盖在上面的油布,打开床单被褥便可以睡;搬动过的桌椅长凳,顺手搬回了原位。在有些刺鼻却感觉很好闻的石灰水气味中,冬树体会到了一种劳顿后的满足,以及对慰劳的期待。
他走出房门,站在屋檐下,瞭望了一番校园。隆冬里,周六的傍晚,学生早放假了,老师该走的也走了,没走的都躲在屋内烤火炖肉,校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阵阵北风吹过回响在掉光叶子的核桃树、苦楝树巅的呜呜声。
回到屋里,冬树在炭火上点燃一支烟,抽烟时他想起了上午在乡政府拿证时遇见的事。
上午有太阳,但没出多久便没了,刮起了北风。冬树和桑姑娘走进乡政府院子的时候,恰逢一阵风把葡萄架上的葡萄藤刮了下来,蛇一般挂在砖柱上,有的还盘到了砖柱外侧的菜地里。小两口(可以这样称呼了)踩着满地枯叶,绕到楼房当头的楼梯,略显忸怩地去了二楼的民政办。从一楼党政办门口经过时,他们看见两个陌生人坐在门口一把废弃的长椅上,灰头土脸,嘴唇发黑,浑身发抖。冬树想问又没问,心想择日高高兴兴来拿证,不能让不相干的人或事影响心情。到了民政办,他们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照和事先开好的单位证明交到民政员手上,三分钟,最多五分钟,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便拿到了手里。结婚照有点意思,不是在县城国营照相馆照的,是一个转乡的照相师照的。照相师手艺不赖,“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笑一笑”,咔嚓按下快门儿便成了,只是后来在县城遇见借过冬树五元钱。冬树穿一件牛仔衣,领子有棱有角;桑姑娘穿一件白底红花毛衣,头发一丝不苟,五官、颈子及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很精致。
下楼再次经过党政办,冬树和桑姑娘看见有人正在盘问两个陌生人,声音很大,态度一点不友好。他们命令两个陌生人把他们的彩条编织袋和牛仔包打开,把包里的行李物品倒在地上。盘问者不是乡政府的干部,也不是派出所的民警,而是木瓜溪街上的愣头青,有一个还是冬树教毕业的学生。
冬树来到后窗,推开一扇,看着窗外差不多落光叶子的青冈和枫树,耳朵里满是从树脚崖下传来的比夏秋小了很多的溪流声。随着溪流声一并传来的还有乡政府院子里那两个陌生人的哭诉:“我们不是抽猪苦胆的,我们是江油人,听人说木瓜溪“出红滩”了,我们是来当“马尾子”的……我们真的不是抽猪苦胆的……”
桑姑娘推门进屋时天已经黑了,冬树在火盆边眯了一会儿刚醒来。“咋买了这么久?我都等睡着了!”冬树站起来说,看着桑姑娘手里纸包的卤肉。桑姑娘没答话,脸颊酡红,径直走到后窗,把纸包放在桌上。
“狠心人,买了这么久!我都等不得了!”冬树走过去,抱住桑姑娘说,“看把你冷的,脸都冻红了,我给你暖暖。”
桑姑娘吻了冬树一下,推开说:“我去时幺姑娘馆子的卤肉还没起锅,等了会儿才起锅,总不能到对面曾家馆子去买,我晓得你爱吃幺姑娘卤的肉。”
“等了一会儿也要不了这么久,你看看表!”冬树说着,走上去又抱住桑姑娘,两只眼睛神经质地看着对方。桑姑娘推了他一下,他把她抱得更紧了,头埋进她的鬓发和颈脖,断断续续、瓮声瓮气地说:“今天证也拿了,这下总可以……”

“想得美?还没办台子呢!等两边办了台子才可以……”桑姑娘说,使劲推开冬树,去到门边临时搭建的灶台准备晚饭,“我汽包子,炒个蒜苗回锅肉,你往火盆上添些炭,多烧两壶水,晚上都洗个澡。”桑姑娘边打火边说。
冬树在原地木桩一般站着,听到“洗澡”二字,挫折感一下没了。续火烧水之前,他走到后窗打开纸包,抓了片卤肉扔在嘴里,是幺姑娘卤肉的味道。
吃饭的时候,冬树问桑姑娘上街听没听见什么风声或看没看见有什么动静。桑姑娘不明白冬树的意思,不知该如何回答,反问了一句:“你是问抽猪苦胆的事?”
“明知故问!”冬树说,“木瓜溪除了抽猪苦胆的事,还能有什么事?”
桑姑娘听了像是放心了,讲起了街上的见闻:家家户户都在划柴,都在借皇桶,准备杀过年猪,都想赶在抽猪苦胆的人来木瓜溪之前把过年猪杀了,不只是杀过年猪,架子猪也杀,除了乳猪不杀。还有老婆婆去水沟子的小庙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她家的过年猪,保佑她家过年猪的胆囊;抽猪苦胆的人已经到了与木瓜溪相邻的蒿溪、片口、白熊几个乡,一夜之间,这几个地方的猪苦胆被抽空了。一百家杀过年猪,有九十九家的猪胆囊都是瘪的,里面没一滴胆汁,刀儿匠把胆囊摘下来,用热水冲洗干净,上面的针眼儿一清二楚,就像是主人家用纳鞋底的针刚刚刺上去的;抽过苦胆的猪肉有剧毒,不能吃,也没人敢吃,青川有一家子舍不得扔,煮了吃全家六口得了败血症。离仙女堡十几公里的柏梓村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扔的猪肉,树上挂的也是猪肉,白熊乡通往九寨沟的公路两边的雪地里也到处是扔的猪肉,一块块冻得硬邦邦的,结成了冰,有豹子和黑熊叼吃了,发现被毒死在了箭竹林……
桑姑娘和冬树碰一下杯就讲一段街头见闻。她碰了杯只抿一小口,冬树则干了杯。当然,桑姑娘讲的未必都有条理,有的地方甚至有些杂乱,但冬树听了会在脑壳里组合,使它们看上去像书架上一码码的书或木瓜溪人家后院一摞摞的柴垛子那样规整有序。
节选毕,阅读全文请订阅《花城》2023年第3期
责任编辑 许泽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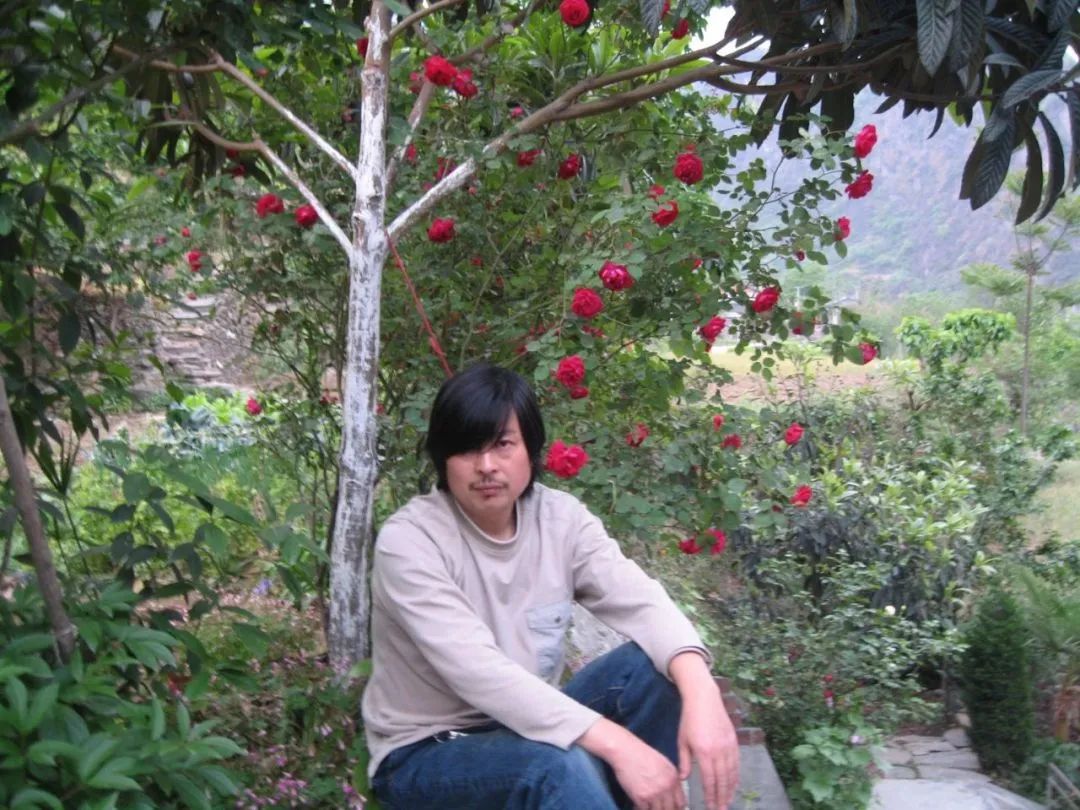
阿贝尔
1987年开始写作。作品见于《上海文学》《天涯》《花城》《四川文学》《中华散文》等期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出版有《隐秘的乡村》《岷山札记》《白马人之书》《飞地》等散文集和长篇小说。《桃花江》是在《花城》发表的第四部中篇小说。现居四川平武。
END
原标题:《阿贝尔:木瓜溪——1992年冬 | 花城中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