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爸是个药罐子,我实在不想再尽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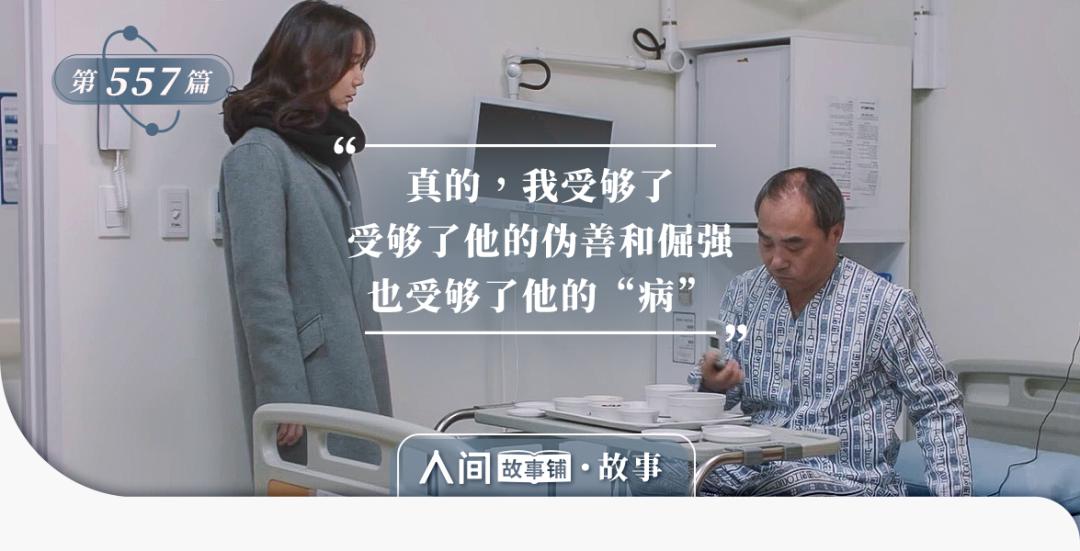
对家人暴躁,对外人友好,这样鲜明的对比在孩子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父女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所有的关心都被屏蔽,唯独留下相看两厌却无法放下的拧巴情绪。
人间故事铺
storytelling
8月份的上海潮湿闷热,六人间的大病房里掺杂了各种排泄物和剩饭菜的异味。房间里多是长期患病的病人,家属生怕他们“着凉”不肯开空调。脸上的汗水混着泪水打湿了口罩,我抹了一把不小心抹进了眼睛,疼得睁不开,让我的心情更加地暴躁。
“你自己收拾东西出院吧,我受够了!”我对着坐在病床上的爸爸大吼。

1

我爸出生在南方一个小乡村,随部队来到北方,在政治部搞剧本创作。我妈当年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方城市。
在外人眼里,我爸爱读书、有文化、有内涵,我妈贤惠、温柔、能干,我有个完美的家庭。但是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爸关上门就是个暴脾气,我妈则是个“怨妇”,最主要的,我爸还是个“药罐子”。
从小经常听爸妈抱怨北方的水土,太干燥,不养人。我爸说,自己一直不能适应北方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所以需要长期吃药。我家里常年弥漫着浓浓的草药味,我爸隔三差五地找大夫开方子“调理”身体,虽然我并没有看出来他哪里有明显的不适。我妈则是从骨子里把泡药煎药刻进了她的每日流程,什么方子需要泡久一点,什么方子需要多熬几泡,她都不用看医嘱。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她每日的抱怨和唠叨。
我对那股草药味深恶痛绝。一年一年熏陶在药味里,我觉得自己都要生病了。
药物的调理没有“治愈”我的爸爸,反而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经常失眠,睡不好早上就心情极差,晚上回家他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他的创作也并不顺利。这样的不顺在夜里会加重他的失眠,失眠又加重他的身体不适,成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恶性循环。而我和我妈,就是他的出气筒。年幼的孩子搞不懂父母为什么而生气吵架,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被大人嫌弃。
但是有一个例外,只要一出家门,温文尔雅的笑容又会立马被“戴”在他脸上。他会乐呵呵地给大院里的同事、朋友、战友主动打招呼,并“熟练”地拉起我的手。邻居们都热情地回应他的客套,并称赞我们和睦的父女关系。有时候我希望每天早上送我上学的时间可以放慢一些,再慢一些,这样不真实的画面就会变得真实,会让我分不清哪一面的爸爸才是真正的他。
2

我的青春期遇上了我爸的职业瓶颈期,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好了。那几年部队陆续传出军改的消息,我爸听说隶属的机构要减员转制,几经纠结决定提前利用政策转业。中考那一年,我爸转业去了一家国企的市直机关,我们家也搬离了家属大院,住进了转业安置给的小区楼房里。
我爸告诉我们,他是新单位的科长,是专门给领导写材料的。他依然压力很大,而且开始加班。我妈抱怨说:“什么破科长,工资还不如之前多。”脱离了部队大院的环境,小区虽然多是转业军人安置时分派的房子,但是很多被转租或者卖出去了,大家互不认识,也没有了过去职级间的恭维和邻里间的客套。我爸出门时的那张“面具”,好像没有再戴上的必要了。我们父女间仅有的一小段温存时光,也不复存在了。
爸爸在家的时间变少了,一开始我觉得轻松了许多。我妈不知道是不是进入了更年期,越来越频繁地跟我絮叨当年如何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做了随军家属,如何为了我维系着这个家,为了我忍耐着这个常年郁郁寡欢的男人。时间久了,母亲的埋怨就像草药煮完后剩下的渣滓,慢慢渗透在这个家里,看不到,摸不着,闻不见,却让我窒息。而年少的我没有足够的是非判别能力,跟随着妈妈把这一切归咎在常年拉长了脸的爸爸身上。

临近中考的那学期,我的叛逆到达了顶峰。学校不准女生留长发,要求统一的齐耳短发,我不听。我不仅留了长头发不去修剪,还背着父母去商场柜台打耳洞。我没有多余的零花钱买高档的饰品,就买廉价的小玩意,再加上柜台人员操作不卫生,很快我的耳洞就发炎溃烂。但这样肢体上的病痛不仅没有吓退我,反而让我上瘾。我的右耳从耳垂到上方耳骨,陆续打了五个耳洞。
老师打电话到家里让父母来学校谈话,我爸在老师面前依然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导致老师也没了脾气,对我的指责轻描淡写,反而说了很多关心我的话。我本来等待着一场“恶战”,但内心的不羁好像被这样和气的面谈浇灭了。
那是我爸头一次陪我从学校回家。我记得爸爸推着他的自行车,我推着我的,谁都没有骑上去。我们迎着夕阳,就那样在马路上走着。我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躲进远处楼房的边缘,暗红色的光晕和清冷的蓝色交织在一起,对比那么强烈,让人感到莫名的忐忑和不真实。
北方3月的风还充满着寒意,但是我的右耳因为发炎红肿而滚烫。这样冷热交替的刺激让我耳朵上的血管一跳一跳地“喘息”着,好像为了让我记一辈子。我想起小时候每天早上出门上学路上的画面,好像也是这样肩并肩走着。
爸爸到家没有开灯,但我分明能看到那张“和气”的脸变了样子。我妈问学校说了什么,一下子激怒了他积攒一路的火气。“你把你闺女培养成了一个......”爸爸骂出了对女人最侮辱的两个字,是的,我没听错,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女儿,我是一个彻底被他嫌弃的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下贱吗?因为我随你,我像你一样病态。别装了,我看你根本不是身体有毛病,你是心理有毛病!你喝再多药也治不好自己的病!”
黑暗中我的右耳突然感受到一阵剧痛,就像一个重物坠在地上那种闷痛。几分钟后我才明白过来,爸爸给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刚好扇在了我的右耳上。
3

我的青春期在右耳的发炎中戛然而止,我们的父女温情也随着那一记耳光而荡然无存。
中考,我考去了当地的寄宿学校,逃离了这个充斥着“病态”的家庭。那时候城市里开始有家庭私家车,周末会有父母开着小车来替孩子拿行李箱。我都是一个人坐公交来,一个人坐公交回。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逐渐消退,我的怒气也逐渐化为失落和冷漠。
高考我没有考入让父母满意的学校,在本地一所专科学校读了三年。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寒暑假我尽可能不回家,宁可一个人待在学校宿舍里。我很少问及父母的事情,只是每周宿舍的电话机会定时响起。我妈一如既往地对我倾泻着一周的怨气和不快,好像我就是她的情绪垃圾桶。
我不喜欢接这样的电话,但是又有点期待,毕竟这是我跟我爸唯一的一点联系。我发现,自己内心是渴望知道他的消息的。从我妈后来的抱怨中,我知道我爸转业后在新单位并不是给领导写材料的“红人”,只是一个部门的文书而已,负责收发下公文和报刊,转转通知。我知道我爸的查体报告越来越不好,尿检指标总是有箭头。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慢慢真如他“期待”般病了。
大学期间我开始打游戏,认识了一个网友华子,他从小家庭不和父母离异,很懂我的苦衷。我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人和人之间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我抑制不住自己对他的倾诉。大专毕业,我们俩决定一起南下找工作,彻底远离北方城市。我感到家里的第二次“大战”要开始了。
果然,趁着我还没离校,我爸“杀”来学校找我谈话。爸爸找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冷饮吧,开了一个单间。学校周边建了很多适合小情侣约会的小店,做点冷饮、咖啡和简餐,不知道他当年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
我点了一份意面,其实就是本地的玉米面条煮好浇了袋装的酱料,我爸不会点,要了跟我一样的。我闷头吃面不说话,味道一点不好吃。我偷瞄爸爸一眼,他吃进第一口就皱了眉头。
“小淼啊,爸爸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你能不能不走?”我没有吭声,心里默默嫌弃了一句,“哼,这么多年了,还拿身体不好当借口。”
“您别劝了,我们已经订好车票了,住处也大概找好了,他在那边有朋友,去了我们会继续找工作。”
本来以为我爸会暴躁,会斥责我打游戏,会斥责我找了不靠谱的男朋友,会斥责我一个三流学校的大专生去大城市根本找不到工作。但是都没有,他那天意外地安静和沉默。或许,他真的病了?
我送爸爸去公交站。不知道是我长高了,还是爸爸走路变慢了,我们过去肩并肩的步速,变成了我走走停停。我不忍心刻意地等待,悄悄放慢了脚步。那一刹那好像回到了十年前,我想让时间变慢的那一刻。

4

我跟华子来了上海,靠我自己的实力确实没找到什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最终在我南方小叔的帮助下找了一家企业打工,一向要面子的爸爸背地里给家里人打了电话求助。
华子方方面面都不是父母心目中的女婿,我也一直没有领他见家长。我们确认关系、租房、同居,都没有告诉我爸妈,我知道他们也都能想象到,只是不想戳破。华子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有着稳定的情绪,他能给我安全感和依靠感。我的失落、我的倔强、我的喜怒无常,他都能包容和安抚。
在上海的第二个中秋,我妈让我回家,在电话中告诉我,我爸真的病了。一开始是尿蛋白和潜血异常,医院确诊肾炎,后来说是肾病综合征,但是控制不住,有可能往尿毒症和肾衰竭发展。我脑海里浮现出大学即将毕业时的那个傍晚,爸爸吃面皱眉头的样子,还有他走路缓慢的样子,那时候的我未曾怀疑过是他反胃和下肢水肿的表现。
我火速订了火车票,查了家乡三甲医院相关专家的信息,第一次如此着急地回家。初秋的北方还带着一丝闷热,我打开家门一股熟悉的草药味涌上来。常年离家,我好像已经忘记我有个“药罐子”父亲了,也早就笃信他的病都是装的。
我妈这才告诉我,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爸就从单位办了病退,天天关在家里。因为是提前退休的,他觉得没面子,单位安排的活动一概不参加,安排的定期查体也不去。本来单位有市医保,但他非不去定点医院正规看病,自己去找“大夫”继续抓些偏方回家煎。那些店铺都不是正规的药店,不能走医保,掏空了很多钱。
我忽然意识到,我这次的归家,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在等着我收拾。
5

我爸果然不同意跟我去医院,还不停骂我妈给我乱打电话,说看到我回来更给他添堵。当天晚上,我爸因为剧烈头痛被120送去了急诊,判定为疑似脑梗,后期诊断是长期肾炎引发的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心包炎,还有贫血、血小板功能异常等并发问题。
住院不到一周,我爸的暴脾气又犯了。我妈在病房里跟我爸吵了起来,说他病好点就又有力气骂她了。这样的画面我再熟悉不过,安静了一年多被唤醒的一点亲情,再次被现实打破。
单位请不了太长的探亲假,我合并中秋也出来十天时间了,只能赶着回去。回到上海不久,我妈来电话说我爸身体又不行了,他们要来上海看病。
我在上海租住的是一室一厅小房,本就空间紧张。华子没有抱怨,当天去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床,清理掉了小客厅的杂物。爸妈到上海只住了一晚,就直奔医院,医生检查结果与上次无异,建议回老家长期治疗。
那天华子做了一桌子菜,他们也算是第一次见他。我妈没有任何为人父母该有的客套,只顾着当面数落我爸的种种不对,说实在忍不了他了。原来这次来上海,是因为我爸完全不听当地医院的医嘱,不忌饮食,不吃出院时开的药,还是迷信那种“名医”,导致再次出现尿血。
我听着他俩一句句的争执,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满是药味的家里。那种气氛就像煮了好多泡的草药,越来越浓,一点点弥漫开,直到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畸形的病态。这种病,不仅仅来自于身体,更深入每个人之间的血缘关系。
6

那次上海的短暂相聚不欢而散,却成了一个不好的开端。不知道是父母真的老了,还是一次急诊有了心理恐惧,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爸妈隔三差五地要来“大城市”看病。一开始我不停地告诉他们,当地的三甲医院也很权威,肾病不是罕见病,不需要来回折腾。但他们每次都会再延伸出新的不适,说出很多骇人听闻的并发症,说必须要去大医院看才放心。
后来我开始一次次嘱咐,如果来看病,要当地医院开转诊,不然报销受限制。他们说医生不给开。我又嘱咐那不开转诊也要记得在老家的医保办做备案,不然异地医保没法结算。他们又说不会弄。再后来,我只能嘱咐他们,即便没有做备案,从上海拿回去的病例和各种票据,要记得一个月内去医保做异地结算报销。我知道,他们一定也没有去。
这些来来回回的琐碎和唠叨,彻底磨碎了我的耐心和仅剩的亲情。我曾经发誓不要做我妈那样的怨妇,现在看来,我也变成了那种执着于唠叨的女人。
最让我头疼和无奈的,是他们疲于走各种医保流程,直接导致异地就医的起付线高,报销比例低。我妈微薄的退休金,我爸提前病退打折扣的养老金,再加上他大半辈子“药罐子”带来的开销,使整个家庭的余额已经捉襟见肘。我和华子平时打工的收入只能维系我们小家庭的开销,根本负担不起一次又一次大医院的检查费和药费。

直到去年夏天,他们再次“南下”看病,下火车当晚我爸二次脑梗,被送进了急诊室。这次不再是“疑似”那么简单,我爸住院十几天,先后换了两个病区。虽然没有落下明显的肢体障碍,但是语言上明显受了影响,说话不是特别清楚了。
当时的上海刚刚经历了大面积的疫情,医疗系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及时入院治疗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爸明显对六人间的大病房有诸多不满,却为了顾及在众人前的面子假装言行得体。
我跟华子交替陪护,租了折叠床。一大早查房收走了床铺,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倚靠在床头柜边的凳子上。我时不时眯眼看着床头的点滴数量,但实在撑不住在打盹。我爸突然重重地拍我,咕哝着让我给隔壁床的大爷捡起毛巾。原来旁边的病患毛巾滑下来了,刚好掉在床下的便盆里。我心里想着肾病的病人本来就排尿少,那个便盆并不脏,更何况我不至于在陌生人面前还这么有眼力见儿吧。隔壁大爷谢了好几声,我强装笑脸捡了起来。
午餐时对面老人的孩子来不了,一直没吃上饭,我爸的“伪善”又发作了,让我在手机上给人家订餐。即便是那位老人家一个劲表示不用订不想吃不好意思,他还是执意操着他含糊不清的普通话要求我,并拿出小时候的严厉。
他果然还是当年那个人,那个把自己最后的一点耐心和善心都用在外人面前的人,那个觉得面子重于一切的人。
7

出院那天正值立秋,但是南方的八月依旧没有一丝凉意。公休假、探亲假甚至病假,一年过半我已经用光了全年的各种假期,实在不能再请假了。早上我先去单位打卡又转地铁来到医院,为了上班穿了尖头小高跟,跑到医院时足尖处已经酸痛难忍。看到爸爸坐在床上在跟隔壁大爷聊天,那满脸的笑容使他看起来是那么地和气和善解人意,就好像小时候家属院里那个令人羡慕的好父亲。
我看着床铺上干干净净,知道行李还一点没收拾,心里一团火升了起来。我没有跟周围人打招呼,闷头收拾东西。
“小淼啊,这位李叔叔家就住在咱家隔壁小区,打完针就可以走了,我们一起把他捎回去好不好?我们晚一点办出院,等等他,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的火气简直要爆发出来了,直接一句话怼了回去:“爸,我们是打车回去。”“我知道啊,所以一起捎回去啊,这样还省一份路费,你知道出租车很贵的。李叔叔一直夸你好孝顺,羡慕我有个好女儿。”
“你自己收拾出院吧,我受够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你不要再演下去了!”
我抛下一句话夺门而出,直奔医院茶水间。真的,我受够了,受够了他的倔强,受够了他的伪善,也受够了他的“病”。一滴眼泪滑下来浸湿了口罩边缘,我顺手抹了一把,夹杂泪水、汗水和化妆品一起被我揉进眼睛,疼得睁不开。我眯着眼下意识地想扶住一个东西,却被热水炉烫了个正着。早就疼麻木的足尖突然也恢复了知觉,我扶着墙脱下一只高跟鞋,发现外侧两个脚趾与鞋子的交汇处,已经是深深的血印。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北方的孩子,“回到”所谓故乡的南方,也并不适应这样的气候。我每天精心打扮后在外人面前装白领的样子,与当年“笑脸相迎”的爸爸如出一辙,这个面具后的现实,原来这么痛。

那一天出院,我和爸爸一起把临床大爷送回了小区。爸妈在我家只住了一晚,便订车票回家了。他们后来没有再来上海复查,虽然我依旧叮嘱我妈记得带他去做复健,叮嘱不要让他吃肉类荤菜,低油低盐低蛋白,但我知道他是不会听的。
8

我跟华子过了一段消停的日子,生活忙碌、疲惫,但没有焦心的烦躁。我生日那天,华子提前回家烧了一桌好菜,发信息要我早点回家。一个高高壮壮的大男人,这些年最擅长的居然是煲汤。家里小没有封闭式厨房,他就尽量用蒸煮煲代替煎炸炒,我知道他是在抚慰我天生的南方胃。
虽然已接近十月,但那天的上海依然高温。一直汗腺发达的我从公司出来的一小段路,腋下和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钻进地铁站又忽然袭来一股冷气,使我下意识地缩起了胳膊。
人挤人的晚高峰里,我一向缩着胳膊站在角落,因为我担心自己举起胳膊抓住扶手的时候,会暴露腋下浸湿的衬衣。每次进地铁时的冷热交替都让我难受,腋下虽然冰冷潮湿,却因为自卑不敢张开胳膊透气。
一位大叔最后一名挤进门里,俨然一副外地人来沪的尴尬和无助。他大概不适应这样高密度的人群环境,不知所措地躲来角落放下行李,并主动让出能抓到扶手的地方。我应付着他的客套,不想去抓扶手,但是他执着地把我让了过去。
看到那种尬却刻意礼貌的样子,我忽然觉得很熟悉,有点想念那个“彬彬有礼”的爸爸。或许在外人眼里,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吧。我被迫站在了扶手下,小心翼翼地举起右臂,握紧上方的扶手。腋下顿时有一股凉意,吹散了那种黏腻的不适。我悄悄用余光扫视周围,其实并没有人在意我。
最近,我已经改掉了穿高跟鞋的习惯,脚上的乐福鞋踩上去软软的,不再有脚趾的麻木和钝痛。我掏出耳机塞进耳朵,脑袋靠在自己的大臂上,身体随着车厢轻微地晃动。地铁冲出了漆黑的隧道,我看到远方的太阳逐渐滑向楼房的边缘,清冷的蓝色刚好接住了暗红色的光晕,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温润的紫色,让人感到踏实。
晚上华子送我一个礼物,是一个红色绒面的老式首饰盒,里面是一颗小小的、金色的耳钉。我已经快十年不戴耳饰了,只保留了一个耳洞没让它闭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结婚吧。”华子轻轻地说出来我心里一直在默念的那句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华子是唯一那个能让我做个“正常人”的人,我的心理状态,也被他一点点修复着。
9

疫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华子说接我父母来上海一起住,万一有个急症也能照应,我没有吭声,我知道自己内心对爸爸的冷漠已经开始转变。“我从来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我反复用这句话给自己洗脑,逼着自己放弃对爸爸的理解,让自己好过一点。
年底那段时间,我跟华子一起发烧请假休息。我们都没有胃口,每天只煲一锅粥,却在一起说了好多话。虽然呆在家里,但我的心一直揪着。我在网上反复搜索肾病患者感染病毒的案例,搜索着家乡的管控政策和就医新闻。一想到因为我的倔强没有听华子话接来父母,爸爸万一真出个状况,我就不敢再想下去。华子看出了我的焦躁,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跟我讲起他小时候的事。
华子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大抵是父亲有了其他人。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是从母亲嘴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一句不好。在他意识到父亲角色缺失的时候,妈妈就会给他描述一个爸爸。后来长大了他觉得有点好笑,因为妈妈每次描述的父亲,都不太一样,那里面有姥爷的影子,也有邻居小孩爸爸的影子,还有电视里父亲角色的影子。他跟母亲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妈妈也是那种不擅长表达的传统长辈,但是他明白,她之所以这样美化一个离家父亲的形象,是不想让他一辈子活在恨里。或许,他健全的情绪控制能力,就得益于他母亲的教育方式。
华子说,住院陪护那段时间,我爸晚上依然失眠,跟他讲了很多事。他打趣说“见识”了各个年龄段的我,懵懂可爱的幼年,叛逆不羁的少年,还有冷漠独立的青年。父亲说,从小家里双亲去世很早,他是家里的长子,早早出去当了兵,努力拉扯后面的弟弟妹妹成年。他很小就发誓,要靠自己的努力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但是很多事事与愿违。这些话我不曾听父亲提起,或许对他这样的男人来说,与最亲近的说心里话,才是最难的事情。
华子说,那个金子做的耳钉,其实是爸爸买的。说爸爸已经买了很多年了,本来想在我毕业时送给我,但是一直没能拿出来,让他悄悄送给我。他说,他很后悔当年打了我的右耳。
封控政策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查了车票,我和华子正式以夫妻的身份回家。正逢跨年夜,我妈张罗了一大桌子菜。我发现爸爸对我妈做的荤菜碰都没碰,只是简单地吃了点煮玉米和蔬菜。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里,没有了草药味,只有饭菜香。

后记

岁月总是不尽如人意,年轻时的爸爸曾经背负着家庭的重担,但中年事业不顺导致他内心自卑,用过度的自尊来挽回自己的面子,用孱弱的身躯作为自己止步不前的借口。步入暮年,一次次急诊经历让他对“生病”真的产生了恐慌,希望抓住亲情这最后一根稻草,却为时已晚,懊恼不已。生性倔强的爸爸不擅长表达爱,吝啬于对身边最亲的人展示自己内心的感受,导致我们的关系越走越远。每一次他沉静很久想拉回一点,两个同样倔强的人都会再次遇到矛盾,把一切弹回原点。
这样的爸爸,反而像一个孩子,他需要被人关注,被人夸奖,他不想被人嫌弃,就像小时候的我。而我,现在就是那个能给他安慰的“大人”。虽然最终我和爸爸谁也没有说出那句“对不起”,但这一次的轮回中,我不想再做那个“生病”的爸爸,趁一切还来得及。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是世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相似的基因造就了相似的性格,很多话我们当面说不出,一辈子说不出,但心里却是彼此最惦念的那个人。
回到上海,我剪了一个短发,就像初中时学校要求的那么短,刚好能露出我的右耳。那里戴着一枚金色的耳钉,好像一颗历经打磨的宝石,终于蜕变成光彩夺目的样子,也像每一段普通的父女之情,那种最不需要伪装的、最真实的情感。
题图 | 图片来自《房子的故事》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原标题:《我爸是个药罐子,我实在不想再尽孝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