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卞之琳:沟通中西诗艺的“寻梦者”
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挣脱传统诗歌文言用语和韵律形式束缚的要求下,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而进行创造的。当它脱离了民族传统诗歌的轨道,努力重建自身艺术传统的时候,始终面临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带有永恒性的命题:如何在外国与民族诗歌艺术营养的双重吸收中,寻找和沟通中西诗歌艺术之间的深层联系,建立现代民族诗歌新的道路和规范。这是中国新诗八十多年来一个最美丽的梦想,现代许多杰出的诗人都为这个梦的实现做过不懈的努力,卞之琳先生就是其中最富建设性的“寻梦者”之一。

青年卞之琳
为了反驳早期新诗倡导者对于民族传统的过分疏离,闻一多先生不但勇于破坏,也勇于建设。他反对“欧化的狂癖”的倾向,提出了创造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的诗歌美学理想。但是他们过分依恋英美古典诗歌的形式美,在摆脱自己镣铐的同时又多少陷入西方新镣铐的束缚。李金发提出在东西方诗人之间“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的“同一”处试为“沟通”和“调和”,但他过于欧化的实践使这些设计成为空洞的理想。周作人提出,在传统诗歌的“兴”与西方诗歌的“象征”之间,进行融合与创造,期望走出新诗比较隐蓄朦胧的道路,但这个空疏的设想也没有可能更多地付诸实践。卞之琳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真正地用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卓越实绩,超过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提供的抒情范式与空间,进入现代诗歌对于日常生活中诗性的发现;超越坦白直露的抒情方式,进入更深层的含蓄隐藏方式的探索;超越单纯模仿象征派造成的生硬晦涩,追求将西方的象征精髓融入民族诗歌固有的灵魂。他在这样的构想框架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自觉地探索着一条民族的现代主义诗歌道路。
1932年,刚刚22岁的卞之琳,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尼柯孙《魏尔伦与象征主义》的译文,在“译者附识”中,他肯定了象征主义诗歌,但反对李金发式的晦涩,明确地提出,这篇文章中提倡的象征派诗的“亲切与暗示”,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旧诗词的长处”,“可惜这种长处大概快要——或早已——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他的慨叹与批评,是自觉地在借“他山之石”,匡正当时中国新诗人过分忽略自己民族的传统诗歌艺术,盲目崇拜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弊病,他想在“暗示与亲切”这两个方面,找到传统与现代诗歌艺术的结合点,为新诗的现代性发展开辟一种新的可能性。“亲切”,就是要用敏锐的感觉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拉近诗的题材与人们情感及生活之间的联系,让诗更加贴近人的心灵。“暗示”,就是要避免诗歌传达的过分明白直露,用“契合”或“客观对应物”,象征和暗示诗人的情感与智性思考,给读者更多吟味和想象的美的空间。卞之琳的《断章》《圆宝盒》《白螺壳》《几个人》《鱼化石》《距离的组织》《半岛》《寂寞》等许多诗篇,之所以耐人寻味,引人遐想,在物象与情趣的巧妙结合中传达朦胧的旨趣,几十年后仍然给人超越时空限制的人生启示和美的享受,原因首先就在这里。
卞之琳与现代主义文学“一见如故”,他喜欢并学过波德莱尔、T. S.艾略特的诗歌,但却从不生硬地模仿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方法。他以人文主义的博大爱心,关注北京街头普通人的痛苦与欢乐、麻木与荒凉、寂寞与辛酸,也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痛苦地追寻人生的真谛,在民族的悲凉中他唱出《尺八》这样的故国之思。为了以美的极致传达自己真实的心,他总是从自身固有的深厚古典诗词修养中,调动自己认为可能具有鲜活性的艺术积累,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方法进行融合与创造,努力探索一种富有民族化的抒情之路。他自觉地探索中国古典诗歌重视“意境”与西方现代诗“戏剧性处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淡化诗的浪漫感伤成分,加强诗的智性与客观色彩,使得诗最大限度地具有像艾略特所说的那种“模糊与浓缩”的特征。卞之琳说:“在自己的白话新体诗里所表现的想法和写法上,古今中外颇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我写抒情诗,像我国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做戏剧性台词。”他把这种追求,说成是倾向“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雕虫纪历》序)。他的诗因此有一种颇具深度的普遍性魅力。《西长安街》中叙述者的声音,与老人,与站岗的黄衣兵的联想,巧妙地纠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历史与现实感极深的批判境界。《几个人》中几个人物真实与荒诞的生活片段,带我们走进一个令人战栗的世界。《白螺壳》在抒情主体的不断转换中完成了对理想追求者永恒怅惘心境的开掘。《水层岩》在拟想的小孩子与母亲在水边的对话中,暗示了时光易逝的生命悲哀的哲理。这悲哀不是属于他个人的:
“水哉,水哉!”沉思人忽叹,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这种抒情诗创作上的小说化,“非个人化”,有利于“跳出小我,开拓视野,由内向到外向,由片面到全面”。他的沟通中西诗艺的形式探索,是为使他的诗走进更多人的心灵世界。
心灵的沟通需要有对于现代艺术的理解。民族象征诗的艺术“寻梦者”戴望舒,为此提出了适应民族接受的诗美的传达尺度:“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之间。”卞之琳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为这样的审美追求做了最好的诠释。他与李健吾先生著名的关于《鱼目集》的反复讨论,他与朱自清先生之间关于《距离的组织》一诗的说明,不仅解除了对于自己诗的误读,也阐明了现代主义诗歌阅读与理解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圆宝盒》,他这样说:“我写这首诗到底不过是直觉的展出具体而流动的美,不应解释得这样‘死’。我以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但即使不确切,这样的解释,未尝无助于使读者知道怎样去理解这一种所谓‘难懂’的,甚至于‘不通’的诗。”他又说:“诗的‘独到之处’,并大量标新立异,在文字上故弄玄虚或者把字句弄得支离破碎,叫人摸不着头脑,假若你自己感觉不具体,思路不清,不能操纵文字,不能达意,那没有话说,要不然,不管你含蓄如何艰深,如何复杂的意思,一点儿窗子,或一点儿线索总应当给人家,如果您并非不愿意他理解或意会或有正确的反应”(《关于鱼目集》)。他翻译纪德的《浪子回家集》中,为《纳蕤思解说》所写的序,更对象征诗的诠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他的许多诗,朦胧而不艰深,含蓄而不隐晦,隐藏复杂但给你可以走进的“一点儿窗子”或“一点儿线索”,他的诗美,也就是读者经过思考可以接近而领悟的了。那首著名的《鱼化石》就是一个例证: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因为诗人给了一个副标题:“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又加了这样的注解:“鱼成化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近一点儿说,往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我们乃珍惜雪泥上的鸿爪,就是纪念。”这样,作者就给了读者在多义上把握这首诗的“窗口”和“线索”。你可以追踪作者的想象,领略更多的艺术给予的美丽。

老年卞之琳
在悼念卞之琳先生离我们而去的悲痛时刻,我头脑中总是回响着他《白螺壳》中这样的诗句:
我梦见你的阑珊: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黄色还诸小鸡雏,
青色还诸小碧梧,
玫瑰色还诸玫瑰,
可是你回顾道旁,
柔嫩的蔷薇刺上
还挂着你的宿泪。
卞之琳是位自觉地追求民族化的现代主义诗人,他有世界的眼光,更有现代的意识。他不拒绝“欧化”,也从不忘记“古化”。他在西方与传统诗歌之间寻找一种艺术结合的平衡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网络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能否写得‘化古’‘化欧’。”诗人几十年后写下的这番充满理性的论述,包含了一个民族现代诗的“寻梦者”一生心血探索的结晶。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的《新诗十讲》,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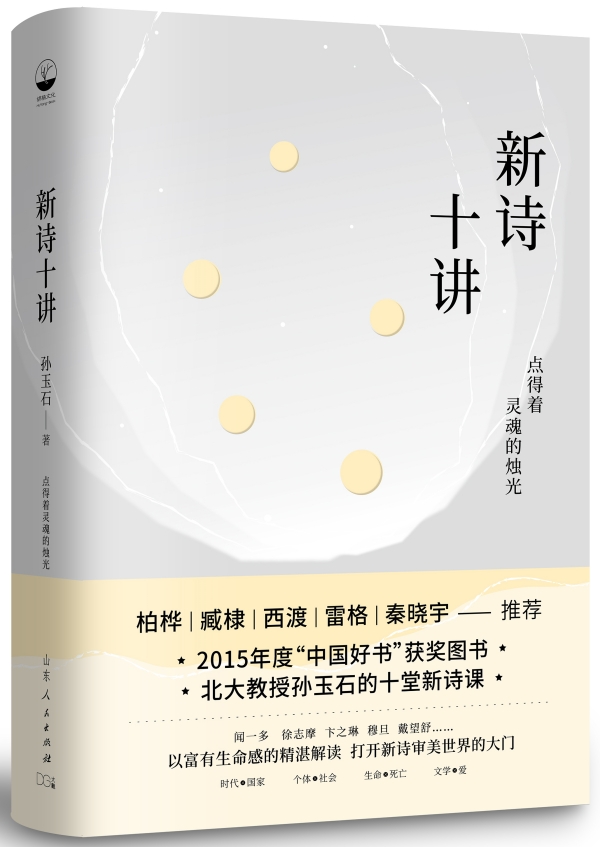
《新诗十讲》,孙玉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胡杨文化,2023年3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