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跳跃的边缘:迈克尔·卡米尔与中世纪艺术的边际

迈克尔·卡米尔在巴黎圣母院北塔(Stuart Michaels摄)
照片中作者出现于他在书中分析过的巴黎圣母院北塔上的一个场景,摆出了与他身后的怪兽客迈拉恰成镜像的单手托腮的姿态,若有所思看着照片外的观者;照片中作为背景的石雕客迈拉,一个凝视着巴黎风景的兽首人身怪物,本来是书中第三章代表着“在大教堂的边缘处”的一个著名形象(也曾出现于我2020年出版的一部新著之中),而在照片中,它曾经具有的“边缘”性已为前景中作者的戏仿形象所代替;二者之间,正好形成了作者书中曾经提到的“元边缘性”现象——一种以镜像方式制造出来的新的“边缘”,意在揭示边缘之所以运作的生产机制。
作者为什么出现于他的研究之中?他在沉思什么?他正看向谁?
在凝视照片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作者之所以出现于他的研究之中,并制造出他书中描述过的“元边缘性”,难道不正是为了向他的所有读者,包括照片的所有观者,包括作为译者的我们,现身说法他书中原理的奥秘?
在正式讨论这种原理之前,无疑有必要首先引入这位作者:他是谁?
一、迈克尔·卡米尔:此何人哉?
2002年10月的一天,当我于6年之后再次抵达巴黎,并在左岸的一家著名的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淘到了这本《边缘图像》时,我对于这位叫Michael Camille的作者尚一无所知,但并不妨碍我从此开始了对他所有作品如醉如痴地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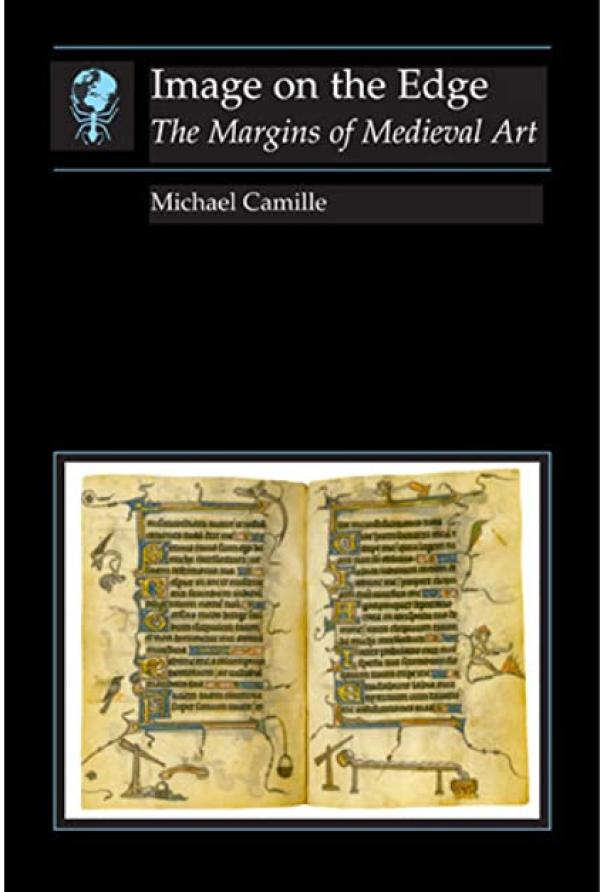
《边缘图像:中世纪艺术的边际》英文版书影
当时的我所不知道的还有,同一年的四月份,这位迈克尔·卡米尔已然辞世。尽管在我心目中,令我真心钦佩的艺术史家并不多,而卡米尔无疑是占据着这一星座的少数形象之一(另外两位是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和罗兰·雷希特),但他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布罗茨基发明的这一表述强调,与我们异时异世的伟大诗人因为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从而“变成了我们的同时代人”;但我更倾向于一种从该词原意出发的理解,即卡米尔事实上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种时间,故他的所作所为,更具有之于我们的参照系意义。
卡米尔有一个与我们一样平凡的出身。他1958年诞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小城基格利(Keighley)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这个家庭与普通中国人非常相像,“家里没有书”;但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毕业于当地的文法学校后,居然破天荒地考上了剑桥大学,据说还是该校五十年来的第一次。这个故事听起来也非常像同一时期中国经常发生的,一个“知识如何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他的本科导师后来回忆,卡米尔告知他在剑桥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晚上,看着学校满壁环绕的书城,曾发誓说“我要把它们全部读完”。这种童年期塑造的对于书籍和知识深入骨髓的饥渴感,也是我们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能够深切地体会的。
卡米尔在剑桥先学文学,然后再学艺术史;他相继于1980、1982和1985年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文学和艺术史的双重背景,也塑造了他一生对于文字与图像关系,以及游走于不同领域的边际和边缘处的敏感。1985年,卡米尔受聘于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那一年他27岁;才华横溢的卡米尔在芝加哥发展神速,不久成为全职的讲座教授(the Mary L. Block Professor)。而芝加哥大学的教职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份工作;从1985年直到2002年他因脑瘤而英年早逝,17年的芝加哥生涯,这位家贫无书的工人子弟贡献了7部专著和超过55篇学术论文,成就了他为知识的一生。他被誉为“自梅耶·夏皮罗以来西方中世纪艺术史界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智力形象”;而他对于艺术史最大的贡献,是将批判理论、性别理论、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接受美学引入艺术史,尤其是中世纪艺术的研究。
1989年,卡米尔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专著《哥特式偶像:中世纪艺术中的意识形态和图像制作》(The Gothic Idol: Ideology and Image-Making in Medieval Art,1989)。众多论者都正确地指出了书中对于中世纪艺术中如何将“异类”如麻风病人、同性恋者以及所谓“偶像崇拜”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加以排斥和污名化的过程,展示卡米尔鲜明地关注被迫害的边缘群体的社会性诉求;但更不应该忘记他在艺术史领域的抱负,即从一开始他就将书放置在与以埃米尔·马勒为代表的传统中世纪艺术史进行对话的语境,试图用对于“哥特式偶像”及其意识形态的研究,来替代埃米尔·马勒建立在19世纪浪漫主义基础上、过于理想化地粉饰和美化中世纪的“哥特式图像”(The Gothic Image)研究——后文还将提到,这种与学术史经典大师的竞争与对话,构成了卡米尔一生的学术激情。
他的第二部专著即本书,全称《边缘图像:中世纪艺术的边际》(Image on the Edge: The Margins of Medieval Art, 1992),出版于1992年,那一年他只有32岁。《边缘图像》不仅是卡米尔所有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也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顾名思义,书中延续了他对于中世纪世界“边缘”位置的考察,探讨了位于修道院、大教堂、宫廷和城市等社会特定权力场所“边缘”处的怪物、乞丐、妓女和农民的图像;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中世纪抄本绘画为例,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边缘所属的“文化空间”:即他除了关注图像的特定母题,还要关注“它们在所处的整幅书页、整篇文本、整个物像或空间内发挥的具体功能”。这一观点的重要艺术史方法论意义,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他的前两部作品总体上属于专题式研究。而他的第三部著作《死亡的大师:插画师皮埃尔·雷米埃死气沉沉的艺术》(Master of Death: The Lifeless Art of Pierre Remiet, Illuminator,1996)与第五部专著《羊皮纸上的镜像:〈鲁特莱尔诗篇〉与中世纪英格兰的制造》(Mirror in Parchment: The Luttrell Psalter and the Making of Medieval England,1998)一样,均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个案研究。《死亡的大师》把一位不见经传的法国插画师皮埃尔·雷米埃一生的绘画,放置在欧洲14-15世纪黑死病肆虐的巴黎背景上加以处理;他的作品都与死亡和肉身的衰朽有关,是谓一种“死气沉沉”的艺术。卡米尔是从书写于一部抄本边缘处的三行文字(写着“雷米埃,这里什么也别画,因为我要在这里画上一个记号”),和书页文本中间一处明显的空白,辨识出这位中世纪艺术家的存在,并将其与大量中世纪手稿中一种独特的手法相匹配,写出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著。对于人生的终极体验“死亡”和迹近遗忘的艺术家的关注,也使《死亡的大师》事实上成为卡米尔《边缘艺术》主题的某种延伸和变奏。至于他的另一部个案研究《羊皮纸上的镜像》,不仅其研究对象《鲁特莱尔诗篇》早已出现于《边缘图像》之中,而且其处理的主题——抄本边缘处农民劳作的“现实主义场景”和怪兽出没的“奇幻场景”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书籍的赞助人和艺术家共同营造的意识形态构造——本身亦可看作是《边缘图像》的某种扩展。
接下来的两部著作《哥特式艺术:辉煌的视像》(Gothic Art: Glorious Visions,1996)和《中世纪爱的艺术——欲望的客体和主体》(The Medieval Art of Love: Objects and Subjects of Desire,1998),属于卡米尔同样擅长的综论式著作类型。第四部专著《哥特式艺术》致力于从“新的视像”(New Visions)角度为理解哥特艺术提供“全新的观看方法”(New Ways of Seeing Gothic Art)。从作者所设置的章节标题(如“新的空间视像”“新的时间视像”“新的上帝视像”“新的自然视像”和“新的自我视像”),同样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与前辈大师相竞胜的意识。前文已述,卡米尔的《哥特式偶像》试图在内容上对于埃米尔·马勒的《哥特式图像》进行改写,而《哥特式艺术》则在结构上承袭了马勒源自博韦的文森所著《大镜》中的宇宙论模式(分成“自然之镜”“学艺之镜”“道德之镜”和“历史之镜”四部分),以期成为马勒版经典名著的一种当代性替代。而作为卡米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中世纪爱的艺术》同样亦可看作是从《边缘图像》“在宫廷的边缘”一章中扩展出来的一部专著,只不过这一次是爱的主题从“边缘”扩展到“中心”而已。另一方面,该书章节内容的设置(如“爱的凝视”“爱的礼物”“爱的场所”“爱的象征”和“爱的目标”),亦存在着与卡米尔前书、与马勒和博韦的文森之间的引用与互文联系。
卡米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巴黎圣母院的滴水兽:中世纪崇拜与现代性的怪兽》(The Gargoyles of Notre-Dame: Medievalism and the Monsters of Modernity,2009)。作为一部遗作,该书于卡米尔逝世7年之后才出版,但书的内容依然是从《边缘图像》“在大教堂的边缘”一章对于巴黎圣母院“滴水兽”图像的讨论中引申而出;不过遗著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巴黎对于这一中世纪景观的现代制造,揭示了以修复师Viollet-le-Duc、作家维克多·雨果等为代表的现代文人所共同创造的一个理想、浪漫而同质化的中世纪形象(书之标题所谓的种种“现代性的怪兽”)的历史过程。这一知识生成的研究亦回应了卡米尔在其第五部专著《羊皮纸上的镜像》中,对于20世纪的英国如何把《鲁特莱尔诗篇》为代表的中世纪抄本,当作独特的“中世纪英格兰”形象加以塑造的有趣分析。
上述作品中若隐若现的互文联系,深刻地诠释了《边缘图像》在卡米尔全部智力创作中的特殊地位。
二、何谓“边缘图像”?
这些侵入中世纪建筑、雕刻和插图抄本边缘处的图像——姿态淫猥的猿猴、口衔尾巴的恶龙、大腹便便的人群、弹奏竖琴的驴子、亲吻屁股的牧师和翻筋斗的杂耍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来自《边缘图像》一书的前言,也被该书英文版印在封底作为广告词。估计每一位读者读到此处,都会被这些问题吸引住目光,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书页去一探究底。在卡米尔之前,传统的艺术史对于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可谓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认为这些怪异的边缘图像是“毫无意义”的“装饰”,它们仅仅为抄本的拥有者提供“娱乐与消遣,或是唤起了他的赞美之情”。这种说法更经典的表述当数埃米尔·马勒,在他眼中的中世纪哥特式图像“相当单纯,令人惊异地纯洁”;而那些从中看出“下流与反讽”等“可怕而淫猥的场景”的“考古学家”,仅仅反映出自己心中的“偏见”。在这种方法论视域影响下,20世纪的学者如亨利·福西永的学生尤吉斯·巴尔特鲁塞提斯则进一步从形式主义角度,对这些图像加以细致的编目和分类——这类做法在卡米尔看来,是将它们“从所属的语境中抽离出来”,依然属于把它们贬低为“纯装饰”的行径。另外一种更为现代的发展,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这些边缘图像看作是绘图师无意识幻想的实现,“类似于今天学生笔记本中的信手涂鸦……是白日梦的象征”。
第二种形态则相反,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认为边缘图像富有意蕴,而且这种意蕴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如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批评家尚弗勒里,即把边缘图像中的蜗牛看作是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农业害虫”;另一位漫画史家则从蜗牛身上,看出“讽刺了身居戒备森严的堡垒却嘲笑遭受暴力威胁的穷人们的有权有势者”的意蕴;而抄本艺术史家莉莲·兰道尔,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1290-1320年间绘制的29部抄本中骑士同蜗牛打斗的图像母题,蜗牛与中世纪社会中一类特定的人群——胆小懦弱的伦巴底人(Lombards)——的关联。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涉及《鲁特莱尔诗篇》中农民农事生活场景的阐释问题,传统的看法均将其看作是中世纪英格兰农业生活的真实反映。
在卡米尔看来,上述两种阐释模式均存在着孤立地看待边缘图像的问题。他所提出的方法论提案,是把边缘图像与页中的文本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边缘并不单独存在,而是与文本一起从属于一个整体的“文化空间”。故而对他来说,图像的特定母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必须联系到“它们在所处的整幅书页、整篇文本、整个物像或空间内发挥的具体功能”来考虑。
首先,他以抄本绘画为例,讨论了这一“文化空间”具体生成的历程。这一部分内容(第一章)被冠以“制造边缘”(Making Margins)的标题,旨在道明“边缘”上的图像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个文化历史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基督教抄本已经存在图像,但正如8世纪著名的凯尔特抄本《凯尔斯书》所示,图像并不位于抄本纸页的边缘,而是与文本交织在一起,占据着文本“神圣话语的内部”的位置。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由这一时期僧侣群体的阅读方式所决定;这种阅读方式被称作“沉思”(meditatio),文本(包括图像)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僧侣们提供记忆或背诵的手段;每个单词需要在他们的大声朗读中“被咀嚼和消化”,故页面的布局或者词语之间的分隔均不重要,只要能帮助达成记忆或者“引发纯粹的幻想”的目的,即可大功告成。
第二阶段从12世纪开始,即艺术史上通常所谓的“罗马式艺术”时期。这一阶段同样发生了阅读方式的变革:它开始于图像被扩展至文本字母边缘以外的领域,由此导致一种全新的文本构成和分析手段的出现,表现为“页面布置或文本的‘布局’(ordinatio)取代了修道院的‘沉思’”。而这种“被言说的文本向被观看的文本的转变”,才是“对边缘图像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时刻。
第三个阶段为“边缘图像”的正式形成阶段。文本与图像的分离在13世纪亦即所谓的“哥特式艺术”时期达到高潮;原先的文本与图像由一人兼任的格局,转化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即文本的抄写员(the scribe)和图像的插图师(the illuminator)角色的分离:文本抄写完毕之后,再交给插图师以完成插画。一方面,这种分离导致文本抄写员地位的上升(他们往往是抄本制作坊的老板)和插图师地位的下降(他们变成抄写员/老板的雇员或订件制作者);另一方面,插图师的劣势地位也导致插图不仅扮演文本的附属和补充的作用(类似于“注解”文本的作用,例如用图像补充一段抄写员抄漏的佚文),更可以形成与文本的张力关系,充任文本的评论、批评乃至异议者的作用。“边缘”形成为一个文化空间中独特的组成部分,呈现出与经院哲学中的“论辩”(disputatio)异曲同工的形态,但却是用图像的方式实现的。这一格局导致“边缘图像”变成中世纪艺术中最具有活力的一个领域,也成为表现社会冲突的舞台。
其次,上述“边缘图像”并不仅仅发生在抄本绘画的“文化空间”,同样发生在其他领域真实的“社会空间”,例如“修道院、大教堂、宫廷和城市”等“中世纪社会中特定权力场所”的“边缘地带”(分别为卡米尔书中第二、三、四、五章的主题)。“社会空间”中“边缘地带”的存在,首先应该归结为中世纪社会结构中权力关系的客观存在。正如书中所分析的完成于1260年左右的《诗篇》中的一幅世界地图所示,这种权力关系开始于页面上方君临一切的上帝,结束于页面下方两条恶龙缠卷的“阴间”;中间的人类世界,则存在着“人们距离位居中央的耶路撒冷越远,身边的万事万物就会变得越来越畸形和怪异”(如右侧边缘非洲所在地的十几个奇形怪状的人形生物)的世界秩序。而上述四个权力场所及其“边缘地带”,与抄本绘画中呈现的“文化空间”一样,都是被镶嵌在这一包罗万象的中世纪世界图景中的层序结构。

《诗篇》抄本插图“世界地图” 犊皮纸彩绘
Add MS 28681号抄本第9r页 17×13cm 1262年至1300年
因此,无论是中世纪的“社会空间”还是“文化空间”,尽管卡米尔书中并没有给出二者孰先孰后的生成关系,但他确实很好地厘清了二者之间共有的结构关系,即一种中心和边缘相持相让、相互依赖同时动态平衡的关系。
这种结构关系首先是所在社会权力结构真实关系的表征。无论是《诗篇》世界地图所显示的上帝与恶龙的对立,是中世纪封建社会教士、贵族与农民的三分,还是男人与女人或者人与魔怪的二元概念,这种结构关系涉及到对于“空间的控制和编码”,必然会在它的边缘处创造出一个被排斥、被弃绝、充满怪异和反常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抄本绘画和修道院、大教堂、城市的边缘处都会充塞着匪夷所思的猿猴、怪兽、乞丐、妓女和农民图像的原因;尽管它们形态各异,其实经常扮演相同的结构功能——都以边缘处的反常和不稳定,巩固和维系了中心处的神圣和庄严。书中为此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分析案例,其中的一个涉及到《兰斯洛特传奇》抄本中一幅有趣的边缘图像:一个修女正露乳给一只猴子喂奶;这一图像其实是对于宗教绘画中的神圣母题“哺乳圣母”(Virgo lactans)的一种戏仿,其目的不是为了颠覆这一母题,而是以某种“反范例”的形式,旨在“使它们所欲悖反的范本变得更加突显”。

《兰斯洛特传奇》边缘图像细节“给猿猴哺乳的修女” ,犊皮纸彩绘、贴金箔 French MS 1号抄本第212r页 约1300年
其次,同样不应忘记由边缘的结构位置以及画师的自主意识所导致的它们对于中心的批判性戏谑、颠覆和竞争。这种关系暴露了边缘之于中心或者图像之于文本的紧张关系。例如,卡米尔提到,一部12世纪末献给坎特伯雷基督教堂的抄本的页面边缘,圣奥古斯丁被画成将手中的箭头指向有他的议论在内的文本,但他的手上却拿着一个写有“non ego”的卷轴,好像在说“我并没有那么说”——显然,图像(插画师)在这里与文本(书写员)唱起了反调。另外一个《鲁特兰诗篇》的例子,画师在边缘处画了一个弓箭手将一支箭射入一个倒地的人鱼之中,但奇怪的是,这支箭与上面文本中一个拉丁文词汇“conspectu”(意为看见或目光穿透)中的字母“p”延长的末端连接在一起——卡米尔认为,这一行径或许意味着画师欲与文本的抄写员相竞胜的意识,表示画师能够用画笔完成与后者同样的任务。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更令人震惊:完成于1323年的一部《弥撒书》中,画师画了一只猴子对着一位抄写员模样的僧侣露出了他的屁股;这个似乎毫无来由的情节或许表示画师对于抄写员身份的嘲弄,但更可能是画师对于抄写员文本中一段话有意的误读:因为上数七行的拉丁文“Liber est a culpa”(“这本书有过错”)中,“culpa”一词的后两个字母被抄写员转写到下一行,故如若按照当时的俗语(法语)理解,这句话就变成了“Liber est a cul”——“这本书是献给屁股的”!这种充满想象力同时也不失具体性的释读,恰可以成为卡米尔前文所述其艺术史方法论的一个范例,即对图像意蕴的解读,不能脱离与页面整体文化空间发生的关系而凭空发生。

《鲁特兰诗篇》边缘图像细节“中箭的人鱼和构成箭矢的字母P”犊皮纸彩绘 ,Add MS 62925号抄本第14r页 29.8×20.3cm 约1260年
卡米尔还把边缘图像概括为“一种有意识的僭越之举”,这一方面他无疑受到了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启迪;他在讨论鲁昂大教堂北袖廊著名的“书商之门”上姿态滑稽的奇异动物与怪物图像时,即沿用了巴赫金的方式,将其与中世纪“傻瓜节”“驴节”等礼仪节庆中,僧侣们受民间文化影响,头戴面具参加狂欢活动或进行戏剧表演联系起来。但与巴赫金更为鲜明的民间文化反对官方文化的阐释模式相比,卡米尔的模式始终保持着对于“文化空间”中结构关系的整体意识;在他看来,即使“狂欢节”本身也受到官方的批准和控制,所有“在节日期间上演的反转、异装、酗酒和游行仪式都出自一道仔细控制、用于开流的阀门”,也就是说,在“狂欢节”中同样存在着“与官方秩序之间的合谋”。
从这种意义上说,抄本边缘处的图像与狂欢节并无二致;那些在边缘处跳跃嬉戏的哥特式怪物,尽管它们的身体如此自由自在,但实际上仍然受到文本的束缚。“它们可以‘嘲弄’文本,却永远无法取代它。”这一“合谋”的意象或许还可以借助卡米尔书中的另一个形象来表达:法国索米尔(Saumur)一座教堂的唱诗班席有一系列雕花椅背凸板(Misericord),它们放下去是座板,抬起来会显露背后的雕塑;其中的一个形象呈现为一个仰面向上的人正将鼻子和嘴巴紧紧贴靠在背板上,而上面正是坐下的教士屁股所在之处——这一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上层的镇守与下层的贴附之间严丝合缝的统一。就此,在“狂欢节”的表象之下,卡米尔冷酷地道出了中世纪文化中令人窒息的一面。
(本文系《边缘图像:中世纪艺术的边际》的译序。经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