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纽约式怀旧,是对“失去”这一永久性存在的宿命般的接受
【编者按】
皮特·哈米尔是纽约最后一代传奇纸媒记者、专栏作家。《纽约下城》是一部饱含个人情感的追忆。在书中,哈米尔漫步曼哈顿——从格林威治村蜿蜒曲折的波希米亚街道,到肉类加工厂区破旧的小巷,再到南街海港饱经风霜的鹅卵石路——他将纽约的历史一层层展现在读者眼前,展现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纽约客为城市所写的挽歌,他经历了纽约发展过程中一些最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始终将这座宏伟而又往事纷繁的城市称为世界上自己最喜欢的都市。本文摘编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即便在今天,我仍会像年轻人那样行走于这座城市。总有什么事能给我带来惊喜,还有其他事会让我好奇。一栋曾经路过一千次的建筑,也会突然令我从一种全新角度去观察。天气好时,我喜欢站着观看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在门口漫无目的地游荡。
纽约人学会了满足于匆匆一瞥。这里的人太多,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所有秘密。在这样一个广大又多元的地方,没有人能吸收一切。你认识自己爱的人,认识一起工作的人,剩余都是匆匆一瞥。而在某些日子里是的,你想永远活下去。
尽管如此,从很多角度来看,这座城市的人还是会表达出一些共同的情绪。每一代人、每一个群体表达出来的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但某些特定情绪还是在几个世纪中不断重复出现。其中之一当然是贪婪,那种难以控制的、想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获得更多金钱的欲望,那种从股票经纪人到抢劫犯都有的欲望。另一种则是突然的怒气,这是太多人住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导致的结果。还有一种,是面对权力机关的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但所有纽约人心中最强烈的,无疑还是“怀旧”这种情绪。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座城市成了怀旧之都。这样的情绪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不断变化这一简单的事实所带来的持久失去感。在这座城市的五个行政区中,曼哈顿尤其拒绝保持原来的模样。曼哈顿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二十岁时似乎永恒不变的东西,大多在你三十岁时就变成了鬼魂。和其他地方每日上演的事情一样,父母会去世,朋友会渐行渐远,生意会破产,餐馆也会永久关门。可在这里,改变仍比绝大多数美国城市更为常见。最为巨大的改变的背后动力,是这片狭小的土地本身。稀缺性可以让人们对可能的巨大财富产生神圣的信念,这也正是房地产“信仰”总会周期性地执行“诫命”的原因——周围街区被清理,建筑物被拆除,新大厦拔地而起,留下的只有回忆。
这本书中满是时间、贪婪,以及所谓“进步”这种含糊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牺牲。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是在曼哈顿上高中时知道的第三大道高架线。有时我会坐这趟地铁兜风,而不是只把它作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交通工具。我喜欢车上咯哒咯哒的噪音,喜欢与1933年的电影《金刚》有关的景象,喜欢沿途光线照过横梁与钢架投下的粗犷阴影,也喜欢透过车窗看到的一排排廉租公寓和爱尔兰酒吧。我对第二大道高架线、第六大道高架线或第九大道高架线没有任何记忆,这些地铁线都已不存。可某种程度上,第三大道高架线似乎和自由女神像一样永恒,而且对我来说,这条线路提供的不只是空间,还能带着我在时间中飞驰。1955年,他们开始拆除这条线路。等1957年我从墨西哥回来时,第三大道高架线也没了。
消失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大量报纸。建筑物拔地而起,如果活得足够长,说不定你还能看到它们被拆掉,被更新、更大胆、更傲慢的结构取代。第三大道高架线消失后,当纽约市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些建筑开始出现在第三大道时,我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总是因为改变而哀叹惋惜没什么意义。这里是纽约,失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第三大道高架线消失的同时,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也消失了。第三大道高架线的消亡就像一个标志,象征着超过了预期寿命的东西到了终点。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棒球队的离开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损失。有些人久久难以释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可以在道奇队的问题上安抚自己说,好吧,至少我曾经拥有过,他们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至今,我的心里还有这样的怀旧情绪。每次看到杰基·罗宾逊奔向本垒的黑白新闻短片时,这种情绪就会涌上心头。可没完没了地谈论道奇队的离开,生活也会非常无趣。纽约会让你学着对几乎一切释怀。
怀旧。就像批评家、教育家内森·西尔弗在他出色的著作《失去纽约》中写到的,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完美描述那种情绪的词汇。
“英语中的这个词寡淡无味得令人绝望。”他在2000年修订1967年的初版时写道,“那似乎表达的是绝望与催泪之间的某种东西,有点儿伤感、遗憾的感觉。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认可,城市的历史能够激发出一种与现在的连贯感。但称这种感觉为‘怀旧’时所激发出的反应,与提及传家宝或刺绣时得到的反应差不多。”
纽约式怀旧,并不仅仅是怀念消失的建筑,也不是指它们仅留存于曾和它们共同生活的一代人的年轻岁月中。纽约式怀旧,是对“失去”这一永久性存在的宿命般的接受。没有什么会一直保持不变。星期二变成星期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会永远变成历史。“现在是”变成了“过去是”。不论失去了什么,你不会重新获得:不管是你深爱的兄长,棒球队、漂亮的酒吧,还是你带着那个日后成为婚姻伴侣的人跳舞的地方。不可逆转的改变在纽约发生的频率太高了,这种经历本身也会影响城市的个性。通过流露更真实的怀旧情绪,纽约用这种方式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再那么多愁善感。多愁善感的对象总是谎言,而怀旧的对象却是消失的真实。没有人会真的为谎言而感伤。
这种紧固的怀旧情绪能够更好地诠释纽约这座城市,它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行为准则,就像DNA一样。除了“改变总在持续”这个解释外,我们最深层次的情感中总是存在另一个共同主题。我相信这也源自创造了这座现代城市的另一个了不起的群体:移民。
每一段纽约历史都会突出强调移民的角色,因为没有移民就讲不出这座城市的故事。从19世纪初开始,这座城市吸收了数百万欧洲移民,很多人成批抵达:爱尔兰人是为了逃离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是为了躲避1848年之后的政治纷争;1880年到1920年间的意大利人、东欧犹太人和其他人组成的移民大潮则是为了摆脱赤贫和充满暴力杀戮的生活环境。我们听说过很多他们的故事,但又对他们知之甚少。很多人是文盲,没写过回忆录或书信,回忆录是他们的孩子才会尝试的东西。但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年轻,也很穷,因为上年纪的人和有钱人通常不会移居到陌生国家。我们知道,这些移民心怀一些共同的希望:他们想让孩子在一个健康、可受教育的地方长大,他们渴望在不问宗教信仰和出身的地方诚实劳动,他们希望在一个任何人无需向君主屈膝的国家获得属于个人的自由。
但很多人却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情感代价,而这种共通的破碎感为纽约带来了怀旧的第二波浪潮。在剩余的人生中,这些19世纪的第一代移民背负着自己的美籍孩子无法完全理解的包袱,也就是那些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是物品,也可能是人或情感,正是它们组成了移民口中的“故国”。那些他们孩童时代生活的地方,那些夏日清晨他们和朋友一起奔跑的地方,那些所有人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地方,那些拥有传统与确定性——包括最终变得无法容忍的残酷的确定性——的地方。在大航海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知道他们这一去将永远离开故国。在爱尔兰,如果又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准备动身前往美国,他们的家人通常会进行“赴美守灵”。他们恸哭,就像为死去的人那样哀悼。
很多德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启程前也会进行类似的仪式,他们穿过欧洲大陆抵达港口,乘船航行在凶险的大西洋上,最终抵达遥远的纽约港。父母们确信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对父母也有同样的感觉。与刚刚过去的历史之间产生的撕裂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迹,这些印迹也不会随着年轻的移民变老而消失。硬要说的话,怀旧情绪往往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苦痛通常会慢慢褪去,但失去的感觉不会消失。有人在纽约炎热的夏夜惊醒,恍惚间以为自己身在西西里岛、梅奥或者明斯克;有人以为自己的母亲正在隔壁房间的壁炉边准备着饭菜,那些老式的饭菜,那些属于故国的吃食。
很多怀旧之情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上百首各种语言的19世纪歌曲,都在描述亲爱的河流、金色的草地等消失的景色,或在讲述女孩或男孩离开时那记忆中的山坡。这些歌曲大多为工业化产物,带着专为迎合移民而作的愤世嫉俗的腔调,但它们却能激发出真挚的感情。依靠劳动,唱着这些歌的移民在纽约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小小一隅。大多数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健康地长高长大,看到他们接受了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也有些移民很少唱歌或回忆,他们沉沦在酒精、毒品或者犯罪之中。有人被纽约及冷酷的现实打垮,羞愧地回到故国。有人对失败的耻辱难以启齿,搬去了西部,走进那片空旷的土地,消失在了美国。
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不管是那些成功的还是没成功的,对他们来说,音乐永远在那里。人们在廉租公寓的厨房里、在舞厅里唱起这些移民歌曲,也在婚礼和葬礼上唱响。从移民潮的初期,他们就在这么做,失去的一切和记忆被编织进纽约的个性中。每一位移民都知道非洲人在奴隶制时代学到了什么:曾经有一个亲密无间的世界,现在消失了。那个世界已经成为历史,不可恢复。在最深层次的内心,你是像非洲人一样被剥夺了过去,还是自己决定抛弃过去,并不重要。在夜晚的某个瞬间,本已消失的过去会栩栩如生地出现。
那种双重意识——即无可挽回的过去埋藏在由现在的世界构成的浅浅坟墓中——被传递给了移民的子女,效力逐渐减弱,又传递给了更多的孙辈。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时间和与之相伴的怀旧之情。更广大世界中发生的事件,通常也能给人施加时间感。我认识的一些老纽约人,至今还把时间分成三个纪元:战争前、战争期间、战争后。他们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个被战争划分的阶段各有专属于自己的怀旧,有属于各自时代的音乐,也有特有的希望、痛苦或失去感。身在纽约大后方的人的战争经历,和身在加州、密西西比州或佛罗里达州的人显然不同。还有些纽约人把1957年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的离开看作个人时间意识的重大转折点。很多对话仍以“道奇队离开前 ……”为开头。其他人则用1963年约翰·F.肯尼迪被刺作为时间标记,而这个事件才是所谓20世纪60年代的真正开端。
可老移民们早已经历过巨大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撕裂,也就是故国和新国家之间的撕裂。这种让人悲痛的破裂并不只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种伤痛不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移民们在这样的伤痛中生活,使之成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经历也在他们参与建造的城市中刻下了永久的精神模板。远走他乡的孩子们现在可以回到故国的老家,带着自己的美籍孩子,参加节日庆祝和婚礼,或者哀悼他们逝去的父母。如果买得起机票,他们可以向孩子展示自己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他们还可以在故国炫耀自己的纽约街道、纽约学校、纽约公寓、纽约毕业典礼、纽约球赛和纽约野餐的照片,说,这就是他们的美国。可那种剧烈的撕裂感,将过去抛在身后的感觉,却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因此也留在了我们心里。他们的怀旧给人熟悉的感觉,生活在纽约廉价公寓中的每一个人在至暗时刻都曾感受过这样的怀旧。
如今,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纽约的有多米尼加人、俄罗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墨西哥人、中国人和韩国人,还有其他在殖民时代到访纽约时会被称为“所有位于天堂之下的国家”的人,甚至还有来自多哥的人。有些人搬进了下城,也就是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提供不完美成长环境的地方。有些人在布鲁克林安家,还有些住进了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经过改造而焕然一新的地方,乘坐地铁前往下城工作。他们总让我感到振奋;他们就是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中仍存在连贯性的证明。
若是运气好,新移民可以像很久以前的许多人那样去了解纽约。他们会发现,了解这个地方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从头开始。也就是说,步行前往下城。他们会走上街道,会看到废墟和纪念碑。他们会吸入过去的灰烬。他们会为生活在这个地方而庆祝,这里住满了表面上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会带着孩子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将奥兹国里洒满晨光的尖顶尽收眼底。
这样的体验不应仅限于城市的初来乍到者。悲哀的是,太多欧洲老移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孩子不了解这座让他们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城市。丹佛如此,纽约亦如此。大部分公立学校不会强调这些故事。电视文化则进一步深化了被动性,阻止人们主动去了解这些故事。但真正的学生,在单纯的好奇心驱动下,仍能找到自己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曾为后代努力拼搏的地方,那时的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后代。在纽约,任何年纪的学生都可以走进留存下来的老街,凝望几座廉价公寓,拜访下东城廉租公寓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在纽约,绝大多数老故事发生在下城。更新一些的故事也是如此。如今在下城,我们几乎从早到晚都能看到新移民。他们在旧建筑的改造工地上工作,在暴风雪中送着中餐、泰国菜或意大利菜外卖。他们在韩国料理熟食店准备着三明治,在餐馆里当厨师。他们送自己年幼的美籍孩子去美国学校读书。到了夏天的周六夜晚,当很多人打开窗户,让凉风吹进家时,在外漫步的人可以听到用不熟悉的语言唱出的熟悉曲调,那些讲述着失去与遗憾的伤心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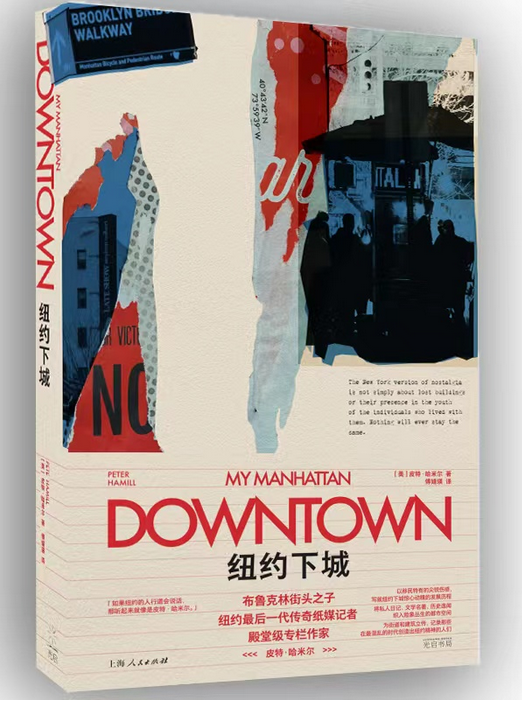
《纽约下城》,[美]皮特·哈米尔著,傅婧瑛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