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碗酸辣肚丝汤,我只要酸辣 |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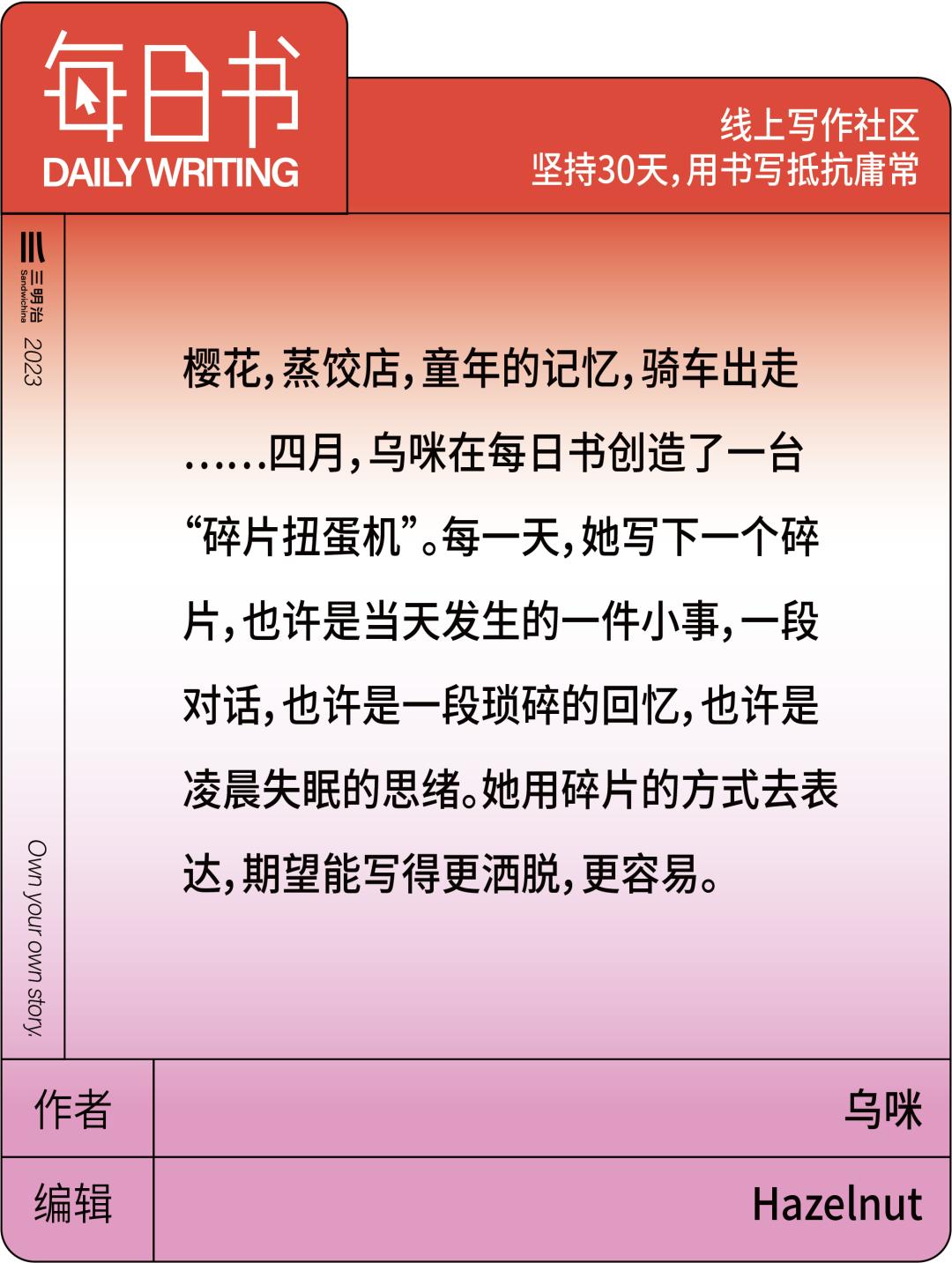
“击剑比赛的现场是这样一个地方,明亮、直线条,光滑、机械。白色灯光。灯光总是很充足的。金属灰白的剑道,选手的衣服是白色与金属质的银灰色相间。手上的细条剑闪着金属光。耳边会不时响起哨子般的金属质感的声音,介于刺耳与白噪声之间。也许,还是偏于刺耳多一些。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过,是什么设备发出的这种机械哨声。”
这是我在四月第一天记下的一个碎片。那天,我陪女儿赶场参加一场击剑比赛。接下来一个月的每一天,我尝试着碎片地、无厘头地写,不要从头到尾写。一个月结束回头看,这种碎片式的写作确实让我更自由了,也保证了出勤率。不过有些碎片还有点大,有些结实。
我期待以后能天马行空一点:不按顺序,不唠叨前因后果,只放大一个想法,一个瞬间,或者,一个感受。

击剑比赛现场,还有金属撞击声,细细的剑互相碰撞的声音,刺到对手胸前护板发出的声音,击剑鞋的鞋底在金属剑道上的摩擦声。也有很嘈杂的人声,因为场地内外都总有很多人。场地里的人不在赛道上时,也会轻声聊天。
场地外挤满了希望钻个空子能进场地看看而不得的家长。即便每个人只是小声交谈,加在一起也发出相当大的嗡嗡声了,而且时不时还会有人拔高声音喊着小孩的名字,提醒他别忘了东西,或者多喝一点水。
这样说来,击剑比赛的现场,和阳光、清新空气、自然的风这些会在潜意识里与“运动”这个词关联在一起的想像一点关系也没有。汗水是有的,只是不会在阳光下闪着光,而是在选手们摘下面罩的时候,从他们额前被沾湿成一绺绺的头发看出来。
眼泪也是有的。好在这还是小孩们的比赛,他们输掉比赛之后,通常只会干脆地痛哭一分钟。
大部分家长被拦在圈外,只有少数挂上领队工作证的家长能出入。我女儿比赛的剑道恰好刁钻地位于踮起脚才有可能看到某一边选手背影的位置。而在关键的淘汰赛时,她正好位于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见的角度,只能看到对手的教练起身支招,直到他们最后欢呼。
在看不到她的时候,眼睛、耳朵和所有感官,都在捕获着击剑馆特有的色彩、声音与气氛。很可惜,这一次她输了比赛,但她没有哭。

每天能看到花树,走路时踏在花瓣上,是何等的奢侈呢?我现在每天都在过着这样的日子。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没有几天了,几乎是数着秒地等它过去。而且,也很难清楚地知道这段时光是怎么结束的,好像就是一夜之间,春花忽然停息了,地上无穷无尽般的落花也一夜消失。时光滑向更深的绿。这些先后盛放又离开的花朵,留下的果实,出现在早市上。那是夏天的好时光了,那也是我从小就爱的季节,但那不是这一段奢侈的春天了。
猛烈的春光就这么短。古时诗词喜欢写伤春的主题,以前我会觉得重点在于“伤”,这样的忧虑与不舍;现在我在想,也许这也表示“看见了”,是说我看见了这样珍贵的春光,我也珍视过它,也写诗挽留过它了。
与前几天地上只是铺了一层细细的粉瓣不同,这两天地上的落花,开始以整朵为多了。这应该代表着,晚樱也终于到了开始落的时候,而不只是被风被雨提前催去一些花瓣而已。
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鞋底边缘沾了半朵粉色落花,没舍得拿下来,这也算是“踏花归来马蹄香”。


地上堆积的粉色,从单瓣更多,到整花更多

今天中午,我们去新房子附近的蒸饺店吃了蒸饺和酸辣肚丝汤。
非常神奇,这附近是个新区,路边像样的小饭馆很少,而我们有一次偶尔走进这家“渭南蒸饺店”,就觉得诡异地熟悉:他家的菜单,和我们家附近开了二十多年的那家渭南蒸饺店一模一样。蒸饺端上来,味道也没差太多。因为我们都不是会和别人搭话聊天的人,所以只是在心里默默猜测,难道渭南的蒸饺店风格都如此一致吗?还是说,这是我们所熟悉那家蒸饺店的分店?
今天走向店门口的时候,我满脑子都在想喝一碗酸辣汤。我见过的饭馆里,酸辣汤一般等于酸辣肚丝汤。而我并不想吃肚丝,我只想喝一碗酸辣汤。队友同意,“酸辣肚丝汤”里,我负责“酸辣”“汤”的部分,他来解决“肚丝”的部分。于是他又向老板追加一声:再来一个肚丝汤。
过了一会儿汤端上来,我看到一碗白白半透明的微稠清汤,漂着些香菜叶、粉丝、和粉丝一样细的干丝,几朵黑木耳,主角肚丝若干,唯独没有我心目中代表“酸酸辣辣”的色彩。完了,老板是不是只记住了“肚丝汤”,忘了酸辣的部分?队友先尝了一口,说,确实是酸辣的!
看着眼前的汤一丝金色、棕色、红色也无的,清淡无味的色泽,真的很难想像。直到我也尝了一口汤。真的,特别酸辣!就是我期待程度的那种酸辣!
我开始一口口喝汤,吃掉里面的粉丝、干丝、木耳,不去碰肚丝。勾过芡的汤热呼呼,酸度醒目,辣味是胡椒的辣,但存在感非常强。喝掉小半碗,就全身暖和,感觉“我又可以了”。

平时蒸饺上得都很快,但那天却迟迟未来,老板有点歉意地说,要等一下。
看到这家老板的脸,完全不需问,就知道他一定与自家附近老蒸饺店的老板是一家人,就算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他们家人都长着和气生财的好面相,圆脸,圆眼睛,脸上没有任何坚硬的角度,长相十分端正,就算略有发福,但看上去干净利落。店面是本地常见的小俗店的布置,也十分干净。
这两位长相如出一辙的店老板,待人风格也相似。你去了,他会看到你,简单地安排你坐下,拿出菜单等你点过蒸饺,再多问一句,喝什么汤?然后,蒸饺和汤或凉菜会迅速、不按顺序地上来。老板总在店里前后眼观六路,并不健谈,也不多与客人寒暄,但透着一股几十年老街坊的亲切感,于是他们的店,也是让人觉得比起是生意来,更像是邻居的店。
多等了不到十分钟,蒸饺出炉,一笼一笼放在我们面前。咬了一口,啊!怎么这么好吃?他家的蒸饺我们早已吃惯了,好自然是好的,今天却格外好,我们要的两种馅,无论是虾肉还是菌菇,都更好吃至少30%!
我猜,原来每次吃蒸饺时,迅速被端上桌的热蒸饺,大概未必是刚蒸出来的,而是续在火上保持热度,而这一次,实实在在是等着它们蒸好的,刚蒸好就端上桌,吃过才发现,热蒸饺与热蒸饺之间,也还有这样的差别。难怪这家好吃的蒸饺店在外卖软件上评分非常一般。我自己也试着点过,完全没有到店吃的感觉。本来就是十分家常的食物,如果少了那股新鲜的热气,就一切都不对头了。

天一冷,一下雨,我就会像蜗牛缩回自己的壳子里,从二月底横贯三月的散步传统几乎又要被颠覆了。
昨天,下了一整天雨,不是春天的雾雨,十分常规的,中至小雨。在我的狂野设想里,我应该单枪匹马出门去大兴善寺看紫藤。当然我没有去。但是,雨水打湿了樱花啊。所以,最后我还是要去看一看,哪怕只是去院子门口,取快递路上那道台阶上走下去,再走上来,看看头顶的樱花,还有脚下落的花瓣。
关山樱的花本来正在盛开,还没到落的时候。不过,这些盛开的花头本来就重,被雨淋透了就更沉重,再也支撑不住自己,花朵的部分全都沉到了树叶的下方。地上也堆起厚厚的花瓣,与晴天时花瓣的飘落感相比。雨天里我见到的花瓣总是不知何时已经落在那里的,然后再被雨水如透明的钉一样敲进浸湿的硬质地面,紧紧地贴住,再动弹不得。

今天也一样。一直到了下午5点钟。才决心把自己从电脑前拔出来。天已经不下雨了,但屋子里仍然很冷。我随便套上件厚衣服出门去。今天地面干爽了,地上仍满是花瓣,不知道是昨天的那些,还是今天新落的。
雨后原本该最繁盛的关山樱的头顶难免被打薄,露出更多的绿叶子来。但它们仍是此处的霸主,这个时段,凡是盛开的花树,几乎全是樱花,而在这一带,樱花树里十之八九,就是关山樱。但东苑里有一棵颜色更浅的樱花,粉白相间,花朵是杂色的,同一簇里,有的花朵更偏白,有的更偏粉。和小区里粉得十分微妙的松月樱不同,松月樱通体白,只有花瓣边缘有一丝粉,使整体色彩呈现非纯白,而能归入最清浅的粉色。而这一棵因为偏白的花与略略偏粉的花挤在一起,看起来更有一种白里透粉的好气色。

我记得以前这边樱花树还小,还比现在多的时候,有一棵小樱花树,上面挂了标牌,赫然写着“杨贵妃”。虽然这样的形容有点俗,但那圆润粉白的樱花,真是唐代大美人的面色。这一棵,是当年的“杨贵妃”吗?我不能确定,它身上已经没了标牌,而此处的花树,已经过了伤筋动骨的大调整。我宁愿相信它是,逃过了被移走的命运,而且长大了。
走过几棵樱花树回望,发现天上有一朵又大又软的白云。看来今天不会再下雨了,很可能明天也不会。这一波阴雨已经过去。果然还是要强迫自己走出门,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让眼睛呼吸一下新鲜的春光。


昨天在新房子里看着师傅装门,同时工长也在装插座开关时,和设计师讨论完关于装修的一些细节,就开始聊会儿天。不知怎么开始聊起他的老家。他老家在陕南,但离西安不远,翻过秦岭就是。他说,山里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某次回家下雨天车轮陷进泥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年轻人来帮忙。
说着说着,说到他小时候在老家,下午放学好早,因为老师们也要早点回家干农活。收麦的时候要放十几天假,让老师们回家收麦子。小孩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家里干活的人送送水,其他时候就全部聚在一起疯玩,上树下河无所不玩。而且也按节令玩,什么时候逮蚂蚱,什么时候上树摘柿子摘核桃,夏天夜里跑去捉青蛙。
再大一点点,就去帮家里放牛,但放牛其实也是玩。傍晚时骑着牛回家,就真像古诗里写的,手里拿着——我正想说,牧笛?他接着说,拿一根长棍,一打一大片……
……这是谁家的古诗啊!
不过笛子也有的,大点的孩子拿着笛子,村里的小孩都相约着一起放牛,走到谁家门口时,懒得喊名字,就吹几声笛子,代表“我来了,你快点”。去放牛的小孩们还会分配好谁带火柴,谁带红薯,到了山上就聚众烤红薯吃。
他小学四年级跟着父母搬到西安,骤然发现,城里小孩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与在乡下时大不一样。他一去,就成了班里跑得最快的人,操场上的单杠双杠在他眼里非常幼稚。他发现城里的小学里,小孩们分帮结派,也可能会孤立一些人。但在老家,这是不会发生的,村里所有的小孩都在一块玩,大点的孩子会看顾小的,维持秩序,内向的小孩可能少说点话,但也会跟着大部队跑来跑去。
特别是现在,一个城里的小孩要出去玩得有多麻烦呢,先出家门,进电梯、出电梯,出单元门,这才只到了院子里。如果想出院子,就更麻烦,要报备,很可能根本不被批准出去。而他小时候,因为家里位置正在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家里爷爷奶奶又喜欢小孩,所以成了小孩们集中的大本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脚迈出门就有得玩。
这么痛快的童年,真是好生让人羡慕。别说现在的城里小孩很少有机会真正痛快地玩。我比他大十几岁,尚且从来没那样痛快地玩过。
美中不足地是他说,女孩们就没这么自由,因为要更多帮家里干活,大点的女孩还得做饭。不过她们也会聚在一起跳皮筋、扔沙包,摘花、聊天、编手绳。我说,每个小孩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童年,女孩们能一样玩得痛快,才是完美的。

离家出走,只要光脚套进跑步鞋,背上带公交卡的包,再把手机塞进包里。去上个厕所,拿起装着茶水的小水瓶。就可以走了。
不说一句话,只要摔上门。
在屋子里冻得手脚冰凉,出门却没有穿外套。好在阳光特别明亮,不穿外套也没有一丝寒冷。刷一辆共享单车,离家出走的冲动要驱使我骑更远的距离,而不是圆润地来一个小环线。我向前骑,然后转弯,在通向公园的路上,没有走下坡的那条小路,骑上高的路。一路爬升的坡度,从奋力蹬车,到实在蹬不动停下休息,再到准备一鼓作气蹬完这条大上坡路后,没鼓起来,于是再而三,三而竭,最后只有推着自行车到达坡顶。
坡顶通向垂直方向的一条大路。我右转骑了一阵之后,穿过十字路口,骑上开放式公园边上的,两边种满关山樱的道路。一直向前骑,向前骑,直到我看到另一个市政自行车的停靠点。原本是想要继续骑行的,因为头顶的关山樱还是很美。但是又想要还了自行车,因为看到了细细的小路通向绿色的公园深处。在樱花步道上骑车徘徊了一个来回,还了车,走着小路下坡,进入公园。
我在公园漫无目的的走——也许不能叫漫无目的,我知道大方向是往来时路走的。
经过一些同样半开半落的关山樱,路过上面长满小孩的大型运动器械,以及他们的父母都长在旁边的长椅上。阳光太好了,刚才的樱花人行道上,有好多在跑步的人,还有骑行的人。公园的每一张长椅上,也都已经有人坐在上面。这几天一直在飘的柳絮,飞一会儿就挂在了草上,草地变成了绿底泛白的颜色。
后来,我又沿着一条细细的上坡小路走出了公园,到了马路边上。路边也有空着的长椅,也有开着鲜花的花圃。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再起身往回走时,到了书店门口。我不想停留,却走了进去。书店一楼的一大块区域摆着文创产品,书反而没那么多。好在有不少空着的座椅。我坐了几分钟,草草翻了几本书。
最后还是走出了书店。不想再扫一辆自行车,虽然刚才费力上坡时,想着回去路上就能报复性下坡了。也不想一直走回去,于是跳上了一辆刚才过来的公交车。坐一站路,就离家很近了。我的出走,一点也不远。最后走回家的路上,我想,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这么快离家出走回来了?我就回答:因为没有穿外套。
如果地球要在5分钟后毁灭,而你正好认识一个外星人,要一起浪迹银河系,据那个外星人说,关键是你得有一条毛巾。只有带着毛巾的银河系搭车客,才是体面人。对我来说,要离家出走,必要穿一件外套。没有穿外套的人,只能在两小时后,太阳落山前回家。
当然,可能像我这样想的人,永远也没办法离家出走。离家出走要准备些什么?我上小学和中学时都花过很多时间想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准备什么,准备多少都不够。也许不是对于一个经济不独立的未成年,而是对于一个会纠结离家出走时要带什么的人,永远都准备不好,永远都走不出去。
小时候看过不止一部美国电影里,有人提到,童年时父亲说出去买包烟,然后就消失了,就此再也没有回家。这件事,在我当时来看,真的不可思议。一个决定离家出走的人,不做准备吗?不写计划吗?不带许多东西吗?甚至……不穿外套吗?
一个说出去买包烟的人,可能就是那么随随便便,兜里只揣着几块钱,头发没梳,外套没穿,就那样走出门,应该5分钟回来,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真正能够离家出走的人,是不会在乎自己要带什么的。

*本故事选自三明治“每日书”
· · · · ·
原标题:《一碗酸辣肚丝汤,我只要酸辣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