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国信 温春来︱南中国的画卷:私盐市场和国家认同
7月16日,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的学术沙龙,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国信、温春来一起与读者谈谈他们的新书——《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两部新著同属北师大出版社“历史人类学小丛书”,丛书策划编辑宋旭景、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王蕾共同主持此次沙龙。本文系沙龙座谈部分的文字整理。

宋旭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温老师和黄老师在书稿编辑过程中跟我交流的一些故事和这套书的缘起。
温老师是这样,基本上我每一次收到他的邮件、微信的时候,他都会问说,旭景,我可不可以再修改一下?我可不可以再修改一下哪个地方,我又发现了一个错误,我又看出了什么问题……大概在二校结束的时候,温老师还做了一些修改。对这套书,别人是很认真,温老师对这本书可能要在“认真”前面要加很多的修饰词。黄老师是用“您”来称呼我。北京人特别喜欢在交流当中用“您”,无论年轻人或者年老的,不太熟的都会称“您”。每次看到黄老师微信都是“旭景,您好”,作为年轻人,我特别受宠若惊,每次都诚惶诚恐的。
其实,“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的出版缘起于2015年12月我们在香港参加科大卫老师AOE计划的会议,当时黄老师和温老师可能比较忙没有去,这套书是和刘志伟、陈春声、科大卫,还有赵世瑜这几位老师一起聊天,大家谈到历史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可以有一种经典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就有了这套书。
今天这个沙龙的主题叫“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这个“我们”,既代表书里的“我们”,也代表黄老师和温老师他们自己研究的故事。
主持人:两位老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切入点,来做这样的一期沙龙?
温春来:我就从历史学的根本讲起。如果我问历史学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肯定是历史学就是研究过去的人类社会。这个回答不能说错,但也不能说准确。为什么?研究人类的过去,可以是历史学,可以是经济学,可以是人类学,也可以是其他学科。我们知道,有的经济学家研究人类的过去,还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研究对象本身并不能清晰界定学科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从研究的方法与取向入手去考察。历史学研究人类过去的时候,用的方法、取向与其他的学科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学研究人类过去的时候,主要研究的是一种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什么叫“抽象的人”?比如说,经济学里面有一种“经济人”的假定。“经济人”的假定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的还是少的,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懂得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人,这是一种经济的“人”,这是抽象的“人”。历史学当然不是讲这种抽象的“人”,我们是研究具体的人。每当我看到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的时候,我就想到高中物理学。在座的各位都学过,我们高中一开始就学牛顿的力学,学牛顿力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们要画牛顿力学的图,一画就发现不论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星也好、人也好、我们做实验用的小车也好,都画成一个点,而且这个点没有大小之分。我们不会去管它们的大小、不会去管它们的形状、不会去管它们的颜色,不会去管它们各自复杂的化学性质,我们只考虑一点,它们都是有质量的点,其它都被我们抽象掉了,被我们忽略掉了,我们只抓住我们认为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它都是有质量的。就像我们讲经济人一样,只抓住一点,所有人都是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
因此,当我看到抽象的“人”的时候,我就想到的牛顿力学。这种概括与抽象对不对?你不能说它错,如果说它错,我们就没办法解释物理学、经济学的辉煌。但是,研究人与研究自然界是有根本差别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对自然界做高度的概括与抽象,它们不会有意见。你不能说我把太阳、星星、月亮都看成一个有质量的点,太阳、星星、月亮就不按牛顿的力学来运动了,不会是这样的。人就不同,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想呈现出自己的个性,不愿意泯然于众人,比如说,放眼望去,今天来参加沙龙的各位我没有看见两个人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穿的衣服、鞋子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一点不大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有愿意与别人混同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个性。
因此,人类社会可以抽象,这就形成社会科学,其中的典范就是经济学。但因为人是有意识的,所以,我们对人、对人类社会高度抽象时,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还需要一种学科,这种学科关注人,而且是关注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社会,关注人作为活生生的人的那一面。它关注具体的人的行动,关注他的思想、价值、尊严与自由。它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拒绝概括与抽象,但是这不是它主要的追求。它主要的追求就是展现人以及人构成的具体社会,展现具体的人以及具体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样的学科就是人文学科。我认为,历史学就是人文学科的典范。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差不多是抽象程度最低的,但很符合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比如说我们讲皇帝,如果你通过概括与抽象,总结出几条规律来,说皇帝就是按这种规律行事的,你们就不要管具体的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了。这样的研究我想我们不满足,我们还想知道而且更加想知道的就是乾隆皇帝、嘉庆皇帝、汉武帝、秦始皇,他们怎样谈恋爱、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怎么搞政治斗争,我们想看到他们伟大光明的那一面,也想看到他们卑鄙下流无聊的那一面,我们就是想看人的复杂性怎样在他们身上呈现。
因此,基于历史学作为典范人文学科的特点,叙述、叙事是历史学永远不会过时的看家本领。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者反而不怎么懂叙事了。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讲两点,首先,因为现在的历史学有一整套复杂的规范,而且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很重视分析,对分析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叙事。在这一系列的规范与分析影响之下,我们史学论著就容易像八股文,枯燥、乏味,也不好懂。
其次,我们容易有本质主义的倾向。我们动不动就会说中国人怎么样,广东人怎么样,岭南文化怎么样,绅士怎么样,这些都是把中国、广东、岭南文化、绅士等等,做了本质主义的抽象。这种抽象不是说不对,而是我们忽略了复杂性的那一面。我们会发现中国人也好,广东人也好,岭南文化也好,宗族也好,绅士也好,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里会呈现出种种复杂性与多样性。我们历史学要注意他们抽象性的那一面,但更要注意他们复杂性的那一面。如果我们把他们简单化、本质化了,那我们的叙事也会因此变得很简单,从而把历史也变得很简单。
当然,到了今天,跟社会科学发生了深入碰撞、对话与交流的历史学,它跟传统的叙事的历史学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差别。现在的历史学,它不只是叙事,也重视分析,它不只是展现过程,而且要在过程里面呈现结构。我们除了叙事,把故事讲好之外,我们还必须在故事里面呈现出一种“理”。而这种“理”不只是对我们研究者个人是有效的,它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的共鸣,哪怕他不研究我的这个事情,不研究我的这段历史,但也能从我讲的这些“理”中产生一种共鸣,不只是对其他历史学工作者,我们讲的“理”,还要能够让其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产生共鸣。
比如像黄老师写的这本书,是历史学家写的,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老师,对黄老师的这本书颇为认可,这说明什么?说明黄老师讲的这个历史故事,他讲的这个理,已经引起有的经济学者的重视了。而我自己过去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改的,就是《从异域到旧疆》,另外一本就是我新出的这本《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这两本书我不能说它写得好,其实很多地方还非常不好,但我感到有一点安慰的是,它们让不研究这个地方的学者、不研究这些人的学者也产生了一点共鸣。有一个学政治学的朋友就对我说,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国家建设。
讲完这些,可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了。我们今天这个沙龙的主题是讲“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那就是尽管我跟黄老师的两本书,看起来差别很大,但是我们都是注重去讲具体的人,注重叙事。我们想强调:具体的人是历史的主体,讲故事是历史学永不过时的手段。
宋旭景:两部新书的主题“私盐市场形成”和“国家认同,看起来有一点不太相关,但其实这两本书的落脚点都是在大制度下的人和人背后的国家。黄老师说他的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而且涉及了经济学,请黄老师好好给大家讲讲这个特别重要的人,以及如何结合经济学的理论来写的这本书。

黄国信: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两个人的主题不相同。但是为什么最后在沙龙的时候弄了同一个主题出来,两个人的主题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的道理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都是人,人跟人有很大差异,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旭景告诉我们说,其实她所看到的这两个作者很不一样。我喜欢说“旭景,您好”。那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我是受中国传统国家的礼仪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这说明,像我这样的人,受到国家的强烈影响。实际上,不仅我,我想,在座的各位,以及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体系下的人,都不可能不受到国家的影响。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汉语里面,“国家”这个词其实是非常含糊的,跟英文之间里面的“国家”,意思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人与国家的时候,其实要想一下,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国家”是哪个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们知道关于“国家”,政治学甚至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有很多的研究。“国家”是什么,我们常常第一反应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国家是一个暴力工具,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但是当我们读到卢梭的时候会发现,“国家”是一个社会契约。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就跟我们说,其实国家它可以是一个暴力工具,也可以是一个契约,我们可以把国家的这两种分析看成两极,一极是暴力工具,一端是契约。但现实中,国家不一定这么极端,它可以在两极的中间而存在,它可既是契约又是暴力工具,两种成分兼具。这是在讨论国家的性质。
当我们讨论国家性质问题的时候,跟我们个人的历史,也许关系不那么大。但当我们回到英文世界里,当我们讲汉文“国家”,它的含义其实非常广泛的。因此,对我们的研究影响很大。比如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国家,没有人怀疑。但是如果我们讲清朝是一个国家,在英文世界就有点怀疑了。它可能觉得你这个应该用“帝国”而不是用“nation”。这个“国家”在西方英文世界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英文世界里面“国家”这个词是很复杂的,它大概至少包括四个含义,前段时间,有个社会学家有很好的总结:
第一个,国家是指版图和范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所控制的版图,我们都可以看作一个国家。这是英文country的概念。第二个,是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形成之后有民族认同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类型的国家。是英文里的nation或者nation state的概念,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当我们在讲国家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另外一层意义,我们常常会讲,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国家怎么样、怎么样。比如我们讲一个乡村,乡村老百姓在建房的时候,国家怎么样,这个时候讲的国家,你发现他讲的不是nation,也不是country,而是一个goverment,就是一个政府机构的问题。
但是温老师讲的“国家”,他讨论的是西南的国家认同的时候,那个是在nation的意义上在讲。
除了上面三个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在西方是state。这个state其实在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就是国家机器,比政府范围更大的概念是国家机器。
当我们两个人来讲我们两本书,一个讲私盐,一个讲西南的认同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但是我们用汉语来表达都叫“国家”。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讲的“国家”,很多时候大家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这是很含糊的概念,我们要很清楚。你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你写这个书的时候“国家”是什么,你自己要清楚。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我们两个人可以放在一起讲,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讲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在中国是无法脱离国家来讨论的。我们所写的历史背后都有一个“国家”,在我的那本书里面所讲的“国家”主要是政府,是私盐贸易问题中的“国家”,就是政府。温老师主要讲的是那个认同这个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意义上的“国家”。所以我们所谓的“国家”大概是这样一个意义。
温春来:黄老师讲的“国家”很清楚了,他讲的“国家”是政府,我讲的“国家”是现在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主要是这个意思。我讨论的就是我们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型到现代民族国家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讲的是在中国建一个nation state的时候,我们少数民族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两个讲的“国家”真的不同。我讲的不是政府意义上的“国家”。
黄国信:我先讲讲我的故事。《市场的形成》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 “从清代私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其实我讲的是私盐市场。
为什么讲私盐市场?这个事情跟我当年写过的硕士论文有一点关系,我的研究涉及到湖南的衡州府,就是今天的衡阳一带。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盐的贸易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清朝的时候,盐是国家专卖的物资,国家有专卖制度,制度里面有一个规定,盐的贸易是分地区进行的。理论上讲,盐区的边界是固定的,不太容易改变。今天衡阳这个地方,也就是清代的衡州府,清朝属于粤盐区,就是销售我们广东沿海生产的盐的。然后到康熙年间,这个地方的一些读书人非常痛苦,发现自己活不下去了。因为什么活不下去?因为盐的问题活不下去,他们整天被地方长官拉去缴盐税。这些人问,为什么要缴盐税?地方官答复就是要缴。为什么?因为政府要收盐税。政府收盐税本来按规矩是向盐商收的,盐税在清代,主要是通过寓价于税来实现的,盐商可以把盐价提高卖给老百姓,老百姓缴的税就直接由他缴了。但是当时衡州府的地方官发现,当时盐的贸易非常不好,盐商纳税不足,所以他们把盐税摊到各家各户,就挨家挨户去收。这引起了士大夫也就是上面说的那批读书人的不满,他们想为所有的老百姓以及他们自己争取切身利益反对地方官的方案。他们自己设计了一个新方案,就是把衡州府从粤盐区改划到淮盐区去,也就是改卖淮盐。因为湖南本来在清代是卖两淮地区的盐,就是今天的江苏盐城跟南通那一带产的盐。这个事情经过读书人告御状告到北京去,过完春节没多少天,正月初几就跑到北京告御状,就是叩阍。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
闹得很大之后,终于清朝把衡州府这个地方划到两淮盐区去,不卖粤盐了。这个事情看起来就很简单得处理完了,没事了。可是,后来的故事就更精彩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衡阳的地方长官发现,他们的老百姓吃的盐其实全部是广东卖过去的走私盐,因为康熙初年这里已经划为两淮盐区,再卖粤盐就属于走私了,结果当地百姓吃的全部是走私的粤盐。很奇怪,为什么地方的文人当年拼死拼命甚至不怕砍头的危险当年告御状要变成两淮盐区,但是最后当地老百姓全部买走私的粤盐。这里一定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想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就在这个过程中,终于发现了我们中山大学图书馆,就是王蕾主任负责的古籍部有一部线装书书叫做《潘氏家乘》,讲了一个嘉庆年间,在广东北部卖粤盐的商人的故事。这个商人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这套书就是他的日记和书信,就收藏在我们的中大图书馆。读他的书信,我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广东南海西樵镇一个村子里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商人。他小时候读书,其实读得还不错,但是考科举考不上。那考不上怎么办?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考科举考不上的,传统基本上是做讼师,代人写讼词,赚点钱。后来他就写讼状。诉状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人命关天,有时候要比较昧着良心说话,他不想这样。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怎么办?他后来就去做生意。做生意总不会侵害那么多人利益。
怎么做生意?他发现,当时在广东沿海地区做生意,有一个机会就是做盐的生意。做盐的生意有准入许可。他在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获得了许可,政府给了一个盐埠给他,叫沙湾埠,让你在这个埠的范围内卖盐,但其实这里盐很难卖,因为在沿海地区,老百姓自己随便弄点海水就可以熬出盐,不需要你盐商卖的盐。但是这样的地方也有一个好处,盐商的准入许可,也就是投资盐埠的价钱会比较低。所以他去隔壁的番禺一个叫沙湾的盐埠申请做盐商,交的钱不多,拿到了盐商的许可证。他明白,做盐的贸易不能在沙湾做,沙湾这个地方靠海太近,很难销盐。于是,他拿到盐商许可证之后去粤北做盐的贸易。实际上,在广东做盐的贸易就要去粤北,粤北这个地方跟湖南交界,跟两淮盐区交界,在那个地方才可以真正把生意做大。于是,他就加入到了一个叫“孔文光”的商号,“孔文光”其实是一个人名,但当时已经变成一个商号,在“孔文光”的商号里面在粤北卖盐。生意越做越大。
然后我就想到,嘉庆年间,当地的地方志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衡州府,虽然名义上是淮盐区,但老百姓吃的实际就是广东盐,而潘进在这里卖的就是广东盐,那他与这个记载有什么关系呢?把《潘氏家乘》,从头到尾一行一行看下去,发现故事很精彩。
精彩到什么程度?最后发现他在跟他的亲朋好友的书信里面详细谈到他如何把把广东盐卖到衡阳去。为什么写信会讲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他遇一个朋友,他哥哥年少时的同学,这个时候刚好从清朝朝廷外放到湖南,做湖南粮储道。然后他就跟这位朋友说,“你现在在湖南做粮储道了,应该再帮帮我的忙。五、六年前,你曾经帮我们跟湖南的衡州、永州、郴州的道台,就是衡永郴道彭应燕打过招呼,让他尽量少干预我们在这个地方卖盐,效果很好。现在你到了湖南来了,能不能引荐我直接跟他们见面什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他哥哥的同学就跟他说,“我早就想让你来了,我们以前不是约定过吗?我知道你很聪明,很有行政才能,早就想请你出山做我的幕僚。现在机会来了,我外放做粮储道了,你来帮我做幕僚吧。”潘进先生就说,“行,明年来,今年我来不了,因为我的合伙商人对我很好,现在盐的很多事情我要处理,处理完了我就过去。你先帮我跟彭道台打打招呼。”然后第二年他就到那边做幕僚去了。他的盐也就大量的卖到两淮盐区的衡州府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这个叫做潘进的盐商利用了他哥哥的同学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官与商的关系,就实现了盐的贸易。但是背后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背后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个问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湖南的地方官会愿意广东的商人把粤盐卖到我这里来?大家知道,从唐朝以来,每一个朝代的地方官都是一个考成责任的,哪个地方没有做好会受处分,会罚俸的,其中就有销盐的考成,地方官辖区盐卖的不好,就会受到处分的。所以,问题是,湖南的地方官为什么冒着考察受处分的情况来帮你,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制度性问题。
这个制度性的问题有两个人告诉过我,一个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久宜先生,还有一个是我们这里的博士生。两个研究都告诉我清代盐的所谓专卖制度,是国家制度,本来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但是,实际上,盐的专卖制度在国家层面只是一个原则,每一个地方,有具体的贸易制度,这个具体的制度是地方官跟朝廷、户部、皇帝不断地协商,不断地谈判,不断地博弈所形成的。那形成的结果是什么?广东在那段时间所实现的盐的贸易制度是每一个县独立成为一个盐埠,每一个县都有独立的销售任务和考成责任。但是湖南、湖北、江西这三个省属于两淮盐区,两淮盐区当时的规定是,销售盐的责任不到县,责任只到哪里?责任只到省的层级。州县没有具体的考成责任。所以湖南的地方官,完全可以帮广东盐商的忙。双方关系好,就可以放你的盐进来,想控制你,我就听总督的命令把你的盐路卡死,是完全可以这样的。
这个制度差异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地方官跟朝廷讨价还价所形成的。我们发现即使像盐这种财政上最重要的制度,很多时候都不是全国一刀切的,很多时候很灵活的,是地方跟中央不断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湖南的地方官才可以这样做事情。盐的贸易,清朝已经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系统。交通道路,价格体制,都已经建立起来,都有一套逻辑。广东盐商就是利用这套逻辑,把自己的盐卖到湖南的两淮盐区去,而湖南的地方官,这个时候只要跟你的关系好,就可以帮你的忙。就不巡查食盐分区贸易的边界线,我不巡查盐的边界线,我就可以让你广东盐进来。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潘进之所以可以把大量的盐卖到衡州府去,是因为当年湖南的地方官配合了他,帮了他们的忙。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故事到这里为止,一般来讲我们读历史的人的感觉就可以下结论了。什么结论?官商勾结。但是实际上只是分析到官商勾结,我觉得我们的分析真的有点浪费材料。为什么?因为官商勾结的结论,谁都能讲得出来,就是普通的高中生都可以总结出来。它里面有很多跟学术上的话题有关系的东西,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在我的研究中,首先在盐的贸易本身这个故事是有意义的,第二个是市场的问题上它是有意义的。
我简单先讲讲这个故事在盐的贸易本身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做盐的贸易,特别做私盐研究,国内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做。大家受到包世臣的影响,他给我们把私盐分成大概十来种。最重要的就是商私和官私。所谓官私就是官员去上任的时候,坐的船,直接夹带私盐。商私又是指什么?就是商人走私盐,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政府给的卖盐凭证,本来只能一次性使用的,用了多次。这就是所谓最重要的两种私盐。
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私盐的贸易最重要的所谓商私跟官私,还有一种就是潘进这种类型,他们得到了两个盐区的地方官的大量支持。首先,两广的地方官,包括两广总督都大力支持。有好几个两广总督,包括蒋攸铦、阮元、邓廷桢等人,都是坚定地站在两广盐商的背后,努力把盐卖到湖南南部去的。另一方面,潘进他们还得到了湖南地方官的支持。所以规模很大。包世臣所谓的官私和商私所囊括的只是这个商私、官私里面份额非常小的一部分,最大量官私与商私,反而是这种官商合作亲密无间的,利用各种制度的这个可能性,然后把私盐卖到另外的盐区去的情况。所以在私盐本身来讲,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那么简单,是真正解释我们清朝的时候为什么私盐量一直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案例。
再接下来讲,它对我们解释私盐市场的形成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一般来讲,我们讲私盐的贸易,以主讲市场形成,还是在经济理性层面上讲的。就是温老师一开始讲的,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理论上,我们要把物品投放到市场中去,不能不看市场价格。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实际上到嘉庆道光年间,广东盐在湖南的衡州府这一带,确实会比两淮的盐价廉物美,这是事实。但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讲康熙年间的故事,那个时候两淮的盐反而受欢迎,这说明,两淮的盐在康熙年间在这里有绝对的价格优势。当时三藩之乱,由于广东盐要运去湖南,就必须绕道广西,经灵渠过去,路途比较远,价钱就高了。价钱确实比嘉庆、道光年间高很多,价格高了,跟两淮比没有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则是广东的盐的销售任务,分到了县,当时,衡州府属于两广盐区,那些地方官要完成盐的销售责任,要完成考成。但当时,衡州府的地方官发现基本没有办法完成本县的考成责任,因为粤盐价钱不便宜,相邻盐区的淮盐反而可能便宜一些,当地人不愿意买粤盐。那么,地方官在销售食盐的考成中,肯定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老百姓说这不关我的事,或者是不大关我的事。但是地方官要把盐税交上去,完成盐税的任务,完成考成。所以他就干脆把盐税摊到各家各户。因此,当地的士绅不干,那些士绅觉得对他们是严重不公平。所以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们把衡州府变成两淮盐区,卖两淮盐,反而没有这样分到一个具体县的考成责任。如果这样,他们觉得地方官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负担,地方官也就不会压榨读书人以及每家每户的老百姓要求纳盐税,让盐商来承担盐税就可以了。所以康熙年间,当地士绅支持把本地划归两淮盐区,其实也是有经济理性在的。而发展到嘉庆、道光年间,两广食盐在衡州府,相对淮盐已经明显有价格优势了,这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事情的落实过程,在经济学里面就被抽象化了,它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经济理性推动的,但具体如何推动,它不告诉我们。用“理性经济人”五个字,就把事情搞定了,就解释了为什么嘉庆、道光年间衡州府会大量销卖粤盐的事情。但是到历史学这边,我们觉得如果解释这个程序,那历史学就不是历史学了,我们历史学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于是,我们注意到人,注意到国家,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真正能实现把广东的具有经济学所谓比较优势的盐卖到湖南去,背后是有一群人在组织,在运作。这一群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怎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故事,我可以利用我的同学在湖南做官,跟湖南打好交道,你们就卖过来吧,我不管你了。然后我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两广的总督衙门和下面的所有盐运司这些机构,他们可以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帮助帮我去跟湖广总督以及户部打交道,以及皇帝打交道,让我们卖盐的办法一直可以维持下来。
但是,淮盐是煎出来的盐,经过铁盘的熬制,所以盐的颜色是灰色的,广东盐是晒的,晒出来是白色的。所以这个白盐卖过去,私盐的色彩太明显。这些广东盐商发明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这个盐,沿着北江往北运,有时被水淹到,我们的盐包湿了,这个盐很难看,不好卖。为了解决这种遇水的盐不好卖的问题,我们在粤北的淮界边界地区,就是广东盐跟湖南的淮盐区的交界地区,我们要设一些熬锅,把盐重新熬一下,然后老百姓才会买我们的盐,不然老百姓就不买。所以他们就设了好多熬锅,专门把两广生产出来晒出来的白色的盐,再重新熬一下变成灰色的跟淮盐一样的盐卖过去。这个事情弄得湖广总督跟户部很恼火,整天来找两广总督的麻烦,说你们这个广东的商人简直无孔不入,坏透了。不仅要把盐卖过来,而且干脆把白色的盐变成灰色的盐,就是跟我们的盐一模一样的再卖过来,于是双方就吵架。吵得非常多。总而言之,广东这边的两广总督有无数的办法,你怎么讲我都是有道理,就是让这个办法能维持下去,而且他们真的一直在跟户部以及皇帝的沟通中,维持了下来。所以广东的盐就可以变成灰盐,就跟淮盐一样,一直卖到湖南去。
在这里你就发现,这个背后其实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湖南的地方官的支持,没有这种在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广东盐商卖盐到衡州府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制度真的是铁板一块,制度没有灵活性,我们的食盐专卖制度没有灵活性,广东的制度跟两淮的制度无差异的话,这个事情也很难做。那样,那个盐区边界的巡逻可能很严格。所以你会发现这背后有国家的制度的问题,有人际网络关系的问题,这样你就终于明白,我们这些人所研究的对象,之所以把广东盐卖到衡州府去,让衡州府的地方官困惑地说,我们这里祖辈在康熙年间,拼老命地要卖淮盐,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地面上卖的全是粤盐呢?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故事说明,这背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在起作用。这个特征,我称之为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这是一个体系,即制度条文并不落实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正式运作过程中,制度跟条文是很不一样的。正是这一体系,才使得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的事情,能够变成一个事实上存在了或者存在过的市场交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所谓私盐市场的形成,是需要表面的制度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需要制度的非正式运作,需要地方官、户部、甚至皇帝,游走在制度的边缘来实现。我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而这个故事还让我们发现,我们历史学处理的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但同时也要处理空间问题。我们常常要解释的是,今天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在时间序列里形成的。但是大家知道,历史学也会用人类学的研究来讨论时间序列,我们常常把今天人类学对非洲和大洋洲的研究,看成是我们人类历史经历的原始社会的样子,我们说原始社会是什么什么样的,很多时候用的都是人类学的材料或者受人类学材料的启发的。这就是直接把今天的空间转化为历史的时间了。
如果我们用相同的办法,把我刚刚讲的故事理一遍,我们发现,虽然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故事,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空间逻辑的话,你就可以把潘进的故事看成是起点,把后来的两广总督跟孔文光一大堆商人的故事看成是潘进故事的发展,将它变成空间逻辑了。你就大概发现了私盐市场的形成及其扩大的空间过程。
我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把时间的层面变成一个空间的逻辑,变成一个扩大的关系。这样,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大概解释私盐市场形成的逻辑,进而我们可以联系到前人的大量研究,比如晋商的研究,晋商跟清政府包括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徽商跟康熙皇帝、跟乾隆皇帝的关系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发现,这样的市场其实是整个明清时期市场的一个基本秩序,大概就是这样的。从潘进的故事可以延伸到整个明清市场的逻辑。
温春来:我觉得黄老师讲得很好,我也来讲讲我的故事。我们现在的历史学要叙事,首先就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所以我先讲讲我的问题意识。
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我从来不主张画地为牢,不要说我是做某一个朝代的,其它朝代就跟我无关,或者说我是做古代史的,就不要碰近代史,我做经济史的,就不要碰民族史,不是这样的。我的专业是社会经济史,我的老师是研究广东的,但我做了一个民族史的研究,而且我不做广东,做了西南。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历史研究应该跟着问题走,跟着材料走。
我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我们把中国跟欧洲做一个比较,会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中国跟欧洲领土面积差不多大,中国比欧洲大一点,然后人口,中国比欧洲多很多,民族的成分,也是差不多复杂。然而,中国是一个国家,欧洲是几十个国家。欧洲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们就很难恢复自己的帝国。而我们中国就算历史上有分裂的时期,我们却一直不断地走向统一,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大一统的趋向,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的研究就是要回应这个问题。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是怎么形成的?我回应这个问题,就走到西南地区去了。为什么走到西南地区?要回应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思想中去寻求答案,这个方面我的兴趣不大,我也不擅长。另一种是选择一个具体的区域,看它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并从中讲出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大一统的“理”,这种区域社会史的取向,是我感兴趣的,也是我稍微擅长一点的。我觉得西南区域很适合回应这个问题,我就找到了西南社会来开展研究。研究西南,自然就绕不开少数民族。因此,是问题把我带进去的,所以我当时根本就没管,我做的是社会经济史还是民族史,从来不管的。
我怎样来讲西南的故事并回应我的问题呢?我想到西南地区是一个很有自身传统的地方。西南的少数民族分为两种,一种就是长期处于部落状态,没有自己的一个政权体系,没有形成阶序化的社会结构,人群很分散。另外一种是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有的还是比较强大的地方政权。这种两种不同的人群状态,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被司马迁所发现。而我通过认真的史料分析得出结论,在宋代,西南地区存在至少十个以上的地方性政权,绝不是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我就选了位于今贵州西北部地区的两个彝族人建立的政权,一个叫水西,一个叫乌撒,看这两个具有独立性的地方性政权,怎样从元代至清代,一步步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秩序,并从这个叙事中揭示出西南地区整合进王朝国家的“理”。这个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在考察的问题。
博士论文写完了,我又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在想中国过去是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但是现在中国不是王朝国家了,是民族国家。中国怎么样由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过渡,这也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就想去回应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但是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中国近现代史,因为问题把我带到这里,材料我也读得懂,为什么不可以去到近现代呢?我就去做近现代史了。
进入近现代史回应我的问题,我就想应该选一个区域,我还是选西南,因为西南的非汉人群,在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很有趣。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民国的建立不只是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中国整个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发生变化,西南的这些少数民族变得很尴尬,你看尽管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西南的非汉人群在正史的书写中就长期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民国建立之后,搞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就麻烦了,西南的少数民族,你说你是汉人吗?不是。你说你是少数民族吗?也不是。满汉蒙回藏五族没有你的地位,因此你就不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你也享受不到你原本应该享有的很多权利。因此,很多西南的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就向国家抗争,要求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比如我书中讲到的曲木藏尧,他是四川越西县的一个彝人,北伐战争胜利了,当时南京是许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他也来到南京,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读书。但面临着困难,他进不去,为什么?蒙藏华侨班收的是什么?蒙古人、藏人还有华侨,他是什么人呢?他都不是,所以就进不去。他是曲木家支的人,他当时用的是一个汉人的名字王治国,灵机一动,改一个名字曲木藏尧,声称自己是西康藏人,这个名字一听就像是天经地义的西藏人,他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有点好笑,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回到历史现场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曲木藏尧,我们是彝人,我们会怎么想?这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们为什么享受不到我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因此,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就要跟国家谈判,要跟国家协商,你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所以,我就决定写这一群人。
探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时,西南的这些彝人怎么样来表达他们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建立的,是各个民族共同建立共同拥有的,我们绝对不应该忽略少数民族的声音。我这本《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写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这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把我从古代史带到了近现代史。
问题清楚了,接下来我得思考,怎样来叙述这段历史,怎样来讲故事。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受到许许多多的感动,很多时候我情绪很激动,我为什么情绪激动?一是这些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还有就是,我在做田野的过程中被打动了。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访问了一些民国少数民族精英的后代,而且非常幸运,我访问了尚在人世的一位“夷族”精英,他就是李仕安先生。李仕安先生去年8月25号去世,去世的时候105岁。在同李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被感动了。
我认识李先生的过程非常有趣。2007年,我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当时我知道我关注的这些夷族精英们基本上都去世了,比如岭光电、曲木藏尧都已去世多年,但是这个李仕安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间。我就拿百度查了一下,百度搜索“李仕安”,查到他2002年的时候还有活动,他那时大概90岁,两年前患了肠癌,还做了手术。我就想,2002年还有活动,到2007年已经5年了,在世的话就95岁了,还经历过癌症,十有八九可能不在了。我就想,不管在不在,我碰一下运气。看了百度搜索,知道他是在雅安,什么单位我也不清楚。我给大家讲讲我怎样找到他,顺便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些技巧和办法。这种老人家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官员,按照惯例,要么是在政协工作,要么是在民宗局工作,反正就是这类单位。然后我就在百度查了这个雅安的区号,打区号加114,一查人家接线员就问我,要什么电话。我就说我想查一下雅安市政协和雅安市民宗局的电话,他们就给我了。拿着这两个电话,我想随便打一个,先打政协吧。政协的人接了电话,问我是谁。我就讲了,我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单位是不是有一位李仕安老先生。他说有,我说老先生身体还好把,他说还好。我说我想找李老先生聊一聊,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他的电话。他说没问题,就给我了。我在北京就马上拿着这个电话拨,一拨就有人接电话了,我说请找一下李仕安老先生。电话里面回答说:我就是。我就马上自报家门,我说老先生,我经常看民国的报纸,看到您写的文章,我想到雅安来找您聊一聊,您看行不行。他说:可以啊,欢迎!于是我马上买了机票从北京到了成都,到成都之后我担心,90多岁的老人家,昨天答应我没问题,说不定今天就有问题了,再打一个电话。我说李老先生,我已经到了成都,我明天准备到雅安来拜访您,您家在哪个地方?他说:你大概几点来?来了之后,你到建安中学门口,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95岁的老先生来接我,吓我一大跳,我不敢让他来接,我说不行,我还是来找你,我找得到的。他说:不用客气,我每天都出来散步的。果然,我那一天大概下午三点我就到了建安中学门口,到了后打电话,老先生就来接我了。老先生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我就到他家,跟他聊了大概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我发现,老先生是一座宝库,但我聊不下去了。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们跟一个人聊天,三个小时你还有多少话题?而且我当时没想到要做田野,录音笔留在广州。所以,聊了三个小时之后我觉得不行,我的准备工作不充分,聊不开也聊不深入。在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时候,你能跟一个人聊三个小时就不错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讲讲这些经验,可能对你们大家,特别是对同学们有点启发和帮助。我觉得我应该下一次再来。我就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之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再去雅安了。这一次我“武装到了牙齿”,对,我把老先生的经历弄得非常清楚,他的朋友们我也弄得非常清楚,我把老先生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放到电脑上,录音笔也带上了。这次跟老先生聊天就聊得时间就很长了。我跟老先生聊得最长的一次,从上午九点聊到晚上九点,中间不休息,就在他家吃饭,老先生一边聊天一边喝白酒,有一次他开玩笑说:我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就是靠白酒。这个我当然不敢学了。后来我每一年都去雅安看他。其实我是叫他爷爷的,然后叫他的太太叫奶奶。我跟他们聊,首先是很感动,我感到以前做的历史,说实话都是冷冰冰的,我做明清时代,资料已经比较丰富了,有时也会有点历史的鲜活感,但总体上还不够有温度。但是做民国史就不同了,我在书上看到的那些人,蒋介石、宋庆龄还有刘文辉、邓秀廷、岭光电等等这些人,老先生跟他们都亲自接触过的,我在报纸上、在史料上、在档案上看到的人和事,跟老先生一聊,老先生的口述与我在纸上看到的东西和谐共鸣,一个个栩栩如生就在我眼前浮现,我非常感慨,历史那么鲜活,我做历史做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
还有一个感动是私人的情感。聊到最后大家的情感就很深了,经常在他家吃饭,我也不客气的。还有他的太太,最后老先生一旦有事情离开,他的太太——王奶奶就会找我来聊天。王奶奶的故事也很精彩,只是因为主题问题不能写到这本书里面。我那时候还是单身,王奶奶握住我的手说,你别担心,我两个弟弟30多岁才结婚,你现在还小,你会有一个好妻子的,以后你要带她来看我。
因为历史那么鲜活,我跟历史的当事人又有很深的情感。所以当时我就想,写这本书的时候绝对不能像过去那样写。过去那样写就像八股文,把鲜活的历史写得冷冰冰的,我必须要写出生命的温度。当然前提是,我这本书必须是学术著作,所有的人和事包括种种细节,都一定要有史料做依据,这是历史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变。但是在呈现时,我要超越现在通行的史学叙述方式。怎么做呢?主要有三点,首先,我决定以人物为中心,这好像传统史学的纪传体,但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我的人物故事不是简单写生平,而是围绕着我的问题来展开。此外,我一共写了七个少数民族精英的故事,但是它们不是孤立的。这七个人的故事可以单独看,但连起来,就描绘出了民国建立之后,西南非汉民族精英向国家争取自身民族地位的历史过程。他们从1930年代开始向中央抗争,到1946年、1948年的时候,国家在宪法上正式规定了他们的权利,李仕安先生等几位“夷人”,按宪法规定,参与竞选并当选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这七个人的故事就把这个过程讲出来,7个人的故事可以分开看,但是又形成一体。
其次,我用的是倒叙手法。历史学一般不会用倒叙的手法。按常理,我应该先写明清再先写民国这一段。但我是先写民国“夷族”精英人物的故事,这是这本小书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写明清乃至更久远的历史,这一部分也写了几个人,因为材料的原因,没有民国哪些人的故事鲜活,但我也尽力去写得有温度。读者读完了这一段,就会明白民国的“夷族”精英们为何那样去思想那样去行事。读者刚刚看完民国这一段,进入古代这一段时,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两张皮,有点疑惑,但是等最后看到安获洁的故事,看到清初滇东北、黔西北的彝人们逃往四川凉山避难时,读者会恍然大悟,原来全书的两个主要部分是浑然一体的。这就是我对本书叙事的构思。
第三、在写的时候,我努力站在这些历史人物他们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角度来思考。我一直在想,我跟他们处于同一场景,就是民国的那个场景。李仕安也好、高玉柱也好,岭光电也好,他们的形象在我眼前浮动,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等都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当我把握住眼前浮动的这种感觉时,我才去写的。比如说我写高玉柱,我是很设身处地去想,高玉柱是云南永胜土司的女儿,但当她登场的时候,她手中拿的是一副烂牌。为什么是烂牌?虽然是土司的女儿,但是她爸爸早就被改土归流了,严格说起来,她已经不是土司之家了,她们家的经济实力也比过去一落千丈,社会地位在下滑。而且,她已经不会少数民族语言了,被汉化了,高玉族那个家族,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全部被划为汉族,一个汉化的人,怎么能代表少数民族呢?更重要的是,她跟云南省的省主席龙云的关系没搞好。龙云的大儿子看上她,龙云也看上她,想让她做儿媳妇,她嫌这个龙云的大公子太粗俗,尽管您是省主席的儿子我也不干,所以同龙家的关系就糟糕。她的手上,真的是一副烂牌。
我就在想,一个一手烂牌的女孩子,最后居然打出一副好牌,让全中国知识分子也好,党政要员也好,黑社会也好,都认为她就是天经地义的西南民族的代言人。她怎么做到的?我感到她这个人很有气魄,胆子非常大,很有全局性的眼光,善于审时度势,不是一般的人。她很能观察局势,1935年的时候,蒋介石围剿红军,红军长征,借着围剿红军的机会,蒋介石的中央军加强了对西南地方的控制。我们知道民国那些地方的军阀独立性很强,所以蒋介石借着围剿红军机会,中央军进来,介入了西南,贵州的军阀王家烈就直接被废掉了。国民党中央加强对西南的控制之后,必然面临着西南的少数民族问题。蒋介石当时在贵阳,就有一个苗族人叫唐明贵,给蒋介石上了一封信,说希望委员长解除我们苗民的痛苦。蒋介石为此专门要贵州地方政府重视民族问题,并拨了20万元经费,在贵州办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学校。中央的权威一展现,高玉柱就明白,中央跟少数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机会来了。第二年她就约了一个云南丽江人喻杰才,应该是纳西族人。跟喻杰才一起跑到南京去,跑到南京去得有一个由头,你来南京干嘛。首先我们向委员长表示衷心的谢意,领袖关心我们,我们代表西南少数民族向领袖表示感谢。其次,我是土司的女儿,我代表土司,喻杰才代表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众,我们要求中央解除我们的痛苦,继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大家想一想,谁赋予他们这个代表权的?西南那么多的土司后代,那么多的非汉民众,有多少人赋予了他们这个代表权?西南的绝大多数人土司与少数民族应该是根本不知谁是高玉柱谁是喻杰才。但这就是他们的策略,我们去找中央,说我们代表西南的少数民族,中央在这个时候也需要代言人是不是?所以中央也不会一下子把你压住是不是?而中央也分不清你究竟有多大代表权是不是?好,只要中央没有否定、质疑我的代表权,我回到西南去,马上就可以说我是得到中央认可的西南民族的代表。发现没有,这是了不起的策略,很厉害的。高玉柱空手套白狼,还真套住了。而且她也很切实地从西南民族代表的角度,跟中央谈西南的意义。首先,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有那么多人,我们把它团结起来对开发西南是很有好处的;其次,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南也有统治危机,不说地方军阀的独立性——至少他们在名义上还是认同并效忠中央的。我们知道,当时法国、英国帝国主义到了我们西南的大门口,英国控制了西藏、缅甸,法国控制了越南,对中国西南边疆虎视眈眈,还有红军长征经过这个地方,很多人跟着红军走。高玉柱他们对中央讲,西南少数民族很落后很愚昧,容易受人蛊惑,弄不好就跟着帝国主义走了,或者跟着红军走了。这样说的潜台词就是,政府必须重视西南民族问题,才能得到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否则我们还有其它选择。第三,高玉柱时时提醒西南少数民族对国家意义。等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高玉柱他们怎么跟中央说,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拥有很多的枪,大约有10万支枪,其中,至少可组织三万支枪起来去抗日。这些东西真的经过认真调查吗?我看没有。相信当时高玉柱也不可能真正去全面调查去全面动员过。但是如果中央政府真的动员组织,也有可能组织得起来吧。当时高玉柱的家乡有一个人叫谭碧波,同高玉柱有过接触,在南京遇到困难时还得到高玉柱的大力帮助。谭碧波晚年的时候,丽江的政协副主席高世祥先生对他做过访谈,他就说,我们家乡这个高玉柱胆子太大了,连蒋介石、宋美龄都敢骗,她有什么东西?都是骗的。其实你也不能说她是骗,很多东西,大家不去想不去做,就没有,一想一做就慢慢有了,她逐渐就被认为是西南民族的代言人,推动了西南民族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进程,她自身得到了发展,也为国家为西南民族做出了贡献。她的事迹轰动了南京跟上海乃至全国,蒋介石回应了她的请求,宋美龄请她吃饭。当过民国总理的唐绍仪、熊希龄这些人都见她,黑社会的杜月笙、季云卿也都见他,学术界的大学校长,还有妇女各界的,各行各业的,黑道白道红道全部都认高玉柱,就这么做起来的。
高玉柱这个人的形象在我眼前浮动,让我一定要把它好好呈现出来,写出来。每一个人的故事我都这样去想,这样去写,就交织成为我这本书的整个故事。故事讲完之后,我还要在故事中呈现出一个“理”。说出来的这个“理”,不只对是我的故事有效,要让不研究这个故事的人,不研究高玉柱、曲木藏尧等西南“夷族”精英的人,都可能对我讲的“理”感兴趣。这个“理”,在我的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直接点明了。我这本书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
宋旭景:其实这两本书的故事里涵盖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是“制度”,比如黄老师讲的是一个制度在每一个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变化。温老师讲的是这一群人是怎么样把自己塞进去这个制度。这里面体现了人的主动性。
我想代表大家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黄老师您的市场理论,跟西方的市场理论是做比较的,能不能对这方面稍微进行一下阐释?第二个是,温老师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国家认同,能不能从西南少数民族争取这样的一个地位,最终是怎么样实现了对大一统的民族认同。第三个还是刚刚说的,在这些共识当中,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人的主动性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跟国家和制度之间是怎么样一种互动?

黄国信:这是个好问题。怎么说呢?我这个书看上去不是跟哪个学科比较,虽然我一开始讲了学术史,关于市场理论的学术史。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我还是认为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先讲了算了。
我讲这个题目很简单,我来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个老师就告诉我说,他的老师跟他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东西可以分头去做,可以做出一个关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的样貌出来。陈(春声)老师做的是米。我选题时,不知道怎么办,陈老师建议做盐。我很快就发现做盐很头疼,因为制度太复杂,盐的制度,每个地方都在跟朝廷讨价还价,制度就复杂的不得了。所以盐史有一点点门槛,所以,我硕士论文选题就缩小范围做两广盐,发现还是很难,后来就集中到私盐,两广的私盐,正因为这样,才会看到我刚刚故事的材料。
读了一批材料之后,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后来发现我做得很不成功。虽然答辩的时候老师反映还可以,但是我自己觉得不成功。原因在哪里?还是材料。关于走私的那些材料,一般都是来自官员,给你讲一下哪个地方谁又走私了,哪个地方有走私的现象。你发现真正看到走私的人怎么做事,他们自己怎么讲的,是看不到的。除非抓到一个走私犯,审案中他供一点,不然就没有了。没有人告诉你说走私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后来我能发现这个材料,要感谢温老师,很多年前,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广东南海有一个地方叫西樵,这个地方有一个西樵山,是风景名胜区,当时地方政府做文化建设,说要进一步打造西樵这座历史文化名山,需要找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找到了温老师。温老师就跟我商量,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做一个跟别人做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不大相同的事情。刚刚温老师跟我们讲,如果我们做历史文化,讨论广东文化有什么特征,西樵文化有什么特征,是不能浮于表面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怎么办呢?我们的办法是对当地的文献做一个普查,包括民间文献、官方文献、以及各种物质层面的资料,还包括口述,包括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等。我们很快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西樵文献普查。在这个普查的过程中,我记得有一天走到一个村子,叫做百西村,那是一个单姓村,村子里的人都姓潘,它们当时的社长叫潘太浩。潘先生就很热情接待了我们,我当时带了几个硕士生一起去那里调查,查他们有什么文献。
在珠江三角洲,老百姓不是很愿意立即给你看文献的。但潘先生很快就给我们看文献,我们看到潘氏的族谱,就讲到他们起家的人就是一个盐商,这个我还没有醒悟过来,这个盐商跟广东盐销售到湖南有关系。后来,我在我们中大图书馆去找族谱,就特别注意潘姓的族谱,就发现了刚刚讲到的《潘氏家乘》,找到《潘氏家乘》就发现了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故事,故事很精彩。关于盐商与官员互相配合卖盐的故事,这样的材料非常难得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读历史的人讲到这个故事,一般就归结为官商勾结,就结束了,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是,我当时在西樵延陵村还看到一个吴氏祠堂。看到祠堂收支的告示,就发现祠堂控制了一大片市场,延陵吴氏有很大的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厦门大学刘永华老师写过一个文章,中国的市场很多时候是地方的宗族组织建设的,我就觉得这些故事,跟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就是我们上中小学读的那个经济理论有一点好像不大吻合。古典经济理论跟我们讲市场怎么形成的呢?一般都说,市场是因为有人要买卖东西,在渡口、码头等人口集中的地方,自然而然形成了市场。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是有人组织建立起市场。所以我对市场有兴趣,读了市场理论的书。就发现这个事情在经济学界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当然主流是两套,一套是古典经济学及其后来发展的逻辑,认为市场是自发形成的,不是人类设计的。只要有买卖,有东西,码头人多,有人去卖东西,广场人多,有人去卖东西。寺庙人多,有人去卖东西,就形成了市场。这是一个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但社会学家们不这样认为,他们发现市场不是那么抽象就可以形成的,他们认为,有一个非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的市场理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波兰尼讲的所谓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他说,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前,人类有三种经济形态,都不是以经济理性处理社会生活的,是荣誉感、社会责任感作为处理社会生活的准则。读到这个之后我就想,这个理论跟市场形成问题是有关系的。它可以让我们解释市场的逻辑及其形成。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段时间桑兵老师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认为我们研究历史要倾听历史的原声,这个我很同意桑老师的说法。我们学历史的人,不能把用概念去图解历史,如果那样,肯定是错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听历史的原声,我们如何去听,如何听懂。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很多忙。所以我发现当读了经济学、社会学跟其他的包括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市场理论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我们在西樵山看到的这个材料,就是我们潘氏家族里面的材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们市场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解释中国传统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市场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一个中国独特的市场逻辑。这个市场逻辑肯定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就是我们读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市场逻辑是不一样的,这个结论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于这一点我可以很自信讲,中国传统的市场逻辑跟大家读的政治经济学里面读到的市场逻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我这个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当我们倾听历史原声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办法来帮我们。我们不是读懂故事本身,就能把历史讲出来,我们需要有分析方法来帮我们。这些分析方法很多时候来自于其他科学理论,这个科学理论不是拿来图解我们的材料用的,而是帮助我们分析这些材料用的。分析材料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故事到底它的深刻含义在哪里,可以跟今天的理论有什么对话。我这个书最后的定位在什么?讲出中国自己的市场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可以跟西方经济学已经有的市场理论可以形成什么对话。我不是想重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是告诉大家说,我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得出了一结论。我是想说,西方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大概是从英国的经验发展出来的,从亚当•斯密他们的逻辑里面发展出来的,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市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中国这个市场,然后就可以回应西方的市场理论,就可能给更宏观的理论,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的市场类型是怎么形成的提供重要的分析基础。当然波兰尼说了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波兰尼讲得还不够。波兰尼直接讨论中国市场的时候,他提出了中国的再分配型市场理论,但是他没有具体展开讨论这个市场如何形成,具体的运作逻辑如何?所以很有必要对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逻辑与市场秩序展开实证的讨论,以便将来的研究可以深刻地总结它。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云南大学最近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书里,收录了刘志伟老师一个讲座记录稿,就是他在云南大学讲的他关于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解。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发现,刘老师已经有关于王朝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很系统的体系建构,但我有点得意的是,原来我跟刘老师想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当然,他是我的老师,我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这个一样,就是我们都在共同努力做一个事情,解释传统中国市场,这个市场理论是希望建构一套跟目前的市场经济的市场理论不一样的理论。这个时候我觉得倾听历史的原声之后,我们其实想做的事情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深度理解,回过头来去影响到社会科学的东西。我们想做这个。。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反过来去挑战他们的理论或者是丰富他们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大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故事,以及我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我的故事没有温老师书的故事精彩。因为我到西樵山去,我一进村,人家都招呼我去喝茶,他们说很欢迎你们过来。然后回到潘家,潘家真的是非常有文化,他们说,我们自己正在做一系列的宗族文化建设,你们来了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当时还在新浪有一个博客,不断的整理他们潘家的事迹。那个整理对我的研究有很多的帮助,大家注意到我的书里面直引了很多他们的整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旭景讲的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所谓历史人类学,你不要想得那么神秘,其实它就是我们做历史的一个正常途径,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旁门左道的途径,我们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子做,如果不是这样子做的话,我就不能发现这个故事。我就发现不了这个材料里面的深刻含义,这就是历史。我们做历史就是这样的,你非要说历史人类学,就是你们跑去进村找庙,跟主流的政治与文化没有关系。可是,要是我刚刚讲的东西跟主流历史没有关系,那就奇怪了。我觉得我们主流历史更加要回应更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历史学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做的。
温春来:我就简单回应一下。讲到历史人类学,我首先强调一条,就是我们现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等高校,这个学术共同体,在做的历史人类学,不是简单的从西方搬过来的。我们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影响的流派基本上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但我们这个历史人类学不是。是我们的老师们,他们基于中国的学术传统,积极与西方历史学人类学对话,在二三十年的时间慢慢发展出来的,而且它是不断开放的,是一个开放的东西,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问我的老师们,什么叫“华南学派”?他们回答就是没有什么“华南学派”,哪有什么“华南学派”。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的东西,你说它是什么,就画地为牢把它桎梏死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发现,你们如果按别人给我们的总结,说我们做的历史人类学,要“进村找庙”、“进庙找碑”,重视民间文献。那你会发现我跟黄老师的这本书都不是历史人类学。我这本书没有庙,没有碑,没有族谱,没有契约,没有讲仪式,没有讲信仰,而且关注的不是普通的民众,我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如果不是我的身份,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把我这本书归入“华南学派”。但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中山大学接受了这个训练,我明白应该怎样去思索,我就慢慢往前走,我没有这些桎梏。总之,我们的历史人类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因为它不断地开放,所以它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
刚才旭景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我讲出我的故事中的“理”。我的第一本书当然是想讲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在西南统治展开的“理”,我总结出一个“从异域到旧疆”的模式,这个不多讲了。我这本《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回应了很多的东西。第一个你看,大家现在经常讲的一个火热话题,zomia,也就是逃避国家统治的地方。按斯科特的说法,他是把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都划入zomia范围。他认为,因为西南这些山区,是不容易大规模生产谷物的,因此自身很难维持一个国家,传统时期的国家也不容易深入这些山区。所以,zomia就是一批人逃离国家的一个地方,中国西南山区就是这样的。这是斯科特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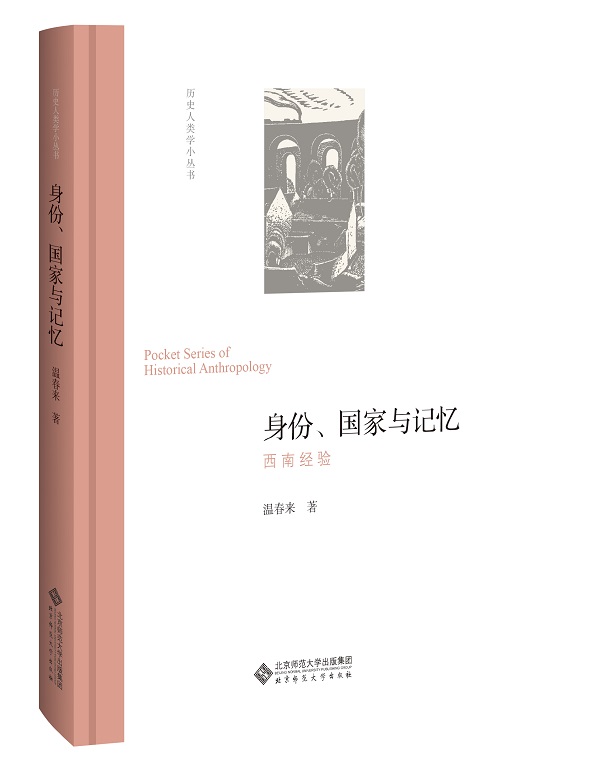
然而,你一看历史你就会发现,西南山区哪里会没有国家?在西南的崇山峻岭里面,2000多年前就有国家一类的实体存在。而且我讲的那些国家,许多根本就不靠谷物作为支撑,我讲的那个很强大的水西政权,主要的税收是牛、羊、马等等,谷物排在最不重要的位置。斯科特的zomia,很多是逻辑推论甚至是猜测,在他的书中,其实实证的部分是非常弱的,严格说起来,它只是提出了一个猜测,但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不过,我的这本书,主要目的不是要同斯科特对话,我主要是讲其它的“理”。
为什么民国时期这一批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们在跟国家抗争的时候,他要跟国家说,我是“夷族”,这个夷当然是蛮夷的“夷”,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而且跨了云南、贵州、西康还有四川几个省的地域这些少数民族都这么说。这个“夷族”跟今天的“彝族”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被划为“彝族”的这群人,可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之间,不能交流,风俗习惯有差异,而且本来没有谁会自称为“彝”,他们的自称有数十种甚至更多。因此,西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上本没有“彝族”,“彝族”是新中国政府建构出来的。但是大家看我写的这本书,一下子就发现了,原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早在新中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之前,在明清甚至更早以前,在今天被划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内,一直有上层精英在建构一个很广大的人群共同体,这个广大的人群共同体横跨了云、贵、川几个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是同他们的国家传统相关的。一个大的人群的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必须要有所支撑,这个支撑可以是宗教,可以是语言,也可能是政治实体。在今天被划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内,古代曾建立过许多地方性政权,这些不同的政权之间,相互通婚,相互继承对方的王权,所他们自然认为大家是同一群人,认为大家有共同的祖先。虽然到清初这些地方性政权都全部消亡了,但影响仍在,而且在他们用自己的文字所书写的材料中,仍然记载着过去的传统。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到民国时期向国家争取自己作为民族的政治权利时,来自这些地方性政权的后裔们,会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但他们的族称为何要用“夷族”呢?因为他们受到汉文献书写传统的影响。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写到西南“夷”,到了明清和民国,“夷”在保持着对非汉人群的泛称的同时,开始明确地指向某些地域的人,“夷”逐渐成为云贵川许多地区非汉人群在讲汉语时的自称。因此,向民国中央政府说我们是“夷族”是很明智选择,因为这个族称有历史依据,而且民国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们都熟悉这个族称,此外,因为大家的自称不同,如果要用自称,不但民国政府不熟悉,而且也很难统一。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族称报上去,必然会失败,当时全国都只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族,你西南一下子要求划几十个族,绝不会得到认可,因此,讲“夷族”是最好的。不过,既然是讲“夷族”,就会超越过去那些地方性政权的人群范围,但也可以接受了。为着现实的政治需要,他们甚至可以把范围划得更大一点,叫“夷苗民族”,但事实上,我们看到,那些精英们,主要就是来自过去那些地方性政权的范围。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这些历史的延续与变异,说“彝族”是新中国政府的建构,学理上是不充分的。
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当这些西南的少数民族要中央要给他们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时,当他们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时,他们其实等于在强调,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是少数民族与我是中华民族之间,没有矛盾,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你中央为什么必须管我们帮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如果中华民族要强壮,必须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强大起来。而且根据孙中山的民族政策,要扶持国内的弱小民族,我们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个弱小民族,所以你们要扶持我们。这个想法其实已深入当时很多少数民族精英的思想中。就像岭光电,他是一个“夷族”,1935年暑假他到了北平,因为他当时是中央军校的学生,所以穿着中国军队的服装,而当时北平已到处是日本军人,旅店的老板好心告诉岭光电说,你不要穿中国军装,遇到日本人可能会惹麻烦。岭光电一听很生气,买一把匕首,插在腰带上,我就要穿我们中国军人的服装,如果你日本人来挑衅,我突然拔出刀来,杀死两个绝对没问题,我死了也行。你看他是有很强烈的中华民族的观念与爱国情怀的。他强调他是“夷族”的时候,就是强调他是中华民族。
在书中我画了一个同心圆来表示这种复杂的认同结构。最里面的那个圆,是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范围,接着是那些地方性政权的范围,再接下来是“夷族”这个范围,再接下来是“夷苗民族”这个范围,最外层的那个圆,是中华民族。这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就是当时西南非汉人群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示意图。民国之前到明清甚至更早,西南非汉人群一直在建构大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建构影响了民国时期那些“夷族”精英们的思想与行动。
那么,民国时期“夷族”精英们建构的那个共同体,与之前建构的共同体有什么差异呢?这就是传统国家时代与民族国家时代的差别了。在传统国家的时代,他们建构的共同体大体上只涵盖上层,不包括下层百姓。而到了民国,他们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影响,他们要建构的共同体是是全民性的,上层下层全部包括下来,因为民族,是跨越阶级的,你不能说只有富人或权贵才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穷人下层老百姓同样也是,大家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种变化叫做从选择性的共同体到普遍性的共同体。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理”。而这些“理”,不是通过枯燥的学术语言表达,我通过具体的人的故事已经自然而然地表达了,我在具体的人的故事的基础之上做一个总结就写出来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