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至爱书 | 《叶芝诗选》byW.B.叶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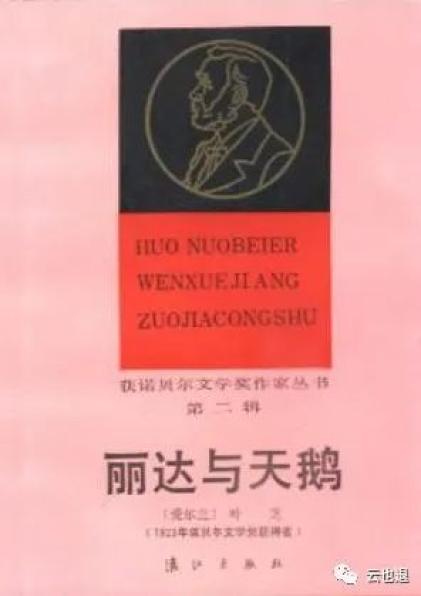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取下这一册书本,/……多少人会爱你欢乐美好的时光,/爱你的美貌,用或真或假的爱情……”
最怕的一首诗,就是叶芝的《当你老了》。不敢想象衰老,更不敢想象的是,连假惺惺怀想我的美貌的人都没有。由于叶芝的缘故,衰老被设立了一个苛严的标准:必须优雅地老,如此才能获得崇高的情操的持续恋慕:“但有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也爱你衰老脸上的哀伤”。
心上人进入晚景,与之相伴的叶芝则朝高尚的境界升华。可是没有灵魂只有皱纹的人怎么办呢?正如一位女同胞的话,她对“原谅我放荡不羁爱自由”这句歌词很是不屑:我不愿也不能放荡不羁,可我也爱自由,行吗?

1923年12月10日,叶芝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
1923年年底,W.B.叶芝去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听完了洋洋洒洒的一大篇对其个人创作历程的回顾和夸赞,叶芝发表了获奖感言。然而,纵观这项演说的所有发表记录,叶芝的那一篇可能是最短的,仅有六七百字,而且内容大多是客套:他说到,自己怎样在接触威廉·布莱克后了解了瑞典18世纪的博学者史威登堡;又说到易卜生和比昂松对于爱尔兰戏剧的重要——但这二人是挪威人,叶芝似乎都没把身在斯德哥尔摩(而非奥斯陆)这事放在心上,他似乎觉得“反正你们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是一家子,多担待吧!”
叶芝是没空,是不得闲,对这件别人极为看重的荣誉,他敷衍了事。叶芝那时有更大的理想,事关民族和世界。他不满足于只是自己一个人得到了文艺的武装,跻身名人之列,而爱尔兰的广大人民及其自由事业与此并无关系。而且那时,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引起了全欧的关注,爱尔兰则刚刚打了几个月的内战。对爱尔兰的失望,和对精英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期待,位列于当时叶芝首要的关切事项。

他挺幸运的,虽然个人总是动不动心事重重,总是为如何兑现那些高于文学之上的抱负而殚精竭虑,可是距离犯下足以导致身败名裂的大错,叶芝总是差那么一点。他倾心的东西跟法西斯的理想很接近了,他对优生学的兴趣从不亚于那些企图净化欧洲民族的政治领袖,可是他从未走出公开支持那些人的一步——而一度为他当秘书的艾兹拉·庞德就没忍住。第一次世纪大战后,叶芝连参议员都当上了,话语权不成问题,但他始终对等着听他讲话的人民大众充满了犹疑,正如他始终不能确定自己的能量除了写诗还能用来干什么。
他的幸运与坚定的信念无关;在他对受奖的敷衍中,我也看不到酷,而只看到沉重的疑虑。《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里的这几句诗,是多么明白的蔑视大众:
“我走过他们时曾点点头/或作无意义的寒暄,/或曾在他们中间待一下,/有过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在谈话未完时就已想到/一个讽刺故事或笑话,……”

“他们”能形成危险的力量,“我”则是知识,是艺术,是语言。“我”并无耐心去跟“他们”说道什么诗歌和思想之美,“我”有心拯救“他们”,同时又清楚“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会辜负这份心意的。可是这种蔑视,与其说是出于一个有才华的人的骄傲,不如说是出于深藏的胆怯。
因为能够压倒叶芝的力量太多了:从他那位能打他耳光的父亲,到对茉德·冈的苦恋,到年迈力衰,再到脾气乖张、行为难测的人民。爱尔兰人是欧洲最难以判断的民族之一。叶芝有许多绝好的诗句,可以有力地启发一个普通人的愚讷脑袋的有力开凿,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自说自话——一如他1925年出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一种“幻视”。比如:
“在极端和极端之中/人走完了他的历程;/火炮,或火热的呼吸/都会来摧毁、来消灭/白天和黑夜/的自相矛盾;/身躯称它为死亡,/心称它为悔恨。/但如果这些话是对的,/什么又是欢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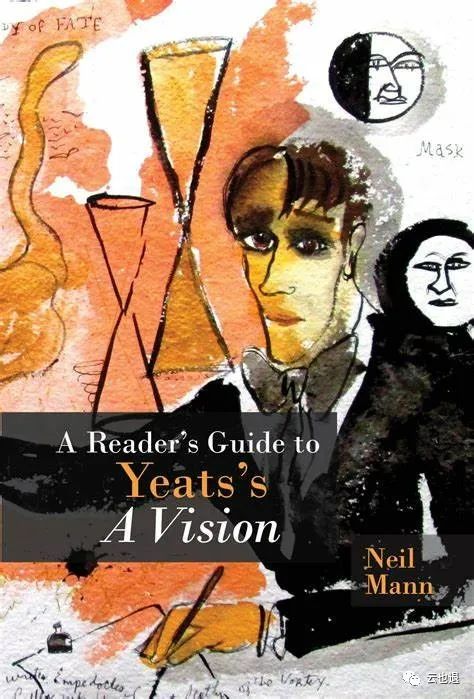
这真是一种很大胆的对生命的阐释,问得也很铿锵。但叶芝式象征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暴露了:他奔腾灼热的情绪,总要表现在抨击一个他自己构建出来的对象。他后期的代表性态度是“怒斥”,不仅从感到衰老时起就一再怒斥“光阴的消逝”,他还怒斥各种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常见的无情的现实,不过,他会先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现实塑造成强有力的对手,因此我觉得,他更看重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愤怒与无力更具有纪念意义。
这是《踌躇》的一部分:
“获得你能获得的黄金和白银,/满足一下野心,使琐碎的日子/充满生气,再用阳光冲撞它们,/但是想一想这些格言:/所有的女人都宠一个闲人,/尽管他们的孩子需要产业丰殷,/真正的过来人绝没有一份/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情。”

叶芝的塔,他的逃避之地
“真正的过来人”都晓得,不能指望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情——在有力的愤嫉中,叶芝轻敲了几下退堂鼓。《偷走的孩子》也是如此,看起来是呼吁“人间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被他厌烦的世界,但实际上,叶芝是拉了孩子来给自己的逃避欲打掩护:
“我们前前后后地跳个不已,/追赶着一个个气泡,/而这个世界充满了烦恼,/甚至在睡眠中也是如此焦虑。/来吧,哦人间的孩子!/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走向荒野和河流,/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偷走的孩子》)
与特朗斯特罗姆《果戈里》一诗中干净利落的“快乘上火马车离开这国度”相比,“这个世界的哭声太多了,你不懂”显得虚夸,有些做作。当然,就连《当你老了》都是做作的,他塑造出一种可咏叹、可怀念的老去,一种浪漫化的老去,从而为他骨子里的胆怯预支安慰。

叶芝倒是不怕文学名声衰落:相对于精力的衰退本身,名声和地位的下滑根本谈不上严重的事情。他对欧洲的形势、世界的格局的思考和评论完全不得要领,他始终没有丢掉诗人这顶陈旧的光环,而转型为一位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分析家。但好在他仍然在写诗。就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夫,累到极致时说“大不了回家种田”一样,叶芝在一次次发表了幼稚含混的时政分析后,心里一定也这么想过:“大不了做回我的诗人。”
诺奖颁发后的第五年,他的最新诗集《塔》又上了一个水平。其中包含诸多真正的名篇:《在学童中间》、《驶向拜占庭》、《内战时期的沉思》,还有《一九一九年》:
“如今的岁月毒龙当道,噩梦/骑在我们的睡眠之上”(《一九一九年》)
“逢人最好是用微笑报微笑,表示出/这个老草人过日子挺舒舒服服。”(《在学童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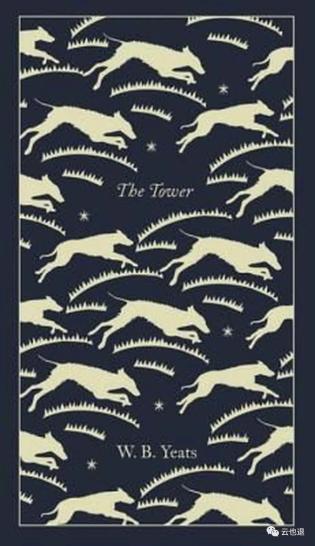
除非灵魂拍手做歌,否则谁能抵挡老去的折磨?因此我才那么喜欢《在学童中间》,它如同杂花生树一般地汇集了各种情感,从讽刺到忧伤,从嘲弄到自嘲。他照样怯怯地、多愁善感地躲藏在典故和议论之中,不过在完成诗的那一刻,在写下“随着音乐摆动的身体,明亮的眼睛,/我们怎样区分舞蹈和跳舞的人?”的那一刻,我也无法区分他和他所向往的智慧了。
本文系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
原标题:《至爱书 | 《叶芝诗选》byW.B.叶芝》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