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工作的围城里寻找尊严的出路 |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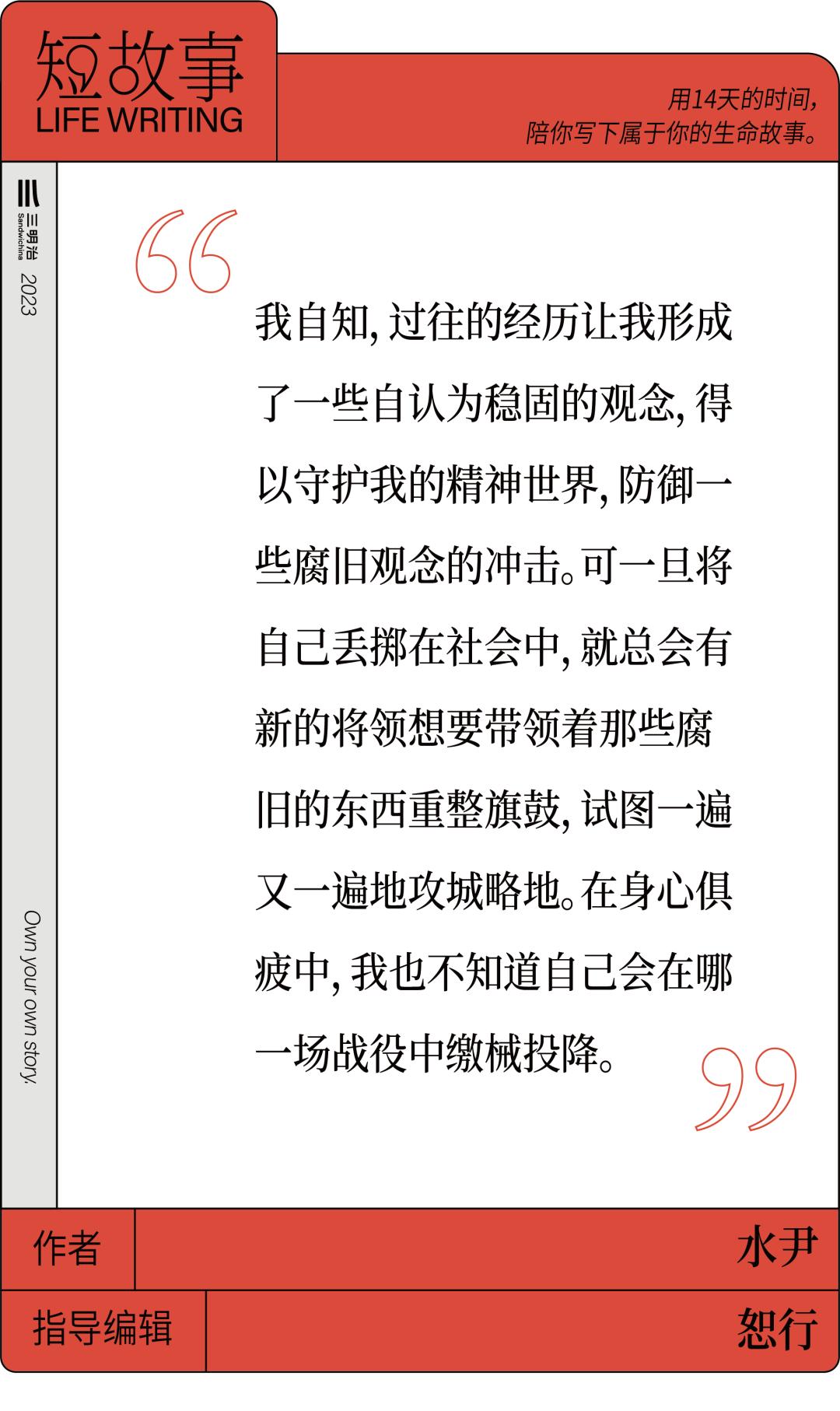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放慢脚步,在拐角处站定,再走五十米,就是我即将入职的律所了。调整呼吸,用手指轻轻蹭了蹭额头的汗,指尖带下来的汗液是乳白色的。我赶紧张开五指,将手变做一只肉扇,希望能挽救一早起来笨手笨脚化好的妆容。毕竟就在前一晚,老板特意发信息叮嘱,“上班后每天要化妆哦!” 或许动作幅度过大,裤子不得不吐出一截衬衫。
西装和衬衫都是昨天临时买的,只因行政突然通知今天要拍个人形象照与合照,需要统一穿深色套装。我翻遍了衣柜,都找不到深色套装,尝试与行政商榷,行政回复:“那可以去买一下,比较好。”
收完汗,我将衬衫重新掖回裤子中,精心调整衬衫的长度,使它能遮住并不相称的运动皮带。做这一切时,我的视线中总有苍蝇腿似的阴翳挥之不去,那是缀满睫毛膏的眼睫毛。
还有十分钟,我的手匆忙将头发放在恰当的位置,双腿迈过拐角,来到律所的大门前。可是律所的玻璃门紧闭着,门口的指纹机提醒我,我尚未获得通行证。隔着玻璃门望去,是开放式会议室,里面坐满了人,所有人的视线落向一处,视线交集处便是侃侃而谈的老板。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饱胀的自信,近乎兴奋。这种神情我见到过,就在几个月前,他劝我来这家律所工作时,也是带着这种神情。
老板曾是我的朋友,我们认识近十年。十年里,我们的来往并不算密切,只是偶尔会见面吃饭喝酒,交流彼此读过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他会分享自己工作中的见闻,一砖一瓦砌出他专业冷静、责任心强、对弱者饱含同情、对不公充满义愤的形象。在我厌倦原有的工作环境的时候,这些特质就成了一棵棵黄澄澄的胡萝卜,明晃晃地挂在了我眼前。
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我。彼时我所在的单位招聘助理,在例会上讨论留用人选。不知为何,一位男性领导开始留意一位应聘女生的体重,担忧其体型是否会影响单位的形象。这个理由令我匪夷所思,却让在场的男性兴奋不已,最终决定让秘书联系这位应聘者,让她立刻赶来,让各位领导“当场看看”,再做决定。我对这种近乎疯狂的荒谬感到震惊,试图提问“我们招人和体重有关系吗”,只得到一位男性老师不怀好意的反问:“你肯定不到100斤吧?” 而我们平日却教导学生要成为正义的人,不要歧视他人。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莫名的耻辱,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开始痛哭。我哭这个世界的疯狂,也哭我自己的懦弱与无力。
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圈子。当朋友了解到我的想法后,立刻打来电话,劝说我去他的律所。他列举了很多理由,电话打了近两个小时。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听他的理由,只是觉得,只要不是这里,哪里都更好。后来他又约我吃饭,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兴奋地预测我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他将我视为他的接班人,并为自己的规划激动地涨红了脸。

眼前的玻璃门打开了,他的脸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只是不再涨红,也没有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妥帖的微笑:“你来啦?”
他带着几分疏离的礼貌,向我解释会议的议程有些延宕,让我去分配好的工位上等他们结束。我一面礼貌回应,一面感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探寻的目光。当我鼓起勇气想要迎上那些目光的来处时,它们又倏地一下,消失不见了。
行政将我引到未来的工位前,客气地嘱咐了几句,又赶去开会。我将椅子拉出,宽大的皮椅将将好卡在桌子下,费了好些力气才拉出来。坐下后,椅子的边缘刚好顶住腘窝,坐久了总让人有伸直腿的冲动。腰部离靠背还有好些距离,只能靠势单力薄的脊柱强撑。我的身体告诉我,这样华丽的皮椅,并不是为我准备的,它可能属于身形更高大的那些人,它在这里,只为服务于某种更高级的氛围,而非某个具体的人。
会议室传来一阵笑声,我站起身,走向墙边的嵌入式书架。书架的选书显示出话事者的漫不经心,只放了一些过时的工具书,一些同行的社交赠书,零星夹着几本成功学的书,其余空白处则靠空壳的装饰书填满。书架前是几排办公桌,每排办公桌都摆着几台电脑,每台电脑标识出一个工位,工位之间毫无隔挡,我就要在这里与我的同事们脸对脸、背靠背、肘碰肘的一起工作。一位合伙人的声音从会议室飘出来:“年轻人就是要奋斗,我总是听到有人说不想加班,如果你想要做出成绩,不加班是不可能的。”
会议在我一人的等待中终于结束。我未来的同事纷纷走向各自工位,大家穿着颜色不一的西装,灰色、蓝色、白色、格纹,等等,我生出疑惑,它们是否也在“统一的深色套装”之列?
行政召集大家拍合照,摄影师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烦,让大家找准自己的位置,但每个人都犹疑地站在原地,相互谦让着。好容易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摄影师开始反复计较灯光,调整大家细微的动作和距离,迟迟不按下相机,众人的情绪开始逐渐变得焦躁,但无人敢抱怨。
最终老板发话,“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摄影师这才不情愿地放过大家。这种近乎吹毛求疵的追求,让我对最终成果抱有期待,但事实上,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张晦暗不明的照片。每个人身着“统一”的彩色制服,表情都是经历挣扎后的敷衍与疲累,但却也不经意揭露了某种真实。

正式入职的第一天是以慌乱开始的。步行去上班的路上,大雨从四面八方来,除了雨伞勉力护住的头顶一方是干燥的,衣裤都被雨水浸湿,鞋袜也因为踩到松动的石砖进水。但写字楼门口迎宾的存在让我竭力作出与建筑气质相符的体面举止,抬头挺胸,暗自咀嚼这份狼狈。
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分钟,电梯口挤满了同类,大家都默契地各安一隅,掩耳盗铃般维持着一种切断真实来路的精致状态。只是当电梯一打开,所有的默契都化为乌有,每个人都试图为自己争夺一个位置,旁若无人。
第一个上午,我端坐在座位上。尽管被告知第一周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培训,但培训的具体时间和主题都不得而知,只让我随时做好准备。这或许也是培训所隐含的内容之一:交付自己的时间,随时随地由他人支配。数小时内,无人交谈。逼仄、精致的空间中,一切都是如此的精心,任何一点非经伪装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我的汗毛每次都会因为后排律师助理带着叹息的粗重呼吸声竖起。期间,一位律师助理过来与我交接工作,寂静的氛围让我们不自觉压低声音,宛若密谋。
交接完工作,我看向我的主办律师的工位,依旧空荡荡。有好心的同事告诉我,由于主办律师的个人原因,他拥有下午才来上班的特权。而其他人,迟到一分钟,就要被扣工资。
我回到座位,看着手上的交接清单,回想前一晚,老板临时告知我,入职后不能如之前说好那般,由他担任我的主办律师,而是安排了另外一位主办律师带我。我问:“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他回:“这是我们管理层开会决定的呢,我不会再与助理直接对接。放心,这也是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我没有再回应,只觉得事情悄悄改变了方向。
我在内心叹了口气,调动一切人生道理中的相关资源,安慰自己生活就是如此,不会一切顺心,然后开始整理接下来的工作思路。
正当我刚进入状态,老板端着杯子悠闲地踱进了会议室。不一会儿,行政通知我立即去会议室,培训要开始了。我与另外一位新入职的助理只能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匆忙响应指示。
培训的第一课主题是介绍律所的理念和执业风险防范,老板讲话的开头自然是附着在一些价值上,但后续的展开却逐渐偏离了这些价值,大部分时间被用于介绍他是如何斥重金拍摄律所的宣传片,并如何为他收回了成本。理念瞬间落入尘世之中,沦为包裹功利心的华美外衣,而风险防范则是为这种功利心配置一个安全阀门。个体经历变成了近乎英雄屠龙的故事被细细讲述。我们在亢奋地讲述中被感染,获得一种幻觉:只要我们复制这种路径,我们也能披襟斩棘,在世俗中走向成功。
光明的内容在正式的场合被传授,非正式的场合也不得喘息。培训间歇,老板与我作闲聊状,试图委婉地提出他的标准,提示我今日的妆容与穿着不如前一日精致。我懊恼自己不自觉落入了标准的规训之中,还未上班就已然作出迎合的姿态,使他以为可以得寸进尺。于是,我也作闲聊状,将层级关系拽回朋友关系,答:“那你只能忍一忍了。”大家心照不宣地讪笑几句,彼此挪开眼神,让心思落到别处去。
一日培训完结,竟觉无所获,只有一些字眼分外强烈地存在于脑海中,其中之一就是“low”。这个字眼的主要用途在于谈论客户的拣选,欲盖弥彰地关联了一些统计学的证据,进而得出有钱的客户意味着高素质的客户这一结论。律所华丽的装潢,律师精致的装扮、耀眼的学历,等等,都是为了吸引这些高素质的客户。而不符合此类的,便是“low”。

晚上,老板在工作群发了一篇他近日写的文章,让大家提建议。大家错落有致地发表赞扬,为表真诚,还会挑选一两句文章中的语句一并发出。我看着那些赞扬,不愿附和。若毫无真心地应和,那么离开上个圈子将变得毫无意义。
带着这种莫名的责任感,我回复了一段话,先是标注出我喜欢的地方,再提了一些建议。这段话发出后,在一条条单句的信息中显得格外魁梧,本来热闹的广场瞬间变成无人烟的荒漠,静悄悄的。不知道过了多久,老板回应了一个大拇指。很快地,其他大拇指也一个接一个出现了。
没多久,老板私信我,问我能否帮他修改文章?我应允。
我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打开电脑,细细读了这个故事。故事是由他办过的一个真实案件改编,为了充实故事,他添加了许多读起来并不真实的细节,叙述的时间顺序也有些混乱。为了不破坏他的叙述风格,我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标注,调整了逻辑有问题的地方,修改了一些错别字、标点符号。修改的过程中,我有些羡慕他占有如此好的写作素材,也记起他曾用这点劝说我换工作。
改好后,我将文章发回给他。过了很久,他回我:“谢谢,我好好看看。”
几天后,文章在公众号发表,一字未改。发表前,他走到我的工位前交代工作任务,末了,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你的修改建议我看了,挺好的,但我觉得会改变我的风格,所以还是保持原状吧。”说话时,他的眼睛望向别处,本来在外面的手插进了裤兜。
文章发表后,他又同我闲聊,“这篇文章发了后,好多人和我说看不懂,说我写得越来越差了。”不等我回应,他开始解释,“可能是我写得太长了,没办法,为了之后出书,毕竟字数有要求。”我没有为他找理由,尽管我知道,作为下属,应当为领导寻找一些体面。

到了第二日,我就开始习惯在工作中等待主办律师们的“突袭”式培训。丛林法则或许包含了这部分的警惕,对某种规则近乎自觉的服膺。
当天培训的是所里的明星律师,因其业务能力强颇受老板倚重。培训时他也袒露出这种自信,格外愿意表达自己对职场和生活的诸多判断,“职场关系就是竞争关系”“不要相信那些虚的,你赚到的钱才是真的”“我不喜欢改编案件,因为那就是假的”,诸如此类。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大概也抱持着某种善意提醒的态度,毕竟,对与生活贴身肉搏的人而言,当下即是全部,无暇顾及别处。
当天下午,我的主办律师也终于出现了。他的工位在我的斜后方,只要他愿意,我的一举一动在他面前一览无余。我犹豫许久,决定以沟通案件为由,主动建立联系。我组织好语言,起身靠近他的工位,保持了一段我自认为恰当的距离。
在发现我的意图后,他开始低头剥手指上的死皮。我与他说话时,他的眼神从未离开他的大拇指,尽管大拇指的死皮已经被他剥光,露出了新鲜的肉,被手边的桔子皮衬得格外红。我面带微笑,说出我的思路。之后是长久的沉默。我用等待对峙,终于换来一句,“先给高院打电话吧。”我下意识调整,回应一个仿佛未受困扰的“好嘞!”
之前交接工作的同事见证了这场尴尬的僵持,好心发来消息安慰,“他就是这样的,但人其实不坏,习惯了就好。高院的电话我发给你,你有空就打,很难打通。”我看着这条信息,想着要习惯的列表里瞬间又多了好几个事项。但在具体的工作面前,我无暇思考这些习惯背后的应当与否,我也害怕我思考的结论与现实相悖时给我带来的精神折磨,而这种折磨,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一种矫情罢了。
另一场由两位女律师合作完成的培训风格截然不同。不同于两位单枪匹马的男律师,她们既没有松弛的自信,也没有对自我无止境的讲述欲望,只对自己经历的案件做了一些琐碎的介绍,细节到去看守所要带上蚊怕水。其中一位Jessica,执业数年,言语间仍然透露出一种局促。文书写作的环节,几乎变成了老板个人作品称颂会,频频发出诸如“你们一定要去看!”“真的写的很好!”“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等感叹,其中一篇不过是在论述时引用了一位作家的文学化表达。在赞叹声中,我窥见了这种局促的来源,或许是某种无法平视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有人被供奉为高高在上的偶像,有人自我驯化为追随者。这种追逐带来的弱势,亦成为了职场生存之道。

Jessica有种与律所工作节奏完全不符的“慢”。早上,当我们已经到达工位,开始一天的工作时,她才带着早餐姗姗来迟。午休后,大家回到工位继续工作时,她会走到水吧开始磨咖啡豆。所有助理的争分夺秒仿佛都是为她创造的富余,被摊薄在磨豆机一下一下的研磨声中,也碾碎了助理的自尊。
终于有一日,一位同事抱怨:“为什么她可以这么闲?活都我们干了。”有人揶揄:“我们是打工的,他们才是一伙的,融入不了的。”大家哄笑附和,尔后沉默。区区数十人,被划为“我们”与“他们”,生存的直觉已然使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触碰到了什么。特权是属于某类人的。
然而,即便是“他们”之中,也区分出了“他”和“她”。Jessica冲的咖啡中,总有老板的一杯,每日的装扮,也都力求符合老板“精致”的标准。一日,老板要我协助Jessica找寻一个辩点的理论依据。临汇报前,Jessica说要先私下讨论一番,讨论中,她的局促与含混都说明她准备的不充分。
汇报时,这种含混触怒了老板,老板表现出我从未见过的不耐烦与暴躁,这种怒火使Jessica更为紧张与含混。出来后,我又收到好心同事的提醒,告知我这是常态,之前Jessica经常被老板骂哭。或许是Jessica平日表现出来的散漫,同事更多地责怪她的不敬业,而鲜有人探究老板怒火的正当性。
我开始有些理解老板为何曾向我说“我把她们当家人。”或许在他看来,家人不仅意味着某种亲密无间,也意味着某种不加掩饰的情绪。然而,他未说明,这种不加掩饰的情绪只能是单向的。所以他又会紧接一句:“她们脾气都比我好,我有点急。”
他并不亲近语言,却又比谁都晓得语言的可怕力量,于是要把那些好的词汇都占据住,仿佛可以因此获得所有美好的品质,就连那“坏”的,也不过是精心包装后恰到好处的坏,因为这样才是人性。唯有如此,他才是一个有些小小瑕疵的完美人儿。
他询问我对强奸受害者的看法,得到答案后便不再继续,只将话题引去别处。后来我才知道,所里的强奸案默认不让女性参与,因为害怕女性对受害者抱有同情影响辩护立场。但有时,他们会挑起一些关于强奸案的讨论,于是有女性主办律师表明立场:“那个男的一看就是倒霉啦,我看这个女的就是没谈拢。”听到这种言论,我不禁觉得悲哀,我们因为性别被自然排除在外,却又在被允许讨论时迫不及待迎合对方的立场,以期获得超越性别身份的“客观冷静”的赞许。

日子开始变得既臃肿又短暂,当我沉浸于案卷中时,我感受到了一些充实的愉悦。当我回到现实,不断被那些细碎的东西打断时,我感到愈来愈沉重的不安与疲惫。我自知,过往的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稳固的观念,得以守护我的精神世界,防御一些腐旧观念的冲击。可一旦将自己丢掷在社会中,就总会有新的将领想要带领着那些腐旧的东西重整旗鼓,试图一遍又一遍地攻城略地。在身心俱疲中,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场战役中缴械投降。
在不安与疲惫的裹挟中,我开始失眠。永远打不通的电话、老板朝令夕改的指令、冗长低效的例会、主办律师阴晴不定的心情、同事们日益凸显的疲累与焦虑,都日复一日滚成巨石,而我是永远无法抵达山顶的西西弗斯。
一日,执行主任找我谈话。她先是向我道歉,由于日常事务太多,拖了这么久才找我谈话,再向我说明,由于格式合同改版,入职这么久才能找我签合同。我都微笑表示理解,也配合地聊了我接下来的工作规划,隐去了我的困惑与不适。她又谨慎地提起了薪资,我表示不介意刚入职的低薪,这个之前已经与老板说过了。她松了口气,仍与我确认了数字。我表示,好像与之前老板说的不同,我需要再与老板确认一下。老板只有些尴尬地回我,“可能是你记错了,以合同为准。”我只能暗自轻笑,又是一个不一样呵。我带着合同回了家,没有签。
那一晚,我依旧失眠。我把那些“说好的”与“不一样”拣出来,细细咀嚼,才惊觉,从一开始,我就在不断地妥协,并用所谓的职场的成熟来为自己开脱。我惊异她人的驯服,而我所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否则别人怎么会觉得一句“你记错了”就可以将我打发呢?而这样不断妥协的我真的就会有朝一日抵达我梦想的某处吗?
我一遍遍审判自己,翻来覆去,直到看见晨曦从窗户爬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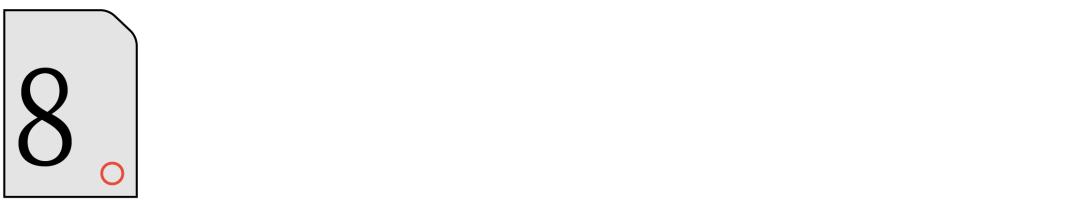
在晨曦的微光中,我作出了决定。那个早上,我没有化妆,穿上正装,出了门。我将手头的工作整理好,然后靠着椅背,开始等待。终于,办公室的玻璃门打开,老板将客户送了出来。我抓住机会,来到办公室门口,敲门,提问,“能聊聊吗?”他应允。
我转身关上玻璃门,走到他面前,拉开椅子,坐下。
短暂的沉默后,我开口,“我想了想,还是不签合同了吧。”
他的吃惊转瞬即逝,问我,“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太适合我。”
“能具体说说吗?”
“太压抑了,很多事情和原来说的都不一样。管理思路也比较混乱。”看着他有些窘迫的表情,我又说,“当然,我知道你们也在探索阶段。”
他表情缓和了下来,对我的理解表示欣慰,我继续,“而且,我不习惯和情绪不稳定的人一起工作。”
他的脸瞬间涨红,“哦,哦,这样。我确实比较容易急。”又仿佛抓住了什么似的,“所以我才没有带你,让别人来带你。”
“如果是这样,那应该一开始就和我说,我可以选择来不来,而不是来了之后被通知。而且你不是说是管理层讨论决定的吗?”
他眼神闪烁,“可是之前Jessica她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你看她们现在都很好啊,我才把她们当家人。”
“也许吧。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接受不了。你和我说的是大家都很平等,如果真的平等,那你能允许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别人也对你发脾气吗?我看到的还是大家只能忍受。你在培训的时候,也强调不喜欢助理反驳,不管对错,只能接受。”
他在宽大的皮椅中不安地扭动了两下,双手交叉,放到桌面上,重振旗鼓,“嗯,其实我是有意制造这种级别的差异,我觉得这有利于管理。而且我会观察的,谁好谁不好,我心里都有判断。”
我开始微笑,“嗯,那可能是你的考虑。但这样一来,就和你当初说的不一样了,那么我来这里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他转变策略,“我和你认识这么久,我知道你喜欢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东西,所以总是看到不好的一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担心的,担心你和其他律师处不好。”
我的笑意更甚,“谢谢夸奖,我很高兴我能有批判性,这正是我追求的。或许像你说的那样,我看到不好的一面,但这样我也不会为自己的不舒服找借口,去欺骗自己。而且我并没有和别人处不好,大家都对我很好,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也是我来这里的收获。但也正是这样,我才更真实地知道她们的疲惫和无能为力。”
他有些窘迫,平复了片刻,做出决定。“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既然你作出了决定,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那个瞬间,我们都如释重负。我说,“谢谢。”
他说,“希望我们以后还是朋友。”
我微笑,点头,起身,出门,将他留在了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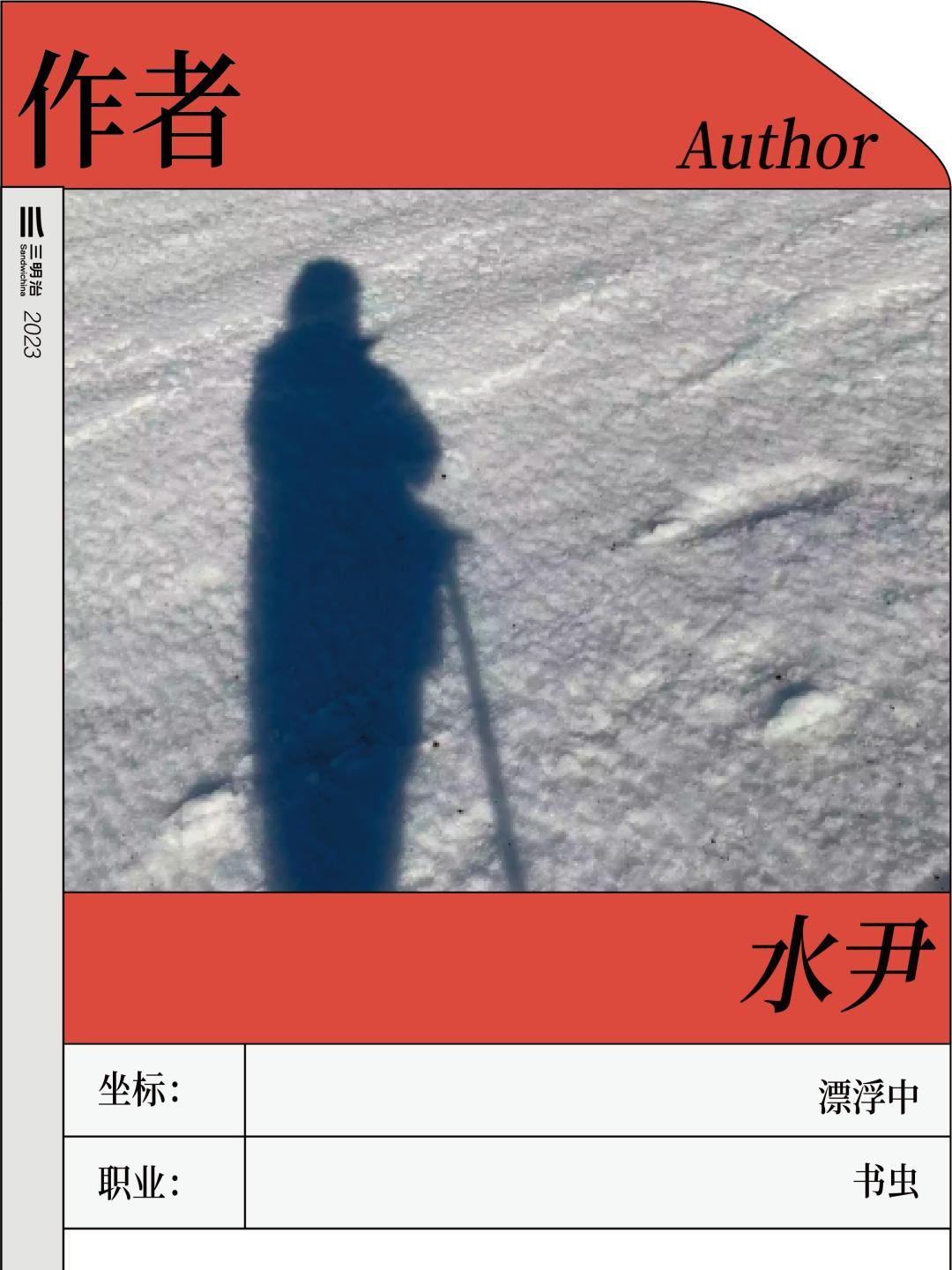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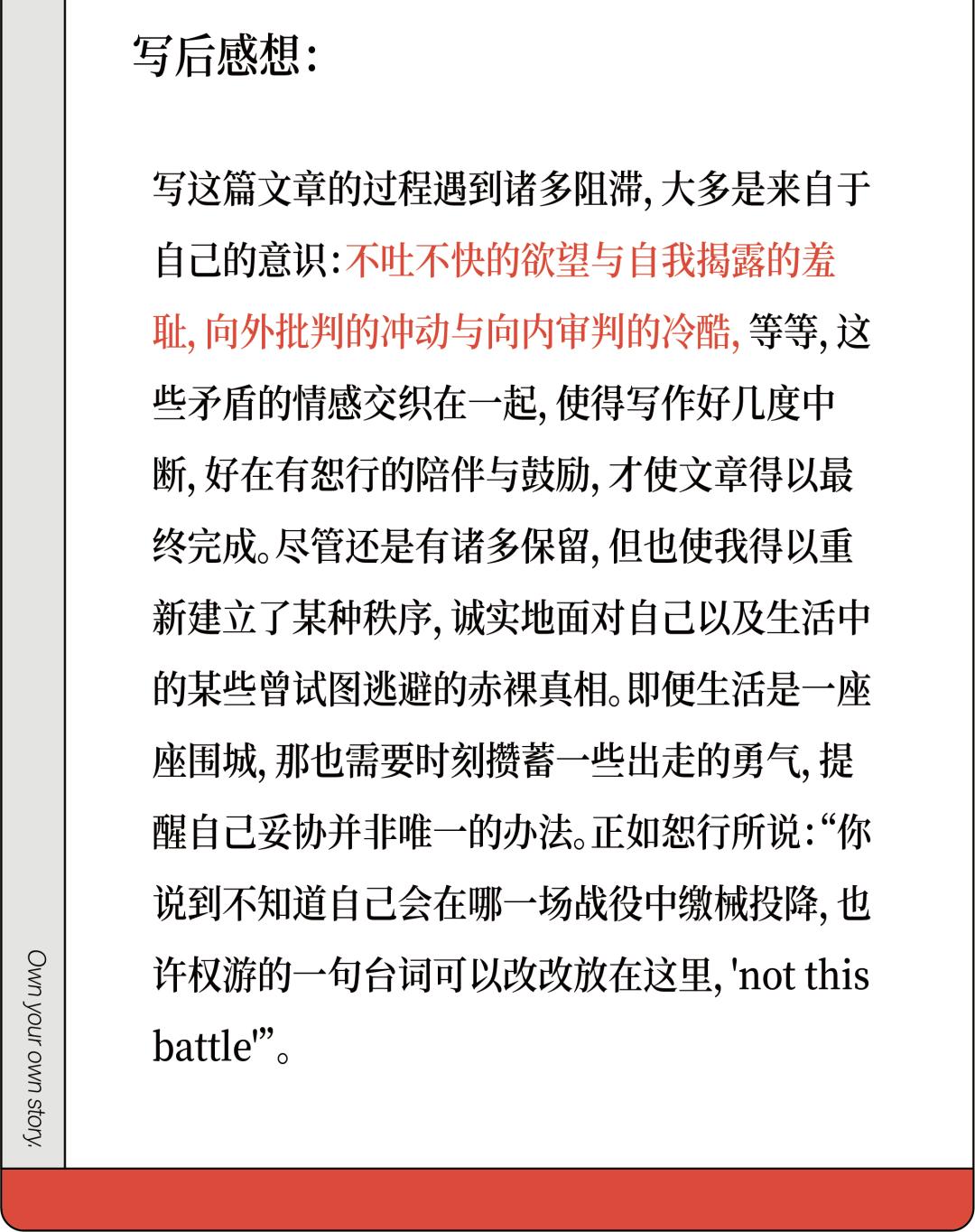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 · · · ·
原标题:《在工作的围城里寻找尊严的出路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