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疫情后的报复性旅行:淄博vs巴黎,到底哪里有旅行的意义?丨涟漪效应

近期,在微博上,一位博主戏称,“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多多少少是带着点‘这日子明天不过了,今天应嗨尽嗨、嗨完就去死’的态度在过日子了”,引发广大网友共鸣。
上海虹桥2023年4月28日当日发往全国范围内所有车站的车票全部售空,这是自晚清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以来,上海市内火车站所有车票第一次全部售空。与此同时,今年五一节,曾经因为疫情受到影响的演出市场迅猛回暖,中国演出行业协会5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5.19亿元,同比增长962.2%。这些无疑都是疫情之后经济强劲复苏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但是落到个体层面,其实就业危机、失业危机、种种生活困境还远远没有消散。一边是经济形势、消费行为枯木逢春一般的繁荣态势,另一边却是私人生活的持续、长久的困境。而近期在社交平台上被热烈讨论的“特种兵式旅游”、“淄博烧烤”的狂欢,似乎都可以被视为这种“割裂”的时代环境下“报复性情绪”的体现,发疯式的消费和出行、“应嗨尽嗨,嗨完就去死”的时代情绪,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大环境之下的一种特别有趣、也特别合理的反应。
我们也感到好奇,五一假期过去了,这些报复性出游的人,获得他们想要的快乐了吗?用游客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将得到怎样奇妙的文化观察?大流行之后,我们的出行和旅游有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年,国人心中的理想旅行圣地一直在变迁,在这种变迁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社会愿景的变化?当我们期待一场旅行时,作为游客的我们,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近期,B站知识区热门up主、播客节目《咸柠七》的主播曹柠,刚刚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欧洲之行,我们有幸邀请到曹柠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以上话题。
以下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或【点击此处前往小宇宙App收听】,效果更佳。
林柳逸:澎湃新闻·镜相栏目编辑
吴筱慧:澎湃新闻·镜相栏目编辑
方益:澎湃新闻·镜相栏目实习编辑
【本期嘉宾】
曹柠:B站知识区热门up主、播客节目《咸柠七》主播
【收听指南】
04:23 临行前,如何挑选旅行读物?
08:57 哪些文艺作品,让我们决定出发
15:02 出游前会做攻略吗?
20:55 “淄博烧烤”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24:25 一个月的“漂泊”,疫情后的欧洲观察
29:12 旅行中有哪些“the moment of being”的瞬间?
36:33 “游客凝视”:我们如何审视异己的文明?
45:18 反“游客凝视”:身为本地人,我们又如何观察游客?
53:47 旅行的艺术,是人与环境斡旋的乐趣
59:53 去卢浮宫和去淄博又有什么区别?
64:45 从西藏到大理,“远方”的变迁反应的是怎样的社会愿景的变化?
70:35 看家乡的游记就像在看别人给自己立传

受挫时代与狂欢旅行:“淄博烧烤”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曹柠: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每一次廉价旅游方式的兴起,都是和那个时代所遭受的一些挫折有关。比如说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催生了很多家庭的本地游。国内之前出现的露营浪潮则是因为疫情而引发的,你看,现在一旦放开之后,就没有人再露营了。我还问过我一个在迪卡侬工作的朋友,这种暴涨又回落的过程在他们的销售数据上能直接地反映出来。当时的那个露营小高潮,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社会情绪和商家共同操作的结果。
林柳逸:
好像这一次的五一,大家都是抱着一种“快不快乐另说,但我一定要出这趟门”的心态去进行的这次旅行。似乎对于“必须出去”这件事情本身的执念已经远远大于对旅行的期待了。
曹柠:
对,今年的很多数据都创造了各种意义上的新高,不管是人次还是价格。可能也跟商家有关系,他们在疫情期间受到的损失需要一些报复性的补偿吧。那么大家明明知道出去要堵在路上,为什么还是要出门呢?这个时候我觉得理性已经不是首要的原因了,就有点像是我们说的“去广场上热闹一下”。
林柳逸:
所以五一出行其实是一次非理性的出游,大家看似很缜密地在那里做规划、做攻略、做安排,其实内里是已经彻底疯掉了。
曹柠:
对啊,我昨天看到迪士尼单日访问量超过 10 万人,我当时整个人都木在那了,这唤起了我 10 年来上海世博会的一些非常不好的记忆。排了一天什么也没排到,然后就走了,一天就去排了两个队。所以我觉得五一去迪士尼的旅游体验肯定是很差的,但是这不妨碍大家很嗨。
包括我们山东淄博的烧烤,这个淄博烧烤到底是什么?我对它的好奇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对它的客观评价,甚至我就是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就想过去。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上,有很多由意外促成的派对都是这么酿成,伍德斯托克(1969年一场盛大的音乐节)就是这样。为什么在一个小镇上办的一个很小的音乐节,突然一下就变成一个嬉皮士大会?因为很多人就是听说,然后觉得“我要去看看”,它变成了不断被创造意义、追加意义的一个活动,最后就留在了历史里。
有很多人在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淄博烧烤,或者把它当成一个奇观去嘲讽,但是你不能否认这种非理性的东西里面没有一些非常浪漫的成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大家经过疫情之后看开了的部分,就是我们重新接受了“生活是很荒谬的”这件事。从理性的角度看,你去淄博想干嘛?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完全不是你的兴趣所在,但你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来看,你对它兴趣盎然。我很想知道淄博现在在发生什么,我想跟那些远道而来的大学生聊聊,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我们就静待它在文化史上留下一笔。
林柳逸:
可能淄博烧烤未来就成了中国亚文化在21世纪20年代的一种变体。

“游客凝视”中的文化滤镜:说白了,没有远方,让附近成为你的远方
林柳逸: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观光客的凝视”,或者翻译成《游客凝视》,它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叫约翰·尤瑞。尤瑞就提到,游客凝视的主要目的是自我愉悦,所有的游历其实也都是为娱乐和消遣这一主要目标服务的。但是我们旅行的初衷和本质目的,其实是为了去了解一种异域的文明,我们是想要去尽可能多地体验和感受的,而游客凝视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我们的体验和感受。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游客凝视?
吴筱慧:
我想到简·莫里斯在《世界》那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她说:“我是带着他者的经验看他者,带着自己的经验看我是谁,我看世界就是为了让世界看我”。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避免游客凝视这件事情,你必然带着自己的经验去观察他人,同时,我们在观察他人的过程中是可以慢慢看清楚自己的。
曹柠:
我在穆斯林国家的时候其实会很害怕,害怕自己犯禁忌,因为你知道你来自于一个世俗化的国度,你对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可能会更熟悉一点,你知道他们的禁忌是什么,但是因为你对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不了解,所以你会带着一点畏惧,这导致很多时候你会有意无意地给自己加戏。比如说,走在商场里,突然他们伊斯兰教的信徒要祷告了,然后我就赶紧闪开,想着别碍人家的事。但事实是根本没有人care你在干嘛,那些人就非常自然的,就像上厕所一样,在洗手间旁边完成了他们的祷告,反而是我自己在一边特别嗨。我就很想把它当成一个文化观察。
其实游客身份跟所谓的了解一个文化本身就是冲突的。因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你并不承载那种生活的重量,你只是轻轻的一瞥,甚至你这一瞥都是带着很多滤镜的。就像我看很多新古典主义的绘画,他们很喜欢东方,喜欢异域风情。比如安格尔、德拉克罗瓦都画过东方,但他们都没到过东方。这其实就是一种投射,最后是产生了一种自我愉悦的感觉,但其实你只是很安全地待在自己的生活里。
林柳逸:
我可能会用游客凝视去看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不是在福建长大的,所以其实每次回到那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游客凝视,而我的凝视的滤镜可能就来源于那些我看过的台湾电影,侯孝贤、杨德昌之类的,甚至还有一些台湾文学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当我带着这种文艺滤镜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反而能感受到很多独属于它的文化,甚至可以让我自己有一种文化认同,也许这也是一种刻奇,但是我还挺愉快的。
曹柠: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台湾的学者,他很小的时候就去香港了,18岁以前没有来过大陆,但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闽南话。他长得也不像本地人,教育经历也完全是西化的留洋背景,但是他的语言沟通是无障碍的。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某种隐秘的联系。我在纽约时很多天都吃得很不好,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被叫去吃一个特别地道的广式茶餐厅,甚至比广州本地的还地道,因为就是 80 年代去纽约的华人做的。当时我就有一种时空错乱感,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沉积岩”,在咱们这边先塌陷了的东西、某个时期的标本,在另一个地方被保留下来了。
林柳逸:
没错,就像是我在马华文学里反而能看到很多关于福建的东西,这会让我很惊喜,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发现文化的“沉积岩”的感觉一样,它错位了,但是又共时了。
曹柠:
我们很难保证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匆匆过客。说白了就是没有远方,只有你在遥望它的时候它才成为你的远方。但现在这个远方不一定是真的遥远的,远方可能就是你的日常。嗯,让附近成为你的远方。

想象的地域共同体:人与空间的关系本质上只是一种“讲述”
方益:
你们觉得如果我们从游客凝视这个视野来看的话,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在地写作计划”,它真的“在地”了吗?
曹柠:
其实本质上都是凝视,只不过游客凝视更短、更片面。赛珍珠的写作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样本:她来到中国,她看到这一切,她写下这一切,她的写作被肯定,然后又重新被否定。我们一度认为她是中国人的好朋友,但后来我们又觉得她是一个殖民者,是一个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观察者。所以,多大程度上你留下的这些东西是符合本地人的认同的?如果以当地人的认同作为一个标准,那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在地写作都不合格,都是外来者的入侵,即,属于一个地域的经验和认同是被外来者塑造的,而当地的生活却是失语的,甚至是已经湮灭了。
林柳逸:
金宇澄和《繁花》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典型例子。他祖籍其实是一个江苏人,其实也不算真正的上海人,但是他在文学界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就是用上海话去写作,而且这种写作是被上海人所认同的,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比当地人更好地呈现了上海遗落的文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地写作的例子。
曹柠:
所以是不是说到底,其实不存在一个地域文化的实体,它只是一种腔调?就像我们的口音一样,你说到底哪个是正宗的?其实它只是在不停地流转。
吴筱慧:
很多纪实类的作品,比如说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也都是外国作家对中国的观察。在某本书中,何伟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写了他在上海某一条街道上的生活经历。他采访了很多年,跟当地人每天打交道,然后写下他们的故事,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他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上的店家,他们开店之余,背后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在地写作就很棒。
林柳逸:
这可能就是游客凝视和在地感的一种平衡。
曹柠:
对,其实你要想清楚你的写作到底对谁有意义,如果只是把一个地方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对生活在本地的人来讲,他不需要这个,因为他已经活在其中了。对于那些匆匆一瞥的人来讲,他也不需要这个,他不需要了解那么深。只有一些闲散人士,或者说那种可以在无意义中创造趣味的人,他会认为这件事情有意义。
就像段义孚讲的“恋地情节”,空间本身没有意义,环境没有意义,无非是你给它加了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消解掉所有这些被建构出的意义的话,那我们跟空间就真的没有关系了。正是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迷恋历史叙事的共同体,所以我们才会不停地试图从这些虚无的空间里创造出一个叙事。
林柳逸: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说,旅行最大的幸福在于人和环境“斡旋”的乐趣。
曹柠:
对,斡旋这个词真好听。这次去意大利,所有的意大利朋友都跟我讲说,你千万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因为意大利出了新规定,就是如果你的钱包被抢了,除了你本人以外,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帮助你去追回,连警察也可以不管。你会在这种“险恶”之中去努力体会那个所谓的“斡旋”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个美妙的东西。很多时候,你是在一个地方迷失,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出路,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你会觉得你对它产生了一些更深的感情。
这种“斡旋”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最后,你会有一种“我战胜了它”,或者说“我原谅了它”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用心导致你更了解这里。所以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其实是阿姆斯特丹,这种“掉进坑里”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可以掌握它,而且从此我有了关于它的故事可以分享,它变成了一种讲述。

机械复制时代的旅行:为什么有人要和名画合影?去淄博和去卢浮宫又有什么区别?
曹柠:
我最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人要跟名画合影,这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去看《蒙娜丽莎》你要先排5分钟的队,然后只能看大概5-10秒钟,但大部分人在这么珍贵的时间里就选择自拍。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利用技术复制图像的这种赋权,其实也折损了很多你本能的感受力。你拍了那么多照片,其实没有多少是你真正印象深刻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在那边画画素描,或者说写一点什么东西,甚至只是发呆,可能你带走的东西比你拍的一堆照片要多得多。
吴筱慧:
我其实觉得拍照的话要看怎么拍,我现在去一个我喜欢的城市也会习惯带个相机,回来以后,除了在那边留下的回忆之外,我也会愿意经常去翻我曾经捕捉到的图像。
方益: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现在过于追求视觉信息,以至于我们退化了其他感官的感知能力,比如说听觉、嗅觉。
吴筱慧:
但其实我现在旅行了这么多年,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我所看到的景象,比如说它非常美,我希望通过相机把它的六七分的美保留下来,那就够了。其次是嗅觉和味觉,比如我吃到的当地的非常好吃的东西。如果满足这两点的话,我觉得这次旅行就很值得。
曹柠:
可能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有的人旅行是去淄博,有的人是去巴黎,但我觉得争论这些话题本身没有意义,这就是一种体验而已。就像老有人喜欢把他的那个游历比作那种就是欧洲的壮游,所谓的“Grace travel”。其实你知道那个旅游完全是一种贵族青年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的,只是为了不让他们废掉,所以制造出的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它并不是真的跟文明贴得很近的一种旅行,他们赋予的那些意义,其实很多只是后期往上加的滤镜。
林柳逸:
你刚刚提到的欧洲人的那种少年游,比如英国人,他们在成年的时候都会有一次那样的旅行,去领略自然的壮阔,想到这里我会有点同情我们中国年轻人、大学生,他们只能去淄博做特种兵。但是我觉得本质上特种兵和欧洲人的少年游也是一样的,你都需要在成年之际去进行那样一次游历。
曹柠:
我觉得一个值得反思的点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有营养且坚实的文化基地,供年轻人去游历。我去欧洲的时候正好是春夏,很多高中生,美国的、欧洲的,他们全在看各种博物馆,虽然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他们也只是在玩乐,拍一些照片发ins,但不管他们能不能看进去,至少他们还是泡在这个文化环境里。如果我们去淄博只是烧烤的话,我觉得少了一些这个部分,那个文化集体的部分。
林柳逸:
虽然都是被“熏入味儿”,但关键是什么味儿。
方益:
烧烤味也挺好的。

从西藏到大理:国人心中“远方”的变迁,反应着社会愿景的变化
林柳逸:
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对远方的想象具体的表征是哪里?我记得在我初高中的时候,去西藏的人特别多。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马原的《刚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都是以西藏为背景,他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野写西藏,可能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有一种西藏情结在了。后来又有安妮宝贝的《莲花》(2006),还有当时现象级的畅销书《藏地密码》(2008),以及大冰的《他们最幸福》(2013)。然后好像这两年对远方的情结和想象又转移了。
曹柠:
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说我要去西藏,要去找寻灵魂,大家会觉得他土。
林柳逸:
前两天看到一条豆瓣很有意思,说大冰就是我们当代的“凯鲁亚克”,因为所有人看了他的书之后都去了西藏。
曹柠:
我是看着大冰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后来那阵子他火了之后,出了一系列畅销书。其实他就是过着这种双重身份的人生,一个斜杠青年,一边在电视里做庸俗娱乐节目主持人,一边做一个特别有诗意情怀的民谣歌手。我觉得那是70后、90后对于浪漫的想象。但我们现在如果再去拉萨,再去丽江,其实已经找不到那个东西了,丽江现在已经完全威尼斯化了,都是外地游客。我觉得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远方变得多元化了。
林柳逸:
这两年我感觉海南、青岛、泉州、大理都特别火。你们觉得这些年远方的变化,它背后折射的是某种社会愿景的变化吗?
吴筱慧:
在我自己的想象中,我觉得以前大家爱去拉萨,现在是爱去大理,“去有风的地方”。好像以前是想要去找信仰,拉萨是类似于某种信仰一样的存在,现在去大理的话,更多的是想要寻求内心的宁静。
曹柠:
小时候我对远方的想象就是我爸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长城玩一玩,去西湖逛一逛,去兵马俑看一看。其实你看,这几个地方现在依旧是热门旅游地,只不过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就先去了。再往外就是去欧洲。但现在去欧洲都不流行了,现在应该是流行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非常的潮。这完全是一种阶级趣味上的鄙视链。这个假期我就刷到 3 个人去埃及,而且是同一天,我很想拉个群让他们认识一下。
林柳逸:
以前大家对于西藏的情结背后其实是有一种对精神性的强调的,那个时候正好是经济发展特别迅猛的一个时期,所以好像去西藏就意味着我要脱离这种城市的物欲、要净化心灵,要苦修。其实还是比较讲究一种自我磨砺的意志的,但是现在大家不会想要去自我磨砺了,生活已经太苦了。
方益:
我在想会不会是曾经我们想要追寻的那个信仰,后来被我们发现其实根本不存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开始质疑我们当时想追寻的那个东西存在的合理性。
林柳逸:
现在甚至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也被大家看得很低了,轻体力劳动为什么那么火?似乎大家开始意识到精神没有那么高尚,或者说世俗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神圣的。这个时代普遍存在一种将日常生活神圣化的趋势。就像安妮宝贝,她后来也不写西藏、不写灵魂净化、心灵求索之类的了,她开始写日常生活,写在长柄煎锅的反射里看到的彩虹。这种将世俗生活神圣化的趋势其实是不可抵挡的。
吴筱慧:
是的,大家都放弃了宏大叙事。
曹柠:
诗和远方,这不是高晓松说的吗?高晓松曾经在节目里讲他去意大利的一次经历,他当时要开车去某一个地方,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导航,所以他开错了,然后刚好就意外地到达了一个他小时候在歌里唱过的地方。特别浪漫。但他觉得这种美妙的意外在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技术决定了我们不会走错路,而且我们一定是做好攻略的。网友们已经告诉你哪边不值得去,哪边要避雷,没有人会说我一定要往雷坑里跳,但是雷坑里就未必没有好东西,我们其实是在错过一些意外的乐趣。
林柳逸:
不变的是,大家一直在强调亲近自然,但其实亲近的方式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向往西藏的那个时代,大家对自然的憧憬是希望有一个比我崇高、比我宏大的东西来战胜我、征服我,但是现在是我要征服这个自然,或者和谐共处。比如很多的中产家庭也开始意识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在大理办私塾、搞新式教育,但这种跟自然的亲近模式已经不再是那种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了。
林柳逸: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两年中产家庭涌入大理的现象的?包括现在的很多乡村建筑,网红建筑,一开始都是为了便利当地村民,到最后都变成当地人根本住不起的网红地,你们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曹柠:
其实我们在东北旅行就是这样,你看到俄国人来了,留下一堆东西,日本人来了留下一堆东西,我们的共和国留下堆东西。到现在为止那些东西都成了遗迹,然后被有乐天精神的当地人重新塑造。所以我并不觉得一定要西风压倒东风,有一个绝对的正确,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可以不要总是推倒重来,而是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文艺复兴到现在,大家对天主教有那么多的不屑,可是当你站在那些天主教的伟大遗迹面前,你依然会赞叹。你知道这些都是当年的罪恶,这都是花了几百年,死了不知多少人修成的。可是你依然会赞叹,这是一个集体的结晶。但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变成一种过度内耗式的建设,我们创造,然后推平,然后再重来,最后就是一片荒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节目中提到的书籍】
《旅行的艺术》阿兰•德波顿
《看不见的城市》伊塔洛•卡尔维诺
《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
《那不勒斯四部曲》埃莱娜•费兰特
《孤独星球》杂志
《游客凝视》约翰•尤瑞
《世界》简•莫里斯
《繁花》金宇澄
《中国三部曲》何伟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
《冈底斯的诱惑》马原
《浪的景观》周嘉宁
【节目中提到的导演与电影】
《路边野餐》
《大象席地而坐》
安东尼奥尼
费德里科•费里尼
伍迪•艾伦
埃里克•侯麦
侯孝贤
杨德昌
【本期配乐】
伤心欲绝——《台北流浪指南》
欢迎大家扫码添加“涟漪效应”微信小助手,进入涟漪效应听友群,在群中与主播畅聊热点话题,您的想法也有机会呈现在节目内容中,群内还有不定期的嘉宾空降与抽奖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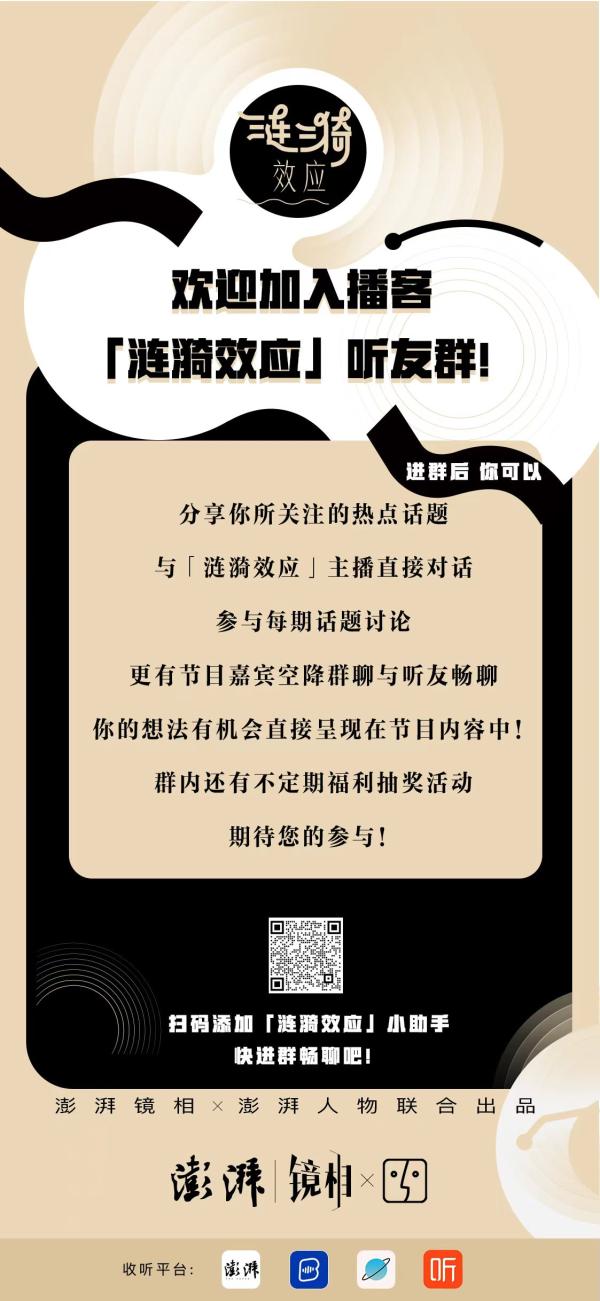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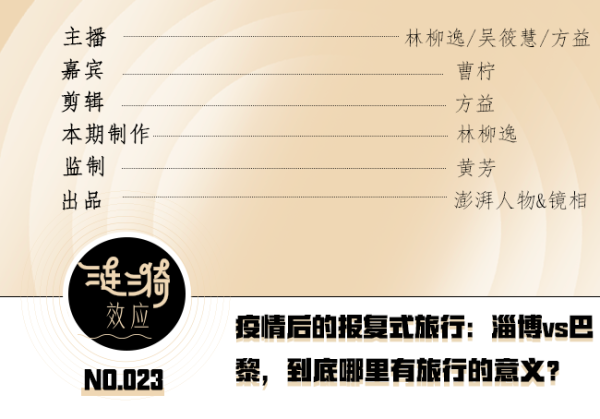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