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魔术师》:聚焦那些被变革之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人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以文学巨擘托马斯·曼为主角的长篇新作《魔术师》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边远小城吕贝克拉开帷幕,男孩托马斯·曼在那里成长,父亲保守,受礼教约束,母亲来自巴西,迷人而难以捉摸。年轻的曼向父亲隐瞒了他的艺术抱负,向所有人隐瞒了他的性取向。他被慕尼黑最富有、最有教养的犹太家庭吸引,娶了这家的女儿卡提娅,生了六个孩子。

托马斯·曼与家人
在意大利度假时,曼对在海滩上遇见的一个男孩产生渴望,并写下《死于威尼斯》的故事。陪卡提娅在瑞士疗养时,他又迷惑于使人无法离开的高山氛围,写下《魔山》。他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反复期待他的政治表态。他逃离德国,前往瑞士、法国,再到达美国。他的漂泊最后结束于苏黎世以南的基尔希贝格。
如《泰晤士报》所评,《魔术师》不是传记,而是一部艺术作品,是对一个变革世纪的情感反思,聚焦了一个努力站稳脚跟但被变革之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人。
科尔姆·托宾致读者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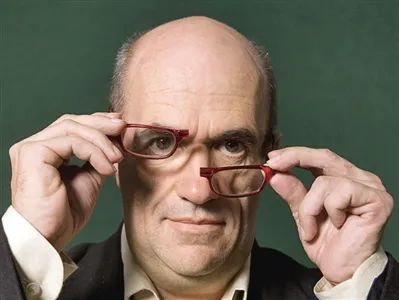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
我在1996年为三部托马斯·曼的传记写了评论。我了解他的作品,但在读这些传记以及曼的日记之前,我对他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我发现他一直在思考一种他得不到的生活。托马斯·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国人,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1912年《死于威尼斯》出版时,没有人想到它来自真实的欲望和真实的事件,那发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时。
后来我读了曼的妻子卡提娅所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是一个对丈夫了如指掌的人。她回忆了1911年旅居威尼斯期间,曼对酒店中一个客人的痴迷之情,她明确写道,她的丈夫“把他从这个迷人的男孩身上得来的愉悦感,转移给了阿申巴赫(小说主人公),并将之风格化为强烈的情感”。

正如曼把他的生活运用到小说中,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点运用到我笔下的曼夫妇之旅中。我把他们放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中,观赏提香的《圣母升天图》,然后带他们去斯拉夫的圣乔治会堂,那里挂着卡尔帕乔的画。我让曼站在我站过的空间里。我用切实的回忆来支撑写作。
1911年托马斯和卡提娅行走于威尼斯时,不可能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希特勒的崛起、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于威尼斯》似乎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字里行间我们能听到一种病弱而优美的音乐、一种渴望感、一种腐朽的气息,以及南北欧之间的鸿沟。这些要素都将在后来的悲剧中发挥作用,在这场悲剧中,世界以托马斯和卡提娅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科尔姆·托宾
选
读

1955年,托马斯·曼和夫人卡蒂娅在苏黎世湖边花园里
在酒店花园的一头,有一处遮阴的地方,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卡提娅和他时常在那用午餐。他们离店前一天,她让他独自吃饭,说她约好了要去见一个裁缝,埃丽卡也要去看牙医。
他坐在桌边,打破寂静的只有鸟雀清亮的啁啾声。托马斯突然想到,这是被人发现晕倒在地的绝佳时机。他笑着想,他穿戴着最好的西装领带和最新的鞋,很适合这一场合,假如被担架抬走,场面一定别具一格。
他闭了一会儿眼,听到有人过来时,他睁开眼。他看到来者是笑容灿烂、手拿菜单的弗兰兹尔,立刻意识到卡提娅和埃丽卡干了什么。莫奇曼一定插手了。他心想是谁付的钱,他希望站在他面前的侍者是从阔绰的莫奇曼那里得了好处。
“我在想你。”他说。
他说话声很轻,希望自己显得温柔。“我想和你保持联系。”他又说。
“我受宠若惊,”侍者说,“希望不会给您添麻烦。”
“我住在这里,最好的事就是遇到了你。”“您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片刻间,他们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彼此。
“我想您一定饿了,”弗兰兹尔说,他脸红了,“今天我们有很好的通心粉,是酒店的一位意大利厨师做的。还有一种特别的温巴赫酒庄的白葡萄酒。您的妻子告诉我您喜欢这个。或许先来一道冷汤?”
“只要你推荐的都好。”托马斯说。
接下来两小时,侍者来来去去,每次来都逗留片刻,他说起了他的父母,聊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冬天时,他战栗起来。
“我怀念在那里滑雪,”他说,“但我不怀念那种酷寒。这里也冷,但没有老家那么冷。”
托马斯对他谈起了加利福尼亚。
“我想去看海,”弗兰兹尔说,“在沙滩上走走。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加利福尼亚。”托马斯忽感悲伤,他就要离开酒店了。“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
托马斯抬眼看了看他。这个问题似乎全然无心,但弗兰兹尔显然多少对他的感情有所领悟。他迟疑着,并非因为他在那一瞬间想到他俩能一起去他的房间,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所能得到的全部,这短暂、虚构的亲密感。
他是一个被服务的老年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会回忆弗兰兹尔转身时的身形。
“不,我不需要别的了,感谢你的服务。”他说,语气刻意地郑重。
“您一定记得,我随时听候您的差遣。”弗兰兹尔回应托马斯的语气说道。

《死于威尼斯》海报
他鞠了一躬,走出他们单独相处的地方,在午后斑驳的阳光下,托马斯目送他离去。他想,他会在此多留片刻,他适才所处的场景,此生再也不会重现。
如今,在两年后他津津有味地回顾那段相遇,比写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小说更来劲。他仍然回味着每一个瞬间,回想着说过的每一句话,试图重构他俩那段短暂时光中的关系。他想,到了他这把年纪,尚有如此强烈的渴求,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他再次翻阅日记,读到一段上次写的内容。“午餐时,那个魅惑者好几次出现在附近。给了他五法郎,因为昨日他的服务很周到。”
“他道谢时眼中的笑意令人销魂,难以描摹。脖子很重。卡提娅为了我的缘故而与他友好。”
他相信,在将来这些日记不会有太大用处。一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上午将会花费在写小说上,而弗兰兹尔远在千里之外,他对自己的记忆已经开始消散。虽然当托马斯构想他穿过酒店大堂时的步伐,他的优雅仪态和笑容时,仍然感到愉快。
他一见到莫奇曼为他们找到的房子时,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房子了,它位于苏黎世南边的基尔希贝格。如果他们能定下来,他的漂泊就到此结束了。他曾有过担忧,在他身后,卡提娅将去何处生活。如今这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位于公路上方,眺望湖面和远处的群山。
在新房子里,他的日常作息不变。他后悔曾对瑞士有过不好的想法,因为如今在这个秩序井然、文明礼貌的村子里,他感到心情舒畅。同样令他惬意的还有湖上变幻的光线,朝他们缓缓飘来的远山的暮色。
他渐渐爱上了他的小说主人公菲利克斯·克鲁尔,就像他从前爱上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还有托尼·布登勃洛克和小汉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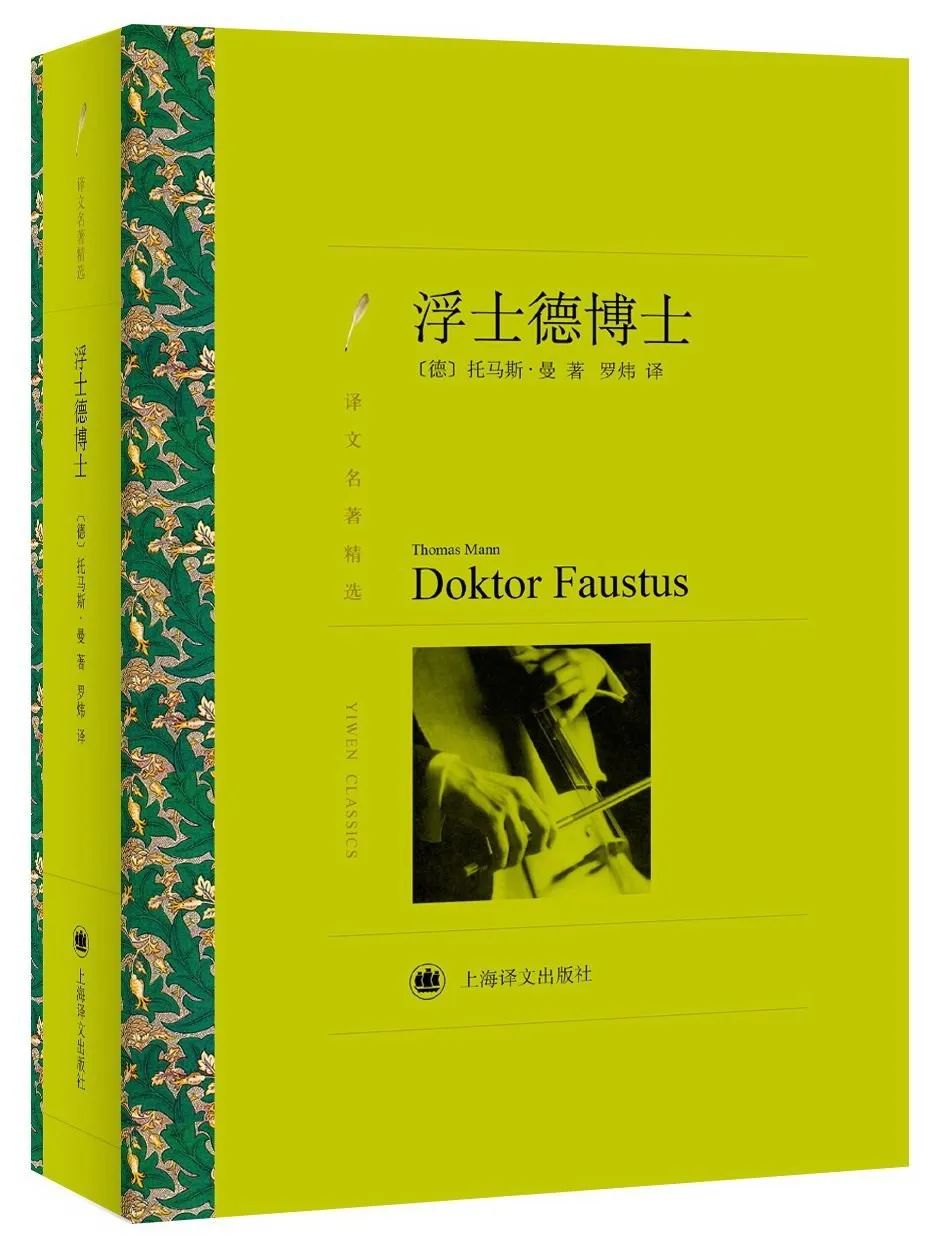
[德] 托马斯·曼 著|罗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读者们也许猜测汉诺带有自传性,也看出了作者与《浮士德博士》中的作曲家之间的共同之处,但无人猜得到他与菲利克斯·克鲁尔是多么气息相通。克鲁尔对世人玩的精密的骗局,不仅仅取材于那些关于骗术师的小说,更是托马斯驾驭自身经历和自我创造,并将之转为一个笑话的方式。克鲁尔善于逃跑,他总是能得手并脱身,总想从不谨慎的人的口袋中偷东西。
当他要买基尔希贝格的房子时,他与卡提娅去了苏黎世,从下车步行到律师办公室的一段路上,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任何一个注意到他的人,看到的都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穿着一丝不苟,步伐稳重,气度尊贵。他带着一张价值相当于房价的银行支票。他育有六个孩子,他所娶的女子能厉害地与房主就留置的设施和车库的安排商量细节。他著有多部文风精致的书,不惧长句和许多旁白,随手拈来德国众神殿中的名人。以任何一种标准来度量,他都是一位伟人。连他的父亲都会对他敬畏三分。
然而在律师办公室的洗手间里,当他面对自己上了年纪的面孔时,感到看到他样子的人不会感到敬畏。他们只会困惑,为他在镜中对自己流露调侃的眼神,还有一闪而过、了然于心的狡猾笑意,仿佛他和他的菲利克斯·克鲁尔一样,再一次高兴自己被戳穿了。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郁郁地想到,住在房子里,就损失了许多与英俊侍者们接触的机会。这时他启用了自身经历,把菲利克斯·克鲁尔写成许多冒险故事中的大酒店侍者,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相貌和制服相当满意,一有客人进来,他就满面春风地上前招呼,为女士们拉开椅子,递上菜单,斟满酒杯。他甚至可以让他英俊的男主角与一位住在酒店中的苏格兰贵族来一段幽会,苏格兰贵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正如托马斯被弗兰兹尔那样。
正如阿诺尔德·勋伯格相信自己会死于某个月的第十三天,他就死于那天,托马斯也相信自己会在七十五岁那年过世,但他没死。于是他把后来的岁月视为某种馈赠,犹如得了一个机会,半只脚踩在时间之外。在书房中,当他寻找某一本书时,他可以轻易地处身于波琴格街,或普林斯顿,或太平洋帕利塞德。
到了下午,风安静下来,湖水随之暗沉,山间蓝灰色的光变得明亮,他寻思着自己是不是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死了,这里只是死后的一段插曲,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能再次见到欧洲,再度拥有一栋房子,然后他渐渐消失,不再有梦。
他从没想过自己能活到八十岁。海因里希在七十九岁生日前过世。维克托死时五十九岁,他的父亲五十一岁,母亲七十一岁。但岁月不知不觉间过去。在他八十岁生日前的十二个月中,埃丽卡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策划着如何庆祝他的生日。
他知道,有些作家认为公开庆祝生日是电影明星的事,他们瞧不起。可他曾被德国粗暴地驱逐,又被美国礼貌地送走,在他侨居的最后一个国家中,在万众瞩目下受人尊崇,他觉得很是不错。

托马斯·曼在柏林酒店 ,1929年
到了那天,他愉快地收到贺信,其中一封来自基尔希贝格邮局,这家邮局不得不处理堆积如山的邮件。如果他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想要飞越太平洋来贺寿,他也丝毫不觉讶异。
他也很高兴比他小一岁的布鲁诺·瓦尔特希望在苏黎世的皇家剧院指挥《弦乐小夜曲》为他祝寿。当他读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称赞“他的人生阐释了他的作品”,便想到了菲利克斯·克鲁尔,他不禁笑了,莫里亚克所知甚少。
他收到了法国总统和瑞士总统的祝贺信,便盼望西德政府也能这么做,可阿登纳将此事交给一个下级部长。
他想他在表演,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人面前充当自己的外交官,而不是本人。
在庆祝生日后的那段时间里,他还活着的孩子们——包括在卡普里把皮肤晒成栗色的莫妮卡——都住在基尔希贝格,他们忙着自己的事,有时不注意他。一天晚上,他说要早睡时,他们才关心起来,要他和他们再多待片刻。
虽然埃丽卡被她的母亲警告过,别和两个妹妹过不去,别打断她们说话,但她还是忍不住对莫妮卡说,不停地游泳和晒太阳,只会让她变得更蠢,她还对伊丽莎白说,在博尔杰塞过世后把两个美国出生的女儿留在菲耶索莱,只会让她们变得无国可归。她应该把她们带回美国。
“她们得有根。”她说。
“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伊丽莎白问。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德国人,”她说,“虽然这对我们没有好处。”
戈洛和米夏埃尔一如既往地小声讨论书和音乐。当托马斯也加入他们时,他发现无论他说什么,两个儿子都只想反驳他。他的四个孙辈找到了共同语言。他喜欢看他们彼此间勇敢地讲美式英语,但一有大人问他们什么,他们立刻切换成德语。弗里多现在十多岁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有趣。
在某些这样的夜晚,托马斯想,他们需要的只是克劳斯的到来。刚从一连串的文艺聚会上回来的克劳斯,筋疲力尽,头发凌乱,只想倒头一睡,但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争论欧洲的事,铁幕、冷战取代了法西斯的话题,让他浑身是劲。
托马斯知道自己快死了。当他腿部的疼痛加剧时,他先去看了村里的医生,开了些止痛药。医生写处方时,托马斯问他,这是否可能是比老年关节炎更严重的病。他看到医生抬眼看了看他,迟疑了一下。这个阴沉而不祥的眼神令他久久无法忘怀。
(《魔术师》[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柏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4月版)
原标题:《《魔术师》:聚焦那些被变革之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