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欧洲人的接触”与美洲原住民的人口衰减有何关联?
我想我一直是这样,
这就是我,
但现在我的力量不再。
我曾徘徊的大地,
那个地方,
听我说:
忘记我吧。
——丹·汉纳(Dan Hanna)作,哈瓦苏派(Havasupai)离别曲,引自布赖恩·斯旺(Brian Swann)编,《重见天日》(Coming to Light, 1994)
他们称之为“大灭绝”(the great dying),即混乱无差别地袭击了或年轻或年迈、互为朋友或敌人的美洲原住民的神秘疾病。疾病随同哥伦布一起航行的征服者们登陆。在几个世代内,罕见传染病就大量毁灭了印度群岛的原住民人口。1492年,埃斯帕尼奥拉(Española,圣多明戈[Santa Domingo]坐落于此)的人口约有100万。到16世纪20年代,只有极少数印第安人还幸存。麻疹和天花是罪魁祸首,通常因呼吸系统疾病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美洲原住民群体都不具备对这些旧世界致病生物的免疫力。
麻疹和天花的灾难像野火一样席卷加勒比。由于历史的偶然,我们得知一名参与围攻特诺奇蒂特兰的黑人征服者在1520年把天花带入墨西卡。一场流行病迅速扫荡了被包围的城市。毁灭性的天花流行病一次次肆虐中美洲,大量削减印第安人口。数字可以为它们自己发声。1519年,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口约有1100万。1540年,经谨慎计算的估值把人口数定位在640万。到1607年,当地印第安居民的人口不足一个世纪前的五分之一。多达14种的主要流行病扫荡了中美洲,或许在1520年至1600年间全秘鲁有17种,这进一步把人口减少了79%至92%。
对于与欧洲人接触后美洲原住民人口减少的程度,我们掌握的确切数据很少。一些有效数据来自对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长时段人口统计研究。超过31万印第安人在1769年西班牙殖民时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到1830年单是沿海人口数就从72000减少至18000。1900年,仅仅2万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幸存,低于欧洲接触前时期人口的7%。这些灾难性削减中有很多可以归咎于西班牙的“缩减”(reduction)政策,它把数千分散的印第安人圈进靠近天主教传教团的拥挤定居点,他们在那里很快受到陌生疾病的侵袭。
评估人口衰减
回溯至16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就疾病造成的屠杀谴责西班牙当局时,关于传染性疾病和美洲原住民的全部议题被情感所阻碍。这个“黑色传奇”被西班牙愤怒地否认,今天仍时而浮出水面,就像它在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时出现的那样。这里存在着关于人类学的巨大争议之一:传染性疾病在美洲原住民的人口减少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杰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等人提出疾病在最初接触后的早期几十年扮演了相对不重要的角色。然而,流行病确实在持续交往后减少了美洲原住民人口。克罗伯认为对这类人口的最初普查反映出在衰减发生之前人口总量为900万人。
相反地,人类学家亨利·多宾斯(Henry Dobyns)、历史人口学家舍伯恩·库克和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设想传染性疾病甚至在隔离群体时期也发挥影响,可能在早于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实际接触的几百年前。所以,即便是最早的接触后的估值也反映出人口比前哥伦布时期的水平缩减高达95%。多宾斯已经提出15世纪早期印第安人口数高达1800万,远高于克罗伯的原始估算。他认为文献所载的1520年特诺奇蒂特兰的流行病,事实上是在群落之间传播直至加拿大,并且向南至智利的普遍流行性疾病。因此他提出,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征服者们行进至他们安第斯王国的心脏时,印加帝国的人口最多有十年前的50%。因此,“欧洲人的接触”不是身体上的对抗,而更多的是微生物的接触及随后人口减少的过程,这通常发生在外国人到来很早之前。
不同于克罗伯,多宾斯在估算原住民人口时从不保守。身体接触前已有人口衰减的确切事实意味着,最初的人口普查反映出不稳定的人口已在适应新环境。多宾斯及其同事立论于结合历史记载和源自人口统计计算的人口减少比例,这两者均非完全可靠。
考古学家安·拉梅诺夫斯基(Ann Ramenovsky)已经评估了克罗伯和多宾斯的假设。她指出多学科方法和新的考古资料都毋庸置疑地表明,持续的文化变迁远早于欧洲人的接触就在所有人类社会展开。例如,威斯康星大学考古学家赫伯特·马施纳已揭示了东南阿拉斯加的海岸社会如何在远早于欧洲人抵达时就达成了文化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的程度在几个世纪间显著波动,反映在定居模式从非常密集的村庄到分散的、通常是防御性定居点的变化上。
拉梅诺夫斯基用考古记录所反映的文化变迁模式来评估人口衰减,独立于民族志或历史记述。她用综合的定居数据测算人口变化以检测一个单纯的考古学假设:“美洲原住民是否经历了直接随欧洲人接触而来的人口暴跌,但是早在文字记录和遭受殖民之前?”她研究了北美洲的三个地区:密西西比河谷下游、纽约州中部和密苏里河谷中部。这个研究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她必须面对不充分又偏倚的考古样本,有关房屋和定居点规模的定量数据的缺乏,还有区域覆盖范围的空白。但是她能够展示考古和历史材料如何证明16世纪——在德·索托(de Soto)探险之后和17世纪晚期法国殖民之前该区域内原住民人口清晰而骤然的减少。
易洛魁“五族同盟”(Five Nations of the Iroquois)在历史时期的初期占据纽约州北部的芬格湖群地区。拉梅诺夫斯基使用定居地和房屋顶部面积数据来证明17世纪易洛魁人口大量缩减。历史文献支持并扩充了16世纪和17世纪人口骤减的考古记录。它们记录下激烈重组的定居地,以及多家庭长屋寓所和早期几世纪间加筑防御工事的群落的最终崩溃。
北方平原的密苏里河谷中部地区见证了肇始于1540年的欧洲人接触,以及三个世纪后永久的殖民。源自大规模流域调查的考古学资料记录了至晚在17世纪原住民定居点模式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与欧洲贸易商品在本地考古遗址的首次出现同时发生。不幸的是,拉梅诺夫斯基的数据没有透露人口衰减是否早于外国贸易物品到达密苏里中部。拉梅诺夫斯基的所有研究趋向证实多宾斯的理论,即人口学上的灾难早于欧洲人大量汇入北美数十年,并且在一些地区早了数世纪。拉梅诺夫斯基估计了北美在欧洲接触前的原住民人口数有约1200万,一个比多宾斯的数据更保守的估算,但是远高于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及其同代人的估计。
人口减少的原因
出于一些尚不明确的原因,新大陆没有与欧洲疾病对等的事物。可能的是,当数量很小的原住人口在数千年前移民到美洲时,寄生虫就被北极圈的温度杀死。此外,严重疾病的存续依赖于被感染个体的持续接触,比如发生在紧密聚集处、小镇和大型村落等长久定居地。北美洲,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中南美洲,缺少欧洲和西亚那样密集的城市定居地,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在那里的城市人口中被固定下来。然而从遗传学角度看,相对同源的美洲原住民在免疫上特别易受攻击。结果就是在那时未受欧洲疾病侵袭的人口中的过高死亡率。
流行病不均衡地传播。从一地到另一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和政治条件。征服者们在对黄金的肆意掠取中猛袭印第安人,奴役数千印第安人来挖掘金属矿藏并且为委托监护地霸占土地。1494年后,奴隶贸易加强。在16世纪早期,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奴隶被船从尼加拉瓜这样的地方运至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1560年,单单在巴西就至少有4万名美洲原住民沦为奴隶。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急剧下降。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把他们的帝国当作庞大的朝贡体系运行。食物供给和所有类型的货物流通依赖于高度有序的土地使用和商品分配系统。当如秘鲁高地和低地间建立已久的交换体系那样的系统随着西班牙的入境(entrada)而瓦解时,很多人陷入饥饿或流入增长中的殖民城市。传染性疾病再一次大幅暴发,成千上万人死亡。
在当地条件助长了传染病时,疾病如野火般蔓延,通常早于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实际的面对面接触。例如,在北美东南部,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于1540年埃尔南多·德·索托从佛罗里达到密西西比河那声名狼藉的探险。即便在那时,天花和其他疾病已经通过更早时期经过的到访者传播至内陆。在南卡罗来纳州塔洛梅科(Talomeco)的村庄,西班牙征服者看到数百具尸体被堆积在四所房子里。1583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海员在佛得角群岛感染了高度传染性的发热疾病,可能是斑疹伤寒。他们袭击了位于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的西班牙定居地,把病毒带上岸。数百名印第安人在由此导致的流行病中死亡。在北部的弗吉尼亚州,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作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注意到是怎样“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我们离开一个又一个……城镇,人们开始非常快速地死亡,并且很多是在邻近地区”(Crosby 1972, 117)。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外来疾病和西方贸易商品都早在欧洲人定居前渗透,在古老的、使用了数世纪的村与村间的道路传播。沿岸地区的流行病推进内陆,使所有村庄的人口减少,有时是当地人口的90%。幸存者常常死于饥荒,特别是疾病在种植或收获期袭来的时候。疟疾是一个早期杀手。易于传播疟疾的按蚊在欧洲人接触前就出现在美洲。一旦某人被传染疟疾并获得了对它的免疫,寄生虫就留存在他们的血液里。疟疾寄生虫可能通过藏匿于看似健康的黑人奴隶的血液来到新大陆。
这样大量的人口减少在文化意义上是毁灭性的,特别是因为疾病常常袭击社会中最年轻和最年迈的成员。老者在全部知识都通过口述代代相传的社会里,是有关文化经验的无价资源。这种知识常在数周或数月中销声匿迹。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血缘和宗教知识消失了,恰是在一个此类知识能以某种形式使人们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时候。在北美东南部,德·索托遇到了大型酋邦(chiefdoms),它们由主持着相当大的群落和很多村庄的酋长统治。随后的流行病的影响将会使至今强大的酋邦分裂成更小型的社会。很多人从其家乡逃离,试图逃避传染,导致了覆盖广泛地域的大规模政治和社会破坏。
流行病不仅增长了死亡率,它们也影响了出生率和美洲原住民从人口危机中恢复的能力。很多传染性的疾病诱发了流产的频发并增加了怀孕女性的死亡。在小型群落,失去妻子和受文化约束相对少的潜在婚姻伴侣可能减缓了生殖率。伴随着婴儿死亡的高发和灾难性死亡率所致的情感压力,即便是暂时性的生殖率断层都可能会威胁维持现有人口所需的高出生率。在很多地区,生物学的和文化的幸存是种例外而非常规。
(本文选自《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美]布赖恩·M.费根著,乔苏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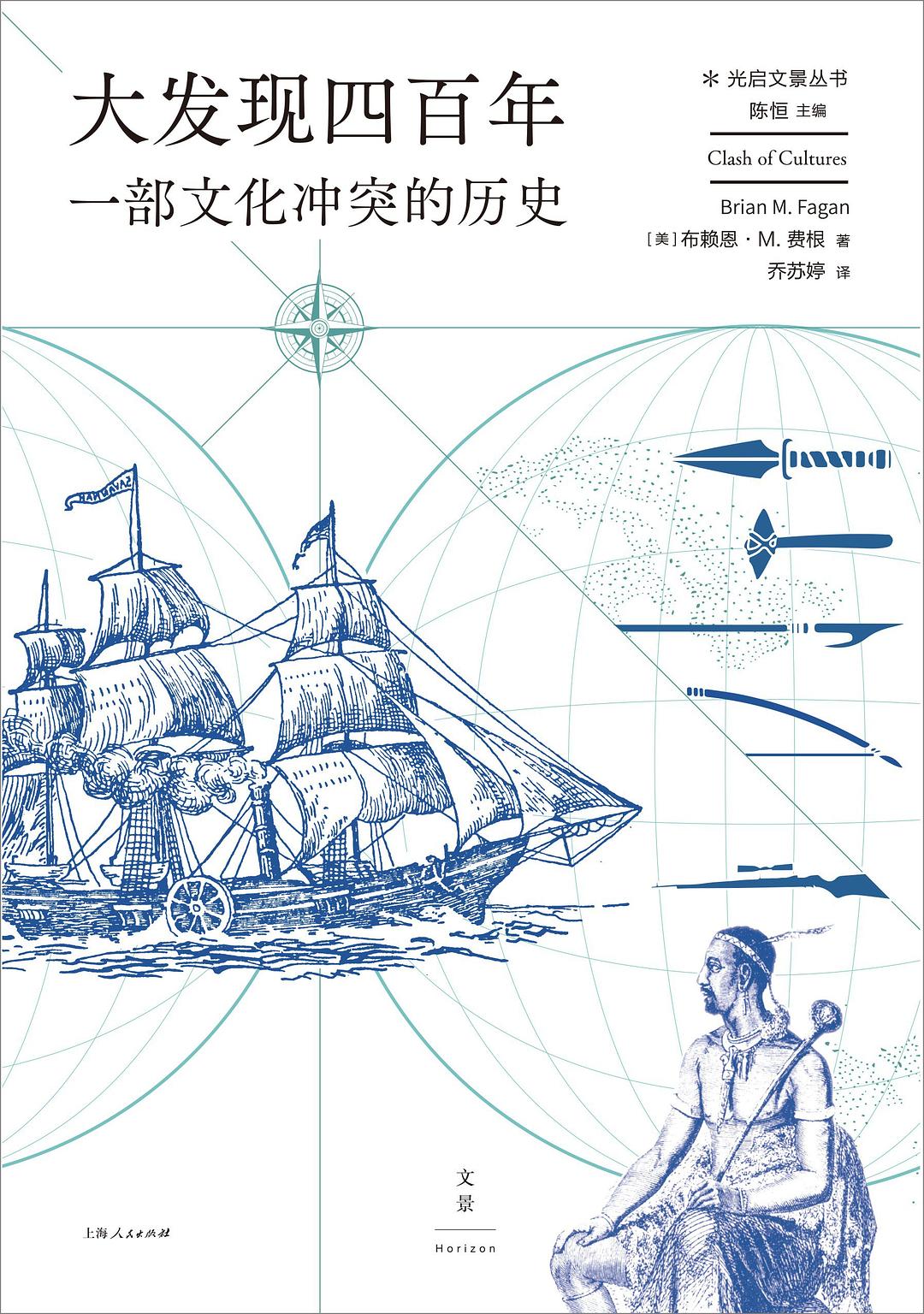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