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诗歌是一种挖掘
今天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39 — 2013)的诞辰。
希尼生于爱尔兰北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十分赞赏祖辈为农场献身的精神,并将其灌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笔为犁,挖掘生活与现实的诗意。
1995年,希尼因“其作品饱含抒情之美以及对伦理的深刻理解,凸显了日常生活的奇迹和历史的现实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4.13 — 2013.8.30),爱尔兰诗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1.
诗歌作为一种挖掘
打算沿着某些原路,折回威廉·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所称的“匿藏地”:
我力量的匿藏地
似乎开着;
我接近,然后它们关上;
现在我隐约瞥见;当年纪渐老,
可能也就完全看不到了,而我将赋予,
在我们还可以的时候,只要文字还能,
赋予我那些感受以实质和生命:
我将珍藏过去的精神
供未来恢复。
在这些诗句中,隐含一种诗观,而我觉得这诗观也隐含于我所写的几首使我有资格讲话的诗中:诗歌作为悟性,诗歌作为自我对自我的启示,作为文化对自身的恢复;诗篇作为延续性的元素,带着考古学的发现物那种气息和确真,也即被埋葬的碎片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被埋葬的城市的重要性而减小;诗歌作为一种挖掘,为寻找发现物而进行的挖掘,那发现物竟然是暗藏之物。

事实上,《挖掘》是我写的第一首我自己认为把感觉带入文字的诗,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认为我的直感进入了文字。它的节奏和噪音现在依然使我喜悦,尽管诗中若干句子更多是有职业枪手的戏剧性而不是有挖掘者的聚精会神。
我是在1964年夏天写出这首诗的,差不多是在我开始“涉猎诗歌”之后两年。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做到不只是安排文字的地方:我觉得我把一支矛插入真实生活中。诗中描写的事实和表面都是真有其事,但更重要的是,由命名它们而带来的兴奋给了我某种气定神闲和某种信心。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它有点使我吃惊,吃惊于它竟然产生一个我会密切注意的立场和理念:
马铃薯霉的冷味,走在湿泥炭上的嘎吱声
和啪嗒声,切下活根茎的短促刀声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干活的铁铲。
在我的食指与拇指之间
夹着这支粗短的笔。
我要用它来挖掘。

如我所说,我是在多年前写下它的,然而也许我应该说,是我把它挖掘出来,因为我意识到甚至早在我写下它之前,它就已在我身上藏了很久了。笔/铁锹的类比是问题的核心,也很简单,无非是一个近乎谚语式的常识问题。在来往学校的途中,常常遇到有人问你上的是什么课,你当天挨了几个巴掌,而他们最后总是无一例外地告诫说,继续读书吧,因为“读书容易”“笔比铁锹轻”。
而这首诗无非是允许这枚智慧的花蕾脱落,尽管在该脉络里重要的一点是,我写这首诗时心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谚语式结构,也没有意识到这首诗只不过是重演另一个挖掘的隐喻,该隐喻直到多年之后才又使我想起。不过,这却是我们上学途中说唱的节奏,并且如同我刚才说的,当时我们并未充分意识到我们在跟什么打交道:
“你的马铃薯干了吗?
它们适合挖了吗?”
“把你的锹插进去试试,”
脏脸麦圭根说。
这里,“挖”成为一个性隐喻,一个受启蒙的象征,如同把你的手伸入灌木丛里或端鸟巢,它是各式各样的自然类比之一,用来指揭开或接触隐秘的事物。现在我相信,《挖掘》一诗对我来说具有受启蒙的力量:我刚才提到的信心,来自一种感觉,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干写诗这活儿,而一旦体验到写诗的兴奋和发泄之后,我注定要一再去寻求这种体验。

02.
找到诗歌的声音
我不想使《挖掘》承载太多意义。它是一首大型挖土机似的粗纹理的诗,但它作为一个例子是很有趣的——不只是作为某位书评家所谓的“罗素广场里结满泥巴的手指”的例子,因为我并不觉得该题材本身有任何特别优点——它有趣是因为可作为我们所称的“找到一个声音”的例子。
找到声音意味着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感觉带入你自己的文字,意味着你的文字有你对它们的感觉;而我相信这甚至不是一个隐喻,因为一个诗歌的声音很可能与诗人的自然声音有非常亲密的联系,那是他写诗时听到的诗句的理想讲话者的声音。
那么,你如何找到它呢?在实践中,你听到它来自某个别人;你感到另一位作家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它流入你的耳朵,进入你头脑的回音室,使你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如此愉快,以至你的反应将是“啊,我希望这是我说的,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事实上,是这另一位作家对你说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你凭直觉就知道是你自己和你的经验之某些方面的真实发声的东西。而你作为一位作家的初步尝试就是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这些流入的、有神秘影响力的声音。

以这种方式影响我的其中一位作家是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在学校阅读霍普金斯的结果是想写作,而当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拿起笔写作时,流出的东西正是曾经流入的东西,常见于霍普金斯诗中充满碰碰磕磕的头韵的音乐、报道式的声线和弹跳的辅音。我记得一首叫作《十月思绪》的诗,在该诗中某些虚弱的田园意象在混合语体的锁子甲下沉没:
椋鸟看守茅屋,突来的燕子
直接冲向筑着泥巢、安卧家中的椽
越过沾满尘埃的干枯蜘蛛网,如同笑声
鬼影般缠住用沼泽橡木、泥煤草皮和柳条做的屋顶……
然后还有“天空色、李子蓝和荆豆带刺般金黄”和“羊栏里铃铛嘀嘀响的叮当声”
回顾起来,我相信存在着一种联系,介于霍普金斯诗歌声音那带有浓重乡音的辅音噪音与北爱尔兰口音独特的地方特色之间。虽然这种联系当时并不明显,但回想起来,却是非常真实的。另一位深受头韵法诱惑的已故诗人W.R.罗杰斯在其《爱尔兰特性》一诗中说,来自他的(以及我的)那个地区的人都是唐突的人民。
他们喜欢说话中尖刺的辅音
认为柔软的辅音是娘娘腔;他们在
管弦乐团里挖掘k和t音,在乐曲中
发现罪恶,在锡罐、摩擦音、通奸中
和断音的谈话中找乐趣,总之
任何或多或少是攻击的事儿,
像米克、塔格、补锅匠的崽子、梵蒂冈。

确实,乌尔斯特口音一般是断音的辅音。我们的舌头更多是敲击辅音的金属小片,而不是绕着元音的圆圈滚动——罗杰斯还提到“南方嘴巴里那饶舌的圆才能”。它是充满能量的、棱角分明的、锋利的,也许正是因为我的第一口音与霍普金斯的古怪之间这种契合,导致我最早那些诗成为它们那个样子。
当然,我不能说我已找到一个声音,但我找到了一个游戏。我知道这只是文字游戏,而我甚至没有胆量署上自己的名字。我把自己称为“Incertus”,意为没把握,一个害羞的灵魂在烦恼之类的。我爱上文字本身,却对一首诗作为一个整体结构一无所知,对一首写得成功的诗如何成为你生命中的踏脚石也毫无经验。那些诗是我们也许可称之为“试验篇什”的东西,是一些笨拙僵硬的小设计,模仿大师那些流畅交织的图案,是通往整个诗歌技艺的笨手笨脚的线索。
我当时正第一次有意识地雕琢文字,基于某种理由,作为历史和神秘性的载体的文字开始邀请我。也许这一切很早就发生了,因为母亲以前常常会背诵一系列词缀和词尾,以及附上英语解释的拉丁词根,这类押韵词都是她在20世纪初所受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也许是开始于收音机调谐度盘上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斯图加特、莱比锡、奥斯陆、希尔弗瑟姆。也许是由旧时英国广播公司天气预报里美丽的跳跃节奏引发的:多格、洛考尔、马林、设得兰、法罗、菲尼斯特尔;或由华丽而空洞的教理问答措辞引发的;或由作为我们家中强制性诗歌一部分的圣母马利亚连祷文引发的:金塔、约柜、天堂之门、晨星、病人的健康、罪人的避难所、受苦人的安慰者。
这些东西在当时没有一样是被有意识地细细品味的,但我觉得,我依然能够轻易地回忆它们,以及陶醉于它们的词语音乐,这个事实表明它们以某种将来可以在上面建筑的语言路基垫层的方式为耳朵打基础。

这是无意识的铺垫,但诗歌也包括有意识地细味文字。这是通过阅读诗歌本身来达到的,以及被要求去背诵一些诗,甚至一些警句,例如济慈的,来自《莱米亚》:
他的船如今
用黄铜色船头刮擦码头石,
或华兹华斯的:
鞋底都装了钢片,
我们在锃亮的冰上咝咝滑过,
或丁尼生的:
老紫杉,抓住了刻着
下面的死者名字的石头,
你的纤维缠着无梦的圆颅,
你的根茎绕着骸骨。
这些诗行都是摘自我在学校最后几年所学的诗,它们有点像试金石,其语言能够引起你某种听觉上的小疙瘩。上大学时,我最初几周陶醉于遇见约翰·韦伯斯特喜怒无常的能量——“我要在他们的内脏里刻花刺绣/如果我有机会回来”——后来又碰上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的尖头石料,以及学习英语本身丰富的地层。唯有词语是确实好的。我甚至写了这些《给自己的诗行》:
在诗歌中我希望你会
避免那欢快的陈腐。
给我们有肉峰和强劲的诗吧,
用歌的皮带结紧,
那种在沉默中爆发的诗,
没有强制,没有暴力。
它的音乐强劲又清晰又有效
像锯子在晒干的木材里嗡嗡响。
你应尝试具体的表达,
半猜测,半表达。
啊哈。在这背后,是麦克莱什和魏尔伦的《诗艺》,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一知半解)和几篇关于“具体实现”的批评文章(我和别人写的)。在大学,我与这整件事情若即若离,为凑热闹而读诗,也为文学杂志写了五六首。但我内心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经验。没有顿悟。全是技艺——而且也没有多少技艺可言——而没有技术。

03.
哽噎找到思想,思想找到词语
我认为,技术是不同于技艺的。技艺是你可以从其他诗歌那里学到的。技艺是制作的技能。它可以在《爱尔兰时报》或《新政治家》的比赛中获胜。它可以施展而不指涉感觉或自我。它知道如何保持有力量的语词体育运动表演;它可以满足于“除了声音什么也没有”,但不是“找到一个声音”这个意义上的声音。
学习技艺是学习转动诗歌之井的辘轳。通常来说,你开始时,是把水桶放到井里半途,然后吊起一桶空气。你是在比手画脚模拟真活,直到有一天链索突然拉紧了,水桶沉入水里,而这将继续诱使你回头再来一次。你将打破你的自我之池的薄层。你的马铃薯将会“适合挖”。
在这个关头,便可以谈论技术而不是技艺了。我愿意把技术定义为不仅包含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格律、节奏和文字肌理的把握,还包含定义他对生命的态度,定义他自己的现实。它包含发现摆脱他正常认知约束并袭击那不可言说之物的途径:一种动态的警惕性,它能够在记忆和经验中的感觉的本源与用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这些本源的手段之间进行调停。
技术意味着给你的观念、声音和思想的基本形态打上水印图案,使它们变成你的诗行的触觉和肌理;它是心灵和肉体的资源的全部创造力被调动起来,在形式的司法权限内把经验的意义表达出来。技术,用叶芝的话来说,乃是把“那捆坐下来吃早餐的偶然和不连贯”变成“一个理念,某种有意图的、圆满的东西”。

这确实是可以设想的,也即一个诗人能够拥有真正的技术和不稳定的技艺——我想,阿伦·刘易斯和帕特里克·卡瓦纳就是如此——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技艺到家却技术失败。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形象可以代表纯粹的技术,我会说卜水者。你无法学会用占卜杖探测水源或占卜的技艺——它是一种与隐秘而真实的存在物保持接触的才能,一种在潜藏的资源与想让这资源浮现和释放的社群之间调停的才能。如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在《为诗辩护》中指出的:“罗马人把诗人称为瓦底斯(Vates),意思跟占卜者差不多……”
写这首诗无非是平息一次兴奋和命名一次经验,同时在语言中赋予那兴奋和经验一次小小的永动。我在这里引用它,不是为了它自身的技术,而是为了诗中所包含的技术的形象。那占卜者在其与隐秘的事物接触这个方面,以及在其有能力把感觉到和触动到的事物表现出来的能力这个方面,都酷似诗人。
占卜者
从绿篱笆砍下一根有杈的榛树棍子,
他握住它V形两边的枝杈,
在地面上兜圈,寻找水的
精气,神经质但很专业地
不慌忙。精气现身,尖锐如螫针。
占杖猛地一动,准确地抽搐,
泉水突然通过绿榛树
播放它的秘密频道。
旁观者会要求让他们试一试。
他二话没说把占杖交给他们。
它在他们手中没动静,直到他冷淡地
握住他们期盼的手腕。榛树又颤动起来。
我青少年时代视为事实的东西,成了记忆中的奇迹。当我现在重读这首诗,我很高兴它以动词“颤动”结束,这也是整个神秘事件的核心。我也很高兴“颤动”(stirred)与“话”(word)押韵,使得“瓦底斯”的两个功能融为一个声音。

技术即是允许那围绕着一个词或一个形象或一个记忆的首次心灵颤动朝着发声的方向生长:不一定是以争辩或解释的方式发声,而是以它自身那能够进行音调和谐的自我再创造的潜力发声。这创造力的激动必须获允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中,用霍普金斯的话说,它才能够“自花受精,自我承担……叫道/我所做是我,为此我来”。
技术确保这第一道微光获得其应有的亮度。我的意思不只是指在用选择词语来生动地表现主题时的巧妙——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那么关键。一首诗可以风格有瑕疵而能生存下来,但不能以死胎生存下来。关键的行动是先于语言的,也即能允许那模糊或不完整地意识到的最初警觉或引诱去发展,让它作为一个思想、一个主题或一个句子去扩大和形成。
罗伯特·弗罗斯特这样描述它:“一首诗以一种哽噎、一种乡愁、一种相思病开始。它找到思想,而思想找到词语。”就我而言,技术更多是有生命力和有感知力地与“哽噎”找到“思想”这一最初活动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思想”找到“词语”联系起来。那最初活动包含占卜、预言、神谕的功能;接下来的活动则包含制作功能。像奥登那样说一首诗是一种“语言新发明物”,就意味着要在你的衣袖里保留一两道招数。

谢默斯·希尼诗三首
01
个人的诗泉
——给迈可尔·朗利
小时候,他们不能阻止我接近水井
以及带水桶和绞盘的老水泵。
我喜欢那黑暗的下坠,那被困住的天空,
那水草、真菌和湿冷苔藓的味道。
砖厂里有一口井,顶盖的木板都朽坏了。
我细味那丰富的碰撞声,当绳子
末端的水桶快速荡下。
如此深,你看不见水里的倒影。
枯竭的石砌水沟下有一口浅井
繁盛如任何养鱼缸。
当你从软腐叶层里拖出长长的根茎
便有一张白脸晃动在水底。
另一些有回声,用清新的音乐
把你自己的呼唤归还你。有一口
怪吓人的,因为从蕨草和高高的毛地黄里
窜出一只老鼠,掠过我的倒影。
如今,探入根茎,用手指挖黏泥,
像睁大眼睛的那喀索斯般凝视泉水
都有损任何成年人的尊严。我作诗
是为了看清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

02
给迈克尔和克里斯托弗的风筝
那整个星期日下午
一个风筝飞翔在星期日上空,
一个绷紧的鼓面,一个粗糠般褐色的飞掠物。
在制造过程中我看见它灰色而滑溜,
当它干透成又白又硬我轻敲过它,
顺着它的六尺尾巴我束紧
一串报纸做的蝴蝶结。
但现在它一会儿远在高处像一只黑色小云雀
一会儿缓慢移动,仿佛鼓胀的牵线
是一条湿绳被拉上来
准备拽起一网鱼。
我的朋友说人的灵魂
重量相当于一只鹬,
然而那停泊在上面的灵魂,
那跌下又升起的牵线,
其重量就像一条犁沟被迎入高天。
在风筝坠入林中
而这条线变无用之前
用双手抓住它吧,儿子们,去感受
悲伤那拨撩、扎根、长尾的拉力。
你们天生能做到。
站在这里,在我面前
承受那绷紧。

03
消失的岛屿
当我们以为给自己打下永久的基础
在它的蓝色群山和那些无沙的海滩之间,
那里我们在祈祷和守夜中度过难熬的晚上,
当我们捡来些漂流木,做了炉床,
把我们的大锅挂在它的苍穹里,
岛屿便在我们脚下破碎如海浪。
支撑我们的土地似乎只有当我们
在绝境中拥抱它时才是坚固的。
我相信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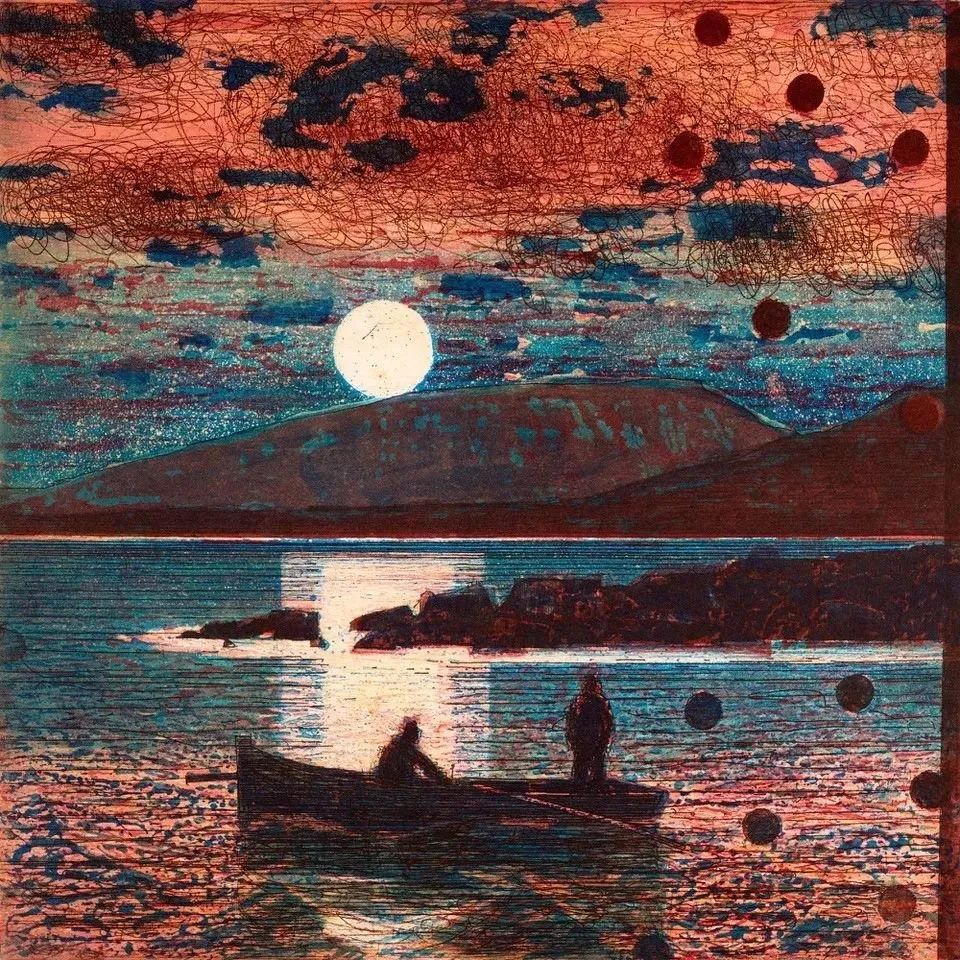
文字丨原题《把感觉带入文字》,选自《希尼三十年文选》,[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 著,黄灿然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诗选自《开垦地:诗选1966—1996》,[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 著,黄灿然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片丨Photo@Niall Naessens
编辑 | Stella
原标题:《诗歌是一种挖掘》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