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街角社会︱知识分子费孝通

2000年春,青年社会学者李友梅等人,与年近九旬的费孝通有过一次三天的长谈。
费孝通说:“我在专家局时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李维汉(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说就是你提出之后,里面觉得要搞知识分子问题,搞大了,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
女儿费宗惠纠正他:“其实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清华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才是公私合营。肃反-改造-合营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把时间弄颠倒了。你再提出知识分子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了。他们说你是改良主义。 ”
但费孝通坚持。
“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
一
1948年早春,在西南联大,费孝通想做的实地研究工作停滞了,他和好朋友历史学家吴晗商量从头学起历史,就召集了一批同仁讨论,并开设“社会结构”课程。
讨论班中,他发表《论知识阶级》,这是费孝通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系统思考——传统知识分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懂自然知识,但却是掌握着规范知识的人。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是“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盛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
而当西学随洋人轰开中国的大炮流入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公式被建立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受到挑战。对此,费孝通给出答案,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打破知识成为阶层的旧形态,让知识分子把知识和技术“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清华大学。国民党派了两架飞机接北平的知识分子去台湾。政权易手之际,费孝通选择留下。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忠诚的批判者”(loyal opposition)。他对访华的美国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说,希望能“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批评共产党——在他觉得有必要提出批评的时候”。
之后,费孝通作为民盟代表被邀请至河北西柏坡——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西柏坡,费孝通见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共产党领导,向民主党派代表张东荪、费孝通(民盟),雷洁琼、严景耀(民进),表达了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的想法。
毛泽东很健谈,他描绘的新政权对现代化国家的构想深深打动了费孝通。与对蒋介石的厌恶不同,费孝通对毛泽东几乎是赞不绝口的。“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也是这一年,成为费孝通人生的一根分界线,他经历了深刻的思想变革。
变革从一幅画面开始:在去西柏坡的黄土平原上,乡民组成的粮队在黑夜中蠕动前行,插着一面单薄的旗粮车没有枪兵看守。只是默默地赶往前线,悄无声息地走出一行红星。
这个场景令费孝通获得了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人民的力量是“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是“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的力量,而反观知识分子,“大言不惭,自以为秀才闭门而知天下事了”,他看到了自己的“懦弱”。
受到了震动的费孝通主动要求改造知识分子,因为“不改是不行的”。对于改造的方式,他曾挣扎良久,最后悟出: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
与Robert Redfield分开半年后的信中,那个原本信心满满做“批判者”的费孝通不见了,代替的是,“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
如此快的转变令人不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曾传达:不少知识分子力求跟上国家前进步伐的一种主动尝试,终归到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时几乎一致相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者,固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但也不是他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成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清廉、经济复苏,并有希望大举加速工业化进程,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共产党。”
知识分子是贯穿了费孝通一生的主题。他反复提醒自己是“五四之子”,是 “后五四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
二
1927年,费孝通17岁。那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捕杀共产党员。校园里,参加运动的同学被国民党扔进长江。费孝通深受参加运动的兄长和五四左翼文学的影响,对国民党痛恨至极。
1927年的费孝通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他身体不好、走不大动路,参与革命的方法是拼命写“大字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还我河山”。等到校长依着笔迹找来时,费孝通只得转学北上,来到司徒雷登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
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和五四思潮帮助民国的学子们完成了启蒙,再至救亡的思想转变。“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
回顾前半生,费孝通感到奇妙:“这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经历, 而是历史决定的。我这样一个人,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这样一个时代, 经历这样一番变化。”
费孝通家住江苏省吴江县城富家桥弄,祖上是个有名望的乡绅世家。但到了祖父一辈时,家道中落,费家几百亩稻田慢慢被出售不剩。
当时的乡绅,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江南绅士阶层在朝堂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祖父去世时,将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托付给了一个镇上有名的读书人杨敦颐。
杨敦颐的一生带着典型的旧知识分子色彩,他从儒学基础转至接受西方思想,1912年编辑了辛亥革命作品文集。杨敦颐极重视教育,女儿杨纫兰就读上海务本女校,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后与养子费璞安成婚。
费璞安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举,吴江县送他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应张謇邀请任教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清王朝最后一年1910年,第五个孩子呱呱落地,费璞安授“孝”(世交张謇的孩子“孝”字辈)和“通”(通州)字以纪念。费孝通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没读过三字经,学算术、拉手风琴等实用学科。

1930年-1938年,从燕京大学到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毕业的八年里,费孝通的学谱形成了一个可观的链接:在燕大三年,他和吴文藻、潘光旦等中国社会学大家交好;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世界级人类学大师史禄国;1935年,费孝通考上公派留学,带着庚子赔款的钱前往英伦来到功能派奠基者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门下。

1939年,《江村经济》的出版使费孝通在全球人类学界名声斐然。作为马林诺斯基的得意门生,偏远的土著部落却唤起不了费孝通的兴趣,他的目光集中在中国,想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了解和改进自己的社会。
在伦敦的费孝通每日上午花半小时读《泰晤士报》上的议会辩论提高英语,晚上沿着安静的泰晤士河散步,大部分时间在思考中国问题,费孝通仍然频繁与国内联系,给天津的《益世报》写文章。费孝通曾坦言,自己并非从兴趣出发学的社会学,而更愿意看作是一种责任——“一个士兵进入战斗后,不能仅仅因为他不喜欢打仗而放下武器开了小差。”
1938年秋,费孝通博士毕业后赶着回国。当客轮从伦敦起航时,彼岸的中国战火纷飞。费孝通来到云南时,半个中国已沦陷了。
三
抗战后,云南边陲的教授们穷得要命。
云南大学教授费孝通家里的米不够了。坐在云南大学下面的茶馆,费孝通摆着摊头写文章,哪家杂志要文章就去茶馆寻他,文章次日见报。
《观察》是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创办人储安平向老师潘光旦要人写文章创报,与同乡同龄同是伦敦回来的费孝通一见如故。储安平有市场头脑,出手阔气,知识分子对他买账。
虽然贫困,但费孝通关心时政,笔力通透,挥斥方遒,月稿量高达5-8篇。四十多年后,费孝通回忆起来,仍能联通上那份乱世中的兴奋感:“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

学者谢泳将《观察》的撰稿人中分为三类人:储安平企图通过办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钱钟书对政治完全看透,钟情学术;而费孝通则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
1945年末,国民政府的军队冲进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正轮到费孝通做“反内战讲演”,子弹飞过他的头顶,他高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人是学生拥护出来的民主教授,同时也写进了特务的黑名单。枪声在7个月后再度响起,李公朴、闻一多遇害。而费孝通家中的墙壁早被特务凿出了地道洞。在费宗惠见到带着黑色眼镜、高高瘦瘦的特务前,美国领事馆的吉普车快一步将费孝通接走了。
虽然费孝通简直为此气得发抖:“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可以随便杀人?”但他其实非常害怕,好友费慰梅不得不将他送去二战后穷得发紧的英国避难。三个月后,费孝通回国至清华任教。
1949年后,费孝通的言行很快被看作成新政权前积极的拥护者。一些参与清华的校务领导的教授,如费孝通、冯友兰、钱端升、张奚若等人,被认为受到共产党的特别礼待,也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四
1960年代,费正清的博士生戴维·阿古什准备为费孝通写传记,作为博士毕业论文。即使当时,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位中国社会学家是否还尚在人世。年轻的阿古什走遍世界各地,访问无数认识费孝通的亲友,写下《费孝通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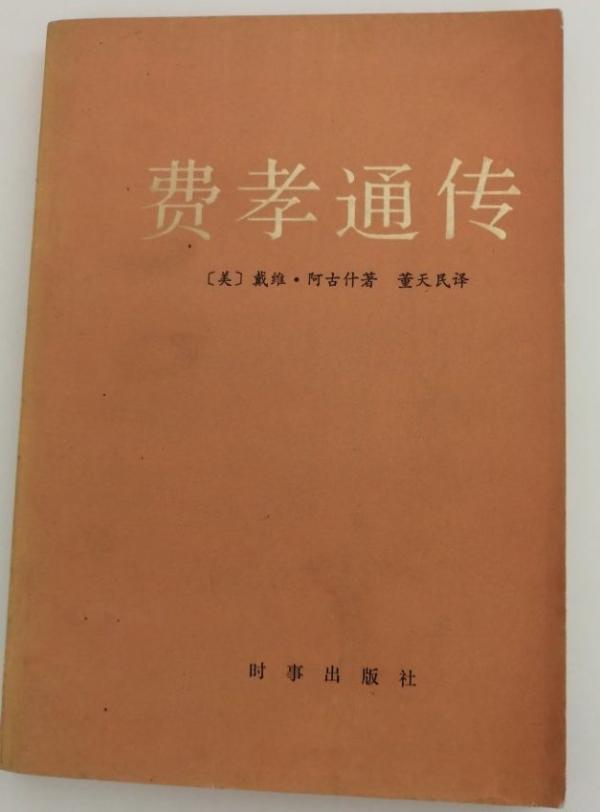
在《费孝通传》中,阿古什概括1949年以后的费孝通:“大多数文章都是解释并肯定党的政策,有少数文章几乎完全根据统一口径表态。一些论外交政策的文章似乎没有他个人的见解。”
但其实,在知识分子如此拘束的1950年代,费孝通仍有两次冒险谏言。
1951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到清华就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听取意见, 费孝通带头反对。第二年中南海会场上, 费孝通见到毛泽东,为了保留社会学,他“苦苦哀求” :“多少留一个种, 留点苗苗”。而毛泽东干脆地挥了手,不能留。
陆定一说,就是因为费孝通他们的反对,院系调整推迟了整整一年。随后,院系调整采用苏联模式,苏联专家强调减少人文社科,增加专业技术课,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
1952年10月,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理科划入北京大学。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假科学,在全国20多所高校被砍。一些教授去研究劳工与人口问题,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人被分配至从事少数民族工作,费孝通的学生史国衡去清华图书馆当了管理员。
1953年底,仅剩的中山大学与云南大学也取消社会学,至1979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前,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彻底消失27年。
随着社会学的中断,费孝通的学术研究陷入了空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曾指出:“在领袖打压学术,令其难酬经世济民之志时,他就真的不做学术了。”“怀疑费1949年以后有无一件这种分量的著作或译作。”
与之对比,潘光旦在1953年写作《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即使1957年“反右”开始后,仍在1964年从二十五史中整理出了有关少数民族的100万字的史料,至“文革”前翻译了达尔文巨著77万字的《人类的由来》。
不同于“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学者,要理解费孝通,就要理解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1930年代,20多岁的费孝通批判“为研究而研究”的观点:“我们可以写出成百篇的文章讨论周朝是否有‘吃人’的风俗,但我要问,这种讨论对实际生活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只知道“真正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学问可能是装饰品,也可能是粮食,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粮食。” 费孝通的学术语境必须是放置在“经世济民”下。
1982年,他对老同学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说:“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 正是生逢社会剧变, 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 简单地说, 是想学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 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 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 郑也夫说“在其经世济民的学术目标中,几乎容不下一丝别的趣味与动机。”
不在学术的日子里,费孝通的仕途拓展了。晚年,费孝通表示:“知识分子是要别人赏识的,李维汉是共产党里面第一个真正赏识我的人。这一直影响到我后面一些事情。我的仕途就这样开始了。”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费孝通出任副院长;8月,费孝通被李维汉拉进民委(中央人民政府事务委员会委员)。两年后,费孝通当选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协会理事。1954年,费孝通当选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反右”,费孝通以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为主。
1953年-1956年,外国友人陆续访华,他们发现顺心愉快的工作圆润了老朋友的脸。这段时期,费孝通走访少数民族,记录下他们生动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为他们受到压迫的悲惨境况四处疾呼。
1955年,《新政治家》杂志编辑金斯利·马丁(曾指责中国不给知识分子自由)访华,“他(费孝通)全心全意地欢迎新中国,从而洗净西方的污泥浊水……他在中国受到重视,有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 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思与费孝通长谈后,把费列为“中国遇到的最感人的宣传共产党的鼓动家”。
1956年是松动的一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提出,知识分子迎来略有缓和的政治环境。

1月,周恩来做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10月,国务院成立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副局长费孝通全国各地走访知识分子,鼓励他们大胆提意见。
在民盟的一次发言中,费孝通表达了对知识分子温和地改良方法,也指出当前知识分子 “一间房,二本书”静静地做功课,但对政策仍有 “不敢鸣,不敢争” 的重重顾虑。
基于这次发言,民盟希望费孝通挺身为知识分子说说话。这样的背景下,有了费孝通的第二次谏言。
后来刊发的文章几乎是由费孝通握笔、民盟的知识分子们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着写的。没人吃得准上面到底要“放”,还是“收”。
1957年2月末,一位民盟常委气喘吁吁地赶到费孝通家中,进门就是大叫:“不要发表!” 他听到文化部的报告,毛泽东批评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天气不对……我看形势是要收了。”
住在隔壁的潘光旦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文化部的一次谈话会,不是收,而是放。”
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回绝了在外地采访的朋友的文章。因为“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 “谁说的?” “传达下来的。”
斟酌很久,费孝通把文章从头改了一遍,删去所有尖锐问题,送出去了。当日正逢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潘光旦进城听了讲话,回来后兴冲冲地找到费孝通,“是放!”两人松下一口气。
1957年3月24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下简称《早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时间,引发全国对天气的讨论。
周恩来在飞机上读了《早春》,他评价:“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但又微妙地转折,“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费孝通说:“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因《早春》一文,费孝通被划为右派,和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潘光旦并列为著名的“民族学院五大右派”。吴泽霖因名额不够被补划为右派,妻子和岳母不堪忍受凌辱,服毒自杀。1980年,学者杨心恒拜访吴泽霖时,老先生在独居的一间筒子楼向阴的房间里用煤油炉做饭。冬天不能开窗,一进屋,全是煤油味。
五
与吴泽霖相比,费孝通的处境好许多,但他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发表题为《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同门师兄林耀华做“阴险丑陋的费孝通”发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有一篇题为《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院长郭沫若高喊着:“在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活动中,右派分子费孝通身兼两职,既是军师,又是闯将!”
从“红得发紫” 一下子跌至众矢之的,哪里是费孝通想得到的?一天内,他大哭一场又大笑了一场。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实验室”里的“旁观者”——哦,原来,“人在神兽之间”。
整个60年代,阿古什没有听到关于费孝通的消息。1966年“文革”开始,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等人被红卫兵从民族学院拉出来批斗。知识分子们开始了批斗与劳改交替的生活,费孝通的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
1967年6月7日晚上,腿脚不便的潘光旦因长时间在潮湿草地劳作膀胱发炎痛得难受,向隔壁的费孝通要止痛片,没有,又来要安眠药,也没有。最后,潘光旦死在费孝通怀中。
费孝通也想过死,但怕连累妻女,只能“逆来顺受,躲风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最终撑过了万念俱灰的十年。
“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晚年,费孝通再谈起那段历史,仍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
从1953年知识分子改造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被烫出了一个焦烂的烟头印。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其主动希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但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为了过关而互相揭发检举、自我检查的风暴。
费孝通不过是深陷其中的一名知识分子,但他多少觉得自己有责任,晚年面对年轻的历史学者时,他不忘强调:“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
“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 在学者余世存眼里,晚年的费孝通带着一种救赎感情。
改革开放后,恢复名誉的费孝通渐渐化成了一个弥勒佛般的笑。相较少年时的体弱多病,他变得脚力健劲,出去调查,吃得比学生邱泽奇和麻国庆都多,马不停蹄地踏遍中国各地调研。
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八次回访江村……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小城镇问题”等回应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的切实建议。官员们很喜欢费孝通的建议文章,当时有官员说:“别人给我文章,我总怕上当受骗,但费老的文章我很欢迎,他是做实地研究的。”

1995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归来,参加北大的高级研讨班,费孝通大声问到,“李友梅呢?录音机带了没有?”李友梅一惊,没带。
费孝通很生气,讲了武则天让上官婉儿试自己的浴袍的故事。武则天对上官婉儿说,“你太瘦了,这个袍子你穿不了!”
2018年6月14日,在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友梅回忆起这段往事,急切地讲:“他心里很急的,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50年都出不出来。中国要发展啊,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儿,也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真的是心里非常难过。”
那天中午,李友梅买了一个录音机。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