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沈书枝|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这个冬天,陪伴在身边的书是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每天早晨起来,我把小朋友送进学校后,回来第一件事是打扫卫生。做这些事时,我用一只蓝牙小音响连上手机,放一些书来听。从十一月起,每天播几章《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来听,等屋子收拾干净,早饭吃罢,便将小音响关闭,坐到桌前,开始这一日的其他事情。心里也并不急着多听或多看一点,像是一种柔和的陪伴,倒宁愿它细水长流些似的。然而不久之后,小学停课,我停止了自己的大部分工作,每日陪小朋友上网课,也改变了打扫卫生时听书的习惯,改放他喜欢的。直到一个月后,有一天我在疲惫中想要听一点自己的书,于是重新放起了《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意外的是,小孩子也很喜欢,不让我关掉,于是那天我们听了很久很久。从第二天起,我从头开始,把这部书重新播放给他听。白天不上课时,他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坐在地上拼乐高或是做其他事情。夜里他在桌前画起探险故事,我帮他写字时,看到那故事里也出现了篝火、山洪以及遇到的种种植物,心里不由得十分感动,这是扣人心弦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灵中染上的痕迹,是如此直接而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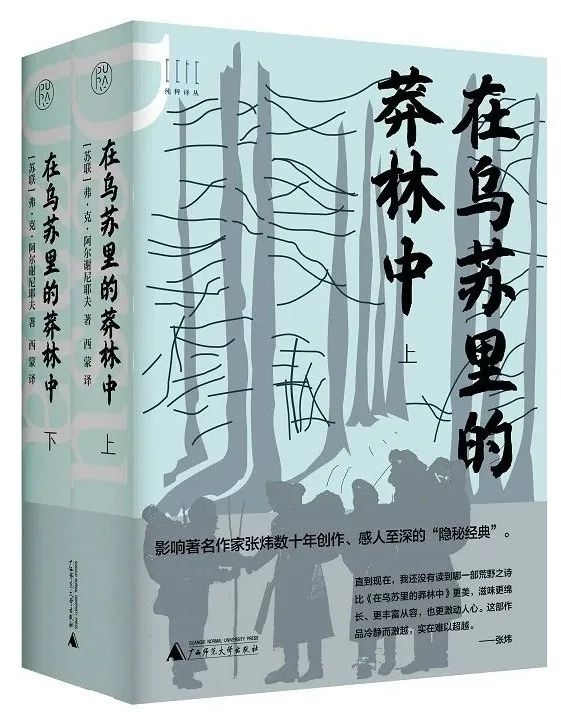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阿尔谢尼耶夫是苏联著名的地理学家,《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他一百多年前在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中探险、考察的故事。阿尔谢尼耶夫一八七二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从小喜欢玩旅行和打猎的游戏。十九岁时,他以后备军士官的身份进入圣彼得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受到地理老师、中亚探险家姆·伊·格鲁姆的影响,对自然考察探险产生了很大兴趣。他阅读大量描写探险的书,对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所描写的西伯利亚和乌苏里地区尤其向往。一八九六年毕业后,阿尔谢尼耶夫被分到位于波兰的军团,在那里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探险的梦想,多次申请后,终于在一九〇〇年被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从一九〇二年起,阿尔谢尼耶夫在南海(珲春东南部海域旧称)附近进行了一些短途考察,积累了一些在原始森林地区考察的经验。一九〇三年一月,阿尔谢尼耶夫被任命为符拉迪沃斯托克骑兵侦察队长官。日俄战争期间,他指挥侦察队,获得三枚勋章。一九〇五年末,阿尔谢尼耶夫被调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滨海军事边区总队;一九〇六年五月,奉命开始对锡霍特山脉的考察。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阿尔谢尼耶夫率领考察队,三次对锡霍特山脉进行了考察。这部书中所记的,就是一九〇二年沿济木河和勒富河的考察,以及一九〇六年在锡霍特山区的初次考察。

苏联地理学家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乌苏里地区是指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土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中从北向南高耸危峻的锡霍特山脉占据了主体,东部则是蜿蜒绵长的太平洋海岸。乌苏里地区原属中国,一八六〇年被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之后沙俄政府向这里移民,并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进行了多次考察。因为这种历史政治背景,我们在其中能看到的是一种多民族混居的状态。既有本土以渔猎为生的原住民,也有移居过去的其他中国人,还有俄国人、朝鲜人,日俄战争后,在人们口中,滨海地区渐渐还出现了日本人。
一百多年前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壮丽广阔的面貌,以及在其中考察的艰辛,是如今生活在极大衰退了的自然中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原始森林中人迹罕至,古木参天,到处都是巨大的倒木,人马在其中行走十分困难,常常需要一边走,一边用斧头开路。夏季的午后和夜晚,林中铺天盖地的蚊蚋,大雨、山洪、暴风雪或山火,恶劣的天气使人陷入困境,常有生命危险。遇到食物短缺或需要补充肉食时,考察队要自己去林中打猎,或是寻找其他食物。阿尔谢尼耶夫工作极其认真,在考察之余,还坚持每天写日记,趁着记忆鲜明时,把当天的见闻或感受记述下来。得益于这种记录,在这基础上形成的书稿不是枯燥专业的调查报告,而是一份关于乌苏里原始森林探险生活的生动记载。在考察队日复一日的行进中,原始森林的地理环境、动植物面貌,以及依附着它的原住民和移民的生活与故事就随之徐徐展开。在原始森林中经历的一切是那样新鲜动人而又艰难苦辛,这使得本书拥有了一种强大的真实的力量,这是一般虚构的探险故事所不能有的。
在这些故事中,最让人感兴趣的莫过于原始地区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这一地区的原住民有乌德海人和赫哲人,他们依靠着原始森林中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或渔或猎为生。这些原住民在适应原始森林的自然生活方面,都显示出高超的技能和惊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书中最具灵魂的人物,是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德尔苏是赫哲族的猎人,从小在原始森林中长大,在一九〇二年遇到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队时,他已经五十多岁,独自在森林中以打猎为生,妻子和孩子因天花逝去已久。他过的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游猎生活,长期在森林中露宿,只在十分寒冷时,才剥下桦树皮为自己搭一个帐篷。出于一种心心相印、相互欣赏,德尔苏开始与考察队同行,以他长期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经验,为他们提供帮助。一九〇六年,当阿尔谢尼耶夫开始在锡霍特山区的考察时,德尔苏又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一起考察。

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
德尔苏是枪法了得的猎手、原始森林中生活的行家,对于原始森林中各种自然现象、鸟兽行为,都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生活的经验。他能看出天空中不同的征兆预示的不同天气,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雨会停,能敏锐地觉察到鸟兽不同寻常的寂静,知晓那可能即将到来的连续的暴风雪,知道如何挑选木柴,烧出很好的火堆,如何在大风或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前,搭出可以救命的藏身之所。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对于原始森林中踪迹的辨认程度,阿尔谢尼耶夫说:“这个赫哲人面对踪迹就像在读一本书那样,能够按照严格的顺序恢复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森林中的任何踪迹都很难逃出德尔苏的眼睛,一点十分微小的痕迹,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许多的信息。他分辨得出森林中人和动物走的不同的路,能够根据树枝折断的情形推断出曾经发生过什么,甚至能够从动物的踪迹判断出它们其时的情绪。旁人看不出的东西,一经他的解释,立刻就显得那么清晰可见、一目了然。
这高超的读踪能力远远超出原始森林中一般的猎人,是长期对森林生活的体察和杰出天赋共同磨炼的结果,因为在原始森林中,若不留意到各种踪迹所传达的讯息,很快就会陷入绝境,无法生存下去。河边一堆燃烧过的篝火,阿尔谢尼耶夫只看出灰烬、黑火炭和烧剩的柴火头,德尔苏看到的却多得多。“首先他发现这里有好几处火堆的痕迹。就是说,经常有人从这里蹚水过河。其次,德尔苏说,最后一次,就是三天前,有人在篝火旁边过夜。这是一个捕兽的中国老头儿,他一夜也没睡觉,到了早晨没敢过河,掉头往回走了。如果说这里曾经有一个人过夜,从沙滩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就可以确定。至于说他没有睡觉,从篝火旁边没有人躺过的痕迹也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是捕兽的,德尔苏是根据一根带豁牙的木棒判断出来的,这种木棍一般是捕捉小动物下套子用的。说他是中国人,德尔苏的根据是从那双扔掉的乌拉和笼火的方法看出来的。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但是德尔苏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老头儿呢?我怎么也猜不出来,于是向他请教。”德尔苏捡起地上的乌拉(地方的一种鞋)给他看,他看到的只是这双乌拉已经破旧不堪,于是德尔苏告诉他,青年人穿鞋先坏前头,老年人穿鞋先坏后跟。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道理,但在未被揭出之前,就极难被注意。可以看出,德尔苏的读踪能力不仅仅是能迅速发现别人没有留意到的东西,而且能够综合在森林中积累的经验和对人情事理的体察,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这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森林中跟着德尔苏寻踪分解很有些读侦探小说的快乐,屡屡为他的本领惊叹,但德尔苏最令人感觉珍贵之处还不是这种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本领之高强,而是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极为淳朴的原始民族的勤劳与善良,它们使得德尔苏将其一身的本领总是用之于关心和照顾他人。在初识不久后,有一天他们在一个猎人的空窝棚中过夜,第二天早晨离开前,德尔苏劈了柴,弄来些桦树皮,把它们全部垛在窝棚里。阿尔谢尼耶夫以为他是想要把窝棚烧毁,德尔苏却向他要一撮盐和一把米,用桦树皮把火柴包好,盐和米也用桦树皮包扎起来,挂在窝棚里。他还把盖在窝棚外的树皮补好,这才准备出发。于是阿尔谢尼耶夫又以为他是打算将来返回到这里,德尔苏却回答说,这样无论谁来,找得到窝棚、干柴、火柴和吃的,就不会死掉。

阿尔谢尼耶夫(左一)和队员
读到这段记述时,很难不像阿尔谢尼耶夫一样,为德尔苏身上留存的原始民族的这种无私的助人与自助精神深深震撼。只有在离开之前,为他日森林中不知何时会来的陌生人准备好米、柴和盐巴,有一天自己在绝境中才有可能遇到相同的援助之手。但德尔苏不是怀着得到报偿之心的,这是一个只关乎给予的契约,他只是极其自然地遵守。在考察过程中,德尔苏往往也是照顾人的那个角色,当大家已停下休息时,他还在忙前忙后,或是和阿尔谢尼耶夫一起去考察、去为队伍打猎,在有危险的夜里,常常主动承担起看守篝火的责任。有德尔苏在,就使人感到放心,原始森林中仿佛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困境,无论遇到什么,他马上就可以想出办法解决。他救过许多次同伴的命,遇到危险时,总是设法让别人先脱离危险,然后才考虑自己。和阿尔谢尼耶夫在兴凯湖单独考察时,归途迷路,遇上暴风雪,是德尔苏让阿尔谢尼耶夫一起拼命割草,并在阿尔谢尼耶夫因为疲劳失温失去知觉后,为两人搭建了温暖的雪下窝棚,利用大雪和草棚的保暖功能,安全度过了暴风雪的寒夜。在大克马河渡河时,木筏将要靠岸,又被急流重新冲走,同伴的撑竿折断,就在木筏快要撞上石头时,也是德尔苏把没有明白过来的阿尔谢尼耶夫扔进水里,让他游上岸,自己独留在木筏上,在木筏撞上石滩粉碎前,抱住河中一根倒木,最后是让同伴放倒河边云杉,借助大树爬上来的。阿尔谢尼耶夫充满感情的描述,使得这些故事读来都十分惊心动魄又感人肺腑,当德尔苏终于成功脱险时,我们简直要随之欢呼起来。
作为深山中久远的原始民族的一员,德尔苏还保留着一些原始民族的习惯,他总是把打来的猎物分给别人,哪怕是住在附近不认识的人。这种原始民族的平均主义,在现在的人看来有种不可思议的单纯。赫哲人把自然万物都看作是有生命的,不管是老虎、野猪、飞鸟,还是河里的鱼,森林中的其他野兽,甚至是天气、水、火,德尔苏都把它们看作是和人一样的、有情感有好坏的“人”。水像人,因为“他会叫,会哭,也会玩”;火也和人一样,它一会明亮,一会暗淡,变幻出不同的形状。他把不好的东西都叫“坏人”。他崇敬老虎,因为曾在森林中猎杀过一只已经准备走掉的老虎,在年岁渐长之后,常觉负疚和恐惧,不再猎杀老虎。每次他们在森林中遇到“阿姆巴”(老虎)的脚印,都是一个紧张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原始森林中的民族的历史里,早已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认识,不利用人类的特长去滥杀其他鸟兽,因此,德尔苏也从不滥杀多余的猎物,更不会如当时很多西方人一样,将猎杀视为一种乐趣。他阻止士兵们有时无谓的猎杀,对于考察过程中有时遇到的其他民族的滥捕滥杀,也总是会感到深深的忧虑。在除了为基本的生存而打猎之外,德尔苏对森林的爱延及所有动物。有一次,阿尔谢尼耶夫把一块吃不掉的鹿肉扔进篝火里,德尔苏看见后,连忙把它从火里抢出来,扔到一边,并责怪他怎么可以白白把肉烧掉,人走了,别的人会来这里吃。阿尔谢尼耶夫说这深山老林中还有谁会来,这时,德尔苏惊异地说:“怎么有谁?貉子啦,獾子啦,还有乌鸦啦;乌鸦的没有——老鼠的来,老鼠的没有——蚂蚁的来。深山老林,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于是阿尔谢尼耶夫明白:德尔苏不仅关心人,还关心动物,甚至关心像蚂蚁这样的小生物。他热爱原始森林和栖息在其中的一切生物,并且千方百计地关心它们。
这个赫哲族猎人虽然几乎一辈子不出原始森林的区域,不知道进化论和食物链,却在与自然淳朴而深入连接的生活中知道了任何一种生物都与它周围的环境环环相扣,而人类是其中力量尤其大的一环,因此更应注意这一点,不浪费森林中的任何事物。书中有一处写到德尔苏的背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天阿尔谢尼耶夫扔掉了一个空酒瓶,德尔苏看到后飞快地跑过去,抓起了瓶子,怪他不该扔掉。对于森林里的原始住民来说,空瓶子是无比珍贵的东西。之后阿尔谢尼耶夫看了德尔苏的背囊:
当他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从背囊里取出来的时候,我越来越惊讶。那里面什么都有啊!空面袋、两件旧衬衣、一卷细皮带、一小捆绳子、旧翁得、子弹壳、火药袋、铅弹、一小盒火柴、一幅帐篷布、一块狍皮、混在烟叶里的一块茶砖、空罐头盒、锥子、小斧头、小铁盒、火柴、火石、火镰、松明、桦树皮、一只小罐子、杯子、小锅、土产小弯刀、筋线、两根针、空线轴、不知名的干草、野猪胆、熊牙和熊爪、麝蹄、一串猞猁爪、两个铜纽扣和一大堆别的破烂。我发现其中一些东西是我从前在路上扔掉的。显然,他全都捡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仔细看了他的东西,分成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劝他扔掉足有一半的破烂。德尔苏恳求我什么都不要动,说保证每件东西以后都会用到。我不再坚持,并决定今后事先没征得德尔苏的同意,什么东西都不扔掉。
这物尽其用的生活,在乡下长大的我看来别有感触。从前乡下的人也是几乎不产生多余的垃圾的,择的菜梗菜皮,可以喂猪喂鸡,或是倒在土地上腐烂,剩下的饭菜也是用来喂家禽家畜;打碎的碗片不扔,可以用来刮洋芋(土豆)皮,舀水的瓢用葫芦制成,轻飘飘浮在水缸上。就是后来塑料制品出现后,也只是一些水桶、筲箕篮子、水瓢之类可以长久使用的日用品,不到用得破了不会扔掉,不像如今身处塑料环伺的世界,几乎买不到不用塑料包装的东西。而这些原始森林中的住民,是怎样在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艰苦寒冷的地方生活,只问自然要那满足生命最本分的东西,而不要更多啊。德尔苏所有的财富就是这一个背囊,夜里他在身后插上树枝,把帐篷蒙在枝条架上,把狍皮铺在地上,坐在上面,披上皮袄,抽起烟袋,几分钟后就坐着睡着了。阿尔谢尼耶夫看着,心想,他的一生都将这样度过,为了生存,这个人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这个捕兽人未必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德尔苏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他是幸福的。阿尔谢尼耶夫的理解是懂得德尔苏的。书里写到近海与山溪区域的原住民乌德海人,过的也是一样艰辛的生活。在库松河附近,阿尔谢尼耶夫遇到一个冬天在外面睡觉不点火堆的乌德海人,担心他会冻坏,结果跑过去一看,这个老头穿着鹿皮翁得(土著的一种靴子),头上戴着白风帽和一顶插着貂尾巴的帽子,头发上挂满白霜,后背也是一层白霜,睡得非常安稳。这些乌德海人住在水边的帐篷里,漫长寒冷的冬季使他们早已习惯严酷的天气,适应了它的训练。孩子们从小冬天就穿得很单薄,在外面干活儿,如果有谁想躲进帐篷里比其他孩子多烤一会火,就会被父亲撵出去。阿尔谢尼耶夫提醒父亲这个孩子冻僵了,这个乌德海人回答:“让他去习惯吧,不然他会饿死的。”
要想在原始森林中长期生存下去,就得能经受住这大自然冷酷无情的考验。不过,这儿的原始住民与原始森林和谐相处的画面,随着移民的迅速增多,在那时已渐被破坏。书中写到伏锦村的村民们对待狩猎的态度很严肃,他们规定狩猎时不许触碰母鹿和幼鹿,在发情期不杀公鹿,自己划出禁猎区,互相保证不在那里打猎。这对保护森林中的野兽资源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后来移居来的俄国人不承认这项规定,开始滥捕滥杀,而他们对此毫无办法。在锡霍特山脉的库卢姆别河考察时,他们看到下套捕麝的朝鲜人的套子:
我们查看的麝窖共下了22个套子。朝鲜人在其中的4个套子上找到了3只母麝,4只公麝,都已经死了。朝鲜人把母麝拖到一边去,扔在那里喂乌鸦。问他为什么扔掉捕获的动物,他们说,只有公麝才有贵重的麝香。中国商人从他们手里收购麝香,1卢布一个。至于麝肉,有一只公麝就足够他们吃了,明天他们还能捕到这么多。据朝鲜人说,一个冬季他们能捕到125只麝,其中75%是母麝。
这种捕杀,尤其是对具有重要的生育价值的母麝的捕杀,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触目惊心的。阿尔谢尼耶夫说:“这次考察带给我很烦闷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会碰到滥伐滥捕的现象。在不久的将来,有着丰富动植物资源的乌苏里地区就会变成一片荒漠。”在沿海地区的小霍别河,他们又看到严重的滥捕滥杀现象,鹿窖绵延了二十四公里,有七十四个能用的陷阱,储物仓里,堆满了一捆一捆、重达七百公斤的干鹿筋。房子的墙上晾着近百张海狗皮,全是小海狗皮。德尔苏说,周围的一切很快就会被统统杀光,再过十年,鹿、紫貂、灰鼠应该全都会不见了。
因此,书中的描述常常又使人感觉到一种悲哀的情感,这不仅是猎捕动物时人自然感觉到的,也因为一百多年后的我们,知道这片原始森林后来急遽的消失和衰落。他们在一起时也曾说过以后这原始森林中的生活该怎么办,德尔苏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最后又问了一遍:“以后的,怎么过呢?”阿尔谢尼耶夫安慰他说:“没关系,老头儿,咱们这辈子够用的了。”这句话像是一句谶言,不仅是后来德尔苏的死去,阿尔谢尼耶夫也在一九三〇年最后一次考察阿穆尔(黑龙江)下游地带的原始森林回来后,因肺炎去世。本书一九三〇年版的序中,他写道:
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原始处女林已经被烧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片落叶松、白桦林和白杨树林。在过去老虎吼叫的地方,如今机车轰鸣;从前稀落孤单的捕兽人居住地,如今出现了一座座俄国大村庄;异族人已经离开,去了北方,原始森林中的野兽数量锐减。
这个地区丧失了自己的本色,正经历着文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变化主要发生在乌苏里地区的南部和乌苏里江右侧各支流的下游地带,而在北纬45°以北的锡霍特山区,则完全保留了荒漠山林的原貌。
这种消失对于我们来说,又更多一层痛惜的意味。美丽壮观的原始森林,一边向人类展示着它错综复杂的美与丰富,以及令人敬畏的力量,一边又显示出它逐渐被加深的伤痕。那美丽和壮观因此带有一种落日余晖的色彩,仿佛森林中黑夜来临前的黄昏鸟儿们最后的活跃。这隐隐浸入的悲哀也和德尔苏不幸的命运有关:因为德尔苏是那样善良、能干,使身边所有人感到安全、可靠,尤其使人为他不幸的命运而伤心。书中不多几处提到德尔苏怀念去世的亲人,都使人感到十分沉浸的悲伤。当考察进行到大半,德尔苏发现自己的视力渐渐变差,不能看见猎物,这是命运给他的另一重击,对于一个在原始森林中以捕猎为生的猎人来说,这一变故是致命的,也最终导致了德尔苏的死亡。此外是故事中其他人生活的不幸:原住的乌德海人染上天花,人数大减,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被移民奴役……这些当时真实的生活都让人感觉难过与沉重。
不过,吸引我们沉浸其中的最终不是悲伤,而是那随时变化的自然,和与这自然相衬的质朴的生活。考察队穿行于原始森林之中,为我们揭开那如今看起来遥远得接近于梦幻的过往。森林中随时的见闻,无论是林中各种各样的鸟儿,出没的走兽,还是森林或海滨的日月晨昏,随便一处,每每读来都非常动人。哥萨克人怎样循蜂找蜜,或大熊如何费尽心机想要掏出蜂巢里的蜂蜜,或是怎样防森林中的“小咬”(一种蚋),这些随处可见的段落,读来都十分有趣,使人感觉新鲜又能增长见识。甚至只是略述林中植被的文字,在喜爱自然的人读来,也充满欣欣的生之魅力。不过最有意思的仍是考察的故事,因为条件的艰难,在很多时候更接近于探险,在遇到连续的暴风雨、暴风雪,或是连续阴雨天后忽然爆发的山洪,或是在林中遇到阿姆巴的足迹,或是遭遇断粮的危险,经受饥饿的折磨,看他们如何在德尔苏的带领下(通常,因为德尔苏的经验丰富,总是能够提前带领大家做好准备),历经艰难险阻,最后终于脱离困境,重新踏上路程;或是可以又一次干爽温暖地坐在篝火边喝茶谈笑。我们也终于能从这紧张里放松下来,从心底里为他们感到快乐,好像我们是跟随着他们一起在原始森林中经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切一样。当地居民的生活,例如还保留着较多原始习俗和语言的乌德海人,在河边树皮搭成的帐篷中生活,如同鱼擅长游水一般擅长行舟;年轻的乌德海人在冬天的森林中围猎野猪,用爬犁滑雪,执扎枪追逐,是那么迅捷骁勇,充满生命力。勤劳的中国移民的生活,也很有趣。他们在原始森林中捕貂、挖参、种地,或是在海滨晒螃蟹肉、干贝,捞海带,捞扇贝,乌德海人如何在冬天的冰上捕鱼。如此种种读来都非常有意思,同时也令人感到遗憾,为这后来因为人类的过度攫取而急遽衰落枯竭的一切,它们曾是如此美丽而丰盛。故事的最后德尔苏死去,正是因为他不能放弃自然的生活,他的死因此仿佛成了这种消逝的某一象征。在这部书里,使人感动的另一方面是阿尔谢尼耶夫与德尔苏的友谊,德尔苏是如此使人眷念,这和阿尔谢尼耶夫对德尔苏的眷念不无关系。德尔苏对他也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到最后,德尔苏死后,书虽然结束了,人却久久不能从这充满了善美与动荡的故事中醒来,因为它怀着爱与美之心,记录下了地球上曾有过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自然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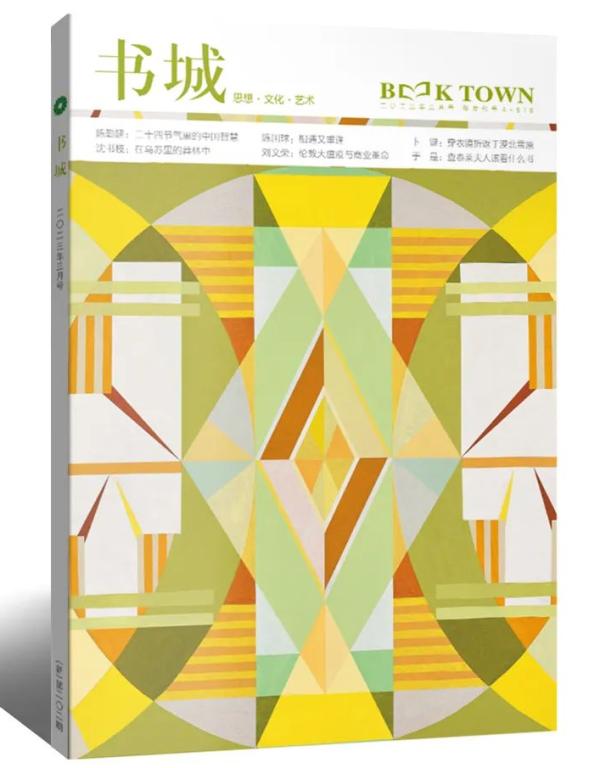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3年3月号),澎湃新闻经《书城》授权刊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