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白玉兰配猎户座,研究星象的作家也在接收写作的信号
原创 东来、栗鹿 文学报
青年漫谈计划
春天的茶话会(下)


都说青年一代很“社恐”不爱社交,那么我们来看看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们在关心些什么?我们将在每个月不定期推出“青年漫谈计划”,由本报记者主持,邀请他们来闲聊漫谈,通过一些生活化的话题打开文学与生活的深度联结。
关于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们总有很多浪漫表达。近期我们邀请了两位青年作家东来和栗鹿,一起和大家分享关于春天的记忆,也聊一聊她们的写作与写作之外的爱好——观鸟和观星。
本期对谈超长预警,只能分为上、下篇推出,因为两位作家聊爱好聊到完全停不下来啦!
本期主持人:阿懒
— Spring —

苍鹭
03
把生命寄托于自然
阿懒: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春天、关于观鸟的感受与乐趣。近年,随着对自然的讨论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自然文学的讨论也在扩大声音。想请大家来聊聊这方面,先推荐一些文学作品。
我自己个人的阅读偏好是喜欢那些情感性、文学性比较强的书。比如去年看的《以鹰之名》,我对鹰本身也没有很了解,它看起来也不会成为我的梦中情鸟,但这本书确实从情感的角度打动了我,是自然治愈人类创伤的好例子;《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一个人可以为了追寻一种鸟去跋山涉水;还有《心向原野》,这本其实是被封面吸引,因为绿色本身就是生命的颜色。
东来:我先推荐一本《游隼》,近期刚好推出了新译本,很有名的一本书,讲述作家在追寻游隼的整个过程。其实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进入生命最后的阶段。他当时患了癌症。他把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想象,包括对力量,速度的最激情澎湃的追求,都寄托在了游隼身上。这本书从头到尾的语言都极度的精致、优美与平滑。我记得晚上自己读的时候,随便翻到哪一页,随便从哪一行开始读,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当时立刻推荐给了很多朋友。这本书不完全是一本观鸟的作品,更是一本散文诗。
还有一本《海鸟的哭泣》,洋溢着英国“老克勒”的味道,写得非常的优雅。弥尔顿啊,莎士比亚呀,各种信手拈来。父亲送给作家一个岛屿,作家记录下海鸟的生存状况,同样是用一种偏文学化的语言来描述海鸟。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怎么去认知这些鸟类,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如何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如果有一天真正动笔写一本关于自然的书,要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句话?这本书能给我一些启发。
你刚刚提到的《以鹰之名》,在我看来,其实是一本关于驯鹰的书,不能算作自然文学吧。驯鹰在英国是属于贵族运动,鹰本是一种性格非常桀骜的动物,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是有强烈的焦虑感的,因为我觉得驯鹰是将鹰的天性强行扭转,它应该属于天空,所以我没有给这本书评分。但这本书的语言、写心理治愈的过程又很丝滑,特别是将作者本人与《苍鹰》的作者T.H.怀特进行了一种平行的对照,我对这部分描写更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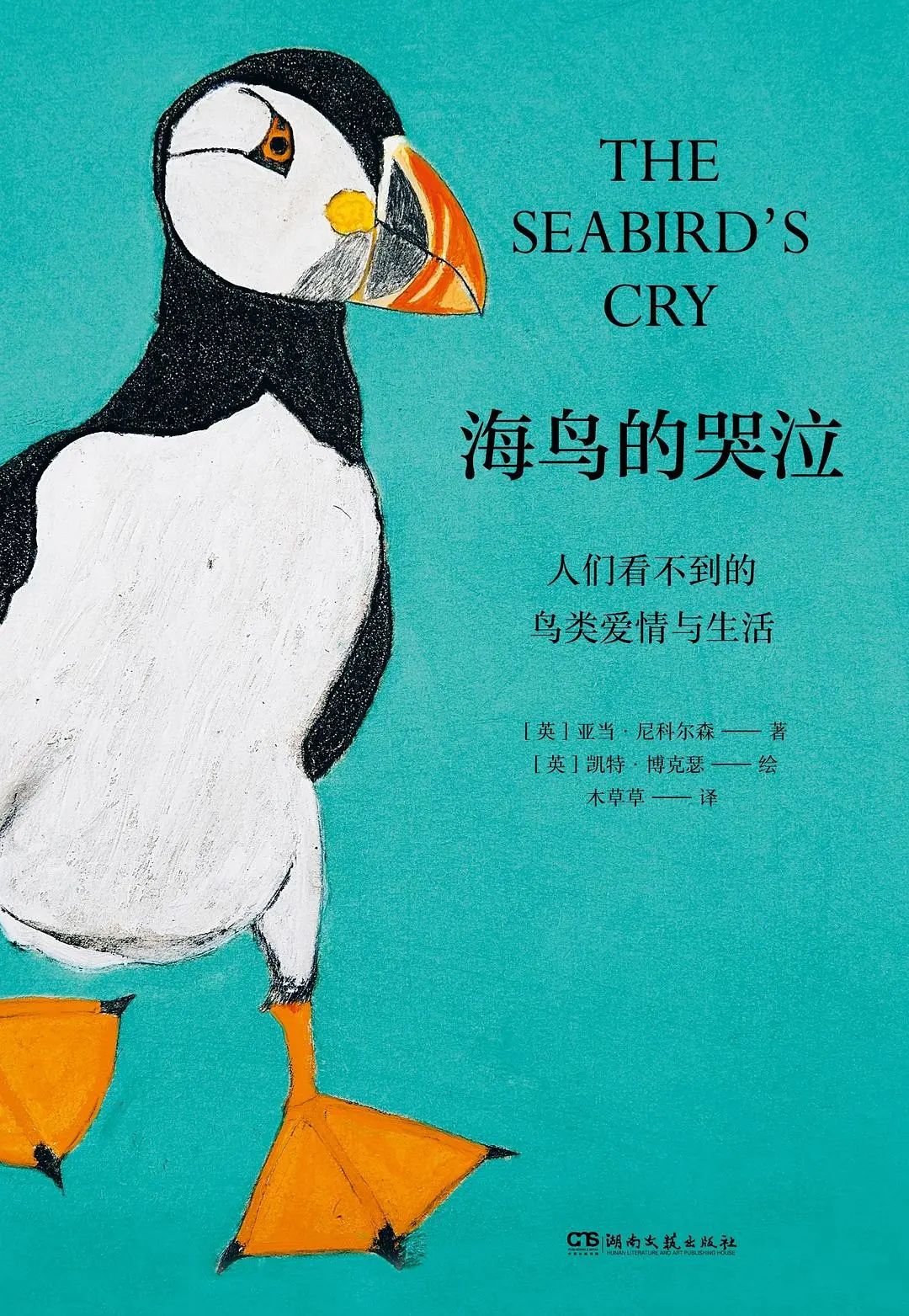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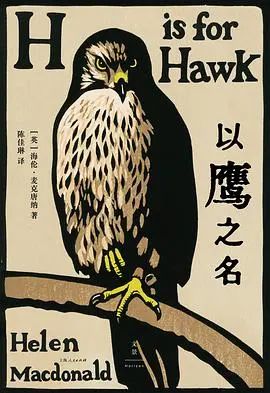
栗鹿:我之前读海明威《非洲的青山》,杀狮子的场景也会让我焦虑。我记得是一位在非洲的摄影师推荐的,他意思是这本书可能是他认识非洲的一个开始,却不是让他真正对非洲有认同感的一本书。海明威在书里也写到杀死狮子以后,晚上会梦到狮子,但更多的恐惧其实还是来自于他自身。我觉得他与自然是存在心理上的隔阂的。
这点在他其他作品里也可以读到,比如最有名的《老人与海》。虽然故事写得很好,很完美,但我可能在心理上无法完全地认同。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需要认同才好,但它不是我心中最好的关于自然的书。我觉得最好的写自然的作家是俄罗斯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代表作是《鱼王》。
我开始读这本书的契机蛮微妙的。刚刚说到我从小在崇明岛长大,到上海的机会其实不多。2010年前,两边都还没通桥,出岛要坐船。船很慢,是一种气垫船,我们叫它腾空船。人坐在上面,感觉没有依仗,像空中航行。到上海要两个多小时的航程,到市中心还要两个小时,真的好远好远。
那时候,上海对岛上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永远难以企及的地方。我们不太熟悉岛外的生活,所以我刚到这里生活的时候,说实话心里面是恐慌的。那时候开始读《鱼王》,故事跟《老人与海》有点像。王小波有句话评价这本书:“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它很难被定义,因为它是一种自白式的关于自然的写作。
在《老人与海》里的搏斗是有输赢的,一个人人生的梦想、信念都在那一刻,是毁灭还是实现,这部分海明威写的非常精彩。但是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事不太一样,人跟动物最后的命运是缠在一起的,越是挣扎缠得越紧。垂死时刻,主人公突然意识到他这一生对自然、对他人攫取得太多了,但最后,那条鱼像个梦一样游走了,他们彼此放过对方一马。
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置于和自然完全平行的位置,他的描写是充满神性的。小说里还有一个片段讲春天来的时候,森林里有很多声音,一种声音是一棵树倒了,它非常巨大,树倒的时候会推倒旁边的一棵树,那棵树又会推倒另一棵树,三棵树全部倒到河里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回旋。故事没有完,从上游游下来的鱼会躲避在回旋区里,聪明的猎人就知道等在这里一定能捉到大鱼。
如果不是作家真的感受过,是不能捕捉到这一切的,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画面,对于他来说,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一个循环。
这本书可以做为一本枕边书,给我一些内心的力量。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作,对家,对故乡的想念,随着人的远离,更清晰了。
再推荐一本新书王自堃的《冰雪海:南极科考沿线所见海鸟与海兽》,我认识他,是想写一篇关于南极的小说,想找一个有南极生活经历的人采访一下。有朋友介绍了他,我们互加联系方式后,却一直联系不上。因为他作为随船记者,当时已经在科考船上,卫星通信的信号不太稳定,发一条消息,大概十天半个月才有回复。
作者本身是一个大佬级的观鸟爱好者,东来可能更了解。


东来:他原来都不知道我观鸟,我们共同在一个叫沙河鸟讯群的群组里,有一天,有组员发了一张图问是什么鸟,我就跳出来回答了一下。王自堃才发现我俩在一个群。后来我才开始了解他观鸟的一些事情。
栗鹿:他之前有本《坛鸟岁时记》,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哪怕我不走出去,在小区里也能观鸟。
东来:你就是citybirder,城市观鸟人。
栗鹿:对。回到推荐的书,我终于知道自己写不出南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去过!
第一篇《驾驶室,谁穿走了我的老布鞋》,描写的场景非常生动。有一次大家去看罗斯海豹,在南极是一种常见海豹,但那天海豹影遁了,逃到了冰裂缝下,冰裂缝就像任意门,跳进去以后就是另一个世界。那次船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就他没看到,他就立志下次一定要看到。等到海豹再出现时,他要出去拍海豹的时候,发现他的鞋不知道被谁穿走了。大家都太兴奋了,一拥而上,也没人管是谁的鞋了。然后,他穿了一只大一只小的鞋子,跑出去拍了张照片,结果啊,还不是罗斯海豹。
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奇遇,对作者而言,他写这本书一直有个影子在,就是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
东来: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栗鹿:南极科考船上可能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有些随船人员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比科学家看得还认真,还勤快,他们看到一些生物就会大叫,希望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让他们来讲解或鉴别新物种。作家就给自己定位了这个身份——会大叫的人。他在书里对《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做了很多致敬,就像重走一遍旅程,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旅行不是单次的,而是重叠式的,作者的灵魂就跟你相遇了。
东来:对,一种重叠的讲述,一种想象力的增生。说回王自堃,第一次见他,感觉非常羞涩内向,但他说我马上要去南极了,我立刻就感觉到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像我们这样很浮躁的人,叫我们去南极,我真的很高兴,但我可能左思右想,最后不去了。而他就是那种特别坚定的人。
《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里有一个科学家叫斯科特,他是在南极遇难的,书里引用了大量他本人的日记。在生存环境极其严峻的时候,他一直坚持记日记。当时我看到那些文字,忍不住潸然泪下,会为一个时代存在着这么一群勇敢的人而感动。
栗鹿:他们其实跟在外星球上探险也没什么区别,因为那里同样人迹罕至,一切都是未知的。扪心自问,我是做不到的。
东来: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社会化程度太高了,我们需要跟周围联系产生的安全感。但有些人他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且丰盈到不需要和外界做太多沟通。
阿懒: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书,很多是从自我出发,偏文学性,这可能算自然文学的一种写法,那有没有一些其他写法的作品推荐?
东来:我想说一本书叫做《绝境:滨鹬与鲎的史诗旅程》,比较偏科学知识性的写法。
另外,我想起的一个作家是乔纳森·弗兰岑,他的《到远方》和《地球尽头的尽头》都有大量观鸟内容。他被他的一个前女友带“入坑”,之后他们分手了,乔纳森自己成为了一个重度观鸟爱好者,并且因为爱好,他观看世界的角度都变了,甚至变成了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从人类本位思想跳脱出来后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关心鸟类的生存环境。
我之前去鄱阳湖观鸟,看到了白鹤迁徙路线的科普,白鹤原来有三条迁徙路线,西线和中线路线因为环境恶化,基本上已经被放弃了。在2007年,巴基斯坦有人观测到了沿着中线迁徙而来的最后一只白鹤,它孤单地穿越了千万里。所以,我们认识的观鸟大佬们总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抓紧看!如果你不看的话,可能过几年就没有了,很多鸟就这样消失了。
栗鹿:就像中国的麋鹿,从很多到很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有一只野生的雄性麋鹿渡江来到了崇明的东滩,角上挂着很多垃圾,有动物专家就说那只麋鹿可能是一只老鹿王,在斗争中败退了,它就选一个地方孤独终老,然后看中了这里。角上的东西是捡来的,它觉得很漂亮。


夜鹭与白鹭
04
捕捉信号的写作
阿懒:如因为观鸟改变生命方式的弗兰岑,我们通常喜欢从作家的爱好或生活里找寻与写作相关的痕迹,这或许是一种“窥探欲”。
东来:我观鸟才三年,它主要是给了我一个观察自然的视角,从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又回头反思自己,像是重新认知自己的生命,对自己过往的历史有了全新的感受,一个新的维度被打开了。比如回看自己的成长经历,会有一些新的记忆浮起来,这些记忆因为观鸟重新闪光,它会进入到写作的文本里,成为文本里的灵光。
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有时候是片段式的,一个个片段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偏于整体的意象。我喜欢旧东西,喜欢一个人待着,喜欢收集那些冷僻知识,其实是一个“边角料爱好者”。
因为成长环境,我可能爱自然胜于爱人类,所以去书写它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阿懒:之前做采访的时候,了解到栗鹿除了是小区观鸟人,也是观星爱好者,我想到你之前说过穿着伴娘服去看星星,结果被以为是拍剧的事儿。实际上,我读你的书,文字整体营造的氛围在我知道你观星的爱好后,有“啊,原来如此”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栗鹿:我一到春天就喜欢散步去看一棵白玉兰。春季是观赏猎户座最好的时节,站在树下看花,正好能看到猎户座运行至此。就是这样半开不开的时候最好,整个猎户座高挂南天,就像树枝自己发出的芽点,浑然一体。等花开满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春天一过,玉兰树长满了叶子,猎户座也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契机,对我来说,我刚刚分享的事情都是在一个时期发生的——2017年生完小孩特别低潮的时候。当时,我看到一则新闻,卡西尼号探测器结束了二十年的深空之旅,为了不破坏周围的卫星,它撞入土星的大气层,以一种自毁的方式结束“生命”。在最后时刻,它把天线对准地球,发送了最后的信号。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甚至和我有一种隐喻的神秘的关系。它唤起了我对星空的好奇,这个好奇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直有的,只是按钮的开关被打开了。
我几乎把关于深空的所有纪录片都看了,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同身受:她觉得一个女性生完小孩恢复好的标志就是她重新建立了对世界的好奇心。
后来我就买了望远镜,一开始买的一款折射望远镜特别便宜,几百块钱,但是你用它就可以看到土星环,看到木星上的云带……几百块带来的巨大快乐。
阿懒:你用几百块拥有了星空。

栗鹿:对,我想的是观鸟者去湖边观鸟,完成了一次旅程;我在自家阳台看到遥远的星辰,我也是在旅游啊!我当时还不会拍摄,光看就让我快乐了一年。
我之前跟阿懒说过一个标志性事件,我拍到了土星环上的一个缝,那个缝叫卡西尼环缝。因为土星环看上去是一个环,但它其实是无数个环组成的,用ABCD标的,在AB之间有个大缝。那天和伙伴捣腾了好久,最后终于拍到了,虽然曝光过度,但那条缝非常得清晰。当天我开心地在所有社交平台上都发了一遍。
之后我的目标是拍到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就是大红斑,为什么要拍到它,是因为那个风暴一直在缩小,风暴刮了三四百年,越来越暗淡了。我原来是电子盲,为了拍到星空,变成了一个器材党。观星也是一个无底洞。
哦,我好像讲的太偏离写作了,绕回来一点,我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的,之前写的都是短篇,一直想写长篇,但没有一个立足之本。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它需要有一个信念支撑你写下来。我好几次写到七八万字就放弃了。
东来:我也写到过七万断掉。
栗鹿:对,我当时觉得我跨不过这道坎,没有一个人物或一个情节,能够让我相信到最后。写作是很难伪装的,如果不用自己的本心去写,伪装出来的东西,自己都知道是假的。就像东来说的,观星唤回了我之前失去的很多记忆。
插个好玩的事,网络上有很多人知道我观星,会有人来问我:你知道月亮下面东偏西方向一颗红色的星是什么星?我就在想我又不是星图,月亮下面东偏西一颗红色的星得有多少颗啊?他们默认我知道天上的每一颗星星。我在慢慢重新认识星空,慢慢“命名”一颗颗星星。
东来:观星让你得到了弥合,也有勇气写长篇了。

土星与木星
栗鹿: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在里面,主要是让我重新找回我的信念。我之前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书,她很喜欢研究星象。她把群星跟人的命运串联起来,我觉得她是把爱好和文学融合得特别好的作家。读了《糜骨之壤》,我甚至可以占星了。而我还不能融合得那么好,我还在寻找一种方式。在《致电蜃景岛》里我也只是写了一小段观星的文字。
东来:你的这本小说有电波的感觉,断断续续的。
栗鹿: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启发了我。我很喜欢最近一部电影的结尾部分,里面大家对着天空发信号,每个人的信号都不一样,我觉得是跟世界的一种羁绊。电波就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我取了这个书名,责编当时还跟我说有点怪,一定卖得不好。但我挺确信的。
阿懒:东来在准备什么新的作品吗?
东来:一个中篇集。我跟栗鹿有点相似的是,也喜欢那些信号,但我不喜欢明确的,而是像雪片似脆弱的,一片一片的,看不到全貌但可以看到轮廓的事物。《大河深处》《奇迹之年》都是对这些事物的描绘。
阿懒:最后,我在想要怎么结束今天的对谈,聊了这么多,我想有一个信号是准确的:不管是观鸟,还是观星,或是写作,想做就赶紧去做!
原标题:《白玉兰配猎户座,研究星象的作家也在接收写作的信号|青年漫谈计划》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