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硕《翦商》:在历史的深渊,一窥我们何以如此,何以至今
编者按:
在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对于背后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纣王“无道”的表现有哪些?商朝王室的贵族生活是怎样的?商朝人的日常生活与祭祀之间有何秘密?2022年10月,青年历史学家李硕,其里程碑式的杰作《翦商》问世,震撼无数人心。从夏朝到周灭商,李硕跨越一千余年的时间隔阂,重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这本书以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这一页,从杀伐与屠戮开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中国古代第一王朝夏朝,沿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杀人献祭”风俗,“人祭”的传统最终在商朝登峰造极。武王灭商后也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直到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由此留下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本书从还原深渊般恐怖的“人祭现场”开始,引领我们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在撒满尸骨的历史荒原上,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
(本文摘自李硕《翦商》)

历史学家李硕
殷商最后的人祭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祭坑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却是绕不开的。下面,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区。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是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三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发掘上千座人祭坑,但大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头),且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2.8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被修整夯打过。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颚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摘自《翦商》)
鸟神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种,最崇高的是“帝”,此外,还有鸟,而这应该跟商族的创始神话和早期图腾有关。
在上古时代,鸟崇拜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画鸟类图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显的鸟崇拜,如古国王族最高级的玉器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旁边相伴的是鸟形图案。
春秋时期,山东南部的土著小国郯国的一个著名传统就是用鸟来命名各种官职。郯国国君说,自己的始祖是“少皞氏”(少昊),而少皞氏建立的国家的各种官职都是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也是东部沿海崇拜鸟的记忆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后所生,说明鸟是天帝和商人联系的纽带。《山海经》这样记载商族第六代首领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看着很含糊,难以确定是人要吃鸟的头,还是鸟要吃人的头,但王亥和鸟的联系在甲骨卜辞中有证据:“辛巳……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
这条卜辞占问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举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显的鸟形,而那些与王亥无关的,
比如地支记日之“亥”,则不会有鸟形。
《易经》中也多次出现过鸟。周人和商族起源不同,并不崇拜鸟,但在创作《易经》时,周文王引用了一些与鸟有关的商人的历史掌故,如《旅》卦上九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这条爻辞涉及王亥在有易氏丧牛和被杀之事。“旅人先笑后号咷”是关于王亥旅行在外的遭遇;而鸟巢被焚毁,则象征王亥的命运。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发现《易经》里隐藏的这段掌故,直到民国时期才被顾颉刚破解:“丧牛于易”是说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难,牛群被夺走。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商王祭祀“鸟”的内容,如焚烧“一羊、一豕、一犬”和“三羊、三豕、三犬”献祭给鸟,但不知道接受祭祀的是随机飞来的野鸟,还是商王专门饲养的神鸟。此外,商王还多次从鸟鸣中占卜吉凶。
《史记·殷本纪》记载,某次祭祀商汤时,一只野鸡落在鼎的耳上不停鸣叫,高宗武丁非常紧张,大臣祖己趁机发表了一番道德说教,最终“(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此事的道德元素应是后人添加的,但野鸡引起武丁紧张之事应当有原型。只不过,这需要放在商人崇拜鸟的背景中才好理解。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曾出现“玄鸟妇”三个字,可能是通灵降神的女巫,负责在王族祭祀中召唤玄鸟之神降临。
那么,商人这种崇拜鸟的宗教,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
其一,在甲骨卜辞中,有多条商王捕猎野鸡“雉”的记载,但未见捕猎其他鸟类,而且从来没有用禽类和蛋类献祭或食用的记载。其二,在商人的遗址和墓葬中,食用家禽的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的确比较少。殷墟宫殿区灰坑中曾发现猛禽和孔雀的骨头,王陵区的少数祭祀坑中也有猛禽骨,可能是王室豢养的猎鹰和珍禽,但不清楚是否有供奉崇拜的神鸟之意。总之,商人对禽和蛋的禁忌要多于别的族群。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其含义不明。有人认为,它是各线条汇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间的中心;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捆支起来进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卜辞中,帝也称“上帝”,有时会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横,是为“上帝”二字的合文。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不管“帝”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关键肯定是神圣之意。作为一个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带有神圣含义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状。
比如,龙,甲骨文中是顶着帝字头的龙形;凤,甲骨文是顶着帝字头的鸟形;商人自己的“商”,甲骨文中,帝字高高站立于一座大门(牌楼)之上,有时上面还会有两个并列的帝字头。

“玄鸟妇”铭文拓片
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妇好的墓,就随葬有多件龙凤造型玉器,而且龙和凤头上都有如甲骨文中的角(帝字头),特别是354号标本,“为一龙与怪鸟的形象,颇似怪鸟负龙升天的画面”:龙头上有一只“角”,怪鸟则有两只。此外,妇好墓371号玉器是跪坐的人形,身上雕刻出衣饰花纹,身后伸出如同羽毛的鸟尾。这些玉器可能都反映了商人对鸟的崇拜。
商族人有奇异的来历,他们开创的王朝也注定不会平凡,特别是王朝建立之初,产生了诸多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摘自《翦商》第五章“商族来源之谜”)
后记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巍兄,一位是高一级的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入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烦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摘自《翦商》“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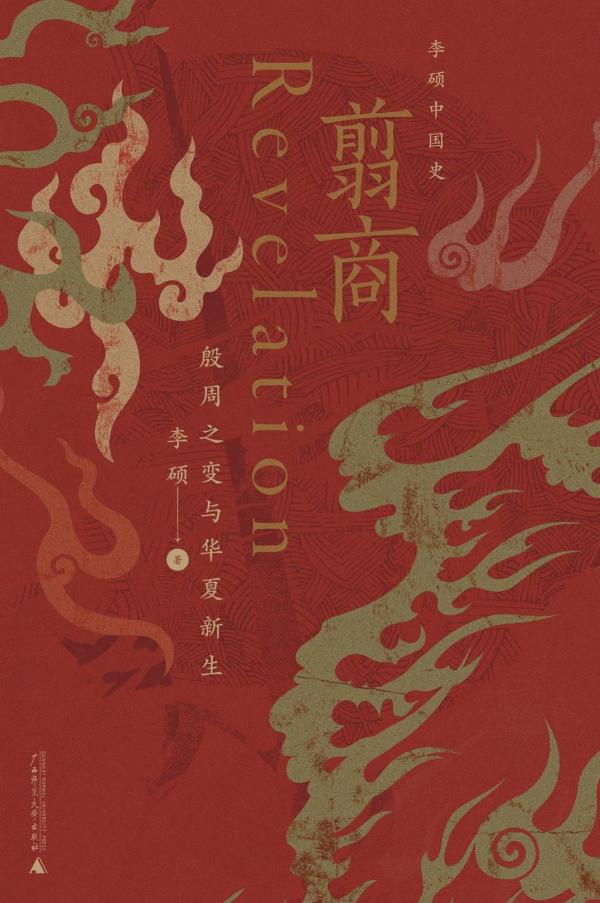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