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韩松刚: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访谈
专栏/访谈
自2022年10月起,江苏省作协与《文学报》合作推出“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专栏文章,推介8位青年批评人才。本期推出的是青年评论家韩松刚。
韩松刚,1985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江苏省第四期、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青年写作等。出版学术专著《当代江南小说论》和文学评论集《现实的表情》《谎言的默许》。曾获第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韩松刚
01
好的作家一定有“批评”的眼光,好的批评家也少不了“创造”的冲动
记者:以我的阅读,你是专注于语言、诗意、抒情等文学的基本命题,不断寻索和钻探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并有自己创见的批评家。你很少炮制热门话题,你的批评文章里也不是那么西化,这在普遍受西方文论深度影响的批评家群体里,显得有些鲜见。基于此,问问你怎么看待文学批评这回事?
韩松刚:作为一名受过多年文学教育的评论者,很难不受西方文论的影响,甚至于一定程度上,我们所面对的文学,就是“理论”中的文学。当然,运用理论去分析、阐释文学,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文学问题,相反,它可能只会制造某种幻觉。这可能也是这些年来,我渐渐开始抵制理论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的沉没,相反,它越发兴盛,而我们也时刻处在理论之中。因此,谈论文学,又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理论的幽灵。虽然从事文学批评已经十几年了,但对于文学批评,很惭愧,我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确定认知,如果一定要做一种评判或理解,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三个层面:一是鉴赏,批评首先是鉴赏,即根据自身的文学经验、趣味、修养来评判作品或作家;二是剖析,就如弗莱《批评的剖析》中一样,试图建立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批评体系,并以此面对文学作品之整体。三是“掘洞”(贝克特语),投入自身,并通过作品、透过语言,去捕捉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东西。这第三个层面,可能就是我认为的理想的文学批评形态。而我对于语言、诗意、抒情等文学命题的专注,可能也是源于这样一种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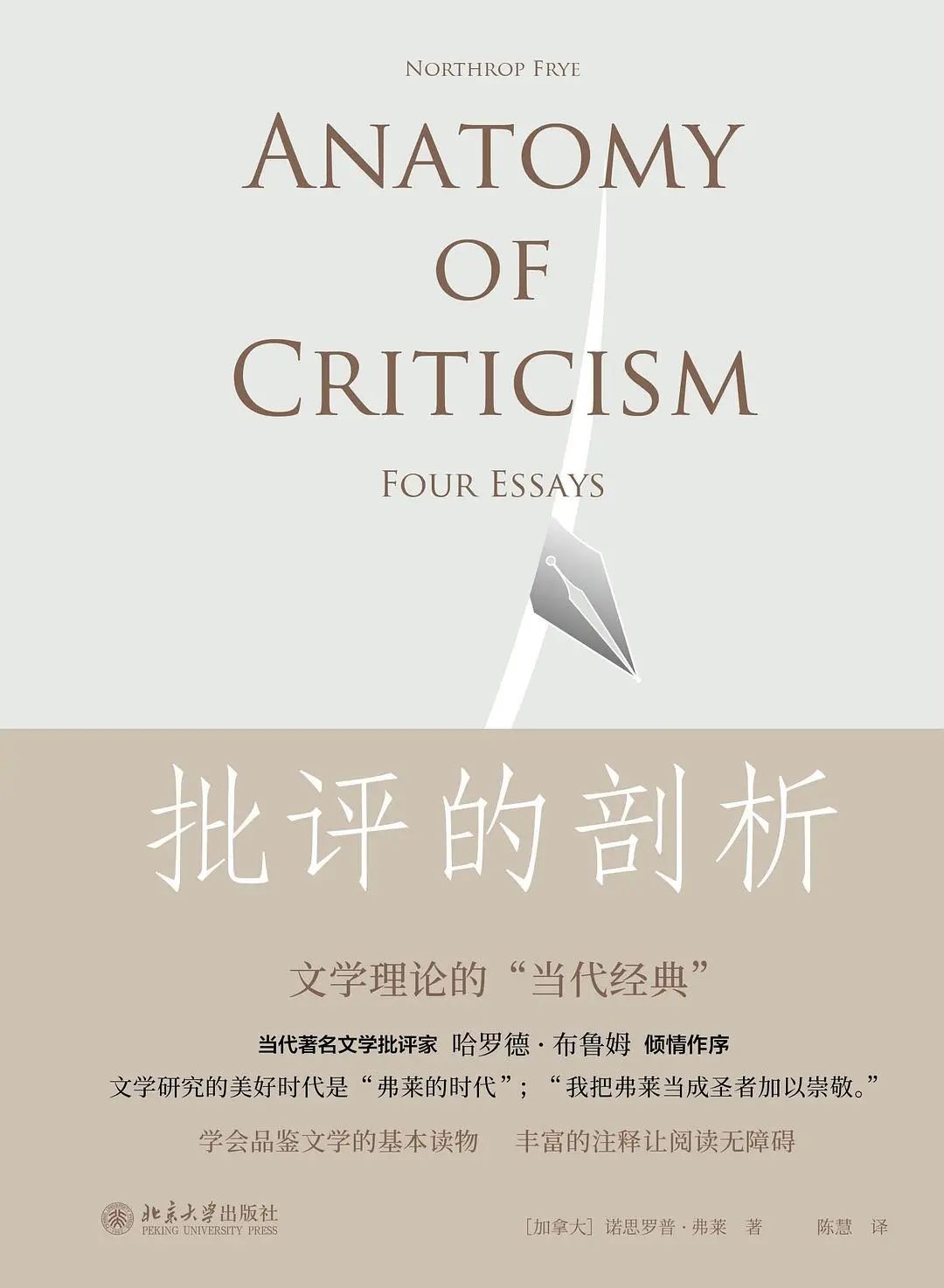
弗莱与《批评的剖析》
记者:在《时代的协奏和个人的低语》等文章里,你谈到你怎样做起了文学批评,尤其谈到南京大学对你治学的影响,我估计也是从那时起,你开始关注文学江南、南方精神。按吴俊老师的理解,南京并非江南,何况你籍贯是山东,所以有些好奇,你怎么想到做这个课题,并为此写了本《当代江南小说论》?
韩松刚:这肯定和我在南京上学,然后又在南京工作有关。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我写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毕飞宇短篇小说《哥儿俩好》的,但这时候的文学研究基本是无意识的。我真正开始关注江苏文学、江南小说,应该是从我到江苏作协工作开始的,又加之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做编辑,所以慢慢地和身边的作家开始有接触和交往,也慢慢地开始大量地阅读江苏作家的作品,并先后写了关于范小青、毕飞宇、苏童、叶兆言、叶弥、朱辉等一批作家的评论。《当代江南小说论》这本书的缘起,是我的博士论文。我2013年考取了黄发有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论文开题的时候,黄老师考虑到我在江苏作协工作,又对江苏作家比较熟悉,当然,也考虑到写作的难度,因为是在职读博,时间上并不充裕,所以选题就以江苏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但又觉得一篇博士论文做一个省域的当代作家研究似乎局限了一些,所以想到从江苏扩展到江南,以江南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为对象,做文化层面和文本层面的多重考察。等到我开始具体写作的时候,黄老师离开了南大,遂将我转到吴俊老师名下,正是在两位老师的共同指导下,我才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也才会有后来的这本书。
记者:我问这个问题,也因为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作家的生活变迁,包括他们在何处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很少问批评家的经历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的批评产生影响。
韩松刚:影响一定会有的。不管是个人的生活经验,还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一个人读书、求学的经历,一定会在自身的文学批评中有所映照。只不过,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因为其所要达成的文学目标不同,所以,由于这些生活的变迁所带来的主体表现和文学诉求也定然不会相同。我们现在喜欢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一种人为的割裂,这是不对的,在我的理解中,好的作家一定也是好的批评家,同样的,好的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作家。当然,区别也有。但是好的作家一定有一种“批评”的眼光,好的批评家也一定少不了“创造”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个人,而不是两种身份。
记者:既然说到江南,你又写了《陆文夫小说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不妨谈谈你怎么看待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诸如“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说法,你认同吗?
韩松刚:很多时候,我们对地方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陷入某种偏颇之中,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或者说递进关系。因此,就会有“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不合逻辑的观点。在我看来,地方和世界是一种平行关系,或者说交叉关系。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可能类似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是相互依附、相互包容、相互成全。地方性更强调特性和差异,以及某种不可复制性,世界性则强调整体和共性,以及某种普遍的认识。因此,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当代作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记者:实际上,你在批评初期倒是研究的自传写作,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领域。你在《“文革”后中国作家自传写作的局限与可能》一文中表示,巴金的《随想录》等,在写作形式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破碎和芜杂,他们写作的随意性、随时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统一性,影响了其思想性的凝聚。西方的自传正好相反。不过后来中国作家的自传写作,在形式上是更为严谨了,但很难说就更有思想性,并且写得更好了,可见还不只是形式问题。
韩松刚:关于中国作家的自传写作研究,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作家并不喜欢写自传。这内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中国作家缺少一种自我剖析、自我审视、自我否定的勇气。通俗一点,可能就是好面子,追求完美人格。因此,这一文体在中国也并不发达。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自传(非严格意义上),因其敢于说真话,敢于自我解剖而为人所称道,可是与西方的作家自传相比,缺少一种精神上的统一性,因此,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不能算是“杰作”。现在很多流行的所谓自传,大多不过是为自己的人生做一包装,没有多少文学的价值,更不要谈什么精神意义了。
022
我们从事的是文学批评,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语言一点都不文学
记者:如果说,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我想你多半会赞同,你关注语言问题,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的思考》。我觉得对于批评家而言,这个问题是怎么讨论都不为过的,因为批评家谈文学,容易一谈就谈作家表达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达。就我自己来说,我有时会问作家们,怎样才算是好的语言,或者好的语言有什么标准。既然你关注语言,在文字表达上也可谓讲究,不如也问问你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你看来,好的批评语言是什么样的?
韩松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作文和做人是一样的。好的批评语言,朴实和文采一定是适中融洽的,不偏于一方,无过,无不及。好的批评语言,一定是尊重常识、符合逻辑的语言,一定是有理、有情、有见地的语言,一定是经得起推敲、可以被反复品味、能够引起情感和思想共鸣的语言。而最重要的是,这语言也一定是文学的语言。我们从事的是文学批评,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语言一点都不文学。当然,我自己的批评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时不时会被一些华丽的修饰、某种程度的言不由衷所裹挟和诱惑。作为批评家,经常会批评作家的语言不行,但就批评家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的语言也不过关。好多年前,我参加过几次博士论文答辩,而论文被诟病最多的就是:文不通句不顺。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做编辑期间,最害怕的也是那种文句不通、逻辑混乱的批评文章,这其中有不少就出自一些知名学者和教授。可见,语言的问题不管是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甚至于学问家都是一个大问题。说一个作家语言不行,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同样的,一个批评家,缺少语言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不能分辨出好的语言、坏的语言,那也一定是文学研究的大灾难。但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很多从事文学研究或批评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不太懂语言,甚至于说不太懂文学。

记者:我想,你眼里好的语言,其中一个标准定然是诗性、诗化,或者诗意。这也是你批评的核心词汇。你写的多篇文章,题目里就包含了“诗意”二字,如《含混的诗意》《毕飞宇小说的诗意》《江南的诗意与失意的江南——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概论》,等等。你说到江南文化诗学的六个认同,其中一项便是诗意认同。你何以如此强调诗意?既然如你所质疑,“当代文学批评更像是一个科学的怪物,它处处透露着科学的价值观带给我们的理性和思辨,而文学意义却无处可寻。”那么,你认为,文学批评又该如何在诗性和理性之间求得平衡?
韩松刚:还真是呢。我自己倒没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诗性的语言是我特别偏爱的。尤其是那种偏于诗化的理论文章,更是我追求的批评目标。我喜欢那种美的批评。我觉得诗意应该是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维度。不管是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程,把质疑、反思变为反抗、对决的过程,把平凡的日常、粗糙的生活凝结成精确的词语、诗化的表达的过程,就是一种诗意的达成。说到底,不管是诗性还是诗意,是偏于感觉的一种模糊东西,而所谓理性、思辨,更像是一种后天科学训练下的技术习得,但我觉得,对于批评来说,这些都还算不上最为关键。因为,比在诗性和理性之间求得平衡更为紧迫的,是文学批评如何做一个文学的捍卫者或保障者,去努力保持对文学变为畸形工具的可能性的敏锐警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做得还太少,还不合格。

记者:刚还想说,你导师黄发有为你的评论集《谎言的默许》写的代序也题为《诗化的细读》。从你的一些文章看,你确实在文本细读上下了功夫。不过批评意义上的细读,似乎容易混同为书评。以我编辑的经验,近些年来,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和评论,多的是书评。而书评虽然也是解读作品,又似乎很难等同于文本细读。你怎样看?在你看来,细读文本,应该读些什么?
韩松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复杂的问题。我曾经写过《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研究》一文,做过一些思考和探讨,但目前看来,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我认为,书评是向读者靠近,接近于作品导读。文本细读则是向文本靠近,它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这两者的驱动力和方向不同,因此差异还是很大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细读方法更接近于一种印象式批评,特别重视作品细节(语言、人物、对话等)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而不是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要对文本做一全面的细致阐释。比如燕卜荪出版于1930年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一书,被认为是典型的“文本细读”之作,其内容就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新批评冠以“批评”二字,但其内里是研究和构建,它从语言、语义、语境等层面所展开的分析,虽然眼光略显狭窄、观念稍有僵化,但是却充满了想象和异趣,说真的,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并不能驾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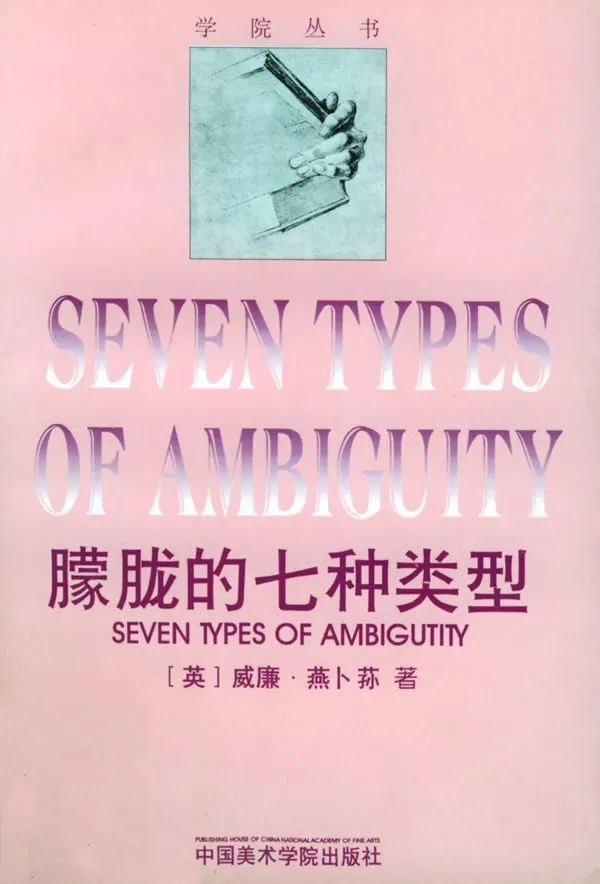
燕卜荪与《朦胧的七种类型》
记者:我觉得正因为靠的细读,你才读出了“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这也是你一篇文章的题目。你的文章《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文学的“情调”——从一个维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等,倒是也多少体现了“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因为无论抒情,还是情调,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之受西方小说叙事影响,这一特性有所弱化。你认为是否有可能,或者说该怎样接续这一文学传统?
韩松刚:对于古典文学特性的关注,还是和我从事江南文化和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有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江南文化内涵的丰富是和古典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儒释道文化的融合、诗性的抒情、唯美的特质等等,都和一代代人的精神发展紧密相连。在我的理解中,好的小说一定是有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或古典精神作为内在支撑。事实上,这些年来,当代的很多小说家包括年轻的小说家,很重视这种古典传统的传承与转换,如莫言、贾平凹的笔记小说、陈春成的一些短篇小说,都在这方面做了探索。至于说如何接续这一文学传统,个人以为,主要是有赖于作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敬重与阅读,在痴迷于西方小说叙事的同时,应竭力在源远流长的古典资源中,寻找与自身生命、个体经验相合相契的精神力量,从而促成自身创作新的觉醒和成长。当然,更要依靠作家自身的才华,去最终完成个体创作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身。
03
排行榜、文学奖在刺激作家成长的同时,也会让他们陷入创作的圈套
记者:前面也说到,你很少炮制话题,却也关注当下文学现象。比如你在《秩序与历史》一文中论及文学排行榜,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眼下不只是盛行文学排行榜,文学奖项也是多多,你怎么看待它们对文学创作或批评所起的作用?
韩松刚:可能是我缺少一颗炮制话题的脑袋。但这是一个从不缺少话题的时代。排行榜、文学奖等等,就是一个一个不断的话题。我觉得文学排行榜、文学奖一定有正面的意义,你说它们学院化、精英化也好,你说它们政策性、导向性也罢,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品质的基本化理解。甚至于说,它们是在一个碎片化、肤浅化的时代,为我们努力拼接出一种文学的可能的精神图景或者理想秩序。但我们也要同样看到排行榜、文学奖背后的那种潜在的危险,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文学奖,在刺激着作家创作、成长的同时,也让作家陷入某种创作的圈套和成长的拘囿之中。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获了奖之后,不仅没有引发创作的新高潮,反而倒逼出了才情的枯水期。

记者:你在《谎言的默许》后记中写道:“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一种自我的感受力和‘稀有的判断力’。”我虽然不是完全明白这其中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所指为何,但我知道这两个“力”,对批评家做好批评,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你觉得经过这些年,你找到了吗?如果说找到了,是怎么找到的?如果说没找到,又当怎样继续寻找?
韩松刚:所谓感受力,主要是指一个人与外部世界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内在感觉,同时,将这种感觉与自身所面对的文学世界相对照,并由此更好地认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所谓判断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独属于个体的自我定义,反对同质化的认知,并为文学的一切可能性辩护。我觉得自己正在努力去实践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理想吧,就像开始时我所谈到的,把自身投入其中,通过语言去抵达文学的精神内部,通过一种非理性的直觉去发掘文本或者作者背后所隐匿的秘密东西。
原标题:《韩松刚: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访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