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学术出版造势: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与出版商
商业科学杂志的崛兴
科学杂志的转型大致发生在19世纪中期,在此之前,科学杂志的性质定位如同“科学家”身份一样是暧昧不清的,它们与科学新发现的宣布并不相关,更像是一种绅士行为准则,如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礼貌性地在《林奈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Linnean Society)上宣布其自然选择理论那样。巴贝奇意图模仿法国科学家们的例子,只因后者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无论何人,科学事业最重要的成果总会在如《巴黎科学院周报》(Comptes rendus)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正式的科学发现通告,这是巩固科学家权威地位的必经道路。
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则是另一番模样。当时绝大部分新成立科学组织的会刊基本上都模仿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四开本、宽边距、大字体、优良光亮的印刷纸,多含有大量手绘彩色插图,经常不定期发行,期号安排不紧不慢。毫无疑问,这样的会刊耗资昂贵,售价亦无法压低,加之不规律的出版节奏,导致印量和销量皆常陷入低迷。购刊顾客主要是资产丰厚的中产阶级绅士与贵族,他们将目光投向讲述地质学、动物学、解剖学、星体天文学等潜在新科学研究的刊物,让此类制作精致的科学刊物充实自己的藏书室,暗示他们收获、储藏的知识是有永恒价值的。
19世纪中期,这些“养尊处优”的会刊遭遇了商业出版公司的新型科学杂志的挑战,它们采纳八开本版式,每月定期发行,重点照顾普通读者的知识储备和阅读口味。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部颇为长寿的《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该刊由苏格兰的铅版改良者亚历山大·蒂洛赫(Alexander Tilloch,1817-1893)创办于1798年,约五十年后,随着杂志合并当时另外三家知名科学杂志——尼科尔森的《自然哲学、化学与艺术期刊》(Journal of Natural Philosophy,Chemistry,and the Arts)、专注化学的《哲学年鉴》(Annals of Philosophy)和《爱丁堡科学学刊》(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它变得更加专业化,涉及知识领域缩小到集中探讨物理与化学两门中坚学科。随后,它成了著名科学出版集团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旗下的重要学术刊物,在伦敦科学出版贸易中享有盛誉。此外,当时集团领导人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1781-1858)在同一时期将博物学研究从中分离出来,单独发行一部《博物学年鉴杂志》(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也兼并了另一批难以为继的博物学月刊,继续面向普通读者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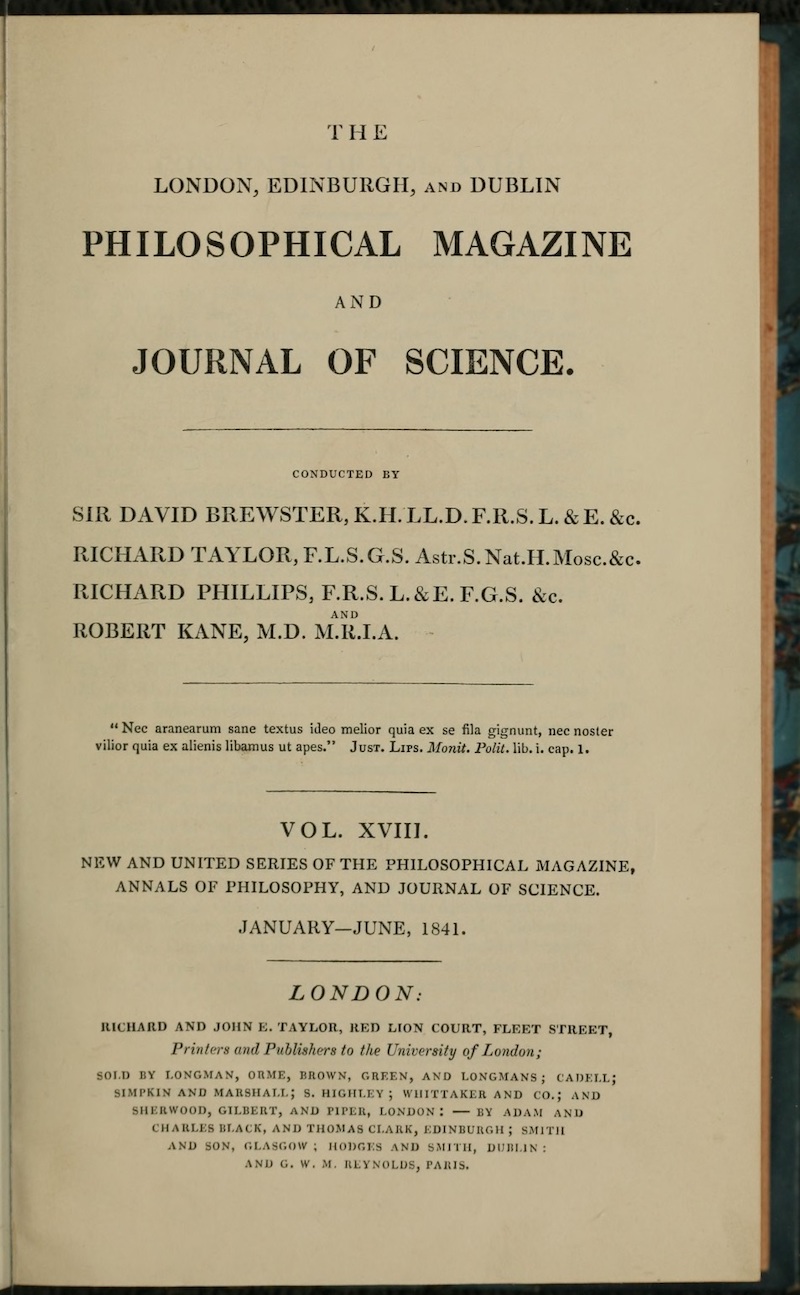
1841年上半年版《哲学杂志》,扉页文字表明该杂志已合并《哲学年鉴》和《爱丁堡科学学刊》
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这一批商业性科学杂志可谓“规则改变者”。它们通过定期出版,强调学术发掘的及时性而非仅是知识的长远价值,注重实用而非冗长的展示,以此重新定义了一部“科学刊物”的现实意义,变得更像英吉利海峡对岸如法国《化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或德国《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那样亲近读者的科学月刊,后者在大众读者中间笼络了一群拥趸,热销一时。这些杂志更加精简、页数更少,内容集中在某些具体的科学新发现上,“探索”甚于“博览”,更像是报纸上的文章。它们是新时代的产物,与读者有种携手并进的亲密关系。
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科学出版取得勃兴的调性,便是在转向集中于笼络普通大众读者的前提下,争取缩小涉及知识范畴,在某一点上着重吸引特定兴趣读者,因为这时候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英国人已经不同往昔,他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度更高,需要更详细深入的科学探究阐释。上述科学刊物的变革与科学出版业的三缕新风相伴随,它们毋庸置疑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以精英学术和大众知识和谐共筑的“科学帝国”基础。
首先,新的科学印刷业成型,尤其是摄影术、机械工程学和科学化管理的应用。到19世纪末,甚至是高度学术化的科学杂志,包括科学书籍中的网目铜版照片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木雕刻印图画,成为图像例证的标准形式。同样,彩印也在横空出世的短短半个世纪内进入许多科学出版物的内页,无论是昂贵的学术专著还是普及性的大众读物,这一切皆因摄影技术更全面反映真实原景原物细节的能力,远非雕工绘画可比拟,也最终保障了科学作家及出版商所希冀作品拥有的学术权威;机械工程学造就了机械制动的印刷与排字工序,极大地增速了书刊的生产流程;科学化管理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让印刷所成了流水线车间,更容易促进印刷程序与工艺制式的双重标准化发展,以及最后书刊的廉价走向。
其次,科学出版社新老交接,坚持“绅士准则”、依赖绅士科学圈子供应的约翰·默里与朗文公司不再是科学出版的独行者,更年轻并充满活力的新一代知识出版商如劳特里奇、麦克米伦、基根·保罗(Kegan Paul,1828-1902),较之前辈而言更注重前沿学术趋势。
最后,是教育改革增长了人们对各个层次的科学教科书与参考书的需求,这是让科学家摆脱私人赞助制度,更多地利用国家与教育机构基金来出版学术作品的一大关键,有专业基础和兴趣的读者与接受过通识教育的读者能够共襄科学进步的盛举。
在此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自然》(Nature)杂志。《自然》早期发家时的自我定位其实是不明晰的,出版商希望延续伦敦《雅典娜学刊》(Athenaeum)立下的传统,用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画像、简单科普性质的绘画和专题介绍来寻求畅销的可能,结果却不受市场青睐,公司也长期陷入资金困难的境地,一度在19世纪末濒临破产。此时,《自然》的出版商才意识到新一代受科学教育训练过的英国人,其阅读口味并非在于科普,因为很可能他们的父辈就已经受过查尔斯·奈特《便士杂志》和《钱伯斯百科全书》等中低端科普书刊的滋养,甚至还读过几位伟大学者的学术论文。他们需要的是科学杂志进一步的“专家化”与“专门化”——换言之,要重新定义何谓“科学杂志”,让它成为扩大学术研究与创新之影响的标志性介质。于是,《自然》开始集结刊发科学新闻与学术讨论,并附带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报告。它在尽可能保证学科分支全面性的努力下,转向更长的出版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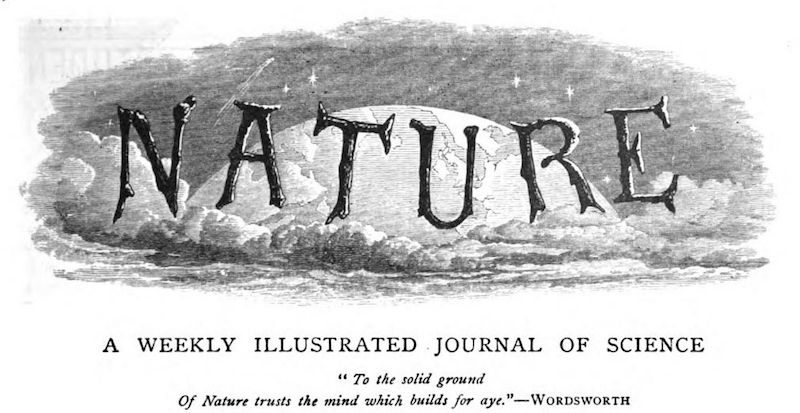
《自然》杂志沿用至20世纪的图文标识
其他一些随同《自然》发展起来的职业科学刊物,则更直接地选择收缩学科专注面。如前所述的《哲学杂志》,明确地瞄准对物理领域有学术旨趣的读者,它在20世纪早期的物质理论大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刊登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约瑟夫·约翰·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等物理学家关于原子结构与量子理论的关键性论文。剑桥大学《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自1878年创刊起,便是生理学教授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1836-1907)的“剑桥实验生理学派”成员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渠道。同样,《遗传学期刊》(Journal of Genetics)也承载着生物学教授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创建新遗传学科的冀望。这些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刷出版的学术刊物逐渐在全世界部署了供稿作者与编辑团队,乃至相应地在全世界各大学、专业图书馆与技术机构拥有了广泛的订阅者。所有这一切的实现,便是商业科学杂志崛兴的自然结果。
科学书籍的传统与变革
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结束,科学知识的学术出版虽仍由期刊行业主导,但19世纪中下期以来科学书籍也开始散发出巨大光芒。期刊的系列出版特性使出版商便于和书店、读者分摊成本,从而通过增进发行量来抢夺市场份额。然而,期刊出版也带来了一些不便,最明显的是个别学科(比如实验物理学与化学)在期刊上获得了绝无仅有的优先权,占据了几乎所有科学杂志的多数版面,是原创研究和“科学公开”类型文章的典型来源,但最终倾向于留存在小范围的专业图书馆馆藏中。科学书籍则不同,这种版式使它们保留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例如作为实用知识的参考文献、作为延伸和引发议论的方式以及作为学科范式的象征。它们有更丰富的读者谱系,常常出现在不同社会地位与等级的人群之间,在公共讨论时亦更容易被注意到。
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科学书籍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作为参考文献,将学术知识的流动“映射”到实用范畴上,这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牛顿、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不列颠悠久传统之传承。像玛丽·萨默维尔的《论物理科学的关联》、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这类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却旨在促使读者理解科学的规范、内涵及其更大的社会目标,它们迥异于科学杂志的专业化趋向,无意专注于特定的分支学科,而是以整个科学为舞台。
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种“映射”所具有的巨大开阔性,尤其显著于激发广大民众对心理科学及进化论的爆发式争论浪潮之中。1844年,一部匿名的书稿《造物的自然志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经由伦敦医药书籍出版商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801-1875)出版,如今已证实是知识出版商同行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65-1933)入行前所著。当时,这部书破天荒地将全面的科学门类以百科全书式的方式整合进发育进化论的机理,并解释为生物按照上帝法则从原始向复杂形态的进化,尽管并没有多少实在的证据,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版在博物学界与民间同时引起了现象级轰动,影响了达尔文、洪堡等一批重要的专业性科学家。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时,民众对人类进化的反应态度已没有那么剧烈了,不仅仅是因为《造物的自然志遗迹》及其后续种种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册子,还因为达尔文与约翰·默里这样拥护专业科学权威的大出版商之间的紧密关联。正如达尔文本人声称,他的书将吸引所有“科学的”与“半科学”的读者,并掀起接下来一个世纪的进化论主题通俗论著的出版之潮,而除默里以外,朗文、麦克米伦、诺格特乃至剑桥和牛津大学的出版社,也多多少少依靠对相关作者的资助最终加入大众科学出版的队伍。
相应地,这些讲求实用的科学书籍也很快进入书商的畅销书单。剑桥大学的出版商约翰·W.帕克(John W.Parker,1791-1870)曾出版一系列科学、哲学、艺术学等方面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书籍,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三卷《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和两卷《归纳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以及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名著《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19世纪下半叶,整合后的麦克米伦成为全英国资本最雄厚的龙头出版公司之一,也开始向科教与学术领域进军,曾出版大量关于达尔文进化论争议双方的书籍以及许多普及性科学论著,如1870年为提出价值边际效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出版基础教科书《逻辑学初级教程》(Elementary Lessons on Logic)和诠释“同类替代(Substitution of Similars)”的论文《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
19世纪末,中产阶级读者兴起带来的结果也是实用性科学书籍规模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交汇出一种新的科学出版现象——科学系列丛书逐渐流行。伦敦出版商基根·保罗公司创建的“国际科学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从1872年开始至一战前夕,共发行98卷,丛书旨在说明其是“精美、珍贵的大众科学文库”,而且拥有“新颖的设计、迷人的形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适中的价格”,对“吸收实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19世纪已有科学著作经典组成的系列丛书也变得层出不穷,比如伦敦出版商约瑟夫·M.登特(Joseph M.Dent,1791-1870)在出版了丁尼生、简·奥斯丁和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系列后,于1904年正式推出“凡人书库丛书(Everyman’s Library Series)”。这套丛书每本售价仅1先令,但主题涉猎广泛,包罗万象,也精选了不少知名科学家,如电磁学家法拉第、地质学家休·米勒(Hugh Miller,1802-1856)等人的经典作品,在20世纪初取得卓越成功。1913年,登特还顺势推出多卷本的《凡人百科全书》(Everyman’s Encyclopaedia)作为补充,各卷可分开购买。
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对外报告实验室研究与田野调查结果方面,科学书籍确实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它们不仅仅映照着“科学”与博物馆的持续联结,而且作为对公共或私人陈列实验标本的周密观察,它们实质上就是一种“纸上博物馆”。在今天,此类科学书籍或可称为“论文集”,它们以作者围绕单一专题撰写的大量论文构成,有时甚至分为多卷。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出版形式逐渐成为作者展现、检验其专业学识与能力的社会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科学论文集的出版形式,本来是很可能被其相对内行的学术话语限制在一小撮职业科学家圈子内的,但它又是如何在维多利亚时代收获足够大的读者群体而得以成为上述“社会标准”?诚然,那些论文集大多设计有十分美观的版式,增添了彩色插图和表格,印刷质量上乘,都有利于向大众传播,但最重要的还是英国18世纪传统的绅士阅读习惯——如古物研究(antiquarianism)的旨趣再次起了作用,被如此自然、正当地吸收进新科学中。尤其在博物学、地质学和机械学方面,学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促使那些针对地方性的、在知识体系上并不细致但较为综合性的书籍不再受专业研究者(如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物理动力学家)青睐,转而成为大众读者争相捧读的对象。比如早些年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1792-1871)的《志留系》(Silurian System)和稍晚些年查尔斯·伯德(Charles Bird,1843-1910)的《约克郡地质学概览》(A Short Sketch of the Geology of Yorkshire),都明确向有志于农业或矿业进步的乡村绅士读者致语,从而让博物学与地质学书籍有了和传统神学、古典书籍并驾齐驱进入绅士藏书室的资格。
既然科学书籍已经突破收支平衡点,进入大众市场,在论文集的出版商眼中,当然获利门道多多益善,因此他们在笼络爱书人、藏书家和对新鲜事物尤有兴趣的绅士读者的同时,自然不会放弃专家读者。例如博物学书籍中常有将动物、花草、鸟类表现得活灵活现的精美插图,很容易给予专家读者直观的感受,激发后者创作学术论著的灵感,形成一个隐形的、非功利性的但却意外富有成效的博物学研究、扩散生态圈。

博物学家约翰·雷的半身肖像,在雷学会的所有资助出版物上皆会印刷该肖像作为学会标志
博物学的这种市场表现在19世纪下半叶达到巅峰。同一时期,潜在的专家分化也开始了,他们以“旨趣集团”为中心的出版行为很可能与学科的细分专业化,特别是动物学、植物学、分类学、化石学和实验生理学相生相随。比如,19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建立了许多专门的科学学会,资助会员在博物学细分领域的书籍出版。成立于1844年、以17世纪英国“博物学之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命名的雷学会(Ray Society)的一大宗旨即发行动物学的新著或译著,曾出版过达尔文关于蔓足纲生物分类的卷宗。而1847年伦敦一批化石专家建立的化石学会(Palaeontographical Society),则是专门为了出版诸如腕足类生物壳体或脊椎生物化石等主题的研究成果。毫不意外,“旨趣集团”的出版实践将同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作者、出版商、书商和读者维系于同一知识通道,大大提高了思想交流的效率。
无论如何,在19、20世纪之交,科学家、出版商、学术机构乃至政府赞助者的联合意味着,科学书籍相比一个世纪前已经破除了诸多传播上的桎梏,拥有了稳定得多的市场商机,所占销售份额亦节节高升。老牌出版商增加了科学书籍出版计划,一些新的出版公司也将科学书籍作为其生意的一项基本组成部分。从出版商的角度说,使之成为可能的——或者说在市场影响上他们最为看重的,当然是科学书籍的实用教育意义,这一点与科学期刊截然不同。如果说如达尔文《物种起源》那样的划时代著作所具有的是宏观象征意义——重新拟定了专业科学的变革方向,那么教科书这一特别书类便在较低的生活层面上不断装点、完善着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大厦,让新的科学思想在大学环境中日趋发酵。
另一个便于出版商发挥力量的地方,便是初等教育。在19世纪之前,小学课堂上还没有标准的几何、代数教科书,对于初阶的数学原理教学,小学教师一般使用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长期通过二手书贸易来满足需求。《几何原本》在18世纪得到了不同种类的改编、调整与修订,不少传统主义教育家仍将其视为当代最好的几何概论书。但到19世纪末,新的科学出版商试图挑战这一古代权威,指出工业经济时代的几何命题不应由一位遥远的古希腊人来指导。
有些专业化的科学分支,如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理学,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大规模进入小学教纲的。虽然钱伯斯兄弟公司从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就已开始定期出版科学教科书,但大部分适用于家庭自学而非正规学校教学。1870年《初等教育法令》(Elementary Education Act)规定实施国家统一标准的世俗学校教育方案,奠定了学校管理教俗分离的基础,开启了近二十载的初等教育转型之路,最终造就了学校对基础科学书籍的巨大需求。麦克米伦公司再次走在了变革前沿,从19世纪60年代起发行了版本众多、特色鲜明的初等科学教科书,如1866年初版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基础生理学教程》(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和亨利·罗斯科(Henry Roscoe,1800-1836)《基础化学教程》(Lessons in Elementary Chemistry),并且在接下来数十年内不断再版,均卖出超过20万本。
此外,面向中学和大学使用的科学教科书亦迎来转机。在当时,大学教育体系本身的改革已然为科学理论、经验与学习法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无论是在学生还是教师群体当中,科学教科书的市场蓬勃扩张。比如,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迈克尔·福斯特的《生理学课本》(A Textbook of Physiology)由麦克米伦于1870年首次出版,此后在英国各大学普及开来,成为大学中建立进化论科研传统的关键角色。相似地,1882年麦克米伦还出版了苏格兰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的大部头《地质学课本》(Text-book of Geology),在各大学同样得到教授们的推荐和使用。19世纪末开始活跃的剑桥与牛津两所大学的出版社,甚至也将科学出版作为事业主要支柱。在“漫长的19世纪”,科学出版物的变迁可以说是一部英国知识精英逐渐走出孤立状态的故事,更不必说维多利亚时代从盛期到晚期,那些作为作者的科学家实际上跻身为科学工业大发展的社会里居于领导的角色之一。他们的出版物传播受益于市场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和各类机构对知识的出版资助,同时也受益于印刷的进步与科学知识出版商的高瞻远瞩,后者将科学家的笔下计划付诸为真正的实践,且为之布下恰当的、富有远见的读者宣传。新的科学杂志与书籍强调“科学”知识在大英帝国中的显著位置,催生了自由科学作家和学科专家的联盟,使科学从实验室既能到达贵族和精英手中,也能到达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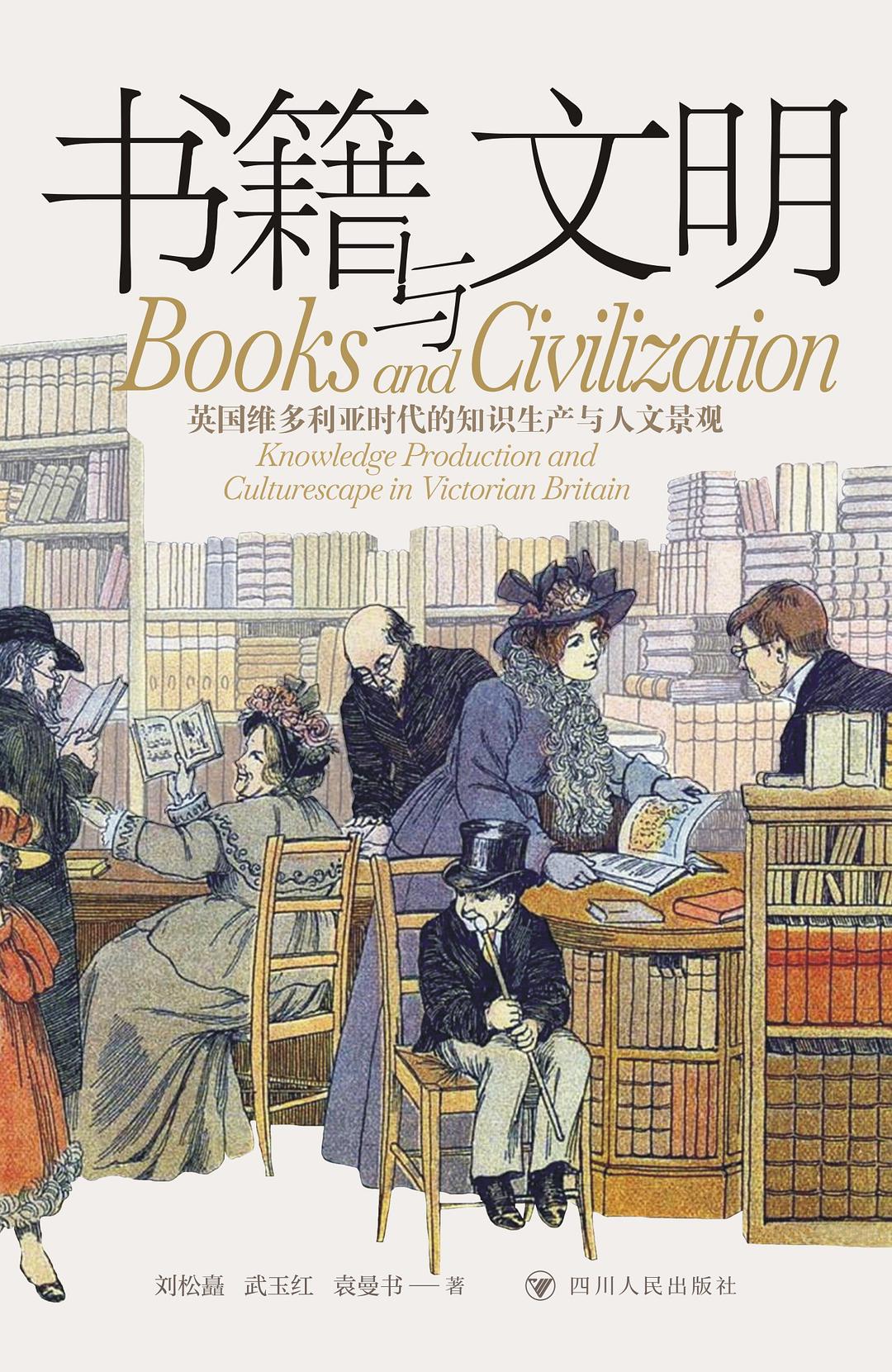
(本文摘自刘松矗、武玉红、袁曼书著《书籍与文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文景观》,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