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塑造观念的人|汉斯·贝尔廷:图像在场与全球未来
2023年1月,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柏林逝世。汉斯·贝尔廷是德国学者与思想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广义)艺术史、拜占庭艺术,以及他命名为“全球艺术”的当代艺术,而所有这些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图像人类学”(Bild-Anthropologie)。

汉斯·贝尔廷
汉斯·贝尔廷于1935年7月7日,出生在位于渗透性边境三角区的罗马小镇安德纳赫(Andernach),诗人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也是安德纳赫人。事有巧合,贝尔廷一生都在对抗瓦尔堡(Aby Warburg)指称的边防警察(Grenzpolizei)。
贝尔廷1959年在约翰内斯·谷登堡-美因茨大学获得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此后他主要的研究与教学活动都在德国,1966年短暂任汉堡大学讲师,1970年到1980年在海德堡大学任艺术史教授,1980年到1992年在慕尼黑大学任艺术史教授,1992年到2022年任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艺术史与媒介史教授。但贝尔廷的学术是世界主义的,他在哈佛大学(尤其是敦巴顿橡树园)、哥伦比亚大学、法兰西学院、西北大学、海德堡科学院、柏林高等研究院、柏林莱布尼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等大学与机构都有过任职痕迹。
贝尔廷曾获得无数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尔赞奖(Balzan Prize),奖金被用于“图像在场:宗教图像”(Iconic Presence. Images in Religion)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在柏林自由大学、莱布尼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马萨里克大学都有设立。
2014年3月22日,贝尔廷在北京大学做了题名《艺术终结了吗——中德学者对话》的讲座,与谈人是潘公凯,主持人是彭锋。根据彭锋微博,讲座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大报告厅现场座无虚席。贝尔廷的讲座内容是其图像学大纲,讲座后的报道特别指出,“反图像崇拜者对于图像的销毁只是有限的成功,它们仅仅销毁了图像的媒体支持,却反而强化了无形图像本身的存在。”这不是贝尔廷第一次来中国。根据付晓东微博,贝尔廷此前于2013年3月25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做过一次讲座。
从透视说起
1924年,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发表了一则题为《透视作为象征形式》(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的文章,从那之后透视学就成了热门话题。正如文章标题所示,帕诺夫斯基称透视为 “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即透视比模仿论多了主观的成分。
透视学最重要的建设者应当是阿尔哈曾(Alhazen),他出生于巴士拉,后主要活动于开罗。他曾受哈里发之命为尼罗河主持治水工程,但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1028年到1038年,阿尔哈曾在哈里发的庇护下撰写流传后世的光学著作,其中就有《光学之书》(Kitāb al-Manāzir,Book of Optics)。《光学之书》流行于安达卢斯(现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精英阶层,大约1200年安达卢斯重回基督教王国后,该书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名为《透视》(Perspectiva)。该书最早的英文版于1989年由瓦尔堡推出。
阿尔哈曾认为,可见物之所以被看见是因为在发光体的照明下,它们以点的形式反射或者发出光线进入了人眼。这与传统认为光线从眼睛发出的理论完全不同。此外,他还涉及了随环境变化而呈现出来的像变(khayāl),以及物体在心像中的心理再现(ma'ānī)。
13、14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对视觉的态度以经验主义为主,图像被看作是感知经验的类似物。东方的精英群体在感觉上保持着对人类经验或人类本质的怀疑,在精神上相信人类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其自身并非创造者,同时东方艺术充满了数学意味,更趋向抽象。在阿尔哈曾看来,图像并不来自眼睛,而是来自想象力。而这决定了西方和东方关于想象力和凝视持有不同的态度。古代西方的想象力与知觉是隔离的,而东方则肯定了想象力和知觉的关联,后者没有妥协,也不全然像西方那样需要一个主体。在古代西方,凝视和眼睛一起行动,凝视是好奇的、大胆的、易受诱惑的,而东方则不同。
在文艺复兴时期,透视(perspective)被引入艺术领域并被看作“光学”(optics)。此前,透视常见诸中世纪科学家的笔下,它代表着来自阿拉伯的视觉理论,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就在双重意义上使用透视一词。
阿尔哈曾的光学创造了现代光学的起点,罗杰·培根(Roger Bacon)、威特罗(Witelo)、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人都接受了他的理论馈赠。罗伯特·弗劳德(Robert Fludd)在1618年为百科全书读者描绘了透视的原理:被分成几个方块的屏幕(tabula)摄取了艺术家所见的景色,而与眼睛相连的笔(stilus)将其写拟在画纸(carta)上。而我们今天熟悉的,阿尔伯蒂的窗口、丢勒的透视仪器、暗箱、摄影、电影,都可以说是阿尔哈曾光学技术化的产物,这份清单还可以扩展下去,建筑、剧院……经由文艺复兴文化,也经由摄影术与照相机,透视被塑造为我们观看的本能,故而贝尔廷称之为一种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

《拜占庭艺术与西方》( Byzantine Art and the West)
透视从东方到西方的历史少有人知,因为贝尔廷念兹在兹的全球与世界在知识世界并不是第一时间存在的,甚至说全球与世界距离成为普世价值仍有漫长的距离。贝尔廷在评论奥托·德穆斯(Otto Demus)的《拜占庭艺术与西方》(Byzantine Art and the West)时就曾指出,如果不是希腊化时代的板画变为拜占庭的圣像画,并被移到西方,西方绘画的主要载体就不会出现,或者很久后才会出现。
图像的力量:圣像
1978年的某一天,艺术史学者迈克尔·卡米耶(Michael Camille)正在新圣母大殿(Basilica di Santa Maria Novella)用所学描述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木十字架的造型,体验着艺术存在所赋予他的快感。此时在教堂角落里,有个黑衣老妇人拉着一个年轻女孩的头发,拖拽着她往十字架走来,老妇人频繁地敲打着女孩的头,嘴里念念有词。迈克尔·卡米耶突然领会到,她在为她驱邪,面前的艺术仿佛打开了另一种面目。
震惊迈克尔·卡米耶的景象与“相似性”(Likeness)概念有关。以贝尔廷在早期著作《中世纪图像及其观众》(Das Bild und sein Publikum im Mittelalter》中提及的13世纪末埃米尔的圣克里斯托弗(Florence,Bibl. Med. Laurenziana,Plut. XXV.3,fol. 383)为例,观众相信观看它时就能获得被保护的力量。
贝尔廷的崇拜图像将目光局限于“艺术哲学图像”(kunstwissenschatliche Ikonenmystik),而摒弃了叙事性图像(narrative imagery)、雕像和金属制品。那些不具有相似性的替身,比如石像(klossos)、纪念碑,也可以看作图像,贝尔廷命名为“非图像性”(aniconic)图像。
基督教在是否描绘神上并无明确的回应——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反对描绘神,而印度教与佛教不反对。回溯来看,在绝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基督徒对描绘基督都表示了支持,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如此丰富的遗产。然而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中期,一场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持续了一百年,这场运动开始于来自叙利亚的伊苏里亚的利奥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圣像毁坏后,取而代之的是十字架,十字架代表着312年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战役见证的神迹。面对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皇帝,教会和信众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
拜占庭文化无疑是保守的,其根源在于等级制度、行政机构渗入到所有细节之中。受过教育的拜占庭人认为,所有非教学性和非宗教性的高雅文学都应该用古希腊的阿提卡方言来书写。在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的想象中,中世纪存在着两股势力,其一是前行的,指向自然真实与智识活动,其一是回溯的、抑制的,意在实体性完美与智识虚无。拜占庭就属于后者,它的束缚并不在想象目的而是艺术。
毁坏圣像运动后,拜占庭教堂重又恢复各类圣像,且面积更大,色彩更绚丽。867年,主教佛提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东侧后堂为一幅巨大的圣母和圣婴镶嵌画举行了揭幕仪式,佛提乌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原样修复。
不妨走出中世纪看一看图像的力量。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地毁坏阿兹特克人的图像,谴责其仅仅是奇怪的物体。在第一时间,他们并不关心这些图像对原住民的意义,而是从这些图像中抽象出他们重新解释为风格的东西,从而消解了图像和媒介的原始共生关系。
如果说殖民时代及之前的历史,图像所蕴藏的能量还可以轻易被丈量、理解,那么殖民时代之后,图像的能量就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2006年,罗马梵蒂冈博物馆为其500周年纪念举办了题为“博物馆的观念:特征、职能和前景”的研讨会。梵蒂冈是一座教堂,且还在使用,如今它又成了一座博物馆。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一直是基督教的圣地,每个基督徒都被要求在他们一生中至少瞻仰一次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容——“真正的圣像”(the true icon)。如今,对此类图像,比如都灵的“耶稣裹尸布”(Holy Shroud),除了全球性的吸引力之外,已经少了许多对其本身重要性的关注。

梵蒂冈
由于技术和网络的存在,从图片到图像的演变逻辑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易、从容,读者躺在沙发就可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图像,关于政治的、关于寓言的、关于个人的,这些图像好像第一次拥有了不死的身体,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让我们如此真实地见证和认知这些图像,而那个只有捕捉这些图像人才能存在的日子早已到来。我们一下子到了如此境地,死亡随时会发生,而发现不死愈发关键。贝尔廷写道,“图像就类似于游牧民族,它们跨越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分隔开来的界限,并借居在处于某个历史的位点和时刻的媒体,而后转移到下一某个,就像沙漠浪人的临时营地。”
“是什么让我们揭竿而起?”像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这样的思想者仍然接近着也许并不古老的图像,“我们暂且可以假定那是一种来自我们记忆的力量,当欲望燃起,欲望的力量与记忆的力量共同燃烧——而图像的任务,则是用我们的记忆,藏在欲望深处的记忆点燃我们的欲望。”
图像人类学
在后来的图像人类学中,贝尔廷将图像视为身体的替代品,并将身体和物理图像视为实体,想象的图像被印记或投射到这些实体上,这与让-克劳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的历史人类学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就如史前人类制作“死亡图像”(Todesbilder)是为了让逝去的死者重新具有形体一样,所有时代的图像的根本目的是使用象征的手段为不在场的某人或某物寻找一个替代物。
图像、媒介、身体,这是贝尔廷“图像、身体、媒介:一个人类学的视角”(Bild-Körper-Medium. Eine anthropologische Perspektive)研究小组的名称,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Bild-Anthropologie: Entwürfe für eine Bildwissenschaft)的副标题。图像、身体、媒介是图像人类学的三位一体,即作为概念的图像,作为载体的媒介,作为图像位于现场的身体。那么图像的定义就是:图像存在于它们媒介中,但它们展演为不在场,在其中它们使自己变得可见。

《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 Bild-Anthropologie: Entwürfe für eine Bildwissenschaft)
汉语词图像与德语词Bild并非完全对应。为了方便解释,引入英语词image/picture(图像/图片或图画)。图片是物质的,可以被破坏和损毁;而图像存在于记忆、叙事、媒介、踪迹和想象中。实物斑驳时,图片也会污损,但图像仍然保存着,呈现着。陈列于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图书馆编号D.O.MS 3的拜占庭神像,经年累月被信徒亲吻,脸部磨损仅留下模糊的痕迹。这些象征着基督之爱的吻,对基督图像并没有伤害,或许恰恰相反,这些吻爱护着基督图像。
简短概括贝尔廷意下的图像:图像既不存在于墙面上或屏幕上,也不独自存在于头脑中,但图像存在着,通过传播和感知,图像被我们拥有,等待着被召唤,它出现或消失的每一次都测量着语言和经验之间的距离。
白南准的录像装置《TV佛》几乎是完美解释图像的标件。《TV佛》是白南准早期的录像艺术作品,也是他第一部被美术馆收藏的作品。该装置仅有佛像、电视监视器、封闭回路的摄像头三个组成部分。白南准一开始没有采用闭路装置的形式,而只是将佛像作为观众观看电视中放映的节目画面。但很快他改变了想法,把佛像放在了电视机的对面,将一台摄像机放置于电视机身后并与之相连接,拍摄这尊佛像的影像使佛像通过这种传输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从佛像到电视监视器到摄像头,佛的图像转了又转,观众几次看到了图像,但图像不在那里,这就像图像在无数故事、描绘、书写之中。
当贝尔廷的艺术史将中世纪艺术和当代艺术结合起来,置入同一叙述和互补辩证中,图像也既存在于前现代的视域,又存在于后现代的视域。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艺术界1990年代以来的趋势,即杂糅了中世纪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美术馆,比如马修·巴尼的神话。在媒介与身体中的图像拥有的是一个超越性的主体。“主体之死之死”,贝尔廷暗示我们,仅仅将主体视为不稳定、流动、多元的存在并不恰当。
1976年时年28岁的杉本博司开始了剧院(Theaters)系列(2013年再次重启),他走访汽车旅馆、电影厅、电影院,进行某种田野志的拍摄。杉本博司在拍摄过程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曝光,一场电影时长几乎相当于十七万张照片同时摄入一张胶卷,暗黑的空间刹那闪耀出白色的光芒,如此神秘崇高的残像被杉本博司称作“死的过剩”。十七万张和一张: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存在之上便有影子落下。那个影子自然地将不是影子的部分截取了模型,存在开始显现形状。这一显现的形状便成为了持续背负着影子的那个存在的代言者。”杉本博司在当时的笔记本中写道。

杉本博司的作品
迈克尔·卡米耶(Michael Camille)批评贝尔廷,“如果图像的历史和物的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图像史只有结合社会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见解,我们才能更进一步,而贝尔廷的学科局限阻止他迈进这一步。比如,贝尔廷将图像崇拜归因于民众,以及来自下面的压力,这在社会学上已被证伪。进而言之,如何谈论和使用神圣的东西,同时将自己完全置于它之外?”
这些批评不仅指向了贝尔廷的研究,还指向了图像学既有的困境。正如其在《艺术史的终结?》中所提及的,“图像学在其最狭窄和最教条的运用上,甚至比风格学的批评更不可能构建其所希望的那种综合的艺术史,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认清那种艺术史的真正的目标。图像学将不得不违心地解除对高雅艺术的古典样式的限制,并拓宽探索其他图像和文本的领域。正像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李格尔确实已经做到了这些。他深思熟虑地把艺术风格发展的概念转换到所有后来被称为物质文化的东西上,转换到时尚和日常消费的客体上。他的方法明显地符合由新艺术实施的生活环境审美化的需要。但恰恰是这种对定义和界限的痴迷,自我暴露了使艺术成为艺术史的目标有多么困难。”
作为文化科学
无疑,贝尔廷继承了瓦尔堡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必须承认,图像人类学的方法是全景式的,它不拘泥于年代、分类学、风格学。如莫克西(Keith Moxey)指出,图像人类学令人想起人文领域内尝试建立的学术客观性传统,这种客观性是由未被注意到的主观性来保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完全屈从于自然科学的压力,那就会导致人文科学的非人性化。
1981年5月,在为庆祝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立二百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统一与多样:心灵的生命”(Unity and Diversity: The Life of the Mind)中,贡布里希发表了题为《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的演讲。贡布里希认为,瓦尔堡研究院的最显著特征并不是它的某种特定研究方法,而是它意识到了文明的整体性,是它坚决不受瓦尔堡称为“学科边防警察”阻挡的决心。未被贡布里希言明的是,瓦尔堡的文化科学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流失了大量养分。在关于忧患之子(Schmerzensmann)的研究中,潘诺夫斯基从类型史(Typengeschichte)的角度追溯忧患之子主题的谱系,对主题的前兆、变体及后来的修正进行整理和分类。而贝尔廷更关注视觉形式的多样性,对他来说形式和功能不可分割。贝尔廷希望打破这个僵局,他取用文化人类学作为起点,其本身就是反对内部外部、内生外生的二元对立。
传统的符号学将图像学限制在符号、信号、交流之内;艺术理论对威胁到其既有且专有的图像理论持保留意见;科学尤其是神经生物学排除了人工制品的感知,而图像学试图留下来收场,这是贝尔廷在《图像、媒介、身体:图像学的新方法》(Image,Medium,Body: A New Approach to Iconology)中所明确的意图。
此外还有常被忽视的一面,即贝尔廷作为中世纪人的一面,中世纪艺术持续地塑造着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史,典型的如哥特式复兴、前拉斐尔派、威廉·沃林格。“图像在场:宗教图像”(Iconic Presence. Images in Religion)涉及人类学、艺术史、宗教研究的相遇。
除了应和人文科学广泛的人类学转向,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还内含了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关于阐释学,他曾表示,每一种自我反思性的艺术史都是以一种阐释学的传统为基础的。而接受美学在不废弃当下经验与当代观众的情况下,谋求当代与传统的历史连续性或者永恒价值,这在贝尔廷的思想实践中表露太多。
图像学有很强的渗透性,以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为例,若将字词、意象、境地替换为图像学中的结构,古典诗歌的精神想象会得到进一步扩充,借由图像学,诗歌被表征为诗学、存在、宇宙的三重对话,而不再只是分开了主客的单一形象。如此说来,图像学是结构主义,也是现象学,同时也是人类学,既向语法之内超越,也向存在之内超越,同时也向万物之内超越。
在某种视域中,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艺术在范畴、概念上的确凿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的、自我认可的艺术——当然,不止当代艺术遭遇了它,其他艺术形式多多少少都遭遇了。图像学的出现,正与此类现象相关。瓦尔堡至今,图像学的流变正与艺术研究与实践的实局息息相关。而从今天的学术实践和策展实践来看,图像学为文化从业者提供了非常之多的工具和能量。
某种意义上说,图像学的发展与媒体世界的快速膨胀有关,传统的媒体研究和舆论研究都太细碎、务实,随着媒体展演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者在内的大部分受众都更认真对待了眼下的这件事,从那时起,媒体就不再是被研究、被注视的客体,而是与人类生活共在的“我世界”。这就是后来的媒介研究,图像学和媒介研究关联甚多。1970年前后,图像学在德国艺术史研究领域开始了复兴,它吸纳了广告、大众摄影、录像、政治符号等议题与方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贝尔廷在英语学术界影响有限,在英语图像转向中也称不上绝对的主流。不妨比较一下英语图像学、法国图像学、德国图像学的差异: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等英语学者关注图像和大众传媒,其旨趣是新教的,也是实用主义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等法国学者带有很强烈的精神分析的印迹,涉及诸多天主教元素,也是跨学科的;德国学者更关注作为媒介的身体(The Body as medium),属于罗马主义的中世纪艺术史一脉,到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 则拓展了“图像行为”等概念与视点。目前看来,英语图像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中介。
终结之后
1980年,贝尔廷赴任慕尼黑大学教席,该教席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汉斯·赛德尔迈尔(Hans Sedlmayr)也曾执掌过。赴任时,贝尔廷发表了题名为《艺术史的终结?》的演讲。
那是一个躁动、变异的时期,终结论和转向论纷纷登场。在艺术史领域发生的故事是,从乔尔乔·瓦萨里、温克尔曼发蘖的古典主义进步观都已失效。在所有终结论中,贝尔廷的终结论大概更加像只是挂了个名。《艺术史的终结?》所谈论的并非艺术史的终结,或者艺术的终结,而是艺术与艺术史的分离。其论点是,艺术史的指导原则及其以时代特点和时代变更为中心的内在逻辑已经失效,一种理所当然的艺术史的内在统一性越衰落,它就越会融入到人们可以将其归纳进去的文化和社会的大环境中。
1979年2月15日,巴黎蓬皮杜中心,埃尔韦‧菲舍尔(Hervé Fischer)手持皮尺,在观众面前走来走去,丈量着大厅的宽度。“艺术的历史是神话起源的历史。巫术的。时代。阶段。嗨!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新主义。样式。吭!离子。症结。波普。嗨!低劣。哮喘。主义。艺术。症结。怪僻。疥癣。滴答。”菲舍尔抓起一根绳子,悬在眼前,剪断它,向观众宣布,“我,在这个喘气的编年表上最后出生的,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在1979年的今天断言并宣布,艺术的历史终结了!关注当代精神的几何图像幻觉已经没有了,从此,我们进入了事件的时代、后历史性艺术(post-historical art)的时代,以及元艺术(META- ART)的时代。”这就是贝尔廷所援引的菲舍尔在《艺术史的终结?》(L'histoire de l'art est terminée?)以神经质的笔触讲述的故事。

《艺术史的终结?》
在如此普遍性的论述、高度个人的观点、超越历史的立场公开展示后,贝尔廷被批评为继承了汉斯·赛德尔迈尔的衣钵,后者认为现代艺术放弃了理想。在汉斯·赛德尔迈尔的视域中,十八世纪末图像学消亡的时期,原本整合统一的艺术被连根拔起,它们分裂和孤立了出去,像难民一样游荡,在艺术市场里寻找栖息之所。赛德尔迈尔甚至概括出七种趋势,1、“纯艺术”领域的确立;2、事物之间的对立性关系的破裂(多元化);3、对无机生命的深入探索;4、对坚固的地表的超越;5、迷恋低俗的而不是高雅的事物;6、人类的地位被贬低的发展趋势;7、顶部和底部之间的界定被解除。 概言之,中间值的丧失,艺术成为离心的艺术。面对当时的变局,赛德尔迈尔担忧整体的人性、帕斯卡的“心灵”统统都会消失,都会受到破坏,而人类及其创造力只能在碎片的状态中获得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贝尔廷的艺术史围绕元杰作(meta-masterpieces)而展开,即那些最吸引思想家与作家的作品,它们以自己的能量放大了艺术理想的可能,这是一个相当窄化的模型。为贝尔廷引述的是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杜尚、托马斯‧施特鲁特(Thomas Struth)、杉本博司,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从贝尔廷的艺术界想象中消失了。
1937年,规模最大的“堕落艺术展”(Entartete Kunst,Degenerate Art)在德国慕尼黑等城市展出,该展览贬斥了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他们被置于一个脆弱的对手——纳粹的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对立面。战后,纯粹的线条、形状、色彩重新被接受,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抽象艺术“支持”了对传统因果关系与逻辑的放弃;而神学家希望抽象艺术修补现代人的分裂。但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出生的一代发现了波普艺术和极简主义,它们强悍到没有任何对手。这就是贝尔廷,以及很多终结论学者比如艺术史领域的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出场时的背景。
换句话说,贝尔廷的艺术史与当代艺术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艺术史力图恢复一种失落的传统价值,而当代的艺术要么是用一种蓄意的现代主义方式逃避传统的规范,要么就是使这种规范成为其反思、评论、质疑和极端肯定的对象。这两种方案的共同之处只是在于他们都相信艺术家的天赋,当艺术史开始探索民族流派的进化和寻求艺术创造的普遍原则时,他们就分道扬镳了。显然,这样两种对立的目标不可能轻易地适应一种综合的处理方式。”贝尔廷在《艺术史的终结?》作了如上总结和展望。贝尔廷的方案并非一个完全综合的方案,毋宁说它是一个古典而又折衷的方案,但个体的、反讽的、错语的现代文化生活从未停止阻抗如此醇厚的全景,以及如此自在的大主体的出现,但它比以往世代都要依赖它的不稳定、它的失落,而贝尔廷的出格即失格正在于此。
从事录像艺术研究的经验向贝尔廷展示了,批评与艺术、理论与话语如何分割的,没有任何完全适用于录像艺术的理论,关于录像艺术的理论都是实验的,“因为理论不是诞生于直观,而是试图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放置在一个相同的概念下考察”。
不过,贝尔廷很了解当代艺术家的诉求。在当代艺术或者全球艺术领域,贝尔廷放弃了艺术史,理由是在一个后历史时期,艺术界的共识是逃离艺术史线性叙事。一如罗纳德·B. 基塔依(Ronald B. Kitaj)在《流散者第一宣言》(First Diasporist Manifesto)中告知的,所有人都在流散之中生活,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同时,贝尔廷富有洞察力地表示,全球艺术家正在将他们的族裔重新定义为个人角色和移民经验 ,如奈保尔以“来自非洲的艺术家”取代“非洲艺术家”。
不一样的欧洲
逝世后,贝尔廷的讣告有很大比例来自捷克语。其中几乎唯一一篇完整为悼念贝尔廷而作的文章也来自捷克,作者是伊万·弗莱蒂(Ivan Foletti),马萨里克大学艺术史系中世纪早期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arly Medieval Studies)现任主任。伊万·弗莱蒂将贝尔廷视为新近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突破了传统艺术史集中于媒介的“禁锢”,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图像上。
2014年12月,贝尔廷来到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艺术史系中世纪早期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会议。此后不久,贝尔廷将其部分藏书捐赠给该中世纪早期研究中心,这批书的到来填补了中心关于冷战时期藏书的空白,随后的2016年4月19日,汉斯·贝尔廷图书馆对公众开放。
“我的一个古老梦想是看到东方和西方之间发展出真正的国际主义。而史前史如此独特,它从康达科夫定居在布拉格时就开始了。”2016年贝尔廷对伊万·弗莱蒂表示,该访谈发表于《欢宴》(Convivium)。《欢宴》是由尼科迪姆·帕夫洛维奇·康达科夫(Nikodim Pavlovič Kondakov)创办的《康达科夫研讨会》(Seminarium Kondakovianum)的再生版,两者都关注中世纪欧洲、拜占庭、地中海的文化、城市、故事。
在贝尔廷与伊万·弗莱蒂的交流中,两者都提到了康达科夫。俄罗斯移民康达科夫于1922年抵达布拉格,由于捷克宽容的政策,康达科夫在布拉克重新发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他再次满怀激情地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康达科夫的活动,拜占庭研究在布拉格蓬勃发展,《康达科夫研讨会》(Seminarium Kondakovianum)、《拜占庭斯拉夫研究》(Byzantinoslavica)也由此起步。
时间拨回到1950年代末,时年23岁在攻读博士的贝尔廷,致信在敦巴顿橡树园的恩斯特·基辛格(Ernst Kitzinger),此前他在慕尼黑某次会议中遇到了战后第一次返乡的基辛格。基辛格1930年代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美术史,纳粹上台的第二年通过博士答辩,答辩次日就离开德国,他于1941年进入敦巴顿橡树园。很快,贝尔廷也来到了这里。当时,伊斯坦布尔圣尤菲米亚(St. Euphemia)壁画正在实施挖掘与考古工作,贝尔廷借此在鲁道夫·瑙曼(Rudolf Naumann)主持的伊斯坦布尔研究所做相关研究工作。
在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员和海德堡大学教授(贝尔廷之前有三人拒绝了该职位)之间,贝尔廷选择了后者,这似乎是最佳选择,因为不久后,教员们和研究员们就先后离开了敦巴顿橡树园。贝尔廷初来时,这里的研究院队伍还很庞大,有大卫·平里(David Pingree)、马古拉斯神父(Father Magoulias)、梅丽娜·梅尔库(Melina Mercouri)、皮娅·施密特(Pia Schmid)、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奥托·德穆斯(Otto Demus)、库尔特·魏茨曼(Kurt Weitzmann)也曾来这里访问。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初大量德国艺术史学者移民美国,比如潘诺夫斯基、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戈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使“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在美国开始扎根。
1972年,贝尔廷在《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Dumbarton Oaks Papers)发表了关于贝内文托公国(Ducatus et Principatus Beneventi)的研究文章。贝尔廷最后一次正式在敦巴顿橡树园出现是1990年参与赫伯特·凯斯勒(Herbert Kessler)主持的关于图像的研讨会,与座还有韦兹曼(Kurt Weitzmann)与恩斯特·基辛格。
在敦巴顿橡树园,贝尔廷接触到了来自东欧的学者,比如弗兰蒂谢克-德沃尼克(František Dvorník),这时,那个完整的欧洲第一次在贝尔廷的头脑中展开。
目光移换
贝尔廷除图像学三部曲外最重要的作品《佛罗伦萨与巴格达:文艺复兴艺术与阿拉伯科学》每一章节结尾都会有一个名为“目光移换”(Blickwechsel)的部分,这个词既可以指 “焦点的转移”(shift of focus),也可以指 “眼神的交流”(exchange of glances)。目光移换,从西方到东方。“与我们有关的两种文化有着长期共同的遭遇史,它们在其中相互启发或相互挑战。”贝尔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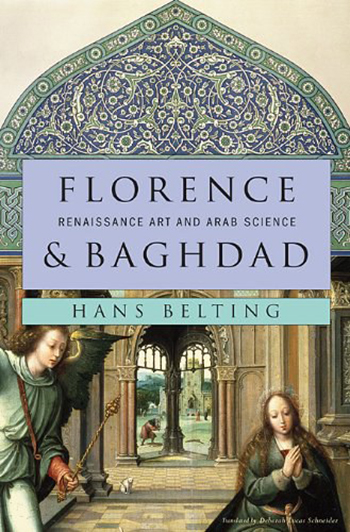
《佛罗伦萨与巴格达:文艺复兴艺术与阿拉伯科学》书封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我的名字叫红》虚构了东方与西方对艺术(细密画)认知的紧张关系。奥斯曼帝国苏丹每两个月“巡视”细密画家画室也就是皇家画家,画师们向苏丹介绍工作进度,绘制哪一本书的哪几页,谁为哪一页镀金、谁为哪一幅图上色,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细密画的制式,细密画师是着色师、格线师、镀金师等队伍中的一员。在另外的章节,借由黑的姨夫之口,读者被告知,细密画是故事的彩色花朵,它们描绘最鲜活的场景:英雄鲁斯塔姆(Rustam)砍下邪恶怪兽的脑袋;为爱而迷失心智的马杰农(Majnun),游荡于贫瘠而荒芜的大地,置身狮子、老虎、雄鹿与豺狼之间;席琳(Shirin)仰头凝望霍斯陆(Khosrow)的相貌时,脸上洋溢着惊喜与爱慕。
细密画及其中的故事,最终指向了生命的精彩、真主的仁爱、信仰与美,而不是细密画家及其想象力。一段关于失明的古老传说将细密画的精神笼罩上了东方主义神秘色彩——东方主义也是帕慕克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绘画就是细密画家对安拉眼中的凡间世界的追寻。然而这种独特的景象,只有当细密画家经过一辈子的辛苦作画,耗尽其一生,眼睛极度疲劳而最终失明之后,才能在记忆之中找到。也就是说,唯有从失明细密画家的记忆中,才能看清安拉眼中的世界。”
帕慕克的虚构在历史中有其参照。纳卡斯·奥斯曼(Nakkas Osman)受命完成十二幅苏丹细密画像系列,与赛义德·洛曼(Seyid Lokman)的文字合成一卷,为了目睹早期苏丹的真颜,奥斯曼请求搜集关于苏丹的威尼斯油画,然而这些油画姗姗来迟,奥斯曼不得不在它们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委任。威尼斯艺术家唤醒了透视,即来自另一侧的光源,以及三维空间;而奥斯曼的肖像画则是二维的,颜色、装饰都被有意选择了,“真实性”消失不见。在帕慕克的虚构中,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两种风格和形式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包容两种世界观但毫无技法可言的作品。
在这个文化历险的故事中,帕慕克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我学已故的姨父用阿拉伯语说。“但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黑说。“细密画家不该屈服于任何形式的支配。”蝴蝶说,“他应该画他认为心中想画的,无需担忧是东方还是西方。”“完全正确,”我对挚爱的蝴蝶说,“我想吻你一下。”
戴维·詹姆斯·罗克斯堡(David J.Roxburgh)认为,贝尔廷对伊朗艺术及其图像的阐释未免失之片面,其对东方艺术和中东思维的抽象与概括有东方主义之嫌,同时贝尔廷没能顾及很多关键的文化轨迹,比如从15世纪到18世纪,巴尔干、萨非王朝、莫卧儿帝国和西方世界的复杂互动,又比如阿尔哈曾的理论与15、16世纪托普卡普宫的几何纹样卷文是否存在着真实的关联。
并非所有人的全球
2006年,贝尔廷与彼得·韦贝尔(Peter Weibel)、安德烈亚·巴登西格(Andrea Buddensieg)、米尔雅姆·沙塔纳维(Mirjam Shatanawi)以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为依托联合发起“全球艺术与博物馆”(GAM - Global Art and the Museum)研究项目。如文所示,“全球艺术与博物馆”项目旨在探究全球艺术与博物馆最新的发展状况,由于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该项目主要投注在“第一世界”之外。在2006年到2016年十年时间内,“全球艺术与博物馆”项目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开幕了两个展览,并在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以及巴西、印度、中国香港等地召开了数场研讨会,同时出版六部研究著作,其中前三部有贝尔廷参与。
贝尔廷对全球艺术的关注是渐次深入的,到了最后阶段,他甚至可以说放弃了“比较”。世纪末,贝尔廷修订了《艺术史的终结?》,补充成《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该书最后一章节“马可波罗和他者文化”(Marco Polo and Other Cultures)目前还未被翻译为中文。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认为,从马可·波罗到今天,中心与边缘被广泛地认知,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成了挂在嘴边的话头,但人们对其它世界的观看始终落脚在异国情调。基于此,贝尔廷否认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追求的普遍修辞(rhetoric of universalism),称其无法适应多元文化的处境,普遍修辞不过是霸权的外衣——在此,贝尔廷暴露了其对大众媒体新近发展的认知缺失,他不知道大众媒体对霸权与监控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否定性。
“我们带着怀疑看待西方(West)的派生物,这尤其是因为我们为将其他文明赶出那个天真、真实、古风的黄金时代而感到内疚。此外这还涉及我们对失去自我与他者(the others)的恐惧,此前我们如此强有力地在他者(otherness)的光芒中定义我们自己。”贝尔廷质疑道。某种更微妙的“第三世界”(third world)、“南方”(the South)是什么?在西方世界和部分东方世界,艺术市场、艺术机构、艺术教育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基础,但在摩洛哥或者叙利亚,艺术还没有真正开始成长。要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艺术场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84年威廉·鲁宾(William Rubin)策展的“原始主义与20世纪艺术”(Primitivism and 20th Century Art)、1989年让-于贝尔·马尔丹(Jean-Hubert Martin)策展的“大地魔术师”(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都昭示了非西方艺术在当代艺术领域的露出与“崛起”。注意“魔术师”的命名,它规避了艺术家的标签,以及文化的命名,马尔丹在与贝尔廷的对话中声明,“有些艺术家来自那些没有艺术史或关于艺术的历史观念的文化区,我想要展示我们所谓的现代或后现代状况属于一种传统。这种观念是满足特定的人群的,和民俗博物馆不同,我并不打算解释这些差异。[……]但是我一直将我们的现代主义放在一种特定的西方问题的语境中。试想,仅仅通过黄永砯的作品,我们怎么可能阐释中国文化的全部内涵呢?”
日后,参展艺术家拉希德·阿拉恩(Rasheed Araeen)在《第三文本》(Third Text)反对“大地的魔术师”展览,认为它没有反映“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的文化异质性”,在“现代的、全球视角的自我(self)表现”中稳固了其差异性,而“他者们”(the others)仍受限于“他们民族的起源”。

桑戈尔
1980年卸任塞内加尔总统后,桑戈尔再次回巴黎居住。桑戈尔在巴黎遇见了现代主义,也在这里重寻他的现代主义,这样的现代主义也包含了某种非洲精神,这种亦此亦彼、亦我亦他的状态就是桑戈尔常常谈及的融合(métissage),这个概念开始于墨提斯(Metis),她是最博学的存在。当桑戈尔再次返回巴黎时,塞内加尔的艺术家也转向了新的技术和媒介,诸如录像艺术、装置,普遍的现代主义精神不见了踪迹,当代性很快袭击了所有人的心智。
图像思想家
回顾贝尔廷的思想生涯,他借由中世纪研究(拜占庭艺术)重新发现了欧洲,一个非末人时代的、多重地理的欧洲;借由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展演的多媒体艺术(影像、装置、摄影)窥见了停留在所有消逝与沉疴中的、暂居在艺术边境的死亡;借由图像人类学对充满壁垒的学科的整合,构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视域,既非理性又非爱,同时不必超越的整体视域。最终,贝尔廷将自己塑造成思想者、实践者,以及“新天使”(Angelus Novus),“我的眼睛很黑很充实/我的凝视从不会空虚/我知道我应该宣布什么/我所知道的还有更多更多”。
贝尔廷关注死亡,图像的诞生部分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随着死亡的淡出,人们对图像的需求就没那么迫切了。传说,皇帝有段时间总是夜不能寐,他入睡时总感受到身边有瀑布声,于是他命画师将宫殿墙上的瀑布抹去,这才能安心入睡。在他关于面容和录像艺术的研究中,脸被他看作是存在的媒介,人的因素似乎都富集在了脸上,脸位于人与神、人与自然的接驳处。
在其思想实践中,贝尔廷努力超克新维也纳学派,某支堕入文本的瓦尔堡学派,以及男性主导的力量,以中世纪圣象和当代录像影像为皿,培育出一方思想的植物群落。同时在现实视域上,贝尔廷的图像没有像W. J. T. 米切尔那样紧迫地接近公众,它和公众保持距离,因此贝尔廷的图像变得像想象力一样神秘但真实,想象力以理想的诗人为宿主,而图像以流动的媒介为宿主。
似乎不可避免地,在从中世纪到超现代、从多维东方到全球的漫游中,贝尔廷暴露出太多的误解、差认、错判,以及稍过度的圣像去“圣”、影像去“艺”。在“寓意”纬度,贝尔廷呈现了一种局限,他似乎无法像伟大的神学家们那样言说,也无法像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沉思,这或许是因为现代学术总抱持一种轻舟已过的态度,但也许,一切才刚刚开始。
贝尔廷重要著作清单
以下三部为约定俗成的图像学三部曲 (Image Trilogy),一说第三部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
《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Bild und Kult: eine Geschichte des Bildes vor dem Zeitalter der Kunst; Likeness and Presence: A History of the Image before the Era of Art)
《隐形的杰作:现代艺术神话》(Das unsichtbare Meisterwerk: die modernen Mythen der Kunst; The Invisible Masterpiece: The Modern Myth of Art)
《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Bild-Anthropologie: Entwürfe für eine Bildwissenschaft;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Medium,Body)
《佛罗伦萨与巴格达:文艺复兴艺术与阿拉伯科学》(Florenz und Bagdad: Eine westöstliche Geschichte des Blicks; Florence and Baghdad : Renaissance art and Arab science)
《脸的历史》(Faces. Eine Geschichte des Gesichts; Face and Mask. A double History)
《艺术史的终结?》(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Art?)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
(以下为合著合编)
《全球当代与新艺术世界的兴起》(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Andrea Buddensieg ,与彼得·韦伯(Peter Weibel)等
《全球艺术世界》(The Global Art World: Audiences,Markets,and Museums)
Andrea Buddensieg,与安娜·贝卢佐(Ana Belluzo)等
《非洲人在巴黎:桑戈尔与非洲未来》(Ein Afrikaner in Paris: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und die Zukunft der Moderne)
Andrea Buddensieg,与安德里亚·巴登西格
“图像在场:宗教图像”(Iconic Presence. Images in Religion)
https://www.zfl-berlin.org/project/iconic-presence-in-religions.html
*限于篇幅,参考资料从略
(李建春、徐傲群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感谢)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