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令人共情的雪山大地,袒露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传承

近期,作家杨志军的长篇新作《雪山大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作系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
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科长父亲到沁多草原蹲点了解牧民的境况,接待他的是由部落世袭头人转变而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角巴安排父亲住在曾经的下人桑杰帐中。一次意外,桑杰的妻子赛毛为救汉族公家人父亲被激浪卷走……
在本书中,杨志军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今天夜读,在关于此书的创作谈与选读中远眺雪山如何改变一代又一代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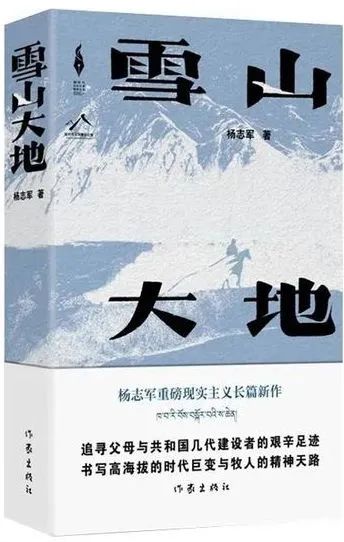
杨志军 / 著,作家出版社
长篇小说《雪山大地》的创作缘起
是流淌的河让我们记住了他们的故事,那条河叫黄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发,裹缠在雪山草原之间,虽然曲折无数,却不改一路向下的姿态。从那里走下来的是藏族人,他们从高海拔走向低海拔,而我的父辈却是一路向高海拔走。
无论向下还是向上,都很难,没有前人修好或踏出的路,人们在大峡谷里仰望举向蓝天的高洁,在沼泽地里遥视推向无边的阔绿。终于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找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一顶迁徙途中的帐房,周围有牛羊,有藏獒,有一匹白马、一匹枣红马。帐房依傍着湖水,天空是瓦蓝的,湖水是湛蓝的。他学藏话,吃糌粑,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他与牧人们成了朋友。两个月后蹲点结束,他留下自己家的地址,离开了那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星斗的分布,虽然稀疏,却熠亮无比——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终于有一天,其中的一个牧人按照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了省城西宁他的家里。他的妻子是医生,牧人是来看病的。
从此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来到他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他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带来了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说着“扎西德勒”,将这些礼物放在一九六〇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五岁的孩子,放进他们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孩子的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而孩子却毫不犹豫地将酥油抓下来,送进了嘴里,每回都这样。
这孩子就是我。

杨志军
以后二十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不远千里来到我家,仍然是为了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寻找相关的同事,请求他们给予治疗,每次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久地成为我们心中的光迹和擦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
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好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而有了工作能负担起家里人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迅速延伸而来的高速公路消解了草原的辽阔和遥远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当年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治疗呢?
偶尔一个机会,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往购物车里挑选东西,这才意识到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是的,发生变化的不光是生活,还有人和那些可以左右生活的观念和意识,还有我们赖以存在的雪山大地。我希望雪山大地的变化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绿色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河源厚土上,袒露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传承。
2022年11月11日
作品选读
”

父亲住进桑杰家的帐房纯属偶然。那一天上午,在沁多公社的康巴基,公社主任角巴拍着头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姜瓦草原上的赛马会刚刚结束,热闹看不上啦,我的儿马日尕跑了第一名你知道吧?”父亲说:“不知道。”“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那我的日尕白跑啦。”父亲笑道:“现在知道啦。”“知道就好。第一名赛马的主人是我,沁多草原的角巴德吉,这个更应该知道。”“噢呀(好的、是的),你的名字翻译成汉话就是幸福的烟斗,我记住啦。”父亲望着对方的坐骑又问,“不会就是这匹马吧?”“你看它像第一名的样子吗?”“不像。”“那就对了嘛,赛马会上的第一名谁舍得骑?”“可我听说好马都是骑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那要看怎么骑啦,像我这个样子是不行的。为了划分草场,忙得我马腿都跑断啦,西一个日头落山,东一个太阳出来,我的这个头,昨天迎南风前天迎北风,再往前迎的是什么风记不清啦,前后左右都是冰凉冰凉的,不信你摸摸。今天不想迎风啦,就想扯呼噜睡大觉,没想到县里的科长来啦。带话的人说你要去野马滩蹲点,蹲点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你是个好人我是知道的。”父亲说:“麻烦啦,我本来想一个人去,但人生地不熟,东南西北分辨不清,更不知道应该住在谁家,还得请你指点我。”角巴戴上攥在手里的羔皮帽说:“不麻烦不麻烦,要是我们对上面的人不好,上面的人对我们也就不好啦。所以嘛,别人的事情不是事情,你的事情才是事情。我们走。”两个人走出了康巴基。父亲说:“你的汉话说得不错。”角巴嘿嘿一笑:“我正要问呢,科长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藏话说得这么地道?”父亲也是嘿嘿一笑,连表情都成了地道的藏族人:“我吃糌粑已经吃了好几年,再不会说藏话就连糌粑也对不起啦,现在除了缺个藏族人的名字,其他方面跟藏族人已经没有两样啦。”“名字好办,我给你起嘛。”角巴想了想又说,“强巴,我看你就叫强巴科长。我过世的阿爸和爷爷都叫这个名字,一个叫强巴,一个叫老强巴,你叫这个名字一点没错。”父亲弯了弯腰说:“那就谢谢啦,你给我起了一个这么尊贵的名字。”

康巴基就是一间房。用石片垒起的“一间房”孤零零地伫立在沁多草原上,远看就像牧人戴旧了的黄氆氇羔皮帽。最早的时候它是部落头人用来迎送客人的驿站,因为这里有开阔平整的原野,又靠近沁多河,还是进出沁多部落的必经之地。如今部落变成了人民公社,他这个进步头人变成了主任,外来的人只要带话给主任,主任就还会来这里迎候。不然该去哪里呢?牧人过的是马背上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公社没有固定办公的地方,主任在哪里公社就在哪里。
角巴主任和父亲骑着各自的马沿着沁多河朝南走去,没走多远,角巴就指着前方哈哈大笑:“不用我去野马滩啦,我现在就指给你,走来的桑杰,塔娃是哩。”父亲看到,远远的草冈上移动着一个骑影和一群牲畜。桑杰也发现了角巴和父亲,翻身下马,丢开缰绳,快步走来,还没到跟前,就弯下腰去,两手朝前抬起,半张着嘴吐出了舌头。父亲知道这是下人见到老爷的礼节,慌忙下马,说着“你好”,弯腰还了一个礼,吓得桑杰连连后退。角巴说:“桑杰你听着,这样的行礼要不得啦,公家人不讲究这个。我,草原上的角巴德吉,也已经是公家人啦。”桑杰“噢呀噢呀”地回应着。角巴从马背上下来,盘腿坐到草地上,用马鞭捣着草丛说:“都坐下,坐下说话。”父亲坐下了。桑杰依然弯腰弓背地站着。

角巴说:“桑杰你是不是宁听老鸦嘎嘎也不听我说话?让你坐你就坐嘛。”桑杰还是不敢坐,木讷呆痴的脸上又增添了一层惶恐。角巴懊恼地说:“都说新社会新草原,这个样子能新到哪里去?你想站着说,那就大家一起站着说。”说着起身,父亲也跟着站了起来。角巴说:“你是野牛沟大队的牧人,不是野马滩大队的牧人,但强巴科长要去野马滩蹲点,也就是要去野马滩吃糌粑,可又要住在你家的帐房里,你说怎么办?”桑杰把手插进凌乱的头发挠了挠说:“主任啦,明白啦,大人的马是会飞的马。”角巴说:“你以为大人是云朵里的天人吗?草原上没有会飞的马。你再想想。”桑杰使劲想着,一脸的困惑:“主任啦,明白啦,大人要去我家的帐房住一晚上再上路。”“你的脑子叫白花花的酸奶糊住啦,连我的马都在摇头笑话你,你今天不是野马滩的牧人,明天也不是吗?你把大人领上,去你家的帐房,再把帐房从野牛沟搬到野马滩,大人不就可以住你家的帐房吃野马滩的糌粑了吗?”“主任啦,你说过我不是野马滩的牧人。”“见多了石羊奔跑,自己的腿也会快起来。你桑杰见我见了多少回?一千回还是一万回?我的聪明怎么一点点也没叫你沾上呢?是不是野马滩的牧人,我角巴说了算嘛。”桑杰答应着,表情渐渐舒展了,脸上的黧黑也好像白了些,恭敬地看看父亲。角巴又说:“你放心,我跟强巴科长在县上见过面,开会时他让我坐在他身边,还领我去食堂吃饭,人家都是各吃各的,他把他的碗和我的碗放到一起,让我夹他碗里的肉,他夹我碗里的菜,不是好人能这样?你怎么对待沁多的头人,不对,应该是沁多公社的主任,就怎么对待强巴科长,我还有事我得走啦。”

父亲后来常常说起这一天的巧遇:如果离开“一间房”后,迎面走来的不是桑杰而是别人,如果角巴德吉不是个率性随意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那些事放在历史中也许不算什么,但对父亲它成了等同于生命的经历,成了命运本身的显现。就像父亲后来总结的那样: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点亮你,熄灭你,一辈子追随你,这还不够,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所有后代。
父亲骑马跟着桑杰,桑杰牵马赶着牛羊。走了一会儿,父亲想:这算什么,我还真成“大人”啦?赶紧跳到地上,也牵着马,跟他边说边走。他们走过了草冈,走向了桑杰的家。桑杰的妻子是个又瘦又小的女人,正在帐房边埋头把稀泥一样的牛粪抟捏成粪饼,听到藏獒的叫声后抬起头,在直射的阳光下看了半天才看清来人,慌忙把满手的牛粪在草地上蹭蹭,又用围裙擦着手,朝帐房里面跑去。
原标题:《令人共情的雪山大地,袒露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传承|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