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康子兴评《贸易的猜忌》︱商业、历史与现代政治

人类事务中的大革命(mighty revolution)已经发生,那么多蜂拥而起的事件走向了古人期待的反面,这足以令我们怀疑,它们将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大卫·休谟,《论公共自由》
一
在《贸易的猜忌》这部文集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贸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贸易的猜忌》,第2页,以下书中引用只注页码)。因此,尽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开创“新政治科学”上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但洪特仍一反传统论调,认为霍布斯并非“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只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其原因仅在于:“霍布斯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第2页)霍布斯的理论是反商业的纯政治学,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就贸易与现代政治之密切关系而言,现代政治学当为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理论家的头把交椅则应当交给大卫·休谟,以及更系统地阐释休谟之洞见、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亦言之,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线为:是否将经济、商业视为核心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
然而,这个判断必然带来更深的疑惑:如果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是秩序的基础与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那么为何政治理论古今之争的焦点不在人性与政体,却在经济;不在理解政治的方式,却在某一特定的人类生活领域?为何在现代政治中,经济与商业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足以定义自身的边界与形态;古人却要将其排除在政治视域之外?或者说,洪特极力修正霍布斯(甚至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学说史上的地位,赋予休谟、斯密以开创性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的这一努力?
实际上,洪特的洞见源自休谟和斯密,他在书中频频引用休谟的《论公共自由》 (“Of Civil Liberty”)以及《国富论》第三卷来阐述古今政治的革故鼎新。我们甚至可以说,洪特有意借用休谟与斯密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与复杂张力,并获得应对现实挑战的理论资源。亦即,他思考、写作的前提是:休谟与斯密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初便敏锐捕捉到,并揭示出其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现代社会之基础在十七世纪奠下,其结构一直稳定地延续到当代世界,其内在精神亦无实质变革。正如洪特所言:“《贸易的猜忌》旨在发掘出十八世纪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那些仍然与二十一世纪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洞见。本书所关注的这段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首次成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本书避开了中间两个世纪那些很成问题的修正,将读者直接带回十八世纪的智识环境中。政治思想史的最大益处在于能够揭示意见不同所造成的僵局并消除重复性的争论模式。《贸易的猜忌》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它将目光聚焦于今天面临的种种挑战。”(第5页)
所以,我们若要正确理解洪特的论断,我们就需要进入他的视野,关注休谟与斯密的政治历史叙述,尤其是他们对自身时代之独特性的理解。的确,在《贸易的猜忌》中,洪特尤为关注休谟与斯密的“历史意识”。此书由七篇论文构成,但其中两个篇章的主题都是“历史”:第一章讨论“四阶段”论的理论基础,第五章则围绕《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事(“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的政治经济学)展开。此中又以第五章最为关键,因为他对“非自然与倒退”发展次序的解读融合了他对“四阶段”理论的分析,并以之作为比较和对照的基本框架——正是相对于由野蛮到文明,由内而外的“四阶段”的自然次序,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史才是“非自然与倒退的”。所以,我们要想恰切理解洪特的洞见,《贸易的猜忌》第五章尤为关键,《国富论》第三卷、休谟的《论公共自由》亦因此十分重要。
二

休谟的《论公共自由》为洪特理解现代政治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历史框架。休谟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了洪特的基本判断。比如,商业造就古今政治分野这一核心论点便源出于此。洪特对之反复揣摩,不仅在导论中予以细致剖析,后又在第五章等处反复引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影响了洪特对《国富论》第三卷的解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视之为对休谟命题的注脚。
《论公共自由》篇幅简练,但立意深远:休谟不仅勾勒出理解古今自由的不同方式,指出商业对现代政治的关键作用,也敏锐地看到欧洲历史中正在发生的巨大革命。我们可以将这篇文章解读为政治理论史纲要,也可将其解读为对政治史的简要勾勒。他将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并将政治理论视为现实历史的一个镜像。休谟就好像历史画廊中一位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批评家。他审视着历史画作,看到并总结其精神、风格的变革,进而分析其原因,预测其发展大势。
比如,他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仍然受缚于时代。马基雅维里尤为关注君主政府,但《君主论》中的原理无一不在后世遭到驳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基雅维里思想浅薄,而是因为其学说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着特定的历史现实。“这个政治家犯下了许多错误……皆因其生活在过早的时代,从而不能成为政治真理的好裁判。”(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iberty Fund, 1982, p.89.)世事推移,时代与社会均已发生了巨大改变,商业的巨大力量开始展露,引列强侧目。
上世纪之前,贸易从未成为国家事务;论述政治的古代作家也少有人提及贸易。甚至,尽管它已然引起国务众臣和理想思考者的关注,但意大利人却对之缄口不言。两大海权国家获得的巨大财富、荣耀与军事成就似乎最先向人类阐释了广泛贸易的重要性。(同上,pp. 88-89.)
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它动摇了古代社会的结构,塑造了新的民情、风俗,甚至“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所以,它也为传统的政体赋予了新的精神、原则与内涵。“尽管所有政府类型都在现代获得了改善,但君主政府似乎获得了朝向完美的最大进步。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称之为文明的君主国(civilized monarchies),他们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尽管这些此前只用来赞美共和国。我们发现,它们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受到秩序、方法与持久性的影响。财产在那里是安全的;工业受到了鼓励;艺术繁荣起来;君主安全地生活在臣民当中,就像父亲生活在孩子当中一样。”(同上,p. 94)商业令绝对君主制变得宽和,甚至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深入发展,对利益的思量终将战胜荣耀与特权,权力滥用会受到治疗,绝对君主制政府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差异将会变得不再明显(同上,p. 95)。
所以,古人确信科学艺术只能在自由政府中变得繁荣,但休谟发现,这一信念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君主制的法国,科学与艺术都发展到堪与任何国家比肩的完美程度(同上,p. 91)。休谟遂将此命题修正为:商业唯有在自由政府中变得繁荣。古人的信念不再适于现代社会,就好像马基雅维里的命题在后世受挫,因为政治理论均有其“历史性”。休谟对命题的修正乃是对社会“革命”的呼应:商业社会兴起,商业成为塑造权力结构、社会风俗的强大力量。自然,商业也可能造就新的腐败,需要政府严加关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业成为国家事务的核心议题;商业也以重新塑造着欧洲的公共自由,将共和精神以风俗和“权力平衡”的方式输入君主国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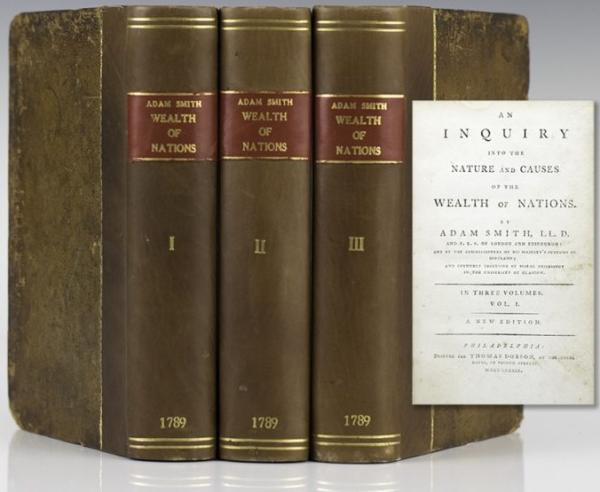
斯密更为系统、细致地阐述了商业塑造欧洲现代自由的历史。因商业而来的社会革命,正是《国富论》第三卷的主题。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陷入普遍的荒芜、野蛮状态。野蛮人征服罗马,也把他们的习俗融入法律。欧洲施行大地产制和农奴制,土地得不到开发,劳动者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生产力普遍低下。不仅如此,欧洲长期实行限嗣继承制,领主众多子女中,只允许一人继承地产。大地产制因此得以固化,避免了因继承产生的土地分裂。因为大地产制,领主在封地享有绝对权力。因此,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欧洲也长期维持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野蛮人摧毁罗马文明,带来政治上的奴役、经济上的贫穷。
由于商业的兴起,这种传统的权力结构逐渐松动,最终瓦解。欧洲在政治上逐渐由奴役走向自由,社会也逐渐由贫穷走向繁荣。斯密将这变化称为“极重要的革命”。在商业尚未发展起来时,领主只能消费地租中较少的部分,其他地租用来豢养门人和附庸。这些人由于在经济上依附于领主,便在政治上效忠于领主,从而构成领主重要的权力资源。商业最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比如荷兰等地。由于法律上的压制,对外贸易最受偏爱;奢侈品贸易因为价值高昂、便于运输,最受推崇。海外奢侈品贸易逐渐带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商业的风气日益深入内陆,并进而影响乡村。当贸易繁荣起来,领主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便会为了昂贵的奢侈品,支付全部土地剩余产物。他购买来精致的工艺品,可完全由自己消费,无需与佃农和家奴共享。为了独享一对钻石纽扣,他不惜支付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同时也舍弃了从中而来的权威。于是,曾经的领主制、大地产制逐渐瓦解,耕作者获得了更大的权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欧洲因此逐渐从野蛮的风俗中复苏,走向自由、文明与繁荣。
这场革命是无意识地、自发产生的,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379页)
现代欧洲重新文明化历史遵循了“非自然与倒退的”次序:对外贸易推动国内贸易,城市带动农村,最终导致整个封建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海权的商业共和国(比如荷兰与英国)取代陆地君主国(比如法国),成为新时代精神的代表。
在很大程度上,洪特将《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事视为斯密对《论公共自由》的注解,并将商业社会与商业共和国的兴起理解为:商业从野蛮人统治和封建暴政下突围,逐渐获得自由立法力量的进程。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贸易之忌”的出现正是这一连续进程的结果。商业不仅塑造了国内的民情与社会结构,也重塑了国际政治体系。“在大型领土国与专业商业政治体之间的劳动分工,从十六世纪晚期开始就被扰乱了。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节节攀升的军费开支压力下,欧洲的主要领土国开始投入到经济权力的竞逐中,努力通过对外贸易产生的盈余来获得霸权优势。一种新型的国际体制应运而生,取代了领土国与体量小但专业化的商业政治体(大部分是商业共和国与城市国家)之间亲密而互补的关系。在这种新型体制中,领土国凭其自身的努力就已成为国际商业主体……用大卫·休谟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在十七世纪,商业首次便成为‘国际事务’。”(349页)
所以,现代世界是一个被商业塑造的世界。国家荣耀、野心与贸易结合起来,海洋和商业成为国家间竞逐争霸的另一个战场。“贸易的猜忌”或重商主义体系虽然注入了商人的贪婪与土地贵族的痴愚,尽管在规范意义上,它应合理地受到“不义”之责;但是,在事实和历史层面,商业和商人绑架了国家,成为了实际的立法者,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尽管近代欧洲的发展遵循着“不自然与倒退的”次序,正是这一次序繁育了重商主义体系的腐败与非理性,然而,它也恰恰体现了商人的力量,以及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与文明社会发展的自然法与自然进程相比,“不自然与倒退的”次序才是真实的历史。正因此,洪特认为,斯密借《国富论》第三卷阐发了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审慎的政治理论,并借机批判重农学派的自然法教条主义,指出其罔顾事实,单凭理论体系塑造社会的危险。“现代早期欧洲君主国早熟的商业发展,对他来说是一个棘手的事实,也是具有极端政治意义的历史事实。诚如斯密之所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不能回避这一事实,或者被教条主义所束缚而反对它。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学会应对过去的历史遗产。”(356页)
《贸易的猜忌》英文版
四
洪特对斯密政治理论的分析具有强烈的史学色彩,所以,在他眼里,《国富论》便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国富论》并不是一部关于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竞争性经济战略的著作。在他的书中,斯密权衡了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求生存的可能机会。”(第8页)亦即,《国富论》以斯密对时代与历史的深刻洞见为基础,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以此观之,《国富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理解为史书,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作品。洪特所谓的政治理论便具有强烈的史学色彩,而非哲学含义。所以,当他说,休谟与斯密才应当是首位现代政治理论家时,他其实是在对现代性作一个历史学的判断:古今的分野正在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理论的变迁不过是历史变迁的映像,古今政治学的分野自当以古今政治史的分野为标准。
然而,当我们细细推敲,当斯密在阐述欧洲历史的“非自然与倒退”次序时,他其实阐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基于道德哲学与神学的“自然智慧”。亦即,《国富论》第三卷不仅仅是一篇历史分析,还是一部极为精彩的自然神学作品。透过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自然历史叙事,斯密亦确立起他的“商业社会哲学”。
就此而言,洪特真正的老师是大卫·休谟,而非亚当·斯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