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别等神作消失了,才学会珍惜
原创 王一恪 硬核读书会

《特洛伊》剧照
今年新疆的冬天格外寒冷,即使过完春节,最低气温也在零下20℃左右。冬天的乌鲁木齐总是有些灰蒙蒙的,这是北方城市统一供暖的通病。
我前往离乌鲁木齐约250公里车程的木垒书院拜访作家刘亮程。去年,他的最新作品《本巴》受到了文艺界的大量关注。
不久前的平遥国际电影节上,《本巴》和《一个人的村庄》入选“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刘亮程是唯一一位有两部作品入选的作家。
当车辆开出乌市,蒙在蓝天上的一层白雾逐渐消失,少了雾霾折射的阳光像箭一般照射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种久违的明亮。
木垒书院的大门是锁着的,首先过来迎接我的是木垒书院的黑狗“月亮”,说是“迎接”,或许“吼叫”更确切些。刘亮程一出现,月亮便停止了吼叫,一路跟在我们后面。在一条小水渠的桥洞里,有三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突然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在刘亮程的书院里,或者说,在这里,狗不允许进入室内,它们不是宠物,在一户人家中有着自己的职责。
刘亮程的工作室中仍然使用炭炉供暖。我们围着炭炉坐下,聊了聊关于《本巴》、《江格尔》史诗和文化传承。
✎作者 | 王一恪
✎编辑 | 程迟
十多年前,刘亮程在新疆北部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参与一个旅游项目的规划实施。和布克赛尔的主要居民是土尔扈特蒙古族,以放牧为生。
游牧生活居无定所,新疆四季分明,牧场的位置也随季节而改变。夏牧场在高海拔的山上,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深山里的草开始变黄,牧民便带着牲畜向山下走。到了冬天,沙漠边上有一种高杆草生长在沙漠的边缘,为牛羊过冬提供食物。到了春天,雪水融化,山坡上的草再次生长出来,牛羊跟随着新鲜的牧草回到山中。生命在这样的平衡中生生不息地繁衍。

《远去的牧歌》剧照
刘亮程参与的项目名为“牧游”。在景色最好、气候宜人的夏季,游客来到夏牧场,跟着牧民沿着牧道和牛羊一起迁徙,晚上便住在蒙古包中。在自然风景之外,人文景观由流传在当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作为核心元素。刘亮程所在的工作室根据《江格尔》为和布克赛尔设计建造了十万平米的江格尔史诗广场,刘亮程也因此接触到了《江格尔》史诗。
《江格尔》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江格尔统领的本巴草原四季如春、人人丰衣足食,但是频繁有外敌入侵的年代。故事的主要内容即以江格尔为首的十二勇士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战争情节为主。

江格尔史诗广场。/ 图片源自爱在塔城公众号
十多年后,刘亮程在小说《本巴》中借用了《江格尔》史诗的背景,为自己写了一部关于童年和游戏的童话。在《本巴》中,本巴草原上的人们永远活在25岁,沉醉在酒宴与梦中。在远方的敌人哈日王向江格尔宣战后,双方展开了一场以时间和梦为战场与武器的战争。
《本巴》是古老史诗在现代作家笔下的另类传承,刘亮程将自己化身为现代江格尔齐,在古人想象力的尽头展开自己无边无际的想象,这也是江格尔史诗在现代作家小说中的一次生长。其不仅借用了史诗的背景,在语言风格上也有一些与史诗相似的地方:重要的场景、角色有着固定的形容词搭配,他们在《本巴》的文本中不断地重复出现。杨宪益曾以散文体而非诗体的形式翻译《奥德修纪》(《奥德赛》),在语言的风格上与《本巴》有着奇妙的相似,其中华丽的短句重复出现令文本充满了节奏感。
《本巴》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2022-1
与史诗相似的文体带来了一种陌生的感觉,令《本巴》的文本读来十分新鲜有趣。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种人类最古老的讲述故事的方式之一,会离现在的我们如此遥远?

为什么是史诗?
《人类简史》中最著名的一个理论是,人类社会建立在虚构的故事之上,不同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史诗可能是最早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的那个故事,是在同一个群体里人人都认同的一个故事。就像《女娲补天》对于中华民族那样,这些史诗在发源的族群中几乎家喻户晓,在语言中也有着从史诗中衍生出的部分。
现代人提到史诗,想到的往往是一些背景庞大的虚构叙事作品,这些史诗的名字出现在语文、历史课本里,成书一般也都是大部头,令人望而却步。而史诗的出现是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在没有载体可以长久地记录故事的年代,人的讲述和记忆承担了这份职责。

《女娲补天》剧照
和《江格尔》相似,史诗讲述的多是英雄的故事。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巴比伦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乌鲁克半人半神的国王吉尔伽美什和他的朋友——曾与野兽为伴的泥人恩奇杜之间的故事;最著名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讲述发生在希腊城邦的特洛伊战争和伊塔卡之王奥德修斯在众神的帮助下返回故乡的历程。
作为一种口述的艺术形式,史诗的传播依靠的是人的记忆和讲述。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史诗也被不断地被润色和修改。曾有西方的学者试图总结史诗具有的十个特点:
1. 从事件的中途开始。
2. 背景广阔,涵盖许多国家、世界或宇宙。
3. 以对灵感的召唤开始。
4. 以对主题的陈述开始。
5. 使用许多形容词。
6. 包含一份很长的清单,称为史诗目录。
7. 充满长篇大论和正式演讲。
8. 显示神对人类事务的干预。
9. 以体现文明价值的英雄为主要角色。
10. 悲剧英雄的结局往往是堕入阴间或地狱。
二十世纪初期,艾伯特·罗德和米尔曼·帕里在研究巴尔干半岛的口传史诗传统中,采用并列模型来解释诗歌内容的组成。他们指出,这些诗歌通常由若干简短情节构成,而每个情节之间的地位、吸引性及重要性都是对等的,而当表演者传唱史诗的时候,这种结构也有助记忆及重现史诗的情节。

《故事形态学》
[俄]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贾放 译
中华书局,2006-11
刘亮程在介绍《江格尔》时提到了其类似的故事结构:“史诗的结构是不复杂的,都是程式化的,只有不断地重复这种结构,才能在口传史诗中靠人的记忆传承下来。在《江格尔》中,每一章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在班布来宫中,大家喝着酒,突然传闻远方又有莽古斯要打过来,侵犯本巴国。这时就有一个英雄站起来,自告奋勇要去灭了这个国家,把国王的人头提过来,在座的勇士就为他敬酒,送这位英雄上路。几个月后英雄或者把这个国家消灭了,或者被敌人打败关起来了,再派下一个英雄去营救他。所有的故事都在这样的一个格式里,开头一场酒宴,胜利归来后又是一场酒宴,故事被装在两个酒宴中间,只有这样古代的江格尔齐——即《江格尔》的讲述者——才能把故事记下来。”

准噶尔古城附近的草原,位于和布克赛尔县城东南5公里处。/ 图片源自江格尔商超公众号
在没有文字的古代,史诗的存在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草原上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剩下就是地下的史诗。它似乎就是这个民族在漫长夜晚中的星光和月光。放眼望去,四周都是遥远地平线,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草原。他们认为自己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或者是最边缘。不像中原大地上的城邦之国,城邦可以遥遥相望,在辽阔的草原上一个人望见另外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在那样的夜晚,部落的人围在江格尔齐的身边,听江格尔齐唱他们本部落创生的英雄故事。那些英雄从江格尔齐的口中被讲述出来,肯定也会进入到听者的梦中。部落创造出英雄,最后史诗中的英雄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个部落,让其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英雄精神,这就是事实。至少现在在新疆,《江格尔》史诗还在活态传承。”
但是现在,故事唾手可得,被记录成了文字的史诗不可避免地遇冷。

史诗死了吗?
有名的史诗常常被提起,如《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但真正将他们的原文翻开阅读的人却很少。刘亮程在《本巴》四章故事全部结束后,将部分《江格尔》的正文设置为第五章。“我们现在知道了好多书的名字,知道了并不去读。你说《荷马史诗》谁都知道,但是谁会去读呢?《江格尔》更是如此。”
史诗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文明的必备品。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汉语史诗?
对于这个问题,刘亮程的看法是汉族过早地拥有了文字和记录的能力,虽然在文字出现之前肯定出现过口传形式的诗歌,但都在很早的时候被整理成了文字。研究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经典作品《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作者钱存训提到“自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以来,直至今日,几乎没有一年缺少编年的记录。”且“至于中国书籍的产量,直到15世纪末,比世界上其他各国书籍的数量还要丰富。”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钱存训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2-11
朱光潜用偏向文学的视角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在史诗悲剧和其他长诗方面并不发达。朱光潜总结了五个原因:
1.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浅薄。
2.西方民族性好动,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是阿喀琉斯、西格弗里、贝奥武夫;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除了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作为。
3.西方文学偏重客观,以悲剧史诗擅长,中国文学偏重主观,以抒情短章擅长。
4.史诗和悲剧都是长篇作品,中国诗偏重抒情,抒情诗不能长,所以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
5.史诗和悲剧都是原始时代宗教思想的结晶,与近代社会状况与文化程度已不相容。
朱光潜仍然有着不少疑惑,“以上五种原因凑合起来,似乎可以完全解释史诗悲剧和其他长籍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的道理。这五种原因有些起于中国民族的弱点,也有些起于中国民族的优点。如依谨严的逻辑,我们似不应把他们相提并论。”或许这个问题本身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

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齐 / 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截图
在刘亮程看来,“口传艺术中最迷人的部分是即兴创作的部分,这种创作让《江格尔》越来越丰富,每一代江格尔齐都不甘心只是死记上一代江格尔齐的讲述,他总是要创造出他自己的一些故事来。”
到了现在,从史诗的生存状况来看,世界确确实实地已经改变了。活形态的口传史诗在人类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虽然现在仍然有人在传唱着《江格尔》史诗,将史诗的完整传承作为一种使命,但更多的是以表演为目的。
是不是发展到有文字的阶段,鲜活的口述史诗注定无法“保鲜”?

有用的遗骸
刘亮程认为,一个民族的史诗是历史、文化、风俗的集大成,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源。
现今的卡尔梅克人,是17世纪初从中国新疆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蒙古族卫拉特部的后裔。随着卫拉特人的迁徙,《江格尔》便传播到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他们后裔中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据刘亮程认识的一位卡尔梅克诗人介绍,她上小学都要背诵江格尔。
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的史诗研究从欧洲古典学的范畴扩展到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语言、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都从史诗研究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
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史诗资源,中国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的篇幅超过20万行。在上世纪70年代时,中国就有学者采访仍在世的江格尔齐,在经历录音、翻译、整理之后,到了八九十年代就有汉文版的《江格尔》史诗出版。2006年,《江格尔》获批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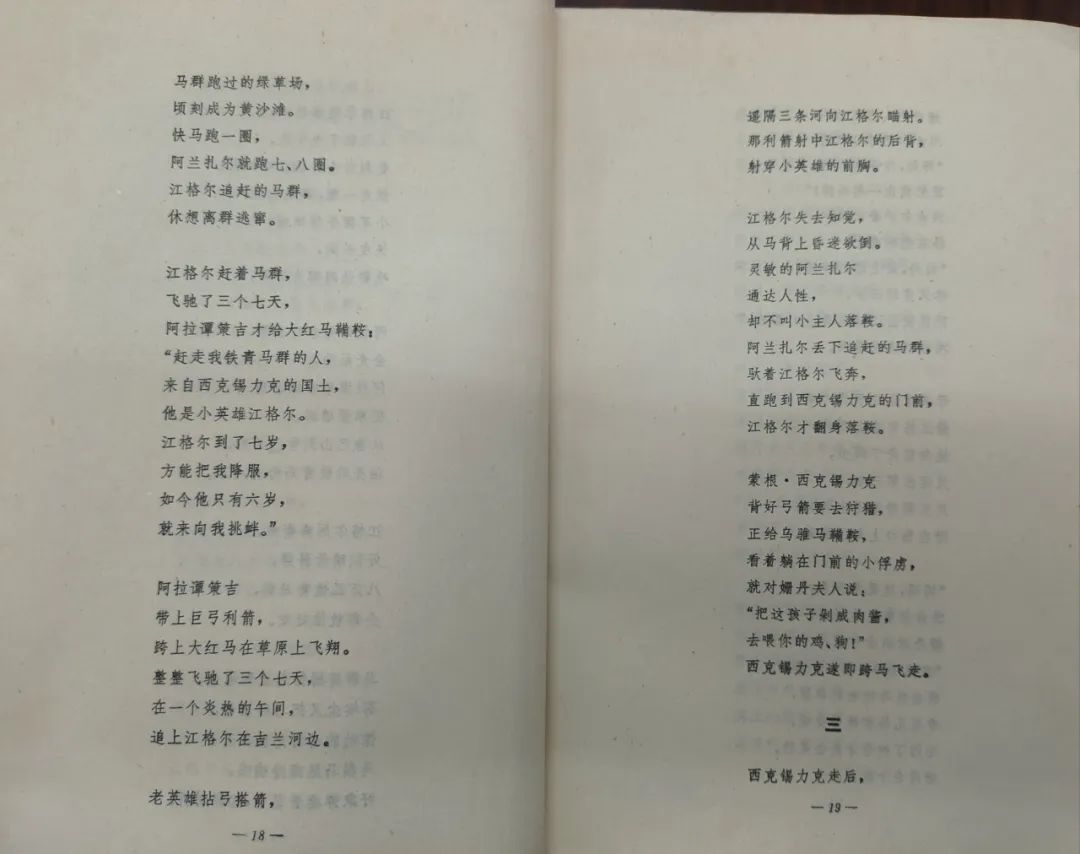
《江格尔》诗文一览。/ 姚炜楠 摄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的小学中现在仍然开设有教授如何口述《江格尔》史诗的“江格尔班”。但活形态的史诗原本的作用在技术的发展中逐渐失去光彩。现在,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宏大叙事故事吗?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平等且具有价值的现代观念也似乎与史诗的英雄叙事格格不入。
但在刘亮程看来,谈论史诗是否存亡其实有些偏题。“口传史诗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但人类既然有了文字,就肯定会依靠文字。史诗的文字化是对其的一种保存。假如史诗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当然口传是最好的传承方式,因为口传是活的,一旦被文字化,史诗就失去了生长性,就变成了著作。但是对前人已经成型的这些口传史诗,做文字的固定保存当然也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江格尔》,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录音整理的江格尔齐的口传史诗,是那年代史诗的样貌,如今《江格尔》和《玛纳斯》依然有演唱者的后代在传承,但是这种传承的盛况不如古代了。现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旅游表演,也没有人有耐心听他们讲一天一夜,最多讲两个小时,就该散场了。但旅游的表演需求,或许已经成为江格尔史诗在现代的一种传承传播方式,毕竟这样的表演可以给江格尔齐带来收益,也让更多的游客欣赏到史诗。”

刘亮程在木垒书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对于语言充满了困惑,也许哪一天今天记录和讲述的方式也会以某种形式被束于历史的高阁。
参考资料:
1. 尹虎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
2. 唐卉《“史诗”词源考》
3. 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 END ·
原标题:《别等神作消失了,才学会珍惜》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