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学中的焦虑:从焦虑的症状表现到显性的焦虑本身
如果要探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中呈现出的焦虑,我们看到的必然是焦虑的症状表现,而不是显性的焦虑本身。尽管在那个时期,公开的、明显的焦虑迹象并不多见,但学者们还是可以发现大量潜在焦虑的症状表现。举个例子,回想一下像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这样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中那种显著的孤独感,以及不停求索的品质——疯狂地、强迫性地追求却一再受挫——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从本书展示的焦虑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情况下的焦虑,在本质上与沃尔夫的《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这一书名所象征的意义密切相关。我们将会看到,神经质焦虑的发生往往是因为这些人无法接受“不能回家”的心理意义,即心理自主权的丧失。人们可能会好奇(因为意识到文学艺术家运用象征手法,以惊人的准确性描述了他们文化中的无意识假设和冲突),沃尔夫笔下的象征意象是否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不仅不能再回家了,而且过去维系安全感的经济、社会和道德标准也不复存在了。这一认识的结果是,伴随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显性的焦虑,它已成为一个意识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看作关于家庭和母亲核心象征的揣测,那么它可能会有效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以更具体的形式,在这项焦虑研究中不断面对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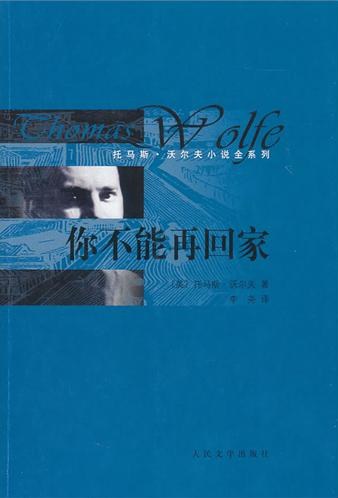
托马斯·沃尔夫《你不能再回家》
到1950年,焦虑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开始了显性表达。诗人奥登用他认为最准确的描述时代特性的词汇,把自己的诗歌命名为《焦虑的年代》。尽管奥登对诗中四个人内心体验的解释是以战争为时代背景的——那时“恐惧已成必然,自由令人厌倦”——但他清楚地表明,诗中人物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焦虑的根本原因并不只在战争,而在更深的层次之中。诗中的四个人物,虽然气质和背景不尽相同,但有着相同的时代特征:孤独、丧失为人的价值、无法体验爱与被爱——尽管他们有共同需求、能共同努力,也有酒精提供的短暂喘息。这种焦虑的根源可以在我们文化的某些基本趋势中找到,在奥登看来,其中之一便是从众(conformity)的压力,它出现在一个商业与机械的价值被奉为神明的世界里:
我们继续前行
如巨轮滚滚;革命
见证一切,兴衰成败
无情的买卖……
……这个愚蠢的世界
精品巧器就是上帝,我们不停交谈,
没完没了,但仍旧孤独,
活着却孤独,归乡——何处?——
像无根的野草。
而诗中的四个人物可能面临的处境是,他们也将被拉入这毫无意义的机械化日常中:
……我们所知的恐惧
是未知。夜晚是否会为我们带来
糟糕的秩序——在一个小镇上
开一家五金店……教进步的女孩
生活的科学——?为时已晚。
我们被人需要过吗?或许我们根本就
不值一提?
他们失去的是体验的能力,不再相信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与此同时,这些象征着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也失去了信任他人的能力,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与奥登的诗名类似,加缪曾把这个时代称作“恐惧的世纪”,他还称17世纪是数学的时代,18世纪是物理学的时代,19世纪是生物学的时代。加缪知道这些描述在逻辑上并不一致,因为恐惧并不是一门学科,但恐惧“必然与科学有所关联,因为科学最新的进展已经到了否定自身的地步,完美的科技正对地球产生毁灭性的威胁。此外,虽然恐惧本身不能被视为一门学科,但它确实能被视作一种技法”。我们的时代也常被称为“心理学的世纪”。恐惧与心理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恐惧是否就是驱使人们去审视自己内心的力量?这些都是贯穿本书始终的问题。
另一位作家卡夫卡也尖锐地描述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焦虑和类似焦虑的状态。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对卡夫卡的作品再次产生浓厚兴趣,这对本书的写作目的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情况展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越发焦虑的状况。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卡夫卡的文字直指人心,他传达了社会大众普遍经历的某些深刻层面。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城堡里的当权者控制着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权决定主人公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的人生意义,而主人公倾其一生都在与当权者周旋,疯狂而绝望。“生命中最原始的渴望:扎根于乡土的诉求,成为社群中一员的需要”,驱使着卡夫卡笔下的平民英雄不断反抗。但是,城堡里的当权者依然高深莫测、难以接近,英雄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支离破碎,甚至隔绝于社群之外。这座城堡具体象征什么,是个可以详细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显而易见,城堡里的当权者是官僚体制效率的缩影,而官僚主义既扼杀了个人的自主权,也抹杀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卡夫卡描写的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方面,在那个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效率的极大提高,个人价值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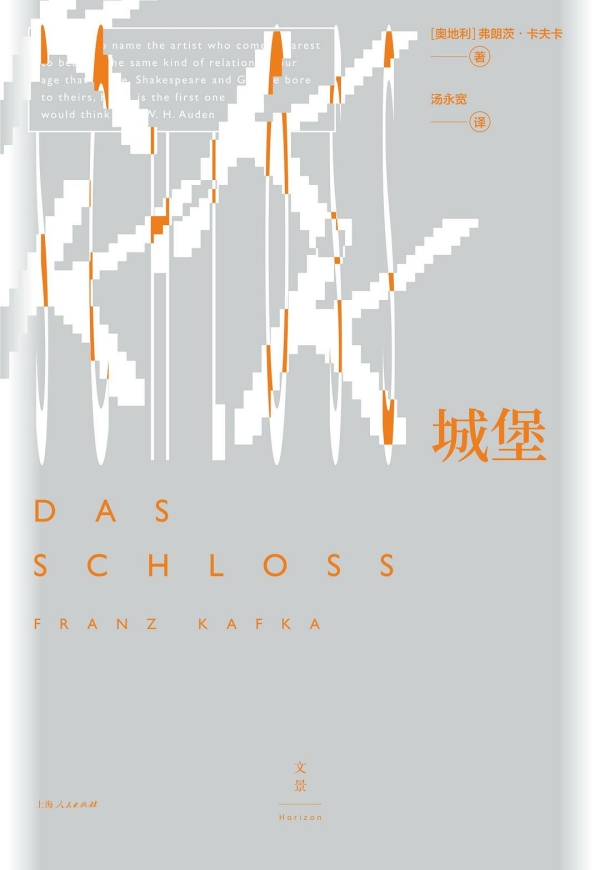
卡夫卡《城堡》
与卡夫卡相比,赫尔曼·黑塞在文学中较少使用象征手法,他更明确地指出了现代人焦虑的根源。20世纪的欧洲比美国更早感知到创伤性的社会变革,因此,黑塞写于1927年的《荒原狼》,比起当时的美国,更贴合20世纪40年代美国显现出来的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他将主人公哈勒尔的故事作为我们时代的寓言。黑塞认为,哈勒尔及同时代人的孤独和焦虑源于这一事实,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强调机械的、理性的“平衡”,其代价是压抑了个人经验中动态的、非理性的因素。哈勒尔试图克服他的孤独和寂寞,为此他释放出先前压抑的感性与非理性的冲动(即书名中的“狼”),但这种被动的方法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事实上,对于当代西方人的焦虑问题,黑塞并没有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因为在他看来,当前的时代正是“整整一代人被困在……两个时代之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标准与控制已经崩溃,但还没有新的社会标准取而代之。
黑塞将哈勒尔的经历视为时代的记录,因为正如我所知,哈勒尔心灵上的疾病,不是单个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哈勒尔所属的整个时代都患了神经症……这种疾病攻击的……恰恰是那些精神强大、天赋异禀的人。
本文摘自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的代表作《焦虑的意义》,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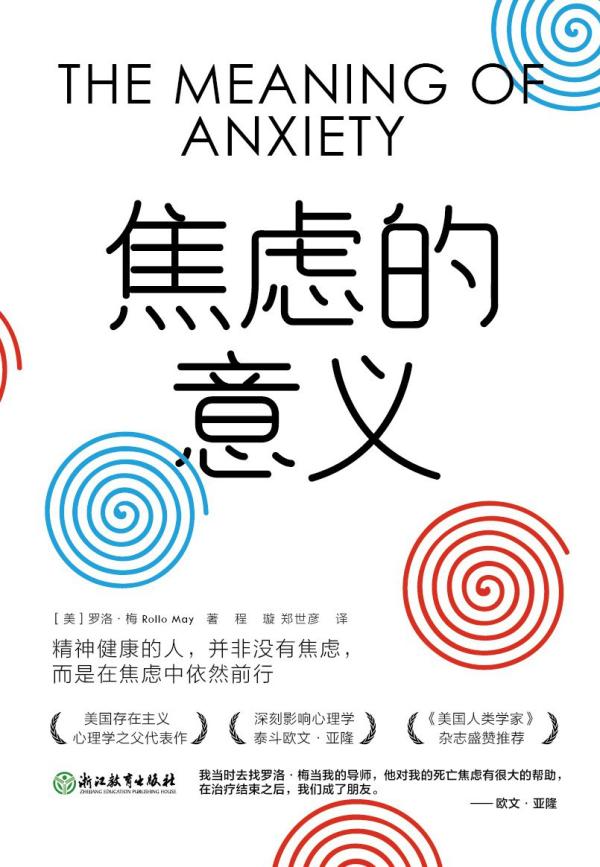
《焦虑的意义》,【美】罗洛·梅/著 程璇、郑世彦/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好读文化,2023年1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