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 +112
访谈︱剑桥大学教授古克礼:仰望星空的历史意义
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BBC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剑桥大学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荣誉教授,达尔文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荣誉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科学史,包括数学史、天文史和医学史等。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3 至 2013 年间担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及该所《中国科学与文明》系列丛书主编。
【采访者说】
古克礼教授应该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学者之一了。用“可爱”形容一位知识渊博、令人尊敬的大学者,似有不妥,不过,面对一个学识高深又活泼有趣的人,你对他的感觉肯定不只是崇敬。古克礼教授是一个纯粹的人,虽然数年前就已退休,但他对很多事物却依然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热爱也始终如一,从未改变。古克礼教授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以及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洒脱与活力,不夸张地说,能为他至少减龄二十岁。前些天意外看到一张 1998 年的老照片,二十年过去,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我于博士二年级时初识古克礼教授。记得那时他刚刚做完一个小手术,大家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雀跃地对我们说:“我感觉棒极了!就像电视里鸟食广告中的小鹦鹉一样,重又恢复到了蹦蹦跳跳的状态。”古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幽默风趣的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时常被他形象的比喻逗笑,当欢笑声还在空气中飘荡时,古老师话锋一转,马上又把大家带到另一个无比有趣的新话题,因为他总是有满脑子的趣事跟我们分享。古老师操着一口悦耳的贵族英语,说话时表情丰富,神采飞扬,无论言者还是听者,都沉浸在对话的喜悦中。我暗自感叹,如果不驻守在学术界,古老师一定会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演员。
当然,关于古老师的记忆并不只是这些好玩儿的家常。在李约瑟研究所,他曾做过一场题为“清代天文学家梅文鼎”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演讲逻辑清晰且生动有趣,坐在台下聆听绝对是一种享受。天文史如此深奥难懂,而那天,他却貌似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其精髓传递给了听众,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仿佛跟着他穿越到了清朝,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中。
2013 年底,李约瑟研究所为古克礼老师举办了一场退休酒会,现场气氛轻松而愉悦。酒过三巡,古老师对我们说:“我现在终于不用去各处为李约瑟所拉赞助,以后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了!我和夫人已经制定了下一步的研究计划,足够我们用三十年来完成!”
一晃四、五个春秋过去,2018 年 4 月,我有幸在李约瑟所采访了古老师。访谈主要围绕中国的天文学传统、古代世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及中国对科学的贡献而展开。

从伊顿物理老师到中文博士
静一:古教授,很荣幸有机会和您交谈。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古克礼:我从 10 岁左右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了。记得有一天,我母亲带我去图书馆,给我找到了一本美国作家写的书,叫作《与龙握手》(Shake Hands with the Dragon)。作者讲述了他与美国当地中国移民交往的故事,并有意通过这一故事来消除当时人们对中国人的歧视。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孔子和中国的文字等,这一切都令我十分着迷。所以说,我从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不过,我真正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静一:您的本科专业是工程,请问您是怎样走入中国古典这一领域的?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古克礼:这要从我上中学的时候说起。我 13 岁的时候,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要决定之后几年专攻哪些科目。学校要求我在德语、科学或希腊语这三门学科中做出选择。我的父母13岁时就辍学了,他们没有能力给我提供职业规划上的指导,于是我就听由学校指挥,选择了科学,虽然我当时对希腊语更感兴趣。
20 岁左右,我开始通过读本学习古代汉语,从《孝经》、《孟子》、《论语》等经典著作入手。后来,在伊顿公学任教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一本古汉语教材,作者是杜胜(Raymond Dawson,1923 - 2002,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后来他得知我在自学古文,就主动邀请我每个月去跟他学习《庄子》。
从牛津大学工程系毕业后,我曾尝试攻读材料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一年后我便放弃了这一学科,转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博士学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对我来说,后者比前者有趣多了!我的个人感受是,当你对一个事物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静一:您曾经是伊顿公学的物理老师。您觉得中学的教学经验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我一直很欣赏您作学术报告的方式,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古克礼:教学对于我做学术报告确实有很深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你应当将观众对你的关注视作一种恩惠而不是你的权利。因此,你应当尽全力展现自己研究中有意思的一面,以及自己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做学术报告时,如果只是一味地读自己的文章,那我们上课、开研讨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成为一名教师之后,我发现我对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完成试题和通过考试这两方面,而我当时并没有能力解释为什么某些方法是正确的,而其它方法却不然。这意味着我应该从头开始学习已获取的知识,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这些知识,从而建立起全新的认识。因此,我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我给我的学生的建议——就是要回到本源,从原始文献出发,而不是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文献入手。这样一来,当你再来参考当代文献的时候,一,你会很高兴地发现这些文献解答了不少令你产生困惑的问题;二,作为“新手”,你或许能发现其他人从未关注的一些点。如果你从其他研究者的文献入手来研究某一课题,你是不可能让自己的思想产生萌芽乃至成长壮大的。
静一:您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地点是巴黎,但偶尔也会回到剑桥。您可否告诉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工作的差异?
古克礼:相较于巴黎,剑桥的图书馆更容易获取跟历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资料,而巴黎相当于伦敦、剑桥与牛津的合体,不用上火车便可以坐拥众多学术资源。在法国,我时常在家里和我的夫人——汉学家詹嘉玲(Catherine Jami)一起工作。最近,因为我的研究兴趣转向她所熟知的十七世纪,我们的交流就更多了。嘉玲可以给我很多有用的建议,如指导我去参考相关文献,我便成了她的“徒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应该不断尝试新的课题,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自己所熟知的那一领域。
静一:所以说,您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改变,是吗?或者说,您现在开始关注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年代?
古克礼:从李约瑟研究所的行政职务解脱出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先是完成了两本书,作为之前工作的总结;然后又开始新的17世纪的课题。17世纪,东西方产生了第一次碰撞与对抗。传教士们熟知中国的传统,并且可以用古汉语撰写书籍,给中国人讲述欧洲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发现。因此,研究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的描述,以及一些中国人,如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对他们的回应,还有由此引发的对自己文化的审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可能对汉代更为熟稔,但研究17世纪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只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我所熟悉的领域而已。
提到传教士,我要补充的是,这些人的意图其实并不邪恶。在这些忠诚的信徒看来,为了不让那些不信基督的中国人下地狱,他们必须用奉献一生来“拯救”他们,即便这意味着自己的牺牲(有些传教士在中国未能得到善终)。
中国的天文学传统
静一:恭喜您的新著《天空的数字》(Heavenly Numbers)2017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能否告诉我们您撰写这本书的初衷?
古克礼:这些年我写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计算天体运行和位置的文章,时间主要集中在约两千年前这一时期,也就是早期帝国时代。我认为,把这些内容串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的责任,这样做也对得起我的薪水。我要做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最有趣的部分,用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有许多有关地中海文明的图书做到了这一点,但我意识到并没有类似的讲述中国古代天体计算的英文著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人提供学习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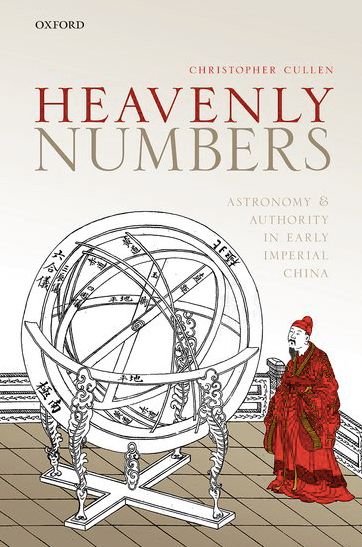
古克礼新著《天空的数字》(Heavenly Numbers) 2017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静一:关于天文史,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首先,天文学(astronomy)和占星术(astrology)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您认为中国天文传统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古克礼:我倾向于用 “astral”-tradition 来形容天文传统,因为这既包含了天文学(拉丁文 astronomia),又包含了占星术(拉丁文 astrologia)。前者可以理解为天体运动的规则,后者可以理解为天体运动对人类世界的意义。
天文传统有多种,我所研究的传统始于帝国时代的初始时期。那时候中国开始有一个由政府建立的组织,长期观察天体运行并进行记录,这就是中国天文传统开始的标志,和《左传》里面的记录截然不同。根据《左传》里的记录,我们可以判断那时候已经有人能够根据天象而预先计划农历日历,并按需添加额外的月份“让季节赶上日历”。但这里涉及到的仅仅是个人,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人们如何学习这些知识,以及什么样的人会做这样的工作。或许是世袭制,但这只是一个猜测。
静一: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关于《易经》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占星术传统源自《易经》吗?
古克礼:《易经》在很多方面都是某种宇宙论的根源,或者至少与特定的宇宙论紧密相关,即选择正确的时间去做事情。在《易经》中,所有宇宙现象被分析成六十四卦。这些联系在一起,可以被称作理性宇宙学的一部分,因为人类不再需要臣服于喜怒无常的神,人类自身有能力理解世界。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阅读《易经》这样一本充满真知灼见的先哲著作。刘歆参考了《易经》的注释《系辞传》,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天文系统中的常量,以及他的大宇宙理论。不过,像《日书》这样的文献并没有直接参考《易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
另一方面,如果说一切都源自《易经》,显然是错误的。《易经》仅仅是众多占卜书中的一本,我们知道,很多占卜书都已失传了。正如《黄帝内经》在中医领域被视作一本经典或权威一样,事实上,如果你查阅《汉书》的目录,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内经》,例如《白氏内经》。很遗憾这些书已经失传,否则我们可能会对中医的本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易经》。所以说,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取决于过去遗留给我们的证据。
静一: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视角理解过去呢?
古克礼:我们不能站在当下的角度来看待古人的行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挑出符合现代科学的那部分并排斥其它所谓“迷信”的部分,这是不对的。上个世纪初期,人们试图排斥一切“封建主义”元素,从历史中提取出“科学”的精华。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接触到活生生的历史,只能留给我们几块破碎的干骨,结果就是,连那些历史人物都不会认出我们究竟是在描述什么。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大背景进行思考:过去的人为什么会有某些行为,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天文的精准计算如此重要,以及他们和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有何不同等等。

中西占星术的异同
静一:可否说,服务个体与服务国家是中西占星术的一个重要区别?
古克礼: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两者的一个区别。西方与中国,占星家所做的工作大致相同,但他们服务的对象有很大差异。西方的占星需求者基本上是个人。面对各式各样的个体,这些占星家必须关怀备至、注重细节,从而让需求者对他的服务感到满意,以便吸引更多的需求者。而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占星家有固定的薪水、制服、休假制度等等,他们不能过度地即兴发挥,必须非常注意自己在皇帝面前的言辞。在中国,天空更像是一个指示器,不同的天体运行蕴含着不同的涵义,例如当观察到某个天体闪烁或发光时,可能预示着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占星家的主要工作是将这些信息汇报给统治者。因此,中国的天文传统更关注于天象对于整个国家或人类的影响。个体的占星术并不是中国天文学的传统内容。
虽说如此,在中国同样有一群人从个体客户那里得到报酬——他们是那些“日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记述日者的章节。人们关注的是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比如说,《日书》会讲述,你的孩子在某个时间出生,那么他将来会如何;或者当一天中的某个时间你的家中被盗,那么小偷会有哪些特征。因此,古代中国也确实有关于个人的咨询,但它并不是关于天体运行的,本质上,它和各种宇宙周期与人们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相关。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科学?
静一:有一个问题在中国仍大有争议:中国对科学有怎样的贡献,或者说中国历史上是否不仅仅有技术,而是同样有科学?面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古克礼:维特根斯坦曾经说,他研习哲学的意义是“让嗡嗡作响的苍蝇飞出瓶口”。怎样让这些询问中国是否有科学的人离开这个瓶子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代西方同样没有科学,中世纪的西方也没有科学。我在之前提到的不要将过去的活动视作现代活动的不完美版本,这一类比也同样适用于此。当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成果时,我们不能认为他与牛顿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而只是没有牛顿做得好。亚里士多德所做的是一套全然不同的工作,并且他的工作很有说服力,但那不是“现代科学”。
所以,我的观点是,所谓的“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它的主要基石是在十九世纪奠定的。而“科学”(science)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这是我与李约瑟共同持有的观点。科学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边界模糊的社会活动,是一个理性理解宇宙的过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约瑟认为科学是人类不断获得更多客观认识的一种渐进式的成就。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其实是由于人们经历了一个对国家感到耻辱和无力的阶段而产生的——为什么西方人看上去那么聪明?他们可以制造先进的武器,可以治愈疾病,可以用各种聪明的方式来理解宇宙,等等。于是,人们开始彻底抛弃自己的传统,学习西方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科学。
四海之内皆兄弟
静一:从您与中国学者和学生的交流或合作中,您认为他们对于天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有什么不同?
古克礼:这涉及到一个时代的问题。我第一次去中国,是 1984 年在友谊宾馆参加中国科学史会议。当时,我见到了中国老一辈的学者。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有时甚至需要匿名出版或发表文章。但他们基本延续了这样一种传统,即调研文献,解释发现了什么,或者找寻一种方法来传达文本内容。因此,当时学者的工作与文本密切相关。当然,有些学者也尝试进行新学科的建设,例如,竺可桢对气象学史的研究。跟过去比,当下的学生显得更加外向、开放,如果隔着屏幕,你很难分辨他们都来自哪里,中国学生会询问和欧美学生同样的问题。我认为,这说明学术在迈向一种普遍性(universalisation)。
静一:您认为这种普遍性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古克礼: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迈向普遍性,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事实上,不管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我们为子女的成长而担忧,我们希望自己的爱人过得好,我们为找不到男/女朋友而发愁,我们担心自己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等等。所以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普遍性的。当然了,如果变得哪里都一样,那就太糟糕了。对中国人来说,我可能是一个“奇怪”的人,而这正是一件好事,因奇怪而有趣!多样性给我们提供的是相互了解的机会,在与他人的接触和交流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的东西,从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交流不同的观点。这让我想起中国古文里的一个句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静一访谈”(yingyifangtan),访谈全文见刊《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二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