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怀中:写作就是经历一场自我羽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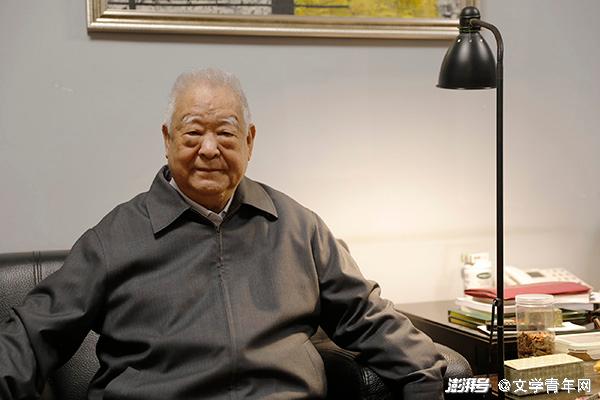
著名作家徐怀中
过去三个月,可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问很多问题,却鲜有答案。2020年1月9日上午9点30分,北方文学创作中心在北京专访了徐怀中先生。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叶圣陶先生“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他的《西线轶事》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2019年,90岁的他凭借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历届最年长获奖作家。同时,他也是莫言笔下的那位“恩师”。
我们相信,这位饱经风霜、戎马一生的军旅作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关于:一个作家和时代的关系,青春的写作,自我的成长,永恒的事物......为了不折损这次难得的采访,我们以文字的形式,为大家奉上专访实录,希望可以弥补我们的愚拙。
采访 | 刘琳
作者 | 予倩
摄影 | 李小敏
人们已经习惯了见面没有问“你好”
记 者:徐老师您好!首先我要行使一下“读者”的权利,最近正在重读您的《牵风记》,写下了这段文字,请您批评指正。

“19岁的汪可逾定格在了《牵风记》里的银杏树下,而由她演奏的古琴空弦音似乎仍在向我发出召唤,我如同那匹红枣马一般寻找着似开似掩的等待撞开的窗子,我常常有一种直觉,她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人世间的某个角落。还是那个标志性地微笑,嘴角即将张开了说出“你好”的姿势,深深浅浅地露出了汉白玉式的一排牙齿,在照片里,在渡船上,在星空下,在黄河边。”
徐怀中:太好啦!你刚才在讲这个微笑,我在里面写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节。这个独立第九旅,欠着她的一个“你好”!她那个样子对大家,从入伍到牺牲,没有过一个人问过她一声你好,不是没有这一种情感,而是战争就是这样,人们已经习惯了见面没有问“你好!”,也不问这些。这些农民出身的人就问你吃过了吗?在部队也不问吃过了,因为他是集体吃饭,没有吃过不吃过的问题,所以他们见面没有什么问好。这就是战争和这个女孩子的心理差别,她的这种美好的感情,完全超越了战争,好像她在部队推广着“你好!”,但始终没有人问过她一声你好!
记 者:但是她和红枣马的之间的那一种感情,让红枣马本身的神性似乎也被唤醒了。
徐怀中:是这样的。
记 者:今天的这个日子选的特别好,徐老师说周四,我一看是九号,《牵风记》里的部队就是“九旅”,那匹红枣马身上的红印也是“九”。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有缘,然后就想以这本《牵风记》来做一个开场。
徐怀中:好,太好啦!
记 者:《牵风记》里有哪些“非虚构”的故事和情节?
徐怀中: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在写这种战场的真实,我比较下力气。其实人们对战争一般的概念都有,比如谁胜利了,什么是胜利,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人们过去写作品,往往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部战争小说,别人首先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在读者头脑中,这些是不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读者,他希望看到战争中间的这种细微的战场生活,他会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打下来的,因为看到整个战争这么惨烈,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居然后来大家那么欢呼雀跃,欢庆这一次胜利,这中间究竟是一种什么过程。尤其是部队战场的这种生活,就好像形成了民间的那种“人情风俗”在部队里。这些东西,我当兵这么多年,我印象也最深。所以我想,应该给读者传达这些。我希望让读者能够了解他们想知道的,而不是一味想向他们讲清楚某些概念。
记 者:《牵风记》里的一个场面,我感觉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观看演出,但是那个汽灯老灭,然后大家就各自干各自的事儿,干什么事儿的都有,汽灯一亮大家都回来,从新接着看。
徐怀中:是的,你想这个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是长期的。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和平时期和平年代是上一次战争和下一次战争的间隙。战争是连年不断的,所以中国人民也就在这种连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灾害的苦海中间。他们不能不正常地活着,就是你战争归战争,但是这种演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会永生难忘。所以后来军事学院的人去访问,老人们记不清这场战争了,但记得住这次演出,记得住这个小女孩。
小说的要义就在于虚构
记 者:您如何在叙事中创造了一种意境美学?
徐怀中: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就转入到比较空幻的一层天地里面。就好像这几个人物,和大自然达成了某种默契,整个的氛围就是这一种亦真亦幻、匪夷所思的。我主要的是想通过这几个人,能够营造出一种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而不是正面的去反应战争。我认为小说的要义就在于虚构,它无力担负起要实录一次战争的事态发展和变化以及如何走向胜利。

那读者不如看战士,看战士往往看双方发的作战电报也是会让你很激动的,但是看小说,读者不希望再去看这些,再去重复战争中间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些虚幻的东西,特别是我到了老年之后,我个人这种阅读的兴趣就完全有了一个转换,就更多地去读一些东方哲学、自然哲学的东西。引发自己很多的思考。特别是人们经常谈到的“个体生命存在”这种终极关怀,脑子经常在这些概念的理性的玄虚的东西里面不能自拔,这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我总是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小说更加生动,如何让读者怀着很大的兴趣来读我的作品,使得作品里面尽管不是那么“张牙舞爪”,但是如何把小说写的更生动更有特色。我晚年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希望能够写出一点自己的哲理思考,能够成为小说的灵魂。尽管这些自己不一定能够完全讲得清楚。
我给人经常谈起“会师”的几句话:他就说着、睡着,故以其已知,遇其未知,而使人知之。尽管他讲的是自己已知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人讲着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还是希望读者能够有所领略。我这个小说最后好像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我不能完全讲清楚,但是我自己写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感觉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羽化”的过程。我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记 者:就像汪可逾的那个乳名一样“纸团儿”。
徐怀中:对!所以说人不是去步步为营,去争取去跟人争劲,要得到要获取。这种在军事学上就恰恰相反,像齐竞这种人,他本来是没有条件做指挥员的,但是他居然可以学成一个指挥员,这种知识分子他本不是像老红军那种都是工农红军过来,他是战争里面打出来的。他到部队里的时间很短,但他完全能够掌握部队的这种战斗精神,如何组织部队的这种精神力量,并且自己作战都是特别勇敢,这种典型。过去人们不知道,以为知识分子就是一种被类型化的,其实不然。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在那种情况下,他总是会让自己很出众。
“战争,就意味着顷刻间的成熟”
记 者:您是如何保持着源源不断的“青春之气”?
徐怀中:这种青春的观念,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写东西的人他也会有这种心理。我觉得这是从生理到心理,总是对生活持有非常活跃的一种态度。特别是我从小就到部队里来,我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到自己能够独立地进行写作,这中间保有的就是这种所谓青春的意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
记 者:古琴响起的时候,红枣马为何破窗而入?
徐怀中:因为这个《关山月》是个古曲,它是一个鼓舞士兵前进的战歌。所以这个马它就会有这种记忆。就是从这些地方,星星点点的出现这种宇宙意识。我相信这种所谓的“通感”或“永久的信息”,人们现在所不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是文化传统的东西和古代的人相知,在我这小说里面,我是想古代的声音我们是可以听到的,应该能够听到。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能听到而已。我也希望从这个战争的状态下,向前扩展,直到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记 者:数次与死亡擦肩对于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徐怀中:我觉得就是意味着在顷刻之间的成熟。就像这个曹水从洞里出来之后,忽然看见天上的星星,他就觉得变了,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就像我到了大别山之后,我们整个机关就全部下去做地方工作。分到我们哪一个区哪一个县哪一个乡,你是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政府的主席等等都给你分好了,这是按照地图分的。我们走的时候,我的那个区在北边还是南边都不知道,出发了到路上去问。我那个区叫虎湾区,问虎湾区在哪?老乡才告诉我们是在哪里。

电影《芳华》剧照 图源网络
那一年1947年,我正好18岁。我在一个小文工团写标语、画漫画、画壁画、刻木刻,而当时那里要成立一个武工队,让我当队长,武工队又没有兵,是我去搜罗那些掉队的、受伤的战士,再找不到部队了就到我这里,就成为了武工队的成员。就是一下子这几天之内,你就要当这个武工队长,马上我们那一个区又被敌人袭击,我们的女同志又全部被俘,我们又要冲过去救她们,就在这很短的时间之内,一下子你就变成一个自己要拿主意的人。
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那几个月中间,很少敢在一个地方连续睡两个晚上,总是睡一个晚上,半夜起来就上山了。第二天再找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你才能维持下来,不被敌人捕捉到你。因为对方的土顽也是在抓我们,所以这种紧张激烈的斗争对人的考验是很严峻的,但是过后也觉得特别好,这次战争我参加了,太好了,要不然我不来就参加不上。
记 者:就如同曹水的成长一样。
徐怀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在人民解放军这种铁的纪律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种人仍然是在部队呆不住的,他在部队为什么能够呆住,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最出色的警卫员。是首长“四大件儿”里面最精彩的一个大件儿,所以首长就保护他,任他怎么样,他就呆下来了。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完全是飞扬跳脱,活出了自己,所以人们会去同情他,而不会用军队的纪律这个概念来限制他。部队这种人还特别多,你看着他平时这样子,可是到了作战打起仗来,他会比别人更勇敢。往往哪个首长到前方去,就会被他背回来。
记 者: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最后比较戏剧的就是地主家的女孩,还出来要跟他一块儿赴刑场,大家也想把这个女孩处死。
徐怀中:所以说战争是最残酷的,也只有战争中间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死去活来、不顾一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炙烈。
“莫言的学习欲望很高,确实很天才”
记 者: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系主任,您还会经常回忆那段“八面来风”的办学经历吗?

首届军艺文学系全体同学 1984年
徐怀中: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这些学员都是部队原来就小有成就的,在部队已经写了一些东西了。只不过他们是缺少这种文学基础的知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那么在文学系这两年,我就从这些层面着重地给他们做着一些补充。
我觉得他们最好的就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会有他们这种形式的学习。正好就是那一段时间,在文艺上也比较开放。他们接受了这些,他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闻所未闻的一些大家的思想,特别是北大、清华、社科院的这些专家、教授来讲课,有些人着急着想写,像莫言他们有几个学生每一课都到,对他们的作用特别大。他们一下子就像是从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了。
记 者:莫言自己回忆说是“换脑”“换心”。
徐怀中:对,我给他们组织的那些课以后再也听不到了,请任继愈来讲宗教课;李德伦来讲交响乐;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来讲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比较;请美术学院的教授来讲古代的美术。莫言写《丰乳肥臀》的那个形象,就是完全听了这个美术课,受到美术老师在课上讲的那种陶俑的启发。所以他们一下子开阔了视野和眼界。当时是三十几个人,后来就扩招了,多要了几个名额。
记 者:据说莫言是被文学系破格录取的?
徐怀中:他是来晚了。我们是一个单位只招收一个人,他是总参的,总参的名额只有一个人。别人已经有一个人报名了。但是他这个作品我一看,我觉得太好了。我就说这个学生,文化课及格不及格都要收他。我已经给他们交代了。后来莫言的考试是全系第二名,文化课很好,还真行。

莫言在军艺文学系学习期间
莫言的学习欲望很高,确实很天才。比如说《丰乳肥臀》,他写的抗日战争的前期,河北山东这一带盗匪四起,我们就做着“会道门”他们的工作,都改编成八路军。那个社会非常混乱,后来红军过来以后,把这片开辟出来一个根据地,这种斗争非常复杂,不能想象。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一段社会生活。莫言他是解放以后长大的,他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写这一段,我感觉他写的太真实了,因为我是经历过的。这一点确实天赋很高。
记 者:包括他后面这本书《透明的红萝卜》,据说这是您给他改的名字。他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回忆的时候觉得是“点睛之笔”。
徐怀中:我给他改了,他也不好说什么。
记 者:那个时候像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徐怀中:是的,像你们现在要读什么书都可以读到,那个时候好多书他们是看不到的。他们在部队什么书也没看过。到了这一看,拼命的读。后来看有几个人发表东西了,大家又急着写。我是力劝他们,我说你们现在不要着急写,一定要把这课全听下来。
记 者:您那个时候用了哪些办法鼓励大家写作?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徐怀中:为了避免学员之间的“文人相轻”,我专门策划了一个“搓澡会”,第一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讨论这个李存葆的小说,当时他的《高山下的花环》已经发表出来了。我们没有讨论好,就产生矛盾了。莫言说了一通,让李存葆很不高兴。我一看他很难转弯儿,就简短地说了一说就收场了,本来想让大家畅所欲言,彼此交换,我看你的稿子,你看我的稿子,甚至都可以帮助对方出主意。我说我们没有老师,就以文会友。可是第一次座谈没有搞好。但是有了这么一次之后,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孙犁没有得到足够好的评价”
记 者:您最初的文学启蒙在什么时候?有哪些对您影响深刻的作家?
徐怀中:看孙犁写的东西,特别亲切,特别自然。高于一般的写战争题材的作家。所以我开始写东西就很注意孙犁的东西。他有一部长篇叫做《风云初记》,我觉得没有得到足够好地评价,最近出版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把孙犁的作品编成第一部,这很好。实际上,我们过去比较突出的几部小说,孙犁和他们相比至少不比他们差。

20世纪80年代作家孙犁在寓所
我小时候读书也没有读到多少,那个时候像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等等这些作品在我们太行中学还是用手写的,老师给我们一句一句地念,念一句我们在底下记一句,用太行山印的那种纸,一动就碎的那种纸。因此整个课文先要花费好长的时间读一遍,然后你自己再去看再讨论。没有课本,就是老师自己找来的课本。还有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选以及苏联的几部作品,像《恐惧与无畏》《铁流》。
后来解放初期就到了重庆,就可以看到书了。印象深刻的就是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还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我觉得这一本书对于我写战争来说,给我的受益是很大的,它整个一本就是九万字,但是把战争中间的这种人性的发挥写的特别好,而且他写那种重大事件和这种虚构的结合也很好,写农民起义的领袖也非常精彩。
还有一部书就是《蒙古秘史》,里面的那种历史感、沧桑感给我印象很深,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写的是俄罗斯旧时代的骑兵,他笔下的这种战场,给人感觉特别残酷,给你的那种震撼力特别强。
让读者看到最真实的地方
记 者:《底色》的本质表达是什么?
徐怀中:因为很少有人用文学的样式把这段历史反映出来。中美苏三个大国,你了解了其中的内幕以后,就可以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了。它的底色,它的本质,你就能看到最真实的地方。这三个国家的互相依存,又互相尖锐的矛盾,以及像越南这种小国在大国斗争的夹缝儿里怎么样求得生存。因为我在越南南方呆了几个月,我钻过地道,我挨过B52轰炸,我对这个越南战争前线的真实过程很清楚。

徐怀中和妻子于增湘
这一本书我最近和爱人还聊过。本来我是应该先写《牵风记》的,但是当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了,我就是很有感触,就想先写一本这个书,没想到一稿子写了八年。年纪老了,写着写着也写不动了,中间就很困难,拖拖拉拉写了这么久,但是总是把它写出来了。
记 者:您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计划?
徐怀中:我新的想法是还要写一些短篇,还是要写这个《牵风记》的未尽之意,因为再往下写也很难写了,但是作为短篇,你每一个都可以另起炉灶,每一篇都是一个很短小很精致的结构,又可以有不同的发挥。总之我觉得还可以写出比这个有所前进的作品,但是很难,只是有一个笼统的想法。
记 者:请您对我们的青年作家说几句寄语。
徐怀中:我很注意过去所谓“先锋作家”那一批人出来,就好像给我一种感觉,只有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能带来一点负氧离子,才能有一点新鲜的气息。战争文学毕竟还是要靠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青年人来写,因为参加过战争的人没有几个。我们的文学也是要靠青年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种气息不是过去的老作家可以想象的到的,总是会增添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希望还在青年。
记 者:感谢徐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