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适合《追忆似水年华》的读法

如果读者与作者能够心有灵犀,相得益彰,那固然最为美妙;如果不能,诚为可惜,但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对此都没有责任,本属无缘之人,即便换一本书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文章节选自《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三联书店2023-2)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阅读《追忆》
《追忆》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谜,甚至是一个不可解之谜。倘若除了写作,没有其他的阅读方式配得上它,如果其他的阅读方式都是被动的、偶像崇拜式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适合《追忆》的读法?难道《追忆》仅仅是为其他作家而写的,或者只为孩童、盖尔芒特亲王之辈而作?

法文版《追忆似水年华》
伽利玛出版社,1990
在《重现的时光》的最后几页,普鲁斯特陈述了他自己对《追忆》全书读法的设想,不得不说他的表述相当严密,甚至可说是过分地严谨,这意味着作家本人的设想与读者们的预期并不相投。在赞颂了那些宏伟如大教堂一般的伟大著作之后—不要忘记《论阅读》一文曾把拉辛、圣西门的作品与古代建筑相提并论—普鲁斯特对自己提出了相反的评价:“不过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实不敢抱任何奢望,要说考虑到将阅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我的读者,那更是言过其实。”我们很难忽视这句话里的双重否定:作家在否定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否认了读者与作品的正面关联。普鲁斯特当然并不像马拉美一样,视读者为无关紧要的人群,但他的确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作品遣返回他们自身:“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这句话倒是和《追忆》对叙述者的阅读史的描述相一致,因为后者在书中追寻的的确是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恋书癖一直引诱着叙述者,在他的世界中挥之不去,但他也的确在抵制这一诱惑:“然而,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以前阅读的时候还没有插入的图像而打开这些书,都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以致即使在这个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意义上,我都可能会失去当一个书痴、珍本收藏家的愿望。”通过小说叙述者与恋书癖的双重关系,普鲁斯特驱使他自己的读者与偶像崇拜展开一种类似的狡诈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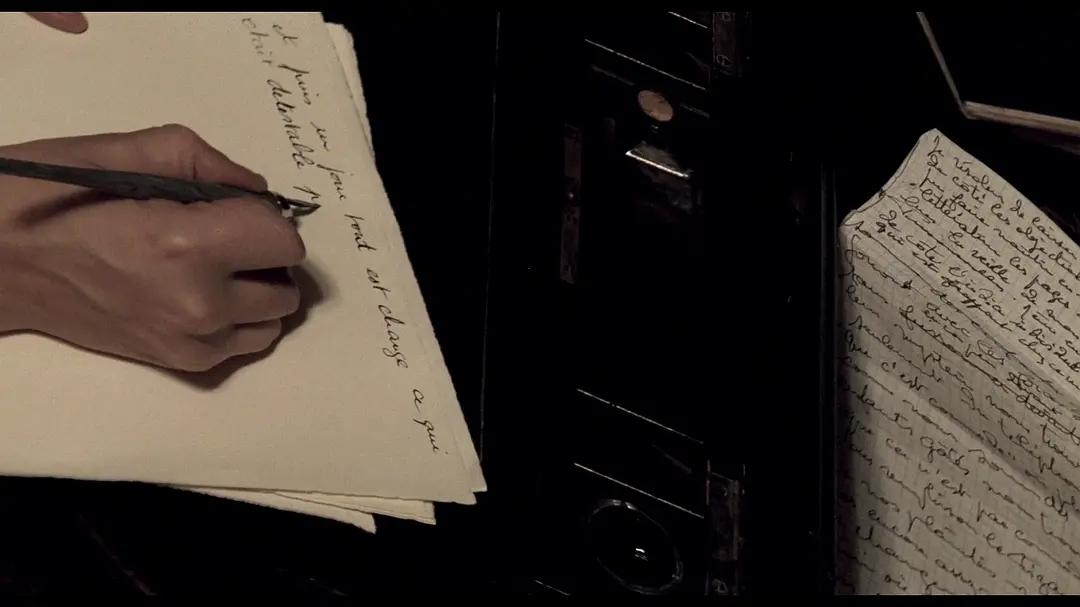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在主题层面,《追忆》中的同性恋问题仿佛扭曲视觉形象的棱镜,读者也可以透过它瞥见书的情貌。在《重现的时光》上文一处提及此问题的段落里,普鲁斯特写道:“作家不应因为性欲倒错者给他笔下的女主角装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气恼……作家只是沿袭惯例,用写序言和题献的那种言不由衷的语言说了一声:‘我的读者。’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他们自己的读者。”作家甚至直接借助与视觉有关的比喻意象来思考什么是读者自反性的阅读:“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的那些东西。”在另外一处地方,他又说“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于是他的作品就好像“放大镜一类的东西,像贡布雷的眼镜商递给顾客的那种玻璃镜片”。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还是小说叙述者将要写出的那本书,都面临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一味把读者反推向他们自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家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呢?随着行文的继续,小说末尾越发把读者推向他们自身。叙述者在向作家转换的过程中,总是牵挂着这本书,“我的书”—“我的书”一语成了《重现的时光》终篇处的主旋律—可他却并不考虑读者或者阅读行为。读者们仿佛成了一群不速之客,普鲁斯特好像一心要将他们拒之千里:“所以,我不要求他们给我赞誉或对我诋毁,只请他们告诉我事情是不是就是如此,他们在自己身上所读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写下的那些话(再说,在这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也并不一定纯然是由我的差错而引起的,有时还可能是由于读者的眼睛还不适应于用我的书观察自我)。”在别处,叙述者又说道,作者应该“给读者留出最大的回旋余地,对他说:‘您自个儿瞧瞧吧,如果用这块镜片能看得更清楚的话,就用这片镜子,要不试试那一块’”。这便是普鲁斯特心中的读者的目光以及书这部“光学仪器”。如果读者与作者能够心有灵犀,相得益彰,那固然最为美妙;如果不能,诚为可惜,但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对此都没有责任,本属无缘之人,即便换一本书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上面所引诸段落会不会包含了太多限制和负面因素,以至于无法用字面含义去理解?很奇怪,作者、读者和书看上去有可能壁垒分明,但它们又竟然会在一本深植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内在的书”里相互交融,乃至丧失彼此的特质,取消彼此的身份,而对这一“内在的书”的阅读就是写作,它的写作则是阅读。或者,一言以蔽之,创作—无论写作还是阅读本质上都是创作—只有以翻译的形式出现才是可能的:“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去杜撰它,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也就是译者的职责和使命。”与这源自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独一无二的书相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似乎轻如鸿毛。于是自相矛盾的是,《重现的时光》表述的关于书的理论却在否定这本书,否定这本以词语写成的实在的书及其阅读和写作行为;而在否定的同时,这一理论又转而拥抱一种神秘莫测的交流行为,普鲁斯特在谈论音乐时对此言之甚详:音乐“也许是所谓心灵交流的唯一实例,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文字的诞生和思想的分析的话”,“音乐仿佛是一粒没有开花结果的种子,只因人类走上了别的道路,即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道路。”如果实在的、词语写成的书真会被非语言的、非物质形态的理想之书否弃,那么写作和阅读合二为一的终极状态又有何益?在这种前提下,阅读和写作的对象“内在之书”,就成了《追忆》从开篇起就不断指涉的那不可言说的理想的最后变体,正是由于这一理想境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阅读和生活本身的融合—的存在,叙述者才意识到写作终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也就是“理想”理论的最后的表达形式了,毕竟《追忆》在终篇时并没有一味扮演天使的角色,只以尊崇彼岸为能事,它同样也在强调劳作的实在性和写作的物质性,例如,它有时也不再参照那“独一无二”的、神秘的书,而是借助其他内容丰赡的作品,如《一千零一夜》或者“也是用夜晚写成的圣西门的《回忆录》”来评判自身。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我的书”,“我的书”……《追忆》的结尾处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短语,却同时将“我的书”理想化、非实体化,仿佛在现实中阅读成了写作自身的盲区,写作遭遇了阅读构成的桎梏,尤其当写作在原则上就拒斥一切非写作的阅读时更是如此。普鲁斯特不会向序言之类例行公事、言不由衷的程式屈服,他在小说中塑造出贝戈特、埃尔斯蒂尔和凡德伊,正是以此寄寓自己的理念:此辈“天才人物”不容于时人,注定只有后世读者才能理解和接受他们。寄望于后世,无疑又是规避现实中写作与阅读间矛盾的又一策略。但这一切仿佛又是在说:“我的书”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应该存在的,即便它真正存在,也不会是理想的那本书。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质疑《追忆》到底是不是一本“书”。它的确是一些语句,也指向一位作者,但普鲁斯特否认它是阅读的单位。终其一生,如果按照批评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来衡量,普鲁斯特其实并未写出任何一本“书”。他宣称自己的心性更接近孩童和盖尔芒特亲王,而这样类型的人物也的确彰显出他与文学体制,与现存的书的世界的疏离。他不停地提及那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觅影踪的“内在的书”“本质的书”和“独一无二的真实的书”,这无疑遮掩了他与真实的作者群落乃至与众多其他书的关联,也遮掩了他与“文学的法庭”,特别是与“法庭文学”的关联。
当然,在插入《重现的时光》,拟仿《龚古尔日记》的文字中(杜撰版的《日记》里,同样的一批人物受到龚古尔兄弟之外的另一个人的观察,但这样的观察行为并未对人物有所揭示),普鲁斯特的确批评了自己的虚荣心和谎言。在经过一番自我批判之后,他是否会因此与文学的法庭决裂呢?在小说前文里,我们读到叙述者的外祖母生前曾对《书简集》(Lettres)的作者塞维涅夫人,以及小说里虚构的回忆录作家、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姐妹博泽让夫人同时心怀敬意,她希望叙述者把两位女作家奉为楷模,而不愿孙子追随波德莱尔、爱伦·坡、魏尔伦和兰波的道路,因为他们既“深陷痛苦”,又“名誉扫地”。不过,被杜撰版的《龚古尔日记》贬斥的却只有两位女作家中的那位虚构人物。博泽让夫人既是杜撰《日记》中的一个“人物”,在叙述者的评论中却又以一位“真实的作家”的面貌出现,于是她的存在就前后两次见证了文学的虚幻不实。然而塞维涅夫人和圣西门毕竟幸免于此劫,他们的文字并不被视为“笔记文学”,而是近于埃尔斯蒂尔的风格。塞维涅夫人的《书简集》和圣西门的《回忆录》虽早已告终,但在文学作品的意义上并没有被完成,除了那些“恋书癖”,众人皆否认它们是“书”,只承认这些文字是两位“作者”写出的一堆“语句”。用评判过《回忆录》其中一卷的斯万(他并不认为这一卷是圣西门最好的文字)的话说,“这不过是一部日记,不过好歹算是一部写得漂亮的日记”。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当《追忆》在结尾处参照《回忆录》等书时,它仍然带着一连串的否定和大堆的谨慎之语,这让小说终篇处的逻辑显得有些扭曲,但毕竟不像上文那么虚空,也更像对具体化的语言劳作的展望:“这倒不是因为我希望写出《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或者写出也是用夜晚写成的圣西门的《回忆录》,或者我在幼稚的童年时代喜爱的那种书……然而,犹如埃尔斯蒂尔·夏尔丹所说,只有抛开我们所爱的东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来……唯其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遭遇被我们所抛开的东西,在忘掉它们的同时写下另一时代的《阿拉伯故事》或圣西门的《回忆录》。”在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我们是否应该学习在贡布雷的平底餐盘上辨认阿里巴巴形象的莱奥妮姨妈,或者效法兼有“贵族大老爷的做派和艺术爱好者的品位”的夏吕斯,“像圣西门一样去描绘各种活生生的景色?”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阅读就仍然和孩童以及盖尔芒特亲王一样近于“物像崇拜”,就像“景色需要活生生”的想法所揭示的一样。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写作之外,的确再无其他的阅读方式可言,而写作终归意味着对阅读的遗忘。我们只能话尽于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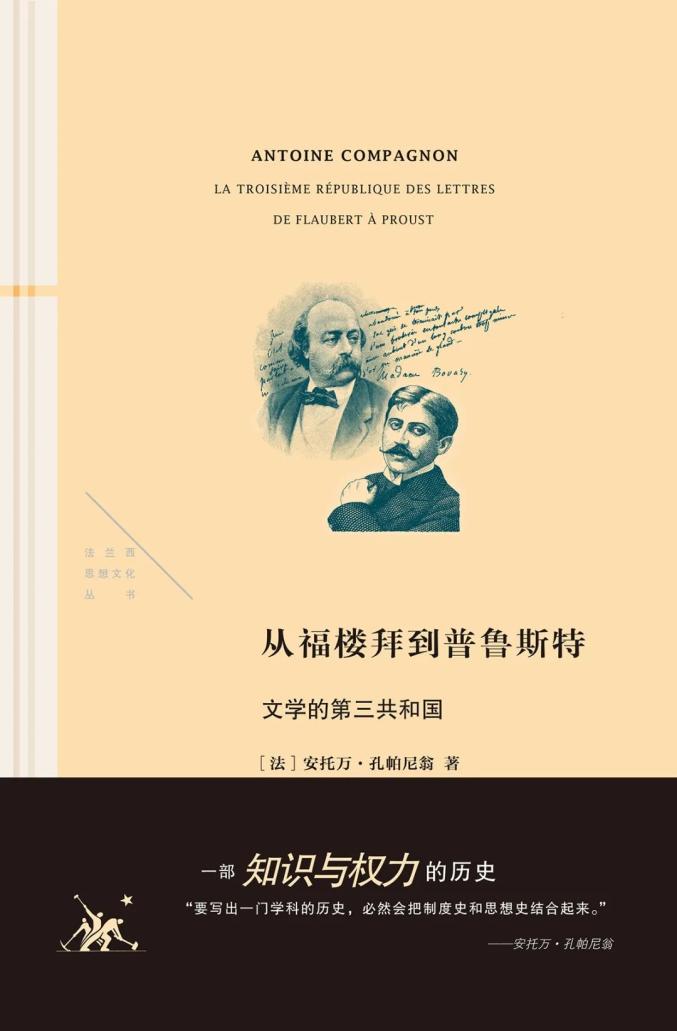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龚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2
ISBN:9787108073761 定价:88.00元
文学研究是自古以来的事业,但作为大学教育的“文学史”并不与生俱来。它的诞生伴随着一次学术权力的此消彼长。
1850年以来,作为学科的“历史学”从历史文学中独立出来,史学家在法国知识界迅速攫取话语权,成为推动中、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力成员。19世纪末法国的政教分离与教育改革促成综合大学的建立,在此之前,属于古典人文学的“文学研究”由修辞学主导,从此以后,在史学家的主导下,文学研究脱离了摆弄辞藻的面貌,被放入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中加以关照。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大学中初露峥嵘,“教育学”这个社会学分支也在此时诞生。朗松之于文学史,就如涂尔干之于社会学,作为两门彼时的新兴学问,二者都试图在文学/历史、哲学/历史间打下楔子,为自己开辟空间。
本书试图描绘的正是从普法战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这段时期内,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以及朗松、涂尔干、圣勃夫、吕西安·费弗尔等一干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第三共和国》甚至可以被当作一部理想的现代小说阅读。

原标题:《适合《追忆似水年华》的读法》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