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走在教育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 我写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的博士论文
廖霞
我已经忘了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第一次提及让我写三线建设研究回忆是何时,但距他在我去年9月的博士论文答辩之际正式邀约我也有快半年之久了。我以为时间久了,这事就渐渐淡忘了,没想到今年过年之前,徐老师再次问及我完成得怎么样了,于是我承诺他年后完成。每过一天,这笔“文债”在我心头就沉重一些,催促着我打开这尘封的文档。
此文之所以搁浅,原因有二。一是我又面临与博士论文后记中同样的问题。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我的答辩专家张宝蓉教授赞誉我的博士论文后记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后记,令我受宠若惊又愧不敢受。于我而言,恰恰最不敢拿出来的就是后记。相比那些流传甚广的博士论文致谢,我的后记既没有记载我一路的求学历程,也没有回顾整个博士生活,只是围绕博士论文写作过程对相关的师友致谢一二,故而势必有太多值得和需要感谢的人未能提及。并且,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伦理,我的论文没有像历史系的论文那样将受访者信息公开,在后记中也没能一一公开致谢我的受访者。虽然对于这样的处理,我和我的受访者一一作了说明,并且专程向他们致谢,大部分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做法,但我仍然心怀不安与愧疚。此时,徐有威教授“三线建设研究回忆录”系列的邀约递到了我的面前。遵循徐老师之美意暂时“混入”历史研究领域之门的我,是否要按照历史研究的做法公开受访者?是否又能尽数表达我的感恩?这是我犹疑的原因之一。
二是我还发现我研究经历中体会最深的问题,前辈已经遇到过并做了专门的深入分析和论述。当我回顾自己在研究中面临的种种两难时,我意识到这是在教育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隔阂”,于是我拟了“游走在教育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标题。而在我写了两千多字后,偶然发现本院前辈刘海峰教授已经写过“在教育与历史之间——高等教育史研究四探”“从历史到教育——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体验”等系列文章,对于横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教育史研究及他的学术经历已做过系统叙述。既然刘老师都数论教育史研究,我是否还有必要写自己的这一教育史研究经历?这是我犹疑的原因之二。
常言道,心债难还,文债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心债。文以致谢,文章是表达感恩偿还心债的方式。文以传道,文章也是传承前辈真知灼见的方式。我想,如果此文通过回忆博士论文研究和写作经历中的真实故事和体会,能够部分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也算有所意义了吧。
一、选题:从教育研究踏入历史研究
我的专业是高等教育学,我的导师邬大光教授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涉猎过众多主题,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但近年来却对“大学迁徙”的历史现象格外关注,将其列为“感兴趣的三大主题”之一、“研究的自留地”,并有心长久研究下去。
受导师的影响,加之自己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偏好,我有幸成为在老师“自留地上”第一个“挖矿”的博士生。而在我选题之初,我远没有料到在教育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之大。因为历史研究似乎离我们不远,在很多的教育研究中都会涉及相关历史的研究,即便其不是研究的重点。而一个专门的历史研究如何展开,是在我接触历史研究的学者后才慢慢了解到的。
2019年11月23日,由三峡大学等主办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在湖北宜昌举行。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外行学生写了一篇浅浅的小文,给会议投了稿。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收到了会议邀请函。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分会场做报告的时候,徐有威教授专程来听我汇报,我讲完还没落座便被徐老师“半路拦截”,徐老师不仅在分会场现场和最后大会总结时毫不吝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还热情主动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在后续给予我更多的点拨和鼓励。徐老师作为三线建设研究的前辈和权威,是我去参会之前就有所了解的,但这位大佬不仅不需要我去主动“套磁”,还热心谦卑至此,却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也是我前所未见的。
后来徐老师慷慨分享各种和我研究相关的史料和讯息,帮我联络受访者,带我拜访德高望重的亲历者,关心和指导我调研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提携后辈之心令我感动。同样对我的研究给予极大宽容和鼓励的还有宜宾学院周明长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教授等老师,会后他们也一直关心和关注我研究的进展。周明长教授看到和想到认为对我有帮助的资料便随时分享给我,即便我有时疏于回复也从不间断,并不曾因此责怪于我。张勇教授一度约我完善我的会议论文在C刊发表,但由于我的史料收集进展缓慢又不愿草草将就,最终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张老师因此选用了其他老师的类似论文,为此还专程电话与我说明,期间张老师还曾从重庆邮寄他的新书慷慨赠与我。对于初涉三线建设领域的我而言,能够得到领域内专家这样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实属荣幸,也铭感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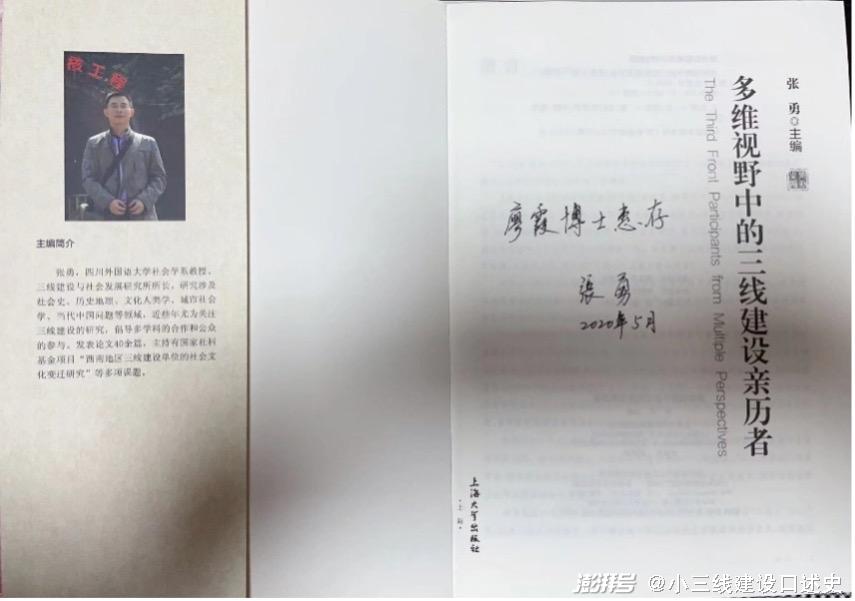
张勇教授慷慨赠书并邮寄给我
经过这次参会,我也几乎确定了我的博士论文要研究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个时期高校迁徙的研究仅有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刘洋老师一篇文章,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时期离现在尚不太久远,便于我收集一手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会我已经初略感受到历史研究与教育研究之间的距离,最浅显的例证就是对于文章参考文献的格式都是不同的。后来,类似的不同频频出现,令我不得不多方请教、反复思考、仔细斟酌和慎重抉择,我最合适的做法是什么。
二、问题与方法:在教育研究与历史研究间摇摆
参会回来以后我对于收集史料跃跃欲试,带着满腔热情希望尽快出去调研,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偏向历史方向。从宜昌回到厦门,我跟老师传达了三线建设领域专家对我选题的认可,同时也汇报了我的想法和徐老师的建议,那就是尽快去已知的几所学校调研。
我满以为导师会支持我的一腔热情,让我尽快进入田野收集史料,但他却给我浇了一大盆冷水,不仅不支持我那么早出去调研,还与我在研究路径上产生了分歧,并且这种分歧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希望从微观层面着手,选取案例收集资料,容易聚焦问题和着手进入研究。而我的导师认为作为一个少有人研究的陌生主题,就像一座不为人所知的大山,应该首先全面俯瞰全山,才能知道哪一块是值得细细赏玩的区域,而不是一上来就盲目钻进某一隅,因此他主张我的研究应该从宏观层面展开,并认为当时我的任务应该是收集信息确认所有迁徙高校,而非进入某些已知的迁徙高校收集资料。为此,老师和我长谈过几次,告诉我他教我的都是方法论,还让我写了几千字的谈话心得,终于又一定程度上将我拉回教育研究轨道,当时我内心诸多不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方能体会到老师的用心良苦。
而另一方面,正如许多做质性研究的学者提及的一样,在去田野之前,主旨问题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历史研究同样如此,在占有和研读史料之前,也常常不确定什么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因而在教师发展中心沙龙上,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向我导师提议,先广泛收集和占有史料,再让我们从中确定问题。同样,在我选修厦门大学历史系刘诗古老师《史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上,我发现历史系的同学和老师都有其领域内的大量史料,相比之下我已到了收集史料的迫切阶段了。
其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席卷全中国,我们也都只能在家中线上上课,刘老师十分理解我的难处,教会我很多实用的已有文献查阅方法,还将他所收集的相关史料无私分享给我,随时解答我作为历史系外行的入门性和基础性提问。刘老师对课程的每一讲都精心筹划和准备,对每一个学生的研究计划细心修改、辅导和讲解,后来每次我有疑问通过微信向刘老师请教时,他都热情释疑,并询问我论文的进展,给予我热心鼓励和有益建议。同样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写作方面给予我指点的还有历史系的张金林、苏颂等师兄,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及写作在规范上有诸多的差异,每当我向他们询问相关规范时,他们都详细给我解释他们的做法,并结合我的情况给予我可行的建议。
正是导师把我“拘”在学校,同时又得益于这些老师和同学的启发和帮助,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有效地找到了与我论文相关的大量二手历史资料。因而,也得以从整体上较为清楚和全面地梳理了三线建设时期的高校迁徙图景,这为我后续研究的开展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三、史料与理论:历史研究与教育研究的融合
历史研究重视史料,强调论从史出,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这是我上过史学研究方法课后的强烈感受。而教育研究重视理论解释,特别是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强调要有理论基础和理论深度,这是我写完初稿后才开始深刻认识到的问题。
(一)原始史料的收集
即便找到了一些二手史料,但对于史料的惆怅也从来没有停止,伴随我从确定选题到开始写作的许多个日日夜夜。一有机会,我就找线索找史料。
1.实地考察校园旧址
2021年1月16日,在几个同学的陪伴下,我去了位于陕西汉中的原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旧址。相比南方小城厦门的勃勃生机,冬天的汉中显得格外萧瑟,特有的青砖建筑增添了校园的历史沧桑感,想起五六十年前和我一般年龄的知识分子和建设者曾在这里热情挥洒青春与智慧,满腔敬意油然而生。我在这里亲眼见到了曾经在这里工作学习的以后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教授饱含深情的褒水连城,真实触摸到了西阶、101等满载亲历者们回忆的教学楼,还听一位亲历者讲述了颇多当时陌生后来渐渐了解的名字和故事。文字里记载的历史场景似向我缓缓走来,历史研究特有的魅力那一刻开始走进我的心里。

2021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旧址
2021年9月,我又走访了南京大学中南分校旧址。这一次,我先联系到了南京大学湖南校友会会长李特南老师,李老师热情分享了他们曾组织亲历者重返中南分校的经历,并向我推荐了几位便于访谈的亲历者。南京大学中南分校没有办学,校园后来为军工企业华南光电集团所用,华南光电原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沈林海老先生就是南京大学留下来的随迁老师。沈老师知道我是湖南宁乡人,特意邀请了我的老乡、已经退休的干部张亚晖老师一同来厂,厂领导也精心安排了孔露娟老师、温晓花老师等几位老师一起带我参观了校园旧址,沈老师给我详细介绍了分校建校和企业发展的历程,还分享给我许多珍贵的老照片,令我收获颇丰。

2021年9月6日于湖南常德,南京大学中南分校旧址。左起依次为温晓花老师、沈林海老师、笔者、张亚晖老师
2.访谈亲历者
2021年7月,徐有威教授来厦门大学参加历史系的会议,邀请我和他几天后一起去北京访谈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的亲历者。这一次我的导师没有反对,他刚好要到北京出差,亲自带我一起到北京并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我的调研,路上还细心叮嘱我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
到北京后,我先去拜访和访谈了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王副校长2020年8月到厦门大学参加潘懋元先生从教八十五周年高峰论坛,经我的导师邬大光教授引荐和介绍,他知道我在研究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后,就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王副校长基于他的工作笔记,对于汉中分校的经历写了十万余字的回忆录,并将其无私分享给了我。这次近距离访谈王副校长,他对我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答,并对于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办学做出了他的整体评价。我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于汉中分校的怀念,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的视野和胸怀,也再次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访谈后他坚持要请我和同行的同学出去吃中餐,我们事先约好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蒋凯老师访谈,王副校长只好遗憾作罢,并邀请我们离京之前再次去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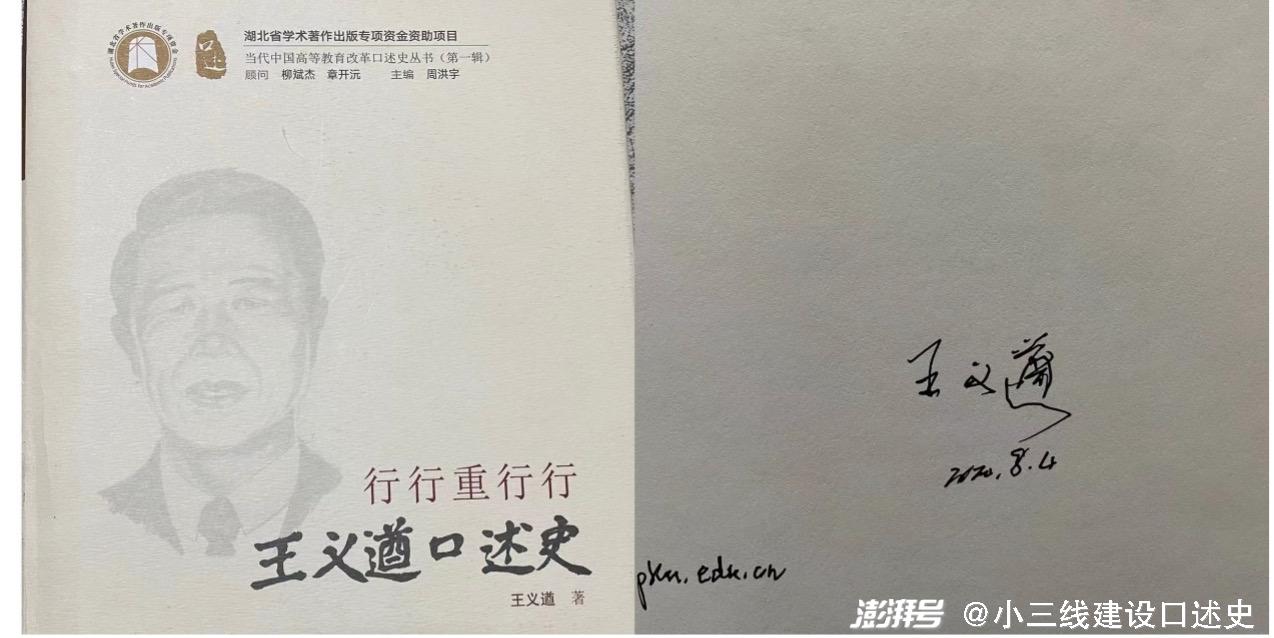
2020年8月王义遒副校长来厦门,我请他为我在他的口述史上签名

2021年7月16日在王义遒副校长北京家中
第二天,通过张从教授的居中介绍,徐有威教授带我和北京大学汉中分校部分亲历者座谈建立了联系。各位老教授谈笑风生忆当年,将各自记忆中的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呈现了出来,让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校园面貌与故事聚合在了一起。赵丰田教授侃侃而谈回忆其与周培源校长的往事,恍惚间我似看到了数十年前那些风华正茂正青春的北大学子。在张从教授和何永克教授的引荐下,徐有威教授还特别带我拜访了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及其夫人。陈校长温文儒雅,在我们即将离开之时,陈校长又陪我们在院子里逛了一圈,才将我们送了出来。

2021年7月17日在北京拜访陈佳洱校长及其夫人。左起依次为徐有威教授、陈佳洱校长及其夫人、张从教授、何永克教授
特殊时代汉中的生活和科研条件艰苦,但却历练和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且学者、学生、后勤人员之间的交往也甚密,关于这些大学者的趣闻和美谈,我在汉中探访时已经听到很多。我曾听汉中的亲历者讲过陈佳洱教授与馒头山的故事,这次亲见陈校长和夫人,也证实了许多当时的趣事。
陈校长坦言在汉中时他一直不间断做科研,为后来回京后的学术发展厚积了基础。王义遒教授也曾透露,他在汉中的科研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校厂合作条件,在大家的精诚合作之下,原子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国际都居于前沿,而后来回京后由于土地、人员等资源条件不足而遗憾中断,这令我们都唏嘘不已。陈校长夫人在汉中时担任作为时为本科生的张从教授、何永克教授的班主任,在他们共同回忆当初学习生活的谈话里,大学生活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却又带着时代的特殊印记,那种师生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时光在只言片语之间叫人无比动容。

左起徐有威教授、陈佳洱校长、张从教授(2021年7月17日 北京)
后来,我又和部分亲历者做了更深入的访谈。张从教授不仅分享了他大学时代从北京迁到汉中的经历,还分享给我多本他参与主编的回忆录,从那些真实又传奇的故事中,仿佛看尽一代人从青年走过来的风雨人生,那些特殊年代的纪实性文字拉近了我与历史的距离,也增进了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在白郁华老师的周到安排下,我在李金龙老师的家中,访谈了白郁华老师、李金龙老师及其夫人,并在他们的热情推荐下,又访谈了唐孝炎院士、刘元方院士等亲历者。唐老师的温柔,刘老师的耿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年才教授说我从北海北到蓝旗营太远,提议在中间的紫竹院公园进行访谈,还为我周到查好了公交路线。于老师年过八旬,身手矫健,但看着他坐公交回去的背影,我心中既感动又愧疚。姚淑德老师当时家事繁忙,后来陕西理工大学的相关老师到北大展开座谈会,姚老师第一时间告知我可以去参与,可惜因为疫情我难以离厦,只好作罢,但我仍十分感念姚老师的用心。
这些老师们有的是从北京随迁到汉中的教师,有的是从其他单位调到汉中的教师,还有的是从北京随迁到汉中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他们不仅见证了学校迁徙和办学的历程,也经历了自身曲折成长历程,还见证了那个时代里一大批青年人的成长。我原来只知道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的教师中有诸多著名的院士、校长、副校长等知识分子,后来才知道就是在北大汉中分校培养的工农兵大学生里也有院士和众多著名知识分子,北大在汉中的14年中为国家培养的人才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旧址的院士墙。2021年1月16日摄于于陕西汉中。
听从导师的建议,我研究的重点还是宏观层面,访谈面没有铺太广,访谈内容也没有问太细。访谈资料一是作为宏观背景层面的佐证材料,二是主要作为“迁建历程”及“迁徙高校办学”章节的相关支撑材料。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珍贵的访谈资料都为我的论文注入了鲜活生命力,和这些老教授的交流也是我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对他们满怀敬意和感恩,这种情意似用任何文字都难以尽表。

2021年7月17日于北京,与徐有威教授一起座谈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亲历者。左起依次为徐有威教授、白郁华教授、姚淑德教授、李金龙教授、赵丰田教授、王义遒教授、张从教授、于年才教授、何永克教授、笔者
3.其他史料收集
调研期间,我还去了部分地方档案馆收集史料。如北京市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不知是我查阅档案经验不足,还是关于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的档案资料在地方档案馆确实较少,地方档案馆查档的收获并不太理想。但是每当将所查档案资料用于论文写作时,却有只言片语胜过万千旁证资料之感,档案资料的魅力尽显无疑。可惜的是,由于疫情和历史等原因,去高校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难上加难。
另外,调研过程中亲历者还分享给我各种相关的文字图片材料。有些是亲历者的回忆录,有些是相关学科的发展史,有些是校园和亲历者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史实全貌,对我的论文写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的虽不一定在论文中一一呈现,但其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可不计。

姚淑德教授赠书《情聚“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纪事》
(二)论文的理论基础与深度
写完初稿后,我的导师给予了我极大的肯定和包容。虽然他已然意识到我的论文在理论深度上的不足,但他和大部分历史研究者一样,十分肯定我在史实梳理上的贡献。但在预答辩过程中,教育学和管理学的专家犀利指出我必须要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对论文进行分析,否则论文将没有落脚点,也无法深入,无法体现理论深度。更有老师直言我的博士论文没有体现出博士生应有的训练,没有理论框架和理论分析,我还是一个没有入门的博士生。历史研究的老师赞誉我的论文弥补了历史空白,而教育学的老师却批评我研究尚未入门,这样的反差令我迷惑又委屈。
即便历史系的老师和博士生告诉我他们的博士论文不一定要有理论分析框架,但是我毕竟是教育学的博士生,还是要按照教育学的规范来做。得益于预答辩专家的宝贵建议,得益于导师的关心鼓励,以及朱平教授、李枭鹰教授等老师的点拨,扎根于史料与史实反复推敲,适宜的理论终于渐渐浮现出来。
最后,我以历史制度主义的“宏观深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为整体分析框架,分别运用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资源空间配置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对应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具体分析,对这一时期高校迁徙进行了理论反思。现在看来,也许我的理论分析高度还很不够,但至少至此为止是一篇较为完整的教育史博士论文。从论文开题到论文答辩的过程中,要感谢参与我开题的徐岚教授、谢作栩教授、陈武元教授、郭建鹏教授、郑宏副教授,参与我预答辩的赵婷婷教授、朱水涌教授、计国君教授、张宝蓉教授、郑宏副教授,参与我答辩的周川教授、蒋凯教授、朱水涌教授、赵婷婷教授、张宝蓉教授等众多专家,是他们的严格要求和宝贵建议,让我的论文日臻完善。同时,我也要感谢别敦荣院长、刘振天书记、黎之静老师、吴晓君老师、冯波老师、郑雯倩老师、陈若凝老师、赖珊珊老师、贾佳师姐等众多老师们给与我的各种关心、鼓励与支持。
诚如刘海峰教授所言,“对教育史学科而言,教育与历史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作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较为盲目,而没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研究则可能流于空洞”,我的这一经历可能完美地诠释了他这一论断,又或可说他这一论断完美地总结了我对于教育史研究的体会和认识。
事非经过,不能体其情、察其意、知其难。在我修历史系刘诗古老师的史学方法课的同时,我还修了本院张亚群教授的《教育史学》课程。张老师在课堂上其实介绍过刘海峰教授的文章,但我却印象不深,直至我的博士论文做完来写研究经历时我才发现我的经历前辈早已经历,并做了高度的理论反思。要说有不同之处,刘老师是从历史学走进教育学,并在两个学科里长期耕耘硕果累累;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之辈,从教育研究走进历史研究,浅尝其意。竟能有此共鸣之感,也是我作为后辈的幸运,以及作为初入门研究新手的幸福吧。故而谨以此文再次深切致谢我研究的所有受访者,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是你们让我拥有了这一份幸运和幸福!
(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对本文提供了宝贵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湖南理工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2022年9月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学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