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抗日战争研究︱彭春凌: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及暌离
引论:章太炎再会井上哲次郎哲学
1899年,章太炎在东京结识明治哲学的“性格决定者”井上哲次郎,两人有多次晤谈。章太炎虽佩服井上哲次郎学识渊博,但他当时还沉迷于社会学,认为哲学“最无用”。章太炎的“心不在焉”使他和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初会”并没有碰撞出太多的思想火花。随着投身革命后思考革命的动力问题,章太炎逐渐对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其阅读、对话的对象也从东京哲学圈姉崎正治、井上圆了的宗教学著述扩展到井上哲次郎自身的哲学作品。从1905年在狱中研读井上哲次郎编辑的《哲学丛书》、撰写《读佛典杂记》,到《民报》时期和井上哲次郎类似、立足于“我”(das Ich)来辨析认识和伦理问题,再到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之《原道》上篇拥有井上哲次郎少作《读韩氏〈原道〉》一些相似的逻辑痕迹,《原道》下篇使用了与井上哲次郎“现象即实在论”相同的核心理论术语“有差别”与“无差别”来诠释“理”和“道”,这整个阶段都是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期。对于曾经真正刺激过自己的思想家,在智识生命的关键时期,总是要一次又一次与他再会。章太炎之于井上哲次郎,情形亦复如是。

章太炎
所谓“现象即实在论”,“乃调和唯物唯心二论而位于其上者”。它试图解决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割裂问题,融合主客观、内外界而生成绝对的、一如的实在。当时有日本学者甚至把它提到民族自尊心角度来理解,谓,现象即实在论“融合康德的先天唯心论和哈特曼的先天实在论而立于其上”,对世界的解释毫无任何障碍,“又称为圆融实在论”。德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界中是最进步的,井上哲次郎让人明白日本的哲学界是“不易侮的”。长期以来,研讨章太炎“转俗成真”时期的思想,或者直接从高远处原理性质的唯识佛学、康德、叔本华德国哲学介入,或者径行落实到切近处章太炎所针对的《新民丛报》立宪改良主张、《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潮等,而往往忽视位居中间层的、以井上哲次郎“现象即实在论”所代表的明治哲学及其政治实践。章太炎从《读佛典杂记》到《原道》等论文中透露出来的井上哲次郎学说的蛛丝马迹,宛如冰山一角。只有从这一角拖拽出井上哲次郎“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观念,才算捕捉到一角下的大冰山,也就是章太炎所再会的井上哲次郎哲学之真正主体。
此前有研究已经注意到章太炎《读佛典杂记》与《哲学丛书》文献上的关联。特别是,《读佛典杂记》第一段无论是援引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快乐不能连续之原因的分析,还是以妇人分娩为例,来证明活动或者摆脱阻碍活动之力才是人行动的目的,其内容脱化于井上哲次郎的学生森内政昌的文章《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森内政昌“人爱活动,非爱快乐”的论述吻合了章太炎对人生的悲苦体验,帮助章太炎厘清了欲望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深得他的认同。尚未引起重视的是,森内政昌其实是在演绎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只有落实了森内政昌文章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内在勾连,章太炎思想转型过程中井上哲次郎本人的哲学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实际功效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作为天皇制国家主义道德意识形态和理论化的代表,井上哲次郎历经明治宪法确定立宪制国家基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日本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家主义思潮膨胀,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涌动,国民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状态的全过程,他一路都在应对并再建构自身的理论。通过与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对话,明治后期日本的政治社会演变和思想论争在章太炎的思想表达中也都留下了印记。这些历史元素究竟如何体现在他们认识论、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之暌离乖违的过程中?本文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为什么是“活动”:从章太炎、森内政昌到井上哲次郎的逻辑溯源
1900年,井上哲次郎在《哲学丛书》上发表了阐述自身认识论、代表“现象即实在论”最终完成的长论文《认识和实在的关系》和谈自身伦理观的文章《利己主义的道德之价值》。森内政昌《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涉及认识论与伦理学的两部分,与上述两文一脉相承。最为关键的是,井上哲次郎和森内政昌的文章同样在《哲学丛书》上刊载,也都在章太炎的阅读范围之内。虽然《读佛典杂记》首段与森内政昌的文章形成了直接的对应,但正因拥有井上哲次郎的作品作为思想的底板,章太炎无疑才能加深对德国哲学的理解。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井上哲次郎哲学在章太炎思想转型过程中长久发挥作用的依据。下面即来一一说明其中的勾连。
章太炎最感兴趣的关于“活动”的问题,在森内文中是从第四章“实在的假定(实在观念)”开始讨论的,而这一章的内容几乎是对井上哲次郎《认识和实在的关系》一文第二章“认识的事实应该如何说明”的概括和归纳。但两者的逻辑顺序是恰相反逆的。森内从总的“宇宙为一大活动”进入,逐层分解剖析物理学的原子运动、有机界的生活生理活动,再到人精神活动的真实要素,即“始原的心的活动”——“动向”(Trieb,今译为“本能冲动”)。而井上哲次郎则是从以“动向”为基础的人之认识的最初阶段“感觉”出发,再逐级上升到无数天体和原子普遍存在的“活动”。井上哲次郎由精微至宏大逐级推演“活动”之普遍性,从这一过程能透彻理解其“现象即实在论”的根本逻辑所在,从而打通森内一些言之不详的逻辑关节。
井上哲次郎从认识是如何生成的来展开讨论。认识的准备阶段即是单纯的感觉,感觉产生于人在行动时身体和围绕物相接触而接受到“感性的印象”(Sinneseindruck),此后从感觉而生知觉,从知觉对合外界的现象而生“写象”(当即Vorstellung,今译为“表象”或者“观念”)。到了产生“写象”,应该说就形成了认识的事实。至于最初阶段的感觉是怎么得到的呢?井上哲次郎说:“盖吾人得到感觉,乃是自发的活动的结果,即以自然的动向为基础。”为了证明“先有自发的活动,之后一切心的官能得以发达”,井上哲次郎主张从进化论特别是生物起源学(genetisch)方面予以考察。他推介的理论来自德国生物学家、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在初版于1868年的《自然创造史》(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中,海克尔提到最劣等的动物、甚至都称不上动物的单纯有机体“阿米巴”(Amoaba),以及在原生生物界(protistenreich)处于最下级位置且更单纯的有机体“毛柰伦”(Moneren)。它们“构成有机无机两界的过渡点,如此单纯的有机体,不能说有感性的知觉,然而,自发的活动却是这样单纯的有机体都具备的”,由此可见“自发的活动先于感觉”。海克尔把心理学看作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对于人的个体而言,心意和身体一样,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发达;新生儿是没有高等的心的作用的,发出啼哭,活动四肢,吸吮乳房,都是自发活动的结果;先有自发的活动,像“认识”那样高等的心的作用才渐次发达出来。“无论就人类一般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其发达的成迹是全然相同的,即种系发生上(Phylogenic)和个体发生上(Ontogenic)并无二致”。这里,井上哲次郎藉助海克尔的“重演”理论来说明个体精神从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类进化历程中精神发展的过程。
接下来,井上哲次郎引介了哲学和心理学者对于上述观点的见解。首先是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冯特认为,“一切精神的官能的真元素乃是感觉和意思尚未分离时的初发的活动力,即是动向。动向作为心的现象的根本,一切精神的发达渊源于此,这是被一般的及个人的发达史所证明的情况”。井上哲次郎继续分析说,“冯特氏以感觉、感情、意思三者,来把握终局的心的作用;其中,感情是以意思为基础的,如此一来,就可归结为感觉和意思两者。然而使两者从开始即组成不能分别的合一的活动者,即是动向。所以动向相比于它分别出来的叫做‘感觉’者、‘意思’者,是先于它们的根本的存在者”。森内政昌介绍冯特对“动向”的分析时,有一段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文字。只是,井上哲次郎所说的“意思”,森内用的是“意志”。总之,动向乃是先于感觉和意志,并使二者合一而不能分别的根本的存在。
继而,井上哲次郎援引了德国哲学家约翰尼斯·雷姆克(Johannes Rehmke)《普通心理学教科书》的内容,进一步将“动向”解释为还不伴随着意思(意志)的精神的自发活动,是先于意思(意志)存在的不任意的行动。复又根据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心理学教科书》指出,一般的动向毋宁说是生理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动向”乃是衔接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初发的活动力。
井上哲次郎紧接着主张,为了避免“动向”这个词的模糊性,用“行动”(Bewegung)这个词是更为恰当的。他先列举了意大利人类学家朱塞佩·塞吉(Giuseppe Sergi)对行动的六种分类:原本(原始)自动的行动、反射的行动、直动(直觉)的行动、情绪的行动、有意的行动、派生自动的行动。前两种属于还不伴随精神作用的纯粹生理的行动,到第三种也见不到意志的存在。由此可证确有先于感觉和意思(意志)的“行动”。随后,他援引丹麦心理学家哈格尔德·霍夫丁(Harald Höffding)和长期在德国工作的生理学家威廉·普莱尔(William T. Preyer)的心理学著作,是想引出关于神经作用的问题。霍夫丁指出,有机体从外界受到刺激,开始伴随着感觉的行动,生成“行动感觉”(Bewegungsempfindung),这种因神经中心富有紧张力而生成的行动,是自发的、无动机的。普莱尔认为一切精神的发达的根本制约是感官活动性;感官活动性的四个阶段,包括神经耸动、感觉、知觉和写象(观念)。第一个阶段神经耸动是超绝于感觉的自发活动,可以看作生理的现象。如此一来,就可见出精神和身体、心理与生理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而在身心关系中起衔接功能的是神经。遍布全身的神经纤维又具备离心和向心两种官能,一是从中枢接受命令引起肌肉收缩,一是将皮肤受到的外部刺激向内传送引起感觉。在神经纤维的两种官能中,精神和物质即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得以成立。行动,在神经纤维的两种官能中是共通的。井上哲次郎颇为得意地总结道,“动向”作为超绝于一切心的作用者,本身就兼具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但“动向”一般来说惯用于有机体。当把“动向”一词转化为“行动”时,“就赋予了其更广泛的意义,行动,即活动,是主观和客观共通的东西,属于内界和外界还未有分离的先天未画的状态”。
为了证明自身的现象即实在论,使用“行动”一词仍不是井上哲次郎的最终目标。他说:“行动乃超越于主观客观者;盖世界乃是一大行动,大到无数天体,小至无数的原子,从外界众多的物理现象到内在众多的心理的现象,全都是行动。为了避免‘行动’的话语必然会预想到空间的麻烦,那么,我称之为‘活动’(Thätigkeit)。”“活动”才是井上哲次郎最为满意的、能够匹配他的实在论的理论术语。井上哲次郎持一元的世界观。在他看来,主观和客观都是不能否定的,从认识的方面来看,主观和客观都是存在的。但认识是有界限的,认知的对象是差别的现象界。因此,作为认识的对象,主观和客观指向的都是差别的观念。唯有对这些差别的观念进行“内面的直观”(innere Anschauung)或者“综合判定”(Synthetisches Urtheil),才可以到达无差别平等的观念。无差别的平等,即是实在。但是不存在离开主观、客观占据第三者位置的“实在”,意即“失去主观、客观之差别者就成为实在(Wesen)”。“如差别同一体使之对立者,则成为主观、客观,如融合主观客观而还原之则成为实在;真可谓一而三、三而一”。“行动”或者“活动”,正是主、客观失去差别之所在、融合之所在。换言之,也是使现象达到实在的所在。而“哲学的终局目的无他,惟在明晰此实在观念”。因此,“行动”或者“活动”就成为理解井上哲次郎“现象即实在论”最为关键的枢纽。
为什么“活动”相比于“行动”更让井上哲次郎倾心呢?这是因为客观的实在是“无差别平等的实在,即是离于空间时间及因果规定的物如”。说到“行动”,还是会产生关于其发生场所的空间的预想,也就是说往往离不开空间的规定性。表意更为广泛、能脱离更多规定情境的“活动”一词就成为描述各界各种各类共通性最好的选择。井上哲次郎说,“活动”是“心理生理物理共通者,扩充而言之,不问内界外界之别,世界万物共通的,都是指向‘活动’;‘活动’也不能直接说是世界的实在,‘活动’是最接近世界的实在者,即是从现象渡入到实在者”。
从指向人心之现象的根本、一切精神发达的源头、汇通生理过程与心理过程的“动向”,到把大至无穷宇宙天体的运转微至原子颗粒的运动皆归入其中、沟通主客观和内外界的“行动”,再到通向心理生理物理等世间万物、离于空间时间和因果之规定性的“活动”,井上哲次郎寻找最合适的词汇的过程,事实上也是论证其“现象即实在论”的过程。对于章太炎来说,通过阅读《认识和实在的关系》,无疑可以补足森内政昌一文从宇宙的“活动”讲到人体生理的“动向”之间的逻辑断层,使他最感兴趣的“活动”之内涵更加明晰化。与此同时,井上哲次郎大量援引关于进化之生物学、心理学等各种重要文献也确实为章太炎提供了丰富的德国思想学术渠道。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之后即赴东京,他在《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俱分进化论》,里面表现出来的对生物学及心理学上的进化论说之熟悉程度令人惊讶。其中自然包含着像《认识和实在的关系》这样的作品所带来的知识养料。比如,为证明“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章太炎谈到,生物随着进化程度逐渐提升、感觉器官会变得更发达,所能体会到的快乐和痛苦都愈发增多,即“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他分析了生物界从最低等生物发展到最高等的哺乳动物——人所能感受到的苦乐的差异。他说:“以生计言,他物所以养欲给求者少,惟人为多。最初生物,若阿米巴,若毛柰伦,期于得食而止耳。视觉、听觉、嗅觉皆未形成,则所以取乐者少。”这其中关于最初生物阿米巴、毛柰伦尚未形成感觉,而只有自发活动的分析,源头显然是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井上哲次郎《认识和实在的关系》完整描述了海克尔对阿米巴、毛柰伦感知状态的分析。可堪对照的是,森内政昌《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提到了海克尔对原生界(Protistenreich)的界定及其描述的最下等有机体、介于有机界与无机界中间的毛柰伦。森内政昌文章在这里并没有同时提及阿米巴,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涉及阿米巴虫。这就意味着,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的描述,不一定来自森内的文章,而很可能本于井上哲次郎《认识和实在的关系》。或者,章太炎至少通过井上哲次郎的渠道又去阅读了日本介绍海克尔学说的著论。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认识论及伦理观的暌离
从“人爱活动”这个判断层层掘进,可以清理出章太炎与森内政昌、井上哲次郎的思想关联。通过井上哲次郎的哲学,章太炎得以进一步汲取以海克尔、冯特为代表的德国进化主义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并明确以“活动”作为宇宙与人的交汇点。然而,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共通性,并不能掩盖他们已在认识论和伦理观上出现深刻分歧的事实。
章太炎思想转俗成真,在认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为趋向主观唯心论。章太炎1906年出狱之后谈及哲学“甚主张精神万能之说,以为万事万物皆本无者,自我心之一念以为有之,始乃有之矣”。章太炎的主观唯心论受到佛教与西洋哲学的交互熏染,理论来源颇为多元。他认为,森罗万象的世界都是“阿赖耶识”这一本体幻出的世界,是心中之幻象。《建立宗教论》用“原型观念”诠释阿赖耶识,受到姉崎正治《上世印度宗教史》相关论述的影响。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以为,“吾人不能承认外物的物质存在,外物只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在吾人感官中映写的观念即记号,乃是外物生成之所”。类似知识也在章太炎的涉猎范围之内。叔本华(即“索宾霍尔”)的意志论将客观世界视作人心之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思想来源。章太炎说:“当海格尔始倡发展论时,索宾霍尔已与相抗,以世界之成立,由于意欲盲动,而知识为之仆隶……其说略取佛家,亦与僧伽论师相近。”
而主观唯心论恰恰是信仰实在论的井上哲次郎及森内政昌所猛烈批判的。森内批评说,“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认为我们所有的认识全都是主观生成之物。如果全部都是主观的话,我们的知觉像也好、概念也好,我们的妄像、妄想、梦也好,都拥有同样的主观的确实性”。换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不能区别现象和妄想”。由此,他认为“贝克莱陷入了一种迷妄论”。井上哲次郎同样不认同万法唯心的“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他非常确定,“客观世界不是主观的结果,是主观以外的实在”;至于“唯心论者以客观世界为心意之所现,戴青色眼镜所见的世界万物皆为青色”,他以为不值一驳,谓“此见解之误,破之不难”。
那么,章太炎的主观唯心论是否真如森内政昌所批评的那样,属于不能区别现象和妄想的迷妄论呢?这里必须提到理解革命时期章太炎思想的关键概念“随顺进化”;在这一概念的内外两侧,他安顿了圆成实自的真如与依他起自的幻象两个世界。从根本上他主张“世界本无,不待消灭而始为无;今之有器世间,为众生依止之所本,由众生眼翳见病所成,都非实有”。然而,在如眼病所见、人心幻化出的世界中,他相信万物仍旧遵循着进化的法则,此即“随顺进化”。当然,要探究这个幻象中的世界,不仅不能陷入迷妄,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方法。“随顺”的姿态与儒佛二教在传统士人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谓一脉相承,以佛养心具有某种功能主义的色彩。
井上哲次郎及森内政昌所推崇的实在,非常接近斯宾塞“不可知”的界域,“同样是非现象、无际限、无形状”。现象界才是认识的对象,实在则要依靠信念而获得。如果将章太炎“随顺”的两侧和井上哲次郎“现象界”与“实在界”进行比较,章太炎所谓人心幻化出的、随顺进化的世界,大体相当于井上哲次郎所言的现象界。然而,井上哲次郎完全不能认同现象界是梦幻泡影。井上哲次郎批评叔本华的意志论,叔本华以意思(意志)为实在,是与活动相近者;然而,“意思(意志)本是个人所有,乃是最初的心的作用”,“合并客观世界为个人所有的最初的心的作用,这一解释偏于主观的考察,亦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实在观念”。井上哲次郎的批评,从侧面点出了章太炎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在生发于个人的自我感知。由此也导向章太炎伦理观的核心乃至政治哲学的出发点,都在由个人之感知扩展出来的个体自主性。章太炎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内面的精神价值。《读佛典杂记》就认为“天下无纯粹之自由,亦无纯粹之不自由”。即便囚徒奴隶,也可在顺从和以死相拒间进行选择。《答铁铮》说,“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其术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道出了如此偏主观唯心的认识论所具备的心理功能。身陷囹圄的艰难危急之时,内心的自由感,令章太炎获得了精神解脱。而“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自贵其心还能激发革命人的战斗精神,确保了革命道德的纯粹性和崇高性。
井上哲次郎的看法与章太炎大相径庭。井上哲次郎融合主客观、包含内外界、无任何际限的一如之实在观,使他将理想的极处置于超出个体之外的绝对的实在之物;他的伦理观走向了否定真的个体之存在、否定个人主义的方向。由此,井上哲次郎的伦理观就与章太炎出现了根本的暌离。
“我现实的世界非世界的全体”,井上哲次郎以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为例,来谈实在界。他说:“我们身边的空间如同没有周围的桶,无论向如何的方面,都是思想所不及之处的非现实。无限的非现实中的一小部分,成为我现实的世界。”至于时间,则由过去、现在、未来组成。只有现在才是现实的,因为过去已经逝去、未来尚未到来,都属于非现实。然而,“现在瞬间成为过去,未来瞬间变成现在。刹那、刹那地变迁推移,从现实向非现实移动,又从非现实向现实移动,无定住之所。”这就意味着,“现在在过去未来之间,然而过去和未来没有际限,没有际限的非现实中的仅仅一小部分,构成我现实的世界”。换言之,我现实的世界“无异于是无限的非现实中浮出的海市”。井上哲次郎指出,上述非现实的世界,即是实在界。
在这样的时空观中,井上哲次郎关注的“我”,自然不是个体。他说,“我是关联父母和子孙的大我,父母是过去的我,子孙是未来的我,我是继续父母者,子孙是继续我者,我和子孙是换得父母的形骸而存续”。与此同时,我心的活动,“差不多是经过了不能思维之程度的遥远的历史遗传下来的”,是在“无限的经历”之后才到达我这里。“扩充而考察之,个体,不过是比较而言的。不存在有真的个体。唯有无限的活动。活动其自身,超越空间、时间及因果的规定”。
至于伦理观,井上哲次郎指出,在讨论道德时,有自然法(Naturgesetz)和伦理法(Sittengesetz)的差别,不能混同理想与事实。“利己”即便是自然欲求的事实,也未必就是道德的。人类需要构造利他的道德理想。道德的行为以理想为目的,是不得不如此。井上哲次郎人生哲学的出发点,终其一生都在辨明包括生存欲、生殖欲的自然欲(Naturtrieb)和与自然欲相对的精神欲,或曰智能欲(intellektueller Trieb)。事实上,强调伦理法则对宇宙法则的制约,是包括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内,思想家们反省进化论之物质宇宙观时通常的取径。森内政昌也认为,“利己心是下等人就有的感情;而爱他心则非知性愈益发达、自觉观念愈益明晰后而不得存在”。总之,他们都强调爱他心处于利己心的上位,是人类知性发达的表现,是道德的依据。
井上哲次郎宣布,“吾人单刀直入追问‘我’(das Ich)的观念,来粉碎利己论者的堡垒”。这里的“我”,附上了德语“das Ich”的表达,目的是将之陌生化、概念化。从定义“我”是什么出发,来辨析人之善与恶、自利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也正是章太炎伦理思想的逻辑所在。从1905年《读佛典杂记》第三段开始,到1906、1907、1908年的《俱分进化论》《人无我论》《四惑论》,对“我”的界定和思考是一以贯之的。《读佛典杂记》提出“自利性与社会性,形式则殊,究极则一”,轰响了批驳井上哲次郎的第一炮;而其中明确“我慢意识”、解析“我”与“我所”,也蕴藏着章太炎成熟期思想的雏形。在研习佛学的同时,与井上哲次郎的伦理观对话,构成了它们共有的背景。
井上哲次郎批评,利己论者的“我”是一己之身、渺然一身之我。他指出,正确的“己”是“连结祖先和子孙无限的连锁的一部分”。一己之身的“我”乃是社会有机体这个“大我”的一部分,不可挣脱地处于五伦的社会性关系网络之中。井上哲次郎“我”的定义,与他的时空感以及实在论是一脉相承的。章太炎在《人无我论》的开篇,就区分了两种“我”。一是“常人所指为我”,普通人从婴儿堕地到一期命尽所体验到的、包含着顺违哀乐之情的人生。一是“邪见所指为我”,它的特性包括恒常、坚住、不可变坏;这样的“我”,本质上是“自性之别名”。章太炎以为,常人所指的“我”,属于依他起自性,由随顺进化的立场是必须要承认的。从常人所指为“我”的角度,他赞赏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念,在井上哲次郎看来是利己主义的,需要批判。回过头来讲,井上哲次郎一旦将“我”视作“连结祖先和子孙无限的连锁的一部分”,“我”就具有了某种“恒常”性,也就成为章太炎所批评的、属于遍计所执自性的“邪见所指”之“我”。

井上哲次郎
关于“自我”产生的原因,章太炎解释说,“自阿赖耶识建立以后,乃知我相所依,即此根本藏识。此识含藏万有,一切见相,皆属此识枝条,而未尝自指为我。于是与此阿赖耶识展转为缘者,名为意根,亦名为末耶〔那〕识,念念执此阿赖耶识以为自我”。阿赖耶识又称“藏识”,属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识”之一种。阿赖耶识“无覆无记”。无记,即无善无恶;无覆,即没有染污。末那识则“有覆无记”。意识“始兼有善恶无记”。章太炎以为,“阿赖邪识亦有善恶种子伏藏其间,如清流水杂有鱼草等物”。末那执此阿赖邪识,以为自我,于是产生好善、好美、好真、好胜四种心。如果人只具备好善、好美、好真之心,那么世间一定有善无恶。然而,好胜心,特别是存在无目的的好胜心,使得世间的恶不可能消失,自利性与社会性会一直并存。所谓无目的的好胜心,又叫“我慢心”。它“执我而起”“纯是恶性”,它“不为追求五欲、财产、权位、名誉而起竞争”,如好弈棋与角力者。《俱分进化论》对“我慢心”的分析,在《读佛典杂记》中已露端倪,第三段谓“贡高傲物,视不己若者,不比方人,此我慢意识也”。“贡高”是佛教用语,意为高傲自大。章太炎认为,贡高和我慢意识,意味着与人争胜的好胜心。
至于《读佛典杂记》所述“我”与“我所”这一组概念,在《人无我论》中进行了相当透彻的解析。“我所”乃意指与“我”相对之外物的佛教语汇。《人无我论》如此界定“我”与“我所”:“自八识六根以至一毛一孔属于内界者,假说为我;自眷属衣食金钱田园以至一切可以摄取受用之物属于外界者,说为我所”。“我”与“我所”、内界与外界的关系是相对的,并非一成不变。“若由内界以望最内之界,则根识形体亦为我所,而惟阿赖耶识可称为我”。章太炎主张,人最爱的是“我”,而非“我所”。营生卒岁的普通人,往往会因摄取受用之物的损伤而感到悲痛,那是因为“彼以摄取受用之‘我所’,胶着于‘我’而不能舍。损及‘我所’,即无异损及于‘我’”。这就好像人用木头裹着身体,铁椎敲击木头,身体也会感到疼痛一样,“此所以宛转顾惜也”。寻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我”与“我所”混淆在一起。只有在自杀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自杀者为了缓解“我”之痛苦,宁愿牺牲根识形体之“我所”。这就说明自杀者所执之“我”,“亦即此阿赖耶识耳”。这就更证明了,“所谓我者,亦此幻形为我之阿赖耶识而已”。
井上哲次郎抨击利己论者以爱他心为利己心之变形。人爱其子,特别是母子之情,乃是他的重要依据。他引用了斯宾塞《伦理学原理》对“物理的利他心”(physical altruism)与“自发的利他心”(automatic altruism)的解说。动物的母体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是有部分消耗的,这是物理的利他行为。从物理的利他行为进化出自发的利他行为,在高级物种中又更进一步进化出有意识的利他行为。
章太炎反驳井上哲次郎“爱子者为社会性”的观点,采用的正是“我”与“我所”关系的逻辑。“名曰爱子,所爱乃我所遗耳”,爱子者所爱的,不过是“我所”。就好像“山鸡之爱其羽,麝父之惜其香,非即当身,但是我所”;山鸡之羽、麝父之香,乃是外在于更内界的“我”、属于形体之一部的“我所”。“我所”胶着于“我”而不能舍,因爱“我”而宛转顾惜爱“我所”。由此而言,爱子亦自利性也。《人无我论》继续思索此一问题。章太炎指出,兄弟之相爱的程度,一般而言不及父母爱其子的程度;而父亲对孩子的爱,又往往不及母亲。因为兄弟关系的成立不需要任何一方付出自己的劳力,而父母要建立与孩子的亲子关系是需要付出劳力的;相较而言,母亲“以种种痛苦之劳力”而得子,付出的劳力最多。“虽父母之爱其子也,亦其爱我之深,非专以子为我所而爱之也”。父母爱子的多少,体现的正是他们爱自己的深刻程度。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森内政昌对人性认知的暌离,必然导致双方在道德实践上的差异。
井上哲次郎和森内政昌都将控制自然欲求、实现至善的理想道德观念作为人生的目标。井上哲次郎更多地是在框定原则。他区分“知的道德”(Verstandesmoral)与“情的道德”(Gefühlsmoral),认为利他的功利主义虽然比利己主义高尚,但其实都属于知的道德,不能充实人的道德心。道德实践的方向是知情合一的真道德,孔子、佛陀、基督的道德皆主情,他们分别倡导的仁、慈悲、爱,都属理想的道德实践。森内政昌则偏向于探索实现理想中圆满的情之活动状态的具体方法。他强调要进行各种调和,尤其要以高尚的情感来抑制位阶更低的情感。儒教的“天命”说则是遭际天灾地异等外界苦痛的身心安顿之道。
章太炎则不然。在他看来,意欲的盲动,或者说意志的表彰,是一切烦恼产生的根源。“灭绝意志”、将意欲“息影于荫下”的厌世观才“稍稍得望涅槃之门”。这当然就是森内政昌所批判的叔本华的观念,即将“意志的否定”(Verneinung des Willens)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然而,对于革命者章太炎来说,参与抵抗和救世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不进行社会动员,以共同行动的方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他将厌世观分为两派。决然引去的出世派不是他的选择。他虽明白世界之沉浊,但愿意引导众生去寻清净殊胜之区,因此选择“以身入此世界,以为接引众生之用,此其志在厌世,而其作用则不必纯为厌世”。
章太炎伦理观的核心是由个人之感知扩展出来的个体自主性。革命的政治活动,使他面临着如何“从个体、自我转向以革命为目标的新的共同性”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要瓦解个体的自主性或泯灭个体的差异性,反而是要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个体性,所谓“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他将佛学与王学铸熔为一,提出“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已”。“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的个体形象,越来越接近尼采所谓的“超人”。而如此自尊自贵的个体,在章太炎看来,“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既没有政党中人的猥贱操行,又能够以自身的超人形象来激发其他怯懦、畏惧之辈自大自尊的气质。在章太炎眼中,愚民妇子因蒙昧寡知而维系着朴素的道德,“上流知学者”最需要破除死生利害之念,激发道德情感。革命的主体就是这些被激发起来的一个个自尊自贵的个体的联合体。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井上哲次郎在1900年出版的《哲学丛书》上大谈伦理学的明治政治和思想背景。中日甲午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文相西园寺公望1895年在演说中号召建立世界主义的道德,批判以偏僻见解说明忠孝。数年前建立的敕语体制有所动摇。加之,伴随着与帝国主义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1899年7月开始,内地杂居(即日本开放内地允许西洋人通商和居住)进入日程,文部省同年8月发布了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训令。自此,“已经不可能在道德论上排斥基督教”,并且“也不可能以排他的方法构筑统一的国民道德”。因应新的时代,《敕语衍义》的作者井上哲次郎需要构想新的国民道德论。他提出伦理的宗教观,试图使天皇制道德意识形态教育再次以普遍化的方式确立其权威性。井上哲次郎集中表述其伦理之宗教观的作品,即是他1899年的《关于宗教的将来之意见》。此文也掀开了明治日本第二次“教育与宗教”冲突论争的帷幕。
《关于宗教的将来之意见》指出,在几大宗教失势、教育与宗教分离、教育界德育不振的关头,要通过各宗教在根柢中的契合点——人天合一的伦理的实在,提出有效力的伦理主张以形成未来的变革的宗教。这篇文章所论析的伦理法和自然法的差异、“大我之声”与“小我之声”的关系、平等无差别的实在等,与后脚登场的1900年《哲学丛书》上《认识和实在的关系》《利己主义的道德之价值》的关键论域和主张是完全相同的。《关于宗教的将来之意见》乃是理解井上哲次郎彼时认识论与伦理观不可或缺的观念背景。
井上哲次郎指出,伦理学是“以人类的道德行为为对象的学科”,既关于知,也关于行。道德行为的要点在于“感受此心之内”,而不是功利主义地单受外界的利害之诱。感受“此内之所”,要感受的其实是萌发于我混沌世界、从超绝一切经验的平等无差别之实在界而来的“先天内容之声”。所谓“先天内容之声”,是先于“个个别别小我的意识”而存在的、融合一切的、无限的“大我之声”。“此大我之声,是独在之时于耳边嗫嚅之声,是夜半暗黑之中可听闻之声,是使人起耻辱或悔恨念想之声;逆此大我之声者,即小我之声,全凭个体之情欲或从私欲中来”。听从“大我之声”还是“小我之声”,在井上哲次郎看来,划定了善恶不两立的疆界。将来应取的宗教,就是通过所有宗教中“常住不灭的真理”——“先天内容之声”或曰“大我之声”建立起来的伦理的宗教。
1901年,佛教哲学家、教育家、哲学馆的创办人井上圆了发表《我所谓宗教》,驳斥《关于宗教的将来之意见》,构成第二次“教育与宗教”冲突论争中重量级的理论交锋。井上圆了虽然只比井上哲次郎小3岁,但井上哲次郎在1884年留学德国之前,曾在东京大学当老师,而井上圆了当时是他的学生。此后两位井上联络呼应颇为频密。《我所谓宗教》意味着两位井上明治后期在思想上的对立以及个人关系难以弥缝的裂痕。
站在为佛教谋取生存权利的立场,井上圆了指出,井上哲次郎主张将诸宗教一包在内的伦理新宗教,展现了进行意识形态统合的权力欲望,是在“暗杀宗教”。井上圆了以“无位无官”的平民身份批评“现时文科大学长”、未来的总长文相,已显其孤勇。井上圆了称,与井上哲次郎“先天内容之大声”相比,他发出的是“小我之声”“蚯蚓之声”“蚊虻之声”。此言不完全是戏谑,而是要站在民间黎庶角度说话。井上圆了指出,井上哲次郎攫取诸种宗教根柢的契合点来组织普遍的伦理的宗教,以所谓人类之一般者来同化佛教、基督教,“不过是学者的迷梦”。根据所有宗教皆排斥异端的惯习,井上哲次郎的作为属于另立宗派。他者也必将视井上哲次郎伦理的宗教为异端,人们将呼之为“巽轩教”“井哲宗”,其本山不称为“井上山巽轩寺”,则必称为“大我山内容寺”。井上圆了指出,以这种高度抽象化的方式制作的伦理之宗教,“全然无味无色”,不仅不能结合人心,就连引人关注都很困难。“除去一切历史的关系和诸宗教的特殊性,将它们根柢普遍的契合点集中起来所制造的宗教,恰如想要除去味噌汁、酱油汁、浓汤、牛奶的特殊性制作出综合的美味,可是却变成蒸馏之后无味无色的水”。
井上圆了的话,点出了他与井上哲次郎于哲学上根本的分歧,在如何理解平等。井上哲次郎是要泯灭世间一切的差别性使之归于那个大我的、绝对的实在,齐其不齐;而井上圆了则是要保护那些小我之声,尊重各种具备历史继承性的特殊样态。处理差别与平等的关系,恰是章太炎从1906年第三次流亡日本到1910年出版《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井上圆了珍视味噌汁、酱油汁、浓汤、牛奶各种特殊的味道,强调文化建设的方向不是将它们都蒸馏后变成无味无色的水,更能得到章太炎“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的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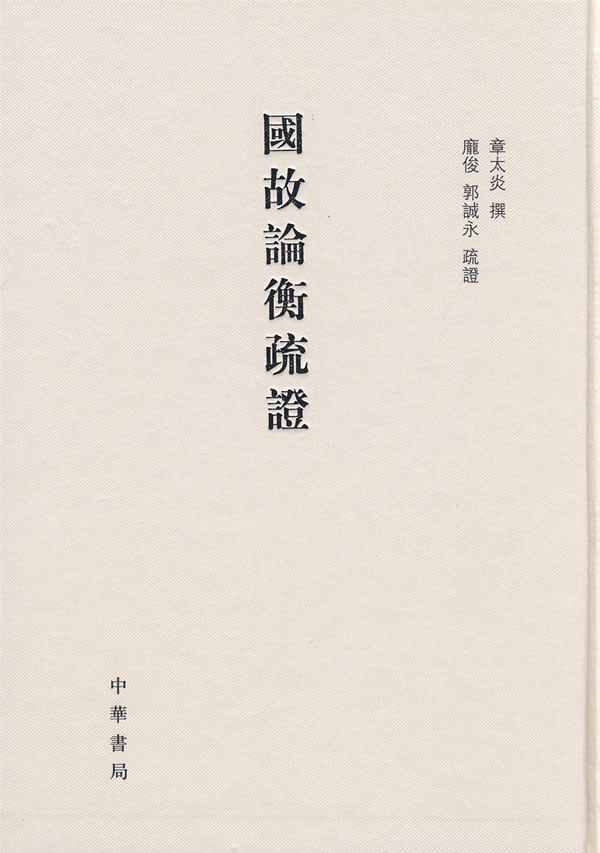
《国故论衡》书封
1903年章太炎好友宋恕在与南条文雄笔谈时,张口就问:“井上甫水先生之佛学何如?井上巽轩氏之学理如何?”井上甫水即井上圆了,井上巽轩乃井上哲次郎。这说明彼时章太炎周边的中国知识人对两位井上是熟悉的,并且往往把两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章太炎本人并非完全不了解井上哲次郎谈论伦理学的日本政治思想背景及论争,包括井上哲次郎和井上圆了的分歧。在《读佛典杂记》有限的篇幅中,章太炎坚持自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意味着认可所有人都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个体。尊重人间的有限和不完美,即是以差别性为立足点,从而拒绝将“大我之声”的伦理法置于压倒性的、绝对的位置上。这里其实已经隐约透露出他政治哲学的方向。换言之,追溯章太炎齐物哲学与明治思想的关系,除了姉崎正治谈论宗教“齐物论而贵贱泯”这一条线索外,还应该重视在批判井上哲次郎“大我之声”上,章太炎和井上圆了的相似性。毕竟,《四惑论》抨击黑格尔“以论理代实在”;而试图以普遍的抽象观念来囊括、取代无数实际存在的特殊性,明治日本“以论理代实在”观念论哲学的代表正是井上哲次郎。当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之《原道》上、中、下三篇中初步完整呈现他的齐物哲学时,他与两个井上之间的思想纠葛就呈现出来了。
去宥成别:章太炎齐物哲学与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的纠葛
章太炎的齐物哲学,将平等的基础建立在尊重世间万物之自然发展所带来的差别性之上。《国故论衡》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同《齐物论释》一样,都是他诠释该学说的代表作。
《原道》上篇通过《韩非子·解老》来解说老聃“非前识”“不上贤”之道。韩非子认为,“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老子反对的“前识”乃是没有对事物进行经验性的切实考察而凭一己之主观臆想来判断事物的性状纹理、进而试图指导行为的活动。“前识”约等于“私智”。章太炎指出,弃绝巫守、废除智术穿凿,使事物之纹理真正得到揭示和体现,才是“道艺之根,政令之原”。“私智不效则问人,问人不效则求图书,图书不效则以身按验”,则是废黜前识弊端的具体途径。因为总会有尚未到来之事、尚未亲睹之物,所以需要“绝圣去智”“不以小慧隐度”;而具体事物之情境又总有古今之差别、方国之差别、详略之差别,典籍能描述梗概但不足以单单取信,这就需要“绝学无忧”。“不上贤”亦即“不尚贤”,指选人用人不贵出身、不重流誉,而是根据其实际技能和功绩。“不尚贤”意味着“远前识而贵参验,执前之有以期后之效也”,将“非前识”的宗旨贯彻到选拔官员上。
章太炎分析了“非前识”在认识事物和政治实践上的表现后,总结了“非前识”的方法和效果,谓:“综是数者,其要在废私智、绝县,不身质疑事而因众以参伍。非出史官周于国闻者,谁与领此?然故去古之宥,成今之别,其名当,其辞辩,小家珍说无所容其迋,诸以伪抵谰者无所阅其奸欺。老聃之言,则可以保傅人天矣!”㛊,指揣量;县㛊,意为悬测揣量。“废私智、绝县㛊”属于“非前识”对个人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自然受到章太炎的青睐。而“去古之宥,成今之别”,简言之,去宥成别,亦可谓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有所蔽曰囿,或谓之宥,反宥则谓之别”。别,意指不同、差别。“反宥则谓之别”或谓“去宥成别”,表明尊重事物的差别,既是去除弊碍局限的手段,又是其归宿。这就进一步阐述了庄周“齐物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的哲学。
我们现在要暂时把时钟拨回到章太炎初识井上哲次郎的1899年。非前识、废私智、去宥成别,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关键性思维方式与井上哲次郎《读韩氏〈原道〉》的逻辑颇为相似。《读韩氏〈原道〉》是一篇全汉文的文章,原刊于1882年的《东洋学艺杂志》,属于井上哲次郎青年时代的作品。1899年《清议报》第17、18两期转载了井上哲次郎的两篇文章,《读韩氏〈原道〉》是其中一篇。该文可谓井上哲次郎在中文学术界最初的登场。彼时章太炎刚到日本东京,住在梁启超的寓所,与井上哲次郎颇多交往,此前此后都为《清议报》撰稿。该文第一时间就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
而如何回应《读韩氏〈原道〉》提出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章太炎心中。经过多年的理论准备与积累,他在《国故论衡》之《原道》三篇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建构了可与井上哲次郎相抗衡的齐物哲学。《原道》上篇与《读韩氏〈原道〉》观念的某些相似性,意味着青年井上哲次郎在章太炎齐物哲学中的“闪现”。这种“闪现”无论发生在章太炎清晰的理性、模糊的意识或者隐藏的潜意识之哪一个层面,从处理的对象和逻辑结构来说,《读韩氏〈原道〉》及此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发展,都足以成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对照物。
韩愈认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井上哲次郎则认为,从行动的动机(是否有利己之心)和效果(吉或凶)之不同组合来看,仁与义、道与德都既可为定名又可为虚位。在初露逻辑缜密的锋芒后,井上哲次郎进入正题。韩愈批评老子“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原因是“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井上哲次郎指出,老子所谓的道德并未去仁义,老子不屑言仁义,因“仁义于大道,犹涓滴于大海也”。井上哲次郎的重点还不在替老子辩护,而是要揭露韩愈思维方式的偏狭与独断。
井上哲次郎直斥韩愈“信己排人”,以自己有限的见解作为全天下都应该遵循的“公言”。“古今如此久矣,东西如此广矣”,漫长的宇宙时间、开阔的地球空间,那些未闻见者却被韩愈视为“私言”,实在是偏颇之极。韩愈所谓“公言”,即便能在“一国”的范围内适用,也并不能囊括全球的普遍情况,也属于某种“私言”。井上哲次郎抵制此类偏于一隅、僵化不前却妄图囊括所有的思想言论,与章太炎“非前识”“废私智”“绝县”的逻辑结构是相似的。章太炎《原道》上篇指出“古今异、方国异、详略异,则方策不独任也”,批判“事有未来,物有未睹”却以“小慧隐度”等,几乎是井上哲次郎观点的另一种说法。
井上哲次郎指出,不能依据思想言论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还是出于少数人之口就确定该思想言论的是非正邪。“盖豪杰常少,而凡庸常多;故豪杰之言,私言也;凡庸之言,公言也”。往往最开始是极个别的少数人冒着生命危险说出真理,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夫真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则真理亦不出也”。针对有人提出,大多数人说的话之可信乃是常态,其不可信则属非常态,“以非常害常,孰若以常害非常”;井上哲次郎又表示,“以常害非常,孰若以常不害非常”。《读韩氏〈原道〉》作于1882年,体现了青年时代的井上哲次郎希望通过批驳韩愈来打掉思想权威和惯习,使日本更容易接受西洋近代化新知。井上哲次郎从“公言”与“私言”的辨析切入,一路剖析凡庸之众与豪杰之独、常态不能伤害非常态,渐次深入到保护差别性、个体性的论域。可以说,《读韩氏〈原道〉》和章太炎《原道》上篇反对“因众以参伍”、倡导“去宥成别”的逻辑是相通的。
章太炎1910年创作的《原道》,闪现着他1899年初识井上哲次郎时所读《读韩氏〈原道〉》的逻辑痕迹。初识之后,章太炎和井上哲次郎的思想伴随着各自国族社会政治的演变而各自演进。
井上哲次郎从1891年编撰《敕语衍义》到1912年出版《国民道德概论》,虽然说都是围绕《教育敕语》的精神在经营国民道德论,但其思想仍旧有一个形成、发展和不断再建构的过程。比如,《敕语衍义》主张,忠孝不仅是日本的传统道德,也是东西洋的普遍道德。而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愈发高涨,井上哲次郎在1899年的《增订敕语衍义》、1906年的《日本德教的位置》等后续作品中越来越强调日本国体和道德的独特性。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节点。井上哲次郎1905年推出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明确以“对国体、帝室尊崇的有无作为思想评价的基准”。这是相比于“日本儒学三部曲”前两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的“异色”所在。总的来说,井上哲次郎以“大我之声”压制“小我之声”的伦理诉求越来越强烈,他的“现象即实在论”在不断地贴合国体论对国民道德统合程度愈发迫切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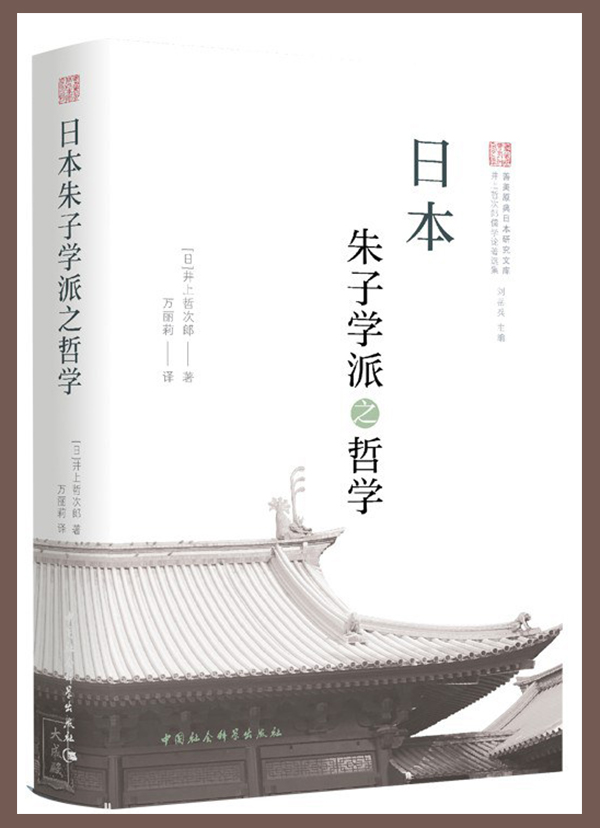
《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书封
1899年后的章太炎逐渐由主张革政而转向革命,立志为一个个具体的下民争取生存空间与权利;“世之有人也,固先于国”,他强调要以尊重人的差别性为前提来建立新国。在长期关注以井上哲次郎为中心的东京哲学圈后,面对以文明论为旗号的殖民主义、革命同志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日本升腾的国家主义,也作为对井上哲次郎哲学的一次总回应,章太炎1910年《原道》篇完整表述“齐物哲学”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原道》下篇再引《韩非子·解老》,谓:“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道者,万物之所以成。……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据《广雅·释诂》,“稽,合也,当也”。所谓道,乃是万物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也是万理相当、相合之所在。理,指的是形成各种具体事物的纹理,或者说自身的条理与规则。事物各自具备自身的纹理而不会互相逼迫、侵扰。道可以相合万物之理,就意味着它必须要变化,而不能定于一执。变化本身令生生死死的自然现象天然生成、人间的智慧错错落落、人事的兴衰成败各有其时。
引用《解老》后,章太炎释曰,“此其言道,犹浮屠之言‘如’耶”,“有差别此谓理,无差别此谓道,死生成败皆道也;虽得之犹无所得;《齐物》之论由此作矣”。《国故论衡》初刊本上述文段以佛之“如”来诠释“道”;在后来的先校本中,章太炎用墨笔增补的一段内容,以佛释庄。他用浮屠之“法无我”来比拟“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道枢”,以浮屠之“补特伽罗无我”(即“人无我”)来归纳“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百骸九窍晐而存,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同时,章太炎将“理”等同于“有差别”,“道”等同于“无差别”;又明确说“有畛即有差别,未始有封即无差别,有差别起于无差别,故万物一如也”。这里“有差别”与“无差别”(平等)间的思辨其实已经进入了明治日本“现象即实在论”的核心论域。
井上圆了和井上哲次郎是明治时期“现象即实在论”的代表。井上圆了在早年的作品《哲学一夕话》(1886年)中就说“无差别心通过差别心而知、差别心通过无差别心而立”。而他在最体系化展开其“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新案》(1909年)中,区分理性之哲学立场的“表观”与信仰之宗教立场的“里观”——“表观”乃是“从物心相对的此岸”观察“绝对一如的彼岸”,“里观”则是“从绝对一如的彼岸”观察“物心相对的此岸”。章太炎通过《哲学丛书》所载《认识和实在的关系》已经了解过井上哲次郎“一如的实在(Wesen)”,“失去主观、客观之差别者就成为实在”“平等无差别的实在”、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明晰此实在观念等诸多论述。这就意味着,章太炎的齐物哲学有与两个井上思想相纠葛的层次。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政治哲学的着眼点和方向几乎是对立的。井上哲次郎由差别性朝上、走向无差别性,在信仰超出于个体之外的绝对实在之物的过程中安顿身心;政治意识表现为越发要求所有的差别性元素都听从“大我之声”的召唤,贴合到作为绝对实在者的天皇制国家体制上。章太炎则指出,无差别的“道”要主动向下,不断变化去相合有差别的万物之“理”。他反复说,道与物相从不违故无伤,即“下连犿无伤”,如此方足以经国。“官天下”的途径在“不慕往古,不师异域,清问下民以制其中”。听从下民之吁求是为政之道,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齐物论释》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两相对比中,“下士之鄙执”暗指的正是如井上哲次郎者。
章太炎和井上圆了,一个要清问下民、不齐而齐,一个要发出“小我之声”“蚯蚓之声”“蚊虻之声”,反对将人间各种美味蒸馏为无味无色的水。他们的观念亲近和谐,呈现相互支撑的态势。井上圆了和井上哲次郎同为明治“现象与实在论”的阐释者,彼此相知亦最深;井上圆了对井上哲次郎的批评,其实从侧面进一步打开了章太炎齐物哲学的诠释空间。
井上哲次郎伦理的宗教论试图将人格的实在从宗教组织中全然除去。井上圆了则指出,宗教以应用为本,需要与现世人间实实在在的个体、形形色色的人生发生关系,这和以理论为终极追求的哲学是不同的。哲学足以证明“绝对平等、无限不可思议的实在”。宗教却需要使这一实在和人接近,从而使人和此体融合。井上圆了说:“人是有限中的有限、相对中的相对、差别中的差别;然而此体却是无限、绝对和平等。要使如此显著的大相径庭者一致冥合,必然要求无限的有限化。”对于宗教来说,将平等不可思议的绝对有限化,其表现就是人间化人格化的实在。佛教中人格化的实在——三身(法身、报身、应身)乃佛教之神髓和命脉,断不能舍弃。井上圆了虽然是从宗教出发来展开论述,但政治和宗教一样,都以实践和应用为本,也都必然要求无限的、平等的“道”向下寻求,针对各种有限的、差别的人生与情境,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也就是章太炎所强调的“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清问下民以制其中,要从“相地以衰征,因俗以定契”开始。
此外,井上圆了还揭示,井上哲次郎所谓的“大我之声”并非超绝一切经验、平等无差别的,而是可知的、有人格性的。井上圆了讽刺道,“我为巽轩博士允许大我之声,而不许大我之形色感到奇怪”;由于看不见“形色”,所以其理想是“盲目的”,“可名之曰大我盲或者色盲的理想”。兼具声、形、色的“大我”,必然也就拥有人格性的欲望和利益诉求,既不超绝也不平等。井上哲次郎的“大我之声”指向的正是天皇制国家体制对国民道德的规训。它携政权之力试图“暗杀”所有既有宗教,压制所有“小我之声”,必定也是专制的。
结合井上圆了对井上哲次郎的批评,再来看《原道》下篇对韩非的批评,章太炎的针对性豁然开朗。“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慈惠廉爱和文学,这些韩非《五蠹》篇看来无用的东西,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仅仅是能吃喝、生育的禽兽之原因所在。用井上圆了的话来说,人作为有限的、不完美的个体只有通过慈惠廉爱的授受和文学的欣赏表达——这些无限的道在人间具体化的形式或中介,才能凭借真正的道德感和智慧辩察的情性,体会到做人的意义所在。章太炎认为韩非子的统治理念,不是把民众当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危险狡诈的虎狼和有工具性价值的牛马来管制和利用。
《原道》指出,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抽象的国家之“虚名”来奴役人民,“世之有人也,固先于国,且建国以为人乎,将人者为国之虚名役也”?章太炎进而批评韩非“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政之弊,以众暴寡,诛岩穴之士。法之弊,以愚割智”。章太炎表面上抨击的,当然是韩非的法家统治思想。然而,他所勾勒的国家统治的形状,无比接近他所流亡生活其间的、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明治日本。他所针对的理论对象,当然包括天皇制国家体制的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言人——井上哲次郎。
结语:围绕“现象即实在论”及其政治实践的对峙
日俄战争后以国定修身教科书为基础,日本的国民道德教育进一步被统合进天皇制的国家体制。在这一大背景下,1912年出版的《国民道德概论》总结了井上哲次郎整个明治时期围绕《教育敕语》所展开的国民道德教育论述。其显著特征在于,明确日本家族制度的特色是万世一系的皇统、以天皇为国家全体之家长的“总合家族制度”。井上哲次郎指出,家族制度有两种,中日两国皆具备“个别家族制度”,唯有日本才有“总合家族制度”。以总合家族制度为基础,方能理解日本的“忠孝一本”。中国有“禅让放伐、易世革命”,相比于忠更重孝;日本则是天皇万世一系,君臣间有父子之情,相比于孝更重忠。此外,为回应20世纪初期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国民道德概论》专辟两章分析家族制度和它们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家族体制,自然不能容忍以平等观念为基底的社会主义。至于个人主义,井上哲次郎认为它是西洋近世文明的特色;个人主义养成自主独立精神之善的方面,在东洋古来的道德中也是具备的。他批评个人主义易流于利己主义,极端者走向无政府主义;“完全实行个人主义的话,国家是不能成立的”。他主张在家族制度的组织内,容纳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这些主张和他哲学观念中关于“大我”与“小我”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总结自身的政治哲学,章太炎《原道》下篇提出了与井上哲次郎国家统制的国民道德论方向截然相反的主张。章太炎区分“政”与“俗”两个不同的领域,“政之所行与俗之所贵,道固相乏,所赏者当在彼,所贵者当在此”。禁止奸害的法律、制定并落实法制的治理——“政”对人类社会来说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非政之所与也”,而是属于“俗”的范围。庄周齐物哲学的要义,在于“分异政俗、无令干位”,“推万类之异情,以为无正味、正色,以其相伐,使并行而不害”。明治中后期日本所建立的国家方向,是以总合家族制度和个别家族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整合进拟血缘制的天皇制国家体制之中;并且,以“忠孝一本”作为伦理原则,要求所有的“小我”都服从天皇制国家这个“大我”的命令。日本的社会空气令章太炎有窒息之感。“采药以为食,凿山以为宫,身无室家农圃之役,升斗之税,不上于王府,虽不臣天子、不耦群众,非法之所禁”。章太炎极力为那些游离在家族和国家体制之外的个人声索生存的空间。毕竟,清末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被压迫的民族对内对外争取自主自由的权利,更是捍卫作为有限的、不完美的个体之芸芸众生的生存权利和尊严。
总体而言,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贯穿在1905年章太炎阅读《哲学丛书》到1910年出版《国故论衡》的整段历史进程里。而章太炎所“会晤”的井上哲次郎哲学,则既有其青年时期冲决罗网之作《读韩氏〈原道〉》,又有最成熟表达其“现象即实在论”的《认识和实在的关系》,还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第二次“教育和宗教”冲突论争《关于宗教的将来之意见》以降,他愈益贴合天皇制国家体制的诸多国民道德论述。章太炎和井上哲次郎各自思想的轨迹,特别是他们围绕“现象即实在论”在认识论、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上的暌离,大体反映出走向革命的清末中国与走向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明治日本两条道路的理论差异。
1911年,章太炎离开日本,此后余生未再赴东瀛。然而,他其实仍关注日本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保持着《原道》下篇的立场。1930年,章太炎读了他在台湾结识的故人白井新太郎之《社会极致论》。该书关注王道和世界统一。其所谓治理社会全体之“王道”,乃是“以政为教、以教成政,政教一致”,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尽其职业,令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五伦各尽其交际。而在人道中,“君道”起统帅作用。换言之,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在君道的统帅下,安于职业身份的规定和五伦的差序位置,尽好自己的职责本分。这俨然是《教育敕语》对国民道德要求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章太炎指出,这样的观念不合时宜,“其说自身及家施于天下,盖儒家之雅论,而为今世所遗弃者也”,“君道亦仅行于日本、英吉利数国,其余大抵变矣”。章太炎认为,君臣之道未必非要拥有实际的君主和臣子,它可以理解为职业化社会对上下级之间的伦理要求。章太炎还继续为“自食其力”“外于朝廷”的隐逸者争取生存空间。这些主张,当然是对“万世一系”天皇制、总合家族制度的极大“冒犯”。章太炎借此实现了与井上哲次郎的隔空对话。
井上哲次郎在《国民道德概论》出版后的岁月里,思想愈发与臣民克忠克孝、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伦理要求浑然一体。他呼吁“必须由皇道来统率所有宗教”,“日本的诸宗教必须为日本而存在,不允许危害日本宗教的存在”。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焦灼时期、《教育敕语》颁布半个世纪之后,井上哲次郎再撰《释明教育敕语衍义》。除了说明颁发《教育敕语》的原委、全文影印《敕语衍义》外,核心的部分是“释明”,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为《教育敕语》“护教与辩诬”,“并赋予其新的历史意义”。《释明教育敕语衍义》谈到《教育敕语》与理性主义的关系时,仍旧主张人类通过理性来抑制自然欲,朝向真善美的方向改善自己。尽管有个别名词的扩充,如将与“自然法”相对的“伦理法”落实为“发展欲”或“完成欲”“完己欲”,其核心论点与1900年《利己主义的道德之价值》是一脉相承的。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则变本加厉,谓,“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谬误的见解”,“根本上,所谓个人者是不存在的”。井上哲次郎敦促个体“互相帮助、构成社会、建立国家,朝向人类最后的理想发展”。井上哲次郎批评崇尚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充斥私欲、腐败堕落,终将动摇、崩溃。这里并非单纯的学理讨论,而是将矛头直指彼时与日本作战的英美两国。在他看来,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乃是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成为“私利私欲的修罗场”;日本拥有与英美各国迥异的、以“清明心”作为道德动机的神道;战争乃是日本发挥神道的过程,日本参与的战争是人类的幸事;“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都是神道不可言说的神秘权威的体现。井上哲次郎将理想寄寓于超出个体之外的绝对实在之物的认识论和伦理观,至此已沦为统合国民思想、对内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欺骗的侵略战争工具。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为《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及暌离》,作者彭春凌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