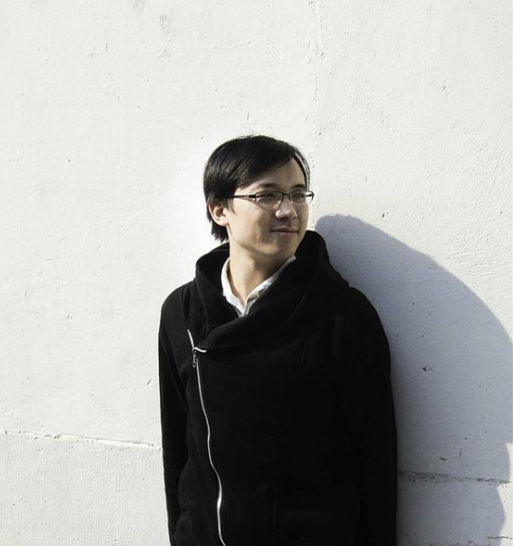- 12
- +1356
隔着除夕夜的视频,大舅最后摸了一次母亲的脸丨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邓安庆
编辑 | 林柳逸

睡意朦胧中忽然听到楼下的开门声,随即是电动三轮车碾在沙子上的声音。我知道母亲要往大舅家里去帮忙了。昨天晚上她上楼来跟我说:“你七点过去就好,多睡一会儿。”再一次睁开眼,是哥哥叫醒我的。他让我赶紧洗漱,他在楼下车里等我。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随即被冰冷的空气包裹住。一边哆哆嗦嗦换衣服,一边找裤子,这才发现昨晚脱下的薄裤子变成了厚裤子,应该是母亲夜里悄悄上来换的。母亲是对的,出门时,冷得直哈白气,稻场前面的菜地下了白白的一层霜。上了哥哥的车后,我问:“爸不去吗?”哥哥摇头,“他走不动路,别折腾了。”

大年初一那天晚上,母亲来房间找我聊天。说父亲的病情,说去年的收成,说我工作的事情,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到走时,母亲的手机忽然响起。一接电话,是大舅妈打来的。母亲手机的声音很大,我听到大舅妈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妹哎,你哥今天晚上七点走了。”母亲惊讶地问:“么回事?昨天我们还说话的。”母亲说的是除夕夜我们拨打视频过去,还跟大舅通了话。那时大舅被他大儿子也就是我松哥接回了家,躺在沙发上,借助制氧机吸着氧气,跟家人们在看春晚。母亲叫了他一声大哥,他已经无法回话了,因为没有牙齿两颊松垂,眼睛盯着视频对面的母亲,抬起手摸了一下视频,像是要抚摸一下我母亲的脸。我们不会想到,那是母亲与他的最后一面。
大舅妈继续跟母亲交代一些事情。因为大舅去世,肯定要回到老家安葬,所以需要母亲这边先去大舅家收拾一下。母亲连连说好。我坐过去,搂着母亲。挂了电话后,母亲没有痛哭,相反看起来很平静。可能也是因为大舅生病多年,母亲早就有心理准备,也可能是她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母亲让我搂着,没有动,手里捏着手机,半晌没有言语。我想倒杯水给她,她忽然站起身来,“你先休息。我下去了。”我问母亲,“你没事吧?”母亲说没事,出门下了楼。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不放心,下到一楼,母亲正在与人通话,听内容是联系刻墓碑的人,问他能多长时间把墓碑刻好;又听到她联系事关葬礼要准备的其他事宜。
母亲的过于平静,让我反而有点担心。母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些年来随着子女定居的城市不同,他们也住在了不同的城市。平日很难见到面,也就每回过年通通电话拜个年。大舅离去,在老家的母亲,在深圳的二舅,在江苏的小舅,在北京的姨娘,都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不知道大舅妈有没有通知他们,只知道大舅大年初二在广州火化后,他的家人会连夜开车赶回老家办葬礼。而唯一一个在老家的母亲,开始为葬礼做先期的准备。乡村的葬礼极复杂,各种仪式都不敢出纰漏,该准备的都要准备起来。
联络完相关的人后,母亲站在过道上发愣。我过去叫了一声她,她才回过神来。我又一次抱抱她,“妈,你要是难过,就不要忍着。”母亲叹了一口气,“不能想。”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不能想。”她转身往堂屋走,“大哥是个极好的人,他一直对我都非常好……”母亲说的,我都明白。除夕视频里大舅脸是浮肿的,这跟我记忆中那个干瘦的大舅很不一样。大舅个子不高,背略微弓起,双手喜欢背在后面,因为长期在外奔波,皮肤黑黑。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严肃的人,脸上总是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但跟他接触久了,就知道他是一个极和善的人。我总记得母亲带我去他家做客,他低身冲我一笑,“又长高了。”接着,微笑地看我母亲,“大妹哎,你又瘦咯。”那个时候,父母亲为了供我和我哥读书,跑到江西种地,过得极苦。母亲还有胆结石,时常在床上疼得直呻吟。这些大舅都知道,时不时会悄悄帮衬我家。这些好,母亲都记得。
其实,大舅家里也不宽裕,他要养三个孩子。一开始,大舅跟母亲一样,都在种地。但他不甘于此,总想去“折腾”。在我这些年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创业者”。小时候,我还记得在他家二楼,养了很多兔子,肥肥壮壮,一个个蹲在那里啃菜叶子,这些可爱的小生命是大舅养来去卖的;又有一段时间,大舅忙着做谷酒,然后到四乡八村去卖;还有段时间,他跟人合开榨油厂,给我们这片村子提供菜籽油……种地很难养活一家人,我家就是例证,而大舅不甘于困在田地上,东奔西闯,去寻觅更好的挣钱方式。我总记得他赶路的模样,是的,不是在走,而是在赶。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嗯”一声,又急急地奔到前头。毕竟,好多事情都需要他去做。他不能停下来。
可是,大舅也并非只晓得忙活而不懂生活的人。在他家的侧边,有一个花坛,种着一株木芙蓉,秋天来时,朵朵红云,点缀枝头,煞是好看。母亲带我来做客时,特别喜欢站在枝头下看那阳光洒在花瓣上,啧啧赞叹。大舅见母亲喜欢,特别给了母亲几枝拿回家。而在原来堆放杂物的侧院,大舅还搭了葡萄架,到了盛夏季节,葡萄叶下阴凉如水,进去后热汗收干,听得外面蝉鸣阵阵,大舅在前面灶屋忙活,见我在,笑笑便说:“要是热,屋里有风扇。”回到屋里,我表哥、表姐在做作业。他们一直成绩很好,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我羡慕大舅能买书给他们看,尤其是那一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表哥一直很珍惜,不肯借给我看。大舅对他们,是不遗余力地疼爱。只要他们愿意读下去,他就一直供下去。这一点,跟我母亲的态度一样。

大舅因为是家中老大,很多事情都是他在默默承担。他不是一个爱表达的人,乡间多人事纠葛,创业也有诸多烦难,他都一并接受,不去辩解,只是埋头做事。二十多年前,外婆外公两年之内接连去世,大舅身为长子,操办葬礼,也是一件件去做好,并不多言。我只记得那时候他没有跟母亲那样哭得不能自已,反而是冷静地交代这个吩咐那个,事情有条不紊地推进下去。他会偷偷地哭泣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已经走在了他妹妹、弟弟的前面,成了母亲需要为之忙碌的人了。再次去看母亲时,她又一次打起了电话,还是关于葬礼的事情。我想有这些复杂的葬礼,某种程度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至少对于活着的亲人们来说是必要的。在准备葬礼的忙碌中,人陷在所有琐细的事情上,不必被悲伤全部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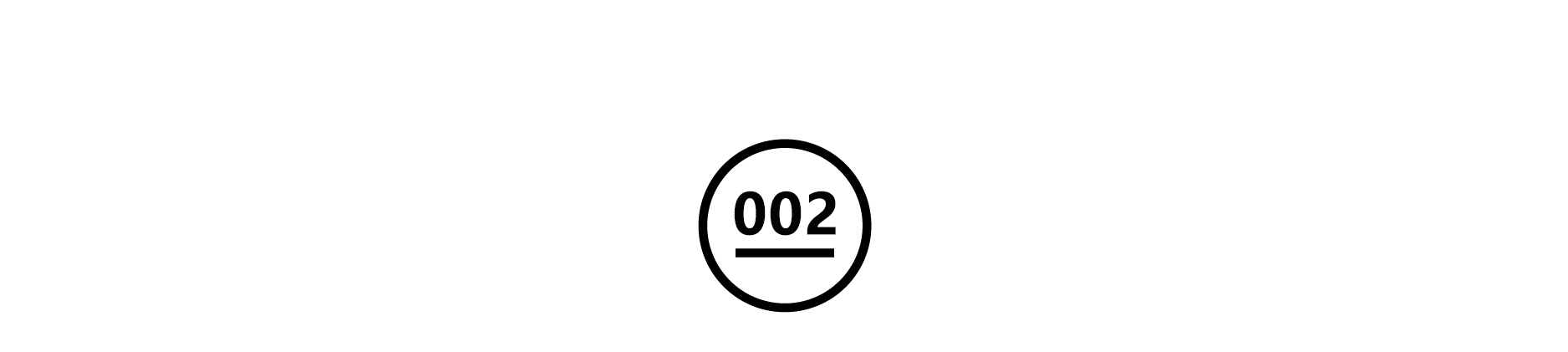
大年初二,大舅火化了。他一家人带着他的骨灰往老家赶。母亲白天去大舅家收拾了一下午。晚上忙完事下楼来,去前厢房,父亲躺在床上看电视,我问:“我妈呢?”他摇头说:“我不晓得。”随即往后厢房去,房间里是黑的,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母亲坐在床上靠着墙正在哭。我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母亲声音小小地说:“我没有哥哥了……”话还没说完,又一次哽咽。过一会儿,父亲过来,看了一眼母亲,说:“明天大哥回来,你不要哭。”我问为什么,父亲回:“你不晓得你妈哭起来几怕人。以前你外婆外公死,她每次哭起来人都昏了过去,手脚都勾了起来。”父亲说的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母亲生气地大声说:“要你管!”父亲退后一步,“你掉眼泪可以,不要那么哭起来。”随后,又回到了前厢房。
大舅家不远,不一会儿车子就开到了。堂屋正中间的桌子上放着大舅的骨灰盒和遗像。小舅、姨妈连夜从各自的城市赶了回来,表姐表弟们也纷纷到了。很多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他们见到我,也要稍微想想,才知道是谁。大舅妈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她一会儿搬个桌子,一会儿又嘱咐儿子去准备什么东西,一会儿又去厨房下面,但一个事情与下一个事情之间没有连系,只有定不下心来的忙乱。她没有往桌子上看一眼,就像是不存在,眼睛却是红肿着。大舅的儿女们也是,这里忙一下,那里忙一下,却都看不到头绪,唯有人来磕头,他们的眼睛突然湿润起来,仿佛是停的那一刹那间就会被悲伤紧紧地揪住。
亲戚们送来的花圈在屋前摆满了,乐队的洋鼓洋号也都来了,做法事的道士开始念经了,大家跪在堂屋,母亲跪在我前面,她的哭声和着道士的念经声,像是缠绕在一起的绳子,把葬礼的哀恸气氛提了起来。阳光照了进来,却一点暖意也没有。冰冷的水泥地,鞭炮的碎屑随风飘起。一个曾经在这个屋子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再也不能从这个厢房走到那个厢房,再也不能在楼上养兔子、在边房做豆腐、在屋后种菜,再也不能叫一声“大妹”……他永永远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忽然想起松哥跟我们说,“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住院,连东西都吃不了,药也不愿意吃了。他总是问大年初一还有几天,我知道他是要在家里过一个年。终于撑到了大年三十,跟家人过了一个除夕。大年初一就陷入了昏迷,直到晚上七点半过世……他总是为了我们着想。大年初一走,我们也正好都有假,给后面的葬礼、头七都预留好了时间。一点不想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到死都如此。”亲戚们听了都连连点头,“他这一生都是这样的人,从来都不想麻烦别人。”姨妈接着说:“每次他从广州回来,就到我屋转转,留他吃饭也不吃,也不说什么。就来看看我这个小妹过得如何。晓得我还好,待一会儿就走咯……”
开始出殡了,我被安排拿着花圈走在了前头,送葬的人跟在后面,远远地还能听到母亲的哭声。回头望去,她跟她的妹妹走在一起,虽然夹杂在众人之中,看起来还是那么孤单。冷风吹来,花圈鼓起,我艰难地把它靠在身上才不至于被吹倒。穿过国道时,迎面来了一溜装扮一新的婚车。它们停下来,让我们先过去。新的一代人结婚,老的一代人离去。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要走自己的路。

等众人挖坟坑时,我抬眼看到母亲往坟地边上走,便跟了过去。等我赶上时,母亲已经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前,跪了下来,“父哎,娘哎,大哥已经过去了。你们在那边团聚了。”我也跟着磕头,然后扶着母亲起身。她走到墓碑前,摸摸碑头,又摸摸碑身,没有说话。我陪在旁边,也不说话。那边,坟坑挖好后,立好石板,松哥跪着把大舅的骨灰盒放了进去。道士念完经后,开始填土。一捧土一捧土下去。我没有大舅了。母亲没有哥哥了。
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冬日的麦田空旷无人,通往村庄的路上拜年的车子来来去去。此一处,彼一处,鞭炮的声音还在延续着过年的喜庆。母亲没有跟着回来,她还想在墓地待一会儿。我跟松哥他们慢慢往垸里走。松哥问我这些年的生活,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走到一处,我指着脚下的路:“我一直记得二十多年前,就是在那条路上,你和我大舅在前面走,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跟在你们后面。大舅问你想找什么样的女孩,你说了你的想法……”跟在我身后的松哥爱人插问道:“他怎么说的?”我笑笑回:“忘了。”我看看她,又看看已经五十多岁的松哥,再看看他那上大学的孩子,眼睛一酸,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关税大棒挥向汽车
- 何立峰与美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
- 举报“台独”邮箱收件323封

- 港股医疗板块持续走高,信达生物涨幅扩大至18%
- 我国首个海洋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完工

- 网络流行词,企业规定员工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下班,不能随意加班
- 我国领土最南端位于南沙群岛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