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此城市|《狂飙》里的城中村往事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狂飙》,以及同样以广州冼村为题材的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都讲述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建浪潮中,财富、土地、权力以及人性的深度纠缠。在中国城市化的深化与加速进程中,“城中村”曾是社会焦点,《狂飙》让许多人重新回想起这段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北京、广州、深圳的城中村,为何区别如此之大?城中村对于理解城市的本质有何帮助?城中村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面临何种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长期关注城市转型、空间政治、城市政治经济。他认为,“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改写我们周遭的空间和我们自己。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在这个过程里被消灭或生成,不同的人群按照各式各样的原则重新排序,进而被整合为特定城市意象之中的元素。”
在一些抽象的“原则”与“蓝图”中,一些城中村与居住其中之人连同他们的记忆成为了“牺牲品”,但这并非城中村的唯一出路。“城市只是纯形式,它变成什么样应当由其中的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去决定”。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联合《信睿周报》旗下播客“信睿电台”,与赵益民共同“走进”城中村,回望土地、权力与记忆如何塑造一座城市。
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

——本期主播:
郝汉、周发发


——收听时间线:
03:40 “城中村”的变迁,是城市一步步“变”出来的过程
06:08 为什么有些大城市的城中村在市中心,有些则在城郊?
14: 25 北京城中村初体验
24:40 城中村的高密度与“脏乱差”,是社会问题的表征,而不是原罪
33:50 上海这座城市为什么较少与“城中村”话题关联
41:40 当形式凌驾于内容:建筑师柯布西耶如何杀死一座城市
50:02 相比拆迁户,借助城中村在大城市落脚的流动人口如何主张居住的权利
54:35 市中心区域的城中村、城市资本积累导向的“士绅化”与被迫离开人们

2020年8月2日,广州市著名城中村——员村街景。人民视觉 资料图
——节目内容摘选
——城中村里的城市生长进程
如此城市: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似乎有所分别。在深圳和广州,城中村并不一定在城市边缘,它可能离市中心是相对近的。但是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城中村可能意味着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在中国谈城中村,它的意义在不同城市不太一样,相应地,关于城中村的看法和治理思路也不尽相同。
赵益民:这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分,其实可以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中村的位置,只是它“此时此刻”的位置。广州之所以在市中心旁边就有城中村,是因为它的市中心只是这二三十年才“长”出来的。广州以前的市中心并不在天河,而在越秀和荔湾。
为什么在珠三角的市中心附近有城中村?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更好地迎接外资、建工业厂房等,当地政府下了大力气去征收原先城市周边的农村农地,但是在征收农地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成本核算问题,就是征收耕地与征收宅基地成本差价太大。
为了节约成本,当时广州、深圳的市政府在征地时大量征收了农民的耕地,而保留下来了宅基地。当这些村落周边的耕地都已经建上厂房,后来逐渐变成新城,新城又变成新的市中心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城市慢慢“走向了”这些村庄,而不是村庄变成城市。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在非常高的现代化建筑背后,有很多密集的“握手楼”。而这样的空间景观在中国北方城市是很难见到的,比如北京,我们并没有那么快速地去推进城市化,一方面没有这个速度,另一方面也没有类似的政策。北京二环里看不到像珠三角城市那样的城中村,而更多的城中村在从前的三四环,现在的五六环的边缘,叫城乡结合部。
可以说,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像广州、深圳那样高密度的城中村。其中包括了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珠三角的实际情况——相对比较完整、稳固的村集体,由宗族主导的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以及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地位(它的存在承载成千上万流动人口的住宿需求,而政府公共服务并没有充分解决这一庞大的需求)。
因此,在广州、深圳,城中村还能以相对低的成本,在基础设施相对缺失的情况下,为城市化及其人口的涌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在住房和社会网络支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世界工厂”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城中村”作为前提条件的,这是珠三角地区的经验。
——城中村改造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
如此城市:北京和广州城中村的不同形态还与哪些因素有关?
赵益民:不光跟产业结构,而且跟各自的治理模式也有紧密的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广州的城中村逐步走向了“公司化”,每一个行政村相当于一个经济联社,村民是联社的股东。加上珠三角的很多村子是以宗族势力作为基础的,在历史上就形成聚落。因此,在一个村子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大的姓氏来主导这些村集体和经济联社。

《狂飙》剧照
正如我们在电视剧《狂飙》里看到的,当市政府开始改造村子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去跟这些宗族势力主导的村集体谈判,加上整个社会比较市场化的倾向,广州的城中村的改造需要给到村委会一定的返利或者返还土地。
与此不同的是在北方,比如北京,自上而下的城市治理能力比广州强势,城乡结合部的拆迁雷厉风行地推进,村民当然是“被动的受益者”,这些村民每家每户能获得的补偿款在那个年代是很高的,能够获得的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也不小。但他们并没有像广州那样,以一个经济联社的身份去集体协商获得比如10%的土地返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被拆迁的村民,反而是原子化地、被动来到城市生活里的人。而广州或者深圳的村民们在拆迁后也并不是原子化的存在,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体。
当我们讨论城中村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城中村的改造或者拆迁影响的是两大类人。不仅是本地居民,更多影响的其实是流动人口。不管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流动人口在面对城中村改造、拆迁的时候,都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不可能拿到任何意义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不被视作本地人。城中村的村民和流动人口分化成了两个人群,一个是收租的,一个是交租的,是社会地位和财富上差异巨大的两类人。
因此,城中村的空间变迁也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剧照
——城中村,不只有一个可能的未来
如此城市:很多城市规划和建设者对“城中村”的态度,都是相对负面的,认为其是一种现代化未完成的状态,并且有将其现代化的强烈冲动与欲望。不仅仅从政府的角度如此,从地产开发商的经济驱动力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随着城中村周围的社区环境、配套的商业基础设施变得完善,城中村的地价水涨船高。在现代化野心与财富的刺激下,“城中村”还会继续存在吗?
赵益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可以思考一下过去的城中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我认为,人们对于城中村“脏、乱、差”的印象,其实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
大量人口进城,但没有相应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造就了环境、卫生安全质量的相对下降,达不到人们预期的现代化城市社区应有的模样。正是面对这样的景象,我们才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污名化的城中村话语,“脏、乱、差”。
反过来,这个“脏、乱、差”的话语又给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对现代性的追寻一拍即合。因为“脏、乱、差”,所以需要改造它。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裹挟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寻,也裹挟着城市管理规划者们对于特定建筑形态和建设环境形态的追寻。这些就是我们的过去改造城中村的逻辑闭环与典型形态,由人口的涌进开始,到“城中村”彻底拆除结束。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比如说土地财政的模式或者说“国家引导的基于土地的城市资本积累”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们最近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地方债务还不上,城投公司、基建公司债务即将违约的消息,当这样一种财富积累模式不可行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去维系之前那样大规模、全方位的“城中村”拆除和重建?这里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接下来的“城中村”要怎么走?
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当面对城中村这样的建成环境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流动人口,视作真正的新市民,将其作为城市人民的相当大比重的存在?
我想,接下来我们应该尝试,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来达到未来的高水平的社会融合。
如何能够采用一种不拆掉“城中村”的方式,让建成环境、公共服务得到提升,让一种别样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矗立在城市空间之中?这是接下来城市政策需要去思考的关键问题。
至于城市与城中村的形态具体要怎么变化,这反而是其次,因为我始终相信,城市的内容永远大于形式,它变成什么样,是由其中的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的。
——制作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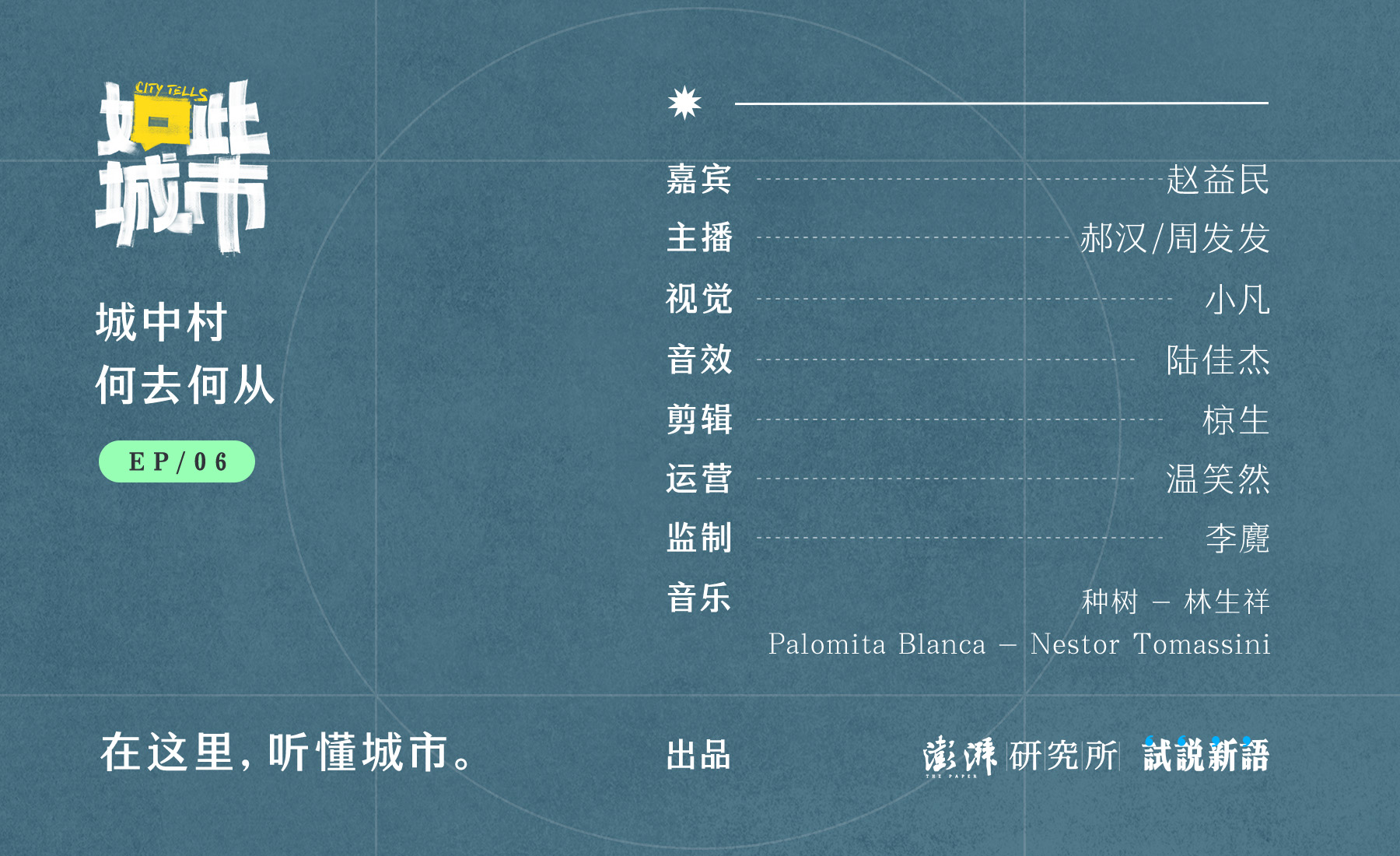
——引导收听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