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锐评《鼎革以文》︱“文质彬彬”:章太炎主义在今天可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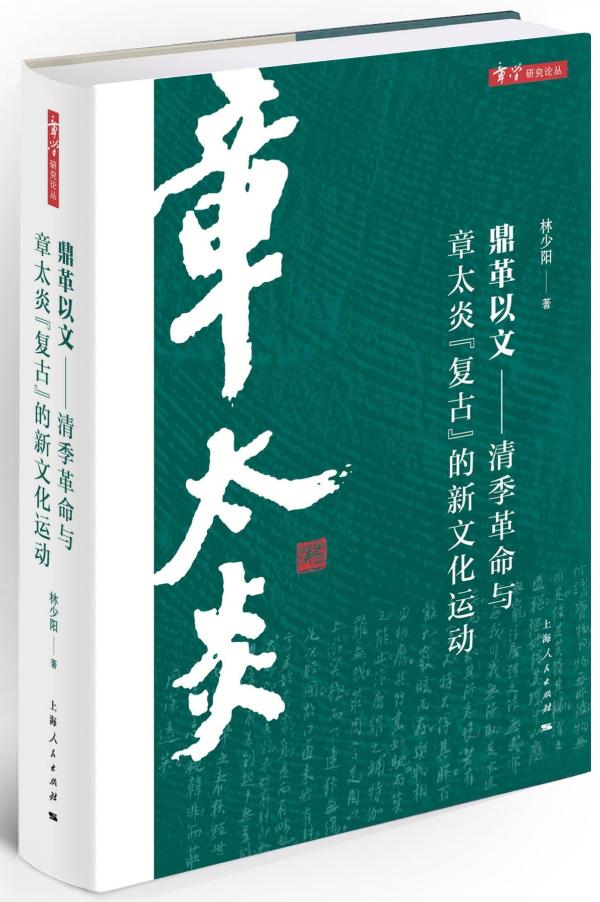
依笔者愚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现象,可能就是许多研究对象所留下的论著,在今天的史学视域下,只有史料的意义,而无思想的意义。西方学界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研究,常从这些先贤的论著中阐释新的思想与学说,丰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使之成为今人思考内外局势的思想资源。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在彼辈看来,未来的道路还需要多重角度的探讨,先贤的思想当中蕴含着许多思考未来新的可能性的因子。与之相对,近代中国许多能称之为思想家的人物,在当下的史学风气里,大概只能成为在史料意义上被解析的对象(也许只有胡适除外)。比如分析他们的文本中,哪些是“因袭”“套用”某一种东洋书籍里的观点,或者是根据其所留下的片段记载,去考订其人某一段或许对其思想主旨之形成并无太大影响的生平经历,借此凸显“学人风范”。如此这般,未尝不可。但这里所暗含的一个潜台词或许便是:历史终结后,我们已经不用再思考一些“大哉问”的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历史终结论”或许早已破产,但在人文领域里历史观的形塑,却多大程度上依然受此影响呢?古人云:“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谓乎?

就此而言,章太炎的思想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总体文化观上,章太炎主张“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7页)。中国的学术,可以在充分被继承、阐发的基础上,与域外学说展开平等对话,互通心得,但决不能以域外之论为标准来裁量中国传统,交流与攀附之间实有巨大的差别。在分析世界局势方面,章太炎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文明论”话语,其背后乃是替近代西方列强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做文饰之辞,“文明论”的实质并非“文明”,而是武力与侵略。在制度设计上,章太炎质疑近代的代议制是否真的能代表广大平民的利益,思考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将造成怎样的危害,探索如何才能设计出一种既符合中国广土众民、地域发展极不平衡之现状,又能保障大多数人民基本权益的制度。他不像同时代以及后世的许多人那样,迷信近代西方的各种制度乃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是从平民而非资本、权贵、精英的立场出发,深入探究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与平等之基本条件。钱基博曾言:“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训诂之劬,而罕体会体国经远之言;知赏窈眇密栗之文,未能体伤心刻骨之意。”(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4页)在近代因国弱民贫而对域外低声下气的情形下,章太炎的许多观点自然难以被认真对待。但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条件、有底气去接续章太炎当年的思考,丰富中国本土的思想话语体系。抚今追昔,章太炎虽已辞世多年,但今天确有形成一种“章太炎主义”的可能性。
在《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称《鼎革以文》)一书里,作者希望“透过对章太炎清季革命中的思想、实践的研究而展开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来“展示重新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可能,并试图探讨章太炎在其中的历史定位。”(《鼎革以文》,107、109页)全书详尽分析了章太炎在清末的革命主张,特别是以“文”为手段而展开的革命论述;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里对“南方话语”的阐释及其时代关怀;章太炎革命论述中对“国家”“民族”等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特征;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论战的思想内涵与话语异同的历史意义;章太炎如何在革命的情势下重新思考儒学,提倡一种“革命儒学”;章太炎与鲁迅之间或显或隐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从中突出章氏“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之理念。就笔者目力所及,本书为近年来章太炎研究领域,甚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难得的一本内容丰富、原创性观点频出、可以给人许多思想启迪的学术著作。

作者认为,审视章太炎在清末的言论,不能只从单一的政治革命的视角着眼,同时需打破“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历史论述,进而更为深入地去挖掘清末思想言说中的深层内涵。对此,笔者想起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立宪派与清末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同样也是体现了相似的思考方式。但《鼎革以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阐述以“文”为手段来表达革命观点的重要性。所谓“文”,一方面指语言、文字之意,它具有“明确的语言属性,它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意味着中国思想传统本来便有着明确的语言属性”(《鼎革以文》,17页)。其次,在与“武”相对的意义上,“‘文’也蕴含着与诸如‘仁’‘义’‘民’‘平’‘均’等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理念的关联,以及一定程度上与‘共和’‘民主’‘自由’等源于西方的伦理、政治理念的关联”,“‘文’更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借以安身立命、有着一定普遍主义色彩的伦理价值相关”(《鼎革以文》,17页)。就此而言,辛亥革命便不止是一场政治变革,而是“涉及如何重振‘天下’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思想的、文化的革命问题”(《鼎革以文》,102页)。以此为出发点,作者分析章太炎思想中与之相关的各个面向,并审视其言论的时代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可以从“传统”与“现代性”、中国与世界两个角度来分析这本书。作者认为,章太炎在清末的言说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章太炎将过去被视为异端,或被人所忽视的传统因素重新挖掘、阐扬,形成一种传统内部的批判视野,通过批判、反思已有僵化趋势的传统,来释放出传统更多新的思想可能性。在文学层面,章太炎通过弘扬魏晋文章的意义,来批判长期作为科举应试文体的八股文,这种“文学复古”的理路,反照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排他性的白话文”所带有的偏狭与局限。
犹有进者,章太炎在清末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论著。在作者看来,“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其动机不仅仅是学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或许可以说,他的方言研究正因为是高度学术的,所以其政治性也变得高度有效”(《鼎革以文》,125页)。具体言之,章太炎强调中国南方地区方言里保留了华夏“古音”,彰显出“南方”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对抗着象征清廷的“北方”,从地域层面论证反清革命的合法性。此外,“南方”还与“南明”“传统”“遗民”等历史文化记忆与符号息息相关,它借由一种文化实践工作,来表达一种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论述,并与日渐普遍化的西方的时间处于紧张关系之中。章氏此论,颇为深刻的影响了南社的文化创作活动,形成清末历史空间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政治行为。用作者的话来说:“章太炎‘文’所起的革命的作用,与千军万马之威力相比,又何逊之有?”(《鼎革以文》,152页)
最后,作者认为章太炎与儒学的关系是复杂的,“这源于儒学在功能上与主体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鼎革以文》,353页)。由于在中国历史流变中,儒学具有监督、批评、制约皇权的一面,因此在近代如何将其此一面向发扬光大,就成为儒学能否适应现代性的关键。章太炎通过重新思考儒学内部关于“狂狷”的表述,凸显其对政治体制、宗族结构、社会精英的批判性格,同时以此为视角来梳理秦汉以降儒学的历史形态,扬榷其得失。此外,作者指出,章太炎的这些讨论,还与他对“明独”的阐释息息相关,即借由“独行”之人来唤醒广大民众,“动员并组织人民,进行革命”(《鼎革以文》,316页)。总之,通过章太炎的论述,展示出“一种不属于体制权力的、立足于主体批判的儒学的面向”。并且就儒学在近代的转型而言,“论次狂狷,高扬狂狷,实践狂狷——晚清章太炎为思考中国儒学革命传统提供了一个例证”(《鼎革以文》,3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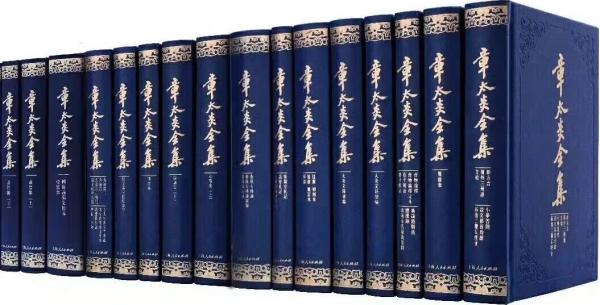
就中国与世界的角度而言,本书同样呈现出颇为精彩的讨论。作者详细考论了章太炎参与组织创办“亚洲和亲会”的来龙去脉,认为章太炎堪称二十世纪亚洲第一批反专制、反帝跨国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思想意义在于:“章太炎的帝国主义批判,也是文化批判,其矛头所指,部分也包括戊戌变法前章太炎本人并未能意识到的一些‘现代’概念,亦即其时源于西方的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框架,如‘种族’‘人种’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问题。相反,章太炎此时已经成为这一类‘现代性’话语最有力的批判者,因为他锐利地看出,‘进步’‘文明’‘人种’等‘现代’话语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之间的呼应。”(《鼎革以文》,194页)由此出发,章太炎发现印度对于中国而言的重要意义,即同时作为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度。在他的“联亚”设想里,“并非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道义的。他认为这一文化、政治的屏障,可以因中印民间的传统友谊而得到强化,并认为印度的独立有着世界史意义,因为这可以阻止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南侵亚洲”(《鼎革以文》,213页)。可见,正因为具备了这些视野,章太炎审视寰宇形势,就不像康有为那样推崇维也纳体系下的帝国,主张借强权来实现大同,对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青睐有加。而是从被压迫地区的立场出发,思考建立新的跨国体系,反抗殖民者所形塑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章太炎虽然批判帝国主义,但对由黑格尔政治哲学所衍生出的“国家”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批判性地看待中国是否应以源自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理论进行国家建设。章氏主张“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依作者之见,章氏实为“否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及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鼎革以文》,296页)。在国内政治方面,章氏认为:“只有人的自主,才有真正意义上国家的自主,而非相反。也就是说这是主权在国,还是主权在民的问题。”而其民族主义主张,也强调构成民族主义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是有着一定异质性的个体。他所阐扬的“国学”,也是一种“批判权力之学,是追求公义之‘国学’”(《鼎革以文》,300页)。因此,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他批判了“国家”以均质性、划一性规训民众,压抑人的自主性。显示出对晚清以降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思潮之警惕。
通观全书,作者立足于清末的历史语境,力图发潜德之幽光,展现章太炎革命话语中丰富的思想因子,为思考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具有历史感的切入点。笔者亦长期以研究章太炎生平与思想为主业,对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无疑心有戚戚焉。同时也正因为这样,愿意提供一些想法,或许有助于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作者所阐释的章太炎之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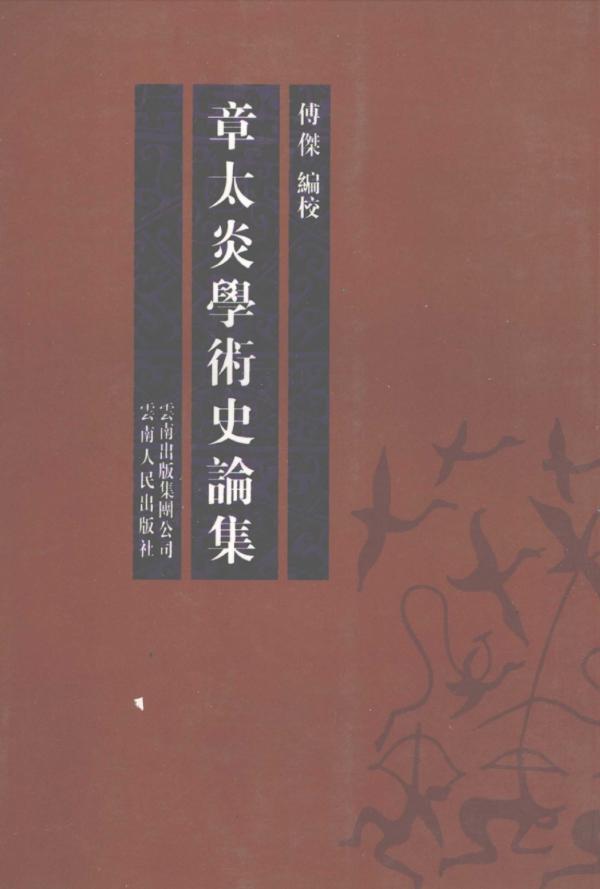
钱穆认为:“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载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493页)在章太炎看来,“历史”为“国粹”最主要的载体。而这种“历史”,虽然参考了近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但又并非能以此来完全概括。在笔者看来,“历史”对于章太炎而言,是他全面思考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借以激励民气,凝聚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主要手段之一。前者的意义在于,章氏强调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在此延续性之上形成的中国自身的社会与政治形态,包括其症结。分析中国的各种问题,必须立足于此,才能提出各种符合中国状况的政治与文化方案。后者的意义在于,正如章氏自言,“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88页)。借用张志强的观点,对近代中国而言,一个“历史民族”的产生,是形成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政治民族”的重要基础。总之,在章太炎那里,历史论述是政治论述的前提,政治论述是历史论述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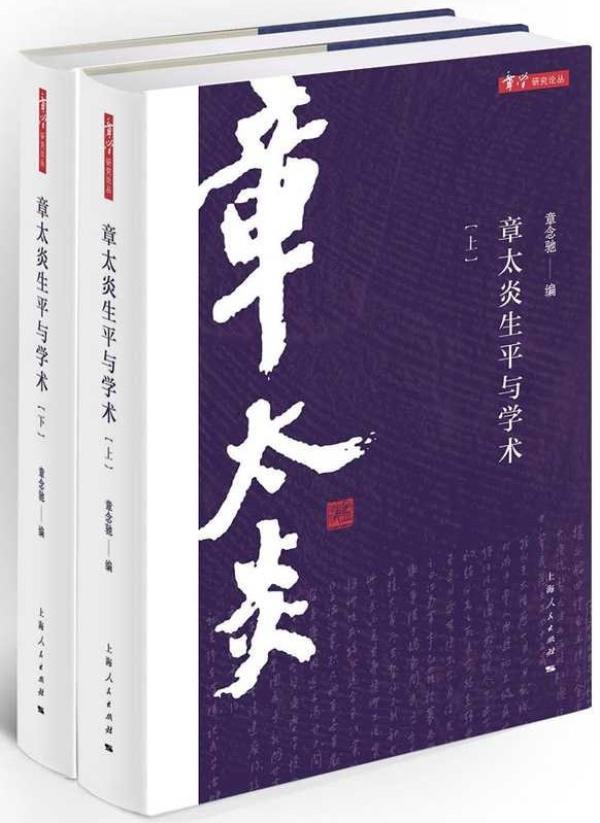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章太炎关于国家及其制度建设的思考。章太炎在清末曾痛言:“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顾有反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册,317页)在近代西潮涌入之际,“盖外人所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侧以求之者也。始宣教师咻之,犹不见听,适会游学西方之士,中其莠言,借科学不如西方之名以为间,谓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一夫狂舞蹈,万众搴裳蹑屣而效之”。此外,“宣教师往主学校,卒令山西大学堂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以是为鼓铸汉奸之长策,而宝藏可任取求矣”(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475页)。从历史上看,儒学(包括中国传统)固然具有超越具体一国一地的天下性格,但它们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依笔者陋见,离不开秦汉以来一整套政治与社会治理架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地方以礼制为出发点的宗族网络。这是保证中国历史能出现长期稳定与经济大体自足的重要基础。各种学说,固然存在批判色彩,但总体来看,其目的还是努力证成、维系、光大这一政治与社会体制。正如陈寅恪所言:“自道光之季,迄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12页)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并非是各种学说自由交流带来的冲击,而是在强势的、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整合的、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东西列强的侵略下,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地敲打、撞击中国自身行之已久、具有内在运作逻辑的政教体系,让人们对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之认同日趋淡漠,这一行为,自昔已然,于今尤烈。就此而言,重新阐扬传统的重要性,离不开一个全新的、稳定的、独立的、完整的政治实体,否则很可能沦为唐君毅所哀叹的“花果飘零”之状。这也正如作者所论,“要解决这些燃眉之急的政治现实问题,就必须确立有着实践可能的政治主体”(《鼎革以文》,2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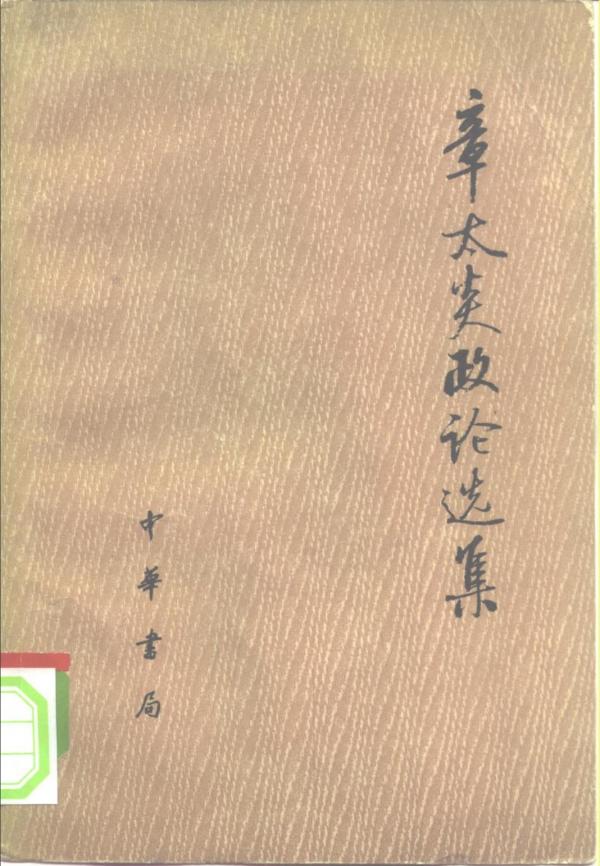
此外,对章太炎而言,思考国家制度问题并非仅是基于文化上的传承。他指出制度建设应和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相符,在中国广土众民、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如果轻率践行代议制度,能够被选为议员的很可能是地方上的豪右富民,他们不会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最后,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里尝试设计一套他理想中的制度,希望真正体现人民民主,而非成为新的压迫工具,应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克服近代资本主义政经体制的诸弊端,让民权思想得以名副其实地在中国生根,同时促进国家统一,维系政治认同。这同时也是在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深刻批判。进一步而言,章太炎在思考中国的制度问题时,时常援引法家的思想遗产。如果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商韩之术真的和马基亚维利之间有可比性的话,对比一下二十世纪西方关于马基亚维利学说的丰富阐释,比如共和主义视角、激进民主视角、批判现代性视角,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于法家的理解,基本不出“专制”“愚民”“权术”“冷酷”等单调的话语。因此如何认识章太炎对法家的阐释,或许也是理解他看待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例如章太炎在《秦政记》一文里借用韩非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分析秦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社会流动与政治平等。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便是如何让底层被压迫的人翻身解放,将其锻造为新的政治主体。笔者初读此书,看到“文”字,不禁想起了孔子的文质之论。虽然“质胜文则野”,但“文胜质则史”。理想的状态应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除了“文”之外,“质”在近代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在章太炎身上有怎样的体现,或许同样不可忽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