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虚构视角进入布莱希特的最后八年,破碎世界中的自我完整
贝尔托·布莱希特是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史诗剧”的创立者,二十世纪德国伟大的剧作家, “在黑暗的时代”仍然书写“关于黑暗时代的歌”的诗人。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莱希特的情人》,揭秘他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如何度过的?
本书作者是法国当代作家、评论家雅克-皮埃尔·阿梅特,1943年生于法国卡尔瓦多斯的小镇,当时那里是德占区,他对德语文学和电影充满热情,在大学时喜爱托马斯·曼和荷尔德林。他搜集大量布莱希特的资料,在小说《外省》里已有体现,《布莱希特的情人》则更是为布莱希特而写的故事,这部小说荣获2003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他还著有《两只豹子》《沉默的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部戏剧作品。

雅克-皮埃尔·阿梅特
《布莱希特的情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8年,50岁的布莱希特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柏林,梦想着建立一座模范剧院。一个美丽的女演员玛丽亚走进了他的戏剧,也走进了他的生活。玛丽亚打开他床边的抽屉,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而窗外,又有一只望远镜观看着一切……
如果说成为间谍便意味着谎言与背叛,那么在这个陷入昏沉的世界里,是否有人能理解自己的生活,握住一点点爱与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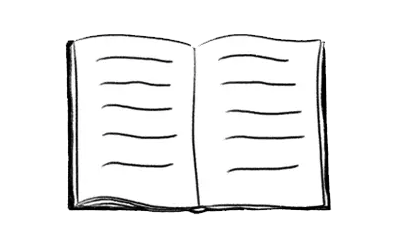
选
reading
读
他久久地凝视着从眼前掠过的红棕色森林。
布莱希特在东西柏林隔离区边界下了车,走进德国警察的哨所,打电话给德意志剧院。他妻子,海伦娜·魏格尔,围着汽车活动活动双腿。壕沟里有一辆生锈的装甲卡车。
一个小时后,三辆黑色轿车来接他们夫妇。来的有阿布施、贝克尔、耶林、杜多夫,都是文化联盟的成员。他们解释说新闻记者在火车站等着,布莱希特说: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他们摆脱掉了!”
他笑了。海伦娜笑了,贝克尔笑了,耶林微微笑了笑,杜多夫没有笑。海伦娜·魏格尔怀抱着一束雏菊,笔挺地站在官员们的中间。她一身黑西装,脸庞骨瘦,目光严肃,头发往后梳着,面带微笑,神情坚定。
布莱希特跟这几个人握了握手。白色的面孔。灰色的面孔。夫妇俩站在身着黑大衣的文化联盟官员中没有动。
这个脸圆圆的,像罗马皇帝那样把头发梳到额头的布莱希特似乎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终于见到了伟大的贝托尔特,德国最著名的戏剧家在十五年之后,又回到了德国的土地上。
当最后一位摄影记者被一名警察推开后,布莱希特关上车门,官方车队便驶了开去。
布莱希特凝视着这条通往柏林的柏油路。
他们不是在进城,而是在走进灰暗。
不堪入目的涂鸦,树,草,无人管理的河流,摇摇欲坠的阳台,无名的植物,矗立在田野里的断瓦残垣。
汽车进入柏林市中心。系着头巾的妇女正在给石头编号。
他于1933年2月28日离开德国的土地。那时候,每条街上都是旗帜和纳粹标记……今天,是1948年10月22日。十五年艰难地过去了。如今,官方的汽车飞速行驶着,超越苏联的卡车和衣衫不整的稀少的行人。

贝托尔·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摇下车窗,叫司机停车。他下了车,点燃一支雪茄,凝视着这片废墟。四周一片寂静,白花花的围墙,发黑的窗户,无数倒塌的建筑。傍晚的落日,风,许多好奇的蝴蝶,一些被拆的炮台,一座碉堡。
布莱希特坐在一块石头上,听司机对他说,如果有金融家参与,城市很快就能重建起来。布莱希特心想,恰恰就是金融家们把城市推倒在地。他上了车,墙壁细长的影子投进车里。
绵延几公里都是废墟,破碎的玻璃,装甲车,路障,带刺的铁丝网前面的苏联士兵。有的房子像洞穴。弹坑,绵延的水域,依旧是废墟,大片的空地,偶有几个行人聚集在有轨电车的车站上。
阿特隆饭店的工作人员从窗户里看着他到来。
布莱希特在宽敞的房间里脱掉了华达呢雨衣和外套。他洗了澡,从箱子里挑了一件衬衣。楼下四层,就是德国的土地。
旅馆的大厅里有欢迎致辞。当说到感谢他到来时,布莱希特有点昏昏欲睡。他想起了在奥格斯堡上高中时读过的,旅居加利福尼亚时曾经回忆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德国故事。一个女仆发现有个熟悉的精灵到炉灶旁坐在她身边,她给他腾了点位置,在冬天的漫漫长夜里与他交谈。有一天,女仆请求海琴(她这样称呼他)显出原形,但是海琴拒绝了。后来,女仆坚持了一阵后,他同意了,叫女仆到地窖里去看他显形。女仆拿了一个烛台,走下地窖,在一只敞开的桶里,她看到一个死婴漂浮在血泊里。而许多年前,女仆偷偷地产下一个婴儿,割断喉咙,藏在一只桶里。
海伦娜·魏格尔轻轻地拍了拍布莱希特的肩膀,让他从昏沉中,更确切地说,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挺起身,镇定自若,心里想着柏林就是一桶血,而德国,从他少年时代的第一次大战起,也是一桶血,他则是海琴的灵魂。
血曾经在慕尼黑的街上流淌,而现代德国又与古老的日耳曼故事中淌着的血流重合。他回到地窖,以卑微的理由,想从此把孩子带出来,让孩子接受教育,用冷水去洗掉地窖地砖上留下的血。歌德用他的《浮士德》,海涅用他的《德国》做过,然而污迹越来越大,德国母亲快要窒息了。
透过窗户,他看见穿着粗笨鞋子的女人在给石头编号。街道没有了,只剩下路和云。
晚些时候,在文化联盟俱乐部的客厅里,顿姆希茨做了高明的简短发言。
布莱希特快乐地看着贝克尔、耶林和杜多夫。多么有趣而不相称的三人帮。他透过雪茄的烟雾想着。他面前的这些人负有引导东德走向艺术博爱之伟大理念的使命。其中两个人曾经是他年轻时的伙伴。
想象一下三个身着深色外套和白衬衫、系着圆点领带的男人的样子。他们,在俱乐部宽敞的海鸥厅里,穿着用可怕的苏联棉布裁剪的西装。顿姆希茨读着三页灰色的纸。他优雅考究,像被提升为校长的大学教授一样保持身材,好吸引年轻的女人。
他的身边是约翰内斯·贝克尔。他没有变。他戴着圆圆的近视眼镜,保留了温和与亲切。贝克尔记得年轻时的布莱希特,瘦瘦的,不快乐,头上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黑雪茄。布莱希特双脚踩在椅子上,读着,更确切地说是揉着柏林的报纸,因为靠《三毛钱歌剧》很快赚了不少钱而得意。他从一本蓝色的硬皮小书里学习“战后经济”,带着几张解剖图散步,想买把斧子劈开领导柏林大舞台的那些软脑壳。他跟着有轨电车跑,一手搂一个女舞蹈演员,爬到剧院的屋顶上。他赠给观众观察社会的巨大眼镜。问题呢?他还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的著作,但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能从中找到无数戏剧点子。
海伦娜·魏格尔也记得贝克尔。在她看来,约翰内斯身上发生的变化,是背:笔直的背,保持与官员身份相称的身材。以前,他懒懒地躺在吊床上,把樱桃核扔到女演员们的头发里。海伦娜想,我会比布莱希特与贝克尔处得更好。
赫伯特·耶林读着一篇简短的发言,他更白,头比较圆,而且光滑,目光扫来扫去,孤独,清醒,考究。他翻着纸张,朗读着他圆而小的字体,带着热情,也保持着距离。他的发言里满是大家爱听的流畅的套词。

《布莱希特的情人》法文版封面
布莱希特记得以前,他读耶林的戏剧评论就好像是在听德高望重的医生作诊断。耶林那时已经是最受人尊敬和畏惧的评论家了。
他老来有了外交官的风度,但他的目光失去了敏锐性。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摆脱了纳粹的影响。重建全民教育政策,缺的就是他这种水平的智者。他用光彩熠熠的语言恭维布莱希特的时候,大厅里的气氛却是冰冷的。他用委婉、平静、柔和的语调结束了发言。随后他伸出左手,搭在布莱希特的肩上,提醒布莱希特,从一开始他就陪伴左右。他用他的手触到了他们年轻时代的神圣实质。然后还有一个发言。
海伦娜·魏格尔听着,沉思着,有些疲倦。她把头凑近布莱希特,在他耳边轻声道:
“那个胖子是谁?就是那边手里拿着帽子的?”
她指的那个人,长得壮实,光秃的额头上满是汗水,穿着一件过紧的外套,扣子没扣好。他巨大的袖口扣子,属于庸俗的小老板那种类型。并且那人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仿佛看见德国的美德用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房间。
“杜多夫!这个无耻的杜多夫!”布莱希特回答道。
斯拉坦·杜多夫也一样,二十年代在柏林工作过。他也是黄金时代布莱希特的一个伙伴,那时候他们花天酒地,神奇的柏林有着轻佻的女人,还有用刚从濒临破产的剧院钱柜里拿出来的钱换来的微薄的快乐。
这个保加利亚人在1926年或1927年左右参与了电影《库勒·旺贝》的剧本创作。1932年,他在警察监视下的莫斯科引导过布莱希特。
他对杜多夫笑笑。贝克尔拥抱魏格尔和布莱希特时,所有的人都鼓了掌。
上了白葡萄酒。
后来,在阿特隆饭店,电话响了(一个又大又老的家伙,仿佛是苏联军队多余的机器),但是接电话的是魏格尔。大家都想看贝托尔特:雷恩、贝克尔、埃尔彭贝克、卢卡契。
楼层服务生拿来了一个放满贺电的托盘。雪茄烟雾后的布莱希特保持着嘲讽、冷静的目光。
夜幕降临。
布莱希特独自坐在房间里。他凝视着他的新通行证。
(《布莱希特的情人》[法]雅克-皮埃尔·阿梅特/著,周小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
原标题:《以虚构视角进入布莱希特的最后八年,破碎世界中如何让自我完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