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卫·阿米蒂奇谈《历史学宣言》:从更久的过去看更远的未来
5月24日下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席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在思南公馆出席了“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读书会,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的李腾对谈,介绍了《历史学宣言》与其主张的长时段问题。本文系活动文字稿,经审定,略有删节。

大卫·阿米蒂奇:我想先简单谈一谈《历史学宣言》这本书的来源以及它的简要内容。首先,这个题目是和另一位作者乔·古尔迪一同想出来的,他也在美国教授历史学,所以我们称之为“历史学宣言”。之所以叫“历史学宣言”是想让它听起来像《共产党宣言》一样,是一本非常激进的书,虽然这场历史学革命不是特别成功,但在英语国家里面让很多人看到它感到非常不开心,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本书开篇第一句就是在效仿《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幽灵,而是短期主义的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事关我们关注问题的时间维度,至少在西方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计划和选举,他们的商业周期以及其他的一些周期,就是那些决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周期现在居然变得越来越短,最多只有5-6年,有些时候只有2年甚至几个月。比如说公司发布财务报表仅仅是一个季度。这种越来越短的时间维度就是书中所批判的,人们越来越忽视长期问题,但长期问题恰恰对于我们世界影响最大而且最急需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这本书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愤怒,尤其是让很多西方史学家感到很愤怒呢?因为我们质疑了他们太过于短期主义的做法,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史学家们关注的历史维度只有5-50年,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维度,整个周期和人的生命周期差不多,这种狭隘历史关注的时间维度,让很多阅读历史的人,还有那些依靠史学家理解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人感到非常的不适,因为这种做法缩短了他们的关注维度。
我们在这本书中鼓励很多史学家让他们能够更有勇气关注更长的历史维度,从一个更加长期、更加广泛的角度思考各种各样的变化、发展以及历史问题,有时候是几十年,有时候几百年,甚至是以千年维度研究许多历史问题的起源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世界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的崩溃,以及国内和国际之间不平衡日益加剧的现象。正是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当今迫切问题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甚至气候变化要追溯到几百年之前,远不是靠研究短期可以解决的。

其实在不久之前很多专业史学家认为要挖掘过去,了解现象,并且以一种过去长时间历史维度思考当今的问题,他们会用这种东西思考塑造各种态度、进行各式各样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甚至所有古代文明中,史学家都扮演这样的角色。如今专业史学家不认为他们有义务去了解过去和解释现在,他们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认为,这种趋势低估了史学家的角色,他们无法让史学家参与到公众辩论当中,而且没有充分利用史学家解释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只有专业的史学家才能真正地运用好这种能力。
我在书中引用了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丘吉尔的话,他说如果人们可以从更长的时段看待历史和过去,他们就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本书向大家展示这个观点。
我们认为史学家可以做到这样的任务,他们或者看通过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浏览历史和传统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一些新方法,尤其是利用大数据,就是说对于很多可以通过电子渠道获得的文件进行直接浏览,或者通过一些统计学和科学上的电子文件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分析,这样可以进行非常长时段的多维度分析,远远超过个人历史学家过去取得的成就。我认为研究资源来源的变革可以带来历史思维的变革,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思考、了解现在一些迫切的问题。
其实我本人也是对我在《历史学宣言》这本书中倡导的研究方法身体力行,最近写的一本关于内战的书,回溯了从古罗马一直到现在叙利亚内战超过2500年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内战,仅仅一本书就横跨了这么多世纪,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全球在内战问题上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拉克和叙利亚内战。《历史学宣言》这本书从理论上提出了应当关注长时段和重大历史问题,我的新书《内战》就是一个实践,希望大家读完《历史学宣言》以后再去读《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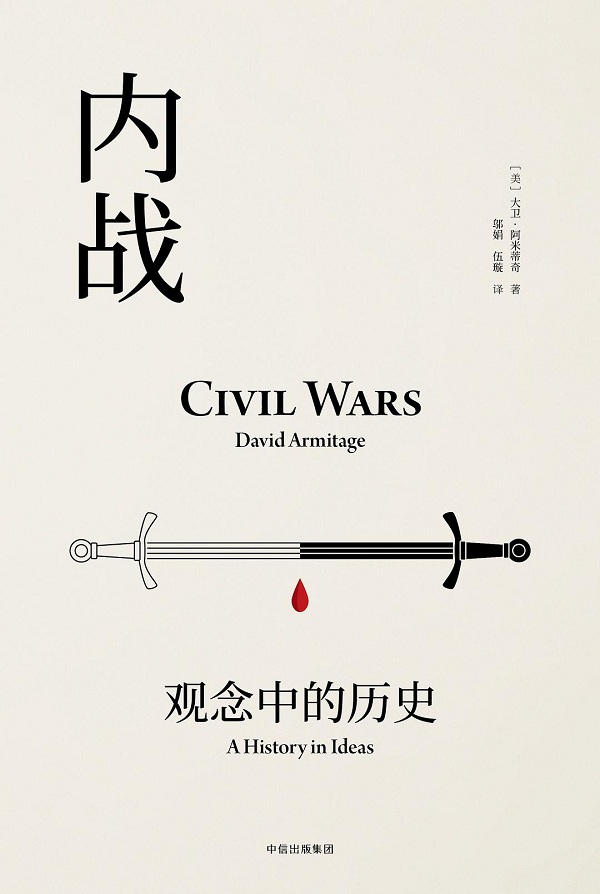
最后我想谈一谈《历史学宣言》最后一句,其实也是呼应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因为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共同的呼声,也是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启发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希望这样的呼声能够在中国得到足够多的共鸣。就像谈起中华文明常常以千年为单位,这恰恰是我们赞颂的长时段,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短期主义。短期主义可以说是现今困扰西方的思维现象。
李腾:在您的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讲到要向权力说话,要向权力讲述真理。为什么必须要向权力说话?您觉得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向权力说话?
大卫·阿米蒂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对参与公众事务并无多少认同,觉得历史学家如果为政治献计献策会失去他们的独立身份。然而,在19、20世纪早期和二战期间,很多历史学家所做的,恰恰就是帮助当局从历史的维度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会帮助公众更好地从历史维度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房屋供给、殖民地等等。我认为历史学家确实有这样的公众责任,他们可以从历史维度进行思考,帮助政策制定者进行更好的决策。同时我也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保持他们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要保持他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李腾: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历史学家,尤其是一战以后欧洲国界划分,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更有意思的是,一战以后欧洲各国和德国边境的划分有一个重要参与者,就是著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一战以后虽然是历史学家建立了这个世界,可是很快就被二战摧毁了。如果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顾问,会不会形成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但是哲学王成了历史王?
大卫·阿米蒂奇:威尔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还做过新泽西州的州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可以说,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典范。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还是可以看到的,而1945年之后,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中的发挥的作用逐渐式微,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断崛起取代了历史学家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现在可以看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是律师,成了议员或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如我们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取代了历史学家、取代了政府智囊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短视现象,越来越缺失历史维度的思考。

大卫·阿米蒂奇:我在书中提到的“长时段”,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布罗代尔提出的。在他那里,长时段的历史就像一个背景,通过这个背景我们可以了解人类各个组织、人类系统、人类意识形态的变更,它就像是提供了短暂之光闪现的大舞台。我们书中所说的这种长时段不太一样,我们关注的时段比布罗代尔说的长时段要短一些,更加有互动性,更加注重历史发展演变,更加有能力。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是更加平静、更加一成不变的长时段。它的著名说法就是长时段像地中海的山一样从来不会变化,这就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我们所主张拓展历史的长时段从100年拓展到1000甚至2000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通过历史视角了解现在的问题,同时不会影响或者委屈对于历史精确的测量。我们认为可以把长时段的历史,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德国实证主义的谱系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继承、可以通过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像大数据研究来研究这些不断出现的新历史资料,同时可以让我们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历史研究成果。
李腾:我本人主要是做12世纪,会更加关注中世纪的问题。您的书中用了麦克尼尔的一个论断,认为公元1000年的时候整个世纪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全球史写作几乎所有人还是按照欧洲体系在写整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东西。那么在中世纪领域,英国和美国都有一个新的讲法叫做全球中世纪。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希腊罗马的思想怎样进入了近代,虽然我没有看过内战那本书,但是根据目录来看好像讲了罗马以后进入了到近代早期,中间好像还是有一千年的断裂。我发现在大的历史叙述当中有时候会把中世纪这1000年忽略掉,您觉得这种倾向是为什么?是因为中世纪太静止了还是太复杂?或者说中世纪的东西在近代早期就都可以表现出来?
大卫·阿米蒂奇: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未必在于中世纪是一个非常静止的时代。如果大家更好地了解一下中世纪会发现当时有各种各样商业活动,各种各样的知识和各种各样学术上的变化层出不穷,社会非常复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等等,历史学家不会害怕解决复杂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所谓历史断层,还是因为我们受制于西方的传统看法,尤其是19世纪德国的看法。所谓整个人类发展史通过西方的视角看待,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如果是这种视角的话,确实中世纪就是黑暗世纪,一个静止的时代,后来才开启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确实,我们要摆脱纯粹西方历史学的视角比较困难。我认为如果要真正实现摆脱的话,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做学理上的倒追,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见和歧视。采取真正全球性的视角审视人类的历史,要关注更长远的发展。比如说同一时期南亚和西亚时期历史的发展,进行真正全球性的历史书写,甚至要从行星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历史。因为不仅要关注人类历史,更要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看到人与自然的演变也是全球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面中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站在时代当中可以看到全世界各个部分的纽带变得日趋紧密,而且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对自然和自然对人的影响逐渐地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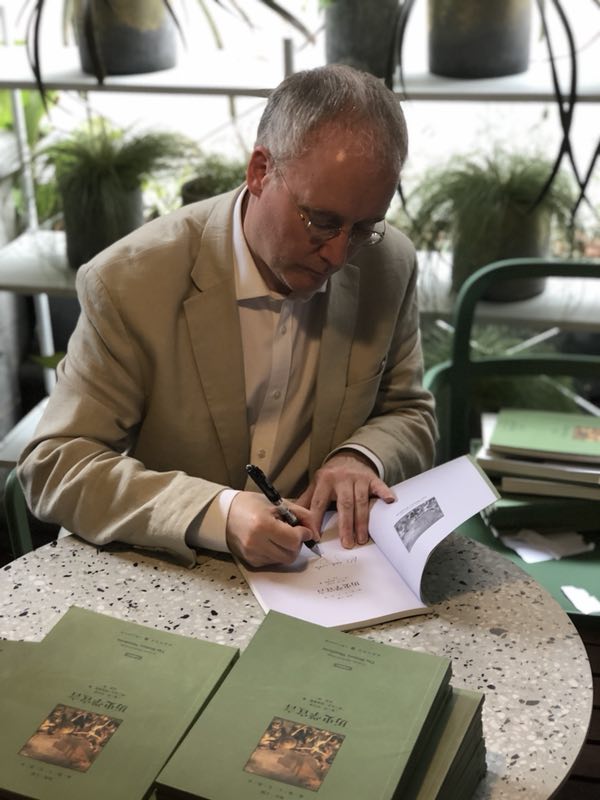
大卫·阿米蒂奇: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实际。在研究当中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时间维度取决于你到底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要研究一个小问题的话自然就要更短的时间维度,如果只关注小的问题的话,恐怕从此在职业生涯当中只会关注这些小的问题,没法着眼于所谓大历史和大问题。对于哈佛的学生,无论他们是做课程论文,还是硕博士的学位论文,无论他们是做什么样的案例研究,哪怕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年,我都会让他们在写之前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怎么样,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这对于他们作为未来史学家非常重要,不仅能提升历史学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广泛阅读。我认为社会科学变得日益重要,自然科学也让他们越来越多关注大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历史进步,同时能够推动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繁荣发展。近几年我带的博士生们关注的时段基本上都是50-100年,因为美国的博士是六年制,同时我们作为老师不断地鼓励他们关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要超越传统维度的藩篱,不仅要关注短时段。只专注于非常狭隘的小问题,意味着他们缺乏学术上的进取心,非常重要的是要关注大问题。我认为关注大问题可以保证小问题的精确性和专业深度两者完全可以兼得。
李腾:最近有两本非常经典的20世纪外国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一个是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还有一个是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他们处理的时间段都是一千年,没有非常具体的主题,非常不同于我们现在一般的研究。这两本书翻译后,中国学术界有一些并不正面的反映,认为它里面的东西太复杂。您所提倡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说法,实际上在过去一些年的中国学界是受批判的。198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倾向于非常实证和考据的研究,好像回到了19世纪德国考据时期。长时间段和考据性以及宏大叙事的回归是否是复兴了传统的途径?
大卫·阿米蒂奇: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非常好,我觉得就像我在《历史学宣言》所说的那样,现在与其说是有一种朝着宏大叙事的转向,不如说是宏大叙事的回归。历史上是有这种传统的,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对细微问题的关注,我们现在是在回到宏大叙事的传统。关于这个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最近有一本新书是写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从史前到现在不断的变迁过程当中来审视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丝绸之路的全球史。他讨论的时候远离了西方视角,而是更多关注以亚洲视角思考问题,谈论了亚洲原本作为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这个中心重新从西方回到了亚洲。书中还提到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传统古代丝绸之路又一种新生命的延续,真的是一种对于宏大叙事的伟大回归,从3世纪一直探讨到19世纪。
李腾:视角的转化确实是非常重要。刚才您所说的西欧视角,就是历史要经过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复兴的演变。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过去我们总把中国视为东亚体系的霸主,总是从中国看周边。而现在,我们可以尝试从周边来看中国,比如说用朝鲜和越南的资料,看看他们当时怎么来看待中国。当视角转变之后,确实就会有很多新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史学理论的魅力。使用了一个新的理论之后,你所用的材料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你再这些材料时候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