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一个人在北京住院手术,术后第一天阳了 | 三明治
原创 elplaneta 三明治 收录于合集 #每日书 386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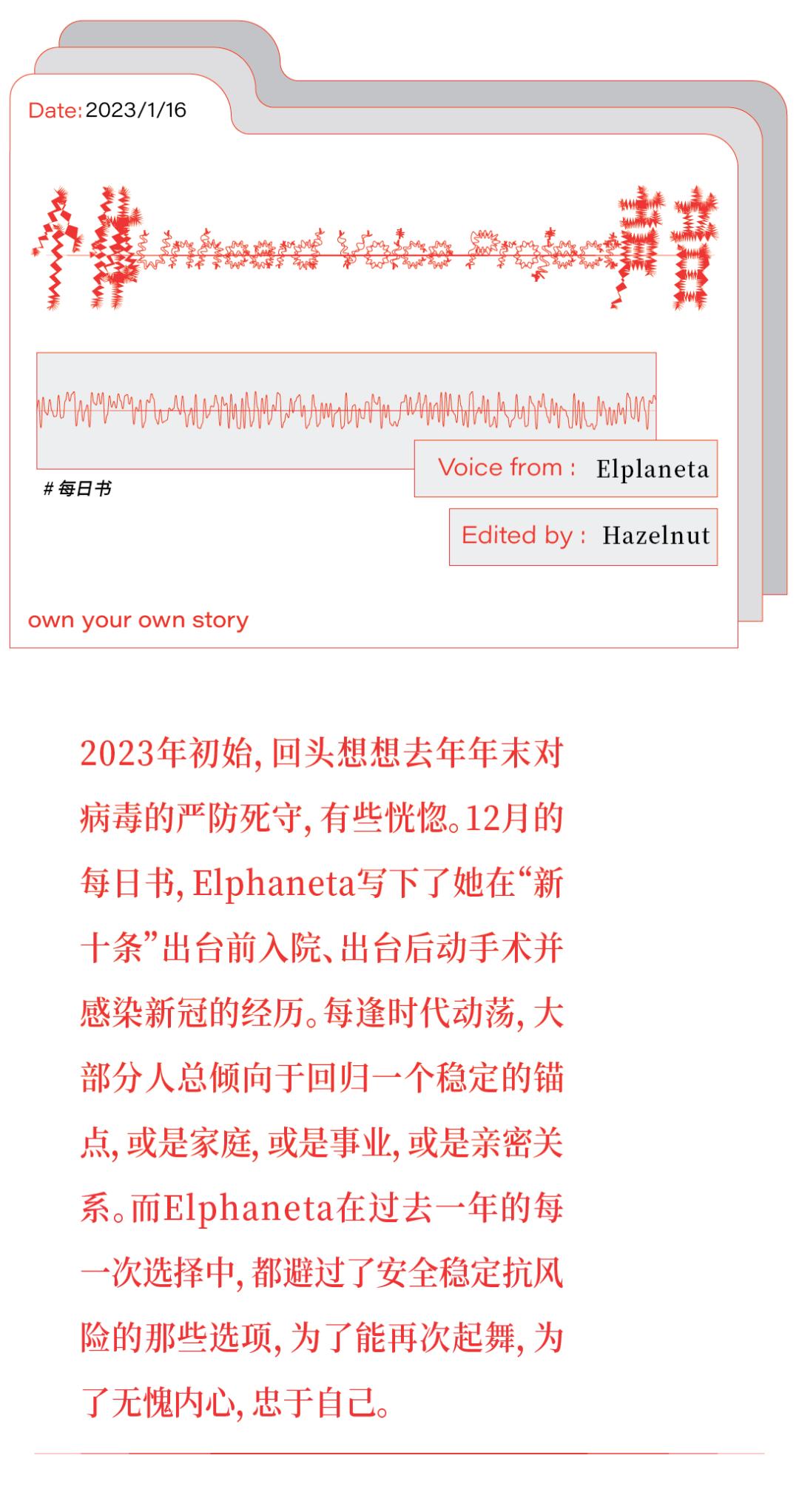
2021年8月,我在拳击时扭伤了脚,久未痊愈。去年12月初,我在北京等待医院解封,好住院手术,距离受伤已经一年零四个月。
在伤病悬而未决的一年里,我经历了疫情中的艰难创业、完成了被防控政策卡着喉咙一拖再拖的艺术项目、陪伴腰椎骨折的母亲从床上站起来、独自度过上海四个月封城的日子。
共计辗转29个临时住处,被封控171天,想自杀3次,和家人断绝关系4次。
11月底,我带着全部家当从检出了阳性客人的酒店连夜逃出,有幸被同学家收留。同学一家人的温暖善意让我从反复崩溃的状态中走出,重拾内心的平静,想要写下这一年的故事。我知道对于那些在疫情中失去生计、失去家人甚至失去生命的人来说,我的经历已十分幸运,但我的小小世界或许也是时代切片中一粒努力颤动着的尘埃。

健身房拳击训练受伤,我本以为静养就能自愈
左直拳,格挡,右勾拳,膝击。厚重拳击手套和层层绷带里的双手开始出汗,不停息地连过十几招让我有些微微气喘。我在上海这家健身房已练了近一年的拳击。
又一次左脚点地转动,腰部发力,带动左臂出拳。突然,我感到左脚大拇指有种别着筋一样的疼痛。“教练,我好像扭到脚了”。我俯身运动了一下扭伤的脚,“好像不是很疼。”“那咱们换一边腿继续”,教练说着,摆好了踢腿用的靶子。
空中鞭腿,肘击,转身出拳。我一边继续训练,一边在动作中感知左脚的疼痛度。这种细小的疼痛令人丧失警惕,也许明天就好了,我想。走出健身房时,我感到左脚内侧在走路时不能用力,只能撇着脚用外侧着地。
当晚,我发现受伤的拇指关节隆起一个大包,整个脚背也肿如面包。疼痛有所加重,但我仍未太过在意,只是喷了点白药,认为三天就能自愈了。
第二天,疼痛愈发明显,水肿也更严重,我决定去医院看看。我的左脚已经肿得穿不进鞋,只得套着拖鞋,单脚蹦跳着出门,去最近的瑞金医院。医院门口的保安大叔见我费力跳跃前进,上来调侃我:“要帮忙吗小姑娘?我可以把你背进去呀?”我连忙摆手拒绝。
照了X光片,开检查报告的医生竟然还将左脚写成了右脚,我又单脚蹦跳着去改。急诊医生看了片子,说骨头应该没事,没有骨折。但是筋断没断就不知道了。
几天后,我去另一家医院又检查了一次。这次我升级了设备,在美团上买了一副双拐。三腿的我健步如飞。骨科医生伸手摸了摸我的关节,判断说筋应该没有断。之后他一边洗手,一边嘱咐“最近尽量少走路”。护士从一只不锈钢桶里舀出粘稠的黑色中药膏,厚厚地敷在我的伤处,缠上了绷带。

◤缠绷带的左脚速写
健步如飞三脚猫◥
回西安后,我的设备再次升级,从双拐三脚猫升级为赛博格机械腿。我也去看了西安最好的骨科医院红会医院,医生说:“多用盐和醋泡脚。”我就安心展开了老年养生生活,以为接下来会是一段平静的养伤时光。

戴着矫形器去散步

结果却是,在和伤病同甘共苦一年半后,它并没有完全离开。于是我来到北京,想要手术来彻底解决问题。经过一系列的封控困扰,终于可以入院了。
朋友的妈妈来送我。办完手续,阿姨帮我把行李拿到了住院部足踝科门口。从这道大门开始,病人们必须独自应对一切,一切外部的探视和物品都不被允许进入。门口的护士问,“东西都带齐了吗?下肢抬高垫、便盆、尿垫、一次性手套都有吗?”“都有”,我说,护士低头看了看我明显超出要求的行李,说:“你东西也够多的。”
前几周,刚做出一个人在疫情封控的北京住院手术的决定时,我在酒店默默哭了一晚上,感到自己没有做好独自应对一场手术的准备,内心充满抗拒。同时也自怨自艾,“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一次人生重大时刻,都没有亲友在身边,只能一个人面对?”
我平日从不在朋友圈发私人内容,但那晚情绪决堤,发了一条“本孤寡也要解锁一个人住院手术的高级技能了”。第二天起来,发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有朋友说“一个人住院很爽,医生护士都很友好”,有辣妈朋友勉励我说“我一个人住院生过孩子,没事”,还有的表示“等我解封了就去看望你”。
在许多慰问下,我也平复了心态,纯粹把眼前的困难当作具体的问题去逐一解决。我开始在知乎上查“住院用品清单”,在淘宝上浏览“住院必备神器”。在装满一整个行李箱、一个大行李袋的住院用品,又准备了一个办公用的床上桌板之后,我有了一种不是去住院而是去旅行的错觉。
这次来北京手术确实一波三折。在西安的家人一直弹窗无法来北京,医院在特殊时期也取消了陪护探视。我从上海迂回到京,恰逢全城居家。检查前一天我自己也被莫名弹窗,冲去社区理论一番后才解除。本来上周就应入院,入院前一天又被通知医院封了,传言要改方舱。当晚,我所住的酒店检出阳性客人,我连夜带着所有家当逃出酒店,所幸被同学一家收留。在同学家等待的一周内,全国局势一天一变,从封城传言到全国疫情宣布结束,政策放开的速度超乎预期。
这周终于得以顺利入院,因为风向已变,原先计划手术前的单间隔离也取消了。我提着行李,被护士带进了三人间。待我收拾好行李、铺好自带的床单,躺下准备休息时,一个护士进来对我皱眉道:“你的床单是花的,不能铺。我们医院的床单是白的,如果你带了纯白的床单可以铺。”我疑惑,“这有很大影响吗?”“不能用自己带的床单。”护士毫无商量余地。“我皮肤过敏,必须用自己的……”我试着坚持。“你晚上可以铺,但是白天不行。”“可是我白天晚上都只能穿着病号服待在床上,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对,不能。”护士不耐烦地走了。我只好将床单收起来。
旁边床位是一位刚做完拇外翻手术三天的阿姨,一直在问护士要止疼药,还不停地给教友发语音,“我在北京做手术,祝我早日康复,为我祈祷,感谢主……”每发完一则语言,她要回放三遍以确认自己的声音。
晚饭时,我被叫到办公室,和实习医生曾医生确认病情。他看了看我的病例说,“你练拳击的?真看不出来,你这体格不像。”旁边的医生冷冷道,“所以这不进来了吗。”我连忙解释,“我不是专业的,只是爱好。”
医生认真地问了我一堆问题,诸如:“从0到10,你怎么判定自己的疼痛指数?”之后又去照相室拍照,他用黑色马克笔在我腿和脚上画了待宰的标记。翻看我的片子时,他说,“你是跑遍了全国最好的足踝科吗?从西安红会,到上海六院,到复旦华山,再到积水潭。你可真厉害。”
虽然有些医生认为“你能走路不就行了,还想运动,你要求太高了”,家人也认为“能不开刀就不开刀”,但为了还能重新起舞和奔跑,这一年来我自己去了无数次医院,确实属于积极自救的患者了。

带了床上桌本打算病床办公一把,
结果医院没WiFi,卷不起来了

昨晚一夜未眠。邻床的阿姨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按铃叫一次护工,上厕所、喝水、刷抖音、发微信语音,依旧是发一遍回放三遍。我也鼻炎发作,鼻塞口干,浑身燥热,鼻腔干痛。整个夜晚,响彻着各个病房此起彼伏的“正在呼叫中”和《献给爱丽丝》的铃声,以及阿姨断断续续的说话、咳嗽和呻吟声。
我躺在病床上,由于鼻塞,只能像鱼一样张着嘴呼吸,感到身体里的水分被抽干,但阿姨明早才能再来给我们打水。外面似乎一天天恢复正常了,居家办公三周的朋友们立刻卷入到加班工作的节奏中。前几周听闻我住院之后频繁和我聊天的朋友们渐渐也不再回复我了。我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倍感凄凉。
八点,主任医生带着一大群年轻医生和实习生来到病房。我垂死梦中惊坐起,还戴着眼罩、嘴角挂着早餐喝粥的印迹,开始解释自己的病情。“她这个有点怪……我不确定是否要动骨头。”主任医生看起来没什么把握。助手们检查了我的片子,要求我把在外地做的检查全部在本院重做一遍。
经过我多次央求,一个好说话的护士终于同意让我换到一间空病房。至少接下来三天,可以好好休息了。
昨天的曾医生又进来,“来,伸出你的宝贝脚。”他再次检查了一遍我的关节活动情况。“你这个背侧和底侧都有问题,奇怪。你下午再去做个核磁和B超吧。”“我哪天手术?”“下周二。”“哪个医生做?”“一般是赖医生。”“赖医生?”我在脑内搜索了一遍,并没有印象。“手术你就不用担心了。”他笑眯眯地走了。
晚上,我们几个同天入院的患者被一个师傅带领着排队去做检查。几天没和活人聊过天,大家都显得热情友好,在核磁室外面等待的时候便相互交谈起来。一个从内蒙过来的大叔,披着军绿色大羽绒服,吊着一只脚走来走去。他的右脚踝曾扭伤多次,四个月前又扭伤,疼痛影响走路。为了做手术已经在北京亲戚家待了一个多月,和我一样历经了北京疫情、医院封锁。
“我们这种骨科小病还好,还能等,那种绝症病人怎么办啊!”大叔感叹。
和这些走路明显一瘸一拐的病友比起来,我显得非常正常,再加上一个人来过无数次练就的熟练业务,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家的助手,帮忙取号、存放手机、指路、超市带货、帮师傅分发片子,俨然反客为主,要不是病号服暴露了我,可能就要被路人叫大夫了。
做完检查,同学的妈妈帮忙送来了洗鼻器、生理盐水和消炎药,由护工阿姨取上来。使用完洗鼻器后瞬间七窍通畅,神清气爽,从鼻腔堵塞粘液倒流的窒息状态中活了过来。闺蜜已经在帮我查出院后的租房信息,甩给我好几个链接。再次被爱拯救的一天,感到自己无比幸运。

早上六点醒来,感冒症状已基本褪去。我给同学妈妈发信息表示感谢,阿姨说,“昨晚我回去发现XX(我同学)发烧了,可能是中招了……”这已经是我亲密朋友圈里第五个了。同学刚刚复工两天,他们公司同事阳了一半,她每天戴N95,不坐电梯,但还是防不胜防。
这几天大家的交流话题都是身边又有谁中招了,要备什么药,微信朋友圈里一片发烧病倒的,还有倒卖抗原的、呼吁早阳早好的。三明治写作群也变成了病情交流群。慰问完同学之后,我又联系了一遍家里的长辈,叮嘱他们注意防护,不要去人群聚集场所。但还是晚了,有长辈已经在发烧了。
恍然间,回到了三年前的纽约。
2020年3月,纽约开始实行居家令,大多数公司开始居家办公,学校在线上课。但居家令其实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政策,公园依旧人满为患,出门也不受限制。最紧张于防护的还是华人,当时我和舍友在家待了4个月,每周全副武装地去超市买一次菜,进门必消毒全身和买来的物品,之后洗热水澡、洗外衣。
因为公寓楼里很多确诊,我甚至用水袋盖住下水槽,用塑料布封住出风口。还有人把门缝都用塑料布封上的。在政府不对个人的生命健康负责的时候,只能自我保护,大家也不会把损失归咎于政府。
三年后,我们也终于迎来了直面病毒的时刻。
再说说住院日常。每天早上八点、下午三点,护士查房,量体温,询问大便情况。周末,医生和检查室不上班,所以病人们清闲了很多。三餐时间是早七点、中午十一点、下午五点,非常有助于健康作息。今天中午伙食很棒,居然有一整根大鸡腿。主食一般是管饱的双份,比如米饭加馒头。由于我还没做手术,整个人精神抖擞,加上独享三人间的怡然自得,显得比查房护士的状态还要好。后来护士已经不进来查房,只是在门口观望一眼之后和记录的同事说“哦,这姑娘,她没啥事儿。”
我本打算住院期间赶一赶申请博士的论文,但因为排了手术之后今年已经来不及,只能明年再申,我便允许自己手术期间放松几天,开启度假心态。一日三餐和热水送到门口,有阿姨一天打扫两次卫生。除却闹人的《献给爱丽丝》的呼叫铃声,几乎就是隔离酒店的休假体验了。

七点未过,我已经收拾好床铺、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把检查片子在床尾摆放好,静候医生查房。这次年轻医生们簇拥着的是一个陌生脸孔的大夫。他听完实习医生的汇报,摆弄了几下我的脚,对其他人说:“我估计是下面的筋受伤之后粘连了。我们回去在电脑上再看看片子。”医生们又鱼贯而出,大夫边走出门边困扰地说“粘连要怎么手术,这可不好做啊……”留下了满心不安的我。
我呆坐在床,思考了许久诸如“这个新医生(赖医生)的说法和主任医生怎么又不一样?”“这个新医生给我做手术会不会没经验?”“会不会做完手术没效果甚至更糟?”“明天就要手术了,今天感觉他们还定不下来方案?”之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最后,我打算做一回案板上的鱼肉,相信现代科学。
午饭时,一个年轻护士冷冰冰地进来,甩给我一份签字单,“你明天手术,今晚十二点过后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药物过敏吧。在这签字。”
“明天什么时候手术?”我问。
“等着叫你。可能早上,可能下午,也可能夜里。”
我又好奇追问,“为什么不能吃不能喝?”
护士有点没好气了,“因为你明天要做手术,要打麻药。”
“是会影响麻药效果吗?”护士非常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你手术还做吗?”
“我做,但是我需要知道谁给我手术,以及手术方案,才能签字吧?”
“那你自己去问医生。我只是负责告诉你,今晚十二点过后喝一口水都做不了手术。我说清楚了吧?”
我签了字,“那我应该去问哪个医生呢?”
护士拿着单子疾步走出,“我给你随便找……我给你找个医生问吧。”
我有点不解,为什么这里的护士都是一副我欠了她们钱的样子呢?
过了一会儿,实习医生进来,“你明天手术,谁给你签字?”
“我能自己签吗?我家人都在外地过不来。”
“原则上,不能自己签……”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鉴于最近疫情的情况,也有一些病人是自己签的。”
“那我自己签吧。”我接过笔,看了看文件,又有些迟疑,“我还是需要先知道主刀医生和手术方案吧?”
医生和我解释了手术的大致方案:需要在足内侧开一条口子,削掉一部分骨头,上面和下面的筋都需要修复打钉。康复需要三个月,前三周每周换药,三周后拆线,一个半月后复查。
“这个手术的风险如何?有没有可能做了之后更糟?”我问。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做了之后比现在更糟的概率也是有的。风险比如说神经损伤……”
“但这个概率应该很小吧?百分之多少呢?”
“你这个病例比较特殊,不像拇外翻等常规手术,我们经常做所以有数据,比如拇外翻病人中有3%是做了之后情况更糟。你这个病例我们一年也遇不到几例,所以没法统计数据,统计也是不准确的。”
我听了心里更悬,“但是……你们还是建议我做的,是吧?”
“对,我们建议做。”医生又开始说起我跑遍全国足踝科的事迹,“你既然一年半以来看了这么多家医院也没看好,说明它自己是不会恢复的。你已经在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了,风险概率会很小的。你这个积极求医的状态很好。”
“好,明白了。”我拿起笔,在几份文件上签下自己和母亲的名字。
对于开刀手术,我并不害怕,只是有些担忧:如果手术之后还是没有恢复,或者变得更糟,该怎么办?一次简单的健身房训练受伤,怎么还变成难住积水潭骨科大夫的疑难杂症了呢?说不定还能为推动我国足踝科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打着厚厚石膏、被消毒水染成酱油色的左腿放置在蓝色抬高垫上,握着止痛泵玻璃瓶、扎着针的左手抱于胸前,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奋力向右上方伸去,企图把一只电脑充电器插入墙上的插头。“砰”,一声巨响标志了行动的失败,沉重的充电器、转换头、鼠标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无奈之下,我只好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请求护工阿姨的帮助。
于是,我终于得以将电脑架在胸前,开始写这篇日记。
昨晚在决定做手术后,妈妈一直在微信上疯狂轰炸我,说她临时联系到一个老中医,让我不要做了,先去试试中医正骨。又让其他亲戚接连电话我,劝说我不要手术。
我不理解,为何一年半以来她并未对此事过多关注,却在手术前夜临时找到一个中医,让我不要任性,听她的放弃手术。我只好说:“我可以理解你很担忧风险,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也是我自己看了全国各地五六家医院后找到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字是我自己签的,我也会自己负责。”
因为我偷瞄了手术排位,自己排在最后一个,网上说术前两小时才需禁水,所以早上我还是没忍住抿了几口水(大家不要学我)。谁能想到,早上八点半,一个师傅进来说,“我来接你去手术了。现在赶紧去上厕所。”和护士确认了这几口水不会影响手术后,我又喷了一些鼻炎药,以防手术时鼻塞喘不过气。“你的家属呢?麻醉需要家属签字的。”“我没有家属……”
我躺上了铺着深绿色被子的移动床,被推去手术室。一路上,我不安分地梗着脖子东张西望,看到墙上的标识从足踝科住院部,逐渐到四层大厅,南楼麻醉室。另外两个护士开始麻利地帮我脱去上衣,戴起头套,输上盐水。广播播放着“XXX的家属,请到麻醉室签字。”“你家属没来吗?”护士问。“来不了。”我说。于是我没有签字,直接被推进了手术室。
浅灰色的推拉门上写着26,大门缓缓打开,因为冷和紧张,我感觉自己开始手脚冰凉。出乎意料,手术室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整个空间包裹着清新和煦的淡绿色挂板,墙和天花之间看不到折角,是圆润的弧面。从墙上伸出许多白色伸缩臂支撑着的显示屏,宛如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手术室里放着轻松的民谣歌曲,各式各样的仪器和管子包围着中间的小小手术台。几个不同角度的圆形手术灯挂在头顶,不锈钢几何结构闪闪发亮。手术室里有六七个人,欢声笑语地闲聊阳性故事。
“麻醉了啊,你多重?”女医生的声音打断了我参观的目光。
“44公斤。”
“你也太瘦了吧,营养不良啊。倒是好打针。”
因为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内裤,盖着薄薄的单子,我一直冷得瑟瑟发抖。加上不可避免的紧张,我感觉身体一阵阵痉挛抽搐,口罩也被淌出的清鼻弄湿。我想起从小到大每次重大考试、面试、登台前,我也是这样手脚冰凉,微微发颤。我咬紧了牙齿,希望止住颤抖。
麻醉师让我蜷曲起身体,另外一个医生按着我,麻醉师开始在我后背上打麻醉。有些钝钝的酸痛。之后又在我左腿窝里打了一针。
腿部开始酥麻沉重,但触碰时仍有感觉。我担忧,“我的腿还有感觉,等下手术也会这样吗?”麻醉师说:“当然,你又不是全麻。有感觉,但没有痛觉。”医生一层一层地把我的左脚刷成酱油猪蹄。
“我还是很冷,可以再多盖点吗?”我请求。
“你不会发烧了吧?”麻醉师有点紧张。
“没有,我刚量过体温。”
我又被压了一层深绿色被单。之后,一个包裹着绿布的小架子被放在我胸前,用来阻隔视线。
“我们会先试试修复你的筋,如果效果不好,再动骨头。”主刀医生说。
我意识清醒地躺在床上,胳膊被固定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姿势。我听到另一拨医生们在聊天。“儿童医院有几个孩子,送过去48小时就没了。”“万一阳了只能自己去住酒店了,现在住店不看核酸了。”“迟早大家都得阳……”
过了一会儿,主刀医生来找我商量:“我们已经把你的筋拉到和右边一样了。你受伤后粘连了,筋全长到一块去了,一大团,我们已经清理好了。你要是能保证术后好好康复训练,我们就不动你的骨头了。”“我好好练”,我连忙表态,“别动骨头。”“好的。你关节还有点损伤,我们再给你稍微修一修。”医生又回到了床尾,继续手术。
我还在思考麻醉剂什么时候能让我睡着时,医生过来向我示意,“已经做完了。现在给你打石膏固定。”他又再三强调康复训练,“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练,不然就白做了。你可以在我们院康复部做,不过他们已经阳了一半了,也可以在外面的康复中心做。”
在麻醉等待区,我看见旁边被裹住全身、只露出圆脑袋的人在和我打招呼:“这么快就做完了?”我辨认出圆脑袋是前几天一起做检查的内蒙古大叔。我们像两只蚕宝宝一样扭着脑袋聊了几句。
被推回病房后,师傅把我翻到侧面,在我身下垫了一张滑板,随后轻轻一推,我便稳稳当当地滑入了病床。随后,师傅抬升起病床两侧的围护栏,把我像婴儿一样圈在中间。护工阿姨帮我垫上了下肢抬高垫。
至此,我终于有了一些病人的样貌,护士姐姐也对我温柔起来,帮我挂上了头孢输液袋。

昨晚一宿未眠,今天筋不痛了,开始伤口灼痛,像针扎火燎,关节一跳一跳地胀痛,好像有什么小生灵要破卵而出。太疼了休息一天,以疼凑字。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昨天下午感觉有些发热。我跟查房护士说,可以帮我量下体温吗?说出这句话后护士和病友都陷入了紧张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戴着一次性手套的护士在我床上丢下一只温度计。我一量,38.5,确实发烧了。我又拿出自带的抗原测试,出现两道杠的刹那,我竟然一阵轻松。该来的总会来。
我给护士台打电话,“我刚自己测了抗原,是阳性。”护士没说话,沉默一会儿说:“现在也不让测核酸了,谁也说不准什么情况,你就自己多喝水多休息吧。”医院药房关门了,而且药房也没有任何退烧感冒药了,善良的病友施舍了一片布洛芬,但是没什么效果。经过三番五次的央求,护士给我打了退烧针和止疼针,早上退烧了。护士几乎不再进我们病房,也没有隔离我。我想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可能已经阳了大半了……
值班的男医生对我避之不及,跟我说话都远远站在病房门口。我因为下不了地,呼铃想叫护工阿姨帮忙上厕所。男医生接到后站在门口远远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那你上啊。
我当时一直38.7度,浑身无力,伤口撕裂痛,我说我发烧而且伤口疼不能下地,我也没有双拐,需要阿姨帮忙。医生说,发烧难受正常啊,谁发烧不难受啊,伤口疼也正常啊。我最后几乎带着哭腔请求,请帮我叫下护工阿姨,我需要她帮助我上厕所,可以吗?
今天早上,查房医生像溜冰一样进来转了一圈,就迅速滑出了,我甚至一句话都没问上。我费力地用嘶哑的嗓子喊:“医生,我今天出院,要换药吗?多久复查?什么时候开始康复训练?……”还没说完他们就溜到了门口,头也不回地说,“出院时都会通知你的。”话音随风飘远,人影已经消失在远方。
后来我还是被转移到了一个空病房。我听见护工和护士经过我的病房时讨论,这就是那个阳性?别进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边的卷云,等待妈妈来接我出院,没想到她错过了飞机。我只得临时找了两个阳性朋友来接我(找没阳的不厚道)。同学妈妈租了轮椅和双拐,把我送到出租屋。我计划再待一个月,复查完再回家。
晚上,妈妈到了。我又烧了起来,加上阳了之后显得愈发剧烈的伤口撕裂痛,退烧药和止痛药又不能一起吃,一晚上都在翻来覆去没怎么睡着。
白细胞:又是下肢伤口又是呼吸道病毒,你是要累死老子吗?双倍工作量,要加薪啊!
我:辛苦了辛苦了,这不是一石二鸟,提高效率嘛。
身体:不公平啊,本来手术和新冠是两次假期,结果赶一块儿,叠加成一次了?
我:攒一票大的,正好休到年后。
左脚、肠胃、头、嗓子、鼻腔一起:可是我们都很疼啊!
我:疼痛只是一种刺激,一种感觉,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树木抽芽,竹笋拔节,羽翼生长,疼痛永远孕育着新生呀。

阳之后的流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加上我的伤口还需要痊愈,身体难受,术后康复也困难,折腾了很长时间。
12月22号,我和心理咨询聊天,把心理咨询师整哭了。
聊天的主题是在说疫情这三年,感觉自己一直在漂泊流浪,随波逐流,大部分时间和力气都用来对抗意外和痛苦。2020年以来,遭遇过疫情裁员、滑雪摔失忆、健身受伤、家人腰椎骨折,今年以来一直辗转求医的同时艰难地做独立艺术家,却又遇到上海封城四个月,全国各地封控,最后在封控的美术馆里打着地铺做完了作品。
一个人来北京手术却又赶上最动荡复杂的时期,北京封城,医院封院,酒店出现阳性被封,连夜逃出后借宿同学家等待,终于等到政策放开,进院做完了手术却感染新冠高烧不退,双重折磨。
最近妈妈来照顾我,妈妈也阳了,我们两个都疼痛无力,状态很差,几乎难以互相照顾。爸爸在十几年前和妈妈离婚后就与我生疏,之前说出院要来看望我,听说我阳了之后,就再无音讯。
之后说起了我在上海封城期间企图自杀的经历。在上海独自隔离四个月期间,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抑郁加重,多次出现自杀自残的倾向。有一天,我在极度崩溃的状态下去厨房举起菜刀想要割腕,在割腕前还下意识地用酒精喷洗了刀面。但我没下去手,害怕自己力气不够虽残不死,于是我出门打算换一种死法。
我们小区当时虽然封控,但有一条内部河道。我整个身体坐在石质围栏上面,看着下面碧绿的河水和水中长着青草的小洲。我想,如果我跳下去,会顺着水流被带走吧,不知道水够不够深,水流够不够急。
正在我凝神望水的时候,一个大叔从这里路过,突然和我搭讪,“你是在看水鸟吗?”接着大叔抓着我开始闲聊,并没有撤退的意思,一直聊了很久很久。从各自的工作聊到附近开着的超市和疫情新闻,聊完之后我也不想自杀了,就回了家。
说到这里我发现视频会议里心理咨询开始捂住了嘴,之后不住地抹眼泪。“感谢那个不认识的大叔救了你”,她哽咽着说,“如果你当时死在了那条河里,我的一部分也会跟着死去的。”
“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活下来了,而且你还在继续做作品,参加展览,这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三年,大家都只是活下来了而已。即使你羡慕很多人有你没有的东西,稳定的事业和感情、和睦的家庭,但这三年你深深了解到这些东西有多么脆弱。你熬过了这三年,你的挣扎是多么带劲儿,多么富有生命力。”
“你的三年没有白费,至少你保全了自己。之后,你可以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所以我之后还会继续选择冒险的生活;也可以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所以我想省省力气,选择安全一些的生活,这没有对错。况且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说,这三年的极端体验,或许也能成为你的素材和养分。”
结束咨询的时候,北京冬日午后的阳光正好照进屋内,照在我用以打发时间的画笔和油画棒上面,照在我戴着支具的肿胀左脚上,我的双拐在金黄色的墙面上投下细细的影子,反光里映照着夕阳。
我在最不确定的时代、最不安分的年纪,选择了最不稳定的事业、困难重重的感情、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我的飘零是一种必然,却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命运,因为在这艰难的自由中,有我始终不能放弃的爱与热望。
我会好好养伤,认真康复,我会专注地恢复力气,恢复信念,不再自我谴责和自我伤害,我会像一棵树一样虔诚地等待春天到来。
我对自己说。

医院康复大厅外的走廊上,新的一年加油!

原标题:《我一个人在北京住院手术,术后第一天阳了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