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类寿命的增长是否存在“海弗利克极限”?
【编者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件事比死亡更古老、更神秘、更无解,我们对其讳莫如深,仿佛只是触及一鳞半爪,都足以让它从黑暗中暴起伤人。可死亡从来不应是未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我们对死亡的疑问越来越多:生命为何有限?生死如何界定?死亡能否逆转?怎样超越死亡?我们是否拥有死亡权?如何商讨临终?谁才是有权拔下插头的那个人?网络社交怎样影响死亡……
在《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一书中美国心脏病学会青年研究者奖得主瓦莱奇博士以亲身临床救治经历结合医学、进化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认知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观点,直面“禁忌”话题,详述人类在死亡相关议题研究方面的点滴变化与前端进展。本文摘编自该书第2章,澎湃新闻经后浪出版授权发布。

历史上,人类寿命基本保持稳定。我们人类,更精确地说是人属(Homo),已存在了约200万年,但直到2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才在非洲出现。约19万年前,人类开始过上狩猎采集的小团体部落生活,继而学会了农耕和畜牧技术。尽管文明进步了,但那时的人们无法从实质上改善健康状况,他们的生命中遍布难以预料的危险。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童年时幸存下来,而青年人和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几乎相同。此外,分娩是发生在一个女性身上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也是当时女性的死亡率远高于男性的原因。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设法延长了自己的寿命: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犹大国王的平均寿命为50岁;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150年,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平均寿命为60岁。然而,这更多是统计概率的产物,而非有价值的干预措施进行干预的结果。
1800年,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这与数万年前农耕时代的人们平均寿命为 20~25岁几乎没什么区别。在此之前,平均寿命每年都会有显著的波动,曲线的上升和下降就像地震时震波图呈现出的笔画一样起伏不定。死亡不仅对个人而言是随机的,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即使是富人对死亡也无计可施,因为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与收入并不挂钩,富裕国家的情况与贫穷国家同样糟糕。
但也就是从这段时间起,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稳步上升,这是历史中任何时期都不曾出现的。每一年,人类平均寿命都会增加大约3个月。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这种增长,部分国家尤为明显,如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从1840年开始,这种增长几近线性。不仅是平均寿命,人类的最高寿命也在增加。过去,根据年龄可以划分出一个呈金字塔形的人口分布,年轻人数量众多位于底层,而老年人数量较少位于塔顶,但按照这种增长速率,这一图形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变为矩形。
我们如何实现了这种转变?第一,人类寿命延长主要得益于儿童死亡率的急剧下降。这是因为,例如进行卫生分娩、规范卫生操作、改善公共卫生、提高营养状况、加强产妇教育、提高产妇保健等公共卫生措施的增加,使得儿童死亡率大大降低。此外,由于抗生素和疫苗的出现,过去对儿童有巨大危害的传染性疾病已在发达国家销声匿迹。第二个重大改变,是中年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下降,这得益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暴力事件致死率大幅降低。这一减少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抹去所有50岁以下的死亡人口数据(约占美国全部死亡人数的12%),平均预期寿命只会再增加3.5年。
直到最近,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才开始在减少老年疾病与死亡风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令1969年后最高寿命的增长率几乎是过去几十年的3倍。令生物学家、人口学家及生态统计学家困扰的是,我们能否维持这种指数式的寿命增长?更重要的是,人类寿命是否存在“海弗利克极限”?
一些科学界人士表示,人类寿命不断增长就已经证明了不存在这种上限。但更多的人相信,人类寿命存在一个更高的极限,这其中就包括列奥纳多·海弗利克本人,近期他这样写道:“衰老过程是所有分子(包括多数原子)的共性,那么对衰老横加干预,大概等同于违反基本物理定律。”许多科学家现在开始相信,我们的寿命或许正在接近平台期。据估计,即使消灭了所有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人类的平均寿命预期仍不会超过90岁。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无任何疾病的人类寿命平均可达85岁,而数学建模的结果表明,人类的最高寿命可达126岁。
詹妮·卡门打破了过去我们所设想的120岁的人类寿命极限,她的寿命与她去世之后数学建模得出的新极限相近,但仍有许多人期待这一数字能得到验证。百岁老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约有30万百岁老人,而这一数值到2050年时将增长10倍。值得一提的是,寿命的这一变化完全是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如环境的改善,以及对疾病的控制等。这就如同我们一直在净化细胞生长的培养液,而不是改变细胞本身。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从40岁增加了1倍,达到80岁左右,这意味着基因变化在我们生命的可塑性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对我们人类而言,普遍高龄其实是一种相当新鲜的体验,也蕴含着耐人寻味的进化意义。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从未经历过绝经后的生活。站在进化的角度来看,绝经会被认为是生殖适应性的巨大失败:对于进化生物学家来说,一个无法生殖、无法帮助物种延续的有机体对族群进化有什么益处呢?科学家曾一度认为,绝经后的生活是人类独有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个错误观念。虎鲸、秀丽隐杆线虫和长冠八哥像人类女性一样,有着钟形的经期生育曲线,且有老年期生命。
然而,现代女性的生命有大部分是在绝经后度过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类寿命显著增长;二是与分娩相关的死亡率大幅降低。此外,女性普遍比同龄男性长寿,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增长更加明显。事实上,在超级百岁老人,即超过110岁的老人中,女性以35∶1的比例远远多于男性。
进化生物学家已经证明,在过去被认为是进化异类的绝经后女性正是人类长寿的关键所在,我们的长寿可能要归功于我们的祖母。在狩猎采集时期(甚至近代),祖母通过帮助女儿抚养后代,将年轻的母亲从为新生儿收集物资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可以专心怀孕生子。1966年,有学者首次提出了“祖母假说”,而数学模型现已证明,这一假说正是人类寿命从猿类寿命迈向现代人类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虎鲸这种与人类寿命相似的哺乳动物中,祖母对延长寿命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对抗死亡的进步已经延长了老年人的寿命,也对生命结构的另一端——儿童——产生了深远影响。人口统计学家指出,父母早逝的孤儿数量已经有所下降。孤儿院过去不仅在狄更斯笔下的英国随处可见,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究其原因,正是各年龄层级的人们死亡率都非常高。人类漫长的童年期一直都吸引着生物学家的注意,尤其是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后代成熟得最晚,依赖他人的时间最长。人类大约在断奶后14年才会进入性成熟期,甚至更久,而我们正处于进化中的近亲黑猩猩只需要约8年。
最初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认为,由于人类的脑容量更大,处理的任务更复杂,比如打猎,所以需要更长时间来培养承担这些任务所需的技能。但是,当人类学家分析了全世界原始部落的打猎觅食行为后,得出的结果令人十分吃惊。对一些原始部落(如靠近澳大利亚的梅尔岛的梅尔人,以及坦桑尼亚的哈扎人)进行观察的结果表明,儿童与成人的觅食能力相差无几。即使存在差异,也是因为儿童的体形较小、力量较弱,而非生存所需的智慧技能有差异。事实上,训练的作用尚不明确,比如哈扎人中,训练较少的儿童与接受严格训练的儿童寿命几乎相同,这表明童年期的长短与生存技能强弱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目前更受支持的理论是,人类儿童的依赖期长度是由我们的寿命延长所决定的。而寿命的延长与怀孕年龄推迟有关,跨物种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母亲怀第一胎的时间越晚,子女的寿命就会越长,所有物种都是如此。社会学家用“资本继承理论”(inherited-capital theory)来解释这种现象,即父母积累的技能与财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为子女更高的生活质量。关于人类的童年期和依赖期为何比其他物种更长,另一个原因就没有这么大公无私了。限制儿童参与成年人的工作生活,可以减少成年个体在社会中面临的竞争,从而展现出成年人的进化适应性。所以,祖母对孩子的溺爱或许只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让孩子晚些成熟,而不是真的考虑到孩子的利益。
尽管科学家还在讨论长寿的利弊,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延长寿命中获益,哪怕我们已经把长寿视为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中生存的正当权利。即使在美国,人们的预期寿命依然存在巨大差异,现代科学与医疗卫生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与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相比,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较低,并且这种差距正在逐渐拉大。美国女性的平均寿命低于智利女性和斯洛文尼亚女性,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医疗花费与人均收入都低于美国。美国男性 和女性的寿命都比他们的加拿大邻居短,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资源——仅匹兹堡市(美国人口排名第61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仪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加拿大的总和。
在美国,一些县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超过了日本和瑞士,另一些县的人均预期寿命却与阿 尔及利亚、孟加拉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趋近。美国男性预期寿命最长(83岁)的县是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而男性预期寿命最短(64岁)的县是西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道威县,但其实两地相距仅约482公里。社会经济差异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差距:费尔法克斯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109383美元,而麦克道威县仅为22972美元。此外,种族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非裔美国人的寿命比美国白人少3.8年,虽然这一差距与1970年的7.6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依然较大。然而重要的是,收入与种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有人会纠 结于这二者的影响孰重孰轻,但必须指出,麦克道威县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白人,比例达89%,而费尔法克斯县仅有53%是白人。
社会经济差异将会影响人们的健康,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是现代的产物。对各国19世纪以来预期寿命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与他储存了多少块金砖毫无关联。事实上,这一影响差距直到20世纪才初露端倪,不仅在富国和穷国之间愈发悬殊,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美国国内所表现出的预期寿命差异就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现代死亡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不平等性。布罗克顿,一个距波士顿仅1.5小时车程的贫穷小镇,这儿的人们依然在以过去的方式死亡。到医院就诊之前,他们没有任何病历,没有做过任何检查,也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离开医院时,一席白布裹住他们的身体,一直盖到眉毛。医学进步塑造了现代死亡,而社会经济变化对现代死亡的塑造力度完全不亚于医学进步。
也许,无论是显微镜还是死亡率表,我们从中学习到的关于死亡的知识都是同等重要的。对我而言,细胞动力学中能学到的东西并不只是研发新的靶向疗法或是抗衰老特效药。细胞的死亡展现了一种超凡的社会意识。一个细胞绝不会在孤立的情况下死亡,而是会在同伴的清晰视野中死亡。一个细胞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死亡,而是被一种更聪明的力量控制着,更高级的机体知道什么时候细胞会对自身和身边的环境造成威胁。细胞比我们人类更清楚“客居过久遭人烦”的下场。虽然我们人类渴望永生,但对细胞而言,永生是最可怕的命运。
人类对抗死亡、延长寿命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谁也无法预料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结果如何。面对现代死亡,我们最清楚的不是人们因何死亡,也不是何时死亡,而是在哪儿死亡。在大多数人最后的死亡场景中,灰白是主色调,身边弥漫着消毒剂的味道,警报声充当着配乐,胡乱敞开的病号服是他们的行头。在人类的历史上,死亡从未像过去几十年一般远离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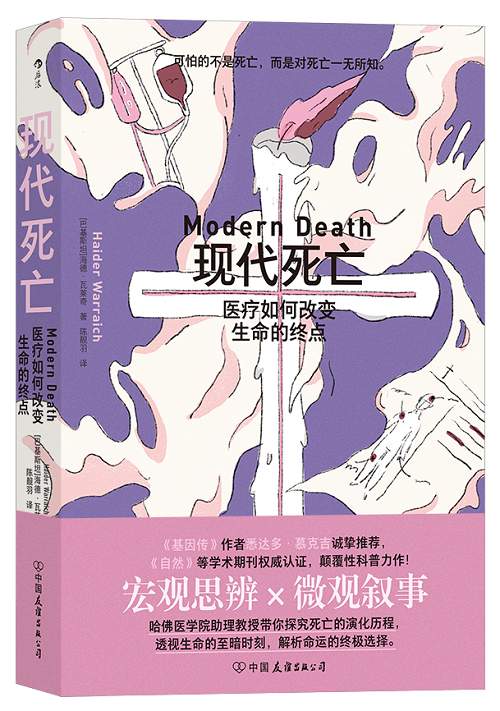
《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巴基斯坦]海德·瓦莱奇(Haider Warraich)著,陈靓羽译,后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年11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