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年度阅读︱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寻找故事
或许现实总会让人失望,我们只好在历史中寻找重生的希望。对于不断遭遇挫败的一年来说,不关心宏大叙事、不关心前沿动态、不关心个体命运。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寻找故事,最容易忘记磋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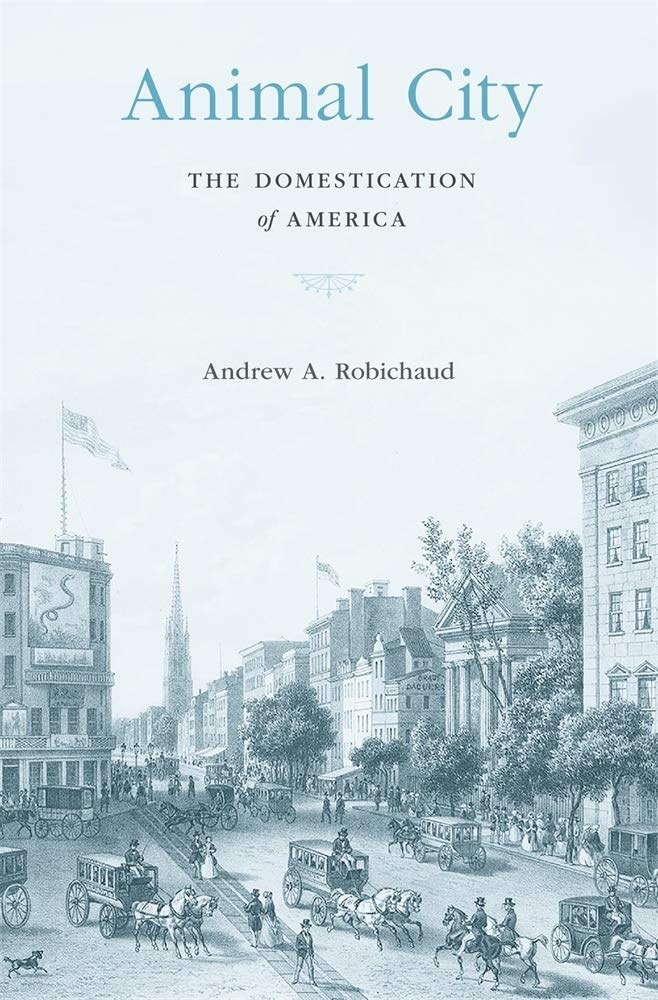
Animal City: The Domestication of Urban America
历史是发生在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的人间故事,也许这样的观点,让历史学家们总是忽略动物在历史上的角色。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等新思潮的风起云涌之下,西方史学界对于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方法论展开了反思,他们尝试突破人类社会来书写历史,将动物、植物乃至非生物因素纳入研究范畴。有的研究者就此提出了史学研究正在经历“动物转向”的说法。与史学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环境史在动物史研究中走得更远,这很容易理解,毕竟环境史致力于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研究者以人与动物关系为切入点,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城市历史研究也不应忽视动物,因为无论作为食物来源还是孤独陪伴,动物在城市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直到十几年前,几代城市历史学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动物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晚近的研究中,安德鲁·罗比查德的《动物之城:城市美国的驯化》(Andrew A. Robichaud, Animal City: The Domestication of Urba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则为城市化的过程和后果提供了全新的、从动物出发的视角。《动物之城》主要关注的是19世纪的旧金山和纽约市,全书共7章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市政当局对作为食物来源的动物的早期监管。城市中的动物曾经与人一样,都享有在城市公共土地上漫游的权利,但与市民不同的是,动物的这一权利是慢慢消失的,这是市政监管的一部分。作为食物来源,动物与城市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供给与消费,本书就谈到,纽约的牛群以廉价酿酒厂的醪液为食,引发了城市改革者们要求监管牛奶的努力;类似的情况在旧金山同样存在,本书接下来重点介绍旧金山的屠宰场改革以及市政当局和商界在市民的压力之下,逐渐将屠宰设施迁移到远离城市核心的郊外。在第二部分,作者将研究对象从动物转移到了与动物相关的城市社会组织。罗比查德调查了首先在纽约成立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影响,接下来追溯了该组织如何在仅仅两年后便在旧金山崛起,以及协会的优先事项因何从保护牛变为保护更容易在街头看到的马匹和宠物。最后,作者又将焦点放在了现代城市人更熟悉的狗身上,借助纽约地方法院的庭审记录,讨论了19世纪中后期纽约市民如何看待一个城市的悠久传统,即是否应该继续使用狗进行劳动。本书第三部分则进一步探讨动物与市民的关系,关注的是公共娱乐表演中的动物。在第6章中,罗比查德将目光投向了费尼尔斯·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创办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Barnum's American Museum)。这家博物馆以怪异的展品著称,包括所谓斐济美人鱼。罗比查德强调了纽约市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中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活动如何成功地减少了该博物馆为引人关注而对动物实施的暴行。在第7章,作者分析了旧金山的动物展览和动物园,以揭示动物在公众视野之外所承受的痛苦。以往,历史学家倾向于单独而不是共同研究这本书讨论的许多城市场域,包括奶牛场、屠宰场、动物园和博物馆。罗比查德则将这些场域收录在了一本书中,因为他认为,动物的经历是城市人共同创造的,而不是分割在不同场景之中的。尽管本书并不总是像作者努力的那样清楚地解释这个共同创造的过程,但他确实在各个章节中证明了,城市居民对他们如何以及何时表达对动物困境的担忧,其实受制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总是以一厢情愿的想法来解释动物的经历,并且更愿意容忍发生在视线之外的虐待动物的行为。本书讲述的故事,例如城市牛车在旧金山街道上轰鸣而过,将有助于扩展美国城市化的传统叙事。以动物为出发点的研究,将持续改变历史学家对19世纪城市的理解方式。对于从不养宠物的人来说,原来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动物离我们并不遥远。人类的城市故事,理应是一部人类与动物共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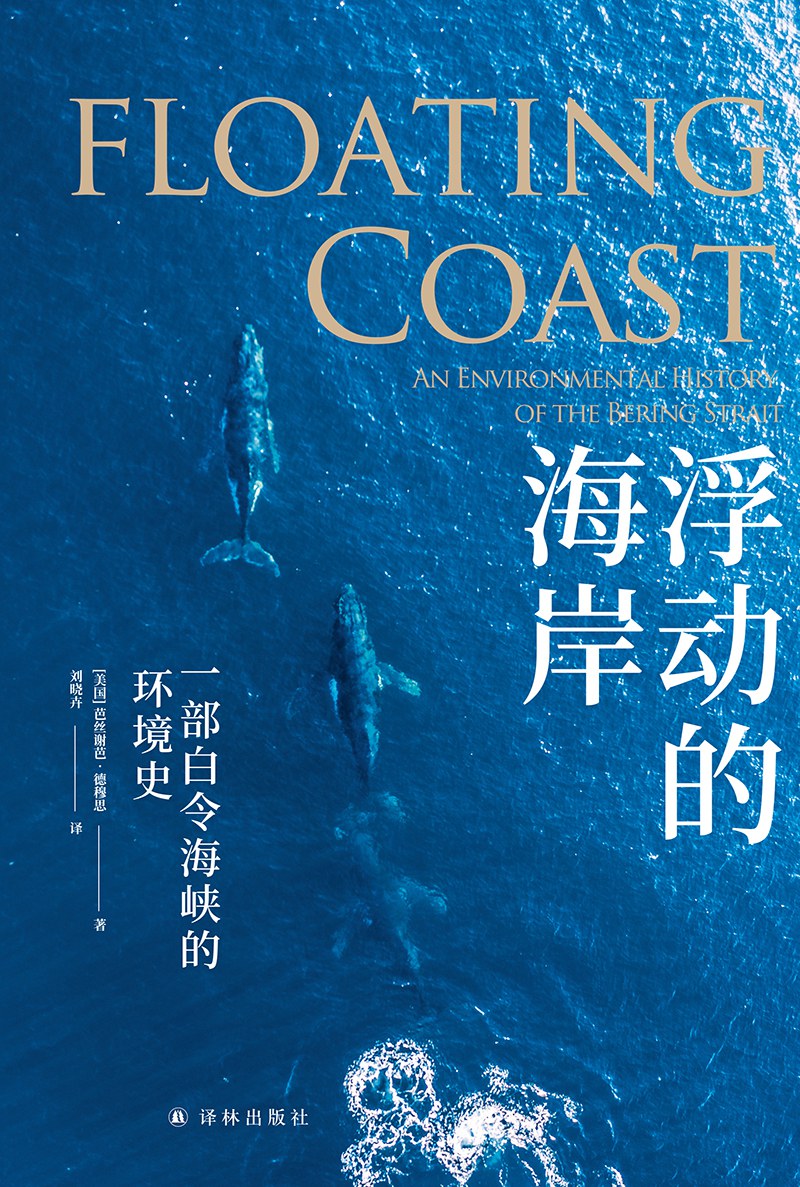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
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二者经常被分开处理,要找到一本整合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书并不容易,直到发现芭丝谢芭·德穆思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中译本由刘晓卉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关于白令陆桥、俄罗斯和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周围的陆地和水域的第一部综合的历史,不仅包括活跃在这里的因纽特人、尤皮克人和楚科奇人,还包括他们捕猎的鲸鱼、狐狸、海象和驯鹿。德穆思讲述了白令海峡175年的历史,涵盖了三种不同政治制度下原住民主权的丧失、对生物体的过度捕捞和食物链的解体,以及远离北极地区的战争和经济活动对北极的影响等问题。边缘地区即便如北极,也持续上演着一幕幕人类和自然互动的故事,本书的魅力正在于将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讲述了该地区社会环境系统的完整故事,探讨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苏联对该地区的干预,如何将生态财富转换为资本和国家实力。自然与人类是德穆思笔下白令海峡故事的两条线索。在前者,作者着重探讨了捕鲸行为的影响。本书汇集了首次来到白令海峡的捕鲸者的日记、捕鲸船队的日志、鲸鱼航运清单和其他重要史料,这些材料读起来既真实又令人心碎。依靠它们,作者详细描述了捕猎的鲸鱼如何被提炼成油,发掘了捕鲸者对鲸鱼数量下降的一手观察。尽管捕鲸者也在感慨自己对鲸鱼的猎杀,但在资本的诱惑下,捕杀并未停止——该地区弓头鲸的数量从1850年的5万多头锐减到20世纪20年代的不到2000头。当鲸鱼数量锐减,捕鲸船便将目光转向了海岸上的海象、驯鹿和狐狸。与这些捕猎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原住民的生活,他们世世代代以弓头鲸和其他北极生物为生。在德穆思笔下,你能读到随着鲸鱼越来越难获得,饥饿在白令海峡加剧;你能读到传教士来到这里,逐渐改变了白令海峡两岸原住民社区的宗教图景;你还能读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政治边界的扩大对原住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必须选择在边界的哪一侧居住,比起自然,政治在切断联系方面的作用更大。《浮动的海岸》使人们能够深入审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通过架设环境历史的镜头,德穆思巧妙地审视了这些不同的经济体系如何头也不回地推进自己的核心利益,却同时将最脆弱的群体抛在后面。本书文字流畅、译笔优美,可以从头读,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篇章单独阅读。无论从哪一页开始,你都能体会到作者将一个长期被忽视地区的深层次的环境与文化历史真正地整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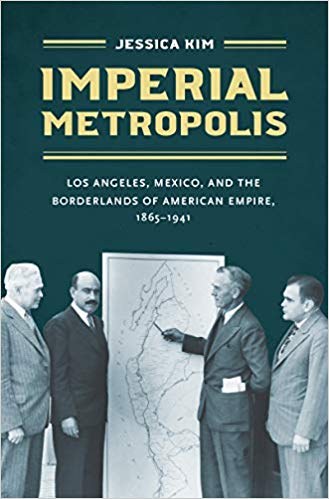
Imperial Metropolis: Los Angeles, Mexico, and the Borderlands of American Empire, 1865–1941
近十几年来,美国媒体和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美利坚帝国”的研究和讨论。一方面,研究者将美利坚帝国视为一个历史现象,从帝国的兴起、表现形式、政策活动以及影响等不同侧面对美利坚帝国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帝国也被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框架,学者们在“帝国”框架之下反思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美国和这些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帝国研究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框架,着力探讨美国对其主权领土之外地区的影响力,与全球史、跨国史等新视角一起,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历史学家杰西卡·金也加入了帝国史讨论的队伍,不过她关注的是帝国的内部,《帝国大都会:洛杉矶、墨西哥与美利坚帝国的边界,1865—1941》(Jessica Kim, Imperial Metropolis: Los Angeles, Mexico, and the Borderlands of American Empire, 1865–194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9.)一书以洛杉矶为研究对象,将这座西海岸大都市视作美利坚帝国构建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许多洛杉矶史研究类似,金的研究抛弃了洛杉矶是“没有历史的城市”的刻板印象,通过从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三种不同的殖民主义入手,追溯了这座城市的形成过程,并探索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这里的种族、移民和土著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金之所以将洛杉矶定义为“帝国大都会”,是因为在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关系中,洛杉矶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边境经济中财富和权力集中的节点”,并且“以不同于民族国家的规模运作”。在研究中,作者关注的是一小群洛杉矶精英,包括《洛杉矶时报》出版商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和哈里·钱德勒(Harry Chandler);石油大亨爱德华·多赫尼(Edward Doheny),他是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出资人;以及投资商人刘易斯·布拉德伯里(Lewis Bradbury)和格里菲斯·格里菲斯(Griffith J. Griffith),他们建造了布拉德伯里大厦和格里菲斯公园的天文台。全书重点探讨了墨西哥革命(1910—1920)与洛杉矶这座距离美墨边境100英里的城市间的联系——墨西哥劳工和无地农民在当地政客的鼓动下如何夺取和侵占美国投资者声称拥有的财产、流亡的革命者弗洛雷斯马贡兄弟如何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煽动革命,以及不再致力于直接投资、而是以促进贸易和旅游为主的洛杉矶商人。权力关系是帝国史研究的主线,本书以经济权力为主题,大部分分析集中在20世纪前40年。但令人意外的是,这40年是美墨关系剧变的时代,美国在1924年《移民法》之后,是否将墨西哥纳入按照来源国的配额制度引起了广泛争议,但这些争议却没有出现在《帝国大都会》中。不过,本书仍旧是对洛杉矶、美国西部和美墨边境地区的历史以及美利坚帝国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洛杉矶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其实与遥远的墨西哥的土地与人民息息相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帝国大都会》为关注具有区域重要性但并非国家首都的城市,在塑造全球帝国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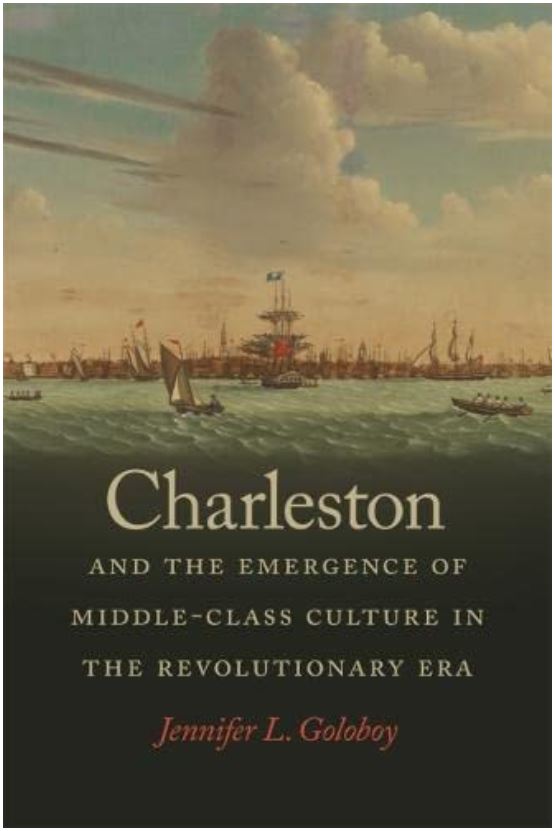
Charlest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iddle-Class Cul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南部城市是美国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奴隶制、棉花田,似乎天然地与城市南辕北辙。尤其是在19世纪以前,除了查尔斯顿,南部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没有其他城市了。对于南部城市的研究,也的确以查尔斯顿最为丰富。珍妮弗·戈洛伯伊的《革命年代的查尔斯顿与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崛起》(Jennifer L. Goloboy, Charlest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iddle-Class Cul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6.)就是其中之一。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查尔斯顿似乎不是研究中产阶级的好地方,因为这是一座满足种植园主需要和维护奴隶制的城市。但珍妮弗·戈洛伯伊却认为,查尔斯顿商人的生活和习惯为了解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史提供了新视角。与E. P.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相似,戈洛伯伊也从文化角度切入阶级的生成,只不过她讨论的是“中产阶级”这个比“无产阶级”更加模糊的概念,她所谓的“革命年代”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的时段。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包括卡尔·马克思、赖特·米尔斯等许多思想家已经做出过不同界定。戈洛伯伊则认为,“中产阶级的关键在于认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中产阶级是一种独特的、属于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家庭的文化”,“使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文化机制发生在会计室和客厅,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本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南部中产阶级形成于美国革命之前而非美国内战之前,标志就在于他们清晰地意识到并表达出自己对于南部种植园经济的重要性。正是基于文化角度来界定中产阶级,戈洛伯伊的研究注意到了南部中产阶级的变化,本书从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而非静态的概念定义出发来理解中产阶级;同时,作者关注了中产阶级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戈洛伯伊指出,推动中产阶级文化出现和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她认为,在查尔斯顿,尊重和克制是殖民时代商业氛围的代名词,而喧闹的野心则定义了后革命时代,这样的变化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变化。革命的爆发和英军占领查尔斯顿冲击了城市原有的等级结构,中产阶级则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随着早期共和国时代商业氛围和制度环境的变迁,中产阶级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她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工匠属于中产阶级,但他们在革命年代里逐渐失去了这一地位,“大多数工匠发现越来越难以赚到足够的钱以留在中产阶级”。不过戈洛伯伊的研究似乎有未尽之处。在殖民时代,出身决定了社会地位;这种等级制度与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否存在冲突?本书涉及的时期正值奴隶制强化、奴隶贸易死灰复燃的时代,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透过戈洛伯伊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南部,除了种植园主、小农场主和奴隶之外,还有一个与北方共享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内战前的南部不是前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与美国其他地区相隔离的独特地区,而革命之后查尔斯顿的故事,更不是一曲衰落港口的挽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