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赵英男读《法理学:主题与概念》|站在哈特的延长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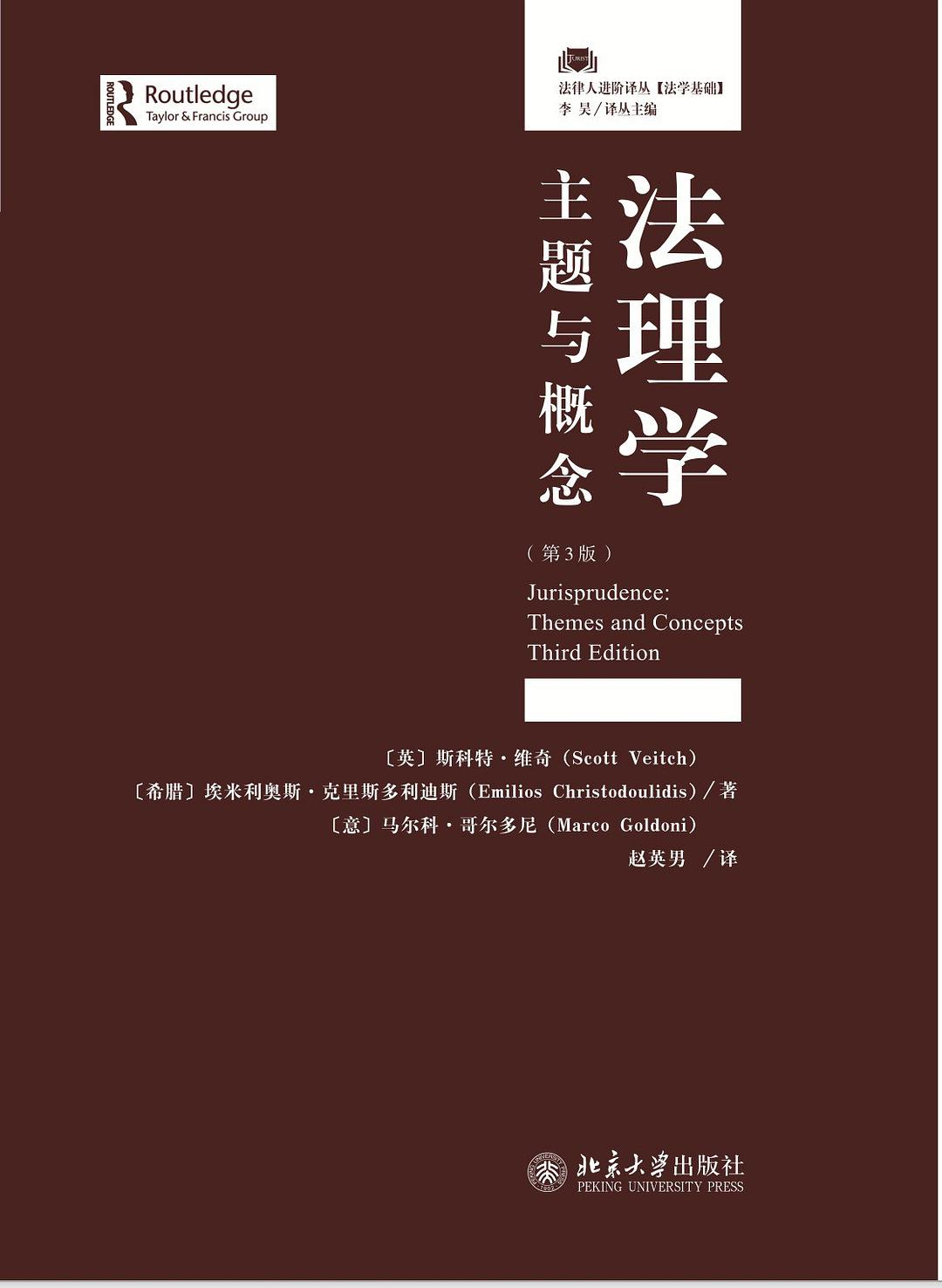
《法理学:主题与概念》,[英]斯科特·维奇、[希腊]埃米利奥斯·克里斯多利迪斯、[意]马尔科·哥尔多尼著,赵英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387页,69.00元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理学家赫伯特·哈特(H. L. A. Hart, 1907-1992)在他最知名的著作也是最成功的法理学教科书《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61)的前言中说道:一部法律理论著作并不是一部有关其他作品讲了什么的著作(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vii)。言下之意,法理学作品不仅应当具有融贯的立场与方法,还应当尽量避免对于他人观点的过多评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大学讲席教授斯科特·维奇(Scott Veitch)领衔推出的教科书《法理学:主题与概念》(Jurisprudence: Themes and Concepts, 3rd ed., Routledge, 2018,以下引用页码源自英文版)似乎完全违背了哈特的教导:这部著作不仅由多位英国新锐学者通力合作完成,而且竭力倡导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多元视角出发,唤醒读者对于法理学理论传统的自觉。这对强调以概念分析为基本方法的英美法理学主流范式而言,不啻于一种“离经叛道”。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强调多元视角,特别是将社会-历史视域融入法哲学研究的风格,依然位于哈特所开创的二十世纪现代法理学的延长线上。我们可以通过法理学在今时今日的发展现状来理解这一点。
法理学的昨日与今天
法理学与民法、刑法、宪法以及行政法等科目不同,并不围绕特定实在法展开,也不以注释和解读法律规范为核心内容。它甚至不同于法律史,并不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以及思想,而是更强调在一般层面对事物或概念的关联分析。比如,令法理学家津津乐道的问题,总是“法律是什么”“法律与道德关系”“道德的法律强制”这些相对抽象和宏大的议题。这种不以实在法为依归的研究进路,往往不利于具体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因此,法理学理论难用甚至无用的观点可以说不绝于耳。比如,中美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曾讨论法理学是否走向终结甚至已经“死亡”的问题(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2016年在《中国法律评论》发表了《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斯科特·赫肖维茨[Scott Hershovitz]2015年在《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讨论法理学的“终结”[The End of Jurisprudence])。他们不仅质疑这门学科对现实的意义,也反思这门学科的理论渊源、基本立场以及方法的价值。
概括来说,有两方面原因使得法理学在今天走入困境。首先,从一般层面来看,法理学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根据通常理解,法理学往往追溯至边沁、奥斯丁与哈特的所开创的传统。在该传统中,法理学或法哲学围绕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权威或规范性、司法裁判三个问题展开,但尤以前两者为核心。在讨论法律的概念或权威时,深受日常语言哲学影响的哈特将此问题转化为有关“法律性质”的分析。他认为讨论法律的概念或权威,就是讨论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强制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而要澄清这些关系,就离不开对于法律或者法律概念的本质必然属性的讨论。通过这种本质必然属性,就能够构建出在一切时空下都成立的法理论,进而解释一切有关法律的社会现象。哈特通过批判奥斯丁与边沁的学说所开启的这一分析法学传统,一直到今天都主导着法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pp.1-2)。哈特以降,无论是其拥趸,比如拉兹、马默、夏皮罗,还是其批判者,比如菲尼斯、德沃金基本都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研究。

哈特
但是随着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认知科学甚至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这种强调概念分析、提出本质必然主张的观点,渐渐就开始受到质疑。比如,当代法律现实主义者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认为,分析概念的用法只能更系统地了解我们的日常直觉,无法提出有关法律本质必然属性的主张;弗雷德里克·肖尔(Frederick Schauer)根据大量认知科学研究成果指出,法理学不应试图区分法律与强制,因为强制力是人们理解并遵从法律时非常普遍和常见的因素,忽略这一因素而认为其他某种事物是法律的本质必然属性,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这些简单的例子表明,法理学的传统理论资源和方法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批判,但全新的主导范式则尚未确立。这使得法理学在当下正经历着一段“迷茫期”。
其次,具体到我国语境中,法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其实际知识供给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我国法理学学科奠基人沈宗灵先生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解释法理学或法律哲学的研究内容时,引述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性质、目的、为实现那些目的所必要的(组织上的和概念上的)手段、法律实效的限度,法律对正义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历史上改变和成长的方式。”(《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简单来说,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现象本身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横向”关系。但在此之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是这样理解法理学定位的。
有学者考证,在1981年到1994年,法理学在我国往往被称为“法学基础理论”,这是因为1980年12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取得学士学位的条件之一,是确已较好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在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基础理论”的要求。在此影响下,当时的法理学学科被称为法学基础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法理学在我国被称为“国家和法权理论”。这一名称源自对前苏联法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此时,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纵向”关系,也即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论述来阐释法律。内容大体上包括原始社会中法律的起源、奴隶制社会法律、封建社会法律、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以及共产主义和法律的消亡。
当时的学者认为,讨论法律纵向关系的“国家和法权理论”这门学科,研究的是一般性的理论概念。这种“一般性”突出地体现为它所具有的“指导功能”。根据今天的研究成果,该指导功能具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意识形态的,也即这门学科中的一般理论概念运用到具体各个法律学科中,保证了这些学科的理论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第二种含义是技术性的,指的是这门学科中的一般理论概念适用于各个具体法律学科。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和法权理论”在当时被定位为所有法学学科的基础或总纲。更形象地说,如果我们想要界定当时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不妨参考数学中“提取公因式”的思路:各个部门法学科中提取出来的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概念、原理、方法就构成了当时人们对法理学内容的理解。
这一理解时至今日仍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在今天特别是我国语境下,学者批评或指责法理学“没用”抑或走入“危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这门学科产出的知识不再能够为各个部门法学科提供有效的指引。比如,当下法理学研究中讨论的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概念不仅无法与民法中相应概念与学说对接,反而有引发混乱、导致矛盾之虞。再比如,在《中国法律评论》专题文章“法理学应对危机的方式”中,有不少学者将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沟通作为法理学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径。法理学的基础地位及其指导功能,依旧是人们在今天对这门学科的期待,但也是必然会落空的期待:在法学各个门类发展成熟、大量法律法规不断涌现的今天,要求法理学可以涵盖一切法学理论问题,不啻于在现代社会要求一个人背下整本辞海,不仅不现实,其实也没必要。
千人千面的探索
法理学发展至今所遭遇的困境,使得许多学者特别是英美法理学家,开始逐步探索革新和拓展法理学研究的可能。比如早在1997年布莱恩·塔玛纳哈(Brian Tamanaha)就在《现实主义社会法律理论》(Realistic Socio-Legal Theory)一书中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对哈特之后以分析哲学为基础的法学理论展开了系统性批判。在2001年的《法律与社会的一般法理学》(A General Jurisprudence of Law and Society)中,他通过尝试整合法理学资源和社会学元素提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一般法理学框架,以便为更具体的经验研究提供参照。在其晚近推出的新作《法律多元主义阐释》(Legal Pluralism Explained, 2021)和《法律理论的社会学方法》(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ories of Law, 2022)中,他甚至提议法理学研究应当摆脱对法概念的关注,不再将哈特所说的这个“恼人不休”的问题视为法理学的核心议题。
前文提过的布莱恩·莱特则主张法理学乃至法学都应当经历一次“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即全盘接受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在有关法律解释、司法裁判等议题上的研究成果,抛弃陈旧的形而上学思辨和基于直觉的断言。罗杰·科特瑞尔(Roger Cotterrell)结合自己的社会学背景提出法理学应当是一种“百衲衣”(bricolage),法理学家不应探究有关法律概念的本质必然属性,而是借助自己已有的理论资源和感兴趣的话题,试图提出能够增进我们理解现实中各式各样法律现象的理论。易言之,法理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事业,而是面向司法实践、解决法律问题的学科,因此应当得到“社会学化”。
同时,仍然遵循哈特所开创的传统的法哲学家也展开了反思。法律与道德哲学家利亚姆·墨菲(Liam Murphy)在《法律的构成》(What Makes Law, 2014)一书中恰恰延续哈特的理论方法与资源,澄清并证明了法哲学当下有关法律与道德、法律规范性的讨论误入歧途,陷入了无谓争论。法哲学家斯科特·夏皮罗(Scott Shapiro)提议应当重新思考法理学与法学(部门法研究)的关系,并尝试参照元伦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将法理学视为对法律命题的意义或真值条件的形而上学反思。斯科特·赫肖维茨(Scott Hershovitz)尝试将法理学吸纳入分析道德推理的道德哲学,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与尼克斯·斯塔夫劳波洛斯(Nicos Stavropoulos)则希望运用当下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学重构法理学的理论框架。
对于这些改变传统范式的声音,传统法理学阵营当然不是没有回应。比如,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在一篇题为“一般法理学还剩下什么?”的文章中辩护了哈特所开创的传统。此外,这些有关革新法理学的讨论虽然火热,但却并没有成为共识。大多数情况下,突破现状的尝试往往不会受到积极评价。比如,雷蒙德·瓦克斯(Raymond Wacks)在他的教科书《读懂法理学》(Understanding Jurisprudence)的结语中写道,有朋友建议他删去书中与法哲学无关的内容,以免使学生偏离正轨(Understanding Jurisprudence: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Theo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17)。布莱恩·比克斯(Brian Bix)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法理学:理论与语境》(Jurisprudence: Theory and Context)虽然内容广泛、主题多样,但对法哲学之外的学科与方法并没有太多关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法律现代性问题做出经典论述的韦伯,几乎只以脚注的形式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出现;对西方法律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法学派,只在五个自然段中得到非常浅显的评论;而涂尔干有关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述,则更是在此书中“芳踪无觅”。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看到法理学发展至今时今日的样貌:一方面,许多学者认识到传统研究范式,特别是以概念分析为主导的法哲学研究,有研究视野过于狭窄、忽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倾向;但另一方面,法理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势力强大,似乎认为有关法律现象的哲学分析与社会科学研究势同水火,难以兼容。
哈特的误会与亚当·斯密的雄心
法理学领域如今出现概念分析与社会科学方法“双峰并峙”的局面,根源还是二十世纪法理学的巨擘赫伯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明确指出,自己的作品既是一部运用概念分析的“分析法学”著作,但同样也是一部“描述社会学”作品。表面来看,哈特似乎认为两种研究方法是彼此兼容的。但是在其他作品中,哈特更明显地流露出对于社会科学的冷淡态度。他认为,“学生花费在法理学中的有限时间最好投入到分析性研究而非社会学法学之中”,因为“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是相对年轻的学科,概念框架并不稳定,从而导致术语也相应地不稳定和多变”,此时“要想阐明法律的性质,对于这些科学的运用一定要充满小心”,同时学生应当“秉持分析性精神,在处理这些主要的法律概念中学会评判它们”(参见H. L. A. Hart,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A Reply to Professor Bodenheimer”, 10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972-974 [1957])。因此,可以说哈特并没有继续发展自己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的社会学方法,并且这种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淡漠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法哲学家斯科特·夏皮罗曾不无怪异地指出:社会科学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律,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它的结论与法理学家无关(参见Scott Shapiro, Legalit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6, n.16)。
这种冷漠态度的根源,在于哈特认为社会科学对于法律现象的研究,仅仅止步于描述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的外在行为,而缺乏有关他们理解法律时内心态度的分析。哈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持有这种观点或许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不成熟。但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已经经历了长足发展,此时依旧拒绝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道理呢?这便牵涉了法理学发展史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往事,它依旧与哈特有关。
哈特的学生也是当今著名的自然法学家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在希伯来大学收藏的哈特捐赠的图书中找到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一部作品。这本书题为“马克斯·韦伯论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是英译者对韦伯去世后由他妻子整理出版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与法律相关的内容的摘编,同时还有详尽的译者导言和注释。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54年推出,并且有哈特仔细的批注。菲尼斯因此认为,哈特应当深受韦伯的影响。但是令他惊讶的是,在当面交流中哈特不仅否认这一点,还强调真正对自己有影响的是英国哲学家彼得·温奇(Peter Winch)的著作《社会科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围绕哈特为何会否认韦伯对自己的影响,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哈特学术传记的作者尼古拉·莱西(Nichola Lacey)提出的,她认为哈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牛津大学对于社会科学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哈特否定韦伯对自己的影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观点免受攻击。但近年来这个观点逐渐被另一种解释取代。这种解释认为,哈特其实在写作《法律的概念》时并不了解韦伯的观点,甚至从整体上说对社会科学也所知有限。比如,哈特的另一位学者,已故的著名法理学家尼尔·麦考密克(Neil McCormick, 1941-2009)在自己有关哈特的研究著作中回忆,自己跟随哈特读书的时候,哈特有段时间的确与自己兴致勃勃地讨论过韦伯,甚至一度为之着迷。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早于1968年。同时哈特的一位朋友在回忆《法律的概念》的诞生过程时提到,如果哈特真的深受彼得·温奇有关社会科学的看法,那么哈特一定也会延续温奇对于韦伯的评价,那就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对于人类行为的外在视角分析。但是这个观点与今天我们对于韦伯的通常理解完全相反:韦伯所倡导的“解释社会学”,其核心立场就是对于行动者内心目的与意图的理解。
诸多法理学家关心哈特与韦伯的关联,不仅是出于对历史轶事的兴趣,更是想要澄清哈特以“外在视角”为理由拒绝社会科学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是否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易言之,法理学家通过挖掘哈特思想发展的细节,想要讨论概念分析甚至更一般的哲学视角是否构成理解法律现象的唯一方法。但是有关思想史细节的考察则表明,哈特在相当程度上误解了韦伯所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法理学与法哲学画上等号,并认为哲学特别是概念分析方法之外理解法律的视角都与法理学无关,可能只是法理学发展历程中令人遗憾的误会。
《法理学:主题与概念》的三位核心作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告别最近几十年来以分析法学的扭曲视角呈现法理学的这种不幸潮流”,因为“这种潮流既导致将法理学分离于其他学科的日渐狭窄的专业化,也导致法理学远离了法学其他课程”(p.3)。其实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分析法学或者说以概念分析为方法的法理学研究,只是在哈特之后逐渐成为主导英美法学界的潮流。在此之前,特别是在《法理学:主题与概念》三位作者都任教过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曾经存在着与此截然不同的法理学传统。这便是时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为法理学创设的“壮志雄心”。他指出,这门学问应当被理解为“有关应被用来指引公民政府的规则的理论”抑或“法律和政府一般原则的理论”(p.1)。这不仅意味着法理学应当关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还意味着维护正义、提供警力、增加税收和修整军备都是这门学科应当实现的目标。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斯密这位担任道德哲学讲席但以经济学研究闻名并对法学保持浓厚兴趣的思想家,对于法理学的界定实在太过宽泛——或许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法理学已经承担不起如此宏伟的“雄心壮志”。但他的观点却至少提醒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的一般理论不应当仅仅关注法律的定义或适用这类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还要关心这些问题如何与政治统治实践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这就与当下中文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法理学:主题与概念》的几位作者所言:长久以来,相比于政府统治,我们对法律本身更感兴趣;相比于制度分析,我们更关注抽象规则。在这种研究倾向下,法理学要么被呈现为不同思想立场之间的对决与论战(比如,自然法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要么变成从一个伟大思想家到另一个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宏伟演进(奥斯丁—哈特—德沃金—拉兹等)。但这两种方案都无助于推进法理学的发展,因为前者呈现理论的方式太过抽象,脱离了每种学说所植根的语境,而后者使得法理学研究仿佛走入了一个密闭世界,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法学家之间的对话,忽略了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久而久之,使得法理学研究似乎是对每种理论或每个人物学说的优点与缺点的分析与罗列,而忽略了每种法律理论实际上都与其所处时代中最紧迫的法律与政治议题密切相关这个事实(p.2)。
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主题与概念》一书无疑是继承并延续亚当·斯密有关法理学“雄心壮志”的一部作品:它试图突破当下英美法理学研究太过狭窄和技术性的风格,希望通过在历史、哲学以及政治语境中对法律及其制度展开研究,复原法理学在主题与方法上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作者在讨论法律实证主义的起源时,没有遵循哈特所开启的传统将边沁、奥斯丁视为法律实证主义的鼻祖,而是直接追溯到霍布斯及其名著《利维坦》中有关自然权利如何过渡到实证法的分析。同时,作者将法律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与伦理领域的两次分离,即第一次与宗教的分离,以及第二次与道德的分离。此外,作者在论述法律与道德关系时,并不仅仅围绕道德或法律的概念与性质展开,而是广泛地援引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以及脱胎于日常生活的思想实验。这会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有关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学说、法律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还有法律权威的讨论,不仅是一种思想史分析,还与诸如连体婴分离手术的风险判定、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以及患者对于自身体细胞的所有权等具体而微却对我们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时更与社会转型正义、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以及现代社会中经济分配等宏大议题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更具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哲学色彩的研究,或许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赫伯特·哈特所倡导的以概念分析为底色的法哲学研究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深而究之,前者其实仍在哈特的延长线上。
从哈特再出发
这是因为无论几位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作者如何想要突破英美法理学的主导范式,《法理学:主题与概念》依旧是一部关注焦点呈现出鲜明英美分析法学与社会法律研究特征的著作。它虽然倡导法理学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方法,但并未提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法律现象的一般法理学框架。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导论性甚至定位为教材的著作来说,这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但理论框架的缺乏,不仅使得全书对讨论主题的拣选略显随意(比如,此书第三部分中有关正义、全球正义以及历史不公的讨论有所重复),也使得每一个主题的讨论显得相对零散,相关论述有时显得过于繁复(比如,有关法律与全球化的分析),但有时又显得太过简略(比如,有关法律推理的讨论)。不过相较于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作者们的力有未逮,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英国社会语境和学术氛围使得他们对相关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此书依旧处于哈特的延长线上。
不过从更深层次来说,侧重社会语境、偏向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哈特学说的距离,要远比采纳社会方法的学者以及哈特自己所认为的要近。哈特本人虽然对社会科学的态度相当冷淡,只是偶尔提及“描述性社会学”这个概念。但是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乃至法哲学家都发现,哈特的学说经过适当调整,可以成为一种容纳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比如,法哲学家朱尔斯·科尔曼(Jules Coleman)就认为,哈特有关法律规则的分析,其实是一种有关法律的社会-科学或功能主义分析,而非纯粹的哲学探讨。前文提及的法哲学家尼古拉·莱西也认为,尽管哈特不承认,但是他有关社会实践参与者内在视角的分析,与韦伯主张理解社会行动参与者的内在意图并无本质区别。人类学家同样持有类似看法。比如,很重要的法律人类学家保罗·博安南(Paul Bohannan)认为,法律人类学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界定和解释“法律”这个概念。以他为代表的众多法律人类学家和法律社会学家,都将哈特对于法律概念的解释视为有待经验事实验证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展开了大量初民社会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法理学家布莱恩·塔玛纳哈曾提出,哈特将法律理解为社会惯习的立场可以被拓展为一种有关法律的“操作性定义”,也即法律是任何社会中被人们贴上“法律”标签的任何事物,通过类似于民族志式的经验研究,可以确定一个社会中“法律”概念的具体所指。
从这个角度来说,倡导将社会科学成果引入法理学研究,并不是对哈特的背离,反而是对其理论立场中长久以来隐而不现的一个方面的继承。当然,对于法理学研究来说,是否继承哈特的立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哈特开创并由拉兹所塑造的分析法哲学范式中,似乎日益有一种将身为社会现象的法律抽离于具体语境、将任何与概念分析不同的方法排斥在法理学研究之外的倾向。这种倾向被法哲学家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戏谑地称为“牛津正统”。言下之意,似乎不从概念分析角度讨论法律的性质、法律的规范性等问题,虽然也算法学理论研究,但却与法理学或法哲学无关。这种倾向最明显的体现在拉兹有关法理学研究的论述中。他虽然曾说“我在狭义上使用‘法律理论’这个概念,指的是法律的性质……我并不打算质疑有关法律的其他理论研究的适切性”,但是当他指出探讨法律性质的“法律理论”可以掌握有关法律的普遍必然为真的真理时,无疑贬斥了法哲学之外的其他方法(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近年来,这一趋势可谓更加明显,随着年轻一代法理学家在哲学训练方面的日渐完备,法理学研究与哲学讨论中的元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逐渐密切。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今时今日,如果不懂语义学、真理论、形而上学等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可能无法看懂大部分法理学作品。
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精细化发展固然可喜,但是这种发展在无形中遮蔽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现象。首先,法理学并不天然地等同于法哲学,哈特崇尚哲学分析而排斥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是一场偶然的历史误会——以他在智识方面的诚实,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也会广泛吸纳社会科学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牛津正统”并不存在。其次,法理学家并不只是展开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家,同时也曾是并应当是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与社会福祉的推动者。哈特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叶就《沃尔芬登报告》与德弗林法官展开激烈论战,如果在今天,以他的勇气和智慧同样也会就公共卫生保护、行政权力边界等议题展开讨论。因此,站在哈特的延长线上,不是为了刻板地严守其观点立场,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评判他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再次出发。《法理学:主题与概念》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