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聚焦 | 一个外卖骑手的2022年
原创 第三新闻中心 新新报NewTimes

“好好的姑娘怎么来这了”。
当我第一次来到桥下时,住在那里的流浪汉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这里是繁华都市中一个隐蔽的角落,看似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地方,却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驻扎于此。
“鱼龙混杂”是我对驻扎在这里的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中有初来深圳为了谋生的年轻人、有家不能回的外卖骑手、爱好露营的发烧友、捡瓶为生的流浪汉,也有不少偷窃建筑材料,入市倒卖的团伙。
住在这的人大多搭着帐篷,但也有人在绿地上草草铺着一层纸皮苟且度日。
来自广西梧州的外卖骑手李小安也是桥下的一员。今年10月,在这座城市辗转多地后,他最终选择搬到这里度过剩下的2022年。
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搬来这里住的人变多了不少。李小安的帐篷旁,也来了几个广西老乡,他们买了卡式炉和锅,开始自己做饭吃。桥下逐渐热闹了起来,李小安仿佛把这过成了自己在异地的家。
“在深圳没钱难道就不用活了吗?不可能!没钱也是要活下去的呀!”
这一期,让我们走进深圳一位普通外卖员的2022年。
采访 | 胡佳琳
撰稿 | 赵姵茹 胡佳琳
内容编辑 | 刘淑欣
运营编辑 | 黄昕婕
出品 | 新闻工作坊·第三新闻中心

辗转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住所。
新建的立交桥将纵向的空间一分为二,桥上平整干净,汽车飞驰;桥下是散落着烟头、塑料瓶、纸皮的绿化带。当视线越过大片的绿植,蓝色、橙色、迷彩色都出现在眼中——这些都是一个个折叠帐篷。外卖骑手李小安,就住在其中一顶橙绿色拼接的帐篷里。
在距离他帐篷300米远的地方,正对着一个日夜施工声不断的建筑工地,这里正在进行穗莞深城际地铁站的修建,白天不时发出“轰”的爆破声。日子久了,李小安的耳朵对施工声已经“免疫”了,即使耳边隆隆声持续不断,他也能睡得着。
帐篷右侧是已经停运的深圳西站,荒凉的铁路上只有拉货或者维修的列车偶尔经过。如同滴入清水里的颜料,色彩各异的帐篷给这里增添了一些生活气息。

桥下的环境 记者摄
在来到这里长住之前,李小安也有过寻常概念里的“住所”。
十月初,他还跟两个室友挤在向南东村的一间合租房里。房子不大,一室一厅30多平,加上水电费,每月花费2600元,三人平摊下来每人将近900块。十月底,疫情悄悄逼近向南东村,他察觉到不对,早早地将行李塞到电动车的后备箱,离开了村子。但他所谓的行李,也只是三件衣服:一件短袖,一件外套,一件羽绒服。
离开出租屋后,李小安在宾馆住了两晚。他的直觉是对的,疫情很快就波及到了向南东村。过了两天,没来得及离开的舍友告诉他“村子封了,没有提前通知”。“都是半夜封,两点半快三点的时候,人在家里面,都在睡觉,肯定不知道的。”
房子是没办法回去了,但工作不能停,得有个歇脚的地方。他舍不得长住宾馆,一天两百多的收入,吃喝花掉十几块,住宾馆再花掉八九十,“住三四天还行,一直住就没钱剩了”。31岁的他,家里已经有三个小孩,因为疫情,妻子在老家的工作也被耽误了,想方设法从生活这块海绵里面挤出如水般流走的钱,成了这位家庭顶梁柱的首要任务。
宾馆不是一个好选择,李小安只能在公园的石椅上露天睡了一个星期。在又硬又凉的石椅上垫上两层纸皮,一张简单的“床”就做好了;一旁的树枝则充当衣架,晾着他在公厕洗好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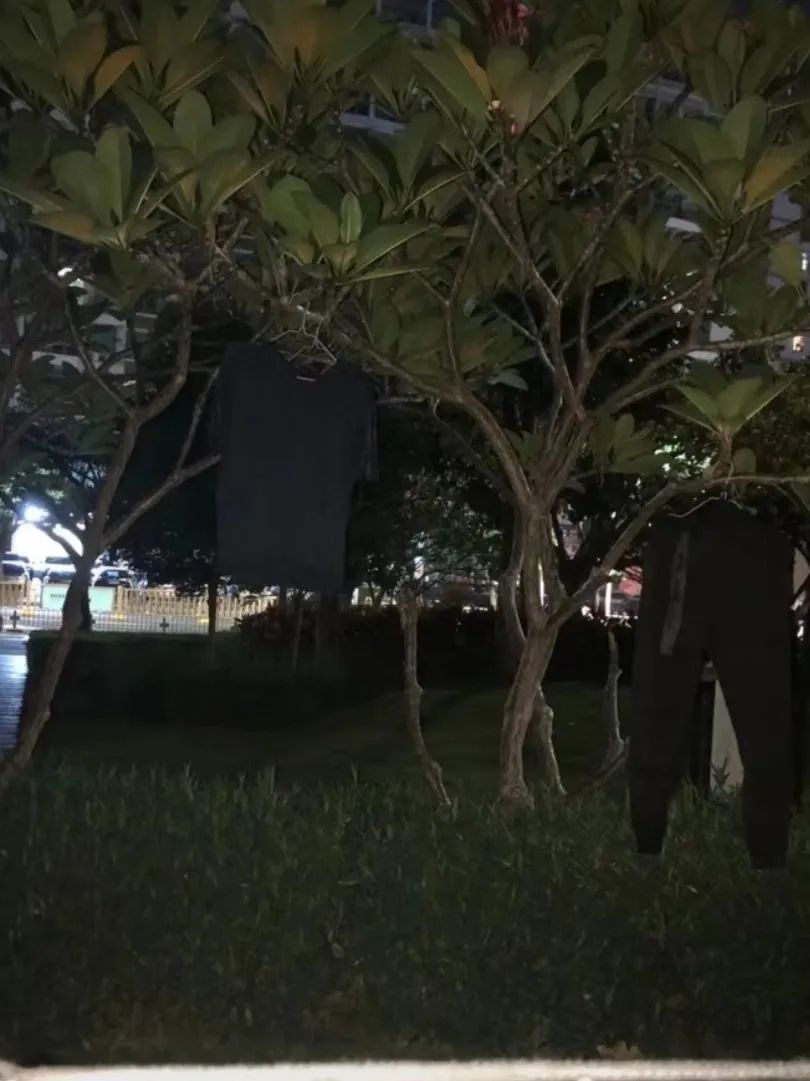
图片源于李小安的抖音
他本想在这里多凑合几天,却不巧碰上连续的小雨,晚上湿气重,等清晨6点在他被环卫工人赶走时,才发现身下的纸皮湿透了,背后的衣服也湿透了。
晚上2点多才收工的李小安,在公园没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只能另择住处。作为外卖骑手,他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对城区的分布了如指掌。早在一年前,他就发现了月亮湾立交桥下的绿化带有人搭帐篷住。
立交桥位于桂庙路和月亮湾大道的交界处,地区交界处属于典型的“两不管”区域,平日里除了这些驻扎在桥下的人,也只有绿化人和城管偶尔会过来。
绿化人只管浇桥下大片的绿植,有时看着他们没处洗澡,也会好心地打开水闸,隔天再关。城管也对搭帐篷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城管也是人”,除非被路过的行人拍抖音传到网上,他们才会过来看看。“可能觉得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桥下的流浪汉说。
李小安花了三四十买了个帐篷,和桥下的所有帐篷一样,都不大。这些一臂宽的帐篷,只能容纳一人,他又额外花了四十多块钱买了个小毯子。兜兜转转,在换了一个又一个住所之后,他带着这顶橙绿拼接的帐篷,在桥下安置了下来。

桥下
对比露天的石椅,桥下的帐篷起码让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现在变冷,有帐篷挡着风,还有一个外套可以盖一下。”为了防潮和保暖,李小安在帐篷下面垫了一层泡沫板和一层纸皮。四十多块钱买来的毯子,只能盖住帐篷一半的面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还是显得有些局促。

帐篷内部 记者摄
搬到桥下的第二天,一直让李小安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感冒,“从公园出来我就担心自己发烧”。这场感冒持续了半个月,他不敢去药店,“去了药店就直接让你去医院”;也不敢去医院,“没有个五百八百出不来”。庆幸的是,五六月份提前准备的一大袋阿咖酚散,成了他半个月里跟感冒进行拉锯战的唯一武器。
阿咖酚散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长期服用会有成瘾的可能性,近年来生产和使用已逐渐减少。这样一种药在李小安眼里却是“啥病都治,便宜实惠”的好东西,“一天吃一包,有些人说会上瘾,我是没啥感觉。”
桥下没水没电,“烂了都没钱换”的电瓶车成了李小安日常生活唯一的电源。铝电池充电太危险,安全起见,他就用换电池代替充电,“去充电柜可以随时换,每个月300多。”
没有水,洗澡自然也成了问题。桥下一公里之外是流光溢彩的立桥金融中心,对面的公共厕所从外部看就如同一个透亮精致的玻璃盒子,里面带着淋浴喷头的厕所隔间就是李小安平日洗澡洗衣服的地方。有时候收工晚,碰到桥下搞绿化,他也会半夜用水管洗澡。“肯定不能白天洗的,要晚上一两点没人再洗。”桥下没办法烧水喝,在帐篷里吃泡面都成了实现不了的事。
电瓶车是他的电源,也像他一个移动的家,大部分的家当都摆在里面。他的日用品只有洗发水、洗衣液、牙刷和牙膏,这些东西每天都被塞在后备箱里,随着他送外卖到处奔波。

李小安的后备箱 记者摄
他不放心将东西留在帐篷里,因为即使桥下住的是一群“没什么东西可偷”的人,小偷还是会来光顾。他曾亲眼目睹过住在旁边的流浪汉被偷,“没什么东西都要翻着偷。”
“其实我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手机。手机能跨越思念,让他和妻儿见面,软件上不时跳出的订单让他得以赚钱养家,里面的健康码更是疫情下他的身份证明,“这个就是苦命的意志,没办法”,他笑着说。
住在桥下,李小安第一个认识并熟知的人就是他的“邻居”——一个50多岁,靠捡瓶为生的流浪汉赵辰龙,在决定流浪街头之前,他还有份稳定的工作,但连续三段的情伤,让他不想和任何人产生联系。
平时两人一起唠嗑,李小安会在工作不顺时找流浪汉倾诉,流浪汉也会经常分享他遇到的“奇闻异事”。可他们互相连名字都不知道,流浪汉称呼李小安叫”广西“,李小安就喊他”糟老头“。顾客退掉的外卖,李小安就拿回来送给流浪汉,“丢了也可惜,送给他吃”。他也经常把电瓶车的电和自己的流量分给流浪汉用,”反正我自己用不完。”
“很多人知道我是流浪汉,都不愿意靠近我,他不会,从来没有。”流浪汉说。
其实在这里住还是租房住,对他来讲都差不多。在哪里住都是洗洗睡,都是担心被封或者被赶走,都是想着怎么省钱。在桥下住,每天的开销只需要四十多块钱,一天两顿。他没有别的爱好,只抽烟不喝酒,再来包解闷的烟,一天花出去的钱就差不多了。一个月工资五六千,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就一千五左右。
“就算解封,我也不太想回村子住了。”

外卖工作
上午十点半,李小安在简单洗漱后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有十年了”。在正式出发前,他会提前检查自己的健康证是否审核通过,这是疫情爆发后外卖平台新增的规定:外卖骑手每日上线必须上传24小时核酸记录,在系统审核无误后才能接单。

健康证明 记者摄
在不同时间段配送外卖,骑手赚的不同,“(早晨)十点以前一单可以赚到5块,午高峰十一点以后,跑一单是6块多钱”。李小安每日的工作时间也因此集中在早高峰十点半到一点半,晚高峰下午五点半开始,凌晨十二点结束,有时也会跑到半夜两点才收工。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为了抢时间跑更多单,两餐他都会避开饭点吃,“一点半到两点吃午饭,晚饭就等到收工12点以后再吃”。每日用在吃饭上的开销不超过30块,一份一荤一素12块左右的快餐是他一顿的标配。
考虑到上班族聚集、订单数量大,李小安一般在南山区跑。幸运时接到代买代送的“跑腿单”,他就不会挑剔距离,“哪都能跑”。普通订单跑4、5公里,能赚4块多,相比之下跑腿单能多赚不少,“跑10公里就有20到30块”。
他曾在一天内送过70多单,这一记录发生在去年,至今没有被打破。“今年没单,没办法”,年初疫情后,他明显感觉深圳少了很多人,行业却涌入了不少竞争者。因为入行门槛低,“送外卖”成了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外地求职者来深圳后的首选。
可送外卖并不是李小安的第一选择。2016年6月,他坐火车从广西梧州来到深圳,作为家里的老幺,在他之上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不想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可他年少得子,在女友18岁时,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女儿。孩子的降临,让李小安意识到了身上的责任,原本每周要拿出一半的工资玩六合彩,后来也开始学着攒钱。
大女儿满月后,他第一次离家踏入这片陌生的土地,满怀期待地拿着招聘广告走遍了城市,却不巧赶上毕业季,跑了两周,也没有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为了生计,他又回到了老家的工厂。2018年,伴随小女儿的出生,他决定再来深圳试试。
第一份工作是在光明区的一家五金厂,没干多久工厂就迁离了深圳,他也辞了工。“工厂(上班)稳定,赚得也比老家多”,他不想就此放弃,奔波了一周后,在一家生产扫地机的工厂里谋得了一份工。
平时李小安在流水线上工作,周末有空他也会去跑跑外卖,随着工厂往东莞方向搬,每天骑车上班的时间也增加到1个小时。“上班的时候感觉送外卖的自由点”,为了逃离漫长的通勤时间和单调的工作环境,李小安干脆辞去工作选择专职送外卖。
可他没想到的是,去年每天接50单的常态,在年初疫情后变了。“今年人口流失严重,单少人多,现在都越来越不好搞了。”李小安说,“一天能送个三十单已经很不错了。”
订单减少,收入也不可避免地缩水,“(今年)在没过八月十五之前,一个月还可以赚到八千多、九千,现在一个月就五六千块钱。”美团现行有三种结算工资的方式:专送,工资按月结;乐跑,工资在骑手跑完一周后再过十天一次性发放;众包,工资按日结。李小安属于众包。
众包骑手没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对他们来说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关掉手机休息。但李小安不会,周末也不会停下来“一般都是这样接着跑”,这种外卖生活持续了三年多。这其中,他只收到过一次差评,发生在今年。
李小安至今还对男人羞辱他的话历历在目。四月份的一个晚上,下着雨,他接到了一个烧烤单。在接单不久,女顾客就连打两个电话催促,李小安在配送时间内赶到楼下时,她再次打来电话投诉骑手超时。李小安尝试跟女人解释,让她有事找客服。可女人并不接受,还叫来了同住的男友,男人在接到电话后破口大骂, “你个傻逼啊,还不送过来,你妈逼……”。
被人骂,李小安起初并没觉得很受气,即使自己之前没有遇到过,也经常从同行口中听闻这类事。但在解释情况后,男人越骂越凶。“骂我可以,别伤害的家人”气愤之下,李小安取消了订单“这个餐就别想吃了”说罢,他挂断了电话。因为这一单系统并未显示骑手超时,且顾客骂人在先,李小安没有承担责任。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他没觉得有多委屈,只是一直重复“别骂我的家人。”

不知所出的帐篷
今年李小安曾不止一次“逃离”小区。
3月,深圳进入疫情管控,要求全市居民原则上居家,除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暂停营业。
为了跑单,在小区封控前,他草草从家里拿了件羽绒服出来。疫情之下,跟他一样坚持在外跑单的骑手不在少数,他身边的朋友有些从家里拿了帐篷,有些还没来得及回家就被封在了外面。
封城的七天,街上除了医护人员,只剩下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开始的几天并不好过,李小安和其他骑手一样晚上露宿街头。可即便没有地方住,他也不想向外界求助,不知何时起的观念甚至让他偏执地认为,他们的死活并不会被在意,“你别想靠着政府,人家会管你吗?说难听一点,现在深圳(人的)死活都没有人管,不做核酸就有人管”。
即使李小安在当时无意中接受了街道办的援助,他也坚持认为那是店家在奉献爱心。
他回忆道,“封控期间,在南山地铁站第三个红绿灯上去大概两百米,左边有两个帐篷。”帐篷建在江味龙虾馆门口,一个帐篷用来储存、发放矿泉水、泡面等物资;另一个帐篷用来住,可以容纳五六个人。“谁来得早抢到位,就可以睡“,因为无偿开放,每天抢着住的人很多,李小安在那里住过4天。
“不可能是别人,帐篷上写着‘江味龙虾馆’。”李小安笃定地说。但当我多次询问店家后,他们都否认了这件事,“不是我们搭的,我们只会在下雨时搭帐篷,害怕外面的顾客淋雨。”店里轮值的经理说。在向店家所属的荔芳社区核实后,证实了帐篷并非店家的善意,而是在政府的参与下,由南山街道办所搭建。
3月疫情期间,为了解决外卖骑手的食宿问题,城市各区建立了面向骑手开放的休息区。在南山区,不仅开展了“暖蜂行动”为骑手提供饼干、泡面、矿泉水等食品与医疗物资,社区还联手各大企业搭建了临时居住点。
在街道办搭建的物资点中,李小安领到过7、8次泡面,“因为跟他们(发放物资人员)比较熟,有时候会给我留一桶”。用作住宿的帐篷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抢位,他也会有抢不到的时候,“抢不到,就在帐篷旁边靠墙的位置放两块纸皮这样睡,有墙挡着风,也不是太冷”。初春的深圳,李小安没有被子,就拿一件黑色羽绒服盖在身上,露天睡。他说,“就算有帐篷,这种情况(露天睡)在年初还是很多。”

十二月
在距离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全国陆续放开。随着消息不断传来,人们期盼已久的“自由”正逐步实现:
12月5号,深圳新冠疫情指挥部办公室发布9号通告规定称全市社区小区、办公场所、餐厅商场及各类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码、场所码进入;12月7号跨地区流动不再查看健康码;12月8号起乘坐地铁也无需查验健康码;12月13号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
外卖平台每日依据骑手24小时核酸记录所审批的健康证,也逐渐放开成48小时、72小时。12月10日,平台全面放开,“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点做核酸了”李小安兴奋地说。
然而,随着社会面的逐步开放,感染人数也在逐日增加。桥下一起住的同事,坚持开工的一天比一天少,一直以来带N95口罩的他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骑手变少,订单多了,三单有两单都是送药的。他想赶在年前的最后一个月多赚点回家,还向流浪汉信心满满地立下自己的目标“一天挣500”。
12月21日,李小安还是发烧了,直觉告诉他应该是感染了。晚上7点多,他送完手上的最后一单,红着脸回到了桥下,把车停在帐篷旁,从后备箱里翻出一包阿咖酚散倒进嘴里,灌了两大口矿泉水将药粉兑了下去。他将黑色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拉了拉,爬进帐篷,在确认自己的闹钟调到半小时后,用毯子蒙着头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流浪汉劝他多休息,晚上就不跑了,“害怕他路上出事”。李小安冲着流浪汉对付地说了句“没事”,打开电动车的灯,扭转车头,骑车离开了桥下。
“过了年很多人不会过来了,包括我吧。”李小安说,“在深圳根本就赚不到钱。每年都没得剩,家里面小孩小,每个月都得要(钱)、读书也要(钱),哪还有钱剩。”他打算明年回老家找份工作,也可以多陪陪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老家有房,开销不大,找个工厂工作,一个月也有四千多。”
旁边的流浪汉听后点起一根烟,用半玩笑的语气冲着李小安说,“瞎说!为了我,你明年也会来。”
(李小安、赵辰龙均为化名)
原标题:《聚焦 | 一个外卖骑手的2022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