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3
如此城市︱严飞对话黄灯:“悬浮”是城市生活的常态吗

“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地,一座梦想之城。”
城市研究学者哈罗德·乔尼对于城市的描绘精准地抓住了城市的特点——变化万千与异质性。而这一主题正是社会学对于城市的重要关切所在。
从乡村来到都市以不同方式谋生的陌生人们是如何生活与行动的?异乡人的都市生存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有机和谐还是失序混乱?曾经流行的“漂”话语与当下“附近的消失”的焦虑,到底折射出当今城市人群的何种心态?
对于这些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在非虚构新作《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一书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他通过记录与分析异乡人大都市生存实景,用“悬浮”来描述漂泊在城市的中国年轻人所共享的某种心灵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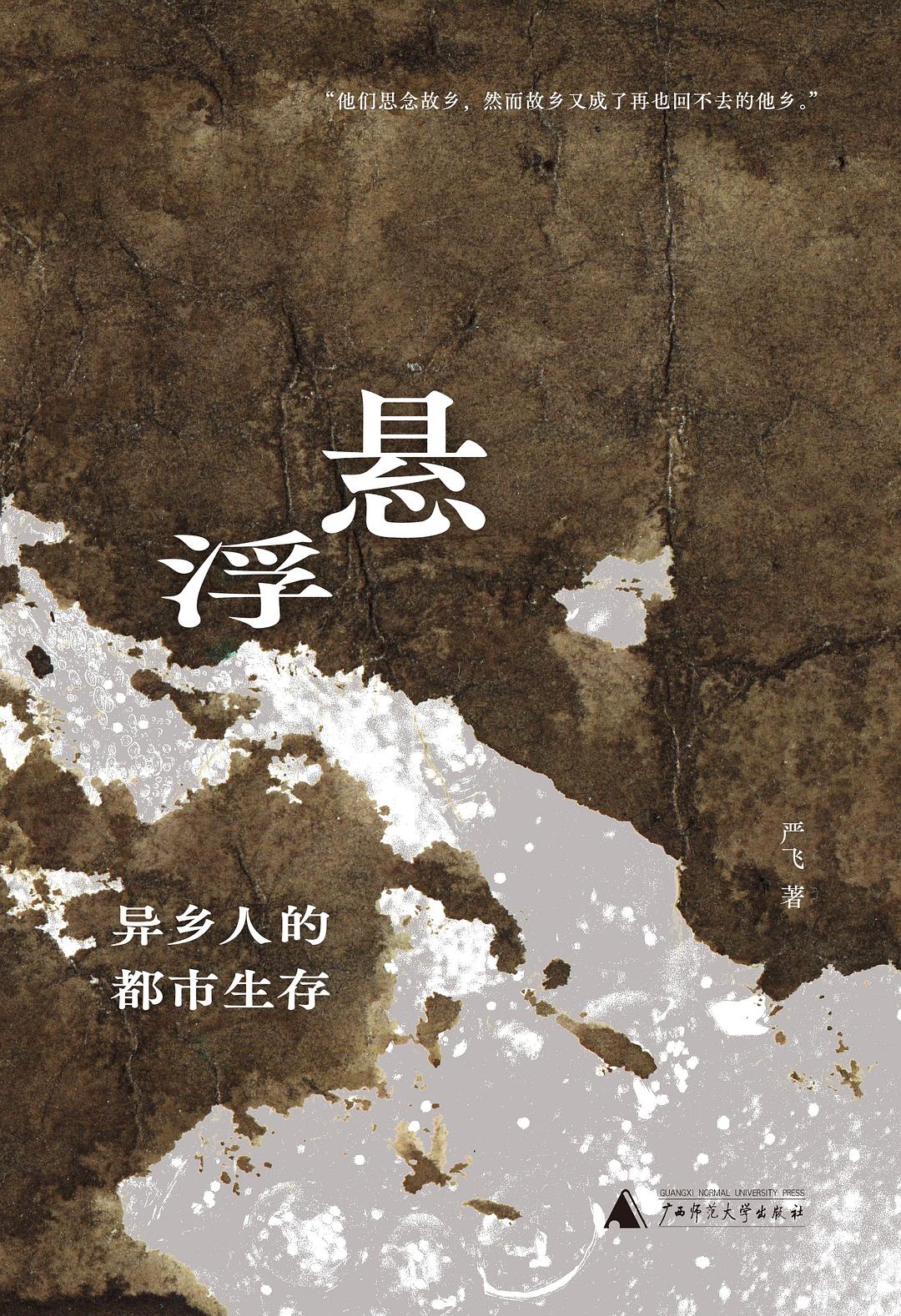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严飞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1
作家黄灯在世纪之初从湘北小城来到广州求学,并在高校任教至今。从检视自己,回望乡土的《大地上的亲人》到观察年轻人命运的《我的二本学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对人的状态的影响,一直是她所关心与书写的主题。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邀请到严飞与黄灯,从作为异乡人的都市生存出发,聊聊城市与人。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黄灯,学者、非虚构作家
——本期主播
郝汉、灵子


——收听时间线
06:30 城市如何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
13:36 21世纪初,来到大都会广州是何种体验?
26:15 房产中介、理发小哥等群体,如何构成城市生活的“附近”?
32:05 70后一代城市生活的“确定性”
48:10 城市生活里的“附近”究竟是什么
52:50 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感到“悬浮”?
64:15 重建身边的小世界,如何抵御都市的冷漠?
75: 55 附近的“技术”,是与周遭事物打交道的能力
——节目内容摘选
——“有机团结”的城市社会
如此城市:社会学诞生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乡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时期。那么,这门学科最初是如何认识城市的?
严飞:社会学家之所以把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实际上是因为城市是乡村的对照。这种对照的进程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在传统的前工业化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存在一种依赖亲属关系、从事相似的土地劳动而建立起来的“机械团结”。但是在资本与工业的齿轮不断推动下,越来越多人从原来的土地脱离,慢慢转变成手工业者、工人,来到城市,当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城市中,工业城市才得以诞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社会产生了一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有机团结”的社会性质,它的特点是人们基于社会分工在一起共同生活,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家属亲缘关系。在这样的进程里,我们会发现,人们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利益、契约等不同基础组成了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里面导致群体之间产生了分化。人群的分化必然导致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的异质性越来越强。
前工业化的村庄里,大家都是亲属关系,从事的大多都是农业劳动,是相对同质的熟人社会。但在城市里,正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城市里的人会更加关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会是原子化的个体。
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一篇文章《大都市的精神生活》里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矜持”,或者用一个负面的词叫“冷漠”,而且会“工于心计”。
可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当“悬浮”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
如此城市:黄灯老师的写作与经历其实深刻地嵌进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悬浮》里谈到的都市异乡人对于城市的向往与体认已经与过去有许多不同。作为来到大都市打拼并顺利留下来的“早期”中国大都会异乡人。在当时与当下,你对城市有何不同的理解?
黄灯:可以特别坦白地说,尽管我的人生变动很多,但在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过程中间,我真的没有产生过今天年轻人所感到的“悬浮”的感觉。2002年,我来到广州读书,后来在广州工作,那种不确定感是没有的。在我们70后那一拨人里,一个人如果能够读到博士,就是在城市能够立足的最好保证了。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哪怕读到博士,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2005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是向上蓬勃与热气腾腾的。我记得在当时广州的北京路,人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一样多,摩肩接踵的感觉。

2023年1月1日,北京路地处广州市中心,是历史上最早建立广州城的位置之所在。市民在千年古楼遗址参观、游玩。视觉中国 图
这些年来,我带过两拨学生。一波是80后,比我小十岁左右,第二批是比我小二十岁左右的90后。你能够明显感到,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确定感与悬浮感明显增强了。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原因不单纯是由于个体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更多的是个体所能够依傍的东西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我参加工作进单位的时候,一个工厂都会给你提供住房。虽然孤身在城市,但我确定地知道我跟这个社会的联系是什么,一份工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庇护。为什么我没有悬浮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让我感到,人还是能够掌控一些东西的。

2022年8月4日,上海地铁站内,高峰人流密集。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严飞:在今天的城市里面,人们所面临的竞争与成本都是在一个“内卷”的赛道里面,而且机会的通道慢慢变窄。为什么年轻人都在进行考公、考研、考证?实际上是因为人们没有信心在不确定加剧的社会里面去博取一些东西,而只想抓住一些相对确定的东西。
我之所以用“悬浮”来命名今天年轻人的某种状态,就是因为他们面临更大的焦虑,对于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而越是没有根基,越会想拼命抓住一些东西,让自己仿佛是确定的。
我在《悬浮》里面打过一个比方,所谓“悬浮”,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列车越开越快,慢慢地飘在了空中,飘在空中以后,人必然是悬浮的,所以车上的人越来越想抓住车的把手、栏杆,来让自己在这个车厢里站稳。但这列车厢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栏杆、把手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我在书里所记录的大都会异乡人多是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这些人群不像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里面奋斗打拼的人那样有退路,这些年轻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乡土的感情已经非常淡漠,甚至有些人就是出生在城市的,对自己家乡的感情会更加疏离。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城市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没办法在大城市里面上小学,只能去上打工子弟学校。种种现实情况让他们加深与所在城市的隔阂。他们的身份认同会更挣扎与撕裂,他们更会觉得自己始终是异乡人的状态。
——“附近”的说法,为什么能打动年轻人?
如此城市:谈到这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附近”的说法,严飞老师写到自己身边的家装工人,房屋中介等等,他们构成了您在城市生活的“附近小世界”。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里,该如何认识附近,甚至创造、感知或是重建它?
严飞:我自己对于“附近”的感觉,是“附近”的内涵变化很大。回到80、90年代,所谓“附近”往往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单位大院,或者职工大楼,里面住的是单位的同事。单位制的“附近”是高度同质化的,而它的边界实际上是非常强的,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之间并没有那么多交流。
而且这种单位内部的“附近”,它的交往模式依旧保留有一种强烈的权力逻辑,例如科层体系里面的交流,单位的领导与职工的交流。
但今天的大城市里面的“附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任意性,它变得高度的异质与混杂,人们会在城市的流动性中产生崭新的交集。这种交叉性是非常强的。正因如此,相比单位制时期的人,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去重新建构一个新的“附近”。越大的城市就拥有越多的人与物、人与空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多重并置之下的丰富“在地性”。
今天谈“附近”,更多还是应该强调它的异质性、混杂性、流动性,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特点,人和人之间黏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带来意外的惊喜,它们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及其闪现出的片段和火花。
——制作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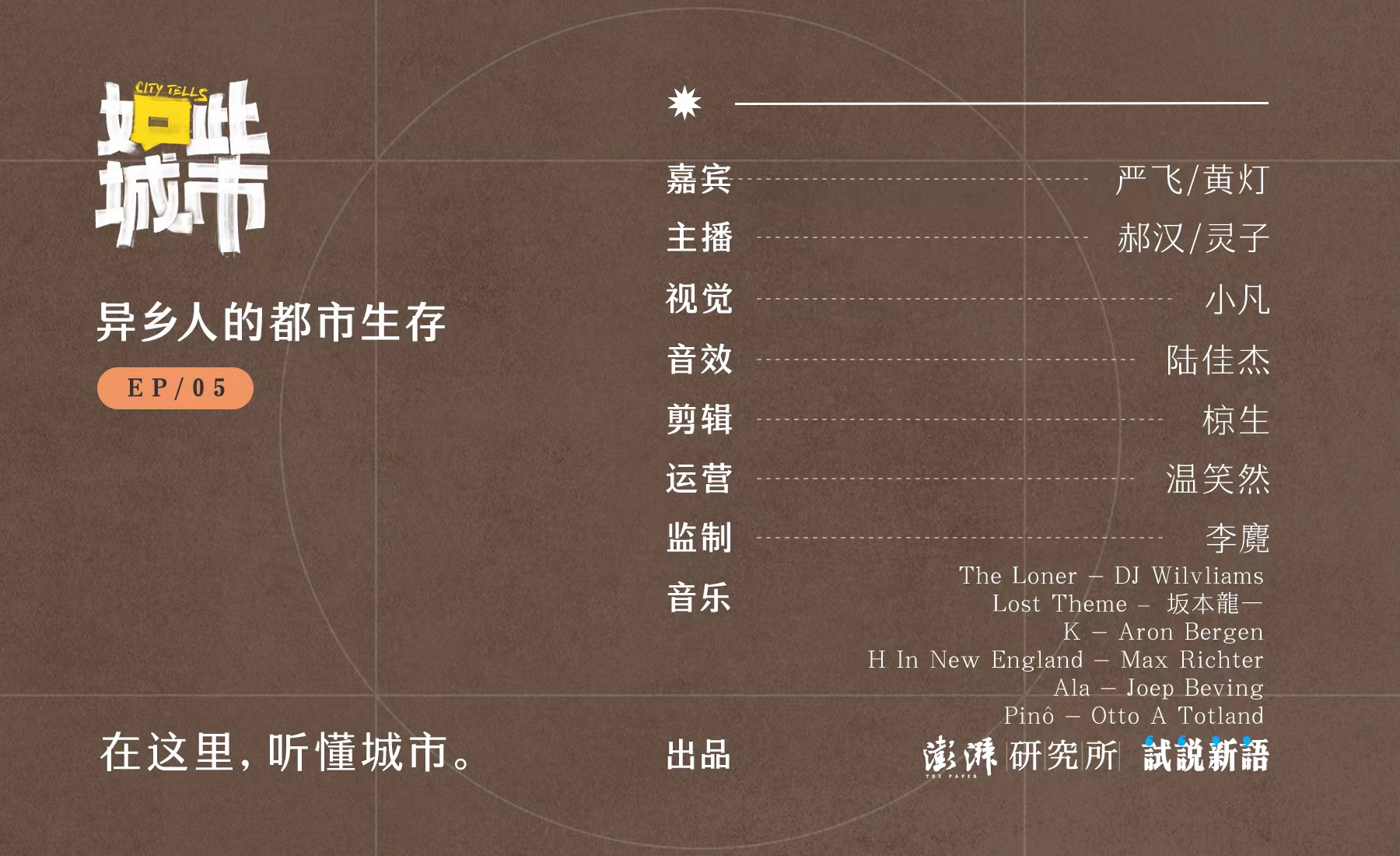
——引导收听


- 全民阅读,满城书香
- 神舟二十号新闻发布会今举行
- 中使馆谈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

- 乌副总理:乌克兰愿意谈判但不会屈服
- 韩国最高法院加速审理李在明案,或影响选情

- 约每76年环绕太阳一周的彗星,是人类首颗有记录的周期彗星
- 一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主人公是一只当警官的黑猫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