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戈达尔与古列斯坦对话录:来自往昔的交谈
从2014年开始,伊朗女导演米特拉·法拉哈尼(میترا فراهانی, Mitra Farahani, b.1975)促成伊朗诗人艾卜拉希姆·古列斯坦(ابراهیم گلستان, Ebrahim Golestan, b.1922)和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 1930-2022)中的一方在每个周五给对方写一封信,另外一方在下个周五回复一封信。在这个被命名为《星期五见,鲁滨逊》的项目开始之前,这两个人并不认识对方,也从未谋面。影片的开端,她引用帕索里尼的名言“我是来自往昔的力量”①来形容这个计划的灵感来源。片名中“À Vendredi”有两种含义,“星期五见”和“致‘星期五’”——他们互为对方的鲁滨逊,或者互为对方的“星期五”,法拉哈尼显然并不在意《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权力关系,也并不在意其殖民语境,而是打算纯粹浪漫化挪用其原有文学概念——孤岛、孤独的个体、隐居生活、文明的碎片和有限空间的绝对统治。

《星期五见,鲁滨逊》海报
尽管影片大部分的拍摄完成于古列斯坦的住所,而戈达尔的素材则大部分是在《影像之书》(Le Livre d'image, 2018)的制作过程中拍摄的,影片中看上去似乎是连贯的图像序列实际拍摄的时间相差甚远,法拉哈尼仍然试图将一种旨在精确的对位关系贯彻到影片的剪辑中,使两位隐居的大师在通信之外产生一层新的对话空间——这是属于电影的任务,也是一种叙事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星期五见,鲁滨逊先生》甚至是一部书信体电影(cinéma épistolaire),它带有这种古典文体的诸多特质,比如贯彻始终的间接性,信息错位和校准,比如时间的延迟感及其产生的情感张力——感伤且缓慢的精神进化过程。
古列斯坦和戈达尔的身份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被归纳为自己国家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代表人物,身份的相似成为《星期五见,鲁滨逊先生》得以成立的前提之一。首先从两个人导演生涯的始端来看,他们的第一部电影都与大型国家资本关联甚密。1958年戈达尔在瑞士迪克桑斯大坝(Grande-Dixence)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混凝土行动》(Opération béton, 1955);几乎与此同时,古列斯坦受刚刚完成重组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委托开始制作影片,并于稍后几年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大火》(یک آتش, A Fire, 1961),一部记录伊朗阿瓦兹油田(Ahwaz-Asmari)天然气火灾艰难扑灭过程的新闻短片。两部影片都以宏大官方的叙事口吻暗示出人类通过大型工程改造自然时的渺小,资本在面对原始力量时的窘迫,这也为他们未来长期贯彻的左翼姿态提供了相当的观察和材料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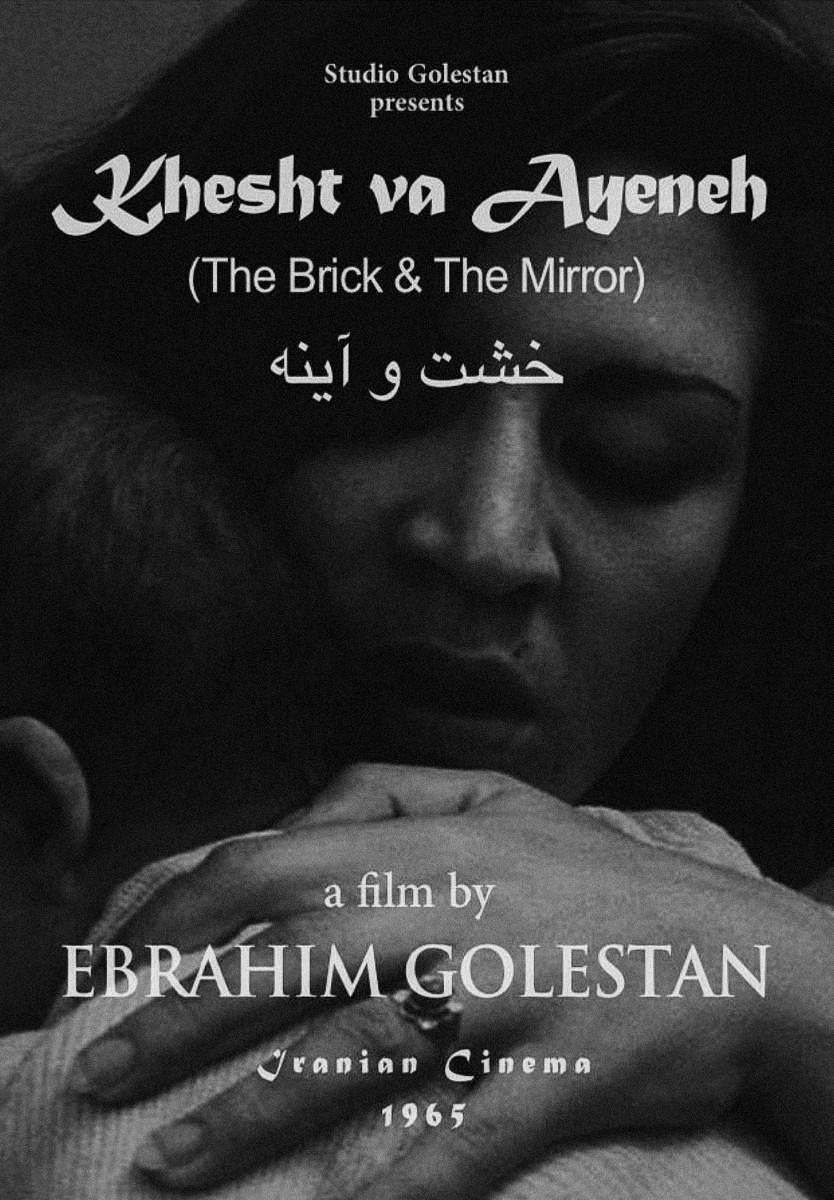
《砖与镜》海报
两人的长片处女作——《精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 1960)和《砖与镜》(خشت و آینه, Brick and Mirror, 1965)被分别认为是“新浪潮运动”的奠基性作品。和《精疲力尽》旨在彻底革新电影语言的勃勃野心不同,也区别于同时期关照农村题材的伊朗新电影(موج نوی سینمای ایران),《砖与镜》更倾向于一种声学上的革新,这部电影不但是第一部采用现场同期录音的伊朗电影,也在对白和人声材料中呈现出伊朗现代诗歌(She're No)洗礼后的波斯语崭新的声响面貌——不单单在其语言和语音的表现力,也在于其兼具现实关照的表现主义风格。出租车司机游荡在摩萨德倒台前夕的德黑兰城市夜景中,汽车电台中播放的广播剧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猎人和猎物辩证关系,古列斯坦亲自为其配音;影片中抛弃亲生婴儿的女乘客由革命诗人和女权运动家、古列斯坦的伴侣和搭档法洛克扎德(فروغ فرخزاد, Forugh Farrokhzad, 1934-1967)出演——两年后她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影片中的她身着罩袍,只短暂露出了部分侧脸,出现如同其生命般短暂而神秘,却深深地困扰着古列斯坦的余生。巧合的是戈达尔同样也企图为后被称为“新浪潮缪斯”的安娜·卡里娜(Hanne Karin Bayer)在《精疲力尽》中安排一个需要半裸出现的小角色,但后者拒绝了出演。
在经历了混杂着情欲和革命,混淆着图像和声音的年代和年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们都感受到身份的危机,对政治的热情和语言的困扰将这种危机推至必须与自己决裂的边缘,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尝试将自己从原生阶层剥离,在经历过全情沉浸、澎湃和幻灭的革命洗礼后,他们又很难不将其特权携带终生。戈达尔加入“维尔托夫小组”,他们将东方的革命语言系统同自己的创作结合,“电影传单 ”(Cinétract)、“传单电影 ”(Filmtract) 、“黑板电影” [Le grand tableau (noir)] 等一系列新奇的极具煽动性的名词被源源不断地发明出来;他和战友将流产的《直至胜利》(Jusqu'à la victoire)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影像和巴黎中产生活混合剪辑成《此处,彼岸》(Ici et ailleurs),这部典型的“黑板电影”以训导和教育为目的,将图像和声音拆解,对“观看”本身进行了批判,这些崭新的特质强烈地展示出“后戈达尔”的代表性倾向,由“革命的电影”更笃定地转向“电影的革命”,半个世纪后,他的作品几乎成为该运动的唯一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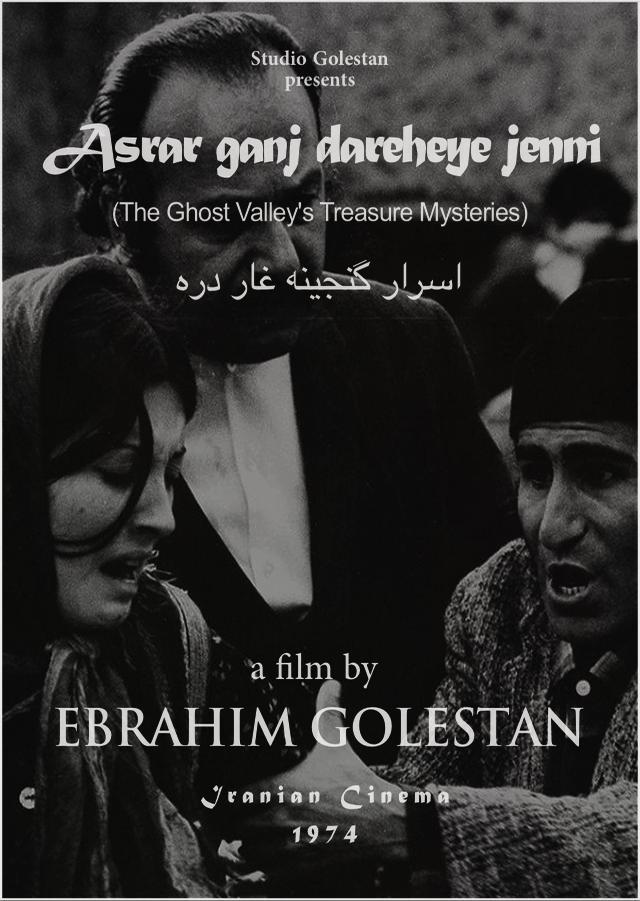
《精灵谷宝藏的秘密》海报
在《此处,彼岸》等待合适机会放映的同时,古列斯坦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故事长片《精灵谷宝藏的秘密》(اسرار گنج درهٔ جنی, Ghost Valley's Treasure Mysteries, 1974),在此之前他曾受伊朗中央银行和王室委任制作了一部离经叛道的短片《伊朗皇冠的宝石》(گنجینههای گوهر, The Crown Jewels of Iran, 1965), 该片公映版几乎被伊朗审查员删除了所有旁白;《精灵谷宝藏的秘密》成为其精神延伸体,将贫瘠和财富、垃圾和宝石、穷人和权贵的冲突用一种当时伊朗电影中少有的讽刺荒诞口吻讲述出来。评论家认为这部政治喜剧电影预言和预演了巴列维沙阿王朝的垮塌。也许是人们并未看出其中的现实投射,该片顺利通过了伊朗的审查制度,甚至在影院中放映了两周才被勒令停止。此时古列斯坦成为伊朗知识分子中的孤岛,他从伊朗共产党内部斗争中被排挤出来,左派忌惮他的出身和阶层,认为他是象牙塔里的革命者,权贵也早已疏远他;在完成《精灵谷宝藏的秘密》后,古列斯坦放弃了他以及名下制片公司剩余的十几部正在筹备或者正在进行的电影项目并离开了伊朗,几经辗转后在英国伦敦南部的萨塞克斯 (Sussex)定居了下来——他再也没有拍摄过任何电影。
从导演生涯和职业早期的活跃程度来看,两个人似乎拥有了一定的对话基础,尽管这个基础仍然带有法拉哈尼一厢情愿的成分,但正如柏林电影节的策划人塞尔吉奥·范特(Sergio Fant)询问法拉哈尼的问题“你究竟在两个人的通信过程中介入到什么程度”,法拉哈尼回答到“整个过程实际上都是戈达尔占据主导,是他提出了通信,也是他寄出了第一封信。”这注定是一个有着大量不确定性的计划,因为我们很快便发现影片中某种理想化的默契的缺失。不过无论如何,法拉哈尼自然没有必要介入两个人的通信(尽管过程中她帮住院中的古列斯坦回过一封),因为这虽然不是她的信,但这终究将是她的电影。

戈雅的“黑暗绘画”之一《农神吞噬其子》
从2014年9月的第一封信开始,戈达尔就(毫不意外地)放弃了常规的文字交流方式,这封邮件的标题为“G/G the wordking class”,应该是戈达尔用“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开了个玩笑,但“文字王”(wordking)也许是自我或相互加冕的最佳名称。邮件里附上三张低像素的图片,其中两张分别是戈雅(Francisco Goya)的“黑暗绘画”(Pinturas negras)之一《农神吞噬其子》(Saturno devorando a su hijo)的局部[戈达尔从《李尔王》(King Lear,1987)开始并反复在晚期的作品中使用这幅画作],以及德国哲学家弗里茨·毛特纳 (Fritz Mauthner) 的《语言》(Le Langage)法译本封面。在信中戈达尔用英语摘录了这本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驱使批判主义直至我们思考/交谈的,冷静而绝望的自我死亡,如果我们不应该使用一种徒有生活外表的文字来驱使这种批判主义,救赎的行为才得以完成。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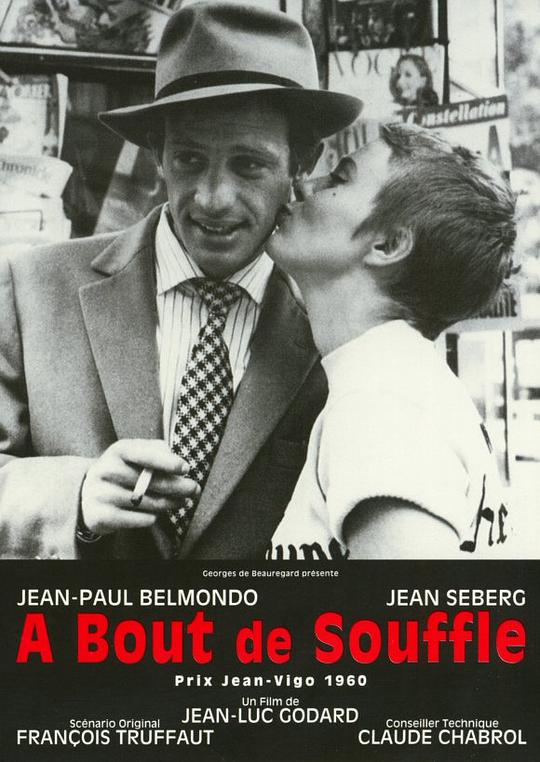
《筋疲力尽》海报
古列斯坦当然认出了这些画作,但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共鸣,面对法拉哈尼迫切的摄影机,他似乎只能从脑海中有限的关于戈达尔的相关信息掏出一些见解。他认为戈雅画中农神的脸庞透露出一种“精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必须持续奔跑到最后一刻,直到自己结束呼吸。”这个说法尽管有些草率,但某个层面上,他的确意外地洞悉到了戈达尔埋藏在谜语之下的无比真挚的生命意愿,信中使用的是英语“自我死亡”(self death),而戈达尔在影片随后的法语独白中复述了这封信,这是一个没有加上“批判主义”(criticism)字眼的版本(细微的改写也是他的一贯手法)——“如果我们能够冷静而绝望地通向我们思想/语言的自愿死亡,如果我们不必携带那些徒有生活外表的文字,救赎的行为才得以完成。③”其中使用的是更明确的法语“自愿死亡”(la mort volontaire)。戈达尔从《再见语言》(Adieu au Langage, 2014)开始就明显表达出对这句话的迷恋,以至于第一封信就如遗书般,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分享了最大也是最后的秘密——八年后他最终选择的离开方式。
古列斯坦是无法接受自杀这种方式和思维的。正如影片随后展示的一个研究“英年早逝”(mort précoce)的博士生对他进行电话采访,也许仍对伊朗作家萨德格·希达亚特(صادق هدایت, Sadegh Hedayat)的自杀仍然感到遗憾,也许是因为他的亲生儿子卡维(Kāveh Golestan),一位就职于BBC的战地记者,过早地死在了伊拉克,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激动和严厉;古列斯坦认为如果一个人活到了高龄,自杀就将不再是个选项,“自杀只会缩短挣扎的时间”,而“救赎”这个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词汇在他看来更是不可思议。在回信中古列斯坦尝试顺着戈达尔的话题谈及了死亡,他从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El 3 de mayo en Madrid)到博罗金诺和阿登战役,奥斯维辛到广岛长崎,旁征博引地试图谈论“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死亡,形而上的死亡,这是他擅长的领域,也或许是想善意地将戈达尔的关注点引开。“死亡”对高龄老人来说是一个共通的话题,此后两位老人的对话也多次在死亡这个危险的话题的周围徘徊,但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古列斯坦几乎不思考自己的死亡(至少不在公开领域),从他早年的考古电影《马尔利克山区》(تپههای مارلیک, The Hills of Marlik, 1963)以来,他思考的几乎都是他者的死亡,人的死亡,过去的逝者对如今存活者的意义,死者的表意(sens)和价值——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对转向相对的概念;而戈达尔关注的是自己的死亡,具身的死亡;也许在他看来,“自己的死亡”是“终极的哲学问题”,一个真正绝对的概念,是比“人的死亡”更终极的命题;他并不是不思考人的死亡,而是用自身的死亡来取代/指代了人的死亡。

被修补过的路面。《星期五见,鲁滨逊》剧照
古列斯坦和戈达尔的旁征博引并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前者的旁征博引是属于文学范畴的,有着清晰的逻辑和论证过程,如同行军般缓缓向观点靠拢包抄;而戈达尔的旁征博引是基于电影的话语,动用材料的指涉和互文等关系构建出一种情境或空间关系,即便征用文字也是基于文字的媒介、材料性和曾经属于的媒介语境,而非仅限于文字表意本身。“戈达尔不再做任何撰写,写作还有什么用,既然这么多东西已经被写下来”④,这也许是为什么戈达尔选择不再继续直接回复古列斯坦的信,他拍下古列斯坦的波斯文书写的局部,附上马蒂斯的画作《蓝色裸体4》(Nu bleu IV)的局部和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段落局部的照片,再加上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巴黎道路保养工人如同书写般用沥青喷射机修补公路裂缝。上述一切被发送到古列斯坦的信箱,并立刻引起了这位伊朗作家的焦虑不安。古列斯坦坦言自己不曾阅读过《芬尼根的守灵夜》,即便他读过所有研究这本书的著作。这几个碎片的拼接也完全没有道理,古列斯坦认为戈达尔是在自娱自乐,并不打算认真交流,同时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上一封信是否过于宽泛而显得平庸。当这种不安平息后,他猜测到戈达尔也许并不是在向他出难题(problem),而是向他提出问题(question)——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
古列斯坦再次写下冗长的回复,阐释他所理解的一种更宽泛的摄像机概念,文字也可以成为摄像机,一个囊括了文学的泛电影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囊括进电影的泛文学概念。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文字和角色拥有其视角和视点,如同见证的摄影机(caméra témoin),荷马史诗和菲尔多西(Ferdowsi)的《列王纪》(Shahnameh)中的战争场景也可以是千年前的电影,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的拍摄比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的改编电影早了三百年,却仍然可以拥有电影的台词效果……古列斯坦强调的并不单单是文字的演绎性,也包括文字的见证,或者文字的义务,如同革命中摄影机的义务,但事实上戈达尔在他的革命年代并不太关心摄影机的义务,法国的革命情景与伊朗相比之下太过模棱,太过借助于表述和想象力,以至于两人失去了探讨电影的共同基础;表达和传达的问题成为革命时期的戈达尔的当务之急,有阶层的原因,也有媒介的原因,但总之在他那里电影的义务、语言的义务盖过了摄影机的义务。
如同发射到茫茫太空寻找外星人的电讯号,这次沟通的愿景似乎又一次落空了。戈达尔在回信中写下了也许是整个通信计划中最多的文字,文字的三个部分都没有直接回应古列斯坦;信中先表示莎士比亚抄袭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时候搞错了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原文(to be or not? to be is the answer?),第二个部分回应古列斯坦认为伊朗塔兹耶(Ta'zieh)无法用语言描绘的观点,将问题延伸至法语的“通用语”(langage courant),“通用语”区别于“俗语”(langage familier)或者“标准语”(langage soutenu),戈达尔取“courant”字面,意为持续流动直至失去其意义的语言,“俗语”和“标准语”都拥有其明确的使用范围(前者小,后者大),而“通用语”则是在流动和讲述中不断变化,不断捡拾和失去意义的,所以“通用语”更倾向于是一种“话语”(parole),而英语和德语中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但恰恰与图像产生“情人般关系”(lovership relation)的是“话语”,而非其他⑤。似乎已经预感到两个人由于缺乏必要的语言系统而难以交流了,戈达尔也随信奉上一段网络热门视频,实际上是从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儿童冒险电影《宙斯和罗克珊》 (Zeus and Roxanne, 1997)将狗和海豚单独剪辑出来的希腊语版本(这段视频本身也是媒介形式不断嬗变的产物)。狗和海豚虽然可以一起嬉戏玩耍,共同历险,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物种,狗可以游泳,海豚也可以跃出海面,但它们终究还是会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环境中。这段视频的最后一个画面,宙斯隔着水下观赏窗与罗克珊四目相对,两者互为图像。正也许正如法拉哈尼所做的,将双方的图像反复带给彼此投影和观看,但也是仅此而已。这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一个段落里,法拉哈尼对“parallèle”进行词汇研究,它兼有“平行”“类似”“相同”和“对比”的意思——类似才可以对比,但平行却无法相交。

《宙斯和罗克珊》剧照。
古列斯坦似乎也失去了耐心,他精疲力尽地写道,“……当牲口群的大多数朝一个方向前进时,随波逐流的会指责那些留在原地或者走向另一个方向的个体。在你看来,我们必须摆脱这种优越感,并且承认我们只是淤泥中的虫子。我们诚然都在同一片淤泥之中。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我们身上侵染的臭味可以证明。然而我既不承认淤泥这个环境,也不承认自己在其中扭动。⑥”这也许携带了一定的偏执和傲慢,法拉哈尼的摄影机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古列斯坦,拍下他的衰老、交谈、开玩笑等私密的场景,然而古列斯坦看似展露无遗,实际上人们对他所知甚少,他某种意义上仍旧是隐居的贵族,对自己的隐私和展示都有着绝妙的调配,而戈达尔的镜头虽少,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却由于更身体力行而更显得展露无遗。

《星期五见,鲁滨逊》剧照
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居所状态来了解他们本人,两个人都不拥有自己的居所,古列斯坦在他宫殿般的别墅中客居数十年,这里古朴豪华,拥有着有明亮高大的落地窗的无数房间以及一个被森林环绕的花园;戈达尔则大多数时间呆在巴黎租来的双层公寓里,天花板低矮,楼梯狭窄,地板上的波斯地毯和杂物充斥着视觉空间。古列斯坦接受访客,常有聚会,有家人和朋友照料他的起居,别墅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戈达尔离群索居,大部分时间自己照顾自己,住所像是他的洞穴,每次散步回来开门如同穴居人推开堵住洞口的巨石般气喘吁吁,巨石般的房门(在通信中他也曾发来自己的影子投在门锁位置的照片)也数次将包括瓦尔达(Agnès Varda)在内的昔日好友挡在外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两种“离群索居”,两位相差甚远的“鲁滨逊”或“星期五”,当古列斯坦在聆听肯普夫(Wilhelm Kempff)弹奏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在豪华的落地窗旁的红色天鹅绒沙发上凝思时,戈达尔喝着兑了水的红酒,观看足球比赛,用手机搜索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 (Vladimir Vysotsky)的《白色浴室》(Ban'ka),观看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荒漠怪客》(Johnny Guitar,1954)并尝试将其剪辑到《影像之书》中。尽管收到一封近乎决裂的信,戈达尔似乎仍要为这个失败的通信计划写下一个结局,他逐字抄下达希尔·哈米特(Samuel Dashiell Hammett)的《瘦子》(The Thin Man)的小说结尾:“‘有可能’,诺拉说,‘但这都相当不尽人意(pretty unsatisfactory)’”⑦,pretty可作“美丽”之意,也可以做“相当”之意。这句话在未来的通信中数次成为其落款。
古列斯坦不像戈达尔般熟识侦探小说,或者不会从如此的通俗文本唤醒同样重要的悸动。但他的兴趣似乎又被召唤回来,并如同心理医生一样,他判定戈达尔有一定量的自命不凡(une certaine dose de prétention),并且断定这种自命不凡来源于自幼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一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为什么自己如此长的写作达不到他如此短的写作同样的复杂性”,他知道戈达尔的意思,却读不懂他的信。戈达尔也许任性,但他终于成功地迫使古列斯坦更明确地承认,他们的无法沟通的问题是语言的分歧——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古列斯坦又一次写下长达五页的,关于语言的回信。古列斯坦可以熟练运用波斯语、英语和法语,戈达尔则讲法语、英语和德语,但正如法拉哈尼在影片中引用戈达尔的画外音“然而语言(langue)终究不是语言(langage)” ⑧所暗示的,两人的分歧的根源不在于langage的不同,而在于langue的不同,但更进一步,又也是langage的不同。戈达尔对语言的期许是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上,一种囊括进图像/话语的总和(une espèce d'ensemble image/parole)。
在观看了戈达尔的一些晚期电影后,古列斯坦更明确地将戈达尔同自己熟识的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他曾最早将海明威的作品翻译为波斯语)比较:“他将各种元素连接起来,而不是编织它们,用碎片形成一种思想框架,是思想的框架让这些碎片形成了意义。”几乎没有办法再将这番对话带有“建设性”地进行下去了,连法拉哈尼也怀疑,所谓的信件往来是否从未发生过。两个人似乎既不能产生对话,也不确定这样泥泞的对话在他们各自生命中可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令人伤感的是,两人的健康情况也分别在恶化,先后住进了医院,同样的生命的状态也许成为了“同样的淤泥”。信件开始有中断,不再有过度冗长的文字,两位老人也互相发送彼此的生活照片,向对方祝福身体健康和新年快乐。古列斯坦有时也开始按照戈达尔的语法进行回复,比如在一封信中,他附上了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基督的洗礼》(The Baptism of Christ)。戈达尔则不时分享自拍、宠物狗的照片、住所旁边的街景、校对到一半的《影像之书》出版物、正在制作的电影截图、《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的封面……邮件常以《瘦子》小说结尾的同一句话作为结尾。在一封名为“特别来信”的邮件中,戈达尔发来了两张照片,躺在医院的古列斯坦和刚刚动完手术的自己。也许只有这种最简单的共情才能跨过设置重重障碍的文字和语言,进入一种纯粹的精神陪伴,如同两个婴儿的交流。先前的无法沟通让两个人降低了对通信计划的期许,然而又必须将对话进行下去,他们必须迅速搭建新的语言系统,或者新的“俗语”(langage familier)。从电影的角度看,这番对话以无效的方式产生了最佳的效果,无效的沟通产生了最有效的电影语言,而为了维持所谓的“沟通”,他们需要使用刚刚完成校准的、崭新却简单的语言模式,对话生效了,但电影却在失效的危险边缘。

《星期五见,鲁滨逊》剧照。
古列斯坦仍旧想聊一些传统话题,比如他提问道“你还相信电影吗?”戈达尔直截了当地形容这个问题如同警察审问,“电影不提问,也不回答,孩子从不问为什么,是大人教他们为什么”。戈达尔质疑的仍然是提问的方式(on peut pas dire ça),而不是问题本身。也许是在最后的影像信中,戈达尔动情地说:我知道你对我第一封信里的“救赎”(redemption)感到不悦,但那不是我说的,那是毛特纳说的,巴赞也曾说“透视(perspective)是西方绘画的原罪,而涅普斯和卢米埃则是其救赎”,接着又一次,戈达尔又一次磕磕绊绊地引用了毛特纳的《语言》的最后一句话,“语言会沉静而绝望地自我死亡,我们无论如何也会渐渐地自我死亡”。正如在一封邮件中他发来自己被夕阳拉长的影子,这是漫长的永别(long adieu)。
法拉哈尼拍摄下人们为了制作铜像,将古列斯坦的头部用石膏蒙住制作模型的过程——紧闭眼睛的白色乳胶像也许是这个百岁老人第一次最直观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世界最终不会遗忘他们,但也许不会以最好的方式铭记他们。法拉哈尼夹在两位巨人中间,尝试用贝多芬和凯鲁比尼的故事来告慰观众(更多是告慰自己)这种尝试没有白费——贝多芬没有写过安魂曲,所以他要求人们在自己下葬时演奏自己最欣赏的作曲家凯鲁比尼的《c小调安魂曲》,然而戈达尔和古列斯坦终究不是这样的关系,音乐也许是一种共通的语言,但却是戈达尔和古列斯坦不曾拥有的语言,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像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中的艺术家们那样豪迈地共同存在,“我是谁?我是诗人!我做什么?我写作!我怎么活着?活着!⑨”,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共同死亡,或者要求在自己的葬礼上安排对方的作品。
如今戈达尔已经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世界,正如他时常引用文本最后的一句话一般,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白和悬念,古列斯坦则刚刚在他清冷的城堡里度过他的百岁生日。他们都曾着迷和挣扎于语言基础如地壳挪移般的变迁,表达的失准和失效所带来的新的语言地貌。法拉哈尼透过这部对话电影,用两人“未通信的通信”和“通信的未通信”暗示出深埋在源于古典主义罅隙中并穿越现代主义朝向两个方向,缠绕至今的绵长错位和缓慢的和解。古列斯坦大体上仍是传统主义的思想巨人,他思辨仍挣扎于现代性框架下的宗教和道德,语言仍旧是语言,语言的问题需要由语言来解决,语言是一种存在。而在戈达尔这里,关于宗教和道德的讨论几乎不需要进行完整有效的探讨,或者这些探讨都必须经由探讨语言来完成,语言已经不再是语言,存在即语言。
最终在法拉哈尼准备的投影机里,古列斯坦看到同样衰老孤单、呼吸困难的戈达尔如同弗朗切西卡《基督的洗礼》背景中正在脱衣服的人一样脱掉外套,他关掉卧室的灯,在黑暗中借助手机照明吃力地阅读《瘦子》的结尾——借由精心准备的图像、声音和对准他的摄影机,借由意象的偶然符合,借由总和近两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他最终触到了跟这位且近且远的老友相同的心理位置——“pretty unsatisfactory”的语意悄然浮现——这两个词汇是在孤独中日渐衰老的两人历经数年的试探、挣扎、揣测、和解,历经殚精竭虑最终达到的唯一成果。他眼眶湿润地低声说道:
“没错,这很明显,这都美好又不尽人意。”
注释:
① “Io sono una forza del passato”(Poesia in forma di rosa)《玫瑰形状的诗篇》
ISBN 978-88-11-14016-0 © Garzanti Editore s.p.a., 1964, 1976 © 1999, 2001, Garzanti Libri s.r.l., Milano Gruppo editoriale Mauri Spagnol
②信的原文为
"the act of redemption would
be accomplished if one could
drive criticism till self death,
quietly desperate, of our
thinking/talking,
if we ought to not conduct that
criticism with words which
have only the appearance
of life"
all the best, your boy Friday
5 september 2014, JLG
③ On accomplirai l’acte rédempteur, si l’on pouvait conduire jusqu’à la mort volontaire,
sagement désespéré, de notre pensée/parlée, s’il ne fallait pas conduire avec les mots qui ont l’apparence de la vie.
④ Godard n'a rien rédigé: à quoi bon écrire, puisque tant de choses ont déjà été écrites. Telle est sa devise. Luc Moullet, “Le film cosmique: Puissance de la parole”, Bref, nº 68, 2005.
⑤信件原文为
Marlowe wrote:
to be or not? to be is the answer?
and then the great Will copied
Wrongly: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
why describe (in your last g/g5)
itinerant ta'zieh playing magic,
with words saying that there are no words to describe all that
magical enchantment,
there must be some rotten devil
in our current langage (in french, we say: langage courant, running langage, and we end
by saying/writing: courant à sa perte, running to its loss
———————————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image
and "parole", the french word, but, but, but, but, but, but
there is no word for
"parole"
in english (only word or speech,
the same in german)
the lovership relation between
image and "parole" can be seen
⑥ Quand la majorité du troupeau va dans un sens, le conformisme stipule que l'élément resté immobile, ou ayant pris un autre chemin, soit isolé qu'il soit montré du doigt, vu comme opposé aux autres. Selon toi, il faut se défaire de ce sentiment de supériorité et admettre que l'on n'est qu'un vermisseau dans la même vase. Certes, nous sommes dans la même vase. Que nous l'admettions ou non, cette puanteur qui nous imprègne en témoigne. Mais je ne reconnais ni la vase comme milieu ni moi-même comme vermisseau qui s'y tortille.
⑦ That maybe, Nora said, but it’s all pretty unsatisfactory.
⑧ Mais la langue ne sera jamais le langage
⑨Chi son? Sono un poeta.
Che cosa faccio? Scrivo.
E come vivo? Vivo.
⑩ Yes, obviously, it is pretty unsatisfactory
参考文献:
Iranian Cinema: Before the Revolution, Shahin Parhami Off Screen Volume 3, issue 6 / November 1999;
Berlinale Archive À vendredi, Robinson, Encounters 2022 Interview · Jan 25, 2022;
Comprendre Godard - 2e édition Travelling avant sur À bout de souffle et Le Mépris Michel Marie, 2006, Armand Colin;
“Le film cosmique: Puissance de la parole”, Luc Moullet, Bref, nº 68, 2005.;
Ebrahim Golestan Treasure of Pre-Revolutionary Iranian Cinema Mehrnaz Saeed-Vafa, Rouge 2007;
Interview with Ebrahim Golestan Stanford Iranian Studies Program by Dr. Abbas Milani.2015.11.3;
Jean-Luc Godard Morale Archéologique,Dmitry Golotyuk et Antonina Derzhitskaya le 12 septembre 2017;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