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鸣生:我与人文社,素交三十年

2022年12月17日,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为表达缅怀之情,今天我们特别推出李鸣生先生写于两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之际的文章《我与人文社,素交三十年》。从《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到《敢为天下先》,人文社与李鸣生先生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已超越友谊。如今斯人已去,再次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不觉生命倏忽。愿来世我们以另一种形式久别重逢,再续前缘。
我与人文社,素交三十年
李鸣生
三十年来我与人文的交往,不过就是一种“素交”罢了。所谓素交,在我理解中就是一种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淡然相处,素似花骨,淡如春风。
一转眼,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七十年了。而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交往,屈指算来,也整整三十年矣。
三十年不算短,想说的话似乎很多,却又不知说啥是好。我知道,作家们写人文社的好文章多了去了,我若再写一篇,也就凑个数而已。既如此,那就简单说说我与人文社三十年来的交往情况吧。
我与人文社第一次交往,是1990年。我之所以与人文社交往,缘于人文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当代》,乃全国响当当的名刊,尽管那时的我还在一个原始的大山沟——西昌卫星发射场——当兵,但《当代》每期发表的报告文学,都是我的必读之作。正因此,我记住了《当代》,也记住了《当代》一位编辑的名字,她叫刘茵。
而我亲眼见到刘茵老师本人,则是十年之后了。198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二年初夏的一天,军艺文学系与《当代》杂志举办座谈会,那天刘茵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当我第一眼从座位牌上看到“刘茵”二字时,我喜出望外,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代》发表报告文学,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刘茵老师就是《当代》专门负责报告文学的编辑。于是会后我找到刘茵老师,把我当时正着手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构思和她简单聊了聊,恳请得到她的指导(当时在场的还有《当代》的年轻编辑杨新岚)。刘茵老师听完我的构想后,说,题材很新鲜,主题也很有新意。这样,你先不要考虑别的,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写完,然后先给我看,我看后再与你联系。听了这话,我好似吃下一粒定心丸;刘茵老师的随和、亲切与真诚,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个月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当即复印一份,寄给了刘茵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给《当代》这样的名刊投稿,有信心却无把握。但十天后,我便接到了刘茵老师的电话:稿子看了,不错,题材新,观念新,思维方式也很新,我们初步考虑刊用。但书稿太长,不能全文发,你最好能来出版社招待所住两天,把书稿再压一压。我放下电话,兴奋不已。但军艺有规定,学员不能在外过夜,我只好利用周六偷偷溜了出去,然后在刘茵老师的安排下住进了人文社招待所。
人文社的招待所位于人文社的后楼,狭小简陋,寂寂无闻,若与北京的豪华大酒店相比,最多算个火柴盒。但后来我才得知,中国不少重量级作家都在这个“火柴盒”里改过稿,并由此登上文坛,扬名天下。我在这个“火柴盒”住了两天,昏天黑地,昼夜不分,顿顿方便面,没出过一次门。改完稿那天,已是凌晨5点,我站在朝内大街166号的门前,望着初升的太阳,像熬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一封发自首都机场的来信,打开一看,是《当代》副主编何启治老师的亲笔,大意说,他现在在首都机场,马上准备登机,但书稿还没看完,不能及时回复,等出差回来后,尽快复我,不要着急。来信虽短短几行字,却令我感动。当时,《当代》的主编是秦兆阳,执行主编是朱盛昌,稿子经何启治、朱盛昌二位老师终审后,很快决定发表。不过后来我听刘茵老师说,稿子决定发表前,编辑部也是有过顾虑的。一是此稿题材重大,内容敏感;二是思维超前,打破了某些写作“禁区”;三是稿子只有保密部门的意见,其他部门还在审查中,结果未卜。发表此稿,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但是,1991年《当代》第1期,还是用头条隆重推出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接着,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等全国上百家报刊先后选发连载了此稿,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可有关部门的某些人很快找上门来,要追究责任。幸而《当代》挺身而出,为我遮风挡雨,其回答很朴实却有力:“《当代》编辑部有严格的三审制,只要作品没有泄密问题,其他问题由我们负责。”这才为我解了后顾之忧。

《飞向太空港》 李鸣生著
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又联合举办了《飞向太空港》作品研讨会,会议由社长陈早春先生主持,老前辈屠岸先生及评论家冯立三、雷达、白烨、李炳银、朱向前等二十多位专家也到场力挺。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一次作品研讨会,对我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者来说,其鼓舞之大可想而知。1992年,《飞向太空港》获1990—1991年度全优秀报告文学奖,它既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也是我的成名作。
我与人文社的第二次交往,是1993年。这年2月,我写完航天系列第二部《澳星风险发射》后,毫不犹豫地又给了《当代》。此稿写的是中国发射连连失败的问题,而失败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选题,何况用一部长篇来写失败,国内尚无先例。但《当代》经认真商讨后,认为此稿虽然写的是失败问题,切入角度却很巧,于是还是在1993年第2期头条推出了此稿(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副主编是朱盛昌、何启治、胡德培);接着,人文社主办的《中华文学选刊》于1993年第2期头条选发了此稿;再接着,《当代》和《中华文学选刊》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澳星风险发射》作品研讨会,会议由朱盛昌老师主持。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二次作品研讨会。此稿后来获1992—1993年505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当代》“大科技杯”征文奖、1985—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当代》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三次交往,是1995年。这年5月,我完成了我的航天系列第三部《走出地球村》。在人文社出书,和当初我希望在《当代》发表作品一样,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但我知道,人文社对书稿要求很高,而我的水平有限,于是当此稿还在构思阶段——大概是1991年下半年时,我便与人文社编辑部主任李昕先生取得联系,在他办公室谈了我的基本构想。李昕主任听罢我的构想后,对其题材和构想都给了充分的肯定,不光提出建设性意见,还对书稿寄予厚望,并一再强调,书稿写完后一定先给他看!而且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李昕主任也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写作进程,每次见面都会问问书稿的进展情况,不光给予我写作的动力,还为写好此书增添了信心。所以书稿刚写完,我便送到李昕主任和刘茵老师的手上。但此稿涉及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正如李昕主任后来在此书的序中所写的那样:“《走出地球村》真正要写的已不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作家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实用意是以我国第一颗卫星研制的线索为经,以冷战环境下的国际对抗和竞争为纬,以一批堪称‘中国的脊梁’的杰出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活动为中心,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史进行一次痛切而深沉的整体剖析和全面反思。”因此,此书的出版难度可想而知。但后经李昕主任和责任编辑龚玉大姐的用心把控,倾力打造,此书还是于1995年12月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李昕主任还特意为此书作序,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认为《走出地球村》不仅是李鸣生个人创作上的一个突破,而且在我国当前乃至整个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它也是独具价值、独具地位、独具光彩的佳作。”

而与此同时,《当代》也于1995年第4期隆重推出此稿(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主编是朱盛昌,副主编是胡德培、常振家、汪兆骞);接着,《中华文学选刊》于1995年第5期头条选发了此稿;再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走出地球村》的作品研讨会。这是人文社为我召开的第三次作品研讨会。1998年,《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四次交往,是1999年。这年《当代》第2期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国家大事》,责任编辑是副主编汪兆骞。兆骞老师既是资深的编辑,又是知名的学者、作家,眼光独到,思想敏锐,我后来看到他力荐《国家大事》而写下的编审意见,可谓言简意赅,深刻精准,一针见血。此稿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在1999年第4期选发,后获中国报告文学首届“正泰杯”大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五次交往,是2003年。这一年,中国宇航员杨利伟上天,我的航天系列第五部《风雨长征号》恰好写完,我便将此稿交到了刚刚出任副社长的潘凯雄手上。凯雄副社长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人文社举办《飞向太空港》研讨会时,他就代表《文艺报》到会捧场;后来他在经济日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还出过我的一部长篇。他到人文社后我们便说好,我的下部书稿交由他出。此稿后经胡玉萍编审和陶良华主任精心编辑,于2003年10月顺利出版。本来,此书人文社也是准备要开个研讨会的,因当时我正在外地忙于一部电影故事片和电影纪录片的创作,本已筹备好的研讨会只好作罢。此书后来入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六次交往,也是2003年。这年年底,人文社出版了我的《毛泽东和他的随行摄影记者》(组稿是副社长潘凯雄,责任编辑是资深编辑龚玉大姐)。此稿属重大题材,加之照片繁多,送审、编辑、排版等工作都颇费周折。但经凯雄副社长精心策划、龚玉大姐认真编辑,此书不仅出版顺利,且品相甚好。
我与人文社的第七次交往,是2010年。这一年,我完成了我航天系列的第七部《发射将军》。由于此书很可能是我“航天七部曲”的最后一部,我自己比较看重,经慎重考虑,便同时交到了编辑室主任脚印和《当代》编委杨新岚的手上。脚印和杨新岚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我很看重、信任的编辑,所以多年前我就有给她俩一部稿子的打算。两位女将思想敏锐,眼光独到,看稿速度极快,短短一周左右,便分别给我打来电话。杨新岚说,稿子不错,留用了。但考虑到有些内容涉及审稿问题,不能全文发,只能从中选发几章。脚印说,书稿看了,也送给潘凯雄社长看了,感觉很好。但有一个问题,此稿属重大题材,按规定,必须走一下送审程序……
听到“送审”二字,我心跳顿时加快。二十年来,由于我写的题材几乎都属“重大”,书稿总是一次次地送审,而每次送审,我的心里都会经历一个战战兢兢的过程;尤其是第一部书稿被审了一年多,最后还无疾而终,此后似乎便落下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后遗症,所以有时宁可书不出,也不愿送审。但我也非常清楚,人文社隶属新闻总署,此稿是必须要走送审程序的。于是我犹豫再三,只有对脚印如实相告:这样,给我一周时间,我给别的出版社看看,如果别的社可以不送审,那请原谅我的自私;如果别的社也要送审,我再拿回来请你出。
结果,很遗憾,全书最终未能在人文社出版。尽管善解人意的脚印宽容大量,并不介意,我却感到愧对脚印。而《当代》这边,由于杨新岚摘选的五六万字无须送审,所以《发射将军》有幸在《当代》2010年第3期得以发表(责任编辑是杨新岚,二审是编委周昌义,三审是主编洪清波)。此稿后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10年第三站冠军。
我与人文社的第八次交往,是2017年。这年8月的一天,接到脚印的电话,说希望出版我的《飞向太空港》。此稿27年前发表于《当代》,27年后居然又成了所谓的“经典”,当时多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都希望出版此书。而我想保证此书的质量,不希望版本出得太多,所以谢绝了多家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的好意。接到脚印的电话,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甚至连合同都不用看。此书出版后(责任编辑是脚印和王蔚),三年时间,再版11次,如今总印数已累计三十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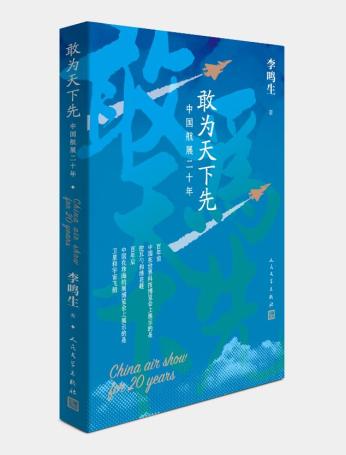
《敢为天下先》 李鸣生著
我与人文社的第九次交往,是2019年。这一年,我完成长篇纪实文学《敢为天下先》后,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脚印,我总觉得欠她一部稿似的。虽然此书也属重大题材,但由于此前相关部门有过审查,再经脚印和张梦瑶两位责任编辑做些技术性处理后,很快得以顺利出版。接着,人文社又为此书举办了作品研讨会,社长臧永清先生主持会议,并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李鸣生是人文社的老朋友了。这么多年,非常感谢李鸣生先生对人文社的信任和支持。《敢为天下先》是人文社近期推出的李鸣生的最新力作,也是当代纪实文学又一新的高度。李鸣生是一位有社会担当、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史诗风范和崇高品格,我想这也是各位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的原因。让我们怀着对李鸣生先生的敬意和钦佩,来共同探讨他的这部最新作品吧。”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四次作品研讨会。
以上,便是我与人文社三十年来九次交往的基本情况。我之所以记录于此,意在证明,在我三十年的创作路上,人文社的确给过我很大的支持、帮助与鼓励;甚至说,没有当年《当代》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我对人文社一直心存感激!
然而,扪心自问,我的这种感激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并无什么实际行动,所以总有一种内疚感。比如说,三十年来,记忆中我好像还从未请人文社的编辑们喝过一杯酒,吃过一次饭,每次去到他们简陋的办公室,坐在摇晃不定的沙发上,一杯清茶,几句寒暄,除了谈稿还是谈稿。尽管其间我也多次想过请他们聚一聚,可不知何故,每次想到要饭桌相见,便踌躇不前。老实说,这还真不是抠门,而是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亵渎了那份多年来自然生成的纯粹?于是便想,对人文社编辑们的最好感激,也许就是尽可能交出两部像样的书稿吧。再比如说,几位曾经给予我很大支持、帮助与鼓励的编辑老师——陈早春、屠岸、高贤均、陶良华、刘茵、朱盛昌,我本该在他们生前给予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可我还没顾得上好好关心、感激他们,他们便匆匆驾鹤西去。每当想起这事,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而尤其让我深感内疚的,是刘茵和朱盛昌两位老师。刘茵老师是2015年2月28日逝世的,在她去世的两天前,我还给她打过电话,说等抽空去看望她,不料两天后,她竟不辞而别。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后悔莫及。刘茵老师是我文学路上的伯乐和恩人,中国不少惊世骇俗、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均经由她手,故在文学界享有“中国报告文学的保姆”的美誉。她高贵的品德、善良的心灵、无私的敬业精神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我树立了人格的榜样。可在她的晚年,我却没能好好地关心她、照顾她,没有尽到一个作者对编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事至今我都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在我看来,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不该只是单纯的作品的关系,除了作品,还有人情,还有善良,甚至还有悲悯与日常。为表达我对她的追思与怀念,在她的追悼会上,我为她敬献的挽联是:
当保姆育作家 呕心沥血两袖清风
做好人爱朋友 良知不灭隐忍一生
朱盛昌老师是2019年1月17日逝世的,本来,好几年前我就有过计划,等退休后一定去拜望他。可惜我一次次错失机会,最终留下遗憾。为表达我对他的追思与怀念,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为他敬献的挽联是:
一生寂默大编辑
两袖书卷真文人
总而言之,三十年来我与人文社的交往,不过就是一种“素交”罢了。所谓素交,在我理解中就是一种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淡然相处,素似花骨,淡如春风;未见时默想着对方,见面时执手相望,无所不聊;即便彼此天涯海角,非但毫不生疏,反而倍感亲近,不为功利,只为懂得与相惜。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所以,在五花八门的人际交往中,我乐意素交。
最后,我想说的是,身为一个写作者,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往三十年,是我的幸运!而我之所以愿意与人文社交往,一是人文社藏龙卧虎,群贤毕至,既有优良的编辑传统,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二是编辑队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编辑水平和鉴赏眼光;三是恪守职业操守,善待作家与作品,讲道义,重友情,守承诺,有信誉。简而言之一句话:值得信任。故此,倘若今后还有机会, 我仍愿与之交往。当然了,君子之交,素交为上,我最乐意并享受的,恐怕还是只有素交了。
2020年12月3日匆匆记于北京

李鸣生
四川简阳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中国863》《全球寻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后地震时代》《德能无量》及“航天七部曲”等二十八部,出版《李鸣生文集》(十六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军文学作品特等奖等。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原标题:《李鸣生:我与人文社,素交三十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