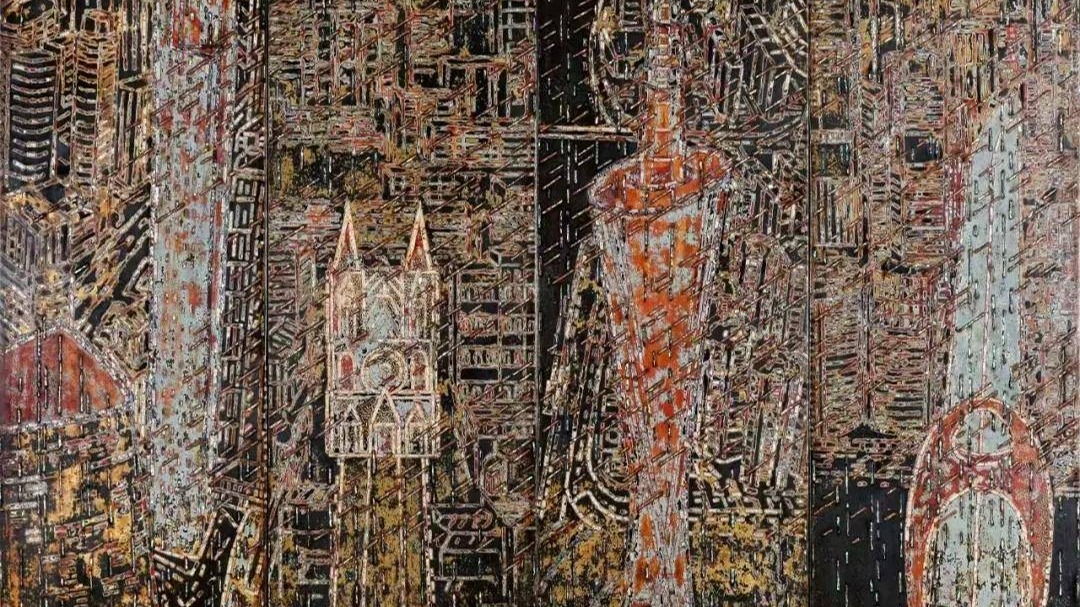- 3
- +1
杨阳:灯不倾灭
原创 Madame Figaro MadameFigaro
拍了半辈子戏后,杨阳打算拍一辈子——哪天感觉灯枯油尽了,那就可以收山。但在此之前要一直拍,一部一部,心无旁骛地,拍下去。

半个月前,新戏《不完美受害人》杀青,杨阳从青岛回到北京。一同抵达的,还有四只鹦鹉和一株不知道名字的绿植。
秋天的时候,杨阳突发奇想,买了十只蛋和一个保温箱放在身边——她想看看孵出来的小鸟什么样。20多天后,戏尚未杀青,四只鹦鹉相继破壳。头天夜里,她起来三次,给它们喂奶粉,一天天地照料着。如今嗷嗷待哺的小家伙都已长成成鸟,杨阳感叹,整个过程跟孕育一部戏很相似。她用新戏剧名给它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布布,一只叫小丸子,剩下两只分别是小美和“受害人”。
北京的家里还有第五只——是《梦华录》里迟衙内养在府上的那只。去年夏天,戏杀青后,大家各自回家,杨阳担心小家伙无处可去,便把它带回了北京。她称自己家是个“动植物乐园”,家里最多的时候有13只鸟,7条狗,两只猫,很多条鱼,半屋子植物。其中大多都是她从各个剧组带回。那株不知道名字的绿植,原本也是戏里的道具,她从拍摄现场带到剧组酒店,后来又带回了北京。

杨阳自小喜欢自然,与动植物亲近,早年间做编剧时曾给自己起过一个“杨梓鹤”的笔名——梓是一种树,喜光,人常说“桑梓有情”;鹤是仙鹤,清正平和。“杨梓鹤”象征着她的内心世界,公共领域里,她则以导演杨阳被大众熟知。百科资料显示,自198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导演专业毕业,杨阳一共执导了16部电视剧,其中包括引发全民收视热潮的《牵手》和《梦华录》。实际数量则远不止于此,杨阳也没认真算过。每次戏播出的时候,她也不看,担心看到不足,自己给自己添堵。
“每部戏完成混录后,我就在心里跟它们say goodbye了。”过往采访里,杨阳多次提到过“归零”。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杨阳身上有这一代人的集体特质,谦逊、勤勉以及脚踏实地。“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了很多。”杨阳说。母亲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小时候在家里,杨阳总能看到她在特别认真背台词,写很厚的人物小传,“写得像小说一样”。起初,她以为母亲演的是主角,等戏上了才知道,其实只是配角。


小时候的杨阳性格腼腆,见到生人会害羞,说话也不敢大声说,话剧院导演的父亲给她选择的道路是拉小提琴。考大学时,她临时起意,报考了导演专业,父亲大怒,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杨阳的父亲就是做导演的,知道这条路非常难。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一名导演的基本特质在当时的杨阳身上并不显性,或者说,她更像是这些的反面——拉小提琴时,她总喜欢躲在乐队后面。除此之外,她还是个女性,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导演凤毛麟角。
父亲的担心,在杨阳的职业初期都一一应验。内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率领团队不够强势,作为年轻的女性导演,在更有经验的合作者看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当时我对自己很失望,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性格,就想说要不算了,不做导演了。但隔了段时间,遇到个好选题,我又激动起来,就又去做,然后又接着失望。”挫败感和创作欲交替闪现,杨阳在其间沉浮过一段时间。



直至1996年拍摄《牛玉琴的树》。杨阳说:“这部戏感召了我,让我忘记了自己性格的弱点,所有杂念抛开,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创作中。”《牛玉琴的树》为杨阳带来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巨大荣誉——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但这部戏的最大意义并不在此,而是在外人无法企及的内心世界,杨阳确知了自己的内心——以后不管再苦再难,都会一直走下去。那时,她依然年轻,依然是个女生,说话声音依然很小,但没有一个人再对她有所质疑。
包括父亲。具体是不是从这部戏开始,杨阳不确定,她没问过,也不敢问。她自小怕他,成为导演后,父亲一直是她非常严苛的一个观众,“或者是千千万万人中最严苛的那个”。她从没在他那里听到过任何表扬,即使当年拿着飞天奖奖杯回到家中,父亲也只是淡淡说了句,这是你运气好。杨阳理解父亲是怕她骄傲,习惯性泼一些冷水。但自己成为母亲后,杨阳还是换了一种方式面对孩子,并不吝鼓励和赞美。

北京广播学院1979年这一届电视系导演专业,一个班一共15人,其中9个男生,6个女生。杨阳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学生,也是唯一现在还在从事导演工作的女性。其他同学,有的留校当了老师,有的在电视台做编导,有的经商、还有的成了画家。
大学时,杨阳学习成绩拔尖,是班上唯二被分配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的——另一位是个男生。当时制作中心被称为中国电视剧的国家队,云集了这个行业最顶尖的人才,86版的《西游记》、87版的《红楼梦》等经典都出自于此。
杨阳从场记做起,副导演、剪辑、编剧,几乎把所有工种都试过一遍。80年代末,她根据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非重点》,执导了自己第一部戏。那是中国电视剧起飞的年代,人人争做精品,杨阳在制作中心活跃也严谨的氛围里完成了早期的职业启蒙。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弥足珍贵。“相当于你刚刚走入社会,就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里,所有人高标准严要求,受到的都是相当规范的训练。”


过去数年,国产电视剧的制作周期不断缩短,杨阳也从以前三五年磨一剑到现在一年一两部戏。“做精品这一初衷从没变过。”杨阳说,创作频率的提升,一方面依赖于电视剧市场需求量变大,另一方面则是拍摄技术的进步以及从业人员专业度的提升。她举例,以前我们都是单机拍摄,现在是3机乃至4机。
大量实景拍摄是杨阳的风格之一。真实呈现以外,杨阳相信自然的光感、风吹树叶的声音给每一位创作人员带来的兴奋感和创造力,是在绿棚里无法企及的。她并非排斥绿棚,只是拒绝“五毛钱特效”。现在行业里通用的LED屏幕辅助拍摄开车戏的手法,因为无限接近真实,杨阳也很是认可。在这件事上,她的标准并不复杂,每部戏开拍前,她都会实地走访采风。“当我觉得实景里感受到的东西,在绿棚里边不太容易做到或者做不了那么好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实景。”
2016年筹备《将夜》,制片人对杨阳说,几百上千人的团队,从襄阳到贵州再到新疆,还有南疆北疆的跨越,团队太折腾,片方压力也大。杨阳还是坚持。“实景风光呈现出来的确不一样。”她说,这方面我可能比较任性,也执拗,但创作关乎真诚,创作者什么样的创作态度,决定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2018年,《将夜》播出。这是杨阳执导的第一部IP 改编作品,在大多男频网文改编的影视剧都不尽如人意之际,《将夜》迎来了口碑和收视的双重认可。豆瓣上7万多人打出了7.4分,其中最高赞的一条短评是:春风亭,年度最佳打戏!再往下,“这就是我心目中将夜的样子”,3274个人点了“有用”。

除了偶尔看看自己微博下的评论,杨阳很少关注网络上的其他声音。今年夏天,《梦华录》一石激起千层浪,杨阳还是感受到了——她甚至在法制报上看到了有关宋制的讨论。
“不管褒贬,所有破圈讨论其实都是这部作品的福气。”杨阳说。她理解大家可能需要这样一部戏来释放他们对相关社会议题的观点和看法,认为如果有人因为争论这部戏生发了更多思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作品本身就在那了。
“是否有一刻想过,当时要是换一种方式处理就好了?”
“没有。创作就是创作,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当时有尽心尽力做,所以无论结果怎样,我都问心无愧。”

身为女性导演,又拍了个女性互助的故事,人们想当然地为杨阳镀上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弧光。但她一再重申,我没有那么强的性别意识。相比“女性”,杨阳更注重的是“导演”。她拍过三个女人的戏,也拍过一群大男人的戏,始终最吸引她的还是“人”的部分。在她的剧组里,有连续合作了多部戏的女性造型指导,也有合作了十多年的男性摄影指导,有留长发的男性,也有剃寸头的女性。而她自己在工作中就是个“中性人”。
起初,这份中性是“装扮”出来的。杨阳回忆,刚入行那会儿,身边都是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她想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一直留短发,从不化妆,经常一身冲锋衣。后来无所谓“装”了,但习惯已成自然。剧组时间也紧凑,她每天起床,把自己收拾干净,头发随意地扎起,有时直接一顶棒球帽带上,就风风火火地开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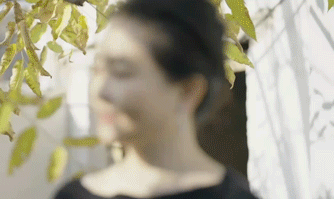

“性别这些其实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的人格魅力,是不是能够带领大家。”杨阳回忆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做导演,面对几十上百人的剧组,自己先露了怯,所以才表现得没那么大说服力。如果是一位刚起步的男性导演呢?杨阳认为困境也同样存在。她说,于创作者而言,困难是不分性别的,不会因为你是男导演就少,女导演就多。
但每年三八妇女节,杨阳会给剧组每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准备一枝玫瑰花。我们聊起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现在的男女学生比例,“一个班28人中有13位是女性”,数量是她上学那会儿的两倍,她欣慰地笑了。

杨阳的剧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设开机宴和关机宴。她称自己有点社恐,一面对饭局这种事就紧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祝酒词什么的更是不会。
以戏会友,是她认为创作者之间更舒服的相处方式。但若是哪天收工早,又或者赶上春节,她也会组织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个饭。“到了随便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时候就不是应酬,只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开心。”《不完美受害人》杀青当晚,杨阳叫上导演组、摄影组、灯光组和很多场务兄弟,一行二三十人,浩浩荡荡地去吃了顿涮羊肉。
杨阳有些感慨,以前她总是一个团队里最小的,现在身边的合作伙伴一个比一个年轻,从80后到90后,00后也越来越普遍。杨阳很少谈论自己年纪,问起时,她俏皮地喊停,“不能说”,而后补充道,“我享受自己跟大家一边大”。
某种程度上,杨阳确实是一个没有年代感的导演。从上世纪90年代的《牵手》、本世纪初《记忆的证明》、10年代的《心术》以及最近20年代的《梦华录》,她的观众跨越各个年龄阶层,作品在不同时代里都掀起过热烈讨论。“保持学习很重要。”杨阳总结。


每拍一部戏,她都力求自己先成为这一方面的学习者。拍历史剧《记忆的证明》,她看了大量二战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影像图片,读战争亲历者写的日记;拍医疗剧《心术》,她去医院做了大量一线采访;新戏《不完美受害人》是个关于法与情的故事,她又开始研究法理。《梦华录》之前,杨阳没拍过宋代的戏,正式开机前,她进行了大半年的前期筹备:看宋代相关的书籍史料,研究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走访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看瓷器展、画展,像个社会学家一样,做各种各样的田野调查。
剧本是文本化的故事,如何转化成自己风格的影像语言,是另一个难题。杨阳每每辗转许久。每一部戏,她都习惯先找到一个特有的氛围或意境,类似一团线里线头的东西,再由着这个线头铺陈开来。众所周知的,《梦华录》的线头是水,《将夜》是大漠风光,更早之前的《牵手》则是歌手苏芮演唱的同名歌曲。
有遇到过那种找不到的情况吗?杨阳笑,我比较幸运,想啊想,找啊找,总是能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杨阳说话轻,语速和缓。不管镜头前接受采访时,还是镜头后拿着对讲机时,她看上去总是很平静,透着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儒雅。
《牛玉琴的树》剧组见过一回杨阳发火的样子。那是拍摄一场痛哭戏,两分多钟的长镜头,演员萨日娜充满激情地完成了表演,最后哭晕倒坐在地上。喊停之后,所有人都很感动,杨阳也在那默默擦眼泪。一旁的录音师突然对她说,导演对不起,我刚才忘了开录音。杨阳顿时感觉“一股血就窜到了脑袋顶上”,她一句话没说,抬腿就往沙漠里走。所有人都吓坏了,跟在后面追,问导演你要去哪。杨阳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她就想一直这样走下去。
录音师吓坏了,跟她说,导演您骂我吧。她还是说不出一句骂人的话,最后只撂下一句,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该道歉的人是萨日娜。“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愤怒的一次。”杨阳形容,非常脑溢血的气法。后来剧组还是会有类似状况发生,但她再也没那么生气过。
“但你说平静吗?我觉得也不是。创作者不可能平静的。他如果太过平静,也很难创作出有激情的东西。”每次接到一部自己喜欢的戏,杨阳都会好一阵兴奋,“就像小孩子得到了一个心仪的玩具”。入行三十余年里,她几乎马不停蹄,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作品和观众见面,很少有真正停下来的时候。印象中最长的一段休息是2020年春,从1月到5月,四个月时间。

偶尔,一部戏临近杀青,杨阳会生出一丝“累”的感觉。她便开始驰想,等杀青了要去哪哪休假。但每每戏一杀青,就是紧锣密鼓的后期,忙完后期,下一部戏的前期筹备又开始了。杨阳说,其实不是你找事干,是很多事来找你,除非把手机关了。显然,现在还不是闭关的时候。过去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生活与创作是一体,知足并感恩当下拥有的一切。
以往每年开年,杨阳都会想,今年有没有可能拍一部电影。她自小喜欢看电影,当初报考导演专业,想的也是以后拍电影。“但不知怎么一直走在了电视剧的创作道路上,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路。”杨阳笑。期间,她也收到过几次电影邀约,看了看题材剧本,最后还是没接。如今,杨阳依然对电影保持着一颗崇敬之心,但拍电影的执念已经过去。她说,其实无论拍什么都是为了表达,是为了把自己心里对大千世界的爱传递出去。
爱不灭,表达就不会停止。拍了半辈子戏后,杨阳打算拍一辈子——哪天感觉灯枯油尽了,那就可以收山。但在此之前要一直拍,一部一部,心无旁骛地,拍下去。
原标题:《杨阳:灯不倾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 习近平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
- 国台办回应美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现况

- 多地自然资源部门回应土地收储涉及的“企业土地成本”:包含出让金及企业投入的各项税费、利息等直接成本
- 加拿大官员:将对美国加征关税作出“有力回应”

- 国漫之光,中国影史票房榜第一;现暂列世界影史票房榜第九
-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哪个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