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了“门当户对”,我向男友隐瞒了自己的贫困县出身 | 三明治

原创 静静收小妖的小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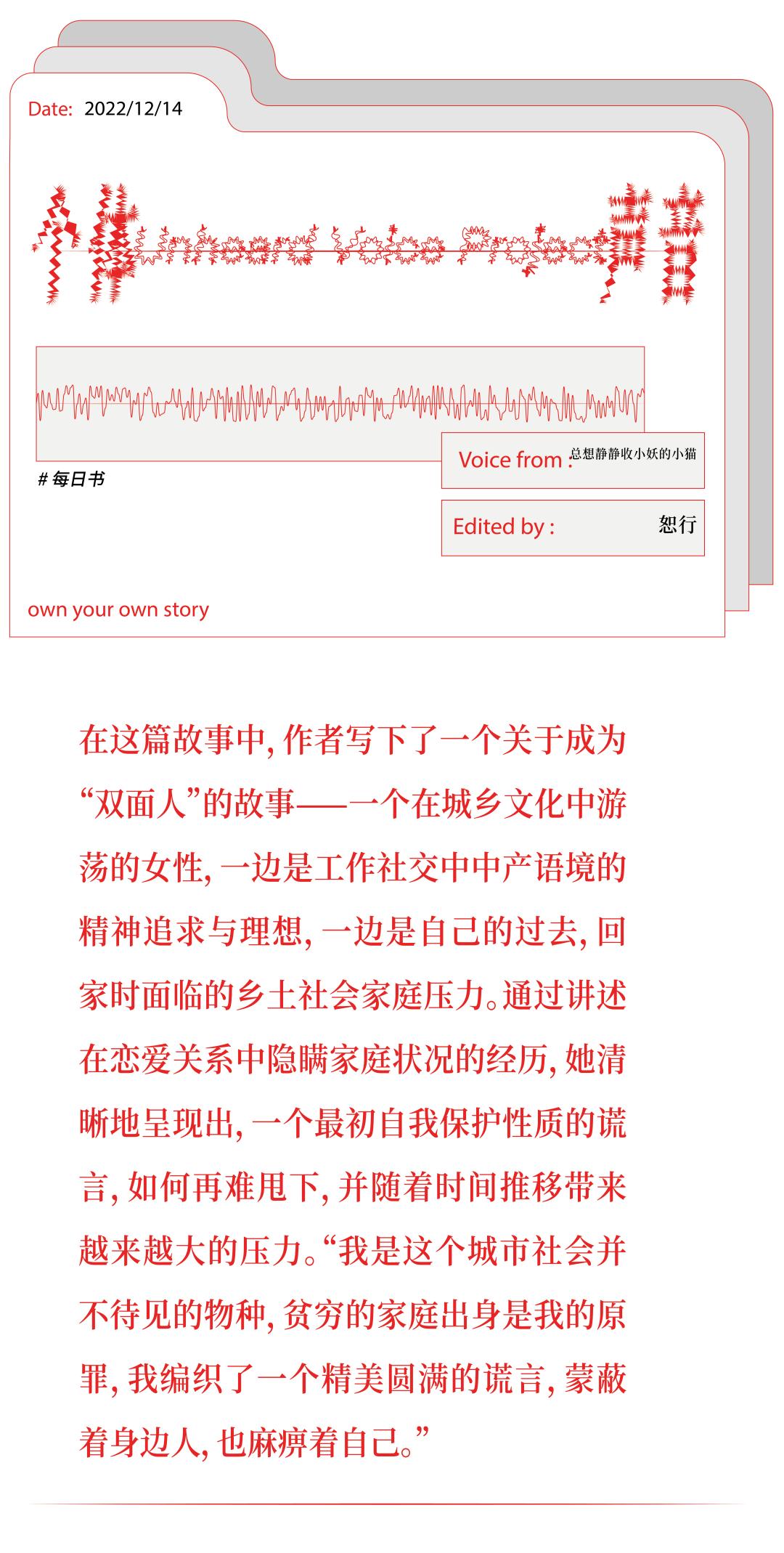

和男友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再次延续了那个精心编织许久的谎言。
在我们聊起家庭时,他说父亲是工程师,妈妈是老师,自己在上海长大。我脱口而出:“我妈也是老师,我是西安人。”自从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维持家境优渥的虚假人设。
我与他相识于一个线下狼人杀社团。散场后,我们恰巧乘坐同一辆地铁,期间聊到了我正在看的《浮生六记》。他认为沈复的妻子芸娘敢于突破封建礼制,大胆的性格很可爱。我说:“沈复和芸娘很恩爱,可惜沈复仕途不顺,两人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可见任何时候经济独立都是根本。”
地铁摇摇晃晃,他的目光透过黑边眼镜拘谨地盯着我的脸,白瘦的脸上带着些许善意的微笑,眼神也随之摇摇晃晃。此时我化着精致的妆容,长发发丝被地铁冷风轻轻吹起,黑色低领连衣裙上的亮片一闪一闪,看起来像是一个精致的都市白领。
果不其然,两天后他约我去国家大剧院看《唐璜》。我对这个邀约感到窃喜,同时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多想。下班后我进入会场,一直穿T恤的他那晚穿了白粉条纹衬衣。2个小时多的演出让人背部不适,我向右扭动身体,却发现他正襟危坐,目光看向舞台。像个王子一样优雅,我想。
演出结束后聊天,他讲起喜欢的戏剧如数家珍,《图兰朵》、《魔笛》、《海鸥》、《樱桃园》...... 兴奋之余,还唱起了《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眠片段。“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剧,下次有演出一定拉着你去看,”他说。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用手机播放《图兰朵》,听着旋律,看着故事,希望自己能快速了解他说的那些歌剧。
第二次见面,他约我去望京的茶馆看书。看着点评网站上人均400多的消费,我有点不理解,看书为什么要去这么贵的地方。那次他在看契诃夫,我和他谈起了苏联文学和共产主义理想,感叹如今我们都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接受996的福报。
我主动提起我听过了《图兰朵》,并哼出了平庞彭的片段。他说,“你音律真准,图兰朵的故事中我最喜欢柳儿,柳儿唱段委婉抒情,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让我很感动。”
“让我感动的片段是孤傲的公主面对卡拉夫毅然决然的表白,冷酷的心也难以抵抗火热的爱情。”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问:“那么你呢,我喜欢你,你考虑谈恋爱吗?”我低下头,别到耳后的刘海掉了下来。
恋爱后,每周一到两次的约会,在银行流水曲线上就是一周一两次的数字剧烈波动。好在交完房租后,我还是攒下了一些钱。
大学时期,我依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的钱来维持学习和生活支出,每天花销严格控制在10元以内,每月支出600元左右。即使如此窘迫,我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依赖别人只会让人更看不起。“一定要坚持AA,大不了少点外卖、吃便宜的水果。”我心里这样想。
他送我的第一件礼物是国外设计师品牌的珐琅珍珠耳环。我开心地戴上,镜子中菱形珐琅块颜色鲜艳,下面的珍珠发出温润的光泽。
“耳环多少钱啊?” 我的心理价位是几百块。
“差不多五六百欧吧,我在奥地利专柜买的,喜欢的话下次带你去奥地利买。”
五六百欧也就是三四千元人民币了,这副昂贵的耳环让我想起一件难堪羞耻的事情。刚上大学时,我手头非常拮据。舍友要过生日,听说她喜欢胸针,我便在淘宝上挑选了一款模仿Chanel的胸针,65元,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同时我再花了12元买了一个Chanel的小包装袋,当时我觉得这份礼物非常得体。
生日当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礼物送给她。有人愣了愣,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香奈儿啊,你真有钱。” 另一个声音纠正道:“不叫香奈儿,叫‘沙奈尔’。”从众人怪异反应中,看到其他舍友送出玩偶、立体地图等日常礼物时,我知道我送了一个错误的礼物。寿星说,“谢谢你,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再后来,我不曾看到舍友戴上那个胸针。
珍珠的闪光折射进镜子里,我看向镜子里的自己。黑色的瞳仁深不见底,周围黄棕色的虹膜充满了谎言,仿佛是那愚蠢难堪的虚荣心。

2014年9月2日的下午,浑身湿淋淋的我和父亲带着边角磨破皮、轮子残缺的行李箱,第一次踏上北京地铁准备去大学报道。两个月前,我从县城唯一的高中毕业,被这所学校录取,并申请“绿色通道”贷款入学。
我穿着紫色的胶底帆布鞋,右脚鞋底漏水,袜子已经湿透了,鞋子有一点磨脚。自从高中后,我在晴天都会穿母亲这双表面完好无损的帆布鞋。
我们父女俩经过3个多小时的长途客车,4个小时的火车站候车,加上13个小时的夜间坐铺火车,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精神。30年前,父亲考了三次大学都没考上,收到我录取的消息后,他花了50块钱带着家人下馆子,说:“你是我的骄傲,是我们刘家第一个大学生。”
来到宿舍,两个舍友装作无意地打量着我和父亲,简单寒暄后,便接着聊起厦门、日本的旅游经历;对面床铺已经化好妆,穿着短裙,背着皮包,看起来非常时髦的舍友计划出门。我拿起父亲在火车站买的印花连衣裙,换掉了身上潮湿许久的衣服。
戴着墨镜和太阳帽,穿着热裤和高跟鞋的舍友刚好回来,看见我的裙子就说:“哇,你的裙子真好看,真适合你。”旁边人都看向了我,我匆忙否认。脸有点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在尴尬中我假装出门,路过镜子时瞟了一眼。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果然,你真的很土、很丑。”
第二天早上,父亲站在宿舍楼门前等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他穿着和昨天相同的白衬衣和灰夹克,衬衣领子有点泛黄,下巴有着乌色的胡茬。他说自己昨晚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沙发上睡了一晚,因为周围的酒店太贵了。我闻到父亲身上的烟味夹杂着的汗味、泡面味愈加明显了。
去食堂的路上,远远看见新舍友打开车门,上了她父亲那辆墨绿色奔驰。“你们学校的学生真洋气,相比之下你就像个初中生。”父亲对我说。
开学紧接着军训,有天中午回到宿舍,发现两个舍友在鬼鬼祟祟地讨论。我凑过去听,原来在说小蕊有狐臭。小蕊是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云南布依族妹子,第一天新生介绍,她热情地拿出自己家种的生板栗分给大家吃,她曾给我讲自己小时候为了零食和弟弟打架的事情,讲的同时睁大眼睛,两只短短的胳膊向前抡出,活泼有趣。
“你天天和小蕊在一块,有没有闻到她有狐臭?”舍友突然问我。
“好像......没有吧,我没闻到。”我眨着眼睛,仔细回忆思索。
“她一直有,可能因为他们村吃生板栗吧。”一个舍友说。
我看着她俩狐疑的眼神,问:“我身上有没有狐臭?”
她俩浅浅地嗅了嗅,摇了摇头。
为了不被别人瞧不起,不再重蹈小蕊的覆辙,我决定隐瞒自己的家世背景。
“你来自哪里?”
“西安,那个十三朝古都。”
大学期间,我故意选择自己不擅长的英语演讲课,自学日语,用勤工俭学的钱报了舞蹈班,学习化妆和穿搭,摸索自己最适合的发型。慢慢地,我仿佛真是的来自于省会城市、家境优渥的女孩。

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和这个喜爱歌剧、举止优雅的男生谈起了恋爱。家里人得知他是上海本地人时,第一句话是,“你俩门不当户不对。” 我有些气恼,顶了回去:“那你们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2020年年初,疫情形势正严峻。工作不顺利的我不顾家里人反对,决定追随男友去上海工作。妈妈非常担心,“现在疫情这么凶险,到火车站的高速路都封了,你走了我晚上怎么睡得着。”
父亲再次详细追问了男友的家庭情况,我回答,“是的,他家条件很好,有房有车,他爸在外企工作,他妈是初中老师,他自己工作也稳定。”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目光透过镜片瞥了我一眼,低头说:“你去了,阶级当然不一样了。”
我去了上海,住进了他父母为我俩准备的“家”。
位于23层的公寓,一切看起来那么让人满意。榻榻米书房挂着鹅黄色的复古蕾丝窗帘,窗帘左边是一架日产KAWAI钢琴,《卡农》从男友的手指尖缓缓流出。听他说,因为小学同桌会谈钢琴,他便央求父母买了钢琴,请了老师,一直学到高三毕业。
他问我,“你会弹钢琴吗?”
我摇摇头。
“介绍我的钢琴老师给你,咱俩之后就可以四手联弹了。”他微笑着对我说。
窗外是一栋栋白墙红瓦的房子,不远处有一处室外泳池,旁边是精心修整的山茶花和绿化带,晴天会传来小孩的嬉戏声和鸟鸣声。钢琴的对面是一个檀色光滑的博古架书柜,我的手轻轻抚摸过每本书,毛姆、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哈代、刘震云、布莱希特......
连书的家都这么精致小资,不像我的家,冬天的水龙头里永远淌着冷水,晚上翻个身,床板和弹簧吱吱呀呀地响,客厅里的父母一个在择菜,一个刷着短视频。
电话里,母亲问我在上海的工作生活情况,我还在投简历。
“不能让你对象的父母安排一个工作吗?一定要找个正式工。”
“妈,人家上海的环境不是这样的,我男友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去见对象父母,他们没表示吗?你嫂子第一次来咱家里,我和你爸一人给了一千块。”
换到我沉默了:“没有,上海没有这样的礼节,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给红包。”
母亲说:“这表示你公婆认不认可你。”
挂掉电话,我有点惆怅。男友贴心地敲门问我,和家里人聊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想你。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是的,他们挺想我的,我是唯一的女儿嘛。”

逐渐地,中产生活变得习以为常,我对食物和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房租水电全免的“优势”下,工资卡上的数字也逐月稳步增长。或许是潜意识也发现我实现了阶层跃升,我变得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更能坦然地面对各种评价。
和男友在餐厅吃饭,我们谈到了婚姻中门当户对的话题。
“所谓的门当户对真的很蠢,但是我觉得咱俩非常门当户对。”他朝我挤挤眼睛,笑着说道。
我刺探性地问他对于伴侣家境的要求,他眉头皱起来,说:“我也很怕负资产、扶弟魔的家庭,可能这个女孩再优秀,我也会放弃吧,我比较软弱。”
我对此有些失望难过。现代婚姻是一部产权法,两个家庭结合,浪漫爱的幻想和经济阶级背道而驰,谁也不愿做亏本的买卖。他身上我喜欢的品质,稳定的情绪、浪漫的艺术文学素养、见多识广的坦然,这些何尝不是他的中产阶级出身和优渥滋养的生活带给他的呢。
“是啊,结婚又不是定向扶贫,”我回复道。
谎言像一颗悬浮在水中的石头,我担心石头飘起将秘密全部曝光,更焦虑石头压在心底,彻夜难眠。
日积月累,谎言开始出现裂纹。我和男友的家庭阶级差异也蔓延到我们的亲密关系中。
厨房里,我准备做个韭菜炒鸡蛋来完成晚饭,却发现他拿着油瓶直接倒向了还沾着水的锅,热油马上四处乱溅。被烫到的我有点生气,大声对他说:“你倒油前没动脑子吗!快点把韭菜择一下。”
他的脸马上垮了下来,撅着嘴,从冰箱拿出韭菜和蒜苗问我:“哪个是韭菜啊?我不会择菜。”
我瞪了他一眼,让他先出去。这使我想起他从小不会接触家务,都是钟点工来做。当我向父亲抱怨男友不会做饭,眼里没活时,父亲却反驳我:“这不算缺点。”
五一旅游,他擅作主张定了五星级酒店,前台告诉我需要付六千多,结完账的我有点心疼钱。回到房间男友察觉出我不太开心,迎面抱着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没说话。男友又问是不是不舒服,我抬起头,说:“五天四晚的酒店要六千多,好贵啊。”他的头轻轻向左歪了一下,“对啊,五星级都是这个价格。”我叹了一口气,讨论之后住性价比更高的民宿,他撒娇道:“可是五星级酒店真的比较舒服,服务也很好。”
我与他不同。看似两人都能入住五星级酒店,六千块钱对他来说只是一次舒适的旅游经历,对于我来说则是在大城市生存的本钱,更是我父母两三个月的收入。
谈起父母的养老问题时,我对此表达了忧虑,他安慰道:“你父母年纪大了,肯定希望女儿的陪伴。”我忍不住激动地吼道:“你懂什么,他们需要的不是陪伴,是钱。”男友用怯怯的眼神看着我,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没有反驳。
我的父母依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要用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支付糖尿病的治疗费用和家庭花销。对比男友父母,婆婆马上要退休,可以拿着每月一万多的退休工资,公公一直保持着长跑、阅读、学法语的习惯。也许这是我父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生活吧。

今年的农历新年,男友被拉去酒店隔离,我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男友给我定了头等舱,头等舱有着舒适的座椅、可口的食物,旁边的乘客或是看书或是工作,与我坐了4年的长途夜间火车不同。那时座位旁大多是农民工模样的大叔,刚趴在小桌子上就打起了呼噜,脚边放着塑料桶和编织袋,后座隐隐飘来一阵裹着热气的泡面味混合着鞋袜的味道,大叔有时睡得太沉把头靠到了我的肩上,要轻轻碰好几次,他才会半睁开眼,换个方向接着睡去。
下了飞机,我买了一张长途客车车票,看着窗外的景色由崭新的商品楼,变成城乡结合部、一排排汽车维修店,沿途路过一些县城的服务站,熟悉的景色逐渐展现在面前,光秃秃、黄蒙蒙的山和沟壑,两三个细长的白色煤矿烟囱飘出烟雾,我知道快要到家了。
母亲很开心地问长问短,我穿着奶白色的毛领羽绒服,行李箱上放着给父亲买的茶叶礼盒,父亲抽着烟看了我一会儿,让我晚上去哥嫂家住,他们房子有暖气。
大年初二走亲戚,父亲让我们三个孩子跟他一起回老家看望舅爷和三姨奶。
“为什么我要去看你的舅舅和三姨,我跟他们又不熟。” 外面下着雨夹雪,山路泥泞,我不想去。
父亲一下子火了,指着我的鼻头骂:“当初他们都知道你考上大学了,我爹妈死的早,他们就是我的爹妈,你走多远,那里都是你的根。今天由不得你。”我很委屈,在妈妈的劝说下,我还是去了。
在三姨奶的屋子里,伯伯、叔叔们围在炉子边烤火,旁边的婶婶在逗弄小孩。父亲炫耀自己解决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剩下的女儿也不用担心,对象已经谈好了。
“听说上海房价得几百万,一套房子值钱得很。”一个不认识的叔叔问我。
“差不多吧。”我尴尬地回复。
“大学生女子不得卖个十万二十万。”有人调侃我父亲道。
父亲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保守的?眼前的他讲着传统、年收入、公务员升迁。小时候,那个教我辨认北斗七星和织女星的父亲不见了,给我讲清朝历史的父亲不见了,认真教我辣椒、西红柿、茄子英文读音的父亲不见了,耳边只能听到:“你确定不考研了吗,反正我是一点也看不上你现在的工作。”
和母亲在厨房一起洗碗时,我们谈起了彩礼问题。我说之前和男友谈过,他不是很赞成,上海没有彩礼,他爸妈当初结婚也没有彩礼。
“娶陕西的女子得按照陕西的习俗来办,你让他家去网上搜搜看,你嫂子的彩礼钱和五金首饰前前后后花了快二十万,你姑姑家的大女子也是十多万。”她很坚持。
“我没法开口要彩礼,你们要多少,我把我的钱给你。”我看向母亲,母亲不说话。
我又来了一句,“你们要彩礼的话,我就不结婚了,反正我也不想结婚。”
“你怎么能不结婚呢?”母亲声音有点哽咽,泪珠掉在了洗碗槽里。
我赶紧抱住母亲,她在我的怀里哭着说:“你在上海看不见摸不着,我担心人家对你不好,你俩早点结婚把这个事定下来。”
我也哭了,安慰母亲说,“他对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受教育程度不高、温柔爱哭的母亲,在我难过时,总会用她久做体力活而健壮的胳膊紧紧抱住我,说:“妈永远相信你。”在妈妈柔软的胸怀里,我既感动又难过。
我对谎言感到愧疚,看到“拜金女”、“扶弟魔”等字眼常常联想到自己。网络上的扶弟魔讨论话题下面,永远在劝分和劝离。我是这个城市社会并不待见的物种,贫穷的家庭出身是我的原罪,我编织了一个精美圆满的谎言,蒙蔽着身边人,也麻痹着自己。
在上海,我和朋友同事谈论旅游奇遇、脱口秀的主流、HBO的新剧和城市生活的倦怠;打通家里的电话,外婆和父亲的健康状况、婆媳矛盾和经济压力一齐向我涌来,这巨浪冲破了谎言,使我在城乡文化之间不断流浪。
结婚与否并不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也不影响他对我好,这样的话,下次讲给妈妈听吧。

回家定了七天的行程,可我第二天就想走了。居住条件的猛然下降、父母忙于生计的无意忽视,以及压力巨大的暴力沟通,让我开始分外想念男友和上海的生活。
在上海的家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决定家居物品、家庭行程和男友的游戏时间。即使发生争吵,他也会偷偷关注我的情绪变化,并在恰当的时候释放和解信号。
我在电话里向男友倾诉回家的感慨和落寞,他安慰我,“没事儿,回家咱们细细说,还有几天就能见到你了好激动。”即使他隔离的酒店空间很小,饭菜也不好吃。
返程那天,男友早早地在停车场等待,我们从环球港、凌空SOHO旁边经过,东方明珠的灯一如既往亮起,我将回到熟悉又陌生的生活。
晚饭期间,也许是快两个月的隔离让男友有点感慨。他突然说:“疫情结束后,我们讨论一下谈婚论嫁的事情吧,见见家长,交交彩礼。我觉得还是你最好。”
感动之余,更多地是有些恐慌,我的音调不由地变高,“那你如何看待我家里人提出的彩礼问题呢,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我不接受被商品化,他们非要的话,我自己支付我的彩礼钱。”
“怎么有种青楼赎身的感觉,”他调侃我。“我对彩礼OK啊,他们也要不了多少钱。”男友的话语开始出现了变化。
我张不开口,脑子里想的是他若见到我真实的父母、我的家、我的哥嫂会作何反应。
看到我沉默,男友又说了一句,“没事没事,我今天有点心血来潮了,还是不见家长了。”
晚上睡觉前,我问他:“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你之前说的婚前财产公证还要吗?我的财产只有工资卡里的钱。”
等了七八秒,他回复:“我和我父母、你和你父母的家庭资产情况还是要沟通一下的,知根知底比较好。”
我把手从他的胳膊上撤开,心里的巨石缓缓压上胸口,身体陷入了柔软的床,有点喘不上气。
一夜未眠,窗外的鸟不知疲惫地叫了起来。天又要亮了。
原标题:《为了“门当户对”,我向男友隐瞒了自己的贫困县出身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