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何为人口问题?1930年代瑞典人口委员会始末
1934年阿尔娃·缪达尔和冈纳·缪达尔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出版之后,在瑞典旋即引起轩然大波,在报纸、杂志、电台乃至政治领域引起轰动和辩论。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创造了”瑞典的人口问题。之后不久,瑞典政府宣布成立“皇家人口委员会”,正式启动了对人口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如果说缪达尔夫妇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构想了瑞典福利国家的蓝图,人口委员会的工作则是要绘制通往福利国家的路线图。
冠以“皇家”和“政府”的各种专业委员会在瑞典有着长期的历史,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1809年。一般是由政府主持提出某方面研究的需求,资助组建专业委员会提供对有关问题的信息、知识和研究报告,为政府制定政策做准备。毫无疑问,这些委员会是社会研究与社会改革之间交叉互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瑞典这一制度又有其特别之处,这些委员会在政府之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统计,1855年至1904年,一共成立过531个委员会;而1905年至1954年,这一数字达到2729个,增长了5倍。[1]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议一般会得到议会(Riksdag)的重视,这一点与当时美国国会或总统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不同。[2]因此,专业委员会成为了瑞典民主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缪达尔夫妇
成立人口委员会
1935年5月17号,时任社会部部长的穆勒(Moller)发布指示:成立1935年皇家人口委员会。穆勒首先强调了瑞典人口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认为无人可以逃避这一危机的影响,人口委员会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制定政策来减少养育孩子使家庭产生的各种花费。具体来说,他建议委员会要考虑如下方面的问题:对结婚和家庭减税、为工作的母亲照护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提供结婚贷款、对怀孕妇女给予现金补贴、提供免费的学校午餐和减免学杂费、为儿童提供全面的健康医疗、为青年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与社会住房委员会合作对家庭住房需求和以家庭为导向的城市规划进行研究。穆勒还要求人口委员会的工作要尽快产生出实际的结果,以便为下一年度(1936年)的议会做准备。[3]社会部长对解决人口危机这一惊人举措,一改之前“人口政策”笼罩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头上的符咒(以往关于家庭、人口问题的讨论都是保守派的阵地),生育问题终于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目标为大家接受了。在这一点上,缪达尔夫妇《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的出版的确是1935年建立人口委员会背后的主要推手。
1932年社会民主党执政之后,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爆发,全球性的大衰退严重打击了瑞典的经济,失业率从1930年的12%快速攀升到1934年的34%,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和社会动荡。[4]瑞典的社会改革迫在眉睫,改革之需引起了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建立,仅在1935年就成立了46个委员会,大部分委员会规模很小,不超过4人。而人口委员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委员会之一,由9名正式成员组成,加上外聘的专家、顾问和工作人员,一共有60多人,可见人口问题是瑞典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由政府指定9名委员,由专家或非专家(非专家一般是有实际经验的议会成员)两部分人员组成。该委员会有两个特点与以往不同,一是专家所占的比例多于非专家(9位委员里有5位教授);二是尽量包括议会中各群体的代表,委员中既有积极参与妇女运动的医生和编辑,也有统计学、经济学生物学方面的教授,还包括了议会中各派代表的议员,其中有保守党(花匠),社会民主党(工人)及自由党(记者)各一名代表。
在人事安排上还有两个插曲。
一个是选择农民党在第一议会的领袖尼尔斯·沃林教授(Nils Wohlin)担任主席,而社会民主党的冈纳·缪达尔只担任秘书。社民党选择沃林出任主席,显示了1933年“红绿联盟”(指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的联合)之后的意识形态转变。社民党以往的改革多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主,在1932年成为执政党之后,在社会改革中则要将国家和保守派的政治基础合并起来。沃林的出身背景代表了瑞典农村的价值观,虽然他不会自愿地支持所有的改革项目,但他会支持对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标准的改革。在人口问题上,沃林会支持以家庭为主的减税,支持增加公共领域里对改善儿童生活的费用,改善家庭住房,保护工作母亲的利益,改进非婚母亲们的待遇等等措施。总而言之,由一位德高望重的保守派人士担任主席来打头阵进行政策上的大型国家实验,对代表比较激进的进步理念的冈纳·缪达尔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是最有专业背景和经验的阿尔娃·缪达尔没有进入委员会,而是由她丈夫冈纳·缪达尔担任委员会秘书。最初,冈纳·缪达尔并不是十分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命。为此,冈纳曾经与时任财政部长的维格福斯(Wigforss)联系,要求考虑阿尔娃代替自己出任委员会的职务,因为阿尔娃在处理实际问题方面具有极大的兴趣与能力。然而,维格福斯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社民党“需要一位男性,而不是女性在委员会里来代表党的领导”。[5]可见,当时的社民党领导层对党内女性主义者的领导能力还是将信将疑。尽管阿尔娃没有进入人口委员会,但她参与撰写了委员会最具挑战性的“性问题报告”。最重要的是,她与冈纳·缪达尔共同撰写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中的思想对委员会的影响终将要通过报告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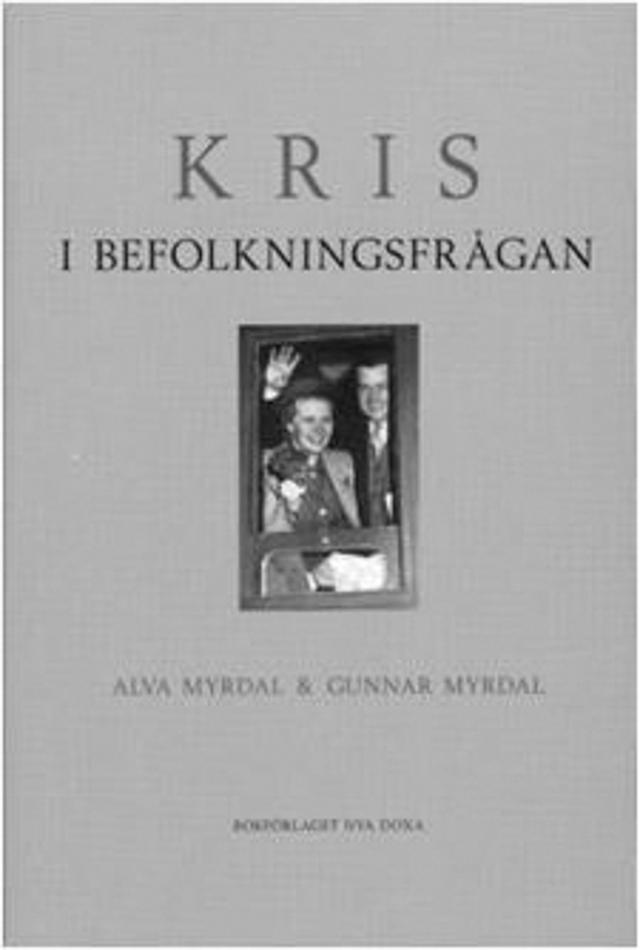
《人口问题的危机》书封
另外,阿尔娃在这一阶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讲演,来阐发她对人口问题的种种看法。人口问题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阿尔娃提出的看法令人惊叹:人口问题不是生育孩子的问题,它是塑造人民健康生活的问题。作为女性,阿尔娃对那种促使妇女生育作为人口政策目标相当厌恶,这一态度经常通过她强调人口问题的“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数量”而显现出来。她认为在人口问题上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社会改革要使儿童获益,二是控制生育的原则,这两个原则要渗透到人口委员会的各种决策中。而且,她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不应是敌对的,而应该是聚合的。因此,她认为那种将社会利益锁定为人口政策的目标,那么人口增长的可能性在开头就没戏了。阿尔娃的这些思想对人口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冈纳·缪达尔自接受任命之后就成为人口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从1935年至1938年6月,冈纳·缪达尔除了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不多的课程之外(这一阶段的授课内容以人口委员会有关研究为主),其余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之中。1936年,他被选为第一议会的成员,这就确保了人口委员会工作的延伸和扩大。在人口委员会里,冈纳不但担任着委员会秘书的工作,还参与了大部分分支委员会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提出讨论的议题,发挥他的知识与学术的影响。自1936年成立了“指导委员会”之后,冈纳是三位成员之一。在人口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冈纳保持着出席几乎全部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会议的空前纪录。由于委员会主席沃林教授还有其它的工作,委员会的一般性运作管理事务就由冈纳主持。同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也支持他在委员会中成为推进意识形态的力量。冈纳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大干一番。
人口委员会的工作
一般来说,瑞典这种为改革做准备的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如下:为政府提供正式出版的工作报告,然后将这些议案送交各地方政府、公民机构和有关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反馈意见;送交最高立法机构投票通过;通过新闻报刊报道,进行大众辩论;送交成人教育机构进行学习讨论。于是,社会改革不只是实验和行政管理的过程,而是通过公开发表、大众批评性地学习研究、分析细节的过程。[6]而大众参与这个方面可能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与当时美国国会或总统的专业委员会非常不同的一点。
1930年瑞典人口委员会共提交了17个工作报告(也有一说是18个),下面()中是报告的编号。
1935年秋,委员会出台了第一个报告(1),提出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已婚妇女可以享受3个月的带薪产假,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国家作为雇主要先行一步,在人性化生育上带个头。
1935年最重要的一步是提出降低住房费用,这一意见始于“住房委员会”,人口委员会报告提出给三孩或三孩以上的家庭减少租金(18)。
1936年,提出所有妇女生育免费(2);国家提供结婚贷款(4);对有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3)。
1936年至1937年,讨论的领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跟“性”有关的问题。这一年出台的报告:绝育(6)、节育(7)、性教育(8)、流产(9)。出台这些报告的目的是,通过对与性有关问题的公开讨论,以便为家庭改革打下基础。这些问题是委员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头戏,目的在于提起全社会对控制生育和性教育必要性的认识。然而,在这些看似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大众讨论的气氛平静而热烈,比预期的想象要好。
上述报告出版之后,送到内阁与议会讨论通过,几乎所有的建议都被一一接受了。在这个阶段启动的人口政策的社会改革几乎是在没有反对的意见的情况下就被接受的,因此,这一段的会期被称为“母亲和儿童日”(Rikaday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1938年,新的系列报告出版:营养问题(10)、儿童服装(11)(这两个报告遇到的阻力比较大,后面将进一步介绍营养问题报告)。
1938年下半年还出版了以前为改革提出的议案:关于反对妇女因结婚和生育被解雇的立法(12)、对幼儿教育的补贴(15)(这两个议案顺利通过)、关于农村人口衰落的研究报告(13)、对不同生殖力的人口统计研究(16)、关于人口问题在道德方面的影响(14)、委员会最终报告(17)。[7]
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人口委员会出台了17(或18)个报告,可以说每个报告都建立在实际调查数据和理论上的探讨的基础之上,成果是丰硕的。
人口委员会成立之时,正值时任首相的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大力宣传推广他提出的“人民之家”的计划。[8]在1936年8月5日的大选前声明里,汉森和社会部长穆勒在谈到未来的改革工作时还特别提到了儿童营养的问题。他们指出,大量的瑞典儿童还得不到他们需要的食品,社会民主党将要指导生产来满足家庭和儿童的需要。他们呼吁为所有的儿童提供营养食品,特别是那些没有父亲和失去双亲的儿童。后来,汉森又进一步将冈纳·缪达尔的人口政策引进到他的“人民之家”计划之中,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转向对青少年一代福利的关注,强调青少年的福祉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未来的本钱。汉森敦促对母亲和儿童给予大量的支持,并提出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主题将是建立在“实际”基础上的“激进的方案”。[9]可以说,人口委员会对福利项目细节的铺陈与汉森所期许的人民之家不谋而合,这也是委员会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保证。

1930年代的瑞典士兵
然而,随着欧洲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政府的经费开支开始向军备方面倾斜。1938年,瑞典议会对人口委员会建议的花钱最多的学校免费午餐、儿童服装补贴和日托中心等项目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同样在1938年,瑞典政府对社会改革按下了暂停键,委员会方案的实施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冈纳·缪达尔几经犹豫之后,最终接受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在1938年决定全家离开瑞典,赴美进行一项大型的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1930年瑞典人口委员会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
解剖麻雀:以营养问题的报告为例
营养问题分支委员会由冈纳·缪达尔担任主席,这就保证了他会始终掌握着讨论的“正确方向”。在第一次会议上,冈纳就告诫分支委会的成员们,好的家庭营养政策将牵扯到学校午餐项目和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同时还需要考虑营养在健康方面的影响、其他各国的范例、瑞典现存的营养标准以及对瑞典农业产出的深入分析。总而言之,冈纳认为,在人口问题有关营养方面的问题需要发展一个全面的“食品政策”。然而,冈纳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人口委员会中的保守党成员(花匠)认为,正在进行的关于食品生产的调查完全没有必要,照这么干下去,这个分支委员会就成了个“猛犸象委员会”(意指行动缓慢)。此人建议,如何提供便宜的学校午餐才是委员会研究的正道。而冈纳的回答直接回到了他的经济学老本行:委员们必须处理营养方面涉及到的消费与生产的问题。后来,经过个别私人间的谈话沟通,冈纳的意见赢得了营养分支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同意:瑞典全部儿童都应该得到免费午餐,无需进行家庭收入测试,所需费用全部由中央政府买单。最后,在1937年9月17号经过激烈的讨论,分支委员会同意关于营养问题的报告基本上要体现冈纳的思路。[10]
1938年初,营养问题的报告出版了,它用大量的数据说话,发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报告中对人口问题和瑞典农业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诸如:农村人口连续不断地进城,农村人口的低生活标准,农村和城市不同的生殖率,对全部儿童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的必要性等问题。调查研究发现,在人口多的大家庭里儿童缺乏营养,特别是缺铁和维生素,其实儿童所缺的就是那些优质的动物食品,如黄油、牛奶、肉类、咸肉和鸡蛋等,而这些都是为市场生产的最重要的农业产品。如何能使儿童吃到这些东西,又不伤害农民的利益,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报告中提出的解决的办法是:需要社区为儿童购买这些产品。在谁来出钱购买这些食品的问题上他们主张,为何不让纳税人用相应的直接比重来购买这些食品,同时也支持了农业,不要让那些贫困的消费者来为经济资源投资。在农产品出口的问题上他们质问,为何不先让瑞典的儿童吃饱吃好,而不是花钱来喂养英国和德国的儿童?[11]简而言之,国家和社会要为儿童营养食品买单。
在分析营养问题上,人口委员会深入到有关整个的农业发展趋势和农民的困境的复杂问题之中。他们认为,营养问题应该整合到农业生产的政策之中。委员会设计了同时帮助问题多多的瑞典农业和孩子多的大家庭的方案。这些政策应该通过下列的三种方式来影响国内农产品的倾销:通过惠及所有儿童学校免费午餐;通过医生开出的惠及母亲和儿童的营养免费食品清单(为怀孕妇女和学龄前儿童提供食品、维生素、医药等);通过建立两种价格体系为农业剩余商品找到出路(为三个及三孩以上的家庭以及单亲家庭发放食品券,来购买减价的食品)。[12]
委员会经过测算,预计在今后10年之中儿童营养方案将扩大到全体国民,那么这一方案每年所需费用大约是3千4百万瑞典克朗,中央政府要出资2千5百万克朗。与人口委员会提出的其他提案相比,这个儿童营养方案是花费最大的一个。不出所料,这一报告又遭到了委员会保守派(花匠)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学校午餐项目是个危险的社会主义发明!他还认为报告中提出的方案既不现实又花费过度。接受资助者们成为依赖国家的人,这就危害了人口大家庭的存在。[13]然而,经过几番较量,最后报告还是如期出版了。
在营养问题上,体现了缪达尔夫妇对人口问题的两个重要思考。
一是追求数量还是质量?显而易见,委员会关于营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与人口政策上追求“数量”和“质量”的政策走向紧密联系着。“质量”上的测量将会改善儿童的经济状况,提高儿童健康标准,而降低婴儿死亡率同样也是关乎“数量”的问题。对不同数量孩子的家庭在花费和收入上的再分配同样起到对家庭生活更为积极的作用。报告体现了缪达尔夫妇在人口上的基本原则:儿童必须是改革的受益者。缪达尔夫妇预测到人口政策会成为未来几十年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会主导着社会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人口的质量标准来制定政策。这也就是瑞典版的“以人为本”。

1930年斯德哥尔摩车站
二是花费(cost)还是投资(investment)?报告强调,必须将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作为一种对未来的公共投资。这样一来,儿童福利方面的花费就变为了一种投资。为什么说为儿童投资就是对未来投资?因为缪达尔夫妇一直认为“儿童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财富”,国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经济财富的重要性,并通过社会政策为之投资。而阿尔娃则有更为形象的比喻,正因为人口是国家财富的主要部分,于是为此投资可能就会有更高的回报,而投资那些工厂、机器和其他财产早晚会生锈腐败和被蛀虫吃掉。[14]
总之,在冈纳·缪达尔强有力的思想和学术影响之下,人口委员会的工作改变了由保守派留下的支离破碎的烂摊子,为社会改革赋予了新的力量。冈纳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数据,将他与阿尔娃共同撰写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中的思想成功地“翻译”到10多个政府报告之中,为瑞典的未来绘制了一份相当激进而又可行的路线图。
注释:
[1]Wisselgren, Per “Reforming the Science-Policy Boundary: the Myrdals and the Swedish Tradition of Governmental Commissions”, in Sven Eliaeson and Ragnvald Kalleberg (ed.), Academic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p. 176.
[2]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29.
[3]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21.
[4] Svensson, Måns; Urinboyev, Rustamjon; Åström, Karsten, “Welfare as A Means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 A Law and Society Analysi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2012,14(2),64-85.
[5]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30.
[6]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163.
[7]一般认为,1930年的人口委员会出台了17个报告,但阿尔娃认为是18个报告,(18)是住房调查报告,见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163-167. 也许因为是与住房委员会合作,最终没有算为人口委员会的报告。
[8]见闵冬潮“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1930年代瑞典福利国家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山西师大学报》2017年6期,第33-38页。
[9]见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71.
[10]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33.
[11]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282.
[12]见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46. 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283.
[13]Carlson,Allan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family politics : the Myrdals and the interwar population crisis, 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146-147.
[14] 见Kalvemark, Ann-Sofie, More Children of better Quality? Aspects on Swedish Population Policy in the 1930’s. Almqvist &Wiksell, Uppsala, 1980, p.54.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