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白乙评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

一件文物,在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前,一般要先通过专家小组周密鉴定,再经研究者深入考据,以准确揭示其性质、价值,进而成为普遍的公众认知。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公众认知也会慢慢随之修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除夕夜,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卷被捧到了春晚舞台,短短几分钟的展示与解说,亿万观众的热情被迅速点燃。这幅长卷原本叫什么名字,因题签早已毁失,我们无从知晓。春晚称“丝路山水地图”,倒是应景,也便传播,但变乱名实,于古无徵,实不可取。文史学者,尤其是对舆图有兴趣的研究者,这时会下意识地回溯上面那个过程,自然也绕不开林梅村教授的专著《蒙古山水地图》。

要弄清这幅长卷的递藏流传过程,最不能忽视的,是现存的舆图目录。好在此前已有胡成等几位先生关注该问题,挖掘出不少此前未受关注的重要材料,推进了此项研究。今细绎目录,参酌其说(胡成:《〈蒙古(丝路)山水地图〉原名考证》: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08714230965151),重新讨论这幅长卷的流传过程及相关问题。
有关清代的舆图资料,除《天下舆图总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所编舆图目录尚有《萝图荟萃》《萝图荟萃续编》《国朝宫史续编》《舆地图一百三十二卷目录清单》等几种。1936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了《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此后,第一历史档案馆又编成《内务府舆图目录》。其中,《萝图荟萃》《国朝宫史续编》二书的著录信息,对研究《蒙古山水地图》颇为重要。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福隆安、裘曰修等人,奉敕查勘内务府舆图房所储舆图,择其中较重要的四百余件,分门别类,编成《萝图荟萃》。所谓“萝图”,应即“籙图”,萝、籙同声,皆来母字(从于省吾说)。古代帝王登位,受命于天,称“受籙图”。后来,词义引申,泛指广义的舆图。“萝图荟萃”即重要舆图之总汇。
这部《萝图荟萃》,“舆地”类著录的二百五十八件舆图,形制分“张”“卷”“排”“套”“轴”“册”六种。在“舆地”目下的“藏卫蒙古回部朝鲜等处”三十一件舆图中,著录“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 一张”。《萝图荟萃》著录题名中的嘉峪关(No.1)、巴达山城(No.147,作“荅”)、天方(No.210)、西海、戎地面(No.211),分见今《蒙古山水地图》卷端、卷中、卷末。据嘉庆年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此图形制、尺寸都与今所见《蒙古山水地图》相合,知应是同一图卷。关于此图形制,《萝图荟萃》著录为“张”,《国朝宫史续编》著录为“卷”,现在所见《蒙古山水地图》也是手卷。如二书著录无误,则此图重新装裱、改成手卷的时间应在乾隆二十六年至嘉庆十一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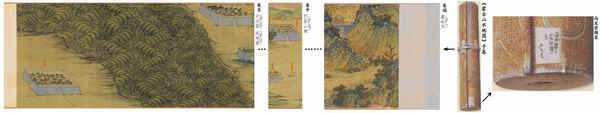
乾隆年间,编《萝图荟萃》时,此卷题签似已毁失。主事者大概是择图中卷端、卷中、卷末的几个地名,才将此图著录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题名中的“回部”,是清乾隆中叶对天山南路一带的通称,带有明显时代痕迹,也非原图旧名。
嘉庆十一年(1806),庆桂等人奉敕编成《国朝宫史续编》,其卷一〇〇也著录了这幅图,且对此图的形制、尺寸有详细记录:“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图一卷: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九丈五尺。”其中,题名脱一“面”字。《蒙古山水地图》中的“巴荅山城”,《国朝宫史续编》作“拔达克山城”,其余几幅图,此处地名,也都作“把荅山城”,译音无定字,但记其音,实为同一处地方。“一卷”“绢本”与《蒙古山水地图》相合,“纵一尺九寸,横九丈五尺”的尺寸也几乎相同。《萝图荟萃》《国朝宫史续编》的著录,与现在所见《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应是同一件东西。
清帝逊位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清点故宫各处所存物品。从1924年到1930年,清点工作一共持续了五年多时间。清点结果汇集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在“造办处”物品清单中,“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已杳无踪迹。1936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重新整理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舆图,复覈《国朝宫史续编》《萝图荟萃》及《续编》,编成《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简称“《初编》”),也已不见《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的影子。

由以上材料,可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乾隆年间,此图尚在内务府舆图房,长卷流传至今,尺幅未变,不存在被裁剪的问题。其二,这幅长卷流出舆图房的时间,应在嘉庆十一年至光绪年间尚友堂开设(详后)之间。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推论或许还可以再稍稍往前迈一步:如果乾隆以前,此图一直藏于内务府,被坊间古董商裁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晚清,《蒙古山水地图》曾流入尚友堂书肆,尚友堂在此图卷端一角附纸题作“蒙古山水地图”,名实不符,也没什么道理可言。明清时期,较有名的尚友堂有两处:一是明末清初苏州金阊安少云开设的书坊尚友堂,曾刻印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二是冀县人赵鸿儒于光绪年间在琉璃厂桥西路北开设的一家书肆尚友堂。据《琉璃厂小志》记载,此书肆先后易师存志(字向仁)、尚善修(字和亭),又易恒顺参局(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书店,2011年,94页)。附纸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应是琉璃厂的尚友堂书肆题写,与苏州安少云的同名书坊没有关系。据我们研究,此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图略》等图性质相类,其原名似应含“西域”二字。因原图题名不详,为行文方便计,姑且暂称“蒙古山水地图”。
除了《萝图荟萃》《国朝宫史续编》,有关这幅长卷的流传线索,当下所见,也仅有尚友堂附纸题签、日本藤井有邻馆及故宫博物院的相关材料。尚未查阅的《天下舆图总折》,其中也很可能会有新的线索。此卷的流传,据此可以理出一条大致的脉络:清内务府舆图房(?)——琉璃厂尚友堂——日本藤井有邻馆——易苏昊——许荣茂——北京故宫博物院。
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凡六章,依次为缘起、元明时代的西域地图、明代刻本和彩绘抄本之发现、明宫内府藏图之流失、艺术流派与科学价值、《西域土地人物略》校勘记、地理简释。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林教授耗时八年,将《西域图略》等与此图相关的珍贵材料挖掘出来,难能可贵,居功至伟。当然,也不能否认,林著忽略了对此图许多基本问题的深入探索,如各类舆图目录,皆付之阙如。
谈这幅图的艺术流派及价值,是建立在对这幅图周密鉴定、细致考据基础上的,弄清基本事实,是深入研讨此图的前提。撇开艺术流派、科学价值等问题,林著对《蒙古山水地图》基本问题的研究结论,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其一,“蒙古山水地图”虽是尚友堂的题签,但极可能是此图原名。此图大约绘制于嘉靖三年(1524)至十八年之间;
其二,此图有两种明代刻本,分别是《西域土地人物图》(《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刻本,简称“明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图略》(《陕西四镇图说》万历四十四年刻本,简称“明刻本《西域图略》”)。一种明代抄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甘肃镇战守图略》明嘉靖抄本,简称“明抄本《西域土地人物图》”);
其三,四图之间的源流关系:《蒙古山水地图》——明抄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刻本《西域图略》;
其四,《蒙古山水地图》原图长四十米,现仅存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从天方至鲁迷)被裁去。这幅图完整的样子,应是从明朝嘉峪关直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尔),堪称“明代丝绸之路地图”。
遗憾的是,以上四点结论,由于缺乏证据,都经不起推敲。林著将此图绘制时间定为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的前提,首先是傅熹年的鉴定结果。关于傅熹年的鉴定意见,林著曾出过一条注释,这条注释说“承蒙易苏昊先生告知傅熹年先生鉴定结果,谨致谢忱”(林著,37页,注释5)。由此可见,林著也只是通过易苏昊的转述,才获悉此次鉴定结果,并不清楚傅熹年的具体鉴定依据。而且,当时似未成立专家鉴定小组,仅傅熹年一人提出了鉴定意见。
据林著转述,傅熹年对此图的鉴定结果为“恐非清代之物,至少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林著,第2页)。直至现在,当时正式的鉴定依据也未见公布,我们仍不清楚此次鉴定的具体过程。然而,林著接下来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由易苏昊转述的鉴定结果展开。我们当然非常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公布此次鉴定留下的材料,由此,可以从这些材料重新出发,沿着相关线索,对这幅图做更为周密、深入的思考,以确定其性质、价值。
以此为前提,林著通过考察地图类型及相关地名,将此图绘制时间范围缩小至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林著,24页)。将时间上限断为嘉靖三年的依据是,图中绘有“嘉峪关”,所以其绘制时间一定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将时间下限断为嘉靖十八年的依据是,图中不见嘉峪关至西的烽火台“永兴后墩”,所以其绘制时间至迟在嘉靖十八年。上限“嘉靖三年”说,张晓东在《明代〈蒙古山水地图〉探微》已有驳正,且极具说服力。张文指出,嘉峪关自洪武五年(1372)始建,图中地名起自嘉峪关,是明人以嘉峪关外为西域的习惯做法,并不一定要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才绘这幅图(张晓东:《明代〈蒙古山水地图〉探微》,《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108页)。
对下限“嘉靖十八年”说,张文也有驳正。不谈其具体观点,仅从逻辑上讲,一般对古舆图绘制时间的考据,在纸张、墨色、形制等经过鉴定后,要据舆图中带有时代痕迹的地名,以考其沿革、辨其时代。其中的道理,自是不言而喻:由于主持绘图者的目的不同,各类與图的性质、用途也不一。同一时代的不同舆图,选绘地名各异,这很容易理解。在一幅图上,绘什么,不绘什么,原因众多,并不一定指向具体地名的历史沿革。因此,据舆图中没有的地名,推考其绘制时间,在逻辑上很难讲通,这样的证据当然是无效的。
上文提到,与此图相关的,还有另外三幅图,分别是明抄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刻本《西域图略》。林著认为,“明清地图往往有刻本”(林著,50页上),遂以手卷《郑和航海图》被收入《武备志》刻本为证据,推论明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图略》是《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是其余三种地图的“源头”。《郑和航海图》是否有刻本,对判断《蒙古山水地图》与其他两种刻本之间的关系,没有直接参考价值,更无法构成厘清三图源流的有效证据。
得出《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这个结论,其依据是:其一,《蒙古山水地图》中某些城镇只画图像而无名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补充了这些名称,所绘城镇多于《蒙古山水地图》,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其二,《蒙古山水地图》无人物和动物,而《西域土地人物图》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
仔细比对四种舆图,唯独《蒙古山水地图》不绘人物、动物。另将四图地名统计、比对,《蒙古山水地图》有二百十一个地名,《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刻本)有一百八十六个地名,《西域图略》(明刻本)有一百七十四个地名,《西域土地人物图》(明抄本)有一百七十二个地名(见附表)。《蒙古山水地图》中有不少地名独异,其馀三图地名大致相同,略存小异。《蒙古山水地图》止于戎地面,《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图略》则向西延伸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仅是四图内容、形制不同的事实,不能构成判断四图关系的证据。林著在两条证据中提到的所谓“补充”“补刻”,都没有周密考证。因此,以上用以支撑《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结论的这两个证据,同样无效。以此未被证实的结论为依据,又去推论《蒙古山水地图》曾被坊间商贾裁掉一部分,更是无稽之谈。三幅图之间具体的关系尚不清楚,仅依据三图的尺幅,推出这样的结论,逻辑再次缺席。
现存此图,止于戎地面,而非天方国。且前文在梳理《蒙古山水地图》的流传脉络时,据《萝图荟萃》《国朝宫史续编》的著录考证,此图在乾隆、嘉庆年间,与今天这幅长卷的尺寸并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林著依据《西域土地人物图》,草率地将其中十三个地名补入《蒙古山水地图》,实是画蛇添足。
经仔细比对,我们认为,以上四幅图之间,应该有某些联系,但它们是否有直接承袭关系,以及具体的源流脉络,还有待仔细考证。从上文附表地名对比可以看到,四幅图所绘地名,部分重合,但又不完全一样。对其馀几幅图的深入研究,也可为准确认识《蒙古山水地图》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有关嘉靖刻本《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与《西域土地人物略》,李之勤有《〈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林著对这部分研究成果,吸收不足,也忽略了对《西域土地人物图》前后两段文字的解读。这两段文字,对我们认识《西域土地人物图》及《蒙古山水地图》,很有帮助。《西域土地人物图》前,有一段题为“西域”的文字,迻录如下:
雍人曰:西域,自古内属之国也。其民皆城郭宫室而居,耕而食,织而衣,非若匈奴迁徙无常、水草是逐、不耕不织、射猎为生、盗窃为心者比也,故其人犹可施以政教焉。燉煌,亦西域地也。方政教行时,其贤才辈出,与三辅无异,可以西戎言耶?盖人之心性本同,使所业又同,政教又同,则其贤才之出,何独不然?若夫匈奴与我,谋食既殊,其心必异,殆犹矢人与函人然,亦胡能同之哉?是故先王尝外之于西戎,则施以政教,此即叙之绩所由底也。今考燉煌,即沙州卫地。哈密去沙州仅三百里,故亦燉煌地。此外诸域,旧称哈密地。图其极边,又有巡检公署及汉人村落屋庐数处,是昔尝内属之域也,故悉图而志之,以俟政教君子思继即叙之烈者,其有所稽焉。
图后有一篇《西域土地人物略》,另附按语云:
愚按:孔子论政曰:“近者悦,远者来。”盖为政在于悦近,悦近在于脩德,脩德之至,则不特用人行政之间,无有过举,虽一喜一怒,亦皆出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矣……今西域诚吾燉煌故地之属,其人亦农桑可导之民,诚欲招来而奠之,为吾有司者,能脩德、悦近如孔子之论,如帝舜之格苗……
从这两段文字看,因西域自古为内属之国,收入《陕西通志》的这幅《西域土地人物图》,其中贯穿着明廷修德以悦近的思路,目的自然是通过施以政教来安抚西域各处。那么,现在拿这半句遥远的古训“修德以悦近”,为今天常讲的“丝绸之路”作一注脚,是否恰当呢?当然,要回答好这个问题,仍要回到对这幅图的周密鉴定、严谨考据上去。如果这一关过了,这个遥远的注脚在广义“丝绸之路”的语境下,还算恰当,也的确到修文德的时候了。
古舆图研究,由于相关数据开放较少,现在查阅仍不很方便。相对其他领域来讲,古舆图研究的成果积累,还不是那么丰厚。虽然这幅《蒙古山水地图》还正走在被检验的路上,但它所引起的公众对古代舆图的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撇开与学术无关的因素,继续挖掘材料,深入研究问题,由此得以精确某些认知,以推动舆图数据开放获取,这也是学术研究本该有的样子。
追记
不久前,朋友通过微信转来林教授回应质疑的文章(题为“《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最新研究进展”,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此文基于2018年3月9日林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3月30日,林教授又在清华大学的新雅讲座发表了同题演讲。
关于这幅长卷是否被裁剪过,在近两次讲演中,林教授已将专著中《蒙古山水地图》“被裁剪掉十米”的观点重新修订为“应还有第二卷”,第二卷的内容是“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欧洲部分)路线,以及文字说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忽略手卷的内容、形式,靠想象去“强硬”分卷,并不符合事实。基于此,林教授又进一步推论,“从《萝图荟萃》的记载来看,这幅地图的第二卷在乾隆二十六年编纂《萝图荟萃》时已经不在宫中”,想象就飞得更远了。另外,重新修订的意见还有,林著曾谈到“蒙古山水地图”虽是尚友堂的题签,但极可能是此图原名(林著,22页),近修订为“这(引者按,指《蒙古山水地图》)也并非此图原名”。
林教授的两次演讲,没有提及李之勤的《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李之勤:《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李著全面讨论了《西域土地人物图》及《西域土地人物略》,对帮助我们认识这几幅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相比李著,在讨论《西域土地人物图》及《西域土地人物略》上,林著到底要逊色些。
附录:林著所录地名异文举隅
林著第六章为“地理简释”,逐一考释图中地名。据林著所述考释体例,“为便于研究,我们把《西域土地人物略》抄录在《蒙古山水地地图》每张局部照片之下,然后逐一考释照片上西域地名”(林著,116页)。细检林著,在书中所附照后片之下,并没有抄录《西域土地人物略》地名。对照林教授2005年的初稿,才能看明白书中所述体例。

林著所录地名,并非据某一特定版本的地图照录,径改、误改之字极多。第六章“地名简释”所列地名,括号中的字,有些依从《西域土地人物略》的写法,有些依从《蒙古山水地图》的写法,也有些是林教授的理校……体例不一,颇为混乱。如《蒙古山水地图》有地名作“园子”,林著改作“围子”,且据此进一步考释为“突厥语地名,《蒙古山水地图》标在黑楼城西北,在今伊朗东境塔叶巴特(Tayyebat)。其名可能是源于突厥语Aran(畜圈、围栏)”(林著,170页)。又如,原件有地名“卜儿思”,林著作“十儿思”,且据此考释为“阿拉伯语地名,《蒙古山水地图》标为“天方”(今沙岛地阿拉伯麦加)东南方向第二个城镇。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提到阿拉伯半岛有个地方,名叫沙尔加(Sharja),‘有两座繁荣兴旺的村镇’。《蒙古山水地图》的‘十儿思’或在此地。据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考证,这个地方在穆珊达姆角的西面”。今复覈原件,将林著所录与《蒙古山水地图》原件不合者,厘为异文、脱字、增字三部分,先列《蒙古山水地图》原件地名,后列林著所录,间附林著释文,迻录如次:
其一,异文(30)
5,三颗树,林作“三棵树”。16,厂剌,林作“卜剌”。(林著,页126:卜刺:突厥语地名,《蒙古山水地图》标在沙州(甘肃敦煌)东南。其名原文作“厂剌”,《西域土地人物略》作“提干卜剌”。那么,这个地名源于突厥语Tikenbulaq,带刺的泉。)18,额失乜,林作“额失也(乜)”。25,吉儿马术,林作“吉儿马术(赤)”。32,也力帖木儿哈力,林作“也[乜]力帖木儿哈力”。34,他失虎都,林作“癿失虎都”。35,秃兀儿把力,林作“秃(畏)兀儿把力”。39,钵和思,林作“钵合思”。 43,卜荅儿,林作“卜答(告)儿”。47,义黑儿哈剌忽,林作“儿(察)黑儿哈剌忽”(林著引《蒙古山水地图》作“儿黑儿哈剌忽”)。69,义失力,林作“叉力失”。102,马荅剌撒,林作“乌荅剌撒”。108,撒刺思,林作“撒力思”。133,朿哈荅,林作“东哈荅”。151,哈刺思盻,林作“哈剌思盼”。159刺巴的帖失尔干,林作“剌巴的帖失[库]尔干”。160,刺巴的兀伦癿,林作“剌巴的兀伦白乙”。163,刺巴的克老干,林作“剌巴的克志干”。176,台户伦,林作“臺護伦”。178,的係哈三,林作“的系哈三”。181,失巴力干,林作“失巴刀(力)干”。182,盻黑城,林作“盼黑城”。184,米卜六罕,林作“米十六罕”。186,俺都回,林作“掩都回”。187,赤戏里堵黑塔兰,林作“赤戏黑堵黑塔兰”。193,园子,林作“围子”。200,台白列思,林作“臺白列思”。204,塞的列,林作“塞地列”。207,哈密,林作“哈(沙)密”。210,卜儿思,林作“十儿思”。
其二,脱字(5)
11,阿丹城,林作“阿丹”。42,速门哈六忽城,林作“速门哈六忽”。104,郎加古力舌比比,林作“郎加古力舌比”。150,刺巴的纳都,林作“剌巴纳都”。164,古巴子火者马黑麻撒力瓦思,林作“古巴子火者马麻撒力瓦思”。
其三,增字(2)
41,阿思他纳,林作“阿思打纳城”。117,巴力,林作“把力干”。
2018年5月2日修订于明永陵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