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生长在汉水边 | 《汉水的身世》新书分享会活动回顾
“其实我写的所有的事情,我记录的所有事情,你都可以说是出于一种难以释怀……写《汉水的身世》,算是还一个愿。”
少年时期目睹了汉江的深流缓行、不动声色,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晾在白光光大堤上的一片小小衣物”的袁凌,应该也始料未及,离家24年之后,身居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天仍能受到汉江的哺育,和他一起喝上、用上千里迢迢而来的汉江水的,有北中国的6000万人口。
袁凌说,当他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我需要为她写些什么,记录她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她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她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于是,从2014年南水北调通水前夕开始,袁凌陆续走访汉江沿线的水坝,采访辗转迁徙的普通人,最终写下了《汉水的身世》,来讲述一条母亲河的前世今生,和她子民们的生命历程。
《汉水的身世》
袁凌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2年11月
11月25日,袁凌和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播客「忽左忽右」主播程衍樑一起,聊了聊汉水的前世今生,在河流书写所开拓的另一种想象空间里,自由地行走。

01 | 希望在喝它水的人、在用它水的人,知道它的名字叫汉江
程衍樑:今天的主角是大方刚刚推出的新书——《汉水的身世》,截取区域的历史地理作为写作对象。我们知道袁老师您是记者出身,再之前还有相关的学术背景,最近几年转向为职业作家。在我看来,这本书里面既结合了非常多学者的观察,也能够呈现您过去作为社会记录者的角色。袁老师,请问您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
袁凌:其实小时候(我)并没有生长在汉江边,而是在汉江的支流上,不过小时候老听到大人们聊到“汉江河”这个说法。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家乡里的每一滴水,包括电线杆子上一滴一滴移动的小水珠,都要流到汉江河里。对我来说,我就想走出这个山村,走得更远,看到汉江。因为我爸老说他曾经横渡汉江,让我很神往,希望有一天也能如法炮制。
读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汉江边,在那里度过了三年。那个时候真的看到了汉江,非常震撼。对于一个小山沟的孩子来说,汉江非常的宽阔,感觉以前狭隘的视野被打开了,感到了远方的东西。汉江的水非常清澈,也很美,能够同时把辽阔和秀美结合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很少见的。我觉得黄河、长江都不是这样的,它们有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我当时经常在汉江游泳,能感觉它兼有力与美两者。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印象非常深。
那时候汉江也刚发过一场洪水,能看到发过洪水的痕迹。所以一方面对于它作为母亲河的亲近有亲身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敬畏之感。
上大学离开家乡,到了西安。因为西安缺水,所以做了一个黑河引水工程,那个工程后来有一小部分的水是从汉江的两个支流,通过穿越秦岭的大隧洞引过来的,可以说是中国最初的南水北调了,小规模的。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汉江边工作了两年。那段时间我和汉江朝夕相处,感受就更深了。那个时候比较荒唐的是,有一次游完泳,跟两个朋友半裸扛着自行车在浅滩上走十几里路回去,(看到的)那些农民觉得我们很怪。对汉江的感情,那几年非常深,一方面觉得要离开这里才行,另一方面又和它有难分难舍的感觉。
后来就出来了,我家在小县城,每次回家乡前我习惯在安康市住一晚,因为安康市挨着汉水。我习惯住在一个离江边不远的宾馆,晚上翻过大堤,到江边走一走。这样就找到了一种归乡的节奏,如果直接回家,我觉得不满足,好像就很匆促。这就是个人对母亲河的一种感情,包括后来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回到汉江边走一走,就像找回一种力量。所以这种对母亲河的感情是从小就有的,后来逐步发展。

现在的安康市下游江边:黄昏乘凉浴狗的人群。
袁凌 | 摄
南水北调慢慢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我就发现,不仅是我个人对于母亲河的感觉,它跟我之间有另外一种更深刻的关系。因为我长期北漂,在北京能够喝到千里迢迢从汉江调来的水,跟我在家乡安康的时候喝的水是一样的。我感觉非常奇特,有种很不寻常的感觉,距离这么远,我仍然受着母亲河对我直接的恩惠。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关系变得重大了。
这就促使我想要不只是写一些回忆性的散文,这种小文章我以前就写过,而是要写一本书。在南水北调的背景下来写汉江,它的付出、它的承担。因为我们在中国北方喝上了它的水,看起来是很美好的事,但是后面是有极大的付出和极大的承担的,汉江本身和它的子民的承担与代价,所以我就有这么一种想法了。
2014年,南水北调马上要通水了,它是12月份通水的,本来是想在国庆期间通水,所以我八九月份就前去采访。我在《博客天下》报了这个选题,那个时候是用带调查性的特稿方式,写了两三万字的一个长报道,今天书里的五个部分,在那个报道里已经有轮廓了。

其中第一章是调水,各种各样的调水。南水北调是最大的一个调水项目,还有陕西省的“引汉济渭”,西安这两年启动了一个更大的省内的南水北调,比以往的要大得多。汉江的水被调走不够了以后,从长江引了两道水,引到丹江口坝下,一个是“引江济汉”,一个是“引江补汉”,用长江水来补汉江,当然最后这个水其实又流回长江了。湖北省又从丹江口库区又启动了一个鄂北分水工程,调了一部分水资源。
第二个就是它的移民。仅仅这一次丹江口水库加高之后,牵涉的移民就多达三十余万,多在湖北、河南两地。如果我们算上1958年第一次丹江口修水库的时候,那个时候搬迁了几十万人,所以它的移民总数有近百万。这些移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背井离乡,1950年代还有很多人迁到青海、柴湖,都是很艰苦的地方。眼下这一代条件当然比那时候好了,但是到一个新的地方,肯定有很多的不适应,发生了相当多的回流现象。
第三部分就是汉江的航运。因为汉江在历史上是南船北马的一个重要漕运通道,那时候中国王朝的统治中心在西边——汉唐都在西安;后来移到中部的洛阳、汴梁,汉江都是漕运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船运一直走到走到襄阳、老河口,然后继续换船或者换马北上,所以汉江漕运非常的重要,一直到后来才衰落。后来兴起了大量的水电站,把航道就隔断了。同时,铁路发达也造成航运衰落,之后大量的水手、纤夫、船长的转行和失业。沿江的码头、市镇,以前的商铺,原来兴盛的都衰落了,牵涉到大量的居民,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是汉江的渔业。由于修了很多的水坝,堵住了鱼类洄游道路,加上水质污染、渔民的竭泽而渔等问题,渔业资源受到很大的影响。竭泽而渔之后,渔民自己也不行了。后来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长江流域10年禁渔,当时抓得很严,渔民们就失业了。所以汉江的“鱼”和“渔”,之间有一个连带关系和生存矛盾,这是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就是环保问题。因为要一江清水送北京,所以上游的环保工作是非常严格的。安康、汉中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关停了很多的企业。当然也有很高的成本,修建了很多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的费用是一个问题。还有很多环保组织,他们也在付出。也有很多环保上的忧虑,一些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丹江口大坝下游,水量减少之后,更容易污染。
这五个方面在我那次的采访当中就已经成型了,受限于采访的时限,没有办法展开,当时很遗憾。我觉得我需要以后在一些比较长的时间里,通过多次纵深的采访,把这五个主题深化,形成一本书。
后来我用了8年时间,中间多次对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一段汉江进行调查采访,当然也有一种沿河流行走的性质。通过前后十几次,每次七八天或者四五天的采访调研,慢慢地把五个主题深化了。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我最后一次去回访移民的现状,最终把我的调查完成了,我就开始写作它。
这就是这本书出生的过程,你可以说它有一个私人的、从小就有的对母亲河的情感,慢慢地发展、深化。到后来跟南水北调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就催生了这么一部把个人跟母亲河的感情,和整个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的大背景下面的、每一个个体跟它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写作的原因,简单一句话概括,希望在喝它水的人、在用它水的人,都知道它的名字,知道汉江。

袁凌
02 | 汉水是我唯一泅渡过的大河,我唯一爱过、至今仍然深爱的大河
程衍樑:袁凌老师是陕西安康人,罗新老师,您好像是湖北襄阳人,汉水对您来说也是一种母亲河的概念。您本身是历史学者,我想听您来讲一讲,汉水在您的记忆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罗新:我是湖北随州人,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在今随县的万和镇与新城镇一带。你要是看一般的水文图,会看到随州的几条大河,都流往东南方向,最后到长江去了。但是,随北桐柏山地区跟河南接界的地方,有几条小河不是向南流,而是向北流入河南。有的流入淮河,有的流入唐河。
我出生在我外祖母家,那个小镇——新城镇,我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名来的——属于汉水流域,因为怀抱新城的两条小河汇流后进入唐河,西入南阳,再向南从襄阳进入汉水。随州的河流分属淮河、汉水和长江三大水系,而我从小生长在汉水流域。但我很晚才知道这一点,到上大学后,才偶然发现原来我的家乡是属于汉水流域的。
我上初三时,就从汉水区域这个非常边缘的桐柏山地,进入到了汉水的中心区域了。初三下学期我到老河口上学,老河口是紧挨着建成不久的丹江口水库的大城市。初中毕业后再读高中,就到了襄阳。所以那几年一直都在汉水边上。
大学毕业之后到武汉工作了4年时间,跟汉水再续前缘。在武汉会为汉水感到骄傲,因为每次过江都能看到清澈的汉江水汇入浊黄的长江,汇流之后,汉水挣扎着不被长江吞噬,清流一脉绵延好几公里,向下游走好远都看得清清楚楚。每次坐汉口与武昌之间的轮渡,特喜欢看汉水与长江这一不情不愿的结合,内心有特别的冲动。
汉水是我唯一爱过的大河,是我唯一横渡过的大河。

引江济汉运河和汉江交汇处,从长江调来的水
颜色更浑浊,分界线明显。
袁凌 | 摄
我看到的汉水比袁凌家乡的上游要宽大得多,因为汇入了许多大的支流,当然现在很小了,因为南水北调。
这几年只能呆在北京,我在北京市内走的多一些。我有几个老同学们喜欢研究北京市的水网,我跟他们一起沿河流渠道徒步调查。我非常意外地发现,北京各处的水都变得特别清澈,比以前好得多。我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北京的水,这是我们湖北的水,是我们丹江口的水,是我们汉水的水。
我忘了是去年还是今年春天,袁凌跟我说他正在写这么一本书,要问我几个问题。我很高兴,我说,终于有人写汉水了。我自己年轻时很想当个作家(当然20多岁就非常及时地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那时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静静的顿河》,我开玩笑说我要写一个《静静的汉水》。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写不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对汉水亏欠着什么。
所以看到袁凌写,我很高兴,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之前,我读过袁凌的小说和几本非虚构作品,比如《生死课》《寂静的孩子》等,都堪称这个时代的杰作,哪怕现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相信将来一定会进入史册。所以,知道他在写汉水,我相信他会写得好。
果然,今年夏天,出版社把试读本发给我,我读后觉得太棒了,是我写不来的,我觉得太好了,非常高兴。作为一个爱汉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也第一时间推荐给我的中学同学。

罗新
03 | 书写一条河流:融合自然、历史、现实、人文与行走
程衍樑: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汉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过非常久远的影响,尤其像袁凌老师的老家安康,再到刚刚罗新老师提到的丹江口水库的那一段,其实这一段在古代是沧浪水,是我们听起来文学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河段。
我记得20世纪初很多的日本学者来到中国考察游历的时候,他们会很关注中国的水。其中有人提到过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其实特别强调“浊水”,这个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所看到的长江黄河都是非常浑浊的,早晨是青色,到了下午以后就变成黄色的、混着大量泥浆的水。而汉水却迥异于此。
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汉水的清,尤其是袁凌,你提到过你写这本书是希望让读者认识到汉水,因为很多人不是生长在汉水边。为了让读者能有更为直白的认识,可以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汉水的特征吗?
袁凌:从我个人直观的感受来说,汉水确实特别的清。它清到什么程度呢?我第一次在安康从跨江大桥上面往下看,就像柳宗元写的《小石潭记》一样,“皆若空游无所依”,你感觉船从桥底下过来的时候,船下是没有水的,它就那么飘过去了。有个专有名词叫“晒滩水”,就是阳光下射可以穿透好几米,把底上的沙照得明明白白的,你可以看到两层光,能依稀看到水面上的一层光,和它透到滩底下的光,像是透过放大镜的聚光,都没有什么损耗的感觉。你还能看到水底下沙的形状,跟山水画一样,那种感觉非常清楚的。
所以明代古人对它有个称呼,叫“中泠水”,在安康上游汉江的江心取中泠水,可以用来泡茶,被宁献王朱权称作天下第七好的水。我以前读到“湘水天下至清”,但是后来我到了湘江去以后,我感觉它的水其实没有汉江这么清,而且湘水带有一种黏糊的感觉,可能跟南方红壤的黏土性质有关系。
我们汉江的水,为什么会这么清?一个原因可能是它的不发达,地处南北交界,没有那么多污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的土质应该是沙土质的。沙土质跟黏土质不一样,水过来以后,经过沙子的过滤会非常的清,如果是黏土质的话,容易把泥巴本身带着,这样就没有那么清了。我采访了移民,他们在上游种花生比较容易,因为是沙土,搬到下游之后,土带有一点黏土性质,不太好种,感觉不透墒。
汉水的重要性,从我所知的历史知识,我也说一点。古代人并称河汉是指黄河和汉水,并不是说黄河和长江。其实汉江流经的汉中和安康,离周代的丰、镐二京的核心统治区并不远,所以它是属于周南、召南的地方。像《诗经》有一首《汉广》是写汉水的,属于周南,就是说的我们那一带。后来汉初中央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区也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从古代来说,汉水离统治中心并不远,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担任着漕运的重要任务。汉江很独特,它本来是东西走向的,但是走到这个丹江口之后,一直往南到武汉,又变成南北走向了。这就给带来一个极大的用处,它成了南方到北方的漕运通道。运粮和盐的船只从南方来,到了老河口一带,要不就是换成马,南船北马;还可以继续往上航行,到褒斜道南口或者子午道南口,也是换成挑担越秦岭到西安;或者从丹江北上,在商洛越秦岭到西安;或者是从唐白河往上走,可能是到平顶山那一带,也是换成陆路再到洛阳。所以它是最重要的漕运通道。后来王朝东移到北京、南京,大运河成了主要的漕运通道,汉江的地位就衰落了。
同时这个地方又一直不发达,它处于南北交界的地方,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大巴山。虽然建国以后搞了一个三线工业,硬性地安插了一些工业在它的上游,现在唯一能保留下来也就十堰的汽车厂,算是比较重要的,其他的都破产了。
但这个给汉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质得以保持。清澈的水质变成一个最大的价值优点,于是被提上了南水北调的主角。南水北调本来是调长江的水的,后来发现调长江水路程又远,水质又不太好;汉江水现成,水质又好,它就变成主角了。
所以我觉得汉水的身世充满了吊诡的地方,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是一个既有悱恻,同时也有它独特传奇的感觉。它始终保持着它的品质,像一个君子一样,同时它又承担了一个起初没有想到的作用。一头一尾,最初重要,中间衰落,但是现在它又重要这么一个感觉。

一段尚在自由流淌的汉江,云山苍茫,江水迅疾。
袁凌 | 摄
罗新:汉水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干净。世界上有许多干净的大河,但是不一样,汉水特别清澈。山里小河很容易清澈,大河这么清澈非常难,一定是各种因素机缘巧合,才让它有这样的水质。
汉水上游流程短,不像有的大河流很远。长江黄河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路上带的腐殖质、黄土很多,影响了水的颜色。世界上很多大河的水质其实很好,可是因为携带腐殖质较多,水色也就很深,看起来不是很清爽。汉水不是从富有森林的地方流出来的,上游地质结构也以砂石为主,没有多少腐殖质,泥土也不多,所以河水特别干净。
可能也因为这种地质地理的特点,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不是很好的航运河流,特别是上游与中游之间,就是从鄂西北到陕南,两者间航运很难。袁凌在书里提到三国时蒋琬的一个想法,就是从汉中沿汉水向下攻击襄阳。后来别人跟他说,顺着汉水往下,顺利了倒挺好,如果不顺利,你怎么回来呢?逆水西归,大概是回不来的,蒋琬一听也就不敢继续了。其实不只是西归很难,就航运来说,往下其实也不容易。袁凌书里写纤夫写得很成功。我觉得中国近代以来研究航运(如大运河)的著作,对纤夫的研究是不够的。而袁凌做了许多采访,这个工作做得很漂亮。为什么有那么多纤夫?就是因为航道糟糕,稍微有点规模的船就上不去。蒋琬要带大军往返,是行不通的。自古以来汉水没有全线通航,都是局部通航,在一个段落之内。
在丹江口水库下面的老河口,汉水清澈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地方,因为丹江口水库的沉淀作用。河水清澈的程度,刚才袁凌也说了。讲讲我自己的观察与体会,我在老河口段汉水游泳的时候,踩水立在水里时,稍一低头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脚趾头,在其他地方没有经历过。我上大学时在密云水库游过泳,也没觉得水很干净。
所以说,汉水是中国所有大河里最干净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干净的大河。
程衍樑:这个特质真的非常的突出。刚刚罗新老师提到了汉水的航道,袁老师也介绍过,汉水作为一个航道,自古以来对中国人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汉水很多条件其实并不利于通航,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之后,发生过非常多航运事故。好像汉水的长途航运很早就衰落了,这块袁老师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这也是您书中重点描写的一个群体。
袁凌:在古代,汉水航运地位主要说的是它的中下游,就是老河口丹江口这一带。再往北上它就折向西边了,那一段滩特别多,就像罗新老师说的,走大船就特别困难了。在老河口以下,它就转成为一个南北向,河也大,滩也少,所以古代的漕运也就是主要利用这一段。
随着航运的发达和一些航道的疏浚,基本上到汉中都可以通航,但是越上走船越小。像十万斤的大船最后就走到安康,再往上就不行了,是这么一种状况。但整体来说,近现代以来,它还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发达的,尤其是木船。轮船其实一直都没发达起来,它的上游特别不适合做轮船,它滩太多了。但木船借助纤夫硬把它往上拉,还是可以的,木船就像穷人比较皮实,就是把它拖过滩去也刮不坏这种感觉。
但到了50年代开始,开始修丹江口水库,如果是那时候修成的话,上下就截断了,就要分成上游和下游了。但是修的过程很曲折,当时刚上马之后就遇到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水库修了一段,但是并没有完全合拢,所以它的导流渠还可以用,船还可以上下走,只是比较麻烦。一直到70年代以后真的是合拢了,也是那个时候襄渝线建成,这两件事情使汉江航运急转直下。
因为丹江口水库一旦建成之后,把上下游分割成两节,它只有一个过船设施,就是升船机。升船机其实非常不方便,耗电量巨大,对电站管理方来说,没有什么动力,而且还容易出事故,曾经发生过摔船,提升对船体本身也是有伤害的,出水又入水,损害比较大。所以它其实建立之后就很少使用。
这样就造成上下游割裂成两段航道了,隔断以后又陆续新建了很多的水坝,现在的汉江干流上新建的这样梯级水坝就有十几座,航道被切割为一段一段的,根本就没办法通航了。

丹江口坝下,高大的升船机。
袁凌 | 摄
虽然上游不太适合航运,但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无数的纤夫、太公、水手的传奇故事。衰落之后,有很大的一批人就失业了,他们的时代就落幕了。而且这个行业的衰落它带来的不光是失业,它也带来了沿途码头的衰落。老河口以前是多么繁华,罗新老师跟我谈过他的亲身经历,他前些年回去,感觉到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抛弃了,连铁路都不通过了,黑灯瞎火,没有人在乎的感觉,有能耐的人都走光了。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是经济形态的改变,还有人的从业方式的转变。
这部分我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写,其中有一个人叫李丰皋,我印象很深。他是一个浪漫的悲剧人物,他是蜀河镇的人,1948年,他一心实现他的梦想,要造一艘汉江上最大的木船。刚刚建立起来,背着很多账给商号运货,用货运费来抵他造船欠的账,结果这才跑了一两年就解放了。解放以后衰落了,很多都收归公家了,私人的船弄不到什么生意,这个船就被贱卖,他本人也破产了,最后还被打成了船主。我觉得他是值得纪念的,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类似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这部分写得比较充分。
所以说,我觉得对那些水手来说,对沿岸的很多码头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黄金年代。当然,现在已经是几乎没有什么了,只有一些旅游轮船跑短途。汉江下游还有一些货运,但是整体来说就远远落到了别的江河的后面,远远不如自己的黄金时代了。

汉江航运博物馆收藏的船上老物件:
油篓、马灯、斗笠和草鞋。
袁凌 | 摄
04 | 书写汉江的子民:公平的做法,是把他们记下来
程衍樑:罗新老师说阅读这一部分,他的感受特别深,尤其是对航运相关的这些群体的采访、描摹,可能从学术界内部来说,罗新老师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其实我很想听罗老师您来谈一谈,听袁凌老师提到对于汉水这些航运产业相关的调研采访之后,您阅读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结合您自己在老河口的经验,来和我们观众聊一聊。
罗新:我觉得袁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跟他写的另外几本书,像《生死课》《寂静的孩子》一样,他关注的是边缘人。他关注那些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数量很大,但通常不为社会那些一般的文化人、更不用说那些达官贵人和有钱人,所在乎、所关心的人。社会主流习惯了对他们视而不见,习惯了忽视,故意忽视,系统性地忽视。这样的人,在袁凌的笔下生动了起来,作为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是可以认识的、有情感有思想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数字。这是袁凌著作一贯的优点,是我们时代的亮点。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寂静的孩子》
袁凌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19年6月
《汉水的身世》也一样。他写汉水,一方面歌颂汉水是我们的母亲河,多么美好、多么重要,即使对今天,对北京来说多么重要,更重要的一方面,他要写的是正在消失的历史人群,因为汉水的重要、因为汉水对别人重要而付出、而牺牲的人群,比如移民。
一方面我们看到汉水往北流,流到北京来,现在连北京那些普通公园用的都是汉水的水,过去的臭水沟,现在都满满地流着清澈的水,都有鱼群和野鸭。不是一两条水渠,一两个小湖,而是整个北京地区的水都变干净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为什么?因为汉水。另一方面,在陕西、河南和湖北,有多少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开始承受不公平的一切。袁凌在书里写到的,比如韩家洲那些人,迁移到我们随州凤凰山去的那些人,你看看他们,他们从此过上了一种自己毫无准备、并不想要的生活。不只是这几十万移民而已,还有更多人,数百万、上千万可能都不止的人,都开始受到影响。
书里提到,现在整个汉水流域严重缺水,从长江来的水又远远不如当年汉水的水。前几年出版的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重点写明清时代为维持大运河而牺牲的淮北地区,跟袁凌此书有一定的可比性,关注点也非常接近。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牺牲一个小小的局部。汉水也是如此,牺牲了一个小小的局部,能够救援的是似乎更加重要的北京、天津、河北,但我们应该看到谁做出了牺牲。公平的做法,是把他们记下来,让我们都知道,都记住,这是当代人起码的、负责任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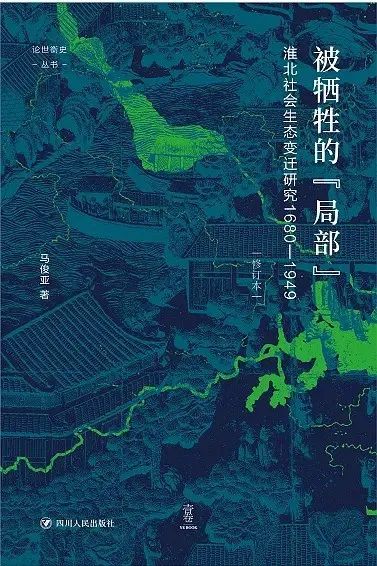
《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
马俊亚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如同马俊亚的书,袁凌《汉水的身世》关注被牺牲的人,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那些不幸的人,那些因汉水变化而面对更大不幸的人,在袁凌书里被记录、被雕刻。这个工作看似平常,其实很不简单,值得赞赏。
程衍樑:是。刚刚其实罗老师提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大的工程或者说大的时代当中利益受损的这些群体,有的是因为航运衰落的这些原因,使他们的职业消失;还有一些是更直接的,像一些重大工程面临一些移民安置问题,在《汉水的身世》这本书里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甚至我们去看整个汉水的历史,好像移民一直是某种主题,可以说在明清时代,甚至明清以前,有大量的人口从南方移民到汉水的,一直往它的上游去进行移民的安置。那么到了近代的话,汉水的重大的工程改造,比如刚刚提到的南水北调,甚至像丹江口水库的修造,它都产生了新的移民。这个是袁凌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采访、回访的主题,能向我们的观众来聊聊你在这方面遇到的一些故事吗?
袁凌:确实,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背后人群的付出。这种付出我们不去评论它,但是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不止要知道汉水的名字,我们还要记住,有一些汉水的子民,他们在为这样一个大的工程付出,在为历史的改变付出。
这里面就是大量的移民,他们都服从了,在异乡也试图努力地扎根,但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国人本来就安土重迁,讲究落叶归根,所以里面我写到了一些老人,他们在晚年就宁愿自己回到老家去,在那里过世。有一些年轻的人,因为在新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移民村的条件也有限,遇到很多问题,好多人回流,回来以后也失去了身份和户口,只能是比较辛苦的打工,这样漂泊,我写了比较多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我觉得他们很卑微,但正是千千万万人的付出,他们的配合,他们的牺牲,才有了这么一个宏大的工程,北方的人才喝上、用上了这么好的水,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不美化,也不去渲染,就是把他们的生活的实际记录下来。
我走访了有6个移民村,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一块在书里面占了一个相当大的篇幅,我写的时候就有点沉重,大家读到这里会感觉有一点沉重,没有那么轻松,我希望大家原谅我,因为我实在也想把它写得轻松一点,但是有时候你轻松不起来。
里面有一个老年人叫韩正龙,他是一个移民,同时也是一个纤夫。他移到凤凰山的时候腿已经有问题了,跟我见面的时候八十多岁,和我回顾他拉纤的经过,好几次就差点死在水里。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辛苦,到晚年的时候又移到新的地方,他的儿子们都回流到老家去挣钱去。当然还有一些是更心酸一点的,我觉得把他们的故事都记录下来,让我们北方、整个北中国用水的人,不仅是知道汉江,也知道汉江的子民。

黄金峡江边小路上,
最后一位在世的“太公”楚建忠踽踽远去的背影。
袁凌 | 摄
我还写到一支很有趣的渔民家族,就是从朱元璋开始,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说,从江西迁过去,世代打鱼。都不上岸的,几千人,全姓肖,一直就在水上,汉江、长江里面随便走,打鱼,中国的吉布赛人。这次10年禁渔之后,他们就被迫上岸了,一上岸就是完全不适应,以前从来没在岸上待过,没有学习岸上的职业,也没有怎么好好上过学。结果就找不着他的位置,非常的失落。
我希望把这些生命的境遇,这些弱者的、承担者砌成的历史地基,宏大的事业下面的地基,我想把他们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煌煌巨大的纪念碑,宏大的工程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但是却必须一锤一锤把它夯实了的地基上。在夯实的过程、捶打的过程当中,这些人又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把他们记住的,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程衍樑:我其实很好奇,你在做采访的时候,是按照不同板块来进行对受访对象的寻找和主题的撰写的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的结构一样,还是都是打乱、穿插在这么多年比较随机的访谈过程中的。
袁凌:第一次感觉是全面的,后来有时候会有一些更明确一点的目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精确。
比如说2016年我专门是冲了移民去的,但采访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别的身份的人。比如在凤凰山移民村里,本来是采移民,但是那个人移民他恰好就是一个老纤夫,我就跟他聊到航运的往事。
比如说我到黄金峡本来是冲着引汉济渭工程去的。去那以后就接触到渔民,比如老杨,他是一个很有道德心的渔民,他就不会瞎用那种特别野蛮的网。所以不会每次去就一定只采一个主题,你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去了后可能发现别的事情,肯定是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期来,这是一个好现象。

黄金峡上游,渔民老杨在汉江上划着他的小船。
腿脚有残疾的他,只有在船上才觉得自在。
袁凌 | 摄
程衍樑:罗新老师,因为您研究历史。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这些,比如说移民,最近这么多年在历史学界也被人们当成一些新的可能研究对象,跟传统史学有一些区别。我不知道您作为历史学者,你看这本书,尤其涉及到这些方向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结合您对于这块一些学术上的期待,或者说过去的一些阅读经验,来和我们的观众做一些分享。
罗新:近年中文世界翻译引进的生态史、环境史著作很多,原创的中文作品也越来越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史学之外,我们有相当多的,主要是记者出身的年轻作家们,他们关注当下的中国,写环境,写生态,把自然的变化跟社会生活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样的作品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袁凌《汉水的身世》就是一个典范。
比较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与袁凌《汉水的身世》,两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对所写的对象,所写的世界,那个社会、那些人有强烈的情感。当然两书表达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马俊亚的感情暴露得充分一些,袁凌比较克制。两个人的写作风格不同,袁凌这个更像是一个记者写出来的,马俊亚的书反映了他的学术训练。可贵的是这类作品的原创性,看得出作者的特立独行。当代作家中,勇于承担,勇于表达,有责任心,有责任感,这样的人已经多起来了。
高质量的作品会越来越多,反映了中国整个文明水平的提升,代表着我们的高水准,代表着中国有希望的那一方面。
05 | 汉水本身的生命,是我最重要的写作对象
程衍樑:我自己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脑子里会弹出一个想法,《汉水的身世》其实采用了一种水域式的区域划分方式,内在隐含了跟流域相关的一切,它可能存在某种整体性,或者说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可以作为一个写作对象。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新奇的写作方式。因为中国的大江大河,可能传统上比较知名的,或者明清以来被纳入版图的,尤其像外东北的那些河流,如果作为写作对象的话,确实迥异于过去我们根据商圈或者政治性的地理划分,以某省某市为写作对象的这种写作方式,这种以流地为写作对象的方式的话,它最终能呈现出来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这片水上的人,还是河流本身?我想听听袁凌老师的一个想法。
袁凌:我写这本书也确实有这么一个念想,想写一条河流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一条河流为主体来写。
如果按我们一般的思路来说,最容易想到的是,首先是跟他有关的人,还是以人为主体。但是我写汉水,我不太想直接从人开始写,虽然我写了很多人,但是我想河流本身,汉水本身的生命,是我的最重要的一个写作对象,在它的生命里面就包容了它的子民,从鱼到人都有。我觉得把汉水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对待,它不仅是一段历史,而是说它里面真的包含了这么多的生命。我是希望包括他的气质,都有一些涉及,所以是有这么一个意识的。
这个意识从哪来?比如类似的,以前我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当时印象很深。他写了几条北方的河和人,当然它是一个小说,有这种类似的气息,可能在我心里面是有某种印象的。徐则臣的《北上》写了个大运河,汉水这个书他就很感兴趣。当时刚完成航运这部分初稿的时候,他就提前给我打招呼了,完了以后我就把航运这部分交给他,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本身写大运河,是以小说形式写的,然后他对非虚构的方式来写河流也有兴趣。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北方的河》
张承志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11月
所以我在想,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标准意义上的河流文学,尤其是以非虚构方式写一条河流。
其实国外是有的,我想我来写这么一本河流的书。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有兴趣的,徐则臣他就有兴趣,可能他以后还会写长江这种。有一个朋友杨潇,写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他是湖南人,家在郴州,湘江发源的地方,所以他可能想写湘江,我还给他介绍湖南河流环保的人认识。其实大家对河流现在是有这么一种念想的,为啥?
因为在这么一个经常会感到沉闷的时代,河流给了一种想象空间,它打开了一个跟我们行政区划不同的一种想象关系。如果我们写一个地域,它可能给你一种安定感、一种安顿感、一种扎实的结构感。但是写一条河流,它肯定有一个另外的想象空间,一种自由的、行走的、变动的空间。
我想罗新老师很喜欢行走,他可能有类似的体会,《从大都到上都》写的是一条路线,我就写这么一条河,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现实中的一种关注,河流受到了很多的改变,它变得不自由了,但是它本身它仍然给我们带来一种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河流的书写。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 著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把河流呈现为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不仅是它的一个问题、一个部分,而是把它整体作为一个生命呈现出来,既给我们一个痛切的感受,给我们一个深刻的体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某种心灵追寻的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也是汉水本身给提供我们的,从《汉广》这个诗就开始,“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这种想象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很美。你看汉水哺育的诗人孟浩然,他写了很多跟汉江有关的诗。王维也写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种感受,他确实能给你带来与日常生活和行政区划不同的想象,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如果一条河流不能自由流动的,都变成了水库,一个河上没有帆船的航行了,它也含有某种想象力的失去,这也是一种审美损失。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生命写下来,保留一份记录和期望。
程衍樑: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点特别好,一个河流它是自由的,如果用一条条水坝、一个个的发电站把它给截断,它的生命力其实就丧失掉了,它中间的这些生命体,这些鱼类都会灭绝、都会死去。这些水无非就是被你榨干,可能变成了电。但是我觉得一个自由流动的河流,尤其是水在河流作为一种意象,作为流质化的一个物质,它和土地传达给人们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寄托的想象也不一样。
在文学里面,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描述的传统,就是你像你会反复提到《诗经》里面的《汉广》,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意识角度的联系在。我不知道罗新老师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罗新:中国很多河流都值得写,比如淮河,马俊亚只写了淮北那一小部分,而且是以大运河为主来写的。其实上游也值得写。现在优秀的年轻作家这么多,如果做这种调查与研究,都可以写得很好。
通过写河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像袁凌写的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独有的,过去的人写不出,未来的人不一定知道。每一代人记录自己的时代。
你刚才问,我们写河流,到底是写河流,还是写的河流上的人?是作为物理世界、自然世界的河,还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人群?当然是写人。当今之世,哪怕是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也会把相当大的篇幅给自然世界中的人,因为这可能是最容易被打动读者的、跟我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
如今这个世界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人。如大历史(big history)所说,我们已经进入地质年代的“人类世”,地球自身的重要变化都源于人类行为,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河流也是如此,河流命运的变化,都是人造成的,所以重点还是在人身上。人造成河流的变化,人承担这个后果。人与人又不同,有的人从变化中得利益,有的人从变化中得痛苦,要把这两方面都写出来。
程衍樑:袁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袁凌:这本书,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还一个愿,对汉水从小有念想,跟我有这种关系。我还特别希望大家知道它本身,也知道它的子民们,就是这些人。
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遗憾,也受到很多限制。作为个人,一个没有(平台依托)身份的个人去采访,面临很大的风险,有很多的困难,没有必要多说。但我觉得我尽力了,这一点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这个欣慰并不能代替汉江本身的境遇,想到它这个境遇,我觉得我还是难以释怀的。
其实我写的所有的事情,我记录的所有事情,你都可以说是出于一种难以释怀,如果说我们真的把它放下了,其实可能就不写了。就是因为难以真的放下,它就压在你心头,你觉得一条江河它可能凝固了,它压在你心头,所以还是把它记录下来。
好像完成了一项的任务,交了一个账的解脱放松,但是同时也有不能释怀的东西。这个是我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后的一个心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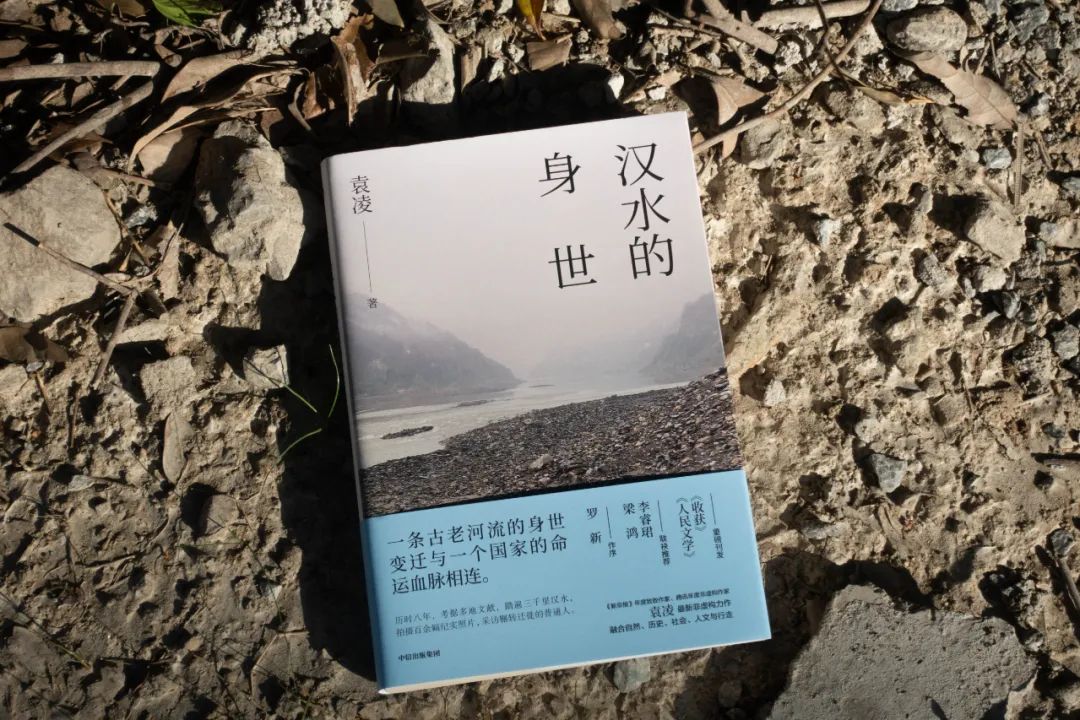
程衍樑:不能释怀。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连线到袁凌老师还有罗新老师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汉水、关于汉江、关于河流它的这些故事本身。其实不只是汉江,包括罗新老师中途推荐的马俊亚老师那本《被牺牲的局部》,也是一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一并推荐给大家。
感谢观看的读者,在本场直播里能够听到非常多的关于这个话题里很细节性的故事。过去可能是在历史当中,非常容易就稍纵而逝,然后会被人遗忘掉。但袁凌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拾起一个个碎片化的素材,变成了今天我们手上的这本书。
好,再次感谢各位以及辛苦两位老师,我们今天这一期直播就到这里。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跳岛FM(Talking Literature)是一档文学播客,一份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节目每周三更新,由中信出版·大方出品。入选“苹果播客2020年度编辑推荐”。
原标题:《我们生长在汉水边 | 《汉水的身世》新书分享会活动回顾》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