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读|地球上那些有“世界杯”的夜晚
鲁迅在小说《社戏》里,写到他小时候去赵庄看戏的经历,赵庄的戏台临着河,掩映在渔火与月色里,要划乌篷船去看,那是南方水乡独有的社戏。
北方的戏是另一种风貌,在我家乡,每年农历二月十九都要唱戏,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天,我不知道这个传统延续了多少年。小时候,“二月十九”就已经是本地的一个特殊名词,大家都不说庙会或赶集,只叫“二月十九”,它包含了所有与其相属的意义,一切尽在不言中。
农历二月十九接近春分,那几天春寒料峭,总有大风卷着尘土飞扬,戏台上的旗帜与棚布在风中劈啪作响。现在回想起来,“二月十九”就是当地的世界杯,以前的世界很小、很慢,在一个小聚落里,庙会就是聚合起所有人的世界杯。而现在的世界很大也很快,在一个地球村内,世界杯取代了地方庙会,成了所有人争赌的一场好戏。
我家乡“世界杯”的戏台背靠着马路,面朝一座观音庙,中间是一片空地,有篮球场那么大,等到好戏开场,老人们坐着小马扎密实的聚拢在这里,出神凝望不远处正在上演的故事。台上通常唱晋剧,偶尔也有京剧,每年都会有《打金枝》《空城计》之类的剧目,人们仿佛看不倦。
鲁迅在小说里,这样描述得知能去看戏的心情:“我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没错的,是这感觉。每年那个时候,也是我盼望的大日子,那几天里,在蜿蜒四五百米的马路上,会洋洋洒洒搭满简易商铺,摇身一变为熙来攘往的商业街。我喜欢穿梭在里边,也喜欢去窥视戏台的后场,台上演什么,我无心去听,只觉得旋律特别激昂,戏台后边有家卖豆腐脑和油条的老铺子,那个口味,我一辈子都会怀念。
小时候,我实在看不懂老一辈的人们,为什么痴迷于那么吵闹而奇怪的表演,就像如今很多人也不懂足球迷们为什么痴迷世界杯。之前的戏剧有一个剧本和套路,可以反复地看。而现在的世界杯则是开放式地自导自演,没人知道这戏走向何方,结局只能在时间分秒地流逝中一寸一寸地剥开。
戏台上的戏,会一直从上午唱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就是夜里的压轴节目——挠羊赛。忻州是中国摔跤之乡,每逢庙会、唱戏,地方都会举办摔跤比赛,而“挠”在我们当地的意思是“扛”和“举”的意思。

忻州挠羊赛
挠羊赛的赛制类似于世界杯淘汰赛,一个人如果能连续摔倒6个,也就是经历6轮淘汰赛,就是获胜者,奖品是一只羊。据说这是受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启发,胜者将羊扛回家,就像捧得一座大力神杯,也可说是“挠”起了大力神杯,这是大力与勇猛的象征。摔跤是很古老的项目,古希腊奥运会上就已常设,据说我们那里的摔跤传统也有千年历史,现在国家摔跤队的主教练就是忻州人。
摔跤在午夜时分开始,那个时候疲惫的人都已回家安睡,所剩都是精力旺盛的男女。他们聚在跤场上看比赛,也会随时忍不住跳进去变为选手,比赛一般进行到凌晨三四点,激情四射的角力与淘汰反复在上演,夜色中,灯光打在人群围成的圆圈内,里边像马超和张飞在挑灯夜战。
这比赛里也会有黑马和冷门。到第二天,大家都会津津乐道昨晚的战况与细节,到处在流传和赞赏,是谁家儿子把羊扛回了家。
我们那地方的“世界杯”大概就是这样,中国戏剧里的“生旦净末丑”、古希腊的悲喜剧和英雄史诗都渗透在那几天的舞台和跤场上,也渗透在那一片乡土中国的白昼、夜色与炊烟里。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现在回想小时候所经历的“世界杯”,有一种人诗意栖居于世界的感觉。
那是一个彼此联动的氛围,所有人聚在一起,感受着地球上这一小块地方的黄昏和夜晚,品味着共同的温暖与激动。大家在向往英雄传奇的情愫之下,有一种对命运共同体很世俗也很有烟火气的自我欣赏。
后来我去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开始看另一种世界杯,它和过去所见的很不相同,但又极为相似。为此,我永远喜欢地球上那些有“世界杯”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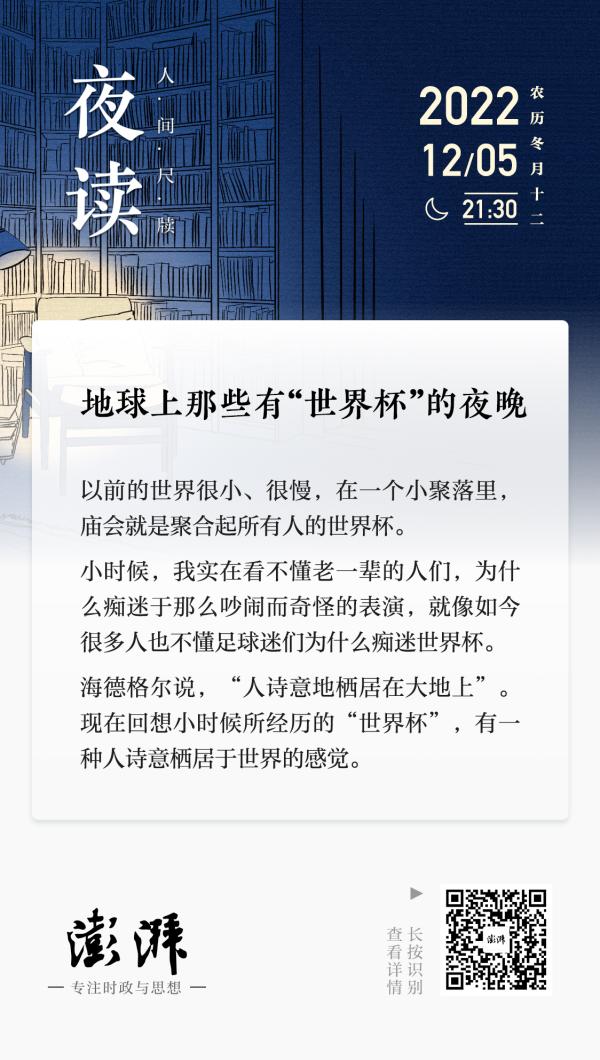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